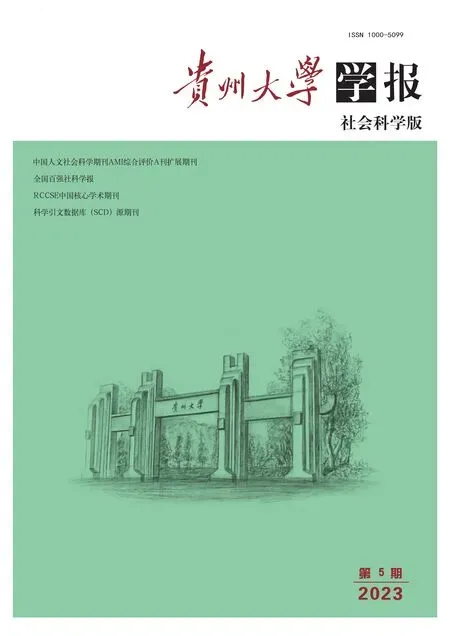汉语语境下前语言时期的儿童哲学探求与检视
陈永宝
(1.厦门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2.厦门大学 哲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国内关于“前语言时期”的研究多集中于医学领域,如尹敏敏等人的《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的前语言阶段发声研究进展》[1],李颖等人的《儿童选配助听器后前语言交流能力发育》[2]等。同时,教育领域关于儿童的前语言时期的研究也有新发之势,如梁露尧的《前语言时期儿童沟通姿势研究综述》[3],郭雨祺的《前语言动作与早期语言发展关系刍议》[4]。但对哲学领域的前语言问题研究,学界仍处于探索阶段。
一般看来,一个人是否具有哲学思想,判定的标准是通过其“说出来的语言”来判定,如泰勒斯(Thales)说:“水是本原。”[5]89哲学思想似乎只有通过“语言”才能得以呈现,语言构成了哲学存在的“容器”。黄裕生认为:“哲学是通过在反思中的概念演绎来摆脱‘这个世界’而走向本源,也就是说,哲学是在追问‘这个世界’为什么这样而不是别样的根据而走向再无根据的本源,因此,哲学需要完成从概念存在者到非概念存在者的跳跃。”[5]22综上,哲学与语言结合的重要性,无论是从日常表达通俗性,还是文本逻辑分析理论性均呈现如此。但是,这种重要性并不表明哲学的表达只有语言这单一模式。如果是这样,那么人类前语言时期是否存在着哲学,就成为一个必须讨论的问题。前语言时期儿童是否存在哲学的问题,不仅关乎前语言时期的哲学存在的合法性问题,涉及哲学的存在是“全体性”还是“部分性”的问题,也涉及哲学与语言、哲学与行为外显的关系问题。
虽然哲学的产生来自古希腊先哲们对世界的一声惊叹与好奇,并最终以语言的方式呈现于世人面前。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哲学呈现的多维面向便慢慢地浮现出来。其中,儿童哲学的出现,将这个问题进一步凸显。学界关于儿童哲学中的语言问题的讨论还处于起步阶段,常见的研究方式是将儿童哲学和语言问题各个分离的加以讨论。不过,这种现象在近些年有所改变。杨研璐认为:“儿童哲学的本真性问题是儿童哲学教育的逻辑前提,……儿童哲学并不要求哲学抛弃抽象的概念和严肃的慎思……儿童哲学与儿童的认知发展理论并不必然产生矛盾。”[6]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儿童哲学与语言的关系正在被学者关注。之所以讨论儿童哲学与语言问题,是因为儿童在生成时期存在着一段“非语言”或者“无语言”的“前语言时期”(1)前语言时期的判定不能以年龄为标准,而是以儿童能否清晰地用母语表达内心所想为标准。这里的“清晰”有两个外在标准:一是指儿童可以用一句完整的语音表达出自己的内心想法;二是指儿童具有“撒谎”的迹象。相较于前者,以后者的验证可能更为简易。因为“谎言”不仅是对现实的模仿或误导,而且也是人的心智成熟的一种自我展现。。
对于这一时期的儿童来讲是否存在着哲学,关乎着哲学整体论的讨论,即哲学是否伴随人的一生,或者是人一生中的某一个阶段?对人而言,哲学是一种整体性还是部分性的存在,关乎到哲学对人的适用范围;同时,如果哲学只发生在人一生中的某个特定阶段,那么这个阶段的界定标准是什么就需要被说明(2)如果界限不清晰,将会导致儿童哲学中的诸多问题只能被悬置或被抛弃,而不是被解决。相对而言,儿童在宗教的视野中一直被认定为是一个“完整的人”,在心理学的视野中也被认定是“完整的人”的一个初级阶段。前者强调儿童不容磨灭的主体性;后者强调儿童心智的发展程度。二者与哲学相比都存在着一个确定的界限,讨论的目的是不再产生过多的歧义。但对于儿童哲学研究而言,这个“界定”本身就需要被讨论。。基于此,关于前语言时期儿童哲学的呈现方式,将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一、前语言时期儿童哲学存在的判定
1.赤子之心的儿童哲学
在汉语哲学语境下的蒙学思考中,保留着对儿童前语言时期的哲学思考。在这种语境下,常见的呈现方式是对儿童哲学的引导偏重于“行为”而非“语言”的视角。其中,《孟子》中的赤子之心是一个典型,它揭示了汉语语境下儿童哲学“非语言”存在的开端。
《孟子》中记载:“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7]272朱熹解释说:“赤子之心,则纯一无伪而已。然大人之所以为大人,正以其不为物诱,而有以全其纯一无伪之本然。是以扩而充之,则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极其大也。”[7]272这是中国哲学对赤子之心典型的描述方式,强调“行”与“心”而非“语言”。
虽然孟子在强调“赤子之心”的哲学内涵时,仍然要依靠语言将其“说”出来,但他的思想侧重点明显在非语言的内心感受及行为表现上。也就是说,在汉语哲学的语境下,行为具有了替代语言成为检证儿童哲学存在的工具可能性。从这一点来看,汉语语境下儿童哲学的讨论界线显然已经超越了李普曼(Matthew Lipman)和马修斯(Gareth B.Matthews)等早期儿童哲学家们所规定的范围。
从赤子之心来看待儿童哲学的边界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心理学方式的行为验证方式。相比较复杂的心理学验证系统,这种强调儿童赤子之心的验证可能更具有简易性和可取性。通过对儿童的当下体认和关照的反馈,判断儿童内心世界的哲学意识与哲学思考。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通过儿童的喜好、厌恶等日常行为发现其善、恶的伦理学取向,进而确定其哲学思想存在的可能。
《孟子》中的诸多断言,因时代性与古文表达方式的局限而过度追求文字表现的简易性。因此,它不会给出当代伦理学所要求的精确行为判断,也不会出现通过体液检验而给出的心理行为的佐证。但在《孟子》中所断言的简易性无形中又打破了当代医学对儿童行为的量化判断,将儿童的心理行为从医学视角中解放出来。于是,正如望闻问切相当于精密的医疗器械和体液的化学检验一样,孟子的“赤子之心”的验证亦存在可挖掘的价值。
当然,赤子之心在验证中存在着朴素性与粗糙性。“朴素性”和“粗糙性”并非错误性,只是一种检证方式的初级方式或首要方式。如急诊科的全科医生对病人所做的初步检查,与专科医生相比较就过于“粗糙”。这种“粗糙”不是错误,且可被接受和被理解。赤子之心有望成为当代儿童哲学检证中“全科医生式”的标准。因此,赤子之心的出现,即反映出哲学呈现的多维方式,打开哲学被语言“禁锢”的弊端。同时,它的朴素性也为“行为验证”的可行性提供了前提。
2.行为的验证标准
中国传统思想中对“知行”的强调(准确来说是行大于知的强调),导致儿童哲学在中国本土化的研究路径上依然要遵循“行”这个大的原则。这是开展中国儿童哲学本土化的研究路径的基石。
“行”为“非语言”的儿童哲学在理论上的发展提供了可行性,对其具体的施行,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思考:
一是建立“非语言”的验证标准体系。所谓建立非语言的验证标准体系,主要是指在考察儿童进行哲学思考与产生问题意识时,是否存在一种非语言的验证标准。也就是说,在考证儿童具有批判性思考时,能否存在用行为和视觉交流等非语言的方式来验证儿童此时已经具有哲学思考和“提出问题”的能力。
二是要思考行为本身存在的可信性问题。相对于语言而言,行为的复杂性造成了行为检验的复杂性。行为的呈现方式与语言的线性状态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行为是以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身体觉等立体状态的存在并关联着。因此,关于语言的验证标准比较容易确定。(如验证一条线是否为直线,只需要找到另一个直线加以比较,答案立明。)但关于行为的验证则不一样,多维存在的行为异常复杂,甚至具有“欺骗性”。如婴儿在求父母抱抱过程中表示出来的开心等行为,则表现为一种“欺骗”行为。于是,在验证儿童是否具有问题意识或批判思维的时候,行为中的验证标准本身就存在可讨论的空间。
但是,因为“行为标准”的复杂性而认为这种标准不可行,也明显过于武断。于是在验证非语言存在的时候,有两条路可以尝试:一是通过研究,简化或者明晰行为验证的细则,使行为的验证标准得以确立。在这一方面,行为心理学已经做出大量的前期工作。二是增加验证的次数与频率,以概率思维来加以判定。如判定一个儿童是“乖小孩”还是“熊孩子”,要以单位时间内其个人行为的频率来综合验证,而不能只以其单次的行为作为依托。显然,行为验证要明显难于语言验证。基于此,在验证前语言时期儿童存在哲学思考能力的时候,是需要付出一定的精力作为代价。这是前语言时期儿童在生长阶段对父母的耐心与细心的一种挑战,这也是儿童本身发展规律的使然。
3.非语言的验证标准
无论是孟子的“赤子之心”,还是当代的行为检验,都尝试建立一种非语言的验证标准。借助这种非语言的验证,寻找一条非语言存在的儿童哲学的验证方法。因此,从“以语言为中心”的哲学思维中跳脱出来,摆脱语言对哲学的束缚,是验证儿童哲学存在的开端。
首先,当人处于婴儿的早期时,对知识的渴求是一种自然显现。习惯怀抱婴儿的家长在婴儿早期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习惯久抱后的婴儿是难以被重新安置在床上。对于婴儿呈现出的外在行为,我们可思考的问题是:他在并不缺乏安全与食物,又无冷暖的干扰下,为何不愿意留在床上,这其实是婴儿对单一知识摄入的厌倦,反映出婴儿对新知识的渴求。婴儿这种渴求与成人对新知识的态度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二者之所以会出现不同,则在于成人在行为上拥有自主性,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行为,使这种渴求在无形中得到满足。婴儿由于行动不便而要“受制于人”,他们对成人产生的强干扰成为一个突出行为的外显。
其次,儿童早期产生的与外界交流的身体“语言”,实际上就是一种独特的行为方式。这种以非语音、非文字为特征的行为方式,是儿童与他人沟通的主要途径。这也可以成为儿童在前语言时期的验证标准。
再次,成人世界中依然存在着“非语言”的验证方式。在现实生活中,因聋哑出现的语言残障人士所使用的手语,是这种通过行为“表达”思维的一个佐证。他们通过手势的不同变化,来描绘内心世界及现实事物,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手语”。这种在我们(拥有正常语言能力的人)无法理解的行为表述中,我们与他们之间并未产生明显的沟通障碍。因此,“手语”表达思维的路径也可为“行”的“非语言”验证提供证明。
最后,非语言验证标准的“反思性”。语言残障人士是可以通过手语来表达他们的反思性思维,如“可能我的行为需要改正”,抑或是“今天某件事我做错了”。这种表达验证了“非语言”的反思性行为的存在,但问题是这些反思性要局限在行为者“心智的成熟”这个范围内。这一点是前语言时期的儿童所无法拥有的。在宗教思维中,儿童一出生(甚至是未出生的胚胎)就已经属于“成人”范畴,但从心理学意义上来说,人的心智成熟是需要后天的时间积淀和经验积累才能达到的成熟状态。前语言时期的儿童显然缺乏这个条件。因此,通过行为验证儿童有“思想”具有了可行性,但要论证前语言时期的儿童有“反思性”,可能需要我们做出进一步的说明。
二、前语言时期儿童哲学存在的合理性检视
1.前语言时期儿童哲学存在的检视
关于儿童哲学的判定标准,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4C思考,即批判性(Critical Thinking)、创造性(Creative Thinking)、关怀性(Care Thinking)和合作性(Cooperative Thinking)[8]32;二是基于西方的“反思性传统”,注重儿童的思维能力而非知识灌输的标准[9]149。三是外显的可观察的表现[9]159。这三类标准既相辅相成,又可突出独自的理论侧重面。
当儿童进入语言时期,三者皆可并存。通过4C思考训练,建立儿童的反思性思维,并通过行为的外显加以实验检证。但儿童处于前语言时期,由于语言摄入的无效性,无法通过“语言”来向儿童传输4C的理念;同时,反思性传统作为对事后的反思,要求儿童有一定的记忆力,而这对于前语言时期的儿童来讲,的确是一个困难。
在长期的婴儿养育中,家长或其他成人给出的强制或非强制的行为,在婴儿的反馈中多只有恐惧或非恐惧的两种表现。至于生气、谩骂等极端性行为,在婴儿的反馈中也只是验证了语言的无效,“语言”并不会发挥本有的作用。婴儿关注的似乎只是“说出语言”时成人行为“秀”出“凶恶”还是“友善”的行为。
马修斯在《与儿童对话》(Dialogues with Children)中同样注意到语言问题对语言时期儿童的困扰。他借助唐纳德(Donald)的语言说:“如果人天生就不会说话,天生只会用东西做动作——应该说不是做动作,是把东西‘秀’出来。虽然这样子做会非常麻烦,但或许是一个行得通的办法。”[10]78可见,“陌生概念”在对儿童的交互过程中呈现出的势弱现实,如同婴儿面对“生气、谩骂”的语言一样。
但相对于前语言时期的儿童来说,语言时期的儿童由于有了语言沉积,对新的概念的接收和使用表现为经历学习后的效果呈现问题。但对于前语言时期的儿童来说,他们的“牙牙舌语”能否被看作是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存在着争议的问题。以此来作为前语言时期的“语言构成”或“检验标准”,显然还需要大量的证据。
因此,探索前语言时期的存在标准,简单以语言为工具显然是过于唐突的。至少我们可以说,语言并非是儿童哲学存在的唯一工具。这里,语言成为检证儿童哲学存在的标尺虽然有效,但范围有限。这需要从“非语言的方式”中寻找替代语言的新标尺:做。“做”的标尺是有效解决受教儿童哲学的孩子的年龄问题,突破了语言的局限。
2.连词与反思性检视
儿童哲学作为一种哲学的教育模式,不同于教育学研究中将其视为一种教育方法,而倾向于启发儿童的哲学思考,帮助儿童梳理哲学问题。因此,反思性活动作为哲学本有的特征,就构成了前语言时期儿童哲学不可回避的难题。
检验前语言时期存在着的反思性活动,不可将其简单地推给“行”就乍然截至。有两个方面需要被说明:一是在“行”的外显中,能否体现反思性的存在?二是语言中连词的天然存在是否反向推导出“行”的先天性?前者试图达到的目标是绕开语言来推测反思性思维存在的可能性。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聋哑的残障人士的手语行为中得到一定的启示。二是“连词”作为一种无现实参照的独特存在,在儿童的表达中可能自然生成,可能意味着语言只是“行”的一种“特殊表现”或者“天然本有”。如果是这样,前语言时期的儿童自出生时刻开始就可能具有了这种反思表达的潜质,而不需要被证明。
语音中的“连词”言说具有独特的作用。马修斯指出:“没有一样东西的名字叫作‘和’,所以没有办法表示或说出‘和’。”[10]76-77对于这个难题,马修斯试验中的“达波”给出了一个解决方式,即“做出某种动作,让别人能够明白那是‘和’的意思”[10]77。在马修斯的这种探讨中,他发现3—6岁的孩子虽然多数具备了语音的言说功能,但名词显然是通过现实世界的反复刺激而被儿童接受或学习。与此对之,连词由于没有现实参照物,在儿童学习的过程中应该是难以被孩子掌握或学习。然而真实的情况是,孩子在使用连词“和”的时候,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卡顿或不适感,这就说明他们在应对外在世界的刺激时,具有先天的反馈机制。这种反馈机制是否近似于哲学中的反思活动;或者说,就是哲学中的反思活动,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地探讨。但对于儿童的反思性验证,这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可参照的路径。
我们可以说,从连词的存在属性,进一步地揭示出儿童的行为中存在着一种行为与语言的产生次第问题,即“先行为后语言”的现实逻辑。反思活动不可能出现在语言刺激产生之后,而是在儿童有对真实世界的反馈行为产生之时。当然,这种推测依然需要神经科学和行为心理的科学实验来再次检证,但在思维逻辑上,这个推导是应该成立的。
3.“做哲学”的检视
由于语言是儿童出生后较晚时期才会形成,因此何时开展儿童哲学教育,也成了儿童哲学研究者探讨的问题。在关于探讨儿童哲学的受教年龄的问题时,迈克尔·西格蒙德(Michael Siegmund)指出:“‘与儿童一起做哲学是一种思考与对话的过程,它是开放且动态的。在这之中,每个人的可能性都得到了扩展。’我在此主张的是对‘做哲学’的相当广义的理解,我想明确地说,对于‘做哲学’而言,并不存在最低年龄的‘下限’。最大的限制莫过于对思想的表达能力。……当代神经科学研究可以帮助了解儿童的学习过程。我认为,将固定年龄定为做哲学(从广义上理解)的下限是荒谬的。”[11]在西格蒙德的表述中,我们可以获得两个信息:一是儿童哲学的侧重点在“做”而不在“说”;二是儿童哲学没有年龄下限,这包括了前语言时期的儿童(或婴儿)。于是,这再次为研究前语言时期儿童哲学的思考提供了一条新的佐证。
相较于以“说哲学”作为验证儿童哲学存在的标准,“做哲学”的先天优势就在于它突破了言说本身存在的年龄界限。于是,反观孟子思想中的“赤子之心”与朱熹蒙学思想,皆将儿童视为成人发展中的一部分,没有出现将儿童进行再次切割的倾向。在孟子看来,成人不应该失去赤子之心所表现出来的“纯一无伪”。朱熹补充说:“盖赤子之心,纯一无伪,而大人之心,亦纯一无伪。但赤子是无知觉底纯一无伪,大人是有知觉底纯一无伪。”[12]同时,朱熹在其蒙学思想中,也诠释了儿童与成人之间哲学教育的连续性。朱熹说:“古者小学,已自是圣贤坯朴子,但未有圣贤许多知见。及其长也,令入大学,使之格物致知,长许多知见。”[13]11又言:“古人于小学,存养已自熟了,根基已深厚了。到大学,只就上点化出些精彩。”[13]11
至此,将西格蒙德与孟子、朱熹的思想进行融合后,我们可发现他们其实都是在强调一种“(知)行”的儿童哲学理路。于是,当我们对儿童哲学的思考或检证从语言的局限中摆脱之后,无论是从“做”的角度,还是“成人与儿童一体化”的角度,都可以寻找到前语言时期儿童哲学进行的可能性。进而,对前语言时期的儿童存在儿童哲学教育的可能性,又夯实了第二个论证。
三、前语言时期儿童哲学的提炼及哲学分析与意义
1.整体性与本体论分析
从哲学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的意义中,思考的问题是儿童哲学在人的教育过程中,是部分性的存在,还是整体性的存在这个问题。在本体论的讨论中,无论是物质与精神,还是思维与存在,都在探讨哲学的统一是存在状态,还是区域性存在状态。
在阅读马修斯及李普曼的儿童哲学作品时,我们发现他们列举的事例基本上集中于3岁以上,抑或是语言时期的儿童群体。如李普曼在《哲学教室》里的陈明宣、李莎、唐宁、齐媛和陆哲雄等,基本是处在幼稚园(幼儿园)和小学阶段;马修斯在《哲学与幼童》中的蒂姆、乔丹、约翰·埃德加、戴维和丹尼斯等,也基本是3岁以上的儿童。基于此,我们在阅读这些著作后的感受是,儿童哲学是否只是儿童在语言形成后的一种存在,儿童哲学只是人在一生中某一部分的存在,而不是整体性的存在;换句话说,论证在前语言时期是否存在儿童哲学,它是关联到人在学习哲学时是否以整体性方式存在的一个核心问题。
儿童哲学作为一种哲学,在本体论中应具有恒定存在的可能性。于是,这种考虑就决定了在思考儿童哲学问题时,对其存在的时间和空间问题需要进行再次的考虑。如果儿童哲学只是“语言存续中儿童的哲学”,是一种将儿童哲学做“部分哲学”的判定。这种判定存在着三个需要回答的问题:一是儿童哲学产生和结束的时间界限如何界定;二是儿童哲学与成人哲学(暂且用这个语词)是否存在连续性和一致性的问题;三是儿童哲学的时间性和地域性考虑。
而在汉语语境下的儿童哲学思想中,则完全不必回答上述问题。如:在中国宋代朱熹的蒙学思想中,蒙学(又称小学,相当于儿童哲学)是成人教育的一部分。朱熹说:“学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为道则一而已。是以方其初幼也,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及其长也,不进之于大学,则无以察天夫天理,措诸事业,而收小学之成功。”[13]16在朱熹的这种表述中,儿童的伦理哲学培养显然不存在时间界限,也不存在儿童哲学与成人哲学连续性和一致性及时间性和地域性等问题。儿童与成人在伦理行为上所构成的一致性,是人在哲学思维培育中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这构成了中国儿童哲学讨论的本体论依据。
儿童哲学研究者注意的本体论问题,以及儿童哲学在人生中的时间跨度和中西方儿童哲学因空间而存在的异同性问题,在这里达成有机的统一。
2.认知取向与知识论分析
前语言时期儿童哲学的价值,是在已有的神经科学、当代医学及心理学的研究基础之后,再探讨人在获取知识和反思辨析的认识问题。在多数的认识思维的观察中,由于语言的便利与显见,它已成为人们判定哲学反思行为存在的主要工具,这是事实,但却又值得商榷。
一个人是否具有哲学反思能力,在认识论中表现为主体与客体之间能否建立有效的反馈与修正行为。本质上应该集中于“行为”本身,而不是由语言构成的现象媒介(或者说中介系统)。这要求在思考人的主客体认识中,能否摆脱语言对哲学检证的钳制,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在以往的研究中,聋哑残障人士的手语等肢体语言,逐步打破了“语言”的禁令。然而,聋哑残障人士所表达的手语抑或是盲文是否也可被认为是一种“语言”,这种讨论又将认识思维再度拉回“语言哲学”的泥潭。
同时,因为聋哑残障人士的思维成熟度,也不宜作为拓展非语言路径下对哲学思维的思考。然而,前语言时期可以逃离“缺乏”“不完整”等概念对思考的误导,而从前语言时期儿童的主体本身来思考人的认识的整体性存在是否可能,以及哲学思考是整一还是区间存在。
3.前语言时期的儿童哲学和伦理意义
儿童哲学是一种整体性哲学而非其他分支哲学,不同于“以科学为哲学探讨对象的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以政治为哲学探讨对象的政治哲学(Philosophy of Politics)、以教育为哲学探讨对象的教育哲学(Philosophy of Education)”[8]14,它应该是一种整体性哲学。之所以强调儿童哲学的这个特征,意在说明儿童哲学在人的整个伦理教育中的关键环节,这同样也是在汉语语境下思考儿童哲学的一个关键问题。
在中国哲学视域中,儿童伦理教育无论是孔子的“仁”思想、孟子的“赤子之心”,还是朱熹等人的蒙学体系,都在试图诠释着儿童的教育是人一生教育的核心。如:仁思想是贯穿于人发展的始终,不因儿童的幼小就可以规避。儿童在学习使用语言之前,父母对他的哲学教育也基本围绕着“仁、义、礼、智、信”等儒家传统价值观而展开,非放任不管;而由“赤子之心”产生的“求放心”[7]312的伦理追求,亦是儿童对成人的伦理反哺。
在孟子的“赤子之心”理念的引导下,发现中国古代的伦理教育意在达到“纯一无伪”的“至诚”思想,这来源于前语言的儿童时期。也在另一个角度上说明了“学而复其初”的伦理行为在前语言时期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至此,前语言时期的儿童哲学研究,也展示出它的重要性。
四、结语
哲学自古希腊以来,常以语言的方式呈现于世人面前,造成了人们对哲学的思考被局限在语言之中,而忽视了哲学本质在于行为。儿童在其生长时期存在着一段“前语言”的时期,这个时期虽被早期的西方哲学所关注,然而却在近现代的语言哲学的浪潮中湮声。在中国,儿童从来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群体,前语言时期的儿童在伦理行为和主客体认识形成的过程中,也是完整的一体。因此,关于儿童在前语言时期是否存在着哲学,就出现了两个研究取向。
从汉语语境下解决前语言时期儿童哲学的整体性问题,回答了哲学是伴随人的一生,还是人一生中的某一个阶段这个难题。也厘清了哲学的价值与意义离不开全体或总体的方式。虽然人是否具有哲学思想的常用判定标准依然是其“说出来的语言”,但突破语言对哲学的钳制,已经成为当代儿童哲学研究者试图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这种研究思想,可以在中国传统思想的沃土中寻找养料,使其以更加合理的方式呈现出来。同时,汉语语境与儿童哲学的结合,也为儿童哲学的中国化、本土化提供了研究基础,值得被“我们”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