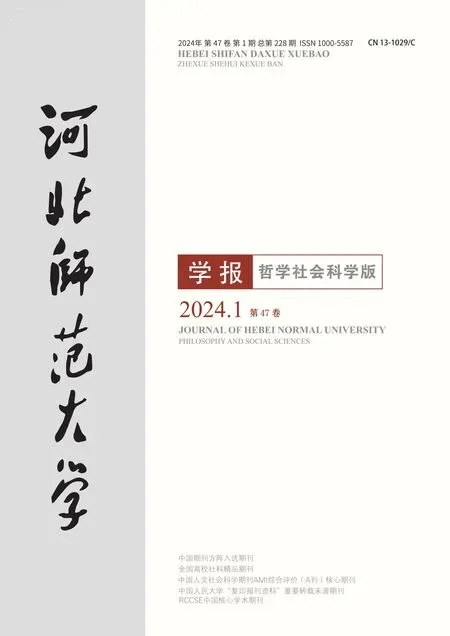从“氏族之人”到“编户齐民”
——试论先秦时期社会成员身份的变迁
晁福林
(北京师范大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北京 100875)
先秦时期社会成员身份变化的最为显著时期是春秋战国。社会成员身份的变化折射出时代的巨大变革,反映了社会形态的深刻变化。(1)晁福林:《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545页。这些变化和变革,值得我们进行探讨,今不揣谫陋,试作分析如下,敬请专家指教。
一、氏族之“人”

“人”与“族”关系密切。起初“人”的观念隐于“族”中,夏商西周时期,社会上几乎所有的人都生活于“族”之中。这些“族”,周代以前称为“氏族”,周代则多称为“宗族”。那个时代少有人逸出于氏族(宗族)之外。甚至可以说,社会上的人都是“族人”。但后来的发展表明,“人”的观念的普遍意义大增,其所指的范围则远大于“族”。例如,《左传》载宋国贵族名华合比者“纳亡人之族”(6)语出《左传》昭公六年。杜预集解,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43,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卷7,第2044页。,逃亡国外的人称“亡人”,这些“亡人”里面包括一些族,所以称为“亡人之族”。战国时期,国家力量对于社会的控制增强,影响力加大,遂将某族之人称为“族人”。这个称谓只见于战国以后,这种情况表示,“族人”只是社会居民的一个部分。战国时期随着经济的繁荣,生口日繁,居民成分渐趋复杂。不少人走出了氏族、宗族谋生,与“族”的关系趋于淡漠。
二、社会成员身份的复杂化
最初的“族”,夏商时期指氏族,至周代则指宗族,战国以降又指家族。一些相近的族则统称为“族类”。春秋时期鲁人语谓“《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7)语出《左传》成公四年。杜预集解,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26,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卷7,第1901页。“族类”即指同类之族。春秋时人还说:“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唐儒孔颖达释其意谓“鬼神”(按,指祖先),所享祭祀,“惟当子孙自祭”(8)语出《左传》僖公三十一年。杜预集解,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17,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卷7,第1832页。,若非子孙之祭,作为祖先的“鬼神”就不会歆享。可见“族类”即指同祖的氏族或宗族。这些同氏族或宗族的人,又称为“族属”或“族党”(9)按,“族属”之称见《礼记·大传》“同姓从宗,合族属”。孔疏云:“同姓,父族也。从宗,从大小宗也。合族属者,谓合聚族人亲疏使昭为一行,穆为一行。”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34,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卷6,第1507页。“族党”之称,见《左传》襄公二三年“尽杀栾氏族党”。“族党”指与栾氏同居一地的同族亲属。杜预集解,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35,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卷6,第1978页,。大致来说,西周春秋时期普通民族以其“族”为称,反映了氏族、宗族的普遍存在。春秋时期强宗大族的影响力甚强。春秋前期宋国的“戴、武、宣、穆、庄之族”(10)语出《左传》庄公十二年。杜预集解,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9,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卷7,第1770页。按,以诸侯国先君为称的“族”,还有“桓庄之族”(《左传》僖公五年,同上书卷12,第1795页)、“穆襄之族”(《左传》文公七年,同上书卷19上,第1845页)、“戴氏之族”(《左传》文公八年,同上书卷19上,第1846页)和“平元之族”(《左传》哀公十二年,同上书卷59,第2171页)等。联合起来平定国内叛乱,这些族就是宋戴公、武公、宣公、穆公、庄公等国君的后裔。他们势力强盛,可以左右宋国政局。还有不少族以著名的任卿大夫的宗族长的名字为称,再如“羊舌氏之族”“伯氏之族”“巫臣之族”“[晏]婴之族”(11)前三均见于《左传》,依次为《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左传》定公四年和《左传》成公七年。分别为杜预集解,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34,第1971页;卷54,第2136页;卷26,第1903页,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卷7。“[晏]婴之族”出自《晏子春秋·内篇·问下》,见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卷4,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4页。等,亦是有影响力的大族。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氏族(宗族)日益壮大,亦不断分化。清儒王梓材辑佚战国时期的记载周代氏族的《世本》一书时,曾经感慨那个时代氏族(宗族)变化之繁杂,说道:
氏族之不知所出者。不可胜稽。其有可稽。而同国同氏实异出者。如齐有国高之高。又有栾高之高。鲁有孝公时臧氏。又有孝公后臧氏。郑有七穆良氏。而良佐已在穆公前。晋有世家箕氏。而韩氏又别为箕氏。襄之世有辅跞。而知过又别为辅氏。又士氏即范氏之先。而先蔑亦称士伯。宋有孔氏。孔父之后也。而襄公之孙。又为孔叔。楚有薳氏。在春秋前。而薳章之后。又为薳氏。周氏为周公之后。而汝南周氏别为一宗。特未见经传耳。王子成父之后为王氏。而太子晋之后亦为王。(12)王梓材:《世本集览通论》,见《世本八种·王梓材撰本》,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60页。按,春秋后期以降,世人对于氏族谱系的重视渐衰,所以当时人对于不少氏族(宗族)的源流不甚了了(上引氏族不知所出,即为其例)。春秋时期能言此者往往被誉为博学。战国时人有追溯氏族源流的潮流,贵族热衷于此,其目的据宋儒郑樵说是“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氏族略第一·氏族序》,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页),所以有《世本》之作。
古人称族为某氏者不可胜数,但“氏族”之称则较晚,盖自东汉时期始用于世。《汉书·叙传》载班彪《王命论》云“刘氏承尧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13)《汉书》卷100《王命论》,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4208页。,其所说的“氏族”,指刘氏之族,虽然已有“氏族”之意,但还未将其用为一词。
夏商时期,普遍存在的社会组织是氏族,至西周春秋时期则是宗族。春秋战国时期,氏族与宗族力量渐退,由国家直接管理的“编户齐民”逐渐走上社会舞台。(14)关于我国古代社会结构的变化,愚有小文加以讨论,敬请参阅。见晁福林:《论中国古史的氏族时代:应用长时段理论的一个考察》,《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在春秋中期,一个地域的民众,非必只有一族,居于某地的民族就被称为某地之人,亦即某地之民。春秋时期的普通民众,一般都同时有两种身份,一是某族之人,二是某国之人。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上古时代经济发展的繁荣期,农业、手工业、商业等都有了长足进展。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人口繁衍的增速。在各地生口数量增加的前提下,从春秋后期以降,直至战国时期居住在同一地区的人,情况渐趋复杂。关于此方面的情况,上古文献里有一份宝贵的资料可资为证。当时齐国统治者曾经为弄清楚居民情况而进行社会调查,为调查而列出的提纲保存在《管子·问》篇里(15)《管子》一书的性质,学界一般认为是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学者们的论文集,其中也包括了稷下学者所能见到的齐国官府的一些文件《问》的性质,黎翔凤谓“此为当时之调查纲要”(黎翔凤:《管子校注》卷9,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84页),其说甚是。,这是我们所能见到的一个非常宝贵的材料。其中关于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宗族情况的调查有以下几项:
问宗子之牧昆弟者,以贫从昆弟者几何家?
余子仕而有田邑者,今入者几何人?
子弟以孝闻于乡里几何人?
余子父母存,不养而出离者几何人?(16)《管子·问》,黎翔凤:《管子校注》卷9,第487页。按,当时不照顾同宗亲属的典型例子,见《管子·轻重丁》篇所载:”城阳大夫嬖宠被絺绤,鹅鹜含余粖,齐钟鼓之声,吹笙篪,同姓不入,伯叔父母远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饥而不得食。”(黎翔凤:《管子校注》卷24,第1490页)。
问国之弃人,何族之子弟也?(17)黎翔凤:《管子校注》卷9,第486页。
从这些调查里可以看到当时宗族变化的情况。依照宗法原则,宗子是宗族的核心,作为宗族嫡长子,宗子是财产的主要继承者,对于庶子之族的贫困无助人员,宗子有“收族”的责任。(18)关于“收族”,有研究者指出,其初始的意义是延续大宗的统绪,使大宗成为聚扰宗族的核心。春秋以降,“收族”之旨逐渐向宗族内部的扶贫济困转变[说见王青:《说“收族”:兼论周代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特色》,《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孔子说:“同姓为宗,合族为属。虽国子之尊,不废其亲,所以崇爱也,是以缀之以食。”(《孔丛子·杂训》,见傅亚庶:《孔丛子校释》,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12页)此可见春秋末期宗族为自身的巩固发展所进行的努力。从这个提纲里可以看到有些宗族依然是大宗占主导地位,宗子之昆弟(亦即庶子)之族,受大宗庇护(“牧”),有些大宗之家衰败而靠昆弟接济(“以贫从昆弟”)。宗族里的庶子(“余子”)因为做官而得到田邑,并从这些田邑收税(“今入”),显然,这些“余子”在这么多方面已经走出了宗族而成为国家之人。这也是宗族制度削弱的一个表现。当时社会上已经出现不守孝道的情况,虽然宗族里也有恪守孝道的人(“子弟以孝闻”),但也有不守孝道,与父母分居别爨的人(“不养而出离者”)。还有的人被宗族逐出,而成为“国之弃人”。
关于居住在乡里而又非宗族之人的普通民众的情况,有如下的调查:
问理园圃而食者几何家?
人之开田而耕者几何家?(19)语出《管子·问》,见黎翔凤:《管子校注》卷9,第487页。
所辟草莱有益于家邑者几何家?
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几何人?吏恶何事?
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几何人?身何事?
群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几何人?
外人之来而未有田宅者几何家?(20)语出《管子·问》,见黎翔凤:《管子校注》卷9,第494页。其中“群臣”的“群”原作“君”,依黎翔凤引豬饲彦博及王引之说(黎翔凤:《管子校注》卷9,第490页注一四)改。
从调查提纲里可以见到当时乡里间有靠种植菜蔬瓜果(“理园圃”)为生的家庭,有开荒种地(“开田而耕”“辟草莱”)为生的家庭。也有有田而不耕种的家庭(“有田不使”“有田不耕”),这些家庭的人以何事(“身何事”)谋生呢?依情理看,无外乎从事手工工艺或商贾之业两类,虽不可确定是哪一项,但其不务农作则是可以肯定的。不务农作的,除了田不耕的农士以外,还有官府小吏(“群臣有位”)以及从外迁徙而来(“外人之来”)的家庭。
关于当时乡里社会居民贫富分化的情况(21)关于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社会基层组织的情况,《国语·齐语》谓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见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卷6,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23页),大致反映了当时居民的组织结构情况。《管子·问》篇有“子弟以孝闻于乡里”之说,实取乡、里二字组词,以“乡里”作为基层社会的代称。,提纲有如下的调查:
问乡之良家,其所牧养者几何人矣?
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
贫士之受责(债)于大夫几何人?
问人之贷粟米有别券者几何家?(22)语出《管子·问》,见黎翔凤:《管子校注》卷9,第486-487页。
当时乡里社会上的贫民为谋生计而投靠富人,富人(“良家”)给予帮助(“牧养”)。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佣耕而食”的情况。关于出卖劳力者的心态,韩非子曾有所论说,他指出:“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畦畤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23)语出《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三》,见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卷1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83-684页。主人剥削“卖庸”者,在调查提纲里被说成“牧养”,虽然颠倒了是非,但在那个时代却是存在于乡里社会的现实。
从上面的调查纲要里可以看出,当时的乡里居民身份显然比过去的氏族制、井田制之下的情况复杂化了。其中有两个方面的情况值得注意:一是,传统的宗法家族在逐渐解体,宗法家族内部的贫富分化在发展,宗法制度对于家族内部普通成员的保护趋于削弱;二是,居民身份多样化,不少居民不依靠宗法家族的保护也可以谋生,甚至生活得比在家族内部还要好一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宗法家族的影响。从乡里居民的生活情况看,贫富分化亦是可见的现象。这两个方面都可以说明当时社会成员间的血缘关系的影响在削弱,而国家地域的关系的影响在增强。
三、“民”之身份的演变
商周时代,民是社会身份低下之人,和奴仆相近,郭沫若从“民”字的源起方面,说明其社会地位低下的情况。他指出:

西周初年分封鲁国时,曾赐予“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分封卫国时,则赐予“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25)语出《左传》定公四年。杜预集解,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54,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卷7,第2134-2135页。。这些商王朝的氏族被分封以后,并不是解散了氏族,都成了周人的家内奴仆,而是还作为氏族存在,只不过其社会地位要比周人之氏族低一些罢了。周人称这些氏族为“殷民”,可见“民”的社会地位不高。
随着社会的发展,民的社会地位在春秋战国时期有逐渐上升的趋势。《国语·周语》中篇载周卿单襄公途经陈国的时候,见到“民将筑台于夏氏”,韦昭注云:“民,陈国之人也。”(26)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卷2,第62页。这说明陈国所居住的所有宗族的人,皆是陈国之“民”。战国时期“人”与“民”皆指某国之民众。两者混用无别,如郭店简《六德》篇谓:
聚人民,任土地,足此民尔,生死之用,非忠信者莫之能也。(27)语出郭店简《六德》第3-4简,见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87页。按,简文“土地”二字由裘锡圭先生释出,见上书第189页注[四]。
这段话的意思是,聚集人民,分发给他们土地,满足民众维持生命的需用,若非忠信之人是不能完成这样任务的。简文的“足此民”的“民”,就是这段话开头所说的“人民”。
春秋战国时期虽然人、民多混用无别,但两者的使用却出现了有所侧重的情况。称某族的成员,可称“某族之人”(28)称“族之人”者,例见《韩诗外传》卷4“以为亲邪?则异族之人也;以为故耶?则未尝相识也”(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卷4,巴蜀书社,1996年版,第391页)。春秋以降的收族与合族多为一事。,但未见称“某族之民”或“族民”者。春秋战国时期,“人”所包涵的范围甚广,各类、各阶层、各个职业以及各地的人员皆可称“人”,但称“民”者则多是某地之民或下层民众。如“向之民”(29)语出《左传》桓公七年,杜预集解,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7,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卷7,第1753页。、“国内之民”(30)语出《左传》庄公十四年,杜预集解,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9,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卷7,第1771页。、“共滕之民,为五千人”(31)语出《左传》闵公二年,杜预集解,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11,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卷7,第1788页。、“晋国之民”(32)语出《左传》襄公十三年,杜预集解,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32,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卷7,第1954页。、“天下之民”(33)语出郭店简《唐虞之道》第7简,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第157页。、“巴越之民”“氐羌之民”(34)语出《吕氏春秋·义赏》,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卷1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86页。、“沃土之民……,瘠土之民”(35)语出《国语·鲁语》下,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卷5,第194页。、“戎狄之民”(36)语出《国语·晋语》二,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卷8,第288页。、“末作之民”(37)语出《韩非子·亡征》,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卷5,第302页。等等。这些不同的称谓提示我们要注意到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即“民”能够以地域为称,但并不以族为称,它所表现的是社会成员的地域特征,而“人”则可以表现其作为某族的血缘关系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成员身份的巨大变化是由氏族(宗族)之人变成了国家控制下的编户齐民。将所有的民众置于国家的名籍之上,这是战国时期各国变革的主旋律。这种变革以秦国最为彻底,楚国也有与秦国类似的情况。反映战国中期楚国情况的《包山楚简》,其中有“集箸(书)”,就是登记汇集各籍的竹简,《周礼·秋官·司民》称“司民”的职守是“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38)《周礼·秋官·司民》,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35,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卷4,第878页。。《周礼》成书于战国后期,“司民”所载其“登万民之数”,应当是当时实行居民登记情况的反映。
《包山楚简》的“集箸(书)”,相当于后世的“户籍”。《包山楚简》的“集箸(书)”记载战国时期那个地区的居民身份有“里人”,如“尚之己里人青辛”“安陆之下里人屈犬”(39)这两例关于“里人”的记载,见《包山楚简》第31、62号简,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上册,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351页、第352-353页。。还有“邑人”,如“罗之庑之者邑人女”“湛母邑人屈庚”(40)这两例关于“邑人”的记载,见《包山楚简》第83号简,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上册,第354页。按简文“”字不识,这个字又见于包山楚简第261号简,或与“”字合为一,以“石”为偏旁,专家指出原简“据红外影像释,石也许是‘’的偏旁”(陈伟主编:《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页注90),若此不误的话,则包山楚简遗册有“二”之载,疑为石制武器之名。疑简文“者”或当为从事某种手工业的工匠(如石匠)之称。,还有只以居住地为称的“人”,如“新都人奠逃”“东阪人登步、东阪人登”“人秦赤”(41)这几例简文,见《包山楚简》第165、167、168、168号简,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上册,第361、362页。,上面这些“里”“邑”是为楚国居民组织之名称,某地(如“新都”“东阪”“”)之人,也应当是属于此地由国家管理的居民。陈伟先生认为关于这些人的简文记载,“体现了纯粹的地缘关系。以这一方式称述的‘人’,当是国家直接控制的居民,相当于后世所谓编户齐民”(42)陈伟:《包山楚简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页。,这个说法是很正确的。由于楚国变法不够彻底,所以社会上还有不少人为封君或官吏私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的力量。这些人见诸包山简者如“鄝莫嚣之人周壬”“阳厩尹郙之人邦”“圣夫人之人宗”(43)这几例简文,见《包山楚简》第29、61、84号简,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上册,第351、352、354页。等等。
“编户齐民”肇端于战国时期诸国授田制度的实施,到秦代则成为国家控制天下民众的最主要的制度。史载汉高祖刘邦及其所率领的将军,当初都是秦王朝的“编户民”(44)《史记》卷8《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92页。,就是一个明证。编户齐民作为系统而完整的制度成型于汉代。汉代规定“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45)《汉书》卷5《景帝纪》,第141页。,国家给予土地,亦是“民年二十受田”(46)《汉书》卷24上《食货志》,第1120页。,颜师古注《高帝纪》云:“傅,著也。言著名籍,给公家徭役也。”(47)《汉书》卷1上《高帝纪》,第38页。汉代所形成的“编户齐民”情况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将民众的人口情况,以户为单位登记在国家的户籍上,所谓“编户”,即在编(“国家户籍”)之户,所谓“齐民”,即编在国家户籍上的居民,因为大家都有同等待遇,整齐化一,故称“齐民”。需要注意的是“汉承秦制”,汉代的这些规定皆源自秦国商鞅变法前后实际的制度,这个制度的最简明的说法,见于《商君书·境内》篇,是篇说:
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48)《商君书·境内》,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卷5,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页。
据此可知,所有的秦民,无论男女在国家的名籍上皆有登记,出生即载,死即削去。
商鞅特别清楚“民”之重要。“编户齐民”是国家赋税的主要交纳者,国家所拥有编户的多寡,直接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影响到王朝的盛衰。所以他变法的着眼点即在于利“民”,他认为“法者,所以爱民也”(49)《商君书·更法》,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卷1,第3页。,商鞅强调不利于“民”的旧礼制必须改变。战国时期各国变法运动的核心是土地制度的变革,秦国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50)《资治通鉴》卷2。关于“开阡陌”的“开”,古有两种理解,一是开辟,即设置;二是废去。20世纪80年代,四川省青川县发现的木牍文字,表明“开阡陌”的“开”,应以前说为是。至于蔡泽所说商鞅“决裂阡陌”(《战国策·秦策》卷3《蔡泽见逐于赵》,范祥雍:《战国策笺证》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60页),指破坏旧的井田之阡陌,与“开阡陌”指开辟(即设置)阡陌之意并不相左。,彻底改变土地制度,又采取措施,推动国家直接控制的个体小农的普遍出现。秦国的社会成员,无论其原先为何族,也不论其原先居住何地,一皆为“秦民”,即秦国之民。
这样的居民,多数成为授田制之下的农民。战国时期秦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变革情况虽不及秦国彻底,但大方向是一致的,即将原先的氏族(宗族)之人,变为国家直接控制的“民”。可以说到了战国后期社会居民的身份大体上已经由原先的氏族之人转变为“编户齐民”。这种居民身份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古代中国的历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