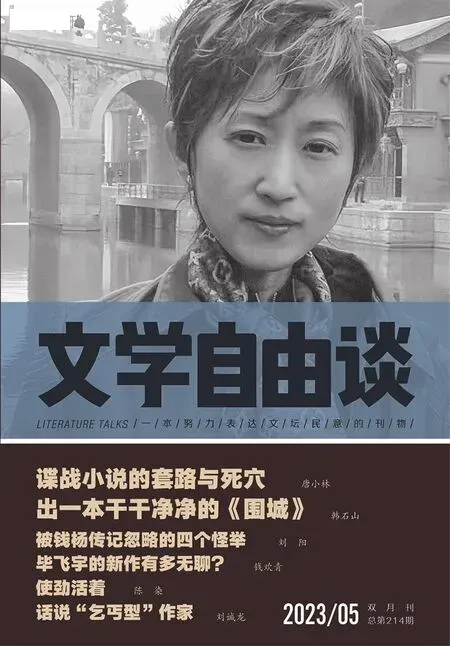和一部经典小说结缘
□宁宗一
上个世纪,我有近五十年的时间是在讲台旁度过的。在教学中,备课、讲课、课堂讨论是我生活中的常态。而论文写作即所谓的科研,几乎都是在教学过程中有所发现才会命笔一写。所以1990年前,我最多出几本论文集而已,直到这一年,我才出版了仅仅十万字的堪称寒碜的小书——《说不尽的〈金瓶梅〉》。没想到,这本小书却开启了我后来探寻小说美学的大半个岁月的学术历程。
其实,我从事研究《金瓶梅》起步很晚。当时,“金学”已经开始热闹起来,老树新花,各逞风采。我厕身其间,难免战战兢兢。跌跌撞撞走了几步,有欢乐和兴奋,也有困惑与烦恼,有时还有一种难言的寂寞和孤独。说真的,对于《金瓶梅》的研究,我曾有一种宿命感:《金瓶梅》竟然和我的人生命运发生了联系。
建国前不去说它了,即使在后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无论在知识界内还是知识界外,总有一些人把《金瓶梅》看成坏书、淫书,理应禁之。1958年在“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运动中,我仅仅因为在给历史系同学讲文学史时,赞美了一句《金瓶梅》的“前无古人”的价值,就被贴了一张大字报,说我“把毒草当香花”,“企图用《金瓶梅》这样的淫秽的坏小说毒害青年学生”。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因手头有一部施蛰存先生整理删节的《金瓶梅词话》,并曾在部分教师和研究生中传阅过,结果在所谓“312室裴多菲俱乐部”的“不正常”活动的诸多错误中,传看和散布《金瓶梅》,也算是我的一条“罪状”。当时针已拨到了八十年代,还有人在窃窃私议,似乎研究《金瓶梅》不像研究《水浒传》《红楼梦》那样光彩,而谁要对《金瓶梅》的价值作充分肯定,谁就似乎也是不道德的了。所以我承认,恐惧思维一直积淀在我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中,以至于很长一个时期我几乎讳谈《金瓶梅》。我怕自己谈多了,会让人感到我和《金瓶梅》一样“不洁”。然而事实却证明,《金瓶梅》就像幽灵一样缠绕着我,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它就给我“招灾惹祸”。
我正式从事《金瓶梅》研究的动因和最初的始因,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1983 年,春风文艺出版社林辰先生在大连组织了一次明清小说研讨会。为了参加这次会议,我还是相当认真地思考了一些问题,最后以《〈金瓶梅〉萌发的小说新观念及其以后之衍化》为题,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表述了我对《金瓶梅》的基本评估。说实话,在论述《金瓶梅》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及其对小说美学的贡献时,我充满了学术激情,我深感《金瓶梅》沉冤数百载,而我的教书生涯又时不时地曾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文章写开去,在理论思辨中更多地融进了自己的感情因素。我意识到,我写这篇文章的内驱力,实际上是二十多年前那张令我心慌和腿发软的大字报,以及那以后围绕着《金瓶梅》的风风雨雨的日子,所以我是在为《金瓶梅》进行辩护,也是在为自己辩护。但是,我能在以后继续研究《金瓶梅》,其关键是复旦大学章培恒先生对我的鼓励,他是第一位把我的论文收进他主编的《金瓶梅研究》中的。没有章先生的支持,我不会有继续写作这方面论文的勇气。
其后,胡文彬和徐朔方两位先生分别编了两本《金瓶梅》研究论文集出版,我看到了美国学者夏志清评论《金瓶梅》的文章。我对他们贬抑《金瓶梅》的观点很不以为然,他们把《金瓶梅》打入“三流”,更是我所不能接受的。至于方非先生在《劳伦斯的颂歌与略萨的控诉》一文中的那种比较研究,我同样认为不会对《金瓶梅》做出科学的价值判断。我直率地表明:《金瓶梅》不应成为人们比较研究的陪衬和反衬或垫脚石,把它置于“反面教材”的位置上进行的任何比较,都是不公正的。这样,我前前后后以历史的美学的观点写了《〈金瓶梅〉萌发的小说新观念及其以后之衍化》《〈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金瓶梅〉思辨录》《〈金瓶梅〉:小说家的小说》《说不尽的〈金瓶梅〉》《“金学”建构刍议》《谈〈读书〉对〈金瓶梅〉的评论》等等。这些文章体现了我的基本思路:为《金瓶梅》一辩!
在此基础上逐步积累,1989年初,我终于完成了“金学”研究专著《说不尽的〈金瓶梅〉》的写作,1990年由天津社科院出版社出版。这只是一本十万多字的地地道道的小册子,我深知拿到读者特别是“金学”研究专家前面,会感到万分寒碜,可是我还是送给了许多“金学”研究专家,目的是在征求意见的同时,向同行朋友们告知:这是我多年来对《金瓶梅》的探索和试笔过程中的一个小小总结,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代表了我研究《金瓶梅》第一阶段的浅薄体会和深深的困惑。此后,我最早的研究生罗君德荣提议,是否联系一些乐意用小说美学来观照《金瓶梅》的朋友,编写一本崭新的《金瓶梅》研究专著?我认为他的意见很好。我不仅积极参与该书构架的设计,而且撰写了长篇导言和头两章的文字。这本由我和罗德荣教授主编、近三十万字的专著,终于在1993年出版,书名径直题为《〈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不久,文化艺术出版社约我主持《〈金瓶梅〉小百科丛书》的组稿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由我主编,弥松颐、刘国辉任副主编的五部专著也出版了。在这里,我们选择“《金瓶梅》小百科”这个总题目,意在思考:我们的研究是否应对揭示出了中国风俗史一面的《金瓶梅》予以更多的考虑?是否应以《金瓶梅》所反映出的种种现象为视角,去探寻一下历史表象背后更深层的东西?是否可以以《金瓶梅》为坐标,把文艺与其他学科交融而成的边缘研究,作为拓宽思维空间的一个通道?因为从文化心理结构来说,很多著名的古代小说中所积淀的民族素质、政治意识、伦理观念、文化品位、心理定势以及民风民俗,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当然,我不是没有怀疑过自己要为《金瓶梅》辩护这一命题的必要性和不可解的“《金瓶梅》情结”。《金瓶梅》的“行情”一直看涨,大有压倒其他几部大书之势;而对一部书的评价,那是一个永远不会取得完全一致意见的事。不过我还是看到无论在社会上、人的心目中,《金瓶梅》都是最易被人误解的书,而且我自己就发现,我虽然殚精竭虑、声嘶力竭地为之辩护,我也仍然是它的误读者之一,因为我在读自己的那些书稿时,就看到了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评估它的价值的矛盾。这其实也反映了研究界、批评界的一种很值得玩味的现象。我发现一个重大差别就是研究者比普通读者更虚伪。首先因为读者意见是口头的,而研究者的意见是书面的,文语本身就比口语多了一层伪饰,而且口语容易个性化,文语则易模式化;同时研究者大多有一种“文化代表”和“社会代表”的自我期待,而一个人总想着代表社会公论,他就必然要掩饰自己的某些东西。在这方面读者就少有面具,往往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怎么想就怎么说。对《金瓶梅》,其实不少研究者未必没有普通读者的阅读感受,可一旦写成文章就冠冕堂皇了。尽管我们分明感到一些批评文章在作假,一看题目就见出了那种做作出来的义正辞严,但这种做作本身就说明了那种观念真实而强大的存在,它逼得人们必须如此,且做作久了就有了一种自欺的效果,真假就难说了。对待《金瓶梅》的性行为描写,我必须承认从前我的文章就有伪饰。现在到了写自叙的时候了,我应该说出自己的心底话:我既不完全同意弗洛伊德的性本能说,也不能苟同以性为低级趣味之佐料,而更无法同意谈性色变之“国粹”。性活动所揭示的人类生存状态往往是极为深刻的。因为,在人类社会里,性已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可以提高到更高的精神境界,得到美的升华,绝不仅仅是一种动物性的本能。所以,我认为《金瓶梅》可以、应该、必须写性,但是由于作者笔触过分直露,因此时常为人们所诟病。我喜欢伟大的喜剧演员W.C.菲尔兹说的颇有意味的一句话:有些东西也许比性更好,有些东西也许比性更糟,但没有任何东西是与之完全相似的。信然!
关于我研究《金瓶梅》的策略和方法,那是在我进行了理性思考以后,选择了回归文本之策。这是因为:第一,在文学领域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无论古今,作家得以表明自己对社会、人生、心灵和文学理解的主要手段就表现在文本之中,同时也是他们可以从社会、人生、心灵和文学中能够得到最高报偿的手段。所以一个写作者真正需要的,除了自身的人格与才能之外,那就是他们的文本本位的信念。因此,对于任何一个真诚的研究者来说,尊重文本都是第一要义;第二,归根结底,只有从作家创造的艺术世界来认识作家,从作家对人类情感世界带来的艺术启示和贡献去评定作家的艺术地位,才是正途。比如笑笑生之所以伟大,准确地说,他的独特贡献,就在于他的创作方式异于同时代和之前时代的作家,因为他找到了一个典型的世俗社会作为表现的对象,并且创造了西门庆这个角色:粗俗、狂野、血腥和血性。他让笔下的人物呈现出原生态,所谓毛茸茸的原汁原味,这是一个崭新的前所未有的叙事策略,而这一切却被当时大多数人所容忍所认同,以至欣赏。而且由于这部小说的诞生,竟然极为迅猛地把原有的小说秩序打乱了,从此很多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到这一场小说变革的思潮中来。毋庸置疑,这一切都是小说文本直接给我们提供出来的。
学术研究是个体生命活动,生命意志和文化精神是难以割裂的。《金瓶梅》研究中的“无我”是讲究客观,“有我”则是讲究积极投入,而理想境界则在物我相融。过去,《金瓶梅》研究中的考据与理论研究往往相互隔阂,甚至相互排斥,结果二者均得不到正常的发展。我们的任务是把二者都纳入到历史与方法的体系之中,并加以科学的审视,只有这样才能体现考据、理论与文本解读的互补相生、互渗相成的新的学术个性。
另外,也许是最重要的,选择回归文本的策略,乃是小说本体的要求。我承认,我从不满足“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和界定,而更看重文学实质上是人的灵魂学、性格学,是人的精神活动的主体学。因为一切伟大的作家最终关怀的恰恰是人类的心灵自由。他们的自救往往也是回归心灵,走向清洁的、尽善尽美的心灵。《金瓶梅》像一切杰出的小说一样,是“我心”的叙事。笑笑生的独特心灵,就在于他在生活的正面和反面、阳光和阴影之间骄傲地宣称:我选择反面与阴影!这当然是他心灵自由的直接产物和表征,所以他才有勇气面对权势、金钱与情欲诸多问题并进行一次深刻的人生反思。如席勒所说:“从非反思向反思的过渡,原来持镜反映自然的艺术,现在也能够持镜反映艺术之镜本身了。”
不可否认,面对旷世名著,那是要求有与之水平相匹配的思想境界的。在研究或阐释作家的思想精神和隐秘心灵时,你必须充当与他水平相当的“对手”,这样庶几有可能理解他的思路和招数。有人把解读名著比喻为下棋,那么我仍承认自己永远不会是称职的对手,因为棋力棋艺相差太远,常有捉襟见肘的困窘,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
我深知,《金瓶梅》所体现的美学价值意义重大,不作整体思考不行,而一旦经过整体思考,我们就会发现,笑笑生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如何思考文化、思考人生。歌德说过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人靠智慧把许多事情分出很多界限,最后又用爱把它们全部沟通。所以,对《金瓶梅》的生命力必须以整体态度加以思考。时至今日,我还是想努力地从宏观思维与微观推敲相结合上入手研究《金瓶梅》文本,并且,自己希望每一篇对《金瓶梅》的解读都是我心灵的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