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记功到志人:史传思维影响下的北宋墓志书写模式变迁
张亚静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一、北宋墓志志文的两种书写架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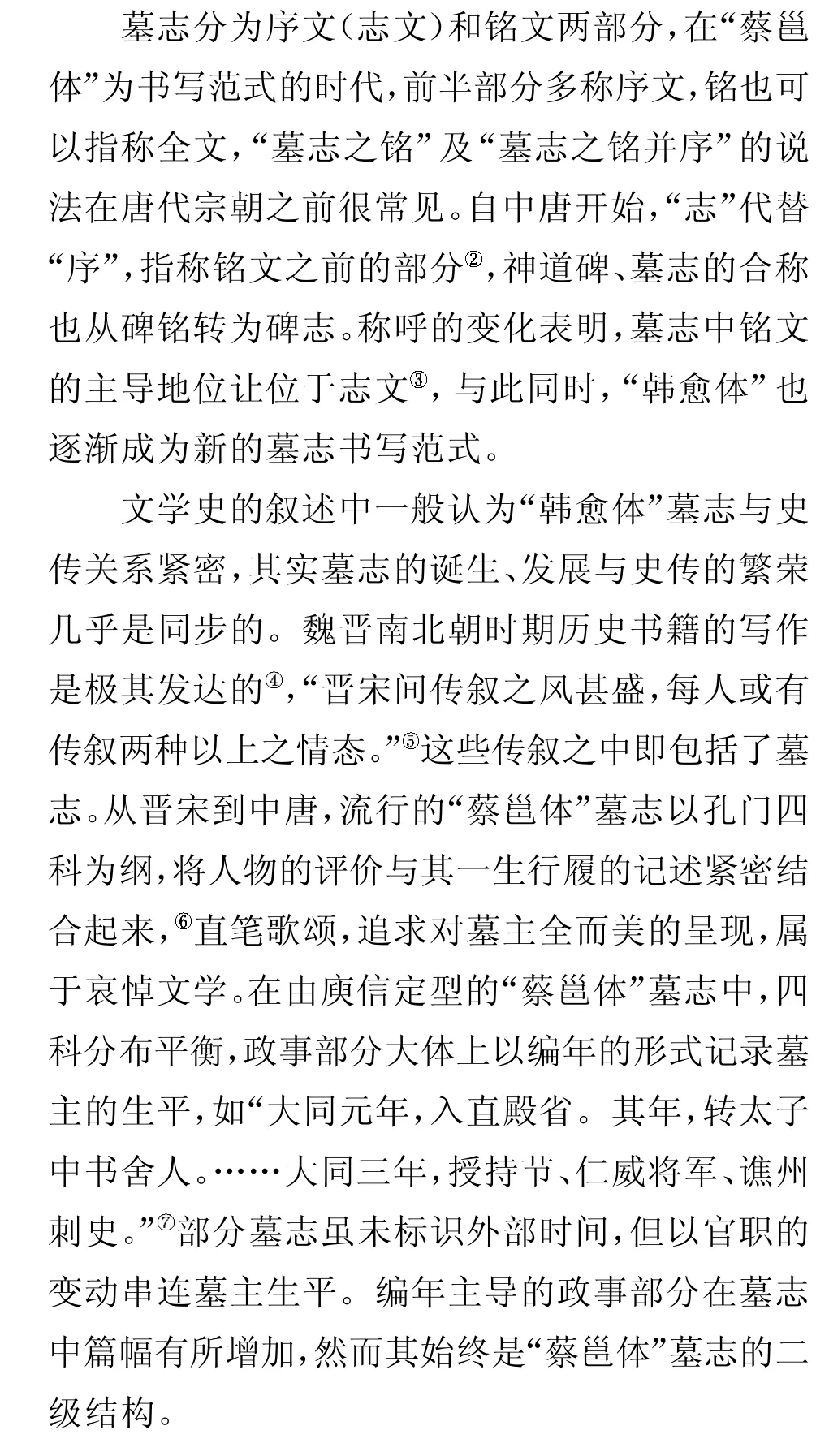
伴随韩愈援引史传笔法和思维方式进入墓志,加之北宋墓志篇幅较唐代出现了大幅度增加,编年体成为墓志的主要架构方式,旨在全方位展示墓主生平,这在张方平、王珪、苏颂等人写作的高级官员墓志中尤为明显。张方平以官职变动为纲叙述了韩亿任官的经历,“知亳之永城县,理声籍甚”,“淮南计台上治最,改大理寺丞”,“丁信国艰,服除,倅淮阳”,从韩亿起官治理永城县,通判陈州,知洋州、相州,安抚淮、浙,直至任开封府判官都是一官一叙。墓志选事类似史书的《循吏传》,“州有冤狱,乃大豪巨奸赂以买直,积十年不决。公一讯情得,罪人自服。”“合肥有陂可溉田,久为强家豪占,公按复之,民至今受赐。”韩亿墓志中早期经历叙事相对简洁,重点强调墓主能力出众、关心民瘼、受他人赏识。随着韩亿职位的晋升,张方平较为详细地记录了他担任河北转运使、御史中丞时如何处事周审、持法严平,事无巨细地叙述了他后期的经历。父祖、儿孙等部分则与历官书写呈现平行关系,编年体此时成为墓志的一级架构方式。
在编年为纲的大框架之下,墓志对于墓主身居高位时的政绩详述其本末。张方平将对韩亿治蜀的来龙去脉予以细致呈现。平蜀、治蜀是北宋前期重要的政治议题,韩亿官位日隆时,蜀地尚不太平。此时“知星者言益部当灾”,因“蜀人易摇”,灾异可能会催生兵变。在这种情况下,宋仁宗打算甄选“才堪镇抚者”赴蜀任职,于是选中了韩亿。陛辞之时,韩亿展现了拳拳为君分忧之心,向仁宗立下军令状,“惟陛下无以蜀为虑也”。到任后,韩亿的确如其所言认真地负起责任,“凡利害事,知无不为”,

尹洙选取王利在河南和沧州两地为官之事说明他不畏权势,为民辨冤,沧州捕盗案、二卒杀人案首尾清晰,波澜尽现。叙事以“其精审皆此类”作总结和评论,说明其在地方行政过程中一以贯之的风格。他将典型事件举一反三地书写,并点明墓主治狱“精审”的特色。后文又说墓主“凡为政清简”,“故所至皆便其治”,精审和清简构成王利为官的特色,其聪明审慎的形象跃然纸上。宝元年间,尹洙的写法在他所处的士人圈中已经开始流行,胡则墓志(范仲淹撰)、林冀墓志(蔡襄撰)、王洙墓志(欧阳修撰)都采用这种结构。
相较于尹洙,欧阳修所撰墓志选事更具代表性,叙事更丰富,抒情更外放。为老友谢绛撰写墓志,他秉持“言天下之公”的原则叙其历官:

欧阳修拈出“上书”一点不断重复,选事虽多但紧扣主题,将墓主历官的所作所为交代清楚。谢绛谏礼制不当,议天灾,请罢佛道,论罢宫廷密法制衣,禁内作器,“皆以职言”。而他谏言政令两出、废后、制乐之事,则是为国体考虑。谢绛不同的上书内容不仅表明了他的政治观点,也突出了他对职与守的坚持。欧阳修将事之本末娓娓道出,人物的风神也慢慢浮现。尹洙、欧阳修以事之本末为经,编年为纬,重在体现墓主在公共领域的身份及个性。
二、北宋墓志核心功能和抒情方式的新变
纪传体史籍综合了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两种形式,与墓志的撰写最相似。然而,有学者认为,传叙家与史家的根本差异在于传叙家以人为中心,史家以事为中心。本纪文字背后无形象,常是大纲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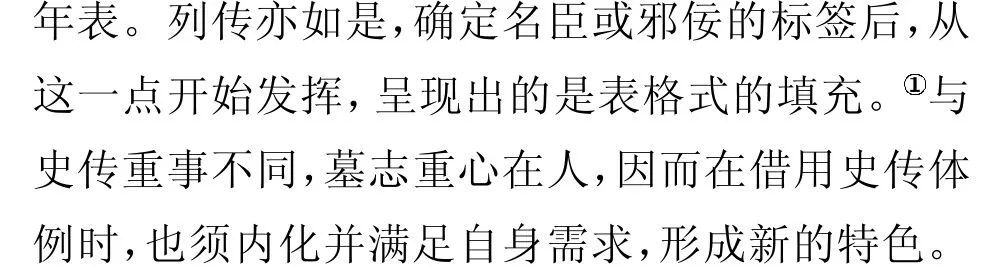
相比已有范式,“韩愈体”的核心竞争力根植于何处?欧阳修和王安石的碑志缘何在当时被奉为圭臬?二人又有何差异?比之欧阳修,王安石的墓志里中下层士人占比更大,选事详略得当,叙事笔调委婉,抒情更克制:
王安石略述杨氏在翁源县、广州市舶司任上的经历,重点叙述他在德兴和余干县治灾、治狱的成就,并以范仲淹的夸奖为其延誉。这篇墓表也以历官为线索叙事,但结构顺畅,详略得当,重点在于塑造墓主廉洁奉公的能吏形象。王安石善于抽绎墓主的生命主线,叙官彻底摆脱了“某年某官”的限制,如曾易占的墓志以“历官—去官—撰书”梳理生平。相比尹洙“历官简述+选事志人”的结构,王安石会根据墓主个人情况合理排布时间和事件,墓志中时间清晰,详略得当。他的贡献在于融合张方平和尹洙的墓志架构,使之更加接近纪传体史书中的人物传记,能抽绎出墓主的生平线索,书写典型事件,由此能更好地实现志人的功能。
就墓主身份而言,高级官员的墓志可以任意选用“蔡邕体”或“韩愈体”,对于缺乏事功的墓主,“韩愈体”提供了一种更易操作、更为实用的写作模式,而欧、王的碑志为一般撰者如何写好“韩愈体”提供了学习范式。这成为经欧阳修、王安石等为代表的宋代文人在继承“韩愈体”传统之后,创新发展出了墓志书写最为核心的形式与内涵,也更适应平民化的社会需求。

欧阳修感叹张汝士去世后,风流云散,当时的长官钱惟演被贬黜,其他人因各种原因也纷纷离开洛阳。二十五年来,往日同游及参加张汝士葬礼的旧友大多已经去世或失去联系,当初撰写志文的尹洙已逝去十余年,而仍然在世的人也像自己一样既病且衰。访旧半为鬼,但所隔何止山岳。西京时期的岁月在欧阳修的心中既是乌托邦,更是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在屡次的书写和回顾中被反复地强化。而故去的张汝士不仅是这段岁月的共同参与者、见证者,他与尹洙、谢绛等人之间的真挚情谊成为了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宋代士大夫的一种生命意象。文中明道二年和嘉祐二年两条时间线相互交错,人事代谢、盛衰之叹一一呈现在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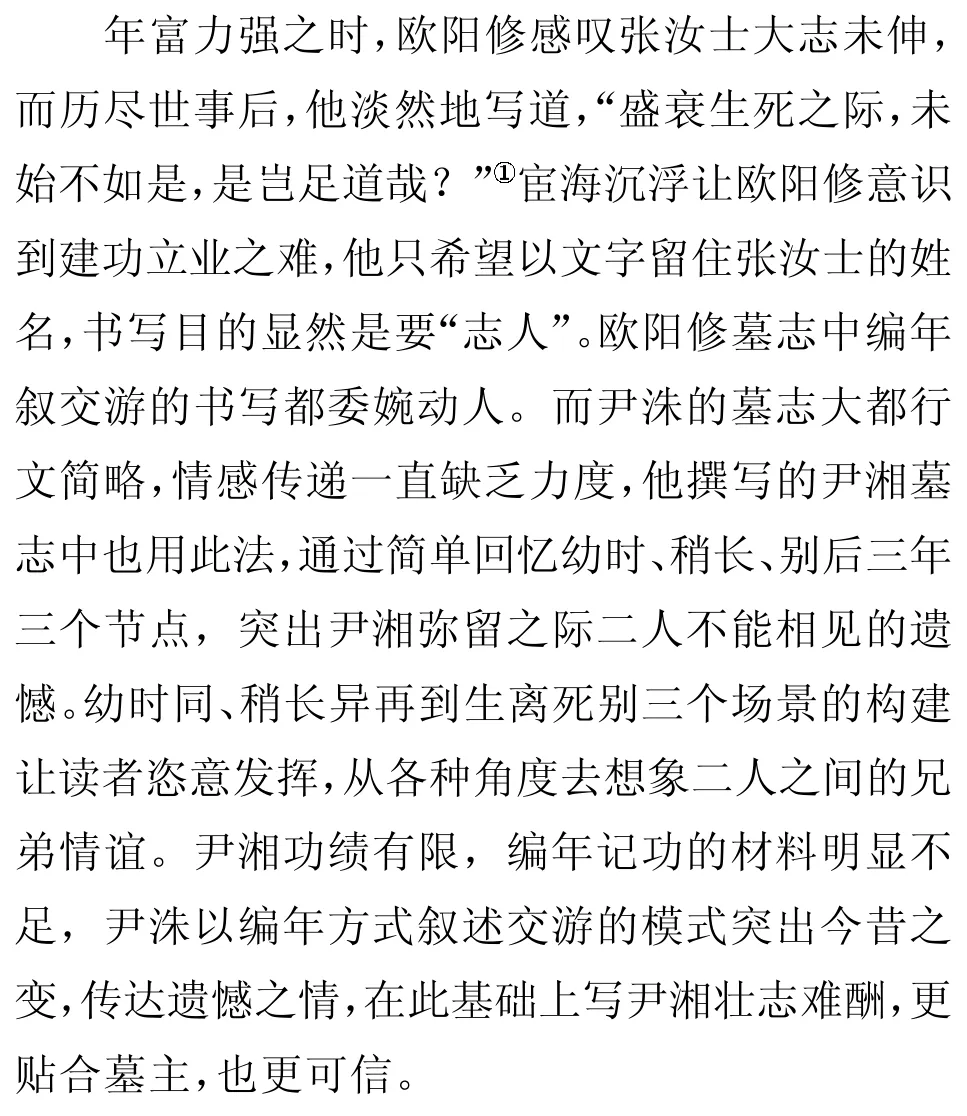
墓志是一种仪式性文体,整体上肃穆、克制,多以第三人称视角呈现,引入第一人称视角,可以用撰者的生命经验去体贴墓主。文中蕴含的今昔之变、亲友谢世之憾是人类共通的感情,容易引起读者共鸣,因此在北宋墓志中,以编年为纲目,于历时线索中追述交游本末成为一种固化的写作模式。韩琦的《故许州观察推官曾君墓志铭》、文同的《梓州处士张公墓志铭》、沈括的《宋故桐庐县尉杜君墓志铭》皆用此法,汤乂的《宋汤君夫人周氏墓志铭》选取了作者求学、登科从仕、罢官而归三次见到墓主周氏的情景,在抒情之外更突破了“女无外事”造成的书写困境。交游本质上是关系的连接,作者叙交游后抒情能被理解、信任。除此之外,墓志叙交游也多与求铭过程重合或关联,作者借机说明了材料的来源,也强调了“实录”,因此墓志看似成为一种“公正的”史料,“志人”的目的也最终达成。
三、墓志“公共化”引发史笔叙事的变异
王安石以孔道辅拒绝宰执的游说来表现其直率的性格和为人,李觏批评富人娇养孩子的风气突出墓主善于培养子女。不论写具体事件还是批评流俗,都是借他者凸显墓主的优秀品质,这种一褒一贬的手法利于塑造人物形象。然而,墓志是奉敕或受请托撰写的,人际关系、政治环境等诸多因素会影响褒贬的力度,因而墓志的贬斥会比史书更加隐晦。庆历时期,反对者通过一系列事件对改革派进行攻击,使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迅速流产。欧阳修对此无法完全释怀,但吕夷简集团在朝廷内外的势力十分强大,因此他的墓志中不像史传指名道姓,而是一直以官名“宰相”称呼吕夷简。熙宁四年,司马光在吕诲墓志中以“侍臣弃官家居者”“新为政者”指代王安石。元丰二年,范祖禹在刘恕墓志中也以“执政”指代王安石。类似此类的书写方式在北宋得以逐渐定型下来,成为了宋代文人士大夫愈益普遍使用的墓志撰写模式。

毕世安的子孙分别于景德二年(1005)和元祐三年(1088)请杨亿、刘挚撰写墓志、神道碑,两篇文章相隔八十余年,风格和关注点截然不同。杨亿在《宋故推忠协谋佐理功臣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食实封四百户赠太傅中书令谥曰文简毕公墓志铭》中秉承“蔡邕体”的文体规范,不铺述时势之艰辛、过程之坎坷,只大力歌颂墓主功绩并归功于上,而刘挚在《毕文简神道碑》采用“韩愈体”,甄选重点事件详述。文章结构上,杨亿以官职变动为纲撰写墓志,力求无所遗漏;刘挚只选取毕士安推荐寇准、澶渊之盟中促成御驾亲征两件事详述。墓志中澶渊之盟占比与其他职任的篇幅区别不大,神道碑中对澶渊之盟的叙述占有绝对优势。细节安排上,墓志以澶渊之盟发生、发展的顺序书写,笔触落在墓主如何拖着病体谋划;神道碑先写议和成功,后补充毕士安带病赶到行在,坚定帝王信心和安排后续事宜,顺叙写澶渊之盟本末,插叙写毕士安的贡献。神道碑为什么主要叙述这两件事?毕士安举荐寇准,所以他们能通力合作,促成了澶渊之盟的缔结。澶渊之盟拟定时,宋人处于优势地位却厚赂敌国,献计的毕士安承受着非议,所以刘挚将事件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交代清楚,这种书写策略也是为毕士安开脱。元祐三年,关于寇准的功过已有定论,澶渊之盟对北宋政治、经济发展的意义不言而明。经过时间的汰洗沉淀,毕士安神道碑的书写重点显豁而出。

结语
墓志诞生于晋宋之际,及至明清,文体只有一次大变,而北宋是“韩愈体”的定型时期。北宋墓志“史传化”由表及里,程度不断加深,史传从一种笔法、框架到思维方式慢慢渗入墓志,但墓志也对它进行了个性化的扬弃。在此过程中,墓志的核心功能从记功转向志人,抒情方式也发生变化,形成了新的写作范式。“公共化”的传播环境使得墓志书写追求“隐恶扬善”,这种功能诉求使其书写积极、消极事件都有失偏颇,私人关系也影响墓志书写,“实录”难以落实,谀笔和曲笔难以避免。
从“蔡邕体”到“庾信体”墓志由哀悼文学变为史传文学,与之平行的是墓志的传播方式由石本主导转向纸本主导,媒介即思维,物质文化的变迁对唐宋墓志的形式、功能及传播还产生了哪些影响值得继续挖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