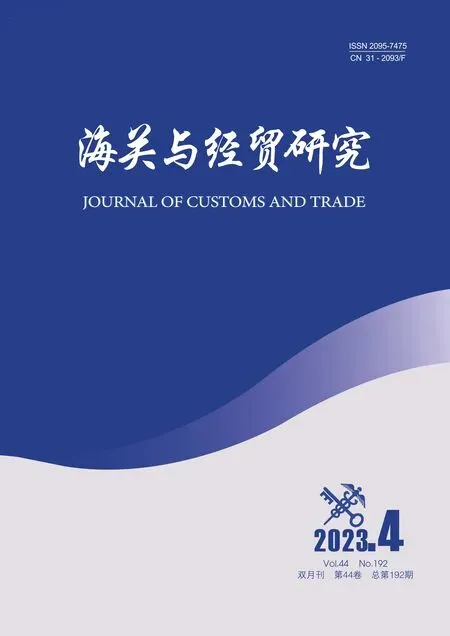国际投资仲裁中的东道国安全例外抗辩与中国对策研究
梁 咏 刘中奇
一、引言
随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更多因素被纳入安全范畴并被付诸实践。近年来,部分国家在对外缔结国际投资条约(以下简称投资条约)(1)本文采用广义的IIAs概念,既涵盖双边投资协定(BIT),也涵盖含有投资规则的自由贸易协定(FTA)。中纳入安全例外条款,(2)在不同协定和论述中,可能以“根本安全利益”(essential security interests)、“安全例外”(security exceptions)、“不排除”(non-preclusion)等措辞表述,本文中概以安全例外条款进行表述。频繁以捍卫“国家安全”为名对外国投资采取特别管制措施,并在争端解决中以安全例外为由进行抗辩,为其违反投资条约或投资合同项下义务寻求豁免。(3)José E.Alvarez,The Return of the State,Minnesot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11 (20) ,p.237.比如,2020年以来美国政府以保护数据安全等为名多次要求强制拆分抖音海外版(TikTok);2020年瑞典邮政电信管理局禁止使用中国华为和中兴设备的运营商参与瑞典国内5G建设(以下简称5G禁令);以及2022年加拿大工业部以“国家矿产和资源安全受到威胁”为由要求中矿(香港)稀有金属资源有限公司等三家中国公司退出在加拿大已进行的锂矿投资。2022年1月,华为以瑞典所采取的5G禁令违反1982年中国—瑞典双边投资条约(以下简称BIT)为由将瑞典诉至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显示出中国投资者比以往更加积极运用法律工具进行反制。针对此类争端,东道国政府可能援引安全例外(如投资条约中存在安全例外条款)或直接依据习惯国际法的“危急情形”进行抗辩。已有研究虽然对安全例外条款进行了一定探讨,但尚未对仲裁庭审理不同类型安全例外条款的逻辑和偏好进行类型化研究,对东道国以安全例外为由进行抗辩的实证研究仍显碎片化。
二、投资条约中安全例外条款的缘起、价值和中国缔约现状
出于对外交往需求,二战后所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对各国主权权力进行了一定约束。(4)王沪宁著:《国家主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2页。在国际投资法领域,资本输出国将纳入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的投资条约积极对外推广,(5)梁咏:《国际投资仲裁机制变革与中国对策》,《厦门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第160页。以期对投资者提供强有力的保护。然而实践中ISDS机制的“正当性危机”,也促使部分国家比以往更频繁地援引安全例外抗辩寻求国际义务豁免,引起各方对投资条约中的安全例外条款予以更多关注。
(一)投资条约中安全例外条款的缘起
在投资条约中纳入安全例外条款为保障缔约方的国家安全留下了“安全阀”,(6)Jaemin Lee,Commercializing National Security:National Security Exceptions’ Outer Parameter under GATT Article XXI,Asian Journal of WTO &International Health Law &Policy,2018(13),p.281.从而在促进投资和保护安全之间进行微妙而关键的平衡。1982年美国—巴拿马BIT第10条首次规定了安全例外条款,2004年美国BIT范本第18条(7)2004年美国BIT范本第18条规定:“本协定不得解释为:(1)要求缔约方提供或允许获得其确定如披露将违背其根本安全利益的任何信息;或(2)阻止缔约方采取其认为对履行其有关维持或者恢复国际和平、安全或保护本国基本安全利益方面的义务所必要的措施。”中增加了“其确定”(it determines)、“其认为”(it considers)的自裁判性措辞,2012年美国BIT范本也沿袭了2004年范本中的该条款。美式安全例外条款在近年来签订的投资条约中被部分效仿。此外,近年来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第21条(安全例外)(8)GATT第21条规定:“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a)要求任何缔约方提供其认为如披露则会违背其基本安全利益的任何信息;(b)阻止任何缔约方采取其认为对保护其基本安全利益所必需的任何行动:(i)与裂变和聚变物质或衍生这些物质的物质有关的行动;(ii)与武器、弹药和作战物资的贸易有关的行动,及与此类贸易所运输的直接或间接供应军事机关的其他货物或物资有关的行动;(iii)在战时或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情况下采取的行动;(c)阻止任何缔约方为履行其在《联合国宪章》项下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义务而采取的任何行动。”为蓝本加以增删的“GATT式”安全例外条款(9)See Ji Yeong Yoo and Dukgeun Ahn,Security Exceptions in the WTO System:Bridge or Bottle-Neck for Trade and Securit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2016(19),p.423.也被较广泛接受。据统计,含自裁性安全例外条款的投资条约在同期签订投资条约中比重已经从2000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迅速上升到2015年60%以上。(10)See Karl P.Sauvant ,Mevelyn Ong,with Katherine Lama and Thor Petersen,The Rise of Self-Judging Essential Security Interest Clause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Columbia FDI Perspectives on Topical Foreign Investment Issues,2016(188),p.1.
(二)IIA中安全例外条款的价值
安全例外条款在投资条约中发挥着“安全阀”与“平衡器”的作用,其本质是通过排除东道国行为违法性以实现对国家主权与安全的保护。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对2575项投资条约统计显示,其中含安全例外条款的有394项,含自裁性安全例外条款仅有148项。(11)UNCTAD对1960年12月22日—2018年10月21日期间签订的IIAs统计结果,参见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iia-mapping,最后访问日期:2023年6月15日。直言之,投资条约中的安全例外条款与实践需求之间存在数重不匹配,具体表现为:第一,投资条约总量中安全例外条款的低占比与近年来安全例外条款被高频援引之间不匹配;第二,安全例外条款的强威慑性与低自裁判之间的不匹配,仅有40%安全例外条款中采用自裁判性措辞,且多集中于近年来签订的投资条约,而目前发生争议的多为签订于2000年之前的投资条约;第三,基本安全利益范围模糊与安全事项扩展之间的不匹配,目前投资条约中仅有不到40%安全例外条款涉及安全例外的定义,(12)IIA Mapping Project数据显示,包含安全例外条款的国际投资协定有394项,其中对安全例外进行定义的仅有156项。且基本没有对适用场景的说明,条款内容高度抽象和模糊需要在ISDS实践中进一步解释和说明。
(三)中国签署投资条约中安全例外规定的现状
中国已签署的132项BIT中,约10%纳入了安全例外规定,大致可分为:(1)“禁止和限制”条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与新加坡、斯里兰卡、新西兰以及毛里求斯BIT中将缔约方为保护其基本安全利益而采取的禁止或限制措施排除在BIT适用范围之外;(2)序言规定:本世纪初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圭亚那BIT序言中纳入了“不影响普遍适用的健康、安全和环境措施”“尊重东道国的主权和法律”等表述,虽未对安全、主权进行定义,但可能为未来争端解决提供目的和宗旨解释的依据;(3)安全例外条款:近年来与加拿大、土耳其BIT和中日韩三方协定中纳入“GATT式”安全例外条款,特别是,2008年中国—新加坡FTA和2020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吸纳GATT第21条的基础上,还将通信、电力和供水设施等关键公共设施也纳入安全例外条款适用范围。截至2023年6月底,中国已签署的20项FTA中有15项纳入了GATT式安全例外条款。概言之,中国签署投资条约中的安全例外规定呈现如下特点:
1.内容差异显著
中国签署FTA中的安全例外条款多以GATT第21条为蓝本进行设计,但其中仍存在明显差别。譬如,2008年中国—新加坡FTA和RCEP在安全例外条款中明确列入了关键公共基础设施;而2019年中国—毛里求斯FTA中未纳入GATT第21条b款“阻止任何缔约方采取其认为对保护其基本安全利益所必需的任何行动”的规定,而b款恰恰是实践中争端最集中的地方。内容差异在BIT中表现更明显突出,仅对基本安全利益的表述中,至少还存在根本安全利益、(13)2012年中国—加拿大BIT第33条第5款、2015年中国—土耳其BIT第4条第2款a项。实质安全利益、(14)2012年中日韩三方投资条约第18条第1款第1项。国家利益(15)2005年中国—比利时BIT第4条第2款。等表述方式,上述差异侧面反映中国在投资条约中对安全事项尚未形成相对稳定的认知。
2.定位存在分歧
中国投资条约中的安全例外规定定位不明确,部分BIT仅在“禁止或限制”条款或序言中有所体现,与常见的安全例外条款存在较大差别。2012年中国—加拿大BIT和2015年中国—土耳其BIT更将安全例外条款置于一般例外条款统辖之下,未充分突出其更高位阶。
3.自裁判权不定
中国投资条约中的安全例外条款中除了含有自裁判性措辞的“GATT式”条款和不含自裁判性措辞的“禁止或例外”条款外,还存在将裁判权交由仲裁庭确定的第三种方式,如2009年中国—秘鲁FTA第141条正文采纳了美式安全例外条款,但又在脚注中规定,缔约方能否援引该条,应由仲裁庭裁定,这将明显减损缔约方援引该条进行抗辩的自裁判权。
当然,安全是国家“自我保全”的基础,因此即便投资条约中未纳入安全例外条款,东道国依然可以援引习惯国际法中的危急情形进行抗辩,甚至直接以国家主权进行“兜底”。
三、ISDS实践中东道国援引安全例外寻求抗辩的类型化探讨
东道国援引安全例外寻求抗辩的情形基本可分为案涉投资条约包含非自裁性安全例外条款、案涉投资条约包含自裁性安全例外条款以及案涉投资条约不含安全例外条款三类。通过对UNCTAD、ICSID和italaw等网站全面检索所得的13个公开案例中,(16)本文涉及的13个ISDS案例除前述“阿根廷串案”和“印度电信双案”外,还包括Wintershall Aktiengesellschaft v.TheArgentine Republic (“Wintershall案”),ICSID Case No.ARB/04/14,Award,8 December 2008; Total S.A.v.The Argentine Republic (“Total案”),ICSID Case No.ARB/04/01,Award,27 November 2013; Bernhard von Pezold and Others v.Republic of Zimbabwe (“Bernhard案”),ICSID Cas No.ARB/10/15,Award,28 July 2015; Urbaser S.A.and Consorcio de Aguas Bilbao Bizkaia,Bilbao Biskaia Ur Partzuergoa v.The Argentine Republic (“Urbaser案”),ICSID Case No.ARB/07/26,Award,8 December 2016; Antaris Solar GmbH and Dr.Michael Göde v.Czech Republic (“Antaris案”),PCA Case No.2014-01,Award,2 May 2018; Unión Fenosa Gas,S.A.v.Arab Republic of Egypt (“Unión案”),ICSID Case No.ARB/14/4,Award,31 August 2018.未发现依据自裁判性安全例外条款寻求抗辩的争端。自WTO成立以来,共有22起争端援引GATT第21条,截至目前,专家组已经对其中4起案件(美国钢铝产品关税组案仅算1起)做出专家组报告。由于“GATT式”安全例外条款在国际投资条约中被较多接纳,未来可能产生援引“GATT式”自裁判性条款的ISDS争端,因此下文进行类型化分析时也将参考前述四案专家组报告意见。
(一)对东道国依据非自裁性安全例外条款寻求抗辩分析
“阿根廷串案”均由阿根廷政府为应对2001—2003年金融危机而采取的特殊管制措施(18)阿根廷政府2002年颁布了《公共紧急状态法》等一系列法律,对阿根廷比索和美元汇率实现浮动汇率,并取消了原本给予基础设施持证人的诸多优惠,削减了针对外资的补助额度。See Nicolas M.Perrone:Investment Treaties and the Legal Imagination,How Foreign Investors Play by Their Own Rul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1,p.155.引发,阿根廷政府在五案中也均援引1991年美国—阿根廷BIT第11条进行抗辩,该条中未包含自裁判性措辞。前三案仲裁庭否认了阿根廷政府的安全例外抗辩,而后两案仲裁庭支持了阿根廷政府的抗辩。特别是,前三案(CMS案、Enron案和Sempra案)裁决又被撤销,使该问题更加扑朔迷离,上述七案大致可以分成两类:
(1)优先适用习惯国际法“危机情形”
在CMS案中,阿根廷政府援引国际法委员会(International Law Committee)通过的2001年《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Draft Articles on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以下简称《草案》)中第25条“危急情形”(19)《草案》第25条“危机情形”是指“1.一国不得援引危急情况作为理由解除不遵守该国某项国际义务的行为的不法性,除非:2.在下列情况下第1款不适用:(a)不可抗力的情况是由援引此种情况的国家的行为单独导致或与其它因素并导致;或(b)该国已承担发生这种情况的风险”。和BIT第11条进行抗辩。仲裁庭优先适用了《草案》第25条,并认为尽管阿根廷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但尚未达到经济全面崩溃的状态,因此阿根廷政府不能因此免责。之后,仲裁庭还将《草案》中的危急情形作为案涉BIT第11条的审查标准,但未对此进行具体解释说明。(20)王楠:《危急情况之习惯国际法与投资条约中的不排除措施条款》,《比较法研究》2010年第1期,第118页。针对CMS仲裁庭这种模糊化处理办法,审查该案的临时委员会以“未适用准据法”为由提出反对意见,并最终撤销该案裁决。在Enron案与Sempra案中,仲裁庭虽然明确案涉BIT第11条与《草案》第25条的适用条件不同,但在分析BIT第11条构成要件时,以该条中未对基本安全利益进行明确定义为由,仍适用《草案》第25条进行审理,(21)Enron,Award,para.333.实际仍以“危急情形”优先。2010年,Enron案和Sempra案先后被ICSID撤销。
(2)优先适用BIT安全例外条款
在LG&E案中,阿根廷政府同样以《草案》第25条和BIT第11条为依据进行抗辩,但仲裁庭优先适用BIT第11条进行审查,认为阿根廷经济基础濒临崩溃严重程度可以等同于武装入侵,构成对其基本安全利益的威胁,(22)LG&E,Decision on Liability,para.238.因此支持了阿根廷的安全例外抗辩。Continental案仲裁庭在强调优先适用BIT同时还指出,《草案》第25条适用条件应更加严格,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并不以东道国发生全面崩溃或灾难性局势为前提,(23)Continental,Award,para.198.因此,仲裁庭支持阿根廷政府援引BIT第11条进行的抗辩。
(3)明确拒绝习惯国际法
印度电信双案是相互牵连的两案,后案申请人Deutsche Telekom是前案申请人CC/Devas的股东,两案均是因为印度政府以可能威胁印度通信安全为名撤销两颗S波段印度卫星合同措施引发。两案分别依据的1998年毛里求斯—印度BIT和1995年德国—印度BIT中均无自裁判性措辞。CC/Devas案中,仲裁庭明确指出援引1998年毛里求斯—印度BIT第11.3条不受习惯国际法“必要性”限制。(24)CC/Devas,Award,paras.252-255.在Deutsche Telekom案中,仲裁庭更尊重东道国对基本安全利益的自裁判权,未要求存在“迫在眉睫的严重后果”。
(二)对东道国依据习惯国际法寻求抗辩的分析

表2 依据习惯国际法寻求抗辩的ISDS案例统计
表2六案所援引的BIT中均不包含安全例外条款,因此针对东道国政府提出的安全例外抗辩,仲裁庭均依据《草案》第25条进行审查,其中Total案、Bernhard案和Unión案分析较为深入,故以三案为例进行讨论。
1.Total案
本案与前述“阿根廷串案”发生背景和争议措施基本一致,由于1991年法国—阿根廷BIT中不包含安全例外条款,因此阿根廷政府援引《草案》第25条进行抗辩。仲裁庭审查后以阿根廷金融危机尚未严重和紧迫到损害国家存在和独立的程度、阿根廷政府未能证明其对Total采取的天然气出口限制与保证阿根廷国内天然气基本供应有关以及存在其他对投资影响更小的替代性措施(25)申请人主张阿根廷政府可以采用向低收入家庭提供补贴以减轻低收入家庭负担方式解决危机,而此种替代措施对外国投资者的影响更小,但阿根廷政府对此未做回应。See Total,Award,paras.242-245.为由,最终驳回了阿根廷政府的安全例外抗辩。
2.Bernhard案
自2001年始,津巴布韦独立战争的移民和退伍军人侵占Bernhard经营的农场,2005年《津巴布韦宪法》修正案更将这种侵占合法化,且不给予Bernhard任何补偿。由于1995年德国—津巴布韦BIT中不包含安全例外条款,津巴布韦政府以无地津巴布韦人大规模运动已经对其基本安全利益构成了严重和迫在眉睫的危险为由,援引《草案》第25条主张安全例外抗辩。(26)Bernhard,Award,para.223.仲裁庭围绕《草案》第25条的构成要素逐一论述:第一,是否构成基本安全利益?仲裁庭认为基本安全利益需与国家的存续或国家政治、经济上的生存有关,本案中无地津巴布韦人运动虽对现政权产生一定威胁,但尚未达到威胁国家基本安全利益的水平,特别是,政权更迭对长期不稳定的津巴布韦也并不罕见;第二,威胁是否是严重和紧迫的?仲裁庭认可了申请人提交的津巴布韦警方对国内游行情况的报告,该报告显示参与游行人数接近58000人,远低于津巴布韦政府在Berhard案中所声称的“数百万占有者”,且警方在报告中做出了其“有能力处理所谓群众运动”和“国家不会因此陷入危机”的判断,据此,仲裁庭认为津巴布韦政府无法证明存在严重和迫切的风险;第三,是否存在对外资影响更小的替代措施?针对津巴布韦政府声称通过宪法修正案满足占领者要求,是平息骚乱的唯一手段的抗辩,仲裁庭认为津巴布韦政府消极应对危机,并没有真正考虑其他替代方案;第四,争议措施是否存在歧视?仲裁庭认为津巴布韦政府实施的土地政策实际是基于土地所有者的国籍、肤色和政治理念等区分对待,不符合非歧视性要求;第五,安全威胁是否是由东道国引起或加剧?仲裁庭结合前述警局报告等证据,认为津巴布韦政府如在游行之初采取有效措施足以控制局势,然而其放任的行为最终引起之后出现危急情形。(27)Bernhard,Award,paras.259-281.综上,仲裁庭驳回了津巴布韦政府提出的安全例外抗辩。
3.Unión案
为缓解其境内天然气短缺,埃及实施了一系列本国电力优先政策,将本国的天然气供应优先满足国内居民生活需求,同时停止了对申请人旗下米埃塔工厂的天然气供应,导致申请人的巨大损失。由于1992年西班牙—埃及BIT不包含安全例外条款,埃及政府援引《草案》第25条予以抗辩,主张实施本国电力优先政策是捍卫埃及基本安全利益的唯一措施。仲裁庭未就《草案》第25条指出的所有要件逐一分析,而明确指出该条款适用具有累积性,应由被申请人证明每一个相关要素,而不是由申请人反驳其中任何一个要素。(28)Unión,Award,para.8.38.简言之,只要有一个要件不成立即不满足该条款的适用条件,之后,仲裁庭围绕“基本安全利益”“严重和紧迫的危险”及“措施的唯一性”三项要件进行分析,最终驳回了埃及政府的抗辩。
(三)对东道国依据自裁性安全例外条款寻求抗辩的分析
学界主流观点认为,自裁性条款与非自裁性条款的最核心区别在于仲裁庭审查权能不同,针对自裁性条款,仲裁庭只能对案情进行善意审查,而针对非自裁性条款,仲裁庭可以对案情进行实质审查。(29)韩秀丽:《双边投资协定中的自裁决条款研究——由“森普拉能源公司撤销案”引发的思考》,《法商研究》2011年第2期,第20页。尽管目前尚无援引自裁判性安全例外条款的ISDS争端,但近年来新签订的相当比例的国际投资条约纳入了“GATT式”安全例外条款,因此WTO争端解决机构对GATT第21条的解释和适用也可能成为未来ISDS争端解决中解释和适用“GATT式”安全例外条款的参考。截至2023年6月15日,WTO争端解决机构已经就DS512、DS544(组案)、DS567、DS597四案发布专家组报告,针对GATT第21条中最富有争议的b款(iii)项的解释和适用,围绕专家组是否有管辖权、争议措施是否是在“战争或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情况”采取、以及争议措施是否是“其认为……所必需(necessary)任何行动”等方面进行论述,结果可分成:
1.支持东道国安全例外抗辩
DS512案中,针对乌克兰提出俄罗斯对乌克兰商品过境管制措施不符合GATT和俄罗斯《入世议定书》的诉请,俄罗斯直接援引GATT第21条b款(iii)项,主张2014年发生的“危急情形”已经构成了对俄罗斯基本安全利益的威胁,专家组对此案无管辖权。专家组报告明确指出第21条b款中“其认为……所必需”的措辞意味着成员方对(i)-(iii)项情形具有自裁判权,但专家组报告结合文本和缔约背景后指出,这种自裁判权并不延伸到判断(i)-(iii)项情形是否成立。尽管专家组没有对b款序言中的“其认为”是否仅限于判定涉诉措施是保护基本安全利益所必需这一问题做出明确结论,但却隐含着成员方应在善意基础上进行解释,争议措施与保护基本安全利益应符合最低合法性要求。(30)DS512,Panel Report,paras.7.131-133,7.138.
DS567专家组基本遵循了DS512案专家组意见,针对卡塔尔提出的沙特“反同情措施”与怠于追究境内盗版者刑事责任的行为违反了沙特在《TRIPS协定》下的义务,(31)2017年6月,沙特以卡塔尔支持并庇护极端组织,危及本国国民安全为由采取了包括断绝与卡塔尔所有的外交关系、阻止所有卡塔尔公民进入沙特领域等一系列封锁举措。受其影响,卡塔尔的一家广播公司BeIN失去了原本拥有的专有广播转播权。与此同时,沙特公司BeoutQ在未经BeIN授权的情况下开始在包括脸书(Facebook)、照片墙(Instagram)以及推特等社交媒体上播放盗版内容。沙特采取的“反同情措施”(the anti-symphony measure)导致BeIN无法在沙特境内得到律师的代理并无法在沙特法院起诉BeoutQ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BeIN将沙特诉至WTO,主张其“反同情措施”与怠于追究境内盗版者刑事责任的行为违反了《TRIPS协定》第41、42、61条项下义务。See DS567,Panel Report,16 June 2020,para.2.2.通过实体审查和善意审查,专家组最终裁定禁止沙特律师以任何目的与卡塔尔国民或企业打交道的“反同情措施”是沙特在两国关系紧张状态下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措施,因此支持了沙特对此提出的安全例外抗辩,但对怠于追究境内盗版者刑事责任的行为与两国国民之间的交往措施,则未支持沙特提出的安全例外抗辩。(32)DS567,Panel Report,para.7.
2.不支持东道国安全例外抗辩
DS544和DS597案中,专家组表现得更加谨慎。在DS544案中,专家组明确在安全利益前面以“基本”修饰是强调此类安全利益应重要到成员方需要根据第21条b款采取行动。(33)DS544,Panel Report,9 December 2022,para.7.110.专家组还强调,“国际关系紧急情形”是至少与战争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程度具有可比性的某种非常严峻的情形,而美国声称的情形显然没有达到此种严峻程度,因此驳回了美国的抗辩。(34)DS544,Panel Report,paras.8.2-8.3.DS597专家组报告表示香港人权状况的情势没有升级到国际关系危急情形的程度,(35)DS597,Panel Report,2 February 2023,para.7.358.因此也未支持美国的抗辩。DS544和DS597专家组报告主要围绕国际关系危急情形进行分析,未对基本安全利益范畴和DS512案中提及的“最低合理性要求”进行分析。(36)值得注意的是,DS597案中,中国香港在开庭陈述中明确主张应遵循DS512案中“最低合理性要求”,See Hong Kong,China’s Opening Statement at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Panel,para.35.概言之,WTO争端解决机构在对安全例外条款持高度谨慎态度,试图平衡成员方的自裁判权和专家组的审查权,虽然强调所保护的基本安全利益应该是安全利益中最核心部分,但未做进一步说明,而将关注重点置于国际关系危急情形是否成立之上。
四、涉安全例外抗辩的ISDS实践特征归纳和逻辑梳理
(一)涉安全例外ISDS实践的特征归纳
通过对东道国援引安全例外寻求抗辩案件的类型化梳理,可以大致归纳出ISDS实践存在的主要特征:
1.尚无援引自裁判性安全例外条款抗辩的案例
现有ISDS争端多依据2000年前签订的投资条约提起,而此类投资条约中纳入自裁判安全例外条款的情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随着新签订的投资条约广泛接纳自裁性安全例外条款,未来ISDS争端中可能出现东道国援引自裁判性安全例外情形,由于自裁判性措辞赋予东道国更大的规制权自由,这使投资者应对东道国援引安全抗辩面临更大不确定性。
2.现有争端多集中在能源矿产行业等行业
本文探讨的13起涉东道国安全例外抗辩的争端中,9起涉及能源矿产业,占比69.2%,另外4起分布在通信(2起)、金融(1起)、农业(1起),上述产业通常被视为与东道国主权权力或整体稳定密切关联,特别是,随着近年来经济、环境、网络等非传统安全因素与传统安全因素“交织融合”,东道国未来援引安全例外抗辩的情形可能更加多元化。
3.援引习惯国际法抗辩难度更高
相较于援引习惯国际法抗辩的6起争端无一获得仲裁庭支持,而援引BIT安全例外条款的7起争端中,有2起得到了明确支持,1起得到部分支持,加之“阿根廷串案”中CMS案、Enron案和Sempra案中对阿根廷政府不利的裁决被撤销,足以佐证在案涉BIT中含有安全例外条款时,东道国所提起的安全例外抗辩可能更容易得到仲裁庭支持。
4.仲裁庭明确其对基本安全利益及与争议措施的相关性有审查权
尽管在“印度电信双案”中,仲裁庭对东道国对基本安全利益自裁判权、危机是否现实发生的解释中对东道国为保护基本安全利益采取的特别管制措施存在更宽容的倾向,但是仲裁庭从未放弃过其对安全例外条款、习惯国际法中“危急情形”的解释和适用权,特别是在WTO专家组围绕GATT第21条这一自裁判性安全例外条款解释时,并未因为其中的自裁判性措辞而削弱对该条款的审查权。
(二)ISDS仲裁庭裁决的逻辑梳理
1.依据非自裁性安全例外条款寻求抗辩的争端
(1)明确BIT与习惯国际法之间的关系
不同仲裁庭对BIT与习惯国际法的适用关系上主要存在以下三种模式:第一,优先适用习惯国际法,如CMS案、Enron案、Sempra案仲裁庭优先适用习惯国际法中的“危急情形”条款或依据《草案》第25条设定标准进行解释;第二,优先适用BIT,并以习惯国际法为补充,如LG&E案和Continental案中,仲裁庭优先适用1991年美国—阿根廷BIT第11条,再以《草案》第25条进行辅助解释;第三,明确拒绝习惯国际法,如印度电信双案仲裁庭则坚持从BIT安全例外条款的本意和宗旨出发,拒绝将习惯国际法引入对案涉条款的解释。针对第一种模式,CMS案专门委员会批评仲裁庭未能正确区分BIT和习惯国际法在适用和内容上的不同,并将本应作为“首要规则”适用的BIT第11条置于《草案》第25条之后适用,分析的内容和顺序存在错误。(37)CMS,Decision of the ad hoc Committee on the Application for Annulment of the Argentine Republic,25 September 2007,paras.131-134.Enron案和Sempra案仲裁庭以BIT第11条中没有规定具体审查标准转而适用《草案》第25条,之后两案专门委员会虽然未对审查标准进一步说明,但两案裁决被撤销足以佐证专门委员会不支持仲裁庭的立场。相较于直接拒绝习惯国际法的第三种模式,本文更支持第二种方式。BIT是缔约方的特别协议,体现了缔约方的真实意愿,但是缔约方之间为了在有限时间中对核心问题达成一致,所达成的安全例外条款通常具有高度抽象性。这种安全例外条款的“建设性模糊”在具体争议场景解决中,则需要进一步解释。根据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以下简称VCLT)第31.3(c)条所确立的条约解释应遵循“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的原则,仲裁庭依据习惯国际法设定的审查标准进行补充,有助于更好寻求各方平衡。
(2)界定东道国基本安全利益的范围
在界定东道国基本安全利益时,仲裁庭呈现两个新动向:第一,将经济、通信等非传统安全事项也纳入基本安全利益的范畴。LG&E案仲裁庭认为国家经济基础濒临崩溃可以等同于武装入侵,(38)LG&E,Decision on Liability,para.238.印度电信双案仲裁庭更将潜在的通信安全也纳入基本安全利益。第二,将安全威胁从现实主义转向预防主义。印度电信双案中,印度政府为了预防通信安全威胁而排挤对S波段具有绝对控制权的外资,足以显示仲裁庭已经将潜在安全威胁也纳入到基本安全利益范畴之中。(39)梁咏:《安全视域下投资条约根本安全利益条款的中国范式》,《环球法律评论》2023年第2期,第29页。仲裁庭以动态发展眼光看待基本安全利益,主要审查影响安全程度,只要威胁足够严重和紧迫,都可能被视为对基本安全利益的威胁。
(3)对争议措施必要性的审查
仲裁庭在审理东道国行为的必要性时,往往会综合运用实体审查和善意审查的方式,其中实体审查是从条款内容出发结合规定的构成要件进行审查;而善意审查作为实体审查的补充,其关注内容是否公正、诚实与合理,(40)赵建文:《条约法中的善意原则》,《当代法学》2013年第4期,第121页。进而确保对东道国行为性质的判定更加具体准确。譬如,CMS案仲裁庭认为应遵循合理依据和以善意、公平方式行事两项标准审查东道国行为;(41)CMS,Award,paras.245-246.Enron案仲裁庭认为阿根廷未采纳投资者提出的协调方案和建议,主观上确有为了推进其政策放任投资者利益损失,其目的并非单纯保护基本安全利益;(42)Enron,Award,para.331.CC/Devas案仲裁庭也在裁决中提到印度政府撤销合同并非“纯粹出于军事和国防安全需求”。(43)CC/Devas,Award,para.354.因此,
2.依据习惯国际法寻求抗辩的争端
(1)对《草案》第25条“累积性”论证
根据《草案》第25条进行论证中,应将相关标准结合起来考虑。(44)James Crawford,The ILC’s Articles on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ro Internationally Wronful Acts:A Retrospect,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02,96(4),p.874.之前探讨的Bernhard案、Total案和Unión案虽然都结合了多个标准进行论证,但是逻辑上稍有不同。Bernhard案仲裁庭先归纳了第25条规定的六个条件,再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逐一论证并逐一否定,最终否定了津巴布韦政府提出的安全例外抗辩。Total案和Unión案仲裁庭则更进一步,要求东道国对援引安全例外承担主要举证责任,即要求东道国证明每一个相关要素,而不是由申请人反驳任何一个要素。因此,两案仲裁庭选取了与本案相关联的部分要件,指明东道国举证存在的问题并最终驳回其抗辩。特别是,在Unión案中,仲裁庭直接提及第25条确立的各项要素是“累积的”(cumulative),相较而言,Total案和Unión案仲裁庭的“累积性”分析比逐一判定相关要素更加简洁高效,降低了仲裁庭的工作量和审理难度,也遵循了应综合东道国具体情形对其基本安全利益判断的要求。特别是,“累积性”论证可以避免仲裁庭为了补齐所有证据而牵强地寻求依据。譬如,Bernhard案仲裁庭为了证明东道国行为“破坏了他国和国际社会基本利益”这一要件,还特别强调津巴布韦政府采取的措施构成种族歧视待遇,(45)Bernhard,Award,para.268.这点似乎存在为补齐所有要件而牵强附会的嫌疑。津巴布韦政府保护无地国民的行为确已违反了对外国投资者给予非歧视保护的义务,但也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对其略过转而集中于论证其他要件更为务实。
(2)对构成要件进行实体审查
相较于BIT安全例外条款中通常对构成要件不作说明,《草案》第25条中已经纳入了清晰具体的构成要件,因此仲裁庭只需依据构成要件进行实体审查即可。以Unión案为例,针对埃及提到的“维护本国基本安全利益”,“对抗严重紧迫危险”这两个要件抗辩,仲裁庭提及2015年埃及革命已经结束而直至案件审理时,埃及政府尚未恢复天然气供应的事实,足以证明切断天然气供应的根本原因不是埃及发生革命或社会动乱,而是埃及天然气缺乏,然而天然气缺乏尚未达到使基本安全利益严重紧迫危险的高度。(46)Unión,Award,paras.217-226.其次,针对埃及切断天然气供应的措施“唯一性”问题,仲裁庭认为埃及在既未充分评估其他可能的替代性措施,也未对本国天然气优先供应政策合理规划、改善国家电网的计划考量的前提下,采取切断对Unión公司下属工厂天然气供应的极端方式,显然不是解决危机的“唯一方案”。(47)Unión,Award,paras.229-235.同时,仲裁庭也指出不应苛求埃及政府能预料到其决策后续可能产生的结果,并据此否认了申请人提出的“东道国行为引发了危机”的主张。因此,即便“累积性”论证决定了否定东道国对任一构成要件的证明即可驳回东道国对安全例外的援引,但在ISDS实践中,仲裁庭依然会对其他构成要件进行逐项论述,因此投资者举证、质证和辩论时,应特别注意寻找对自身最有利即东道国抗辩最薄弱的点进行突破。
(三)WTO争端解决机构的论证参考
尽管GATT第21条中纳入了自裁判性措辞,但四案专家组报告都确认对成员方援引该条款抗辩时,专家组拥有审查权。四案专家组基本围绕基本安全利益和“战时或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情况”两个问题展开。
1.对基本安全利益的认定
四案专家组尽管均允许成员方依据GATT第21条b款序言中的“其认为”对判断争议措施是否是保护其基本安全利益“所必需”这一问题行使自由裁量权,(48)DS512,Panel Report,para.7.128.但在DS512案中明确无论如何基本安全利益要比安全利益狭窄得多,应理解为与国家基本职能有关的利益。不仅如此,成员方必须在善意基础上进行解释,且争议措施与保护基本安全利益之间必须满足最低合理性要求。这一基调在DS567和DS544案中也得到了遵循。
2.对战时或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情况的认定
四案专家组对战时或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情况进行了具体考量,并明确呈现两极化特征。针对DS512案和DS567案各自所处于的2014年以来的俄乌冲突、沙特和卡塔尔之间外交断绝的背景,专家组支持存在国际关系紧急情形,而针对美国以所谓关于全球钢铁和产量过剩担忧及香港人权危机为由而滥用基本安全利益的主张,则明确其尚未达到国际关系危急情形的程度,通过比较不难看出整体上专家组对国际关系紧急情形认定秉持高度克制和谨慎的态度。
尽管WTO争端解决实践并没有先例作用,但由于实践中对之前争端解决结果的“交叉引用”,使WTO争端解决结果对之后的争端解决具有一定指导价值。同理,未来围绕GATT式安全例外条款的ISDS争端解决中,WTO争端解决实践也可能发生一定指引作用。
五、中国投资者对东道国滥用安全例外抗辩的对策
改革开放45年来,中国已经成长为双向投资大国,并积极推动全球化向更加开放和均衡的方向发展。(49)石静霞:《“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法——基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视角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第158页。截至2021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高达2.78万亿美元,分布在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50)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2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统计出版社2022年版,第20—25页。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布情况看,投向目的地国(地区)相对集中,其中前二十大投资目的地国(地区)(51)截至2021年底,中国OFDI存量前二十大国家(地区)依次为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荷兰、印度尼西亚、英国、卢森堡、瑞典、德国、加拿大、中国澳门、越南、俄罗斯、马来西亚、老挝、泰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除了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新加坡、荷兰等是著名的税收筹划地,相当部分投资将转投第三国(地区)或进行返程投资,其他主要投资目的地国中,美国、英国、瑞典、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近年来频频以国家安全为名对中国企业投资予以限制甚至排除;印度尼西亚、越南、老挝、俄罗斯、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在制度发展和政策演进过程中发生突然性政策转向风险较高。未来如果发生争端,东道国援引安全例外为其涉诉措施寻求正当性的可能很高,因此,中国投资者应对东道国援引安全例外进行抗辩的已有实践和论证逻辑予以充分关切,以便做好提前筹划和系统布局。
(一)明确可能适用的条款及其性质
实证研究显示,仲裁庭对东道国援引安全例外抗辩进行审查时,首先会确定应适用BIT的安全例外条款还是《草案》第25条。因此,中国投资者在启动ISDS机制之前,首先应明确:
1.明确案涉BIT是否存在安全例外条款
在前述Total案中,阿根廷政府试图通过将1991年法国—阿根廷BIT第5条第3款(战争与动乱条款)(52)1991年法国—阿根廷BIT第5条第3款规定:“缔约一方的投资者,其投资因缔约另一方领土或海域内的战争或任何其他武装冲突、革命、国家紧急状态或起义而遭受损失的,缔约另一方给予其投资者的待遇应不低于给予其本国投资者或最惠国投资者的待遇”。扩张解释为安全例外条款,但未得到仲裁庭支持。仲裁庭明确该条款不是例外条款,而是要求东道国在特定情形下保障对投资者优惠待遇的条款,实质上对阿根廷政府施加更多义务。据此,中国投资者应知晓如果东道国政府试图通过“移花接木”借用其他条款作为援引安全例外抗辩的依据,则应坚决予以抵制。
2.明确案涉安全例外条款是否为自裁判性条款
如果案涉BIT中存在安全例外条款,则应确认条款中是否含有“其认为”“其确定”“必要”等标志性措辞;同时还应结合上下文、BIT序言以及BIT的解释效力条款(如有),进而明确东道国正当管理权可能的行使范围。以往ISDS实践中,尚未出现过针对自裁判性安全例外条款的争端,但是结合WTO争端解决实践大致可以预判,仲裁庭仅会对争议措施进行善意审查,因此中国投资者应将重点置于东道国是否善意的问题上,中国投资者可以根据东道国所面临威胁的危急程度以及东道国对其他外国投资者待遇进行充分举证。对于非自裁判性安全例外条款,中国投资者则应依据以《草案》为代表的习惯国际法围绕安全例外抗辩的构成要件,逐一做好举证准备。
(二)重视《草案》第25条审查标准的解释与适用
在以往涉东道国安全例外抗辩的ISDS实践中,仲裁庭援引《草案》第25条的频率很高,除了在BIT安全例外条款缺位时单独予以适用外,也可能解释BIT中的非自裁性安全例外条款的补充。因此,中国投资者应特别重视仲裁庭对《草案》第25条的解释与适用逻辑,具体表现为:
1.围绕东道国遭遇的安全危险性质及紧迫性的充分举证
《草案》第25条第1款明确要求,诉争行为应是“该国保护基本利益,对抗某项严重迫切危险的唯一办法”,要让仲裁庭否定东道国援引安全例外抗辩的正当性,投资者首先应从“基本利益”和“严重迫切危险”入手,努力证明东道国所面临的安全危险尚未达到此种程度。Bernhard案仲裁庭指出,本条款所称的危机应是“足以破坏一国之存在,或是威胁到一国根本政治或经济利益的危机”,(53)Bernhard,Award,para.253.因此,建议中国投资者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积极举证:第一,危机应属于东道国的生存危急、政治危机或经济危急,原则上不应延伸到社会危机、文化危急等;第二,危机原则上应针对整个国家,仅针对当前政权,执政党或少数利益集团的危机不在此列;(54)Bernhard案仲裁庭主张无地者的游行示威仅是对当前政权的危机而非对整个国家的危机,即属此类。第三,危机应达到迫切而严重的程度,尽管以往ISDS实践未对“迫切”和“严重”两个词进行具体解释,本文认为应将其并列解释,其中“迫切”强调时间的紧急性,如不立刻采取措施将引致更加严重的后果;“严重”则强调危机的广度和深度,具体标准则需要中国投资者在个案中结合东道国具体情况做出判断。
2.围绕争议措施对投资者造成的影响和危害的充分举证
以往ISDS实践显示,ISDS仲裁庭会围绕《草案》第25条确立的审查标准对争议措施逐项审查。因此,中国投资者主张东道国违反投资承诺时应尽量逐项列举其不当行为及影响,使诉求依据更加充分,也更有说服力。此外,还应注意到《草案》第25条第2款“该行为并不严重损害作为所负义务对象的一国或数国或整个国际社会的基本利益”的规定,虽然明确了可以排除其适用的条件,但对其中所涉及的“严重损害”“基本利益”等高度抽象的措辞未作进一步说明,实践中也远未达成共识。Bernhard案仲裁庭认定东道国存在种族歧视,涉嫌对“全人类基本利益”损害(55)Bernhard,Award,para.255.的结论虽稍显牵强,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拓宽中国投资者运用该条款的思路,不仅应关注经济损失,也可以从更高价值和站位对争议措施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3.围绕存在对外资负面影响更小的替代性措施的充分举证
中国投资者在面临争端时应将矛头指向东道国规制行为本身,除了指出争议措施引发的广泛的消极影响外,更要关注是否存在对外资影响更小的替代方案。建议中国投资者至少可以从三个维度入手:第一,建议中国投资者全面收集东道国面临危机期间的各类报道、会议信息、执法记录和计划方案等,关注其中存在全面评估以及是否考虑过其他替代性方案。(56)Bernhard案中,投资者提供的津巴布韦警局的游行执法报告及给出的方案,就是这一类证据的典型。Bernhard,Award,para.257.第二,建议中国投资者在危机爆发前或爆发初期积极协助东道国探寻解决危机方案,提供自己的意见并做好相关记录。不论东道国最终是否采纳,但此类意见都可能作为仲裁庭审查的可能的替代方案。第三,及时关注第三方(包括其他投资者、非政府组织及第三国)提出缓解危机的建议方案,记录可能存在的替代方案并在争端解决中进行举证。譬如,Bernhard案仲裁庭就注意到2000年英国曾提出向津巴布韦政府援助3600万英镑但要求津巴布韦政府“首先结束对农场的占领和暴力”的方案,但津巴布韦政府以“坚持无条件提供财政援助”为由拒绝了这一方案,(57)Bernhard,Award,para.259.这对仲裁庭最终驳回津巴布韦政府安全例外抗辩也有影响。
(三)针对不同东道国做好差异化安排
由于中国对外投资流向国(地区)安全风险存在差异,因此建议中国投资者进行差异化安排。针对以安全例外为名行限制中国投资之实的瑞典、加拿大等国,如果其与中国签订了BIT,建议应重点关注援引BIT对东道国滥用安全例外进行反制。针对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可能发生突然政策转向而对中国对外投资产生的不利,除了注意援引BIT外,中国投资者应尽力在投资合同中纳入稳定条款,对东道国可能采取的突然性政策转向予以预先防范。
(四)其他配套措施
1.争端爆发前——投资背景审查与风险评估预警
对于中国投资者而言,事先防范并及时止损应该是避免此类争端最有效的方式。在做出投资决定之前,中国投资者应对东道国特别是整体欠稳定的发展中东道国进行充分的背景调查。特别是,面对不同的投资环境和风险状况,中国投资者应选择合适的投资形式。如采用与东道国合作方合作方式,在东道国可能以保护国家安全为名采取特殊管制措施时,东道国合作方为保护其自身利益,通常会积极进行斡旋和游说,最终可能使东道国取消或缓解特殊管制措施。
2.争端爆发时——多渠道沟通协商与矛盾化解
当东道国以国家安全为由行使特别管制权,损害中国投资者利益时,中国投资者在启动仲裁或诉讼等刚性解决方式前,应先通过在东道国国内进行协商、沟通与游说,争取以最小的代价对投资方式和投资项目等进行适当调整,减少可能带来的损失。倘若东道国确实面临了严重且紧迫的危机,则应考虑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同时为东道国提供合适的应对建议,寻求对投资影响最小的替代措施。
3.争端爆发后——多元解决路径与兜底方案
当双方的争端已经难以调和,只能寻求仲裁或诉讼等强约束力途径予以解决时,应对不同的争端解决方式有明确的安排。首先,可以通过东道国行政复议或诉讼的方式在当地寻求救济,例如华为在将瑞典政府诉至ICSID之前,曾在当地寻求行政复议和诉讼,尽管以失败告终,但其不仅可以为后续仲裁做好准备和积累经验,客观上也对东道国可能援引安全例外进行抗辩予以必要尊重。其次,以ISDS机制特别是以ICSID受理争端作为首选。以往涉东道国安全例外抗辩的13个ISDS争端中,仲裁庭均明确对此类案件拥有管辖权,这对东道国可能滥用或误用安全例外予以一定反制。最后,建议理性看待调解机制的效用。尽管便利、高效、寻求当事人共识的投资争端调解机制有助于矫正ISDS机制的弊端,但涉及安全例外抗辩的争端多涉及能源、金融等与东道国国计民生高度相关的行业,出于政治正确性等因素的考虑,在调解中东道国放弃援引安全例外抗辩的可能性不大。
4.中国政府积极推进投资条约改革
中国现行有效的投资条约大多签署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对投资条约的“防御性作用”关注有余,对投资条约的“进取性作用”关注不足,同时对在投资条约中保留东道国必要的自由裁量权关注也不充分。因此,在未来投资条约发展进程中,中国应继续坚持严格援引安全例外的纪律,相对厘清安全例外条款的核心概念和标准,并综合运用各种国内与国际法律工具,协同约束对安全例外条款可能的滥用或误用。
六、结语
随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投资法成为国家间围绕国家安全、国家主权博弈的新场域,少数东道国频繁、过度援引安全例外为其背离投资条约和投资合同的行为寻求义务豁免,已经影响到中国投资者正当投资权益,对此中国投资者应予以事先考虑。
本文从中国投资者视角出发,建议中国投资者明确可能适用的安全例外的条款及其性质、重视《草案》第25条审查标准、针对不同的东道国做好差异化安排,并建构起覆盖争端发生前、发生时和发生后全过程的配套措施。唯有此,方能保障中国投资者对外投资可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