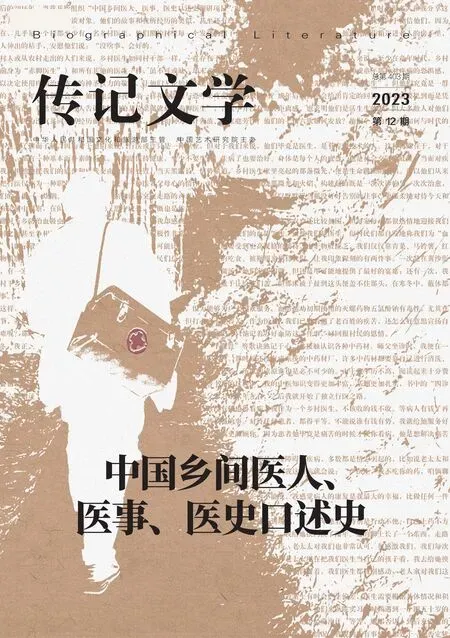青稞:农耕文明的高原式书写
白 玮
在人类不断寻找、开发适合人类食用的农作物物种的同时,其实,农作物也在寻找着属于它们的一方土地。
如小米在西北的高坡上繁育,水稻在南方的水田里蔓延,小麦在中原的黄土地里生根,在广袤高原之巅雪水滋养的土地上,一种神奇的物种也在悄悄御寒而生。它,就是青稞。
如果说,中国西北部的半坡高地是小米文明的起源,南方的水田是水稻文明的故乡,中原黄河冲积平原是属于小麦文明的领地。那么,青藏高原则是孕育青稞文明的土壤。它们相互连通,共同作用,经过长期的交流与融合,从而构筑起华夏农耕文明的食物版图。
与青藏高原的相遇
就像中国早期的先民在北方的半坡高地,通过狗尾草驯化出了黍和稷,美洲的印第安人在荒野里找到了玉米,拉丁美洲的人们在半山坡上发现了土豆,两河流域的居民在新月沃地遇见了小麦一样,神奇的高原地带,经过数万年的寻觅,也最终找到了属于高原的独特作物,这便是青稞。
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的第三极,因为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海拔高度以及常年的高寒和缺氧,在人们的印象中,是蛮荒的生命禁区,是被积雪冰封的沉睡着的大地。因此,能在这一恶劣环境下顽强生长的植物物种,多会被视为具有某种神性。比如神奇的冬虫夏草、毛茸茸的水母雪莲、穿越生死线的红景天和长得像宝塔一样的塔黄,它们都如高原的精灵一样,在幽静、苦寒的高原上闪烁着生命的光华。其中,青稞最具特色,是青藏高原环境条件下植物适应性进化的典型代表,也是生长面积最广泛的作物。

青稞穗
青稞是大麦的一种,属于禾本科,根据人们对它的普遍认识,依照现代植物基因序列的比对,发现它的原主祖先是粗山羊草。在没有被驯化为农作物的青稞之前,在高原之上,它已经生长了大约1700 万年。
在藏语的语系里,青藏高原的人们都亲切地把青稞唤作“乃”,在现代汉语的表述里,除了学名的青稞之外,它还被称作“裸大麦”和元麦。之所以把它称为“元麦”,取自一元更始之意,足见其物种的古老,既是一种敬意,也是一种感恩。这种表述,就类似对元始天尊的敬仰一样,它是高原之上的元物种。
青稞属一年生草本作物,三秆直立,相对于中原地区相对低矮的小麦植株来说,它相对高大,茎秆高时可达100 厘米以上。虽然都被称为青稞,但它的种类也比较繁多,而且颜色各异,可分为白青稞、花青稞、黑青稞、紫青稞等类别。如按青稞的穗形来分,又可分为二棱裸大麦、四棱裸大麦和六棱裸大麦。在西藏大部分地区,主要栽培的是六棱裸大麦,青海地区则主要以四棱裸大麦为主,因地理环境属性的不同,显然,不同棱形的裸大麦的属性也略有不同。
也许是物竞天择的自然结果,也许原本就是造物主的顶层设计,总之,青稞与青藏高原的相遇本身就是一个“你选择了我,我也选择了你”的物种奇遇。高原常年寒冷、寂寞,温暖的时间十分短暂,生存条件极其艰苦。而恰恰青稞喜冷,耐寒性极强,它能在零下10℃的环境里顽强生长。更重要的是,青稞的适应性也强,生长期短,在高原短暂而有限的温暖时间里,它不仅能快速早熟,还能获得稳定的产量。
凡是在严酷环境下生长的物种,在它们的生命体内一定有某种神奇的生命基因,青稞显然也不例外。现代科学研究表明,青稞是世界上麦类作物中含B-葡聚糖最高的作物。它的可溶性纤维和总纤维含量均高于其他谷类作物,这也为它被加工成高原人民不可或缺的糌粑奠定了底层基础。
其实,早在唐代的《本草拾遗》中,古人就对青稞神奇的药用价值进行了考察,发现其有“下气宽中、壮精益力、除湿发汗”等功效。据藏医典籍《晶珠本草》记载:“早熟青稞(为一种播种后60 日就成熟的青稞)性凉,轻、糙,功效开胃口。白青稞味甘,性糙、凉、重,食后胃中略嘈杂。功效开通下气……治感冒、祛痰,顺气。蓝青稞治小儿肺热闭塞症、肠绞痛。炒蓝青稞治肺病。黑青稞治疮、黄水疮伤、辟邪。其他青稞性重、凉、润,味甘,生肌增力。”[1]高原人民在把青稞作为食物的同时,也把它作为一种重要的药材,用于治疗多种疾病。
因为有了高原的衬托,青稞才显得更为神秘和坚韧;高原也因为有了青稞,才充满勃勃生机;而对于在高原上生活的人们来说,正因为有了这饱满、仁慈的青稞,才更加拥有了一种赖以存活的温情食粮。
农耕文明的精神图腾
因为有了青稞,苦寒的高原才更具生命的活力,同时,也才使得高寒之地得以开启农耕文明的传奇。
关于青稞与高原人民的相遇,在藏区的民间有多种版本的传说。它们分别以不同的形式在民间流传,有的是神话故事出现,有的是民间传说,还有的被编成歌谣,广为传唱。内容大都是描绘青稞的第一粒种子是如何降落在高原之上。至于青稞是被哪位神灵具体带往高原的,不同的版本说法也各有不同。有的说是鸟儿或其他动物叼来的,也有的说是神灵赐予的,还有说法是文成公主从大唐带来的。
在多种版本的传说中,有一则名为《青稞种子的来历》的神话故事流传最为广泛。说是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名叫阿初的王子,从蛇王那里盗来青稞种子。后来被蛇王发现,罚他变成了一只狗。由于大土司的女儿感佩于他的勇毅果敢,不顾父母的反对,坚定地爱上了他,并帮助他最终恢复了人身[2]。藏区百姓至今感恩于阿初王子的仁德,给他们带来这难得的青稞种子。
深受佛教影响的藏区百姓也将青稞的来历谱上一层佛教文化的光影。犹如全球各地的百姓都将人间的第一粒粮食赋予一种神性的力量一样,高原之上很多地方的人们也认为青稞是观音菩萨赐予他们的圣物。据《西藏王统记》记载:“尔时圣者起立,从须弥山缝间,取出青稞、小麦、豆、荞、大麦,播于地上。其地即充满不种自生之香谷。”[3]观音菩萨从须弥山的山缝间,取出青稞、小麦、豆、荞、大麦的种子,播于大地之上,从而使得人们开启了丰衣足食的农耕生活。
当然,由于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的千古传奇,也有很多人认为,高原之上的青稞种子是由文成公主当年远嫁吐蕃时从大唐带来的。
关于第一例青稞种子进藏的传奇,无论是阿初王子盗来的神话传说,还是观音菩萨赐予的佛教说法,抑或是文成公主带来的民间颂歌,虽然都只是故事流传,但它们却都深刻地反映出藏区人民善良、朴素的感恩意识,感谢上苍神灵和人间圣者给他们带去赖以存活的粮食。这正如中原的百姓感恩于神农炎帝和周人的祖先后稷给我们带来小米一样,在后世的祭祀中,崇敬地把他们奉上神圣的祭坛,并成为一个族群共同的精神信仰。
人类从狩猎采集第一次转向农耕种植总是充满偶然和艰辛,因此,这场农耕的启幕被誉为人类一次伟大的文明革命。在平原的沃土之上开启农耕尤为不易,显而易见,在高原之巅开启农耕革命更为艰难。除了藏区民间流传的美丽善良的种子传说,那么,高原地带的藏区百姓究竟是怎样开启青稞的种植和农耕文明的革命的呢?显然,我们最终要回到考古的实证中来,通过古代高原人民留下的遗迹,重温久远的历史现场。
大约是在1991 年,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的工作人员在位于山南市贡嘎县昌果乡雅鲁藏布江中游的一个宽谷处,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古文明遗址,这个位于高原之上的古文明遗址就是著名的昌果沟新石器文化遗址。
1994 年夏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组成联合考察队,对该处古文明遗址进行了全面挖掘,出土了大量青稞和粟米的碳化粒种子。后来经过碳-14测定,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大致年代距今有3300 年到3500 年。
考古表明,山南地区的昌果沟遗址是西藏第一个粟麦混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这一重大的考古发现至少反映两大事实:第一,它说明至少在3500 年前,高原之上的人民就已经开启了农耕时代,并开始广泛种植青稞。自此之后,青稞便成为高原地区最主要的食粮;第二,从粟米碳化粒的事实推定,说明在3500 年前,高原地区的先民们就已经和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实现了一定的交流和文明对话。
根据今天的基因测序显示,恰恰证明了这一点:“2018 年,中国学者从西藏和邻近的青海、云南等区域选择了能代表现在西藏大麦遗传多样性的69 个青稞地方品种、35个青稞育成品种以及10 个西藏半野生大麦进行全基因组重测序,结合已经发表的260 份全球野生和地方品种的外显子测序数据,共437 个大麦材料一起分析,发现青稞起源于东方栽培大麦。它们大约在4500年前到3500 年前,通过巴基斯坦北部、印度和尼泊尔进入西藏南部。”[4]
从此,青稞与高原的故事书写就此全面展开,青稞也伴随着高原人民走过了一年又一年的寒冷、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一直流传到今天。如今,青稞早已深深地被镌刻在高原人民的生活和血液中,逐渐升华为高原人民的精神信仰和食物图腾。
食物文明的融合
人的流动带动着食物的传播,也带动着食物文明间的交流与融合。
自远古以来,雪域高原与中原王朝之间就从来没有停止过食物和文明的交流。尽管中原通向高原的路关山重重、艰险崎岖,但食物文明间的交流却依然能够跨越万里沟壑,实现着伟大的融合,这不能不说是个人间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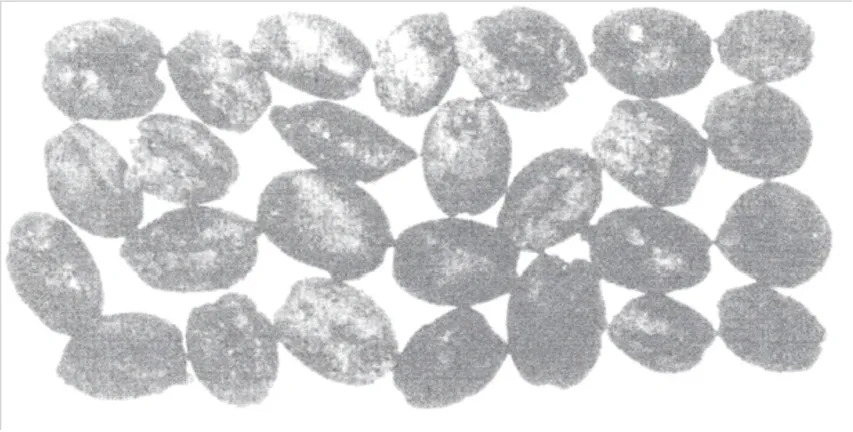
昌果沟遗址出土的古青稞碳化粒
正如前文所述,根据昌果沟遗址的考古报告显示,早在35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青稞与粟米的对话;如果再从位于昌都的卡若文化遗址中发掘出来的食物遗存来看,这种食物间的文化交流一直都没有间断。
进入封建王朝时代,通过细碎的历史旧影,人们得以发现,这种食物间的流动变得日益频繁——从古老的茶马古道开始,中原的茶叶和芒康盐井的盐,就沿着一代又一代马帮驼队踩出的痕迹,源源不断地在高原与平原之间进行着繁忙的流动。恰恰也正是因为茶叶与牦牛的结合,才缔造出了青藏高原酥油茶的神奇与独特。

本文作者在西藏考察青稞
而作为高原的代表性食物,青稞的身影最早进入中原王朝的历史叙事视野的,是《隋书·附国传》对它的记载:“其土高,气候凉,多风少雨,土宜小麦、青稞。”这里所说的附国,是指隋唐时期分布于今天四川西部甘孜地区和西藏昌都地区的政权。“附国者,蜀郡西北二千余里,即汉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其东部,所居种姓自相率领,土俗与附国同,言语少殊,不相统一。其人并无姓氏。”[5]
在隋朝时期,喜欢大场面的隋炀帝曾越过祁连山脉的扁都口,在张掖举行过声势浩大的万国峰会,当时的盛况不亚于今天的万国博览会。来此参展交易的客商包括当时的藏区商贸团队,交易的货物就包括青稞。
《隋书》之后,青稞之名不断出现于中原的各类史书和笔记中。《旧唐书》也曾对青稞记载说:“其地气候大寒,不出秔稻,有青稞麦、小麦、荞麦。”[6]
进入吐蕃时期后,随着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的联姻,青藏高原与中原内地的货物交易就更加频繁。文成公主除了带来大唐先进的中原文化和农业技术外,还带来了大量中原的食物物种及烹饪技术,尤为重要的是,她把大唐的黄酒酿造技术带往了青藏高原。当中原的酿酒技术与青稞结合,从而酿造出了独具高原气息的青稞酒。
松赞干布因迎娶了唐朝的公主,从而便开始慕羡大唐华风。为此,他时常派吐蕃贵族子弟到长安学习诗书,并聘请唐朝文士为他掌管表疏,还向唐请求给予蚕种及碾硙、纸墨的工匠。而随着碾磨技术的传入,又直接催生了糌粑的问世。自从糌粑这一食物在藏地广泛流传开来,藏区百姓的饮食生活也实现了大规模的“唐化”。
唐代诗人陈陶在《陇西行》一诗中就特意描绘了当时的情景:“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
无疑,文成公主的入藏,大范围带动了汉藏两地饮食的发展与融合,尤其是青稞酒与糌粑的诞生,更是两地民间饮食文化融合的结晶和见证。
高原人民的青稞食俗
“一杯茶水,香满庭户;有糌粑相伴,胜过多少春露。”提到糌粑,以诗歌闻名于世的仓央嘉措,曾在他的这首《菲菲春露》一诗中有过相当惆怅的描述。
糌粑,无疑是藏地百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食物,是他们在高原之地赖以生存的能量棒。
所谓糌粑,就是青稞面。虽然都是谷物颗粒的粉状物,但青稞面与中原地区的小麦面粉却大有不同。中原的面粉是由生小麦碾磨加工而成,而藏地的青稞面则是将青稞米晒干炒熟,再碾磨成粉。
青藏高原传统炒制青稞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把沙子在炒锅内爆热,然后再用沙子的热温把青稞炒熟。此种方式用于炒制量较大的青稞,一般使用的都是陶锅;另一种则是直接把青稞在炒锅内加热炒熟,此种方式适用于炒制小量或者临时性的炒制青稞。这种炒制方式,一般使用的都是铁锅。将炒熟后的青稞碾碎成糌粑后,就可以食用了。
糌粑的吃法有很多,藏地百姓日常最常见、也是最传统的吃法就是手抓糌粑。食用的时候,用左手托起一个小碗,先倒上半碗热乎乎的酥油茶,然后就像我们日常冲泡豆浆、藕粉、咖啡伴侣或奶粉一样,往碗里加入适量的糌粑。然后,左手五指撑起小碗,慢慢旋转。这个时候,再抬起右手,食指跟中指合并一处,将漂浮在酥油茶之上的糌粑逐渐没入茶中,让茶与糌粑充分融合。这些过程完毕后,再用右手顺着碗壁在碗中搅拌、抓捏,如和面一般,把糌粑捏成干湿适度、软硬适中的小面团,一碗带着酥油茶和青稞芬芳的二合一糌粑食物就做成了。

糌粑
对于高原上的人们来说,糌粑由于携带方便,制作简单,它既是干粮,也还是行囊;既是食物,也是信仰;既是寄托,也是希望。它是写在生命基因里的食物,更是辽阔高原上的歌唱。因此,对青稞的崇拜与祭祀就像时间的刻度一样,刻写在他们的记忆里。
在西藏农户人家的年度日历中,除了藏历的新年,还有两个盛大的节日是必须过的:一个是青稞的种植节,就是通常所说的启耕节;一个是青稞的收获节,就是通常所说的望果节。
每年的藏历正月,藏地的百姓就要举行盛大的启耕节。这一天,他们都会身着民族盛装,背着青稞酒,手捧五谷斗,扶老携幼,齐聚地头,圈成一圈播下青稞种子,并向空中抛洒糌粑,企望上苍带给他们丰收。
到了9 月,待青稞成熟,就是一年一度的丰收节,也就是望果节的到来。这一天,当地人们都会穿上节日服装,打着各色彩旗,手擎着青稞穗,像转山一样,围着青稞田,载歌载舞。行进过程中,还不断地吹号、打鼓、唱诵诗句,祈求青稞的灵魂,像天仙下凡一样,从高远辽阔的天空中降落人间。
此时那一棵棵青稞,已经不再是一个田间的庄稼、一种普通的食物,更包含了高原人民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和感恩,从而化作他们的精神寄托与文化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