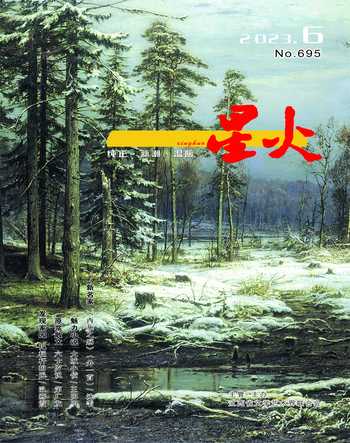嗦螺
漆宇勤,1981年生,江西萍乡人。中国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4届高研班结业,参加第35届青春诗会。在《人民文学》《人民日报》《诗刊》《星星》《青年文学》《北京文学》《散文》等报刊发表诗歌散文3300余首(篇)。出版作品集《在人间打盹》《靠山而居》《翠微》《放鹅少年》《抵达》等21部。
嗦螺是一个名词,嗦螺也是一个动词。
作为名词的嗦螺指带壳烹炒的螺蛳,作为动词的嗦螺指吸食螺蛳的动作。
螺蛳是个古老到了极致的物种。我们看遥远时代的化石,螺贝是品类繁多又最常见的类别。与它同时代的那些物種,后来有的进化出奇怪凶猛的外表,有的演变出更加娇弱的体质。狭窄的食物谱系和适应空间,让它们其中的很多现在都成了要靠特殊保护才能维持基本种群数量的珍稀动物。
而螺蛳要随性得多,几乎适应各类水生态环境。不拘江河湖海,不拘滩涂湿地,不拘池塘稻田,不拘山沟水渠,螺蛳随遇而安,落地就繁衍。有一年春天,我从村子里的灌溉渠里捡了几个螺蛳扔进家里的鱼缸。几个月过去,整个鱼缸爬满了细密的小螺蛳。
它们不挑食。湿地里的植物水藻、细碎的有机物、水中可以滤出的各种浮游生物都是螺蛳的食物。
它们也耐旱。母亲一直跟我说,螺蛳不怕干三年,就怕扔过三丘田。我对这句俗语的理解是,螺蛳耐旱,但是不耐震撞磕碰。以前乡下有的池塘没有水源,全靠春天里下雨蓄起满塘的水,然后逐渐被灌溉消耗或蒸发渗漏掉。中秋过后,池塘渐渐就干枯见底了。到第二年春天涨春水前,我们去池塘里板结的泥地上玩,看见一个个圆形的深凹坑,往下掏摸,总能在十几二十厘米深处掏出螺蛳。在池塘干枯四五个月后,它们依旧活着。
即便到了现代,除了自己种的植物与养的动物之外,采集、渔猎依旧是人类满足生活所需的一种补充,更不用说古代了。采集野果野菜野蜂蜜,猎取山里的飞禽走兽爬虫,捕捞水里的各类水生物。这其中,捡拾螺蛳可能是相对容易的事情。螺蛳没有尖牙利爪,捡拾时也不需进入深水区和深山区,不需掐准草木时令,甚至不需要长途跋涉、目的明确地去寻找。它一年四季就在村头村尾,稻田间,水渠中,池塘里。因此,螺蛳仿佛具有了某种身边物与家常物的性质。
很小的时候就听过那个让人神往的故事。故事说,勤劳老实的农民捡回家的大田螺每日化身为少女给他做饭。后来我长大一些,通过不同的书本,发现在这个故事梗概下,衍生出了细节稍异的各种版本。故事的发生地,几乎遍布了中国南方和中部多数有水有湖有田的地方。
中国的民间传说故事都有典型的现实根基。田螺姑娘寄寓了众多乡村独身青年的憧憬,也寄寓着众多农民的幻想。他们选择了日常多见的田螺作为载体,让梦想的可能性与可亲性比那些虚无缥缈的神仙幻想强了许多—毕竟,将同样可能成精的狐狸和田螺进行比较,田螺还是更接近身旁。
想一想吧,在日常劳作、日常途经的田间地头,俯身就可捡拾到数量繁多的田螺。如果稍微多花费一点时间,就可以为晚餐添加一碗佐餐的佳肴。这可是比鱼类更容易获取、比蔬植更富营养的肉食荤腥。它们背着厚厚的外壳,却又没有用来跑路的脚。因此即便是被惊扰了,田螺也只是迅速收回外探的触角和大半个身子,整体缩回自己的壳里,然后一动不动。所以赣西俗语说,“三个指头抓田螺,十拿九稳”。
我相信,定曾有过那么一些村子与村民,依靠螺蛳缓解食物匮乏的困窘。
在我生活的龙背岭,人们也时常在夏秋两季到沟渠水田和池塘里捞田螺。我们叫捡螺蛳。是的,在这里,我们将田螺与螺蛳简单地进行了模糊处理。实际上,龙背岭常见的螺蛳有几种。其中一种外壳狭长,我们称其为石螺;另外一种外壳短圆,我们称其为田螺。但是这种具体化的专业称呼只在很少的时候使用。更多的时候,我们将村子里能够看见的一切螺蛳都统称为田螺—我们也不知道中华圆田螺、环棱螺这一类的名称。
春天里,田螺完成了它一年中的第一次繁衍。夏天开始,我们便下到水里捡田螺了。河流浅水洄旋处的田螺经常是成群成堆地出现,捡田螺的人躬下身便捧起一大把,可惜一般都是中小个头的;池塘里的田螺总是缩在淤泥里,捡田螺的人得靠双脚或双手一路摸索过去,泥巴里捏出一个硬物,基本就是田螺或河蚌了;稻田里的田螺显露于田埂边、稻苗下,人们总是在干耘田除草放水等农活时顺手将它们给捡回家;而沟渠里的田螺一目了然,站在水圳边上便可以看到,这里一枚,那里一枚,捡田螺的人基本都是挑个头硕大的往脸盆或者荷叶芋头叶里放,往往有二三十枚就可以炒上一小菜碗。
捡田螺的最佳时间是早晚时分。这时气温不高,田螺们都从泥洞里钻出来了,一目了然。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早晚是一天劳作之余的零星时间,捡田螺不耽搁干活。
田螺们都保持磊落的古风。它们在淤泥里安家,必然会在泥面上留下特点鲜明的凹洞,掏下去一抓一个准。即便是外出觅食或者迁徙,也会留下一路滑行的明显痕迹。可能再没有其他动物像田螺一样在大地上留下如此真实连贯的足迹了。
有时候,浅水清澈透底的田间和水圳里,一只螺蛳、两只螺蛳在平整的泥底划出曲线,像一个外出旅行的人留下深深的轨迹或车辙。这抽象的线条与倒映在水中的草木之影相得益彰,很适宜一个无聊又无事的少年在田埂上观望和想象,消耗时光。二十多年前,我初学摄影,最喜欢拍摄家门口泥池里田螺的移动轨迹,那些透过水面显露的光影线条,仿佛在底片上形成了某种神秘的符篆。
捡回家的田螺都会暂养在水盆水桶里三五天,待到它们吐净泥沙了,再进入烹饪的程序。要将田螺肉从曲廊回旋的螺蛳壳里取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龙背岭的主妇们习惯将吐净泥沙的田螺放进开水里迅速焯一下,然后拿尖竹签、钢针之类的工具将螺肉挑出。挑螺蛳肉也是个技术活,要迅速地去掉粘连在螺肉上圆盖一般封堵螺蛳壳口的厣,将螺肉挑出并去掉不适宜食用的部分,既考验细心,也考验耐心—或者,还要考验狠心。田螺是卵胎生动物,雌螺体内往往揣着数以百计的幼体。很多田螺在螺肉被挑出的过程中,都能从螺壳底部带出一大簇的小田螺,其中很多已经完全成形,是缩微版田螺的样子。
我记得有一回捡的田螺有点多又有点小,我蹲在家门口的柚子树下挑田螺肉,大半个小时过去了,依旧没能完工。暮色深处,田螺的腥味吸引了成群的蚊子嗡嗡飞舞,叮得我浑身疼痒,偏偏两手都是黏糊糊的脏污,既打不得蚊子,又挠不得痒。
但田螺肉炒红辣椒,是无比鲜美可口的菜肴,既下饭,又滋补。
也有不用于制作佐餐的菜肴而是侧重休闲口味的时候。这时的田螺就不用去壳挑肉了,直接剪去田螺壳的尖尾,连壳带肉加入大量的调料放锅里烹炒。这样炒制出来香辣无比的田螺被我们称为嗦螺。撮一粒在嘴里吮吸,浓郁的调料味与田螺的本味杂糅,让人越吃越想吃,欲罢而不能。
辣椒炒田螺肉是母亲的拿手菜。嗦螺却不是她所擅長的菜式。炒嗦螺的高手集中在本县另外一个镇子里。
这是一个名叫桐木的镇子,江西与湖南两省在这个镇子里有着犬牙交错般的边界。当地一个老人很认真地告诉我:镇子里有人家的房子厅堂在上栗,卧室在宜春,厨房在浏阳。我将老人的话当成夸张与玩笑,不太相信边界插花地带会有宅基地选得这么巧合。但这个10万人口的乡镇地处赣湘两省三市的边界,倒真实不虚。
桐木镇炒嗦螺的高手也不是遍布全镇,而是主要集中在一个村子里。
这是一个名叫楚山的村子。楚是楚国的楚,山是山岭的山。村子里有楚王台,有供奉楚昭王的祠庙,也有信奉屈原的民间信仰。楚山之上,石壁上依旧有种种牵强附会但又隐有联系的传说,还有韩愈诗《楚王台》“真迹”。楚王台全国各地有不少,韩愈写了《楚王台》也确凿,他曾到过赣西上栗也是史实。但石壁上的简化字毛笔笔迹透出村民们某种可爱的天真。
既然已经说了与楚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那么楚国那沟渠密布、湿地沼泽随处点缀的地理特性,自然也适用于桐木,适用于楚山。
可以想见,在农耕时代,桐木或者楚山的沟渠稻田、河流水塘、湿地沼泽,到处都是螺蛳活跃的空间。
那时的田螺,因为食物丰富又少有打扰,生得年深日久者(实际田螺只在前几年生长体型),想来偶尔会有突破常规,长得拳头大小一个的吧。个头大了,年岁久了,自然田螺姑娘的故事也就有了基础,更多与田螺有关的神话传奇也就有了基础。幼年时,读过一本缺页的《仙佛全传演义》,隐约记得里面有田螺成道,后来因缘际会诸多仙佛人物在螺壳里汇聚做法事的情节。我一直将此视为俗语“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源头。但近来查看网络资料,却大都说这一俗语的来源是另外的民间传说。
不管来源如何,螺蛳壳里做道场,形象又贴切。尤其是对于经常捡田螺、吃田螺、熟悉螺蛳壳的人来说,这样一句俗语的丰富且复杂的况味,细细一咂摸,就会不禁沉默。
楚山村的楚是楚昭王的楚,楚王台的王是昭王的王。《孔子家语》说楚昭王在萍乡渡江捡到一个漂浮的红色果实却不知名,最后孔子辨识出来说是“萍实”。后来黄庭坚也专门写诗说起这个典故,说萍乡就是因为萍实之乡而得名。楚山村属于桐木镇,桐木镇属于上栗县,上栗县属于萍乡市。楚山人相信,当年楚昭王捡到萍实的地方,就是在上栗的大河里,楚昭王曾在桐木留下大量的活动痕迹。
我跟村里的老人开玩笑,那当时楚山人有没有给楚昭王炒上几碗嗦螺呢?
大家都笑。我们都没有专业的历史知识,不清楚楚昭王时代的食物烹煮水平和调料普及程度是个什么情况。那时的人们,学会了将田螺作为食物来源吗?又学会了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烹制螺蛳呢?
如果从楚山人现在烹炒嗦螺的几种主要调料在历史上被普遍使用的时间来看,至少当时楚昭王是没有口福尝到今天这种口味的嗦螺。
今天这种口味的嗦螺汇集了赣西地区最常见的辣、鲜、咸、香等诸多口味,甚至也汇集了大众美食所需要的各种视觉和嗅觉效果。村子里的人实诚,老老实实将自己村子里常用配方和烹炒方法制作出来的嗦螺冠以村名,称为楚山田螺。没有哪一家哪一户将此作为私有的品牌,也没有哪一家哪一户对烹炒工艺讳莫如深。
这种开放的态度,催生了大批的夜宵店铺以楚山田螺为招牌,也催生了近十家的食品工厂专门生产楚山田螺。
每到夏天的夜晚,赣西地区的夜宵摊点上,总是少不了一份嗦螺。夜宵摊点是个神奇的地方,夜宵相聚的人应该都是亲密的人。
我不常见陌生的人相约一起吃夜宵、吃嗦螺,他们只宜到酒店包厢里正襟危坐进行交流。而一起吃嗦螺,总是有几分亲近和随意,不讲究排场而侧重个体的放松体验。
嗦螺的吃法似乎有几分粗犷,几个大老爷们配上几瓶啤酒,边嗦边大声说话,那嗦螺的香味,很快就弥漫整个就餐空间。
但是,不要忘了,嗦螺的菜碗前,女性似乎也不少。想象一下,餐桌前的纤纤玉手,伸出两根手指,撮起一粒螺,放嘴边轻嘬。转眼间身前就堆满了螺蛳壳,转眼间两手就满是汤汁。对于讲究的人来说,这样的场景只宜在亲密者面前呈现。
实际上一起嗦螺的人都没有这种顾忌。既然是嗦螺,要的就是这种酣畅淋漓,要的就是这种味蕾爆炸。所以,我一直认为,能够一起吃嗦螺的人,定然都是随和随性的人。
就像嗦螺本身,用各种调料随性地翻炒烹煮。也像田螺本身,在各种场所随性活,随性吃,随性长。超强的适应性,让田螺成了自然生态水体里治污的好物种。超强的繁殖力,让田螺在一些养殖场成了螃蟹、青鱼的好食物。
同样随性的夜宵摊,渐渐也衍生出了夜市经济的概念,衍生出了吃嗦螺和炒嗦螺的人的烟火人间,衍生出了一个嗦螺生产产业。
在吃过嗦螺很多年,也早已不到水里捡田螺很多年后,我偶然来到了楚山村。那一次之后,我到楚山村,不为访古,也不为考据,只为了嗦螺而来。在这个村子里的田螺繁育基地,各种各样的螺蛳扎着堆。但田螺食品厂的采购经理告诉我,这样的画面根本算不了什么。在一些大湖大河里,在螺蛳的主产区,工人们都是用挖掘机采挖螺蛳的,经常是数十吨一次地出货。在这个村子里的田螺加工厂,各种口味各种包装的田螺堆成山。但附近临时摊点排成两公里长的夜宵街上的厨师告诉我,这样的产量根本算不了什么,嗦螺几乎是有多少就能消耗多少。
我看着一个小小村庄里的田螺清洗池,看着一张窄窄出货单上各色口味的嗦螺货品,看着每天数字惊人的交易量,仿佛看到了餐桌前撮起嗦螺的纤纤玉手,仿佛看到了河湖间举起挖掘斗的捕捞船。
突然地,就想起了幼时乡间赤脚下水捡田螺的朴素与天然,想起田螺姑娘的故事和红辣椒炒田螺的鲜香。那种佐餐的乡间菜肴,与嗦螺有着完全不同的滋味。突然地,就想起来要感谢田螺强大的适应性和繁殖力,要感谢养殖田螺、繁育田螺的人,让天然水域的一部分田螺,还能够绕过嗦螺产业的碾压,继续野生野长,让古老的田螺继续绵延自己的传奇,让更多喜欢嗦螺的人在很多年之后还可以继续有螺可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