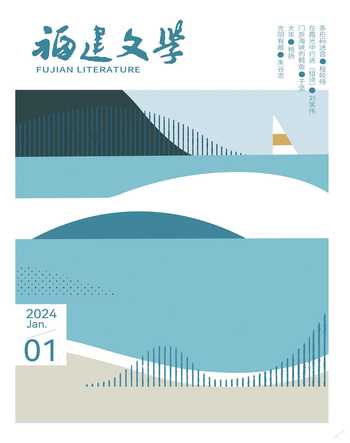风吹塔里木
张扬

1
到新疆的第一夜,入住在库尔勒市。较之于内地城市,孔雀河畔的夜色姗姗来迟,天幕上长留银质般的光芒,人也显得亢奋。晚风舒缓而柔和,有着近似小提琴曲的节奏与美妙。树叶在光影交错中轻舞,发出沙沙的声响,好似一阵雨来。槐花、合欢的清香幽幽飘散,也有丝丝缕缕汇到一起,凝在行人的鼻尖。
每一种植物,或许都有其生命的胎记与生存密码。槐树、合欢以及桑树等,是南方常见的树種。它们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东北边缘繁茂生长,与高低错落的众多建筑一样,让从内地来的我觉得眼熟,生出亲切感。植物如人类一样,有着漫长的迁徙过程。实际上,桑树是从高海拔往低海拔移植的,而后又从东往西,远到异国他乡。茶叶也是一路迁徙、播种,从中国“移民”到欧洲。亦有从西往东,来中国落户的植物,比如西瓜、西红柿、胡萝卜、仙人掌等。在古代,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发生了太多“移民”故事,包括植物、动物。
库尔勒曾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座重镇,现属南北疆交通枢纽。库尔勒街头的香梨树、杨树,店铺中的抓饭、馕饼、羊毛毯、铜茶壶之类,合成一组特殊的意象与符号,也像提示外来者,这里是有别于其他地方的城市。
连续的高温天气,忽地戛然而止。出门时,天阴着,雨滴三三两两飞落。塔里木盆地干旱少雨,风沙强劲。古来万事万物难占全,地下累积海量油气,地表缺着溪流湖泊。若雨量充沛,说不定到处流水潺潺,绿树葱茏,花团锦簇。水草丰茂,物产富饶,人丁兴旺,是古国古城的依仗,也是今日城池繁荣的象征。
远古时期,山崩地裂、海枯石烂的全景,实难想象。在塔里木盆地,曾多次发生地质演变,每一次构造变动,都交替着速亡与速生。沧海桑田之后,海水离场,地层中的油气聚集埋藏。风不分年月,也不知疲倦,搬动着沙粒、土壤。盆地中,遗存着被称为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一些山体夹杂着苍白的贝壳、粗粝的鹅卵石,透着无比古奥与荒凉。
天山,昆仑山,以及阿尔金山,环绕着塔里木盆地。“白云在天,丘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复能来?”这首《白云谣》,传说是住在昆仑山的西王母,与周穆王诀别时所唱。故事的结局并不圆满,周穆王未再返回,西王母郁郁而终。依照《山海经》描绘,女神西王母竟是豹尾虎齿,蓬发如戴胜鸟,半人半兽一般。
云天漠漠,极目之下,山大多赤裸,无一草一木装扮。路两旁的山,干枯到手一碰即可粉碎似的。实则,刀砍斧削一样的山体,有的特别坚硬。金庸笔下的玄铁,也许就潜藏其中。稍远些的山,笼着蒙蒙尘烟,似有千军万马在奔突、鏖战。此时,铅灰色云团缓缓移动,风从地面吹向沟沟壑壑的山里,又在荒无人烟的山谷打着旋,成了天上地下浑然一色的组成。
更远处的,是隐现在天际的高山。山尖绕云,一束耀眼的光柱从灰色云层中射出,对准山之巅,照得积雪莹莹然。那正是蒙着神秘面纱的雪山,犹如遥远而不可及的古国,突然露出冰山一角。
1946年,于右任至天山南北,望山得句:
雪似山之衣,云似山之冠。
修洁复修洁,容君面面看。
雪山偶现的那一刻,人所能做的,就是不言不语,面向雪山凝神、远观。现场情况正是如此,众人在一瞬间陷入了集体沉思。
雪山亘古沉默。自雪山而下的水,先是势若猛兽,而后由强到弱,或徘徊不前,或倔强流淌。枯水之季,盆地中的河流,有的明显变浅,有的似有若无。
2
洪荒远去,绝处逢生。由盆地边缘,向盆地中心,亦即塔克拉玛干沙漠进发。沿途所见,像电影镜头,闪现着绿色、灰色、黄色以及红色。此季的青杨、白杨一律青绿,没有秋日下那般热烈绚烂。戈壁滩或沙丘之间的红柳枝条,近似松柏。其枝叶间,盛开着米粒般的小红花,密密麻麻,似要证明它们的强大,环境再恶劣,也能绽放其美,冲淡大面积的冷色调与沉闷的氛围。
以芦苇编织的草方格,嵌在沙漠公路两旁的沙丘中,用来阻挡、延缓流沙。车窗外,高压电线伸向远方,钻井、站房不时闪过。风不甘寂寞,一路追随,无休无止地扑打着车身。车屁股上,啪啦啪啦地响个不停,似雨点猛砸。车窗甫一打开,肉眼看不见的细沙、微尘,随着一股风,呼地涌入车内。车内的人,赶紧将车窗摇起。一天跑下来,车身便蒙了厚厚一层灰尘。
去往轮探1井的路上,遍地可见枯死的胡杨。这时的风,如染土黄色,充斥着肃杀之气。它从伏地的胡杨、立着的梭梭上刮过,发出尖厉的呼啸声。一不留神,我的右眼迷了沙尘,被磨得生疼,接连几天,都是红肿模样。
连绵不绝的沙丘,是塔里木盆地中心最明显最厚重的地表呈现,它刺激到人的视觉,让人震撼、眩晕,也让人感到枯燥。路越走越远,天地间的赭黄愈发深重。在这样的空间中,人的所有想象、欲念与行动,与无垠的沙地纠缠在一起。每一日,人在看沙,沙也在看人。为着油气勘探、开采的人们,长期身在沙漠,其体会应当更为深刻。
大漠里的天气,说变就变。一日之中,或晴,或雨,或阴,或为沙尘暴,或复归于晴天。紧随变化的,是难以捉摸的风。风有时凌厉如刀,有时如温热毛巾敷面,有时干爽不惹尘埃似的。风是无形的,善于变着戏法,又仿佛被灌注神奇力量,幻化出具象,成为长者、诗人、浪子或者魔鬼,忽而和蔼,忽而斯文,忽而调皮,忽而森然恐怖。
沙漠辽阔,原本无路可走,凭着人力,硬是从中蹚出宽路、窄路。路平坦或坎坷,俱要人走;沙冷沙热,也需人来感知。月照千古,风吹万里,昔日出访的使者,布道的僧侣,戍边的士兵,流放的官员,冒险的考古者、旅行家,踽踽独行有之,三五成群有之,涉足不毛之地,或命丧于此。
风卷起黄沙,驼铃一声复一声。65年前,一支特殊的勘探队,行进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这支勘探队规模不小,由320峰骆驼与120人组成,九进九出“死亡之海”。最终,70多峰骆驼倒在了沙漠里,再也没能站起。今日若立一座碑,纪念这些骆驼和曾经的壮举,未尝不可。
此后,勘探、修路乃至运输物资,动用了多种“重武器”。天上飞机低翔,沙丘上奔驰着特种运输汽车。塔中1井飞机跑道,是塔里木油田唯一留存的钢板跑道。这条千米长的跑道,承载过运输的重任。名为双水獭的飞机,在这里起起落落,每天载人载物,往返于塔中至500公里外的廓尔勒。
在塔中1井飞机跑道,几位中年人放下矜持,像孩子一样撒欢。每个人都张开双手臂,沿着跑道向前,加速、加速、再加速,想象着自己腾空而起,想象着御风而行。风,微微吹着,有清泠之意。众人的笑声,回荡在湛蓝而高远的天空。时光匆匆,曾经少年,秀眉白面,鲜衣怒马,为赋新词,无愁说愁。如今中年,可高歌,可欢呼,可发少年狂。将来老了,也是温暖的回忆。
在塔里木,油田人日行千余里,家常便饭而已。于我,身体则有些吃不消。有一天,赶了长长的路,途经坑坑洼洼的地方,车颠簸如船行汪洋,全身骨头被颠得几乎散了架。往满深5-H10井的路上,所有人的手机信号都中断了,失去联系与导航功能,好像一下子与世隔绝了。行进的路,一再走错。弯弯绕绕之后,目的地才被找到,一时人困马乏。
转来转去,这一带的沙漠,光秃秃一片,未见胡杨,也无其他植物。之前下了雨,沙丘半干半湿,像浓酽的咖啡现出拉花图案。此时此刻,沙海近似枯黄色,呈现出柔美的线条。在风的策动下,它一旦有了动静,简直山呼海啸。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春季的风沙,尤其频繁,肆无忌惮。在沙漠中忙碌的人,睁眼有沙,呼吸有沙,张口有沙。每到一处,油田的人,总会提及沙尘暴。未经历沙尘暴的我,有些无知无畏,甚至期待遇见。
过塔里木河的那天,一开始天阴沉着,雨点飞溅到车窗玻璃上。奔向轮西油田桑吉公寓的路上,烟雾状的沙尘随风腾起,由远及近,越来越浓,直至遮天蔽日,一片昏暗。风沙四面围合,刮着车顶、车厢、车的底盘,轰然作响。车速不得不慢下来。初见沙尘暴,人很紧张,又有点兴奋。逢遇极端天气,人除了尽力规避、抵御,有时差不多束手无策。幸而,这场沙尘暴的烈度有限,车冲出了其肆虐地带。重见了蓝天,人长吐一口气。
3
万顷流沙下,覆盖着沉积亿万年的岩石。穿越坚厚无比的岩石,开掘出一条万米深的油气通道,难似登天。深地塔科1井,中国首口万米科学探索井。这口特深井的启动,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探险,地质科学家、工程师、油气勘探者所要应对的,属于极限挑战,包括极高温、极高压与极高的地应力等。开钻前,沙尘暴几乎天天袭来。太阳在人们的眼里变换着颜色,一会儿是灰的,过一会儿成了黄色,再一会儿,一片红了。戴上安全帽与护目镜,工人仍是灰头灰脸,少不了吃沙土。几十年前,在沙漠流动作业,遇到沙尘暴,勘探者住的帐篷,呼地就被吹翻了,生活物品也被吹得无影无踪。现在进行类似作业,以集装箱组成工作间、宿舍,可挡一挡风沙。
深地塔科1井正式开钻时,碰上了吉日,当天风平沙静,一切顺顺当当,所有人的眉头都舒展了。钻井以每天200米左右的速度,向地层深处掘进。要穿越十余套地层,掘至万米深,如在茫茫夜色中,由珠穆朗玛峰的峰顶向山麓,作精准投篮。
2023年7月30日,一行十余人,到了深地塔科1井工地。地面上的井塔,高不足百米。井下,已钻至5856米,触及5亿年前形成的地层。井一段一段掘,地层深处的钻井动态,自有“火眼金睛”般的监测系统盯防。工地上,摆了一排木盒子,分装着取自地层深处的岩屑,并一一编了号。从盒子里,我选了一枚岩屑,采自地深5643米,深灰色,指甲盖大小,用手捏住它,好似触摸到地球内部秘密。之后,在戈壁滩上,捡到一枚指节长的风凌石,我将它与那枚岩屑包在一起。历经地火淬炼的岩屑,与经受风侵雨蚀的风凌石,相遇在了浪荡乾坤。
无风无雨时,一只沙漠之狐蹑足而来,在深地塔科1井工地探头探脑。工人们见了,轻手轻脚干活,生怕惊动了它。有人拿出自己带的面包,丢在沙地上。狐狸慢慢走近,试探地嗅了嗅,又警惕地往左右看了看,才衔起面包,转身而去。不几日,这只狐狸又来工地讨食,工人们掰了馒头,扔给它,它的胆子大了,在作业区轉了转,才离开。一来二去,这只狐狸踩准了工人作息时间,到了饭点就来转悠,甚至拖家带口讨食。半年不到,它长壮了,尾巴上的黄毛又厚又亮。
在油田开车的一位司机,遇过沙漠之狼。那天傍晚,他停稳车,下来歇息,就看到一头狼盯着他。狼看他,他也看狼。狼并无进攻、侵犯的架势,他也就不慌不忙地掏出手机,朝狼拍照。手机闪光时,那头狼霍地掉转头,跑远了。
塔克拉玛干沙漠,一度被称作生命禁区,纵然如此,也阻挡不了探索者的步伐,又不乏其他生命活跃。那几日,听到多桩与沙漠动物相遇、相伴的故事,想看到它们的念头更强了。
走走停停,几次遇到蜥蜴。这小动物,跳跃起来,快如疾风,只有当它静静地伏在沙石上,才可见其样貌。空旷的沙漠或戈壁滩上,鸟声显得微弱,仿佛一不小心就被风吸走了。白尾地鸦、黑顶麻雀、小沙百灵只管飞来跳去,它们尤其迷恋“沙漠绿洲”,早早晚晚鸣叫不休。
地气充满神奇,塔里木盆地物产自有其美。风吹红了一颗颗大红枣、金丝枣、沙枣,也吹熟了棉花、玉米、白杏、西瓜、哈密瓜。在塔里木油田,入住的每一处公寓,房前或屋后都有油田人开垦的池沼、菜地。水池里,大鱼小鱼浮浮沉沉。菜地里,生长着傲娇的辣椒,紫得发亮的茄子,藤蔓缠绕的南瓜,粉刺满身的黄瓜,甜蜜蜜的白兰瓜。沙地上,向日葵开得正欢;场院中,诱人的葡萄缀满一丛丛葡萄架。
风吹在牧羊人的身上,牧羊人形同一尊雕塑。往塔里木油田大北1202井路上,遇到一位牧羊人。他戴了一顶帽子,满脸黝黑,络腮胡黑中泛白,一双手反背在身后,且横握了一根白色木棍。牧羊人的身体靠近一处山崖,往前走一两步,便是漏斗式的山谷与褶皱山脉。放牧时,自家的一只羊走丢了,牧羊人沿着山路徒步找寻,途中向油田工人打听。在沙漠中,但凡碰见受伤的羊,油田人都会带回去救治,然后归还给牧民。山坡上的风,一阵强过一阵,像河流中的旋涡,欲将人卷走似的。站在坡顶的牧羊人,一遍遍扫视着山谷,期望发现羊的踪影。
少时诵读古代民歌与边塞诗,幻想自己奔跑在大漠草原,花鲜草肥,牛羊成群,手把牧鞭高高扬起。待到人至中年,但知事事如意难,人间辛苦多,放牧的活,其实并不轻松。
从大北1202井区返程,颠簸而行。三只野羚羊,不声不响,从山坡的一侧蹿出,迅疾不见了,唯余一股尘烟弥漫着。绘画者善用留白,野羚羊似通其妙,它们现身、遁去,仅仅一刹那间,让人惊喜,又意犹未尽。
傍晚,回住处路上,见到几十峰骆驼散在戈壁滩上。落日熔金,戈壁滩闪着金光,瘦而高的骆驼低头啃食,身上薄薄的绒毛也披了一层金光。风悠悠,骆驼闲闲。
骆驼啃着的,是一簇簇骆驼刺。它们也爱吃梭梭的嫩枝。梭梭貌不惊人,又不同寻常,承受力超强。它耐旱,也耐寒,还抗盐碱,其根系入地,可深达八九米。正所谓竹竿打蛇,一物降一物,梭梭可用来防风固沙。梭梭的根部,往往寄生着“沙漠人参”肉苁蓉。其嫩枝可作饲料,也能为羊毛纱线着色。梭梭结的果,常被误作花样。它的种子,有如蒲公英,随风到处飘散。梭梭当柴火燃烧,火力奇旺,有“荒漠活煤”之誉。陶宗仪《辍耕录》说,用梭梭燃火,经年不灭,且不作灰。
4
风拂过条条林带、片片林网,掀起层层绿浪。塔中,建有全国首条零碳沙漠公路。这是一条绿色长廊,连通着塔里木30多座油气田。无水维系,绿色长廊难以为继。每隔4公里,路边就有一口水源井,井旁,盖着低矮的红顶蓝墙的水井房。水井房附近,穿插栽植着大量梭梭,以及红柳、沙拐枣等。夏日到这里,清凉的气息,无声无息地沿着人的体表,渗透进每一个毛孔。
沙漠之中,一株树两株树三株树挺立,一朵花两朵花三朵花盛开,都有诗意情味。驻守水井的工人,如园丁一样,看护着井区的林木、花草植被,定期给植物浇水、施肥。梭梭是天选之物,管护工是绿色守护者,均显示着生命韧度。
罗宗苹与老伴龚义明,早已习惯这里的风吹日晒。他们驻守32号水源井,将井区的植物料理得活泼泼的。别人随手带来的一束满天星,也被他们栽活了,长成了一大蓬。
2023年7月24日,晨风轻微,沙丘如睡。罗宗苹同往常一样,走出水井房。进入东面的草木丛,她突然大喊:“老龚,快来,快来看!”比她早7年来这里当管护工的老伴,听到老婆呼喊,以为发生了什么事,赶紧跨出门,一看,原来梭梭开花了。龚义明乐了,他笑老婆大惊小怪。不知为何,罗宗苹来这里已9年,尚是首次见到梭梭开花。她弯下腰,凑近闻了闻,拿手机拍了照。与远在浙江的女儿通电话时,她也聊到梭梭开花。一朵小花,成了她生活的一份惊喜与念想。老伴的身体不大好,罗宗苹悉心照顾着。烦闷时,她便与草木说话,又似一个人自言自语。当我来到32号水源井,她说起梭梭开花的事,还领着我,去看开过花的那一株梭梭。
又是一天,风呼呼吹着夜行的人。在月夜,唐代诗人李贺胸臆难抒,慨叹大漠沙如雪。那夜,我随众人穿越沙丘与沙垄。月如琥珀,星光熠熠,身前身后黑黢黢的。脚下的沙,也非清亮如雪,只是细而软,特别缠脚。走到油田管理区时,近旁灌木丛中,蓦然跃出一只野兔,其毛色为黄白相间,耳朵尖而长。它时而跳跃,时而静卧,几分钟后忽然停下来,一动不动,像在等人。众人走近,七嘴八舌问好,说它是玉兔下凡。兔子竖了竖耳朵,颇似得意,倏地蹿回灌木丛。
风日日吹在大漠里,吹到西气东输第一站,似乎减缓了节奏。站控室内外,一派整洁,又井然有序。这里被称为“塔里木油田的心脏”,关联着大“气脉”。每时每刻,从这里源源不断,向外输送着清洁能源。
克拉是钻石的度量,以克拉命名的一口口井,犹如嵌入地层的一颗颗巨大钻石。克拉2—7井,每天出气,足够近千万人口城市一天用量。与其他单井一样,这口井无须人现场值守。这边厢,安安静静,独守一处;那边厢,万家灯火,流光溢彩。风喜欢来探视、嬉戏,从一根根红色的管道上钻进钻出。浅浅流沙经过,风一吹再吹,细沙又远去了。偶尔,雨滴从空中飘落井区,惊了鬼头鬼脑的蜥蜴、沙鼠。
5
往塔中镇的路上,风几乎停歇了。一轮圆月由东升起,西边的太阳,尚未落下。众人又一次触景谈诗。茫茫大漠中,孤烟直上,长河静流,落日浑圆。这般景象,若非诗人经历,断断难以状摹。王维的《使至塞上》中,潜藏着孤独意味,更有慷慨之情、豁达之风。
不惧风沙的油田人,宛如行走的诗人,用双脚在大漠中写下一行行诗,诗中兼有叙事、抒情与说理。他们熟悉这里的每一天,懂得春风的多愁与烦恼,体会到夏日蒸腾似热锅,惊叹秋色的铺排与烂漫,也为冬雪覆盖沙漠的壮美所震撼。比起他们,初来乍到的我,只是暂时从一种生活经验中抽离出来,进入一种新的奇特的环境,不过是匆匆过客,也不过是共情未深的观众。
那天,在塔里木油田哈得一联合站,看到墙报上写着“高兴也是生产力”七个字,就停下了脚步。这一行大字,上下左右都配了工人的笑脸图。他们个个灿然,让人看了,如沐清风。一撥拨年轻人,带着热血与憧憬,自天南地北奔来,披上石油红,顶风而行,踏沙而歌。时间长了,他们也会褪去青涩,像一株株梭梭扎根于此。
千里之行,行于塔里木盆地。一路走来,如同读书不断。仿佛这里是一座巨型熔炉,人与风,与沙,与梭梭,与苍鹰野兔,与高山河流,与一切存在者,同受冶炼,直面生死。在塔里木盆地,对于身外之物,一个人很可能觉得不过尔尔,而眼前的一滴油、一瓶水、一碗饭,又让人切切珍惜。轮台,焉耆,尉犁,若羌,库车,且末,拜城……遇见的每一个地名,都萦绕在我的脑际。它们如竹简木牍、古玉琉璃,折叠着过往,又让来访者听到风中传递的密语,见识到它的沧桑、沉静与奇绝。
时光流转不停,塔里木盆地有鬼斧神工,更有人的创造之力。新风徐来,当长出大片大片的花木,结出满园满地的瓜果,它们缤纷可爱,芬芳可亲,与簇簇灯火构成繁华盛景。彼时,日月昌明,水波荡漾,人潮涌起,飞禽走兽出没。
责任编辑陈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