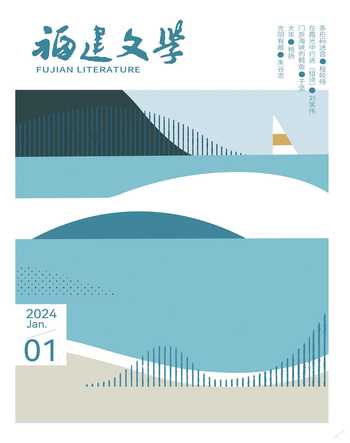他就是诗人鲁藜
吴尔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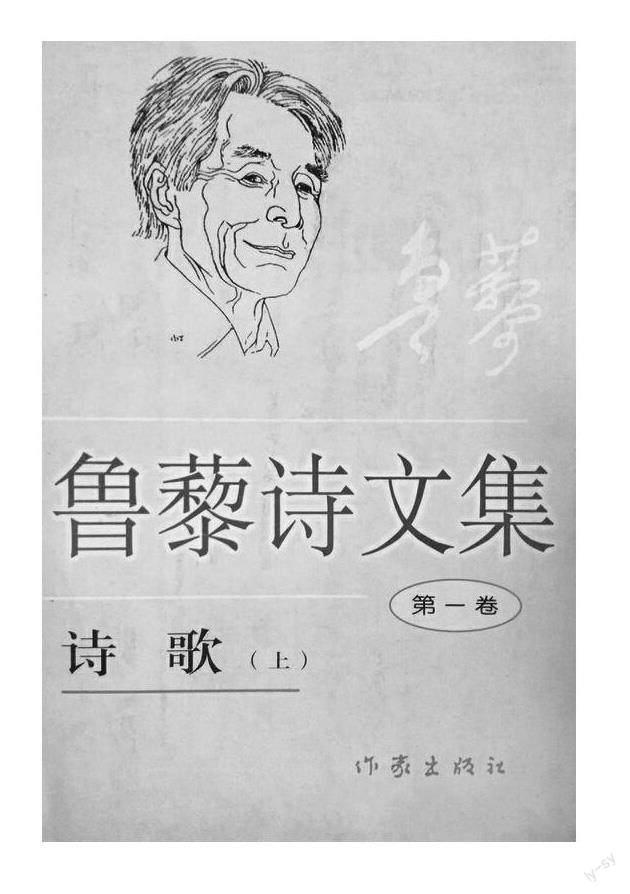
近了,近了,故乡近在眼前。
问故乡,问故乡,别来无恙否?
可是诗人的眼前一片模糊,他什么也看不见,纵横的老泪蒙住了双眼。
52年,超过半个世纪啊!52年前离开故乡时,他还是迎风而立的热血青年,此时呢?诗人已经整整70岁,身形不再挺拔,腰弯背驼,头发斑白稀疏,步履蹒跚。他需要扶住村口的大榕树,才不至于跌倒。
这棵大榕树长在自家的西南侧,树高冠阔,虬髯飘拂,长长的分枝深深地扎进土里,弯成一座榕根“拱桥”,成为一道别样的风景。诗人不知道它几岁了,只知道村民都叫它“东角榕”。
当年,诗人在家乡搞农运,被军警深夜围捕,便是踏着这榕树越墙逃脱,再次离开故乡的。那是诗人第二次离开故乡,第一次他太小,才3岁,没有任何记忆。流落异国他乡后听父亲说,这个叫许厝的故乡,是他的出生地。
父亲说有一座叫“小盈岭”的山岭,上接三魁山,下连鸿渐山,山脉延绵到天边,神仙都走不到头。鸿渐山脉的左侧有一座香山,北侧的山脚下有一座小小的村落,那就是许厝村。
许氏先辈在这贫瘠的土地上繁衍生息,按族谱辈分排列,到了父亲这一辈已是第十九代,是“派”字辈,父亲名叫许派缠,是个寡言少语之人。
宣统皇帝下台的那一年,恐慌中的许派缠又添加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命运弄人哪,许妻已经生下10胎,这第11胎是个女孩多好,可竟然是俩儿子,这可怎么得了?许派缠横下心,送出去小的,留下大的,还给他取了个“涂地”的名字,意思是依靠耕种农田养活。虽然母亲生了11胎,但许涂地只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兵荒马乱的,孩子养不活呀。
许涂地3岁那年,张勋留辫子,废帝又登基,局势更乱了,兵匪不分,盗贼蜂起,哪有穷人的活路?为了躲天灾避人祸,许派缠变卖耕牛和口粮,连一块山地也转了,勉强凑上20块银圆,买到一张许厝人叫“大字”的出国证书,带着一家人搭乘木篷船,从沙坡尾厦门港起程,漂洋过海来到越南湄公河畔,落脚在堤岸市边沿一个唐人聚集的贫民窟。这个当时叫“二十九间”的地方,后来叫胡志明市五区。
父亲不识字,做不了体面的事,终日在一家小作坊干粗活。当杂工的母亲更累,没日没夜地操劳,腰杆没有直过,肩膀没有闲过。这个可怜的女人裤管永远是湿的,眼睛因睡眠不足肿得像两只烂柿子。她常常累得在炉灶下打盹,东家就往她的脑门上泼冷水,将她激醒。
尽管夫妇俩累得后脚踩前脚,尽管全家饥一顿饱一顿,但许派缠以一个庄稼人的质朴,认定这个小儿子是块读书的料,再苦再难,也要供他上学。
于是,年幼的许涂地进了当地一所华侨小学,老师觉得“涂地”两个字太土,便谐音取了个学名“许徒弟”,要收他为徒的意思。
许徒弟着了魔似的用功读书,每科成绩都拿5分,给许派缠争了脸,也给二十九间的华侨争了脸。
然而好景不长,许徒弟上高小第一年,母亲又生了个妹妹,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家境更加困窘。父亲为了多赚一点小钱,去码头扛大包。12岁的许徒弟辍学了,先到一家面条铺当学徒,学会做面;面条铺关门,他就在华侨聚居的二十九间沿街叫卖;叫卖不来钱,只好混进码头,给父亲当帮手。可是人小体弱的许徒弟实在扛不动大包,绝望中沿着湄公河漂泊。
湄公河默默地流淌,一个羸弱的身影悄悄地沿岸行走,那个苦难的少年流浪汉就是许徒弟。许徒弟常常坐在岸边,注视河水急速地往前,不知道苦日子何时是个尽头。
冬天是百业的淡季,家里断粮是常有的事,母亲虽然还在哺乳期,还是自己空着肚子,将最后的食物留给丈夫和孩子们。许徒弟的心揪得更紧了。为了让母亲不挨饿,他自己到河边转悠,捡一点能入嘴的东西,植物的叶子和根茎,就是他的佳肴。即使找不到食物,许徒弟也故意拖到深夜才回家。可是,不论夜有多深,母亲都坐在家里等他,眼里饱含泪水。
给许徒弟黑暗的生活带来一丝亮光的,是一位叫陈天助的邻居。陈天助叔叔来自台湾,住在一间终年不见阳光的小屋里,他行走江湖,靠拔牙镶牙赚钱度日。重要的是,这个牙医识文断字,能用闽南话吟诵唐诗宋词。
闽南话保留了中原普通话的基本特征,尤其是唐诗,用闽南话朗读平仄是最对味的。这对失学的许徒弟来说,吸引力太大了。在陈天助的指导下,许徒弟阅读了大量古诗文,为少年的想象插上飞翔的翅膀。许徒弟想,有那么一天,我也能写诗,那该多好呀!我一定要写出人间的悲与喜、苦与乐,写出自己的盼望与期待。
少年许徒弟的内心有太多的苦闷与烦恼,他用最朴素的语言,将诗与歌写在地上,写在墙上,写在纸上,写在天空。一个流落天涯的诗人种子,在湄公河畔的土壤中发芽、生根,以破土的身姿迎迓东方辉煌的日出。
18岁,许徒弟出落成一个风度翩翩的青年。这个青年带着梦想,满怀激情,以超越的目光打量翻天覆地的世界。国内传来的消息,每一条都让青年许徒弟震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日军向辽西发动总攻,十九路军浴血闸北,溥仪开始满洲国傀儡生涯……许徒弟多想踏进祖国的土地,成就一番文学事业。
许徒弟做梦也想不到,他会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回国。
这一年,父亲许派缠身患重病,魂归故土成了他最后的夙愿。许徒弟决心帮父亲了却心愿,护送生命垂危的病人回到故乡。
父子同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许徒弟托人帮忙,把父亲藏在堆放煤块的货船舱底,自己装扮成船上的伙夫,逃过了关检,逃过了人头税,成功偷渡。
当许徒弟背着父亲走进香山脚下的许厝,兵连祸结的故乡已经是怎样的满目疮痍?到处残垣断壁,村民衣衫褴褛,农田抛荒长稗,连骨瘦如柴的狗,见了陌生人都只龇一下牙,没有力气叫唤。此时此刻,青年许徒弟才真正理解“窮乡僻壤”这个词的含义。
3岁离家的青年脑筋转不过弯来,难道这就是自己魂牵梦萦的故乡?如此破败,如此凋敝,看哪,在那荒草丛中,竟然有狐狸出没。再看祖屋老家,更是不堪入目:面阔三间其实不算小,进深一间,块石构砌墙裙,土坯砖墙,卷棚脊,硬山顶。可是厝前野草萋萋,房后的庭院改建成的小护厝已多处坍塌。
还好,淳朴的乡亲见流落他乡的父子归来,操上锄头劈刀就来帮忙,总算把病重的许派缠安顿下来。
不久,许派缠就告别了人世。许派缠的亲属都在湄公河畔,灵前只有一个对家乡陌生无知的儿子,后事怎么办?正好,在集美乡师当指导员的许有韬老师回到许厝的家,见这个丧父的英俊青年彷徨无措,便带头张罗出殡的事。乡亲们有的送米,有的送钱,让许徒弟有了依靠。
收殓时,许徒弟买不起棺木,左邻右舍又凑了一点钱,买了四块松木板,钉成棺。两个土工抬着薄薄的棺柩,许徒弟哭在其后,乡亲们一起送上山头。没钱买石灰,土工只好用常见的赤土堆了一座矮坟。于是,秃岭上便多了一抔黄土,一个逃难出海、重病归来的老华侨被埋在里面,落叶总算归了根。
目睹父亲如此悲惨的结局,许徒弟的心底深深扎下愤懑的种子:这个世道溃败了,得变。如今,父亲躺在里边,母亲远在天边,祖国处在悬崖边,放眼海峡两岸,哪里是我的家呢?身为中华儿女,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不挺身而出,有何脸面在家乡吃闲饭?
苦悶的许徒弟徘徊在榕树下,有时仰天长叹,有时埋头短吁。许有韬老师看在眼里,明白一个热血青年的无助。不能改变出身的许徒弟,发誓要靠知识改变命运。关键时刻,许有韬给许徒弟指明了一条道路:去集美乡师读书。陈嘉庚创办的集美乡村师范实验学校,不要学费,还包膳宿,只是考试严格,最适合许徒弟这种会读书的贫穷青年。
果然,许徒弟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入集美乡师,并在厦门的《江声报》发表了诗歌处女作《母亲》。许徒弟以高挑的身姿、清澈的眼神、温和的面容、激情的文字,很快就成为同学中的明星。
接着,许徒弟从厦门来到上海,在陶行知创办的“山海工学团”担任夜校辅导员。诗歌《我们的进行曲》发表在《读书生活》时,出于对鲁迅的崇敬,许徒弟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鲁藜。在纪念普希金逝世100周年的集会上,鲁藜巧遇邹韬奋,邹韬奋高兴地握着他的手,向周围的朋友介绍说:“他就是诗人鲁藜啊!”
从此,许厝村的许徒弟消失了,文坛出现一个青年诗人鲁藜。
从此,鲁藜投身滚滚的革命洪流,成为一名革命战士、一名战地记者,成为“七月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呼应“以血泪为文章,为正义而呐喊”的时代要求。他有一颗永恒炽热的心灵,性情温和如水,内心热烈似火。他的诗歌格调清新明丽,有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交融的韵味,自成一家,不但得到朱自清、闻一多、胡风等名家的称赞,也得到文学史家王瑶的推崇,受到很多关注和肯定。“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经漫长岁月冶炼,你属于纯金。”艾青这样评价鲁藜。
鲁藜自称“忧患的宠儿”,不料一语成谶。
为诗而活的鲁藜,为诗而战的鲁藜,在坚硬的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他的人生没有丝毫诗情画意,有的只是坎坷不断,波折不停,不管是感情,还是创作,都是磕磕绊绊、跌跌撞撞、起起落落。他的名字和一个叫“胡风”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的火热年华跟国家一个动荡的年代高度重叠,他的命运怎么能好呢?
经历了26年的折磨,鲁藜身体瘦弱,额纹深陷,风华正茂的青年诗人成了骨瘦如柴的老人,穷得只剩下一双筷子、一只碗、一个黑乎乎的锅、一张小行军床。让人难以置信的是,鲁藜的眼里仍然闪烁着热情的光芒,眉宇间照样堆满童真的笑容。这是一张诗人的脸啊,他的脸就是一首史诗,有艰辛的内涵,有明快的表征。
真的,鲁藜的一生就是一首悲壮的诗,只是在他痛苦的深渊里“浮出彩霞的光彩”。
诗人珍惜“命运留给我的一片晚霞”,以衰弱的身躯和刚强的内心不倦地歌唱。他要与死神赛跑,抓住诗神的尾巴,在生命结束之前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于是,诗人发出了最欢愉的声音:“我只要一滴水/我就可以尽情歌唱/
唱得天地间/只有阳光、花朵与诗歌。”
他顶住了年老多病的困扰,顶住了激情与灵感的濒临枯竭,彻夜写作,滚烫的诗页如夜幕降临的倦鸟,匆匆飞向可以栖息的枝丫。短短五年,就在《诗刊》《人民文学》等刊物发表100多首诗作,其中一部分结集为《鹅毛集》《天青集》出版。
这是怎样的晚年呀,鲁藜巴不得把轻盈的身体摆上诗歌的祭坛,掏出尚能跳动的心对天起誓:诗神啊,我爱你,胜过爱自己。“诗人老去诗情在”,于是鲁藜晚年的诗,进入弥漫着哲理思考的内省天地。
这么一个历尽苦难痴情不改的赤子诗人,当时隔52年再次重返故乡,内心会是怎样的凄凄惨惨,抑或波澜壮阔?
1984年4月,火红的凤凰花在鹭岛盛开的时候,鲁藜偕夫人刘颖西回来,到厦门大学参加“台湾文学研讨会”。诗人欣喜地看到:故乡的诗歌活动犹如滚滚海潮,后浪推前浪,一浪高过一浪;青年的诗人们宛若郁郁相思树,一茬高过一茬。新时期以来,厦门每年都举办“鹭岛诗会”,恰似凤凰花开,洋溢热烈生机。
一个星光璀璨的夜晚,厦门市工人文化宫的大厅灯火辉煌,热闹非凡,第三届“鹭岛诗会”拉开帷幕。那是一个诗的时代,充满诗的激情,诗的表达,诗的远方。这一届诗会,因老诗人的归来而异常鼎沸,诗歌爱好者欢聚一堂,以凤凰花的绚烂心情、相思林的蔚然阵容、鹭江潮般经久不息的掌声,热烈欢迎久经劫难而诗心如磐的新诗先行者——鲁藜的莅临。面对乡亲们洋溢的笑靥、后来者赞叹的声浪,诗人心潮逐浪高,文思胜泉涌,即兴朗诵《献给白鹭诗人的歌》。
他动情地说:“我是写诗的,今生仍然要为亲爱的祖国做贡献,仍然要为诗而燃烧!”
会议结束后,鲁藜归心似箭,携妻子返回翔安许厝村。
近了,近了,故乡近在眼前。
然而,近乡情更怯,旧时巷陌今何在?亲朋故友可安好?诗人展开双臂,要把故乡揽进胸膛,他来不及洗去车旅的劳累,就到田间地头走亲访友。
“我回来了,故乡!”这是鲁藜对所有人的问候。他“迸发着泪花投进”许厝的怀抱。诗人回到熟悉又陌生的故土,感慨何止万千:“我依偎着车窗凝望过去/心涛如澎湃的鹭江/半个世纪绯艳的风云/如同一道瞬息变幻的彩虹。”
夜深沉,寂静的山村弥漫着流岚,鲁藜躺在木床上,心中涌出从未有过的踏实。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就像成熟的果实,无枝可依,飘落大地是唯一的归宿。都说叶落归根,其实真正归根的是果实,融进泥里,生根发芽,成长为故乡的风景。朦胧的夜色透进窗棂,如粉般散落床前。屋后的榕树发出哗哗的林涛,那是对游子归来的问候吗?
第二天清晨,鲁藜牵手妻子在村中漫步,乡亲们见到传说中的诗人都颔首相迎,用最淳朴的闽南话问道:“吃了没?”
“吃了。”鲁藜用生硬的闽南语应答。
伫立在榕树下思考,是鲁藜的至爱。浓荫如巨盖、气根如飘髯的榕树是诗人的精神源泉。坐在榕树下,鲁藜可以彻底忘我,像一滴水融入海中,像一口气呼出空中,像一个诗人融化在诗情画意中。“树啊,你能否告诉我/我那些游伴都星散何方/也许都像金色的种子/各自飘落于黑色的土壤去孕育希望。”
这一次,鲁藜夫妇在许厝住了7天,正好一周,每一天家里都是高朋满座;这一次,诗人会见所有慕名前来拜访的诗歌爱好者,倾其所有指导晚辈;这一次,70岁的老人重修了父亲的坟墓,交代了后事;这一次,难道当年的许涂地知道自己是重返家园的最后一次?
1999年1月13日,在漫天飞雪中,鲁藜安详离世。
再过一年,就是人类的21世纪,鲁藜离去了,他的诗歌却在21世纪被传诵。
在翔安建区20周年之际,笔者来到鲁藜的故乡,看到在内厝镇政府、在第二实验小学、在鲁藜小学、在许厝村,在每一个显眼的位置,都赫然立着鲁藜的半身塑像。在厦门,他的诗作代代相传;在翔安,他的故事为人津津乐道。
如今,许涂地的故居旧厝,已打造成鲁藜纪念馆。墙上悬挂诗人自己书写的代表作《泥土》,每个文友都在这张书法作品前驻足。因为这首短短的四句诗值得每个人铭记,也值得时代铭记。
老是把自己当作珍珠
就时时有怕被埋没的痛苦
把自己当作泥土吧
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
责任编辑陈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