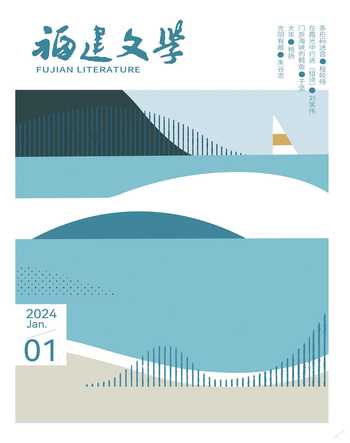光阴有痕
朱谷忠

山里的外婆
我的外婆是山里人,当年的婚姻自然是包办的。她的娘家,在闽中很深的山里,离她嫁的山村至少有数十里远,对此她心里很不满意,但也没办法。原来,她曾希望自己能嫁到山外去。为什么呢?我是后来才听母亲说过,外婆从小到大都在山里,见惯了茅舍、竹篱、山崖、梯田、杂树、野草,却从未见过山外到底是什么样子。
再说迎娶外婆的村子,与她娘家没多大差别,土屋毗邻,小路窄瘦;同样的,只有男人才一个月两次到山外的一个小镇去赶集,卖炭或卖山货,回来时捎点盐巴、咸鱼或日用品等。到了晚间,几个男人聚一块喝酒,讲点山外圩上喧闹吵嚷、拥挤凌乱或花花绿绿的事,且大大渲染了一番,总把不曾去过山外的女人们听得一愣一愣的。外婆也一样,只能在心里想象山外那是一种怎样广阔的田野、弯曲的河流和村巷,熙来攘往的情景便无从想象了。很长时间里,每逢秋天,眼见日子像村头那棵老柿树的叶子一片一片掉下,“不甘”两字便从她心里不由自主地流淌出来。
据说有一次,外婆怀揣上平日积攒的一些零钱,偷偷约了同村一个要好的女人,假装去地瓜田培土,却抄了小路拐进通往山下的土路。下山后一路走一路問,快到中午才来到一个小镇模样的地方。她们惊奇地看到,街中心全以青石板铺筑,从北到南,随形就势,都是店铺;两旁岔路,弯弯绕绕,或长或短,或宽或窄。不少土木结构的房屋,门扇上的朱红的油漆已然剥落。偶见一家门前坐着一位缠足的老妇,手中拿捏着针线,缝合着怀中的衣衫,却不停地拿眼睛打量她们。外婆她们也不敢与人搭话,只顾并肩携手,边走边瞧。不知不觉,来到一家杂货店门前,进去一看,里边的货物真是琳琅满目、古色古香,特别是胭脂、牛角梳、发夹,令人爱不释手,只是一问价格便赶紧放回去,因为兜里没有那么多的钱。总之,后来她们在一家点心店吃了两碗“粉插”,便匆匆离去。途中,两人统一了口径,任凭家里男人怎么问,只说是临时起意,进深山古寺烧香去了。
外婆二十来岁生下我舅舅,再过两年生下我母亲。不幸的是没过几年,家里老婆婆与她的男人便相继去世了。个子不高但生性倔强的外婆,从此挑起一家人生活的担子,干农活、打猪草、编斗笠……最是教人佩服的是,每逢山外圩日,外婆从不怕别人议论什么,总是和村里男人们一样挑炭下山售卖……多年后,我曾写过一首诗这样赞颂外婆:“总是在风中挺起身子/在崎岖的山道上迈开双脚/搁在肩上的重担/每一次都要压出汗水几瓢/卖炭回来默无一言/抄起镰刀又去割草/歇息时抬头若有所思/日落的方向飞着几只小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一天她终于躬下了腰/她的女儿这时直起身子/执拗地说——我来挑……”
这诗中写到的“女儿”,自然就是我后来的母亲,她的执拗,让外婆心里深感欣慰。从此,卖炭的日子里,我母亲代替了外婆的角色。其实,那一年我母亲才十九岁。如花的年龄,无惧无畏地分担着贫困生活的重压,却没有叫苦,也没有眼泪。她甚至舍不得在镇上吃一次点心,每一次回到家里,只用一碗米汤的清淡,消除全身的疲惫。
然而不到一年,我母亲却做出了一件令外婆也没想到的事。原来,我母亲在卖炭的圩市上认识了一位制作杆秤的老匠人的儿子。那位老匠人制作的杆秤,一直以不差分毫赢得三乡五邻的赞誉,在镇上几乎家喻户晓。因此他的儿子——后来成为我的父亲,每逢圩日,都持一把大秤在圩市里为买卖双方公平过秤,收一点费用。他手脚麻利,诚挚热情,大家都信得过。奇怪的是,我母亲与这位老匠人儿子打过几次交道后,却发觉有点不对了,因为这个掌秤的后生仔再也不肯收我母亲的费用了。也许,就在他俩曾经互相打量过对方的那一天起,爱的种子已不约而同地播进心里去了。公平的杆秤,斤两没有误差,却在不知不觉间,为人世间倾斜了一段有缘相识的爱情。
这就是我母亲和父亲相恋的故事,简单、质朴。不过,当年我外婆却是个细心的明白人。早先,外婆就有几次发现,我母亲从山外回来,总偷偷地回屋里去照镜子,还显出若有所思的样子。更可疑的是有一次我母亲还神使鬼差般地带了一盒胭脂、一把牛角梳和几个发夹回来,这都是外婆当年想要却买不起的东西,至少是一担木炭的价钱。终于,禁不住外婆几句盘问,我母亲就吞吞吐吐地坦白了:这是圩市上一个掌秤的后生仔给她买的。外婆问:“你真的喜欢他?”我母亲答:“是的。”外婆又问:“你想好了?”我母亲说:“想好了!”这时,外婆突然跳起来厉声问道:“你真的、真的想好了?”我母亲一听,有点慌了,但很快又镇定下来,破天荒地面对着外婆扯嗓喊道:“想好了!我真的想好了!”戏剧性的一幕终于以喜剧结尾:外婆听罢,转了转身子,突然扑向她疼爱的女儿:“好啊好!我早就想着有朝一日把你嫁到山外去……”
那时的婚姻,即便是自由恋爱,也得找个媒人定八字、订婚约、拣日子。可外婆不兴这一套,只是挑了一个双日,把我母亲带回的胭脂在脸上轻抹几下,又用牛角梳把头发梳了又梳,最后在后脑髻上按了一个发夹,再捎带一些红菇,竟带上我母亲,趁天刚亮时下山,亲自上门议谈婚事。不用说,当一对赤脚蒙尘但却光鲜的母女走进老匠人家中,说明来意,饱经世面的老匠人也吓了一跳,据说他懵得当场说不出话来。闻声出来的老匠人儿子,也不装聋作哑了。我外婆一见到未来的“准女婿”,便定定地把他从头到脚细细瞧了一遍,最后毫不掩饰地,脸上笑成一朵花。随后,双方坐下挑明了情况,甚至不去细问各自家庭的收支情况,有关嫁娶的事宜就摆上桌面。总之,一切有违常规,一切却变得简单、明晰又水到渠成了。最终,两家自主联姻,成了山里山外一桩不大不小的“新闻”。
一年后,母亲生下了我姐姐。又一年,母亲生下了我哥哥。再过两年,母亲前后生下了我和弟弟。这使我的爷爷——老匠人乐得合不拢嘴,原来爷爷祖上几代都是单传,不想一下人丁兴旺,真是喜从天降。外婆呢,更是每逢我母亲临盆时就亲临现场,调度指挥,有条不紊。住十天半个月回去后,还不时派我舅舅前来,送些山里补身子的食品、药材。我母亲对我说过,我刚学会说话后,有一次外婆来看我,我躺在外婆怀里一口一声叫着“阿嬷”,乐得外婆差点被椅子绊倒。后来我们这些孩子们长大后,每年都分别到外婆家住一两天,和舅舅、舅妈的孩子去看好玩的风景,或到山里去采野果,玩得非常尽兴。而更多的时候,总是外婆下山来看我们,每次都会带山里的糯米粿、柿饼或橄榄给大家吃。临走时,家里也买些食品和日用品让外婆带回家去。
可惜,时间淌过许多年后,外婆的腰也显得越来越弯,最后完全佝偻了。从此便再没下山过。而我们姐弟几人,也因外出做工或读书,很少去外婆家了。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外婆去世,我们一家人才赶去山里为她作了送行。
人世单薄,亲情厚重。多少年又过去了,如今,在外蛰居的我,偶尔返乡,望见夕阳那边的青山,总还会想起遥远的外婆。有一年清明,我上山祭祀了爷爷、父母,下山后还叫儿子开车,带着家人去了山里,为的是去跪拜一下外婆的土坟。回来后,思绪如潮,遂又写了如下的几行诗:“雾谷云崖依旧闪绿/飞泉还挂在外婆家的屋角/路有了/电有了/饭碗也端在自己手上了/但外婆却早早走了/我只能一次次复读她的身影/让泪水无声地滚过眼角……”
绿色的邮筒
很久以来,我只知道矗立于街头巷尾的邮筒,是用来收集外寄信件的邮政便民设施。但邮筒有什么来历,为什么是绿色的,却浑然不知。
有一次,我带小孩出去散步,遇到街旁一个绿色邮筒,偏偏她就这么问我,让我支吾了半天也讲不清楚。回去后,连忙翻出词典查阅,这才了解到:原来世界上最早的邮筒,竟然是一只靴子。那是1488年,葡萄牙著名航海家迪亚士率领的船队在海上遇险,他乘坐的那只船得以幸免,其余则全部覆没。返航前,迪亚士用一只靴子给可能生还的同胞留下一封信,并把它挂在树上。一年后,葡萄牙的另一位航海家途经此地,看到靴子里的那封信,获知了当年发生的一切。若干年后,“靴子传信”的故事渐被传为佳话。此后,设立邮筒投寄信件这一形式也在世界各地流传开来。
中国邮筒设立于1897年。以绿色作为邮政专用标志,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邮政会议上一致决定的。因为绿色象征和平、青春和茂盛。有了这个规定,中国的邮筒、邮递员的衣服以及邮包、邮政车都一律采用绿色。
我没有忘记把这些都告诉小孩,也不知她听懂没有,但心里不免惭愧。
其实,我与邮筒有着多年的接触。20世纪60年代末,我中学毕业后在乡下务农,离家不远的一条老街上,就有一家小邮局,门外矗着一个邮筒,大约有些年月了,绿迹斑驳。记得,那时母亲每年都会叫我在家里写几封信给在外的父亲,内容大多是把家中缺粮少钱的情况说一遍,希望及时寄点钱回来接济,最后写几句“在外身体要照顾好”什么的。写好后给母亲念了一遍,等她点头同意,或再补充几句话,我就立即装进写好的信封,再取一张8分钱的邮票,上浆,贴好,用手掌按压一遍,这才上街把信塞进小邮局外边的邮筒。
后来,我偷偷学会了给报纸投稿,没钱买稿纸,便用旧作业本的反面写字。那时,给报纸投稿属“邮资总付”,所以我只需花一点钱买信封就行。不过,刚开始怕人知道,基本都是在夜间来到小邮局的邮筒前,趁人不注意时把厚厚的信封塞进去。结果几个月过去,投去的稿件却一篇篇如泥牛入海,音信全无……有些灰心丧气的我有时经过邮局,觉得那邮筒似有些僵硬、冰冷。有一次,我竟用狐疑的眼光不停地打量着它,想到是不是装稿件的信封太重,沉在筒底沒被拣出……后来去问一位文化站的人,他一听就笑了,说邮筒每天都要打开收信两次,不可能遗留在里面。又听说我是给报纸写稿的,便安慰我要有耐心坚持下去。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那一年,村里推广种植矮秆晚季稻获得成功,为此我写了一篇报道,经村里还有公社办公室盖章,投给省里报纸,没想到居然给登了出来。文化站的同志看到这篇报道后,立即向村里干部通报了这件好事,还在广播里广播了三天。这一下,我成了村内外许多人知晓的一支“笔杆子”,走到哪里,都有人问:“阿忠,最近又写了什么?”“厉害呀,省报都登了文章!”我听了,表面谦虚一番,心里却乐滋滋的。从此,我投稿再也不遮人耳目了,每次都堂堂正正把稿子塞进邮筒,还对邮筒自言自语道:拜托了!拜托了……那些日子,邮筒的绿色变成我眼中最美的颜色,因为它能让我充满想象和期待。
然而,当时我还无法掏钱订报,为了解我发给报社的稿件是否登出,一有机会我就会来到街上小邮局,站在邮筒旁看贴在墙上的报纸。那时看报的人似乎比现在多,有时刊登国家大事,想看的人挤都挤不进去。不过,我一心注意的只是文艺副刊,搜索上面有没有刊出我的豆腐块文章。有几次,果真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我顿时瞪大了眼睛,美滋滋地扫了一遍又一遍。临走,还兴奋地用手拍了拍绿色的邮筒,喃喃自语道:感谢!感谢……
当然,不声不响的邮筒也是有故事的。有一天午后,我上街经过小邮局,突然注意到有个女子,手拿着一封厚厚的信在邮筒旁边徘徊着,至少有几次,她好像想把手中的信塞进去,却又把手抽了回来,样子十分犹豫;最终,只见她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下定决心似的把信投进了邮筒。没想到,刚走几步,她却转身回来,用手拍着邮筒叫道:“我不寄了!我不寄了!快帮我拿出来……”喊声惊动了小邮局里的人,一个大约是负责人模样的人走了出来。他来到女子身边,不知问了几句什么,就把那女子带进邮局。好久,一个邮递员出来了,他打开邮筒下面那个长方形口子,把里边一沓一沓的信件都掏出来,装进绿色邮包,就提了进去。又过了许久,才见那个女子如释重负地从邮局走出,神情上已看不到任何异样了。至于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局外人谁也不清楚。大约过了半年,才听到街上传言,说是那个女子与同村在外做工的一个青年谈恋爱,但父母嫌男方家庭贫穷,坚决不同意,日日威逼她写信给在外的青年表明断绝关系。女子在身心俱疲下只好写了那封信,于是上演了邮筒前的那一幕。至于后来,当事人结局到底如何,就再也没人过问了。
还有一件事也和邮筒有关,即当时我有一个好伙伴,正暗恋着同村一个女子,但一直怯于表白。我曾用古诗中的两句取笑他,“思君不可得,愁见江水碧”。也不知他听懂了没有,却来了个脑筋急转弯,要我为他代写情书,他来抄正。这下我傻了,推辞不得,只得应允。但信要怎么送呢?请我,肯定不合适,请别人去,又怕走漏风声,于是我想到让邮筒来传递。他一听,连拍大腿叫道:“太好了,这主意只有你能想得出呢!”老天爷,这是什么话呢?幸亏我念及平素与他的情谊,也就不去计较了。那天夜里,我搜索枯肠为他写了两页给女方的爱慕心情与甜言蜜语。他喜不自胜又有点鬼鬼祟祟地抄正后,署了名,又在信封上写了收信人的地址、姓名,还无师自通地在信封下边隐去寄信人的信息,再拉上我,趁着夜色溜到街上,一股脑投进了邮筒。随后才过几天,他就急盼着对方能用这个办法回信。可惜过去了半个月,人俱在同村,仍渺无音信。于是他亲自写了一封寄去,结果也一样。这真又应了两句古诗:“乡书不可寄,秋雁又南回。”伤心失望的伙伴,终于拉我上街喝酒消气。席间,他赌咒发誓说:“今后只要远远地看见她,我就折路回头!”幸好那阵子我怕惹出什么乱子,便尽心尽力地劝慰了他好几番,还将一本当时的禁书《第二次握手》借给他,为他化解心中郁闷,帮助他度过了心思茫然又烦恼的青春时光。如今想来,这就是单相思最好的结果吧?
岁月更迭,人世沧桑。许多年过去了,伫立在小街上的邮筒,承载过多少人间烟火和喜悲过往,以及我的生活经历的点点滴滴。直到后来进城工作的许多年,我还用邮筒投递过一封封给亲人和朋友的信件或明信片。每次投寄毕,离开邮筒,心里就会期盼寄件能尽快到达收件人的手里,有时还会想象远方的人收到信件时的那种高兴和释然的心情。的确,流年深处,我就是以念想为笺,以素心为笔,以邮筒为载体,常常与相知或初识的朋友互相交流。由此,我也常常收到他们的回信,有的言语投契,宛如知己;有的惜墨如金,却一语中的。展读时,往往为其真心融汇,常徒生相见恨晚之叹!
现在,联络用手机,交流用微信,坚持写信的人愈来愈少了。邮局前一些绿色的邮筒,看上去分外沉默。但在我眼里,邮筒依然是一个美好的使者,它满足人们的交流需要,维系人们的情感。如今,它还矗立着,一如既往地接纳着需要它的人。由此,对于安在邮局前的绿色邮筒,以及维护它的人们,我都会在心里表达由衷的敬意。
责任编辑 陈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