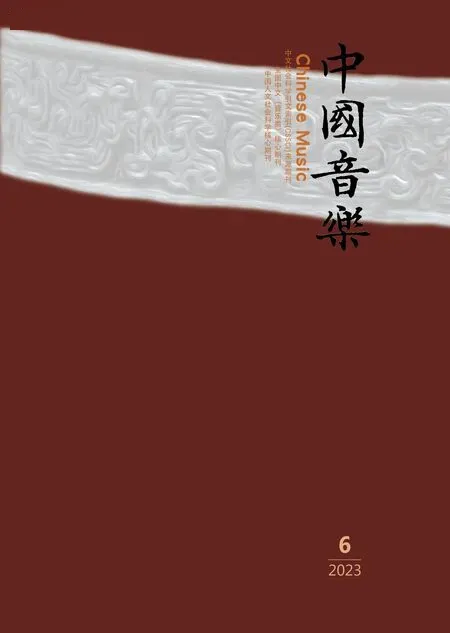中西音乐批评范式的差异与融合
○ 陈艳伟
感性、理性和悟性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三种基本途径,但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理论侧重。一般而言,西方文化侧重理性,西方音乐中的复调、对位、和声、曲式、配器都带有很强的理性特质,西方音乐批评活动也大都把乐谱的理性分析当作基本前提,正如内特尔引述西方音乐学家们的一个典型的说辞:“在我看到乐谱之前,我无话可说。”①沈洽:《描写音乐形态学之定位及其核心概念》(上),《中国音乐学》,2011年,第3期,第7页。中国文化注重悟性,强调对于音乐的直觉体验,因此传统的音乐审美和音乐批评活动常常跳过乐谱,直接针对作品的音响形态进行感悟。如季札评论周乐时所说的“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②蔡仲德注释:《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增订版)》(上),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年,第31页。以及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所说的“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等等。由于中国文化不太注重理性分析,因此,中国传统音乐批评中的措辞不仅简短,而且还具有很大跳跃性,甚至有些不合逻辑,这就和西方音乐批评形成了巨大反差。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中西方音乐批评范式的差异并无高下优劣之分,而是由于看问题的视角不同才形成了“峰”和“岭”的差异。本文拟在于润洋先生音乐学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融入传统音乐批评中的悟性维度,探究一种感性、理性、悟性相融合的三位一体的分析方法。
一、感性和理性:西方音乐批评中的两个基本维度
音乐学分析是1993年于润洋先生在《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和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中首次提出来的。虽然“音乐学分析”和西方传统的“音乐分析”仅有一字之差,但两者在分析的对象、方法和目标上有着显著不同。于润洋先生认为:“音乐学分析则应该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具有综合性质的专业性分析;它既要考察音乐作品的艺术风格语言、审美特征,又要揭示音乐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并作出历史的和现实的价值判断,而且应该努力使这二者融汇在一起,从而对音乐作品的整体形成一种高层次的认识。对一部历史上的或是当代的音乐作品所作的音乐学分析,从性质上讲,它应该是一种广义上的‘音乐批评’,而这种批评应该既是美学的或审美的批评,又是社会—历史的批评。”③于润洋:《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下),《音乐研究》,1993年,第2期,第100页。也就是说,音乐学分析的对象不仅包括了音乐文本,同时也囊括了社会文本,并要设法使这两种互不相干的事物“互相指涉、互相说明,最终到达从音乐的理解过渡到对社会和文化的理解”④姚亚平:《什么是音乐学分析:一种研究方法的探求》,《黄钟》,2007年,第4期,第8页。。由于音乐文本的评价最终取决于感性效果,而社会文本的理解主要依靠理性分析,因此从认识论角度来看,音乐学分析方法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实现了感性与理性的有机融合。
按照常识,感性和理性本来就是协调在一起的,为什么还需要融合呢?原因在于,在专业音乐领域,感性效果与理性分析之间并不总是一致的,在很多时候两者会出现明显的冲突和分歧。宋瑾在《理性分析与感性效果之间的差异》⑤宋瑾:《理性分析与感性效果之间的差异》,《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第5-13页。一文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比如某些序列主义音乐作品,从乐谱分析来看是非常规律和规整的(理性分析),但实际的听觉效果却杂乱无章(感性效果);某些音乐作品从乐谱分析来看似乎中间大两头小、不成比例(理性分析),但在听觉效果上却恰到好处(感性效果)……当理性分析与感性效果之间出现类似矛盾时,音乐批评究竟应该以哪个为根本标准?这就必然涉及感性和理性哪个更可靠、谁才是“第一性”的问题。而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在西方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具有根本性的哲学问题。这个问题自古希腊时期就已在西方文化中出现了:如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水”,这显然是从感性经验得出的结论;而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数”,这就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了;柏拉图的“理念”是理性思辨的结晶,但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则是可感可知的范畴。近代英美哲学中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都把感性经验当作理论基础,而欧洲大陆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则普遍认为所有的经验知识都必须经受理性的批判。
感性与理性在西方文化中的冲突也必然影响音乐领域:中世纪的宗教圣咏和复调音乐强调理性对感性欲望的克制,而游吟诗人歌曲则侧重对世俗情感的表达;古典主义音乐作品体现出理性控制下的感性和谐,而浪漫主义音乐则突破理性的限制来表达情感;序列主义音乐强调理性对于音乐材料的全方位控制,而偶然音乐和印象主义音乐则侧重表现感性的碎片化和模糊性……由于西方音乐实践中普遍存在着感性和理性的分野,音乐学领域自然也会表现出相似的特征,比如见诸报端的音乐评论常常把音乐作品的感性效果作为评价的依据。而作曲领域的“音乐分析”则是一种技术性的、工艺性的理性分析,无论是和声曲式分析、“申克分析法”“音集集合分析法”等等都是如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于润洋先生的“音乐学分析”才表现出重要的学术价值,因为这一方法正是要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缝合西方音乐文化中感性与理论之间的千年裂隙。下面笔者就以于润洋先生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和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为例,具体说明音乐学分析方法是如何将感性和理性融合起来的。
在分析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和终曲时,于润洋先生从技术分析、审美分析、史学分析和艺术批评四个层次来逐步拓宽音乐分析视野。其中,技术分析属于理性维度,审美分析属于感性维度,史学分析和艺术批评则对上述两个维度进行的理论综合。技术分析以乐谱为出发点,着重阐述音乐作品构成上的技术要点。如谱例1为该剧前奏曲中的一个音乐主题,于润洋先生对此的技术分析是:该音乐主题“在由一个不协和和弦解决到另外一个不协和和弦的和声背景上,漂浮着一个半音进行的短小旋律型。这样构成的一个乐句,相继在其上方的大二度和小三度上两次模进,和声的功能关系在向上方扩展,配器的音响在增厚,力度也在递增”⑥于润洋:《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上),《音乐研究》,1993年,第1期,第41-42;44页。。
谱例1 瓦格纳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中的第一个音乐主题

一般的曲式分析和“音乐分析”主要就是进行类似的技术分析工作,于润洋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探讨了作品的实际听觉效果,这就是审美分析:“在《前奏曲》长达十几分钟的音乐中,作为核心性的a小调主和弦始终没有出现……它使听者在感受它的过程中形成这样一种心理体验:似乎总是在期待着什么,渴望着什么,然而却又总是找不到归宿,得不到解脱。而在瓦格纳的这部音乐故事中,正是这种没有尽头的期待和渴望自始至终折磨着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这两颗不安、焦虑的心灵。”⑦于润洋:《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上),《音乐研究》,1993年,第1期,第41-42;44页。
如果说技术分析隶属于理性维度,那么审美分析显然就是一种感性体验了。如何把这两个维度进行综合呢?于润洋先生通过历史(纵向)和社会(横向)视角的比较进行了历史分析和音乐批评:“比如,他在分析‘特里斯坦和弦’时,谈到波兰音乐学家布罗纳夫斯基的‘肖邦和弦’;分析半音和声时,涉及巴赫的钢琴平均律赋格;分析结构时,列举了历史上序曲与戏剧风马牛不相及的情况种种。类似的情况在论文中还可以找到很多。这种论述方式除了加强形式描述的历史感以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形式分析的工艺化倾向,将历史描述(以及审美描述)与形式分析交织在一起,夹叙夹议,为化解音乐文本与社会文本分离起到了重要作用。”⑧同注④,第9页。
由上可知,于润洋先生的“音乐学分析”并没有纠结于感性和理性哪个更可靠、谁是“第一性”的问题。因为这一方法的哲学立足点并不是认识论,而是基于历史、社会和文化视野下的实践辩证法。关于这一点,于润洋就曾明确指出,“我的这种看法(指音乐学分析)来自我们的一位先哲—恩格斯”⑨同注③。。也就是说,音乐学分析是站在社会历史实践的立场上统一感性和理性分歧的,其目的不只是为了获得关于作品的客观认识,而是要借助音乐作品获得关于社会、历史、文化和生命层面的高层次体验,因为“真正的音乐应该是生命体验的真实袒露,是心灵—情感的一面镜子”⑩于润洋:《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1-2页。。这种对于音乐存在方式和音乐批评范式的理解与中国传统音乐批评所强调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音乐学分析虽然是一种从西方文化中发展出来的音乐批评范式,但同时也为中国传统音乐批评的融入提供了理论空间。
二、感悟“弦外之音”:中国传统音乐批评的审美追求
强调“言外之意”和“弦外之音”是中国传统音乐批评的一个根本特征,也是其区别于西方音乐批评的一个重要标志。在音乐学分析中,以音乐文本为出发点,通过技术分析、审美分析、历史分析和艺术批评的层层解析,人们就能够透过音乐文本理解音乐之外的社会文本。由于社会文本并不直接表现在音乐中,而是被音乐文本所指向、象征和暗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音乐学分析中的社会文本也可以看作是音乐作品的“言外之意”或“弦外之音”,这是现代音乐学分析和中国传统音乐批评的相通之处。比如本文开篇时提到的季札的音乐评论:“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其实质就是从音乐文本的审美分析直接跳跃到了社会文本中。当然,严格来讲,音乐学分析中的社会文本还不是中国传统音乐批评中的“言外之意”。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言外之意”和“弦外之音”是有专门的、特定指向的。它们和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中的“道”“大音希声”“天人合一”具有密切的关系,都是指宇宙自然、社会历史和生命活动的本质性存在。也就是说,所谓“言外之意”和“弦外之音”并不是指社会文本,而是指社会文本(也包括历史文本和生命现象)的本质。
中国文化认为,社会自然和生命活动的本质是无法通过理性分析获得的,它只能通过“感悟”的方式,也即感性与悟性的共同配合来得到。比如孔子曾感叹:“四时兴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⑪《论语·大学·中庸》,陈小芬、徐儒宗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14页。(《论语·阳货》)大意是说,天地的奥秘已经通过春夏秋冬和万物生长表现出来了,不需要用理性的语言诠释,直接用感官去感受、用悟性去体会就可以了。《老子》第一章中也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⑫《老子》,饶尚宽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页。其含义是说,作为宇宙和生命本质的“道”是无法用理性分析和表达的,一旦用理性的语言表达出来就不再是“道”本身,而只是一种文字躯壳。其中的道理也不难理解,我们可以举出一个浅显的例子,比如你在聆听音乐时产生了某种感受,你怎样用理性语言去表达呢?无论你用“高兴”“悲伤”“兴奋”等哪一种言辞都只能说出一个粗略的概况。究竟是怎样地“悲”、怎样地“喜”,每个人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连最表层的感性体验尚且如此,更何况是世界和生命的终极本质呢?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粗精焉。”⑬《庄子》,方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60页。(《庄子·秋水》)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音乐创作和音乐批评都不强调理性,而是把重点放在了感性和悟性上来。其音乐创作的一个基本思路是:通过音乐材料塑造出指向某种“言外之意”的“意象”“意境”,让人们通过感性和悟性来直接感悟之。这样审美者就可以越过粗糙的、不精确的理性分析而直接领悟作品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中国传统音乐批评常常体现出很大的思维跳跃性,主要就是越过理性思维直接进行感悟的缘故。对于感性和理性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因此,下面笔者再阐述一下悟性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朱良志教授在《中国美学中的悟性说》中有详细阐述。该文认为:“妙悟活动(即悟性)是在无思无虑无喜无乐的状态下进行的,通过理和情的排除而恢复灵魂的觉性,恢复生命的活力和智慧。妙悟活动以人本来具有的生命智慧来观照,生命的本元性就是推动妙悟活动的动力因素。这个本元的觉性即中国美学中常说的‘悟性’。”⑭朱良志:《中国美学中的悟性说》,《齐鲁学刊》,2003年,第6期,第5页。笔者认同这一看法,但由于“灵魂的觉性”“生命智慧”“本元的觉性”等措辞带有一定的文学性和隐喻性,其本身就包含着需要“悟”的内容,因而给人感觉还不够明晰,所以下面笔者就转换一种更加清楚的表述方式:
所谓“悟”是“心”和“吾”的组合,其直接含义是“我的心”。这个“心”既不是指肉体的心脏,也不是现代人常说的意识,而是指一切心理活动和精神活动的本体,古人称之为“心性”“本性”“佛性”,现代心理学称之为“潜意识”。如孟子的“性善论”认为,恻隐之心、善恶之心、恭敬之心不是后天学习来的,而是从人们自出生之时就本来具备的(“我固有之”)⑮《孟子》,方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18页。原文如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禅宗中的“明心见性”也不是指人们的表层意识,而要求人们透过表层的感性和理性,寻找到一切心理活动和精神活动的真实本体。由于心性本体在大多数时候是潜藏着的、隐微难见的,所以它和西方现代心理学中提到的潜意识是大体一致的,由此本文将悟性能力解释为潜意识的认识功能,这样更便于现代人的理解。当然,西方文化中的潜意识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性”“佛性”等范畴虽具有相通性,但并不完全相同。中国文化中的“心性”和“佛性”一般指已经彻底净化之后的潜意识,而不是指常人的,那种存储了很多负面心理能量的潜意识。然而,无论潜意识是否经过净化,悟性始终是隶属于它的认识功能,只不过净化之后的潜意识悟性能力较强,而未经净化的潜意识则悟性较弱罢了。这就好比干净的镜面照物的能力更清晰,而污秽的镜面照物比较模糊,但无论干净还是污秽,照物的功能都隶属于镜面一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潜意识与中国传统的心性范畴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本文暂不做严格区分,因为这并不影响本文对于悟性功能的探讨。
朱良志先生认为悟性是在“无思无虑无喜无乐”的情况下发挥作用的,其原因就可以从潜意识的角度进行解释:当表层意识中的感性和理性发挥作用时,潜意识的悟性功能就被遮蔽起来了,就好像白天的阳光会把浩瀚的星空遮蔽起来,只有日落西山之后,璀璨的星光才会显露出来一样。传统道家哲学中的“心斋”与“坐忘”、佛教中的“止观”和“禅修”等方法,其原理就是要通过暂停表层意识的活动(无思无虑无喜无乐)来训练和增强潜意识的悟性功能。关于感性、理性和悟性之区别与联系,笔者简要列表如下。(见表1)

表1 感性、理性和悟性功能对照简表
结 语
本文探讨了一种理性、感性和悟性三位一体的音乐学分析方法,这一方法由于综合了中西方音乐批评范式的特色和优点,具有较强的理论普适性。它不仅适合于分析具有中国特质的、“文以载道”的音乐作品,而且对于西方音乐作品也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从认识论角度看,无论西方音乐是否注重悟性维度,悟性作为人类潜意识的认识功能一定是普遍存在的,这就如同中国传统文化不太注重理性,但中国人同样具备理性是同样的道理。关于这个问题,于润洋先生在音乐学分析方法提出二十年之后撰写了《试从中国的“意境”理论看西方音乐》⑯于润洋:《试从中国的“意境”理论看西方音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第3-9页。一文,专门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境”在西方音乐作品中的表现,并认为西方音乐创作中虽然并没有采用“意境”这样的术语,但同样存在着同质性范畴,存在着超越于社会历史现象之上的哲理内涵。这一研究方向是十分耐人寻味的。音乐学分析毕竟是一种来自西方的音乐批评范式,它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音乐作品仍存在“水土不服”之处。用中国“意境”理论去反观西方音乐作品,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要用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现代音乐批评范式进行理论改造和理论完善。由此可知,本文在现有的音乐批评范式中融入悟性维度是完全符合于润洋先生提出音乐学分析方法的本意和初衷的。由于融入了悟性维度的分析方法充分发挥了人类表层意识与深层潜意识的双重认识功能,它对于中西方音乐作品的解析和阐释都是同样适用的,该方法有助于我们对中西方音乐作品展开更加充分全面的分析,有助于人们从音乐作品中获得更加综合性的、高层次性的理解、认知和深度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