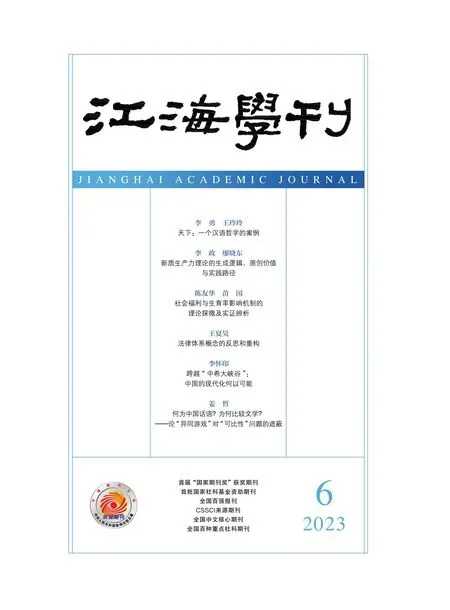法律体系概念的反思和重构
王夏昊
在中国法学话语中,我们常常面对下列两对概念各自之间的区分问题:法的渊源中的“宪法”与法律体系中的“宪法”之间如何区分?法的渊源中的“行政法规”与法律体系中的“行政法”有何不同?这些问题关系着法律体系观的塑造与法理学理论解释能力的提升,也成为法理学中日用而无感之问题的典范。但是,随着法典化进程的推进,部门法学者关心的法律体系概念不重视这些问题,而中国法理学通常所谓的法律体系,即由部门法作为构成要素的法律体系,又面临划分标准上的不充分性,以至于无法彻底回答这些问题。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法律体系概念本身的理解。因此,本文第一部分处理部门法的划分问题,即对中国法理学中关于部门法划分的主流观点进行反思;第二部分论证法律体系的性质;第三部分论证现代社会的法律适用为何必然需要法律体系;第四部分对中国法学话语中常常混淆的术语及有争议的问题予以厘清。
法律体系的构成要素的区分
中国法理学的主流观点认为,法律体系是由部门法(也称法律部门)所构成的统一有机整体,而部门法是指根据一定的标准对法律规范进行分类而形成的同类法律规范的总和。通说按照两类标准对法律规范进行分类以形成部门法:(1)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2)法律规范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方法。
按照第一种分类标准,部门法被进一步定义为调整同类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但是应该如何通过对社会关系的分类而划分出通常所谓的部门法呢?有的教材认为:“人们可以将社会关系分为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宗教关系、家庭关系等,当这些不同领域的社会关系成为法律调整领域之后,它们便成了法律部门形成的基础,而调整不同领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又形成了不同的法律部门。”(1)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9页。这种观点在实质上是按照社会关系的领域或内容对社会关系进行分类的。但是,按照这个标准对社会关系进行分类并不能形成通常所谓的部门法,因为我们不能主张下列命题:凡是调整政治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形成一个部门法即政治法,凡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形成一个部门法即经济法,等等。更进一步,这种分类会面临两个不可解决的问题:一方面,按照这个标准对社会关系进行分类会形成很多甚至无数种类的社会关系,进而划分出许多不同的部门法,这必然会产生部门法在种类和数量上的不确定性,进而与划分部门法的目的以及所形成的法律体系的功能相背离。另一方面,前述以社会关系的领域或内容为标准对社会关系进行的分类与法学中通常所谓的宪法、行政法、民法、商法等部门法在经验层面并不一致。
那么,这些部门法是按照何种社会关系标准形成的呢?有人认为是按照社会关系的不同性质形成的,例如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2)雷磊:《法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3页。这种观点所谓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实质上是指社会关系之中双方主体之间的地位。但是,按照这种标准,我们仅仅只能区分出两种社会关系,即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只能区分出两类部门法,即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与调整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该教材并没有明确指出这两类法律规范总和的名称,而只是通过举例表明,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属于民法这个部门法,调整不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属于宪法这个部门法。总之,根据社会关系的性质划分部门法的做法并不能清楚且完备地区分出法学中通常所谓的部门法。
通说认为,仅仅按照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而划分部门法不能完整地划分出法律体系原本应该包含的一切部门法,因此,还需要按照法律规范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方法来进行。刑法作为一个部门法就是根据其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方法的独特性而形成的。问题在于,除了刑法这个部门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部门法是按照调整方法而被划分出来的呢?前文引述的那两本法理学教材对该问题都作出了肯定回答。前一本教材认为“可将凡属以刑罚制裁方法为特征的法律规范划分为刑法部门,将以承担民事责任方式的法律规范划分为民法法律部门”。(3)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三版),第129页。这个观点面临两个问题:一方面,作为独立的部门法的民法到底是按照调整对象的标准而划分的,还是按照调整方法而划分的呢?至少主流的法学观点都主张是前者。另一方面,这个观点中关于民法的划分违背了逻辑,即存在同义反复,因为唯有划分出了民法这个部门法才可能有所谓的民事法律规范,有了后者才可能有所谓的民事违法行为,有了民事违法行为才可能有所谓的民事责任。后一本教材认为商法和经济法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交往关系”,后者调整的是“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管理关系”。同时,该教材认为商法与经济法之间的区别在于它们各自对经济关系的调整方法的不同。(4)雷磊:《法理学》,第53页。这种观点同样有前后矛盾之嫌,因为该观点既承认调整对象的性质差异,也承认调整方法之不同。
部门法划分标准之所以如此混乱,原因在于中国法理学是按照两个不同标准对同一个对象即法律规范进行分类的,所以划分出来的类别必然是相互交叉的。但是这种情况与法律体系本身的概念相背离,因为法律体系之所以被称为体系就在于它的构成要素是相互和谐和有机统一的。所以,中国法理学按照两个不同标准对法律规范进行分类而划分部门法在理论上存在不足。至此自然就会产生一个新问题:中国法理学为什么要按照两种不同标准对法律规范进行分类而划分部门法呢?
要想回答前述问题,首先要强调的是:由诸如民法、商法、宪法、行政法等部门法所构成的法律体系的概念本身是大陆法系的概念。大陆法系的法学对部门法的划分并不是直接按照一定标准对法律规范进行分类而划分出一个个具体的部门法,而是首先采取了“二分法”,即按照一定标准将法律区分为两大部门法:公法和私法。这里所谓的区分标准是什么呢?大陆法系的法学理论提供了五种标准:(1)公共当局主体论,(2)主从关系论,(3)强制规范论,(4)利益论,(5)折中论。折中论将前四种标准进行合并,其中的主流观点是将公共当局论和主从关系论相合并。(5)René David, et al., “Structure and the Divisions of Law”, in René David, eds., The Legal Systems of the World: Their Comparison and Unification, Tübingen: Mohr Siebeck, 1971, pp.22-24.虽然在理论上公私法的划分存在着不同的标准,但是,“这种划分在大多数大陆法学家看来是基本的和必要的,从法律制度的整体来看也是明确的”。(6)[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第二版),顾培东、禄正平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虽然公私法的划分标准在理论上存在着争议,但是,大陆法系各个国家——无论在法国还是德国——普遍认为:公法包括宪法与行政法,私法包括民法与商法。就公法而言,宪法是行政法的基础,没有宪法,行政法无从产生,缺乏指导思想,至多不过是一大堆零乱的细则;行政法是宪法的实施,是其动态部分,没有行政法,宪法就完全可能是一些空洞的僵死的纲领。(7)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就私法而言,商法是私法的一个特别部门法,如果商法典的成文法规中没有专门的相关民法规范和原则的条文时,民法可作为“普通法”适用于商事行为。由此可见,大陆法系在划分出公法和私法两大部门法之后,又按照一般和特别的标准,将公法区分为宪法与行政法,将私法区分为民法和商法。此外,大陆法系的法学理论又按照实体和程序的标准将法律区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我们前述的宪法和行政法、民法和商法都属于所谓的实体法,跟这些实体法相对应的程序法是行政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
但刑法并没有出现在这种划分中。因此,现在的问题是:按照大陆法系的公私法的划分标准,作为部门法的刑法属于公法还是私法呢?法国认为刑法属于私法,德国认为刑法属于公法。这两个国家之所以会有不同看法,主要因为两个国家的法学家对刑法中的两个基本范畴在刑法中的地位看法不同。我们一般将刑法定义为:所有规定犯罪和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因此,刑法中的两个基本范畴是“犯罪”和“刑罚”。犯罪本位认为,一个人的行为是犯罪,因此,应该对该人施加刑罚。刑罚本位认为,一个人的行为之所以是犯罪,这是因为该人的行为是值得刑罚的行为。法国法学主张前一种观点即“犯罪”处于本位,而规定“犯罪”的法律规范旨在调整社会关系,所以虽然刑法具有公法性质,但是因为它有许多条款是调整私人关系的,这就决定了刑法属于私法。德国法学主张后一种观点即“刑罚”处于本位,同时认为“刑罚权”属于一种国家权力即公权力,因此,刑法属于公法。同时,刑法也是一种实体法,与此相对应的程序法是刑事诉讼法。
所以,法学中所谓的部门法并不是直接通过按照法律规范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等标准而划分出来的。这也许就是中国法理学不能清楚地、确定地、完整地划分出各个具体的部门法的根本原因所在。一方面,大陆法系法学按照法律规范的调整对象即社会关系的分类而划分部门法,但是,它们对社会关系的分类永远是二分的,即使不同的人是按照不同标准对社会关系进行二分;相反,中国法理学是直接通过对社会关系进行不同分类而划分出部门法。另一方面,法理学教材按照法律规范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方法而划分部门法,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划分出刑法这个部门法。之所以认为刑法是一个独立部门法就在于它是运用刑事制裁方法即刑罚来调整或保护社会关系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法理学类似于德国法学,即“刑罚”处于本位。但是,正如前述,德国通过这一观点来确定刑法是属于公法还是属于私法;中国通过这一观点来证明可以按照调整方法的标准而划分出独立的部门法。这也许是中国法理学对划分部门法的理论作出的一个贡献。但是,问题在于:同时按照不同标准对同一个对象进行分类而形成的要素之间必然无法满足追求统一性之体系的要求。
法律体系的性质
法律体系是通过对法律规范进行分类而形成的部门法所构成的统一有机整体。法律规范是法律的基本细胞;法学家们根据一定的标准对法律规范进行分类形成各种部门法,这些部门法又构成一个统一有机的整体,即法律体系。这样的一种思想是伽利略所开创、笛卡尔最终完成的分析综合方法运用的结果。分析综合方法就是运用分析方法来寻找基本元素,并且试图从这些基本元素出发来解释一切其他事物。这种方法实质上是人类努力摆脱其有限经验的束缚,将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加以理想化或观念化的尝试。(8)倪梁康:《自识与反思——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6—13页。这是我们理解法律体系性质时的基本前提。
无论是公法和私法、一般法和特别法、实体法和程序法,还是宪法、刑法、民法等具体的部门法,它们本身是一系列的概念。法律体系也是一系列概念所构成的体系。概念既不是物也不是事件,它是物或事件的表象(representation)(9)Howard Caygill, A Kant Dictionar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5, p.118.或精神陈述。(10)[美]威廉姆·沃克·阿特金森:《逻辑十九讲》,李奇译,新世界出版社2013年版,第18页。但是,概念不是对一个物或一件事情的表象或精神陈述,而是对一切同类事物或事件的表象或精神陈述。例如,“动物”这个概念是包括了一切动物的各种特性的抽象性观念。因此,概念也不是人对物或事件的一个意象或图像。事物或事件的意象或图像是人的感官可知觉的,是一个反映真实事物或事件的精神产品。但是,概念本身不是人的感官可知觉的,而是思想的替代物,是一个反映同类物体或事件共同属性的纯粹想法或观念。(11)[美]威廉姆·沃克·阿特金森:《逻辑十九讲》,第39—42页。所以,当我们说宪法、刑法、民法等是概念时,它们各自既不是特定国家所制定的一个个法律文件,也不是这些法律文件的集合,因为这些法律文件的集合都是人们的感官可知觉的。这就意味着法律体系本身不是特定国家所制定的一切法律文件所组成的集合体本身,即使这些法律文件按照一定的原则构成了一个统一体。既然法律体系与规范性和非规范性法律文件所组成的体系不是同一回事,那么,它们之间有没有关系呢?如果它们之间有关系,这种关系是什么呢?
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指出:“‘私法’和‘公法’的概念只是先验意义上的概念。”(12)[德]G.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王朴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页。在德国哲学中,先验概念又被称为纯粹概念,与它相对应的是经验概念。一个概念要么是先验概念要么是经验概念。先验概念仅仅在知性中有其来源,而经验概念是从许多经验中抽象归纳出来的概念。前者具有严格的普遍性,后者具有相对的普遍性。严格的普遍性是指先验概念的有效性与特定时空下的事物和事件没有关系,它可以适用于任何特定时空下的事物和事件。相对的普遍性是指经验概念的有效性只存在于特定时空下,它只能适用于特定时空下的事件和行为,即使它能适用于我们迄今能观察到的一切事物和事件,但是它的有效性也不能保证不会出现例外。先验概念与经验概念都适用于经验的事物或事件,后者来自经验因此不可能超越经验,前者不依赖于经验因此可以超越经验,但是如果它超越了人的一切可能经验之外,它就不再是先验概念了。(13)[德]康德:《康德三大批判合集》,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40页。在世界范围内的法学中,如果说“私法”和“公法”是先验概念,那么,英美法系之中的“普通法”和“衡平法”就是经验概念。因为后一对概念是在英国法律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依次在特定时空下产生的,这对概念只能适用于英美法系的法律分类而不能适用于其他国家的法律分类;相反,“私法”和“公法”这对概念不仅被大陆法系沿用,而且英美法学家,如霍兰德和萨尔蒙德,也用它们来区分“普通法”或“衡平法”中对应于私法和公法的内容。
因为,特定国家的实证法是处于特定时空之下的,是经验性的,所以,“私法”和“公法”的概念“不是实证法的概念,它也不能满足任何一个实证的法律规则,当然,它可以为所有法律经验做先导,并且从一开始就为每一个法律经验主张有效性。”(14)[德]G.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第127页。作为先验概念,“私法和公法的区分已经在法律概念自身中被确定了。如果由立法机关为个体共同生活制定的规则,也就是私法规则真正满足了所有私法的存在基础——法的安定性,那么,立法机关自己也就必然与法的安定性紧密相连了——但是立法机关和与其相对的法律受众之间的联系,即掌权者与隶属者之间的联系一定是公法关系”。“私法和公法的区别不仅仅存在于法律概念之中,而且也存在于法律理念之中。如果正义要么是矫正正义要么是分配正义,也就是说,正义不是被平等地划分者之间的正义,就是掌权者与隶属者关系中的正义,那么,正义自身就已经指明了它的两个基石,即公法和私法。”(15)[德]G.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第128页。与“私法”和“公法”的概念一样,一般法和特别法、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概念都是先验概念而不是经验概念,按照它们区分出的部门法概念即宪法、刑法、民法等概念也是先验概念而不是经验概念。因此,法律体系其实是一系列先验概念的体系。
既然法律体系是先验概念体系,那么,各种部门法就是一系列认识论的概念或范畴。因为“先验”与其说是处理对象的,不如说是处理知识的认识方式的。(16)[德]康德:《康德三大批判合集》,第16页。一方面,既然这些先验概念是认识论的范畴,它们就必然被运用于特定国家的实在法;离开经验的特定国家的实在法,这些先验概念就成为空洞的和无实质意义的概念或范畴体系。另一方面,我们要想获取经验的特定国家的实在法的知识必须凭借着这一系列的先验概念;离开了这一系列先验概念,特定时空下的特定国家的那些实在法就成为无逻辑的、缺乏内在一致性的、杂乱的一系列规范性法律文件或非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聚集体。这一系列先验概念对于我们对特定时空下的特定国家的实在法的认识或知识来说就是构成性的而不是调整性的。同时从这两个方面看,特定时空下的特定国家的实在法只是该国家的法律体系的质料,而这一系列先验概念本身的体系是该国家的法律体系的结构形式。当我们说到特定时空下的特定国家的法律体系时,该法律体系同时包括了质料和结构形式,它是两者的统一体。任何特定时空下的任何特定国家的法律体系在结构形式方面是相同的,但是,它们各自的具体内容是不同的。
所以,法学中通常所谓的一个个具体部门法作为概念是先验概念或认识论范畴,它们是普遍的,是认识对象的形式;任何特定时空下的特定国家的实在法是质料,它们是具体的,具有杂多性。两者各自的这些特性就导致了现实中下列情况的发生:当前者之中的一个概念被适用于后者时,尤其适用于特定时空下的特定国家的一个具体的实在法时,具有普遍性的前者并不能将具有杂多性的后者的一切内容或特性涵摄在其下。这种情况或现象就是法学通常所谓的一个领域中的法律处于私法和公法之间的混杂状态之中,例如劳动法和经济法。但这种混杂状态不足以否定部门法划分本身,因为就劳动法和经济法而言,“如果想借助于社会矫正的方法,通过一个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权力来支援社会弱势群体,限制强势群体的话,那么,公法和私法就必须可以区分但又不可割裂地并存于这两个群体之中”。就整体而言,“只有通过由那种法律规则订立的公法和私法彼此并立关系和法律规则划分为私法和公法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方法,一项法律规则的特点才能够非常明确地表达出来”。(17)[德]G.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第130页。
既然特定国家的法律体系是通过将那一系列先验概念运用于该国家现行有效的实在法而形成的或被建构出来的,那么,这就意味着特定国家的法律体系是该国家的法学尤其法教义学对该国家的现行有效实在法的重新阐释而形成的。如果说法社会学、法史学等其他有关法的学科均系概括地研究“法”这个标的的话,法教义学原则上针对当时的、特定的法秩序。如果它想维持其法教义学的角色,不仅必须假定现行法秩序大体看来是合理的,而且必须假定它所研究的素材具有一定的内在秩序。法教义学的工作目标就是“发掘规范内在的一体性及其一贯的意义关联”。(18)[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76—77、120页。与其他学科相比,法教义学的任务特殊性在于对特定国家的现行有效的实在法进行解释并将其解释结果体系化。
既然特定国家的法律体系是通过法教义学被建构的,那么,它就具有理想的维度。因为法教义学不仅包括一个由诸概念所构成的概念之网,这些概念是由一系列基本观念、安排这些观念之间关系的原则以及运用这些观念所凭借的推论规则所组成的,而且包括诸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的规范性基础。这个概念之网和规范性基础总是奠定在一定的思想形态背景假定的根基之上。(19)Aulis Aarnio, Essays on the Doctrinal Study of Law, Dordrecht: Springer, 2011, p.178.另一方面,特定国家的法律体系也具有实在维度。因为特定国家的法律体系的质料或内容是特定国家在特定时空下的现行有效的实在法。因此,任何特定国家的法律体系既具有一个理想的维度也具有一个实在的维度。这样的双重性维度就使得任何特定国家的法律体系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也具有一定的变化性。特定国家的法律体系的稳定性是由它的理想维度所保证的。因为作为科学的法教义学所包括的概念、规范性基础及思想形态背景假设是相对不变的,如果这些东西变化,法教义学作为科学就会产生革命性的变化。
法律体系的必然性
我们通过前述的内容可以看到,特定国家的法律体系的构建既不是立法者的任务也不是司法者和执法者的任务,而是法学家的任务。因此,有人就会提出下列问题:特定国家的法律实践(包括法学实践)为什么需要通过法(教义)学对该国家的具有杂多性的现行有效的实在法进行重新阐释而予以体系化呢?美国法学家兹拉蒂兹认为,法律体系化有利于法学研究和教学,使得法典化成为可能,使得将案件进行分类进而划归不同类法院管辖成为可能,并为现行有效实在法的解释奠定理论基础。(20)René David, et al., “Structure and the Divisions of Law”, in René David, eds., The Legal Systems of the World: Their Comparison and Unification, p.15.瑞典法学家阿尔尼奥认为,法律体系化的理由有:(1)法律体系化会生产出对众多法律规范的一个概览。现代社会中的任何特定国家都存有许多有效的法律规范,这些规范依赖效力位阶联结成整体。(2)法律体系化是法律思想追求效率的体现。法律的体系化可以节省时间和精力,法律人不用在适用他们所属国家的某一部分现行有效实在法时重新分别阐述规范整体。(3)法律体系化使得法律思维具有精确性。法律的体系化使法律人获得了一面洞察规范整体的透镜,使得对最终决定所要选择的法律解释结果的确认成为可能。(21)Aulis Aarnio, Essays on the Doctrinal Study of Law, p.177.两位法学家都从功能角度出发证立了法律体系的必要性。但是,功能角度并不能证成特定国家的法律实践为什么必然地需要法律体系的问题。因为,一方面,这里所谓“必然地需要”是指特定国家的法律实践在客观上必需法律的体系化。另一方面,从法律体系的功能角度回答为什么需要法律体系,这只能提供一系列经验论据;而经验论据只能保证它所证成的命题的一般性而不能保证它所证成的命题的普遍性,即不能保证它所证成的命题不会出现例外,一个命题不具有普遍性也就不具有必然性。如果特定国家的法律实践并不必然地需要法律体系,那么,这就意味着法律体系是可有可无的;如果法律体系对于法律实践是可有可无的,那么,这就意味着法教义学是可有可无的——因为法律体系是通过法教义学而被建构的。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与前述两位法学家的观点不同,本文不仅仅要回答特定国家的法律实践为什么需要法律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回答特定国家的法律实践为什么必然需要法律体系。回答该问题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方面,这里所谓的“特定国家的法律实践”仅仅是指特定国家的法律适用,即特定国家的法律人将该国的现行有效实在法适用于特定案件事实作出正当法律决定。因此,这里所要回答的问题就具体化为下列问题:特定国家的法律人适用法律时,为什么必然需要法律体系?另一方面,特定国家的法律实践是指现代社会中的特定国家的法律实践而不包括传统或古代社会中的法律实践。这就意味着,传统社会中特定国家的法律实践不需要法教义学将其所属国家的现行有效实在法体系化。
因此,这里要回答的真正问题就变成:为什么现代社会中特定国家的法律适用必然需要法律体系?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明白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的区别。这里需要按照法律与法律适用的不同特性对它们进行区分。按照涂尔干的观点,传统社会是一个分化程度比较低的机械团结的社会,这种社会的运作依赖于一系列僵硬的、构成具体的规则,这些规则建立在制裁的基础之上,它们的适用是以一种不考虑具体个案特殊情形的权威方式而进行的。现代社会是一个按照劳动分工而被组织起来的有机团结的社会,这种社会的运作依赖于一系列抽象规范,而这些抽象规范是以一种“自由”方式而被适用于非常不同的具体情形之中。(22)Klaus Günther, “Impartial Application of Moral and Legal Norms: A Contribution to Discourse Ethics”, in Universalism vs. Communitarianism: Contemporary Debates in Ethics, Ed by David Rasmussen, The MIT Press, 1990, p.201.传统社会的法律是由一系列被暂时一般化、实质一般化和社会一般化的法律规范组成,即实质合理性的法律,这些法律规范的有效性仍然跟一个群体或共同体的具体语境关联在一起,这个语境保证了这些规范在一系列清楚的语境中被适用的适当性。因此,就法律适用的特性而言,虽然立法和司法在传统社会中已经在制度上分离了,但是,决定法律规范有效性问题的机关即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规范的同时已决定该法律规范在可能的一系列清楚语境中被适用的适当性。也即,法律规范的有效性的证成与法律规范适用的适当性的证成在传统社会中还没有分离。现代社会中的法律是由一系列抽象的法律规范组成的,法律规范的有效性与特定的语境相分离,即形式合理性的法律;因此,就法律规范适用的特性而言,法律规范的有效性不能保证它们各自在具体情形中被适用的适当性,它们在被适用时必须按照公正适用的观念而确立它们被适用的适当性。也即,法律规范的有效性的证成与法律规范适用的适当性的证成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分离。(23)Klaus Günther, The Sense of Appropriateness: Application Discourses in Morality and Law, Translated by John Farrell,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p.256.这样,根据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在法律适用上的区分,问题就转换为:法律规范适用的适当性证成与法律规范的有效性证成之间的分离为什么必然需要法律体系呢?
正如前述,现代社会中的法律是抽象的或形式理性化的法律。因此,现代社会的法律规范的有效性与特定语境相分离,法律规范的有效性只会考虑它将要可能适用于那些案件相同的情形或条件。但是,一个有效的、可普遍化的法律规范所要适用于的那个具体案件不仅具有该法律规范所规定的那些相同的情形或条件,也一定具有该法律规范没有规定的该案件特有的情形或条件。法律人为了保证他针对该案件所得到的一个法律决定是适当的或正当的,他就不仅要考虑适用案件的法律规范所规定的相同情形或条件,而且要考虑案件中的那些特有的情形或条件。这就导致,对于同一个案件,有两个以上有效的、可普遍化的法律规范都可以适用,也即会发生碰撞。举例来说:甲向他的朋友张某承诺他会去参加张某的生日晚会;但是,当甲准备动身去参加张某的生日晚会时,他的另一个朋友赵某打电话说:他生病了需要甲的帮助。甲是应该去参加张某的生日晚会还是应该去帮助赵某呢?
我们从前述的内容可以得到下列结论:现代社会中的法律特性导致了有效的法律规范在适用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碰撞,而解决碰撞又必然要求特定国家的一切有效的法律规范是一个融贯的体系。但是,这个结论并没有回答,为什么法律体系必须由该国的法教义学来建构呢?一方面,现代社会中的法律规范的有效性的证成是由立法机关承担的,现代社会中法律的抽象性或形式理性化必然要求立法机关对有效性的证成只考虑该法律规范可能适用的一切案件的那些相同情形和条件,因此,不能保证该有效法律规范适用于特定案件的适当性。另一方面,两个以上的有效的法律规范之间的碰撞只是发生在对特定案件的处理过程之中,这就意味着法律规范之间碰撞只能由法律适用者(法官)在单个案件的裁决过程中予以解决。这种解决方案会导致下列双重的偶然性:第一,法律适用者针对特定案件解决有效法律规范之间的碰撞而获得唯一正当或适当的法律决定,他或她必须能够对该案件的一切情形和条件予以完整地描述,而且必须就该完整描述而建构一切有效法律规范的融贯体系,这两者就必然要求法律适用者具有无限的时间和无限的知识。这个无限时间和无限知识的必然要求就是德沃金提出哲学王型法官“赫拉克勒斯”的原因。(25)Ronald Dworkin, Take Rights seriousl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05.但是,现实的法律适用者不得不在有限的时间与知识的前提下解决有效的法律规范之间的碰撞。第二,即使我们假定法律适用者有能力对特定案件的一切情形和条件予以完整描述,并且有能力针对特定案件建构融贯的法律体系,那么,法律适用者也只能每一次针对特定案件而重新建构融贯的法律体系。这就意味着,就特定案件而解决法律规范之间的碰撞所得到的法律决定,对于该法律共同体的每一个人来说不具有确定性或可预测性。这种不确定性或不可预测性跟法律保证人的行动预期的稳定化功能相违背。如何克服法律适用的这个双重偶然性呢?这要求特定国家的法律体系,一方面,提前解释法律规范之间碰撞的典型情况;另一方面,在法律体系之中提前固定证成结论所需的不同论据。这两个方面的要求不仅是法教义学所承担的任务,而且是法律适用为什么需要法教义学的理由。(26)Klaus Günther, “A Normative Conception of Coherence for a Discursive Theory of Legal Justification”, Ratio Juris, Vol.2, No.2, 1989, p.164.
法律体系与法律秩序的区分
正如前述,特定国家的法律体系是通过法教义学对该国家现行有效的实在法的重新阐释而形成的一个统一体。但是,特定国家的现行有效的实在法在体系化之前也是一个统一体,只不过是一个未被体系化或前体系化(pre-systemised)的统一体,即法律秩序(legal order)。(27)Aulis Aarnio, Essays on the Doctrinal Study of Law, p.177.特定国家的那些具有杂多性的现行有效实在法是通过该国家的有权国家机关依据法定程序而制定并公布的。不同国家机关的权力等级是不相同的,因此,不同国家机关依照其拥有的法定权力和程序所制定并公布的实在法的效力大小或等级不同。但是,与其他组织或机构不同,国家是拥有主权的公共组织或机构,而主权是对内对外的最高权力,一个国家只有一个主权者或最高统治者。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法律秩序,在一个法律秩序之内只有一个命令和允许意志,因此,特定国家的不同国家机关依照法定权力和程序所制定并公布的那些具有不同效力等级的实在法之间是统一的。(28)Georg Henrik Von Wright, Norm and Action: A Logical Enquir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3, p.206.
由此可见,特定国家的法律秩序是依据特定实在法本身所具有的效力大小对该国家一切现行有效实在法区分为不同层级而形成的一个统一体;而特定实在法本身的效力大小依赖于制定该实在法的特定国家机关的权力等级而取得。因此,只要特定的一切现行有效实在法是该国家享有不同等级权力的不同国家机关依据各自的权力和程序而制定,那么,由于国家是拥有主权的机构或组织,特定国家的一切现行有效实在法作为一个整体自身必然就是一个统一体。特定国家的法律秩序作为统一体是社会权力运作的结果,是一个权力秩序,(29)Aulis Aarnio, Reason and Authority: A Treatise on the Dynamic Paradigm of Legal Dogmatics, Brookfield: Dartmouth, 1997, p.237.它只是一个纯然事实,只具有实在维度;但是,特定国家的法律体系是通过法教义学对该国家的一切现行有效实在法予以重新阐释而形成的一个统一体,因此,它既具有实在维度也具有理想维度。只具有实在维度的特定国家的法律秩序,不仅给该国家的公民提供行为模式,而且给国家机构解决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冲突提供根据。(30)Aulis Aarnio, Essays on the Doctrinal Study of Law, p. 177.
正如前述,法律秩序是一个不同层级组成的统一体,而且每个国家只有一个主权者;因此,就现代国家而言,一个国家在其主权范围之内只能有一个具有最高效力的实在法(即具有最高效力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特定国家现行有效的宪法典在该国家的法律秩序中处于第一层级或最高层级。紧接着是第二层级的实在法,在当今的中国,它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依据其法定权力和程序制定并公布的规范性文件,即通常所谓的狭义上的“法律”。紧接着是第三层级的实在法,在当今的中国,它是国务院依据其法定权力和程序制定并公布的规范性文件,即通常所谓的“行政法规”。依次,在特定国家的法律秩序之中还可能有第四层级、第五层级的实在法。那么,特定国家的法律秩序之中到底有多少层级的实在法呢?这取决于特定国家现行的政治体制和法律历史文化传统,即使同一国家的法律秩序的层级数量在不同时期也是不相同的。职是之故,特定国家的法律秩序之中的层级数量问题是一个不能脱离特定时间与空间的经验问题。相反,构成特定国家法律体系的那些要素即部门法的种类数量是一个超越特定时间和空间的问题,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之中部门法的种类数量是相同的,因为它们都是先验的概念。
法律秩序的层级呈现出一个金字塔型的格局。特定国家的法律秩序中处于第一层级或最高层级的实在法的数量就一般来说只有一个,第二层级的实在法的效力来自第一层级的实在法的效力,因此,它不能与第一层级的实在法冲突;而且一般而言,处于第二层级的实在法的数量比第一层级的实在法的数量要多得多;后面各层级可依此类推。相反,特定国家的法律体系中的部门法之间的关系不是效力层级关系,这就意味着部门法与部门法之间就它们各自的效力而言是平行关系。具体来说,在特定国家的法律体系之中,我们不仅不能主张作为部门法的宪法的效力高于行政法,更不能主张公法的效力高于私法的效力。其原因在于,部门法之间的区分根源于其背后的不同法观念或法理念。例如,我们可以说私法关注私人自治的观念,而公法特别关注国家行为在实现公共利益上的作用。因为它们各自针对的社会关系不同:私法针对的社会关系是当事人彼此平等的关系,国家只是公断者;公法针对的社会关系是国家作为一方当事人的社会关系,而国家在这种关系中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因此,具有高于其他任何人的权威。(31)[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第二版),第97—98页。
我们现在可以对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问题予以回答了。中国法理学话语中作为法的渊源的“宪法”就是指当今中国的主权范围内具有最高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即1982年宪法典及其修正案所组成的规范性文件。因此,就本文的语境而言,所谓作为法的渊源的“宪法”就是当今中国法律秩序中处于第一层级或最高层级的那个实在法。这个意义上的“宪法”与法律体系中作为一个部门法的“宪法”的意义是不相同的。在中国的法律秩序之中,具有最高效力的实在法或规范性文件只有并且只能有一个。但是,作为法律体系构成要素的部门法的“宪法”所包括的宪法规范涉及1982年的宪法典及其修正案组成的规范性文件,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等。根据前述的法律秩序与法律体系之间的区分原理:我们既不能主张,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这些规范性文件中所规定的法律规范不属于作为部门法的宪法的组成部分;同时,我们也不能主张,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这些规范性文件在中国的法律秩序中具有最高效力或处于第一层级。
同样,我们现在也可以厘清作为法的渊源的行政法规与作为部门法的行政法的不同。前者是中国法律秩序中第三层级的实在法,后者是中国法律体系的一个构成要素。一方面,在中国,作为部门法的行政法包括全部的行政法律规范,不仅仅是“行政法规”这个层级的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法律规范,而且包括了法律秩序中的其他层级的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法律规范;后者的一个例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它所规定的法律规范是构成行政法这个部门法的一部分,但是,就效力等级来说,它属于中国法律秩序之中第二层级的“法律”。另一方面,在中国,行政法规所规定的法律规范有可能属于行政法这个部门法,也可能属于其他部门法;举例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所规定的法律规范并不都是行政法中的法律规范,也有一部分属于民法或者其他部门法。
此外,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厘清中国法学中有关“宪法”与“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如关于宪法的具体化、合宪性解释和合宪性审查等问题的争议。一般来说,中国宪法学界肯定了这三种关系,但是,有人只肯定了这三种关系之中的合宪性审查。(32)陈景辉:《宪法的性质:法律总则还是法律环境?从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出发》,《中外法学》2021年第2期。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将前一种观点简称为“肯定说”,将后一种观点简称为“否定说”。无论肯定说还是否定说都没有对“宪法”和“部门法”进行界定。即使持否定说的学者引用了拉兹关于“宪法”的不同意义:宪法的概念命题、宪法的实在法命题与宪法的价值命题,(33)陈景辉:《宪法的性质:法律总则还是法律环境?从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出发》,《中外法学》2021年第2期。但是,该学者并没有说明这三种意义的“宪法”分别对应于中国法学语境中的哪种意义的“宪法”。为了点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将拉兹关于宪法的三种意义转换为英美宪法学界关于宪法的三种概念:元宪法、作为符号的宪法与作为规范的宪法。元宪法是指特定政治共同体中人们关于何谓善的共同体的生活的观念,包括正义原则、政治道德的其他方面、明智政府的原则,以及为了最大程度实现这些原则的制度安排的观念。作为符号宪法是指表达这些观念或原则的文件或文本。作为规范的宪法是指符号宪法中的一个个宪法条文所表达的意义即宪法规范的组成。(34)Larry Alexander, ed., Constitutionalism: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4.拉兹关于宪法的概念命题相当于作为规范的宪法,宪法的实在法命题相当于作为符号的宪法,宪法的价值命题相当于元宪法。在本文的语境中,作为符号的宪法是指特定国家法律秩序中处于第一层级或最高效力层级的那个宪法,作为规范的宪法是指特定国家法律体系之中作为一个部门法的宪法。
如果中国法学界所谓的“宪法”和“部门法”之间的三种关系中的“宪法”是指部门法,那么,宪法的具体化和合宪性审查这两点就不成立;因为,根据本文关于法律秩序与法律体系之间的区分,作为部门法的宪法和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平行关系。如果中国法学界所谓的“宪法”和“部门法”之间的三种关系中的“宪法”是指特定国家法律秩序中的“宪法”和其他层级的实在法,那么,宪法的具体化和合宪性审查就成立;因为,特定国家的法律秩序是一个统一体,宪法处于第一层级或最高层级的实在法,因此,其他层级的实在法——例如我国的法律、行政法规等——必须以宪法为根据,不能跟宪法相矛盾和冲突。在厘清了这两种关系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合宪性解释在哪种意义上可以成立。如果中国法学界所谓的合宪性解释中的“宪法”是指元宪法,那么,特定国家的法教义学在对该国家的实在法进行解释时必须按照元宪法进行,即合宪性解释是成立的。因为,正如前述,法教义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和实在法的理论,总是建立在一定思想形态或观念形态的背景预设的基础之上,这些背景预设当然包括了特定共同体的人们关于善的共同体生活的观念。这就意味着,合宪性解释的关系不是指特定国家法秩序之中的宪法与其他层级的实在法之间的关系,因为,正如前述,特定国家的一切现行有效实在法作为一个整体自身必然就是一个统一体,即特定国家的法律秩序作为一个统一体是一个纯然事实,它根本不需要解释。
所以,中国法学界之所以对“宪法”与“部门法”之间的关系争议不断,其症结在于,他们既没有区分法律秩序和法律体系的概念,也没有区分“宪法”概念的不同意义。
结 语
相对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而且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因此,现代社会的法律不仅越来越抽象,而且法律实施过程中也更频繁地遭遇疑难案件。所以,现代社会中特定国家的一切现行有效实在法必须通过法教义学的重新阐释而形成一个融贯的统一体,即法律体系。为了特定国家的实在法的体系化,法教义学必须根据法律概念和法律理念将法律区分为各个部门法,而每一个部门法都有其自己的观念和原则。这样,作为法律体系的构成要素的部门法本身是一系列先验概念和认识论范畴。在这个意义上,特定国家的法律体系是认识活动的一个产品,这个认识活动将该国家的法律秩序的内容组织成为观念关系的统一体。(35)Aulis Aarnio, Reason and Authority: A Treatise on the Dynamic Paradigm of Legal Dogmatics, p.237.中国法学界没有从这样一个角度理解和认识法律体系的概念,因此,不仅导致了根据不同标准划分出的部门法之间的重叠和混淆——这跟法律体系概念本身是矛盾的,而且导致法律体系概念与法律秩序概念之间的混淆;后一种混淆不仅进一步导致中国法学界不能对法律中一些概念予以清楚且适当地区分,而且进一步模糊了相关讨论的背景。法教义学作为专门的知识领域跟任何其他知识领域一样,其合理性的前提条件就在于其所必然使用的那些概念之间具有清晰性、一致性和融贯性。(36)Robert Alexy, 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Translated by Julian Riv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p.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