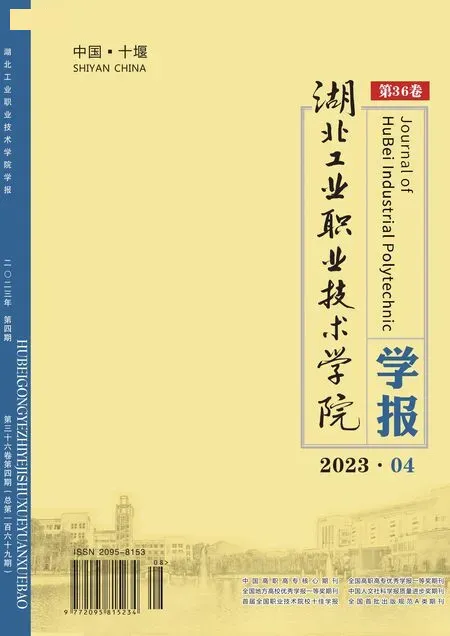打开时间的大门 寻找生命的延续
——郝景芳和蒋方舟科幻小说之比较
罗 樟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科幻文学创作在如今的中国乃至世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未来社会的图景有着或好或坏,或乐观或悲观的想象。郝景芳的很多作品描绘了人们所期望的可能存在的未来世界,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思考和隐忧。与此同时,面对纷繁复杂的时代与社会,面对不曾历经的沧桑与苦难,像蒋方舟这样感觉到被束缚了的80后作家,也不得不寻求另一种表达方式:或许在极致的虚构与想象中更能书写现实潜在的暗流。郝景芳写于2017年的《永生医院》与2020年蒋方舟的新作《边境来了陌生人》《在威尼斯重建时间》,巧合地形成了一种呼应与张力。这三篇中短篇小说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逝去的时间与回忆,涉及到记忆与永生的话题。这些故事所呈现的科技元素或神话元素,离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现实十分遥远,却是作家基于现实所进行的一种推想,最终反过来对现实的事件或思想完成了反思。
一、故事在时间与回忆中
时间和回忆是很多叙事作品的重要关键词。正是在时间的流转中,才有了生老病死的生命历程,才有了可供回忆的内容。在这三篇小说中,故事里带有回忆的内容不仅通过人物表现出对时光流逝的独特感触,还作为叙事的关键因素,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同时,作者还在文本中玩转时间,使得故事读起来充满悬疑色彩,引人入胜。
他人的离世、遭病或失踪,造成叙事时间闪回,从而引发人物对过往时光的回忆,这是《永生医院》和《在威尼斯重建时间》所具有的相似情节。在《永生医院》中,主人公钱睿的母亲已经癌症晚期,生命垂危,被送至费用高昂的妙手医院。当钱睿看着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的脸色蜡黄的母亲,他才开始为自己曾经因工作忙碌而忽略了亲情的陪伴而后悔。《在威尼斯重建时间》的主人公“我”,在等候飞机时收到了父亲去世的信息。当“我”在一周后拿到父亲的照片,父亲那让我感觉到不那么熟悉的样子,激发了二十年不曾归家的“我”关于父亲以及关于母亲的死的回忆。其中“我”与父亲未解的心结也随着父亲生命的消失而重新叩问“我”的心灵。而《边境来了陌生人》的情节是:边境小屋来了一个陌生人,遇上了正在小屋内聚会的四个人,于是五个人开始围桌讲故事,几个故事分别涉及到爱人记忆的缺失,相当于爱人已死;涉及到丈夫的离去和兄弟的死亡等,当每一个人讲述起自己的故事时,真真假假暗藏在其中。
这些在生命中具有独特意义的“他人”就此离开,却恰好引出一段回忆,成就了这些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为了弥补自己曾经没有好好孝敬母亲的遗憾,虽然医院规定家属不可进医院探视病人,但是最终钱睿还是每晚偷偷地成功溜进了医院。妙手医院能够起死回生、妙手回春的案例数不胜数,全国闻名,但是钱睿每一次偷偷去探望时,只感觉到母亲的生命气息分明一天接着一天、一丝丝地流走。直到有一天,他本想回家与父亲商量母亲的丧事,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回到家却看到一个活生生的母亲,好端端地在家吃饭。无论是外貌、服装,还是动作,都向他证明了这就是母亲——正是自认为已经病入膏肓,即将离世的母亲。钱睿不断地回忆自己与母亲的过往,从中寻出所谓的亲情考验题,没想到这个活生生的母亲都能一一“应付”,让钱睿的质疑不攻自破。而在钱睿的回忆中,母亲给自己的独特感觉却又那么清晰地证明着眼前这个女人并非真正的母亲。同样不可思议的是,《在威尼斯重建时间》中的“我”,仿佛被扔进了一个连环梦的漩涡。“我”一下子回到童年生病的时候,梦到自己进入了《海底两万里》的世界。当“我”睁开了眼睛,眼前却是前来关心“我”的妈妈,与此同时,妈妈在生命垂暮时的画面同时在我脑子浮现。于是,八岁的“我”,告诉父母自己梦到他们都死了,父亲怒不可遏,而我不断地恳求母亲第二天去医院检查身体,因为“我”早已知悉母亲死于癌症。但是到了第二天,“我”转眼成了十八岁的自己,我满屋子找妈妈,被父亲恶狠狠地训了一顿,到头来发现妈妈已经去世了。叙事时间一次一次闪回到“我”的过去,“我”只能通过房间的各种物品的变化,包括挂在墙壁上的母亲的遗照,才能模糊确认“我”所处的时间。甚至后来,“我”还梦到了我的陌生的妻子,梦到“我”和妻子回到中国看望父亲,叙事时间闪前到“我”曾经未曾经历过的未来,父亲的脾气还是那么顽固不化。
两位作者不断地在这两篇小说中玩转叙事时间,真相和答案似乎也藏在叙事时间的闪回里。由于钱睿无法接受母亲所谓重生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在质疑的过程中,他还发觉出院之后的母亲脾气有所变化,母亲不再那么多牢骚和抱怨,不仅对自己的忙碌十分理解,还对父亲的各种行为也温柔以待。母亲生前的画面,以及母亲躺在妙手医院病床上奄奄一息的画面,间接性地在叙事过程中以钱睿的视角不断闪回。在母亲的前后对比中,他加深了怀疑,也在对母亲死前的画面回忆中,鼓动着他想要得到真相的心情。于是,他找到侦探朋友进行调查,确定了现在的母亲实际上是医院制造的“假人”,实为一个复制品:医院用病人的 DNA 复制躯体,然后扫描大脑的所有意识和思维,包括记忆,将神经元连接模式转化为数据程序,然后接入新的躯体。他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他认为永生医院欺骗了他,并试图去向社会揭露永生医院的诈骗行为。但父亲却阻止他去揭露,那个复制的母亲也极力劝阻。直到永生医院的总裁约见他,向他公布了真相,原来他自己就是这个永生医院的产品,真正的钱睿早已在八岁时便死于车祸意外。故事时间被拉回到钱睿八岁之时,真相得以呈现。《在威尼斯重建时间》的一个一个混乱的似梦非梦的情景中,“我”梦到了脑神经专家让我得以“重建时间”的场景,这是一次关键的叙事闪回。作为物理学家的“我”同脑神经专家D,在意识与时间的关系这一命题上达成共识,“我”便兴奋地自愿接受了一次实验。此后,“我”成为了一个“时间跳跃者”:面对无序、复杂,如同网一般错综交缠的非梦的真实世界。而我之所以愿意成为被试者,除了自己对此实验颇感兴趣,更重要的是“我”本想回到过去,得到父亲的道歉,从而实现父子的和解,却没想到父亲的衰老过程让“我”意识到,其实自己真正想要得到的是父亲的原谅。《边境来了陌生人》可以说是以回忆为基础形成的故事,采用了大故事套小故事的叙事结构,最终通过表层结构完成对深层结构的讲述。每一个人都陷入了自己的回忆,讲述自己的故事,同时也基本解释了他们各自为何来到了这人迹罕至的边境,当然其中有的人撒了谎,为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责开脱。而这些都逃不过主人公的“法眼”,最后一个故事轮到主人公来讲,他在回忆与现实之间来回讲述,闪前闪回叙事时间交错,为另外四个人,也为读者解开了那些故事中的谜团和那些自私的谎言。
真相呼之欲出,故事的一切皆起于永生。《永生医院》中以所谓的以“新人”换“旧人”是永生的一种形式,《在威尼斯重建时间》中时间的无序其实也指向了另一种永生的形式,即一旦成为“时间跳跃者”,那么人的生生死死都不再是线性的,也许死去的人在第二天便又重新活在了我们生命中的过去或未来的某个时刻,与我们相逢。《边境来了陌生人》的主角也是一个永生之人,他几乎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看尽了各个城镇及其居民因为永生的存在而变得混乱且扭曲的悲剧。
三篇小说的故事都呈现于复杂而破碎的时间与回忆之中,那么,故事的完成度以及故事的代入感或可信度成了创作的难题。为了使故事讲述得更有代入感,蒋方舟的两篇小说都突出了内聚焦叙事视角的运用。《在威尼斯重建时间》直接以第一人称的“我”为叙事视角,整篇小说都讲述的是“我”的所见所感,在“我”陷入时间漩涡的过程中,从一开始的木讷、困惑,到逐渐清醒,并知道用日记记录下自己每一天的经历,真实感在“我”的细腻想法中得以体现。而《边境来了陌生人》虽然以非聚焦视角开头,但是之后的故事转为内聚焦视角叙事,每一个人完成自己的回忆和讲述。郝景芳的《永生医院》采用的是非聚焦视角,但是这篇和《边境来了陌生人》中的非聚焦视角一样,在客观叙述人物动作和表情时,总会插入一些的人物的感叹与猜想,从而更好地表现和点明人物的情绪。比如《永生医院》中竟然会突然插入主人公的内心想法,并且不带“引用”的标点符号,其实这一定程度上是叙述者在设置悬念:“如果这个女人是母亲,那么家中谈笑风生的女人是谁?”[1]7而《边境来了陌生人》则主要是借比喻的修辞来实现这一效果:“这笑容就像印在一张面具上”[2]218“毫无表情,像是他在路上看到的死在路边的鸽子。”[2]219
二、关于永生的一场幻梦
永生,是这三篇小说与所谓科幻小说能够建立起联系的立足点。不过,虽然都与永生有关,但是三篇小说的永生形态是完全不同的,这也对应着人们对永生的理解的多元,以及基于科学技术现实进行的构想的不同。如此,对于永生之后引发的一系列猜想也不尽相同。
《永生医院》和《在威尼斯重建时间》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关联性较强,它们创造出两种后人类形象。《永生医院》直接将永生和医院联系起来,很显然,作者设想的是医院借助现代医学技术能够帮助患者实现所谓的永生。医院复制病人的基因,制造出与之一模一样的人体,同时扫描病人的大脑,包括人的意识、人的回忆,形成一块芯片。芯片将被植入新造的人体大脑中,与大脑一起生长并且逐渐消融,之后大脑几乎可以实现独立运行。《在威尼斯重建时间》同样是对人的大脑进行实践,采用的方式是将人脑中感知时间的部分去除。虽然这样做并不直接指向我们通常认为的永生,但是一旦人脑失去时间,那么他人的生死都将失去时间逻辑,一种虚实相生的“死而复生”将会时常发生,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永生。这两种获取永生的方式,其实改变了人类现有的身体状况,打破了人体与机器、物质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
“人类社会从自然选择到伦理选择再到科学选择的过程,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逻辑进程。”[3]33这两篇作品中的两种后人类类型可以说已经到了科学选择的阶段,这个选择过程其实包含着难以解决的伦理问题。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人的生理异化问题,即“何为人?”这关乎到伦理身份问题。尤其是《永生医院》里的“新人”。在小说中,郝景芳其实非常直接地通过医院总裁和钱睿的对话,抛出了“旧人”和“新人”亦或“假人”的问题。在钱睿看来,永生医院其实就是“用假人给病人家庭,充当治愈患者”,这些重新回到家庭的人是“假人”。而总裁却坚持认为出院的不是“假人”,而是“新人”,“新人就是病人自身,重新生活的病人。”但是很明显,不管是“假人”还是“新人”,这都不是实实在在的“旧人”了。当钱睿知道自己其实也是医院再造出来的人后,他“疯狂地摇头,他觉得自己的神经快要错乱了,心中大骇,他本能地后退,拒绝,他不想听,还想回到从未听过这个消息的时间里。他无法理解自己听到的信息。怎么突然之间,他就成了那个他想要揭穿的身份。身体的变与不变,头脑的变与不变。母亲知道,母亲不知道。拒绝。接受。痛苦。爱。”此时,钱睿从母亲的伦理身份问题转移到自己的伦理身份问题上。这是极为痛苦的事实。当他知道母亲是再造人后,他实实在在的清楚,自己原来的那个真正的母亲,已经去世了,自己却还要接受一个另外的人;而当他知道自己也是再造人后,其实引发了另一个伦理问题,那就是:其实母亲早已知道自己的孩子从八岁时就已经是“新人”了,但是只有谎言才能完成正常的伦理身份建构。再造的母亲说的一段话值得思考:“其实重要的不是你知道你是你,而是你周围其他人都知道你是你就行了。”[1]20的确,人的身份建构往往依赖他人,这或许是谎言能够生效的关键。这一问题超出了伦理身份认同的个人层面。当钱睿知道全国上下已经有数百万计的再造人,他知道自己已经无能为力。这已经是具有极大社会性的伦理身份认同问题,并不是揭露真相就能豁然开朗的了。未满十八岁的孩子需要通过父母同意才能进行手术,当这些所谓的“新人”知道自己是“后人类”了,和真正的人类,和过去的自己并非一样,他们该如何认识自己成了问题。而那些自愿签署了合同的人,其实已经死而成灰,家人如何面对这些“新人”则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整个社会会怎样对待“新人”这一特殊群体,则是更大的问题。《在威尼斯重建时间》中的“我”也意识到:“我以为时间跳跃者是获得了某种超能力,其实恰恰相反,我永远丧失了理解时间的能力。”[2]199无法想象,如果全人类都处于时间无序之中,世界会呈现出怎样的情况;也无法想象,如果只有少数人成为“时间跳跃者”,这一少数群体会受到怎样的对待。届时,无论是个人还是他人,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都不得不做出伦理选择。
“现代生物技术已经具有操纵生命活动、干预自然进化的力量,因而可以说,几乎在其所有生物技术领域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负面效应,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该’与‘不该’发展、‘应当如何’发展的问题。”[4]191前面两篇小说都只是稍稍提到了当人在某种程度获得永生之后的个人层面或社会层面的情状,而《边境来了陌生人》的重点便是“永生之后”,包括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奥德修斯从《荷马史诗》的故事而来,他阴差阳错得到了岛上女王的永生之法,离岛后四处漂泊。永生并没有给他带去多么美好的体验。他为自己给某处大陆带去了有关时间和生命的观念而遗憾,当地的人发现他不会生老病死,便开始怨恨这种不公,甚至开始自相残杀,因为他们以为杀了一个人,死者没用完的寿命就会转移到自己身上;他也曾被不可一世的国王想尽办法处死,却终将是徒劳。尽管他“没有将永生的方法告诉任何一个人,但贪婪还是驱使人们用自己的能力和野心逐渐接近,甚至实现了它。”他“见过太多永生的故事,它们惊人地相似:一小部分人发现了延长寿命的诀窍,他们是最富有的人、最有权有势的人、最聪明的人。”[2]279永生成为了一种特权,随之而来的是嫉妒与屠杀。甚至在一个城邦,不配长寿的人,从婴幼儿时期开始,手背上就会被做上记号加以区分。可以说,在《永生医院》中也是这样,妙手医院的高昂费用就注定了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享受这样的永生技术。
根据斯芬克斯因子,人的身上具有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但是其中人性因子是高级因子,兽性因子是低级因子,因此前者能够控制后者从而使人成为有伦理意识的人。很显然,为了获得永生而造成的不和谐,实质上来源于人类内心对于生命特权或不平等的不平衡状态,从而激发出更多的兽性因子,甚至超过了人性因子,如此,人便失掉了伦理意识[3]38。
三、从幻想中来,到现实中去
科幻小说,不管是所谓“硬科幻”还是“软科幻”,都不应该只是为了科幻而科幻。正如吴岩曾指出科幻小说是“人类科学、文化的实验室,是创新思考的实验室。”[5]178郝景芳和蒋方舟的这几篇作品所谈及的永生等问题,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有一定距离,但是实际上其中也有对我们的现实生活的反映。通过基于现实社会进行的未来推想,恰恰体现出作者对现实的清醒认识,最终指向的是在某种情况的发展下社会的未来面貌,这其实就是一个现实问题。
郝景芳的小说一直以来被视为“科幻现实主义”,对于郝景芳来说,“虚幻现实可以让现实以更纯净的方式突显出来”,她采用科幻的形式,是为了更好地表达现实、关心现实[6]29。而在蒋方舟的新作中科学技术含量更少,所以更准确来讲,其作品如她自己所言是所谓“推想小说”:“推想小说讲这个世界未曾发生的历史,平行时空里的未来。其实非常简单,它可以由两个问句组成,第一个问句是‘如果这个世界变成某种样子,那我们会怎么样?’第二个问句是‘如果我们设想的这种世界继续的话,那么会发生什么?’”[7]而世界的变化及其设想都是基于现实的,基于现实中人们的各种欲望和社会现象。
简而言之,郝景芳和蒋方舟不仅在小说中表现了当下社会存在的问题,同时还设想或者说推想了将来社会可能呈现的面目,其中隐藏着危机。这三部作品都谈到了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永生医院》和《在威尼斯重建时间》都涉及了亲情的淡漠。《永生医院》中的钱睿在母亲健在时总以忙碌为借口“假意敷衍”,较少归家,等到母亲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了才深感到遗憾,于是想要在医院陪伴母亲。而《在威尼斯重建时间》中的主人公更是长达二十年不曾归国,直到收到父亲去世的信息。在无数次时间回转的过程中,他以为自己想回到过去是希望得到父亲的道歉,因为在他心里他和母亲都是父亲蛮横专断的受害者,但是没想到自己回到过去真正想要做的其实是祈求父亲的原谅。在《边境来了陌生人》里,人们不再想要生育和抚养孩子,甚至有人喝下了“忘忧水”,无数次的恋爱和失恋,都会在清除记忆之后重新来过,这无疑洞悉了现代社会男男女女的感情观的一个侧面。小说中的K,为了活下来,为了消除自己的低等人身份,杀掉了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夺走了他人的身份苟活于世,这是对扭曲社会之下的人性扭曲的极大讽刺,而这种扭曲皆来自于永生的特权,在于阶级的不平等。永生医院只有高收入阶层能够进入,当然,或许其中还暗含着权势等等,并非所有人都能享受基因复制的技术。在没有资格获得永生的人身上做上记号加以区分,这更是可怕的,人从一出生就被划分的等级。但是,如果像在《永生医院》中那些获得永生的所谓“新人”,他们只占少数,那么真相一旦被识破,那么他们作为少数群体该如何生存?这些“新人”会不会成为《边境来了陌生人》中那些被画上记号的低等人?联系到现实社会,男性和女性的对立、性少数群体的尊严问题、种族歧视等问题难以消弭。还有一种情况,如果所有人都获得永生呢?蒋方舟幻想了一个彩票国,这个城邦人人永生,但是他们后来意识到了不公平的存在,比如有的人房子更大,有的人有恋人,有的人老婆更美,这些也成了不公平的体现。于是人们对此发出抗议,行政官没办法,决定将一切交给命运,所以整个城邦大兴彩票制度,彩票成为各人转换人生的机会。而在整个社会乱成一片之后,人们又取消了彩票制度,最终导致人们丧失了自主选择的能力,包括用哪一只脚踏出大门。
郝景芳在《人之彼岸》的前言中谈到了人工智能(AI)问题:“人之彼岸的意思是,人在此岸,AI 在彼岸,对彼岸的遥望让我们观照此岸。”[8]而蒋方舟在小说集的后记中直接告诉读者灵感来源:她看到一个教授进行基因编辑的新闻,深受震撼。后来在创作时,看新闻中马斯克大喊:大脑与计算机结合,人类将与AI共生[2]293。他们以人们所渴望的乌托邦世界为创作起点,最终其实走向了反乌托邦或恶托邦世界。当然,真正让人担忧的不是那个单纯的美好的梦想,而是伴随梦想实现而产生的基于人性而产生的问题。每个人在畅想未来时可能都会将自己当成是受益者,却不曾想自己可能是那个被遗弃的人。
基于现实的未来想象,其实同时指向现实和未来,这也是科幻小说最值得去把握同时也是最可怕的内容。因为一旦基于现实,那么作品中的未来都将在现实中寻找答案。小说创作常常被理解为对现实的反映,但是正如蒋方舟在后记中所感叹的:“当现实变得像小说,小说就成了我们理解现实的方式。”[2]294这或许是小说创作的一体两面。郝景芳和蒋方舟都是80后青年作家,他们要面对的也许正是写什么的问题。“先锋小说”以来,中国文学创作就呈现出所谓“去历史化”的趋势,事到如今,有研究者甚至认为已经实现了“非”历史化。与此同时,也有青年作家又开始重新关注历史,在作品中体现历史意识。但是直接面对现实的书写,能否在写法上、思想深度上突破甚至超越文学前辈,能否在揭露现实时保持文学性,而非对社会新闻事件的简单重复,是否能够在文学政策之中获得足够的自由空间,这都是值得思考和探索的。当然无论是书写历史、现实还是未来,其实最终指向的都是现实,郝景芳和蒋方舟的写作或许是青年写作的一个新的方向,同时也算是乘着科幻文学的风,到未来去寻找现实的答案。科幻小说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在未来的叙述中,破坏现实,重建未来。而伟大的文学或许就是在破坏与重建现实与未来。
四、结语
这三篇小说或说是“科幻现实主义”小说,或说是“推想小说”,其实不外乎是基于现实与科技从而对未来展开的想象。它们同时关注到了永生的话题,当然还有关于时间、回忆等内容的讨论。小说重点突出了科技发展到将来可能出现的社会状况,分析了可能存在的伦理问题和后果。文本中也涉及到了一些现实中大家普遍关注的社会现象,体现出作者的现实关怀。这三篇小说拥有引人入胜的故事和令人深省的主题,不过也得注意小说潜在的问题。一方面,小说中的人物或情节的设置和叙事语言的表达相对来说不够自然,这种想象型小说如何使读者更有代入感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语言表达如何体现平衡思想性、科学性与文学性的平衡则是另一个问题。另一方面,传统文学的审美评价标准是否适应新的文学创作方向和现象,这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不管怎样,郝景芳和蒋方舟作为80后青年作家尝试以面向未来的姿态书写现实,努力实践写作的新路径,是理应得到更多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