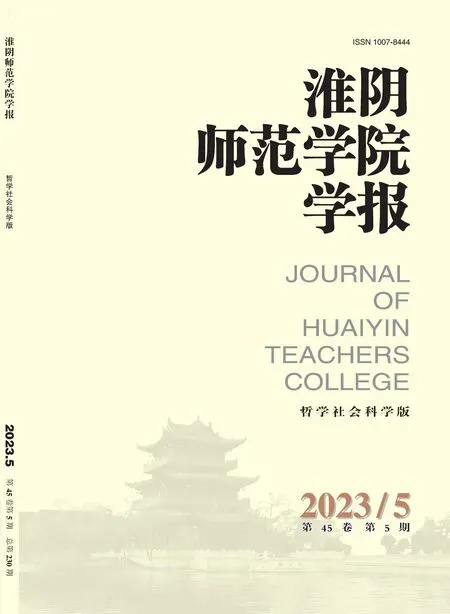论儿童视角下的反战主题电影
——《穿条纹睡衣的男孩》与《乔乔的异想世界》比较分析
王海燕
(江苏警官学院 基础课教研部, 江苏 南京 210012)
纵观中外电影史,曾经出现过许多经典的反战主题电影,其中一些电影用儿童视角策略来表达反战主题。如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中国电影《三毛从军记》等。2008年由马克·赫曼执导的《穿条纹睡衣的男孩》和2019年由塔伊加·维迪提执导的《乔乔的异想世界》,都是通过德国儿童视角来叙述故事的。本文将比较这两部电影叙事手段和表达方式的异同,分析它们如何通过儿童视角表达深刻的反战主题,及其不同的戏剧效果。
一、不同战壕之间儿童的友谊
相对于成人世界,儿童有着未被世俗丑恶玷污的纯真和美好人性。即使身在战争之中,并被当局政治意识形态洗脑,但他们的本性没有泯灭。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惨绝人寰。《穿条纹睡衣的男孩》和《乔乔的异想世界》这两部影片都以此为背景,选取德国与犹太孩童之间的友情作为故事的叙述主体。相对于成人世界的你死我活,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的无情杀戮,这份不同战壕间的友谊稀有且弥足珍贵。
两部影片的“审美倾向与体验是由儿童的思维方式与想象力所建构的”[1]。正如《穿条纹睡衣的男孩》的片首语“在黑暗的理性到来之前,用以丈量童年的是听觉、嗅觉以及视觉”。孩子对于外界给他们呈现的东西一般都全盘接受。德国纳粹军官的儿子布鲁诺之所以误入集中营送死,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父亲自诩“为让德国人民生活更美好而工作”深信不疑,同时对纳粹迫害犹太人的血腥事实一无所知。他对战争的认知是被屏蔽的,甚至是被误导的。纳粹用以欺骗世界的宣传片把集中营描绘成人人友爱的大家庭,这种宣传影响了布鲁诺的认知,他穿上条纹囚衣,偷偷潜入集中营,为犹太男孩希姆尔寻找失踪的父亲。在他看来,这仅仅是为帮助好朋友采取的刺激的冒险行动,对于随之而来的危险他并不能预知。他们全家随纳粹军官父亲来到集中营,集中营散发出的焚烧犹太人尸体的难闻气味,布鲁诺和他的母亲虽然奇怪,但都不明真相。影片一开始呈现的是布鲁诺无忧无虑地与小伙伴们张开双臂奔跑的嬉戏场面,同时,也穿插了犹太人被纳粹赶出家门、赶上货车的镜头。显然,这个德国军官的孩子对此并不知情,他拥有富足的物质生活,平和安宁的生活状态,唯一的烦恼是父亲升迁搬家至乡村后的孤单和无聊,以及对同龄伙伴的渴望。在这种情况下,他对不远处他认为的农场、实际上的集中营里穿着条纹睡衣的人产生好奇,甚至羡慕那里的孩子有玩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与集中营里同是8岁的犹太孩子希姆尔相遇,并建立起孩童间的纯真友谊。对希姆尔来说,虽然布鲁诺是他讨厌的德国士兵的孩子,并且因为布鲁诺说谎导致他遭受严厉的惩罚,但他还是接纳了布鲁诺并与他成为好朋友。集中营的铁丝网隔不开他们的友谊。他俩一个灰头土脸、忍受饥饿和折磨,一个外表光鲜、衣食无忧,这种外表和境遇的差异并没有影响他们建立友谊。布鲁诺偷偷从家里给希姆尔带来好吃的,他们在铁丝网边下棋、聊天、抛足球,画面是感人的,也是让人心酸的。孩子的双眸里没有种族仇恨和战争的罪恶,孩子之间友谊的单纯和美好更反衬出现实的丑陋和残酷。
电影《乔乔的异想世界》的社会背景是二战末期,与布鲁诺不同的是,年仅10岁的德国儿童乔乔是纳粹的小狂热分子,他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和其他孩子一起被训练成纳粹的后备力量。他们被告知犹太人是“长着犄角和尾巴的怪物”,而德国人作为雅利安人,“文明程度和先进性是任何其他种族的1 000倍”。虽然布鲁诺父亲和家庭教师也向布鲁诺妖魔化犹太人,但布鲁诺没有认同此观点,在他眼里,穿着条纹睡衣的人只是外表奇怪,但不影响他们成为他的朋友。与布鲁诺不同,乔乔对种族歧视的观念却是认同的,他的房间里到处张贴着纳粹海报和青年团的军旗。所以,当他无意中看到被母亲藏在阁楼的犹太女孩艾尔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去告密。因为怕连累母亲才打消了这个念头。多次冲突之后,乔乔逐步消除了种族偏见,与这个犹太女孩建立起生死相依的情谊。
乔乔这个艺术形象显然比布鲁诺复杂得多。影片一开始就表现他的善良本性,在希特勒青年团训练时,因不忍杀死兔子被同伴嘲笑为“乔乔兔”。这为后面他对犹太人认知的转变埋下伏笔。乔乔母亲对他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布鲁诺的母亲只是在心里同情犹太人,为此与丈夫争执并绝望。乔乔的母亲萝茜则投身保护犹太人和反战的行动中。萝茜清楚地预料到德国战败的结局,并为此高兴。面对儿子的质疑,她说,“我爱我的国家,但我反对战争”。萝茜甚至为反战献出生命。这位头脑清醒的英雄妈妈给儿子的教育也与法西斯的宣传完全不同:“总有一天你会发现有比金属、炸药和肌肉更坚强的东西,那就是爱。”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乔乔接受了这样难能可贵的教育,母亲说:“做一个平凡真正的人:浪漫、自由、随时起舞、心中有蝴蝶。”“10岁小孩不应该歌颂战争,讨论政治,你应该去爬树,然后从树上摔下来。”这与纳粹宣传的“我发誓我会全力以赴,以奉献给我们国家的救世主”,“元首说等我们打赢了,就轮到我们这些小孩去统治世界了”形成鲜明的对比。就如片尾呈现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诗句:“让一切临到你/美与恐惧/走下去/情感并非最远之物。”母亲教会乔乔热爱生命和乐观,要做一个孩子应有的样子,单纯、善良、好玩,保持孩童的天性,而不是做杀人机器。尽管起初乔乔的想法与母亲有冲突,但最终他还是用行动接受了母亲的价值观。影片善于用细节表现情感主题。譬如,母亲两次给乔乔系鞋带,乔乔给被吊死的母亲系鞋带,乔乔弯腰给艾尔莎系鞋带。系鞋带的细节呈现乔乔成长的心路历程。这也是让观众动容之处。再比如跳舞的细节,母亲说,“要用舞蹈来告诉上帝我们感激生而为人”,“跳舞是自由的人干的事”。母亲与乔乔跳舞和战争结束后乔乔与艾尔莎跳舞的细节,影射了人们对于自由的向往。影片将人物对人的自然本性的追求巧妙地隐藏在这些温馨的细节之中。
二、不同的戏剧表现类型
反映二战期间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电影,一般都用悲惨的故事控诉纳粹的惨无人道。比如《辛德勒名单》《钢琴家》《一袋子弹》《黑暗弥漫》《安妮日记》《死亡终点站》等。《穿条纹睡衣的男孩》以两个男孩和其他犹太人一起赴死为结局,是悲剧。而《乔乔的异想世界》则以喜剧的形式展开故事,是笑中带泪。
《穿条纹睡衣的男孩》是典型的悲剧电影。影片以布鲁诺与伙伴们欢腾的奔跑开始,孩子们无忧无虑的欢乐和成人世界的焦灼形成对比。生活环境的变化让布鲁诺感到孤独并因此闷闷不乐,但他对未知世界又充满探索的热情,这跟他喜欢冒险的天性有关。偶然遇到的穿着条纹睡衣(其实是囚衣)的犹太男孩希姆尔在他眼里是剥离了标签的,他只是要一个朋友,至于对方是不是犹太人并不重要。影片在看似平静的叙事里暗流涌动,犹太仆人小心翼翼却避免不了最终被无情地殴打残害。不远处集中营上空浓烟滚滚传来难闻的气味,犹太男孩因为布鲁诺的胆怯说谎被军官体罚。这样的氛围让人觉得很压抑,这些丑恶在布鲁诺惊愕的注视下和懊悔的哭泣中暴露无遗。但幼小的布鲁诺对此无能为力,他的母亲除了跟父亲争吵之外也爱莫能助。就是这样一个纯真弱小的男孩最终被自己父亲的纳粹同伙无意中无情地杀死,对于纳粹们来说,这又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影片最后在暴风雨中,一家人四处紧张地寻找布鲁诺,母亲看到铁丝网外布鲁诺的衣服痛苦地哀号,父亲意识到儿子已经误入毒气室被毒死,露出痛苦绝望的神色。观众在为善良的孩子布鲁诺生命痛惜而洒泪的同时,也会思考一个问题:这个纳粹父亲此刻是否能够通过儿子的悲剧反省自己的屠杀行为?他值不值得同情?这个德国军官家庭的悲剧只是个案,与此同时,又有多少犹太家庭被毁灭?多少悲剧在上演?当战争这个恶魔肆意横行的时候,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乔乔的异想世界》将悲剧的内核裹在喜剧的外衣之下。影片用让人捧腹的台词、夸张的手法、喜剧性格的人物形象,表现对丑恶的嘲讽和对美好的肯定。与作家克里斯汀·勒南斯的原著《牢笼中的天空》不同的是,影片另加了乔乔假想的希特勒形象。这当然不是历史上真实的希特勒,由导演塔伊加·维迪提亲自扮演的这一角色憨态可掬、滑稽搞笑。他要么在乔乔彷徨迷茫时跳出来给乔乔打气加油,要么给乔乔灌输激进的思想。这是一个大胆设想的艺术形象,他是外界给孩子灌输的希特勒形象与朋友的结合体,也是孩子在战场上失踪的父亲的替代者。他们之间的对话也是对乔乔思想活动的补充。但当通过自己的眼睛发现战争的残酷与荒唐之后,乔乔最终一脚将这个想象的希特勒踢出窗外,这标志着纳粹军国主义的思想被他彻底摒弃。乔乔已经长大,有了自己独立的世界观。
在《乔乔的异想世界》中,沉闷紧张的场景和搞笑的镜头互相融合,很好地杂糅了幽默与悲情,让人发笑,又引人深思。比如,五个盖世太保突然搜查乔乔的家,当观众为躲在阁楼的犹太女孩捏一把汗的时候,又为在场的人多次反复说的一句“希特勒万岁”忍俊不禁。犹太女孩故作淡定地从阁楼走出来,冒充乔乔死去的姐姐骗过盖世太保,众人再次用“希特勒万岁”来打招呼,女孩刚说出这句话时的犹豫也是必然的,但为了活命,她不得已跟他们周旋。“希特勒万岁”这句口号在影片开头乔乔与假想的希特勒对话里,也反复出现,充满了孩童的戏谑味。同时,反复切入的历史真实的黑白影像中,一群狂热的孩子高举起手行纳粹礼,对纳粹头目希特勒顶礼膜拜、疯狂追随,并卷入战争的滚滚车轮。显然,导演的目标不是靠恶搞取悦大众,而是为了让人们在笑声中反思。
K上尉的艺术形象塑造也是成功的,避免了脸谱化。与银幕上常见的残忍冷酷的纳粹军官不一样,他是充满人情味的。这位因在战场上炸坏一只眼睛而转为教官的纳粹军官,在给孩子们训练时直言不讳承认帝国必然失败的结局。骨子里他是善良的,在关键时刻,他两次解救了犹太女孩和乔乔。他甚至是浪漫的、可爱的。在最后的战斗中,他和副官身穿自己设计的红色披风的军服上阵,颠覆了人们对冷酷的、充当杀人机器的德国军官的认知。
三、儿童视角叙事的意义
“叙述视角又称叙述聚焦,是指叙述语言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特定角度。”[2]用儿童视角来表达社会苦痛的电影叙事手法越来越受到青睐。儿童视角是“借助儿童眼光或口吻讲述故事,呈现儿童思维特征,小说的叙述调子、姿态、结构及心理意识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选定的儿童叙事角度”[3]。本文关注的两部电影都是采用儿童视角的叙事手法,虽然戏剧的表现类型不同,呈现出不一样的艺术效果,但殊途同归,它们最终都是指向反战的主题。
相对于成年人来说,儿童天真而单纯,无法把握成人世界的严酷现实。二战中的德国儿童被纳粹洗脑,播下种族歧视的种子。如乔乔起初对犹太人的态度是源于认同法西斯宣传的煽动性话语:“我们会把敌人碾成渣滓,然后把他们的坟墓当厕所。”而布鲁诺则相信虚假宣传片里纳粹友善地对待犹太人,集中营里充满欢声笑语。当谎言终被揭穿,乔乔选择和正义站在一起,布鲁诺则是走向生命的终结。
对未知世界的探求欲也是孩子的天性。但他们无法像成人那样理性地、趋利避害地思考和权衡。一旦他们因此被伤害,更易引起人们的同情和惋惜,也更加映照了成人世界的冷酷无情与惨烈悲怆。两部影片的小演员都有着可爱的大眼睛,圆圆的脑袋,惹人怜爱的外表和纯洁善良的灵魂,让观众一下子就喜爱上他们。饰演布鲁诺的小演员眼神里带着天然的忧郁,当他和一群犹太人一起被赶往毒气室,观众们都为他揪心。乔乔虽然被同伴认为是胆怯的“乔乔兔”,但当盖世太保搜查他家的时候,他表现得很勇敢,乔乔也渐渐在对旧我的舍弃中成长。
儿童视角不会是纯粹的,成人的写作意图依附于童年视角叙事得以实现。儿童身份叙事和成人身份叙事的交替存在,成人对现实世界情感的失落和苦痛,以儿童视角叙事的形式委婉地表达出来。“成年人现实的评论声音总是掩饰不住地显示在儿童的叙述中。”[4]电影和小说相比,可以凭借多种形式表现主题,比如色彩、音乐、蒙太奇的手法等。《穿条纹睡衣的男孩》的悲剧意义是单一的,人们为这个德国军官儿子的死亡扼腕的同时,感受到战争的残酷。而像《乔乔的异想世界》这样的电影,要用喜剧的形式表达悲剧的主题,有一定的难度,该影片获得包括6项奥斯卡提名等不少奖项,也是对它艺术成就的肯定。
《乔乔的异想世界》将反战主题进行延展。影片不仅仅控诉了战争的残酷,更向我们展示了要树立更为积极的人生观。面对苦痛,人们除了哭泣之外,更应该着手去改变。这不是要忘记苦痛,忘记战争带来的创伤,而是思考如何苦中作乐,如何疗伤。因为战争,乔乔和犹太女孩艾尔莎都失去了双亲,但他们相依为命,以乐观的姿态迎接战争的结束。乔乔的坚强源于母亲的教育,母亲的人生态度是值得肯定的:接受生活给我们的馈赠,用爱来疗愈受伤的心灵。从这一点来看,《乔乔的异想世界》带给观众更多的思考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