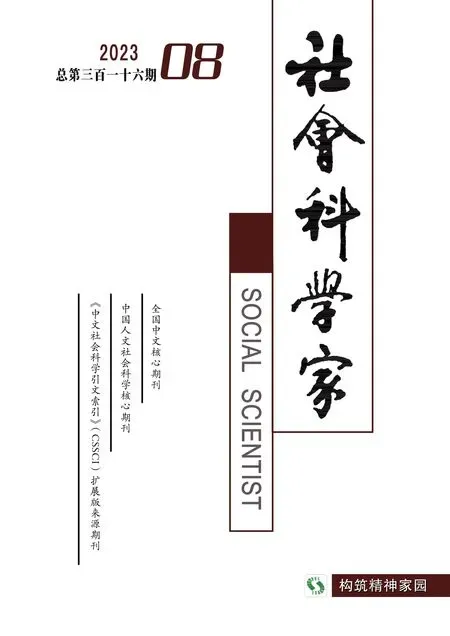论于伶戏剧的诗性特征
何菲菲
(新疆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中国现代剧作家大多都是带着深厚的古典文学传统,同时又受外国文学的影响而走向现代戏剧创作的。“诗的国度”的传统文化底蕴,中原传统的诗学理论和戏曲诗化传统是中国现代戏剧家们汲取诗性艺术的深层来源,他们把民族的艺术精神,包括民族戏曲的质素融入了现代戏剧的创作中。西方的诗学与理论以及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对中国现代戏剧的诗化倾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为中国话剧诗化传统的开拓者,田汉、郭沫若都是浪漫主义诗人,他们很容易地就把诗融入戏剧,同时,他们也都看到戏剧的诗本体特性。郭沫若就认为,“诗是文学的本质,小说和戏剧是诗的分化”[1]。
田汉的戏剧作品具有鲜明的抒情诗的特征,是典型的“抒情剧”。从诗到诗剧再到历史剧,体现出郭沫若戏剧诗化的过程,他熔诗于剧,诗剧合一,尤其是其历史剧创作诗情浓烈,诗与剧浑然一体。曹禺可以说是中国现代话剧诗化传统之集大成者,是话剧诗化的典范,他自觉地把话剧作为诗来写,其话剧创作的本质特征就是“以剧写诗”。夏衍则写出了一部部“政治抒情诗”,把诗与现实的关系逐步推向更纯熟的高度,呼应了世界现代戏剧艺术“诗与现实”相结合的美学趋向。经过田汉、郭沫若、曹禺、夏衍等人的探索,中国现代话剧的诗性特征最终成型,他们的实践探索和戏剧作品也深深影响了中国现当代话剧艺术家们的美学追求。于伶是继他们之后继续探索戏剧诗性的一位剧作家,于伶戏剧中的诗性特征是中国现代戏剧诗化的扩展。
一、诗人气质
在《〈夜上海〉和〈沉渊〉》中,李健吾指出“诗和俗的化合”是于伶剧作的特征;在《于伶先生与〈女儿国〉》中,李健吾认为“《女儿国》是现实的,然而是诗的”[2]。夏衍在《于伶小论》中进一步指出,于伶“学会了战斗,接触了‘浅俗’,他懂得了千万上海市民的心,他真实地从浅俗的材料中去提炼惊心动魄的气韵,使他完成了一种‘诗与俗的化合’的风格,使他写下了令人不能忘记的迂回曲折地传达了上海五百万市民绝不屈服于侵略者的意志的作品”[3]。至此,于伶戏剧创作“诗与俗的化合”的特点基本定型。这其中的“诗”是“生活的诗,心灵的诗,也是政治抒情诗”[4]。
少年时期,对定庵杂诗、剑南诗钞与稼轩词的阅读①于伶在《爱好戏剧的开始——学剧随忆之一》一文中写道,“在父亲鼓励我看完他传给我的章回小说之后,我曾沉溺于《雪鸿泪史》《玉梨魂》《断鸿零雁》等所谓哀情说部里,我歌泣呻吟于曼殊绝句、定庵杂诗、剑南诗抄与稼轩词等作品中”。为于伶的“诗化愁绪”和诗性底色打下了基础。杜甫、陆游、辛弃疾、龚自珍的诗作带给于伶忧国忧民的孤愤之情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在阅读前人诗作时,于伶感受着诗人的情绪和表达,他学着写旧体诗,在不同的时代环境中写下了许多诗作,借以抒发自己的感情,后结集为《于伶诗钞》②《于伶诗钞》,1997 年7 月由学林出版社出版,这是唯一的一本辑录于伶诗作的小书,收录于伶所作的115 首诗,王元化、刘厚生分别作序,袁鹰所作《霜叶红于二月花——记于伶和他的诗》以附录出现在最后。《于伶诗钞》分为忆吟草、归吟草、余灰录、新篇章四个部分。诗作内容多为回忆和纪念,怀旧诗居多,形式多为旧体诗。。1930 年冬,于伶在北平大学法学院俄文系废弃图书馆的危楼上,借着街灯,偷读马列著作,曾写下《危楼偷读》:“危楼不许通电线,一波煤烟多盏灯。俯仰浩瀚心万里,红书偷读意飞腾!”③该诗曾在《由〈女儿国〉谈起——雪中废话》中出现,但由于当时的环境,该文公开发表时,后两句改为“惯伏几头诨不语,热情且喜已成冰!”夏衍说如果于伶“早生这么二三十年,那么也许可以是一个佯狂歌哭用诗酒来排遣他‘国民孤愤’的南社诗人吧!”[3]正是这样的诗人气质在于伶的戏剧创作中留下了诗性的底色。
除了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带给于伶诗人的气质外,郭沫若和田汉作品的浪漫主义诗情也对于伶诗人气质的养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于伶自述:“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之前,当我感到政治与思想上受压迫,苦闷,彷徨,追求出路,如饥如渴地读课外书的时刻,连续得到的恩物是《创造》《创造周报》《洪水》《创造季刊》以及‘创造社’出的丛书。郭老的诗、剧、小说、散文与译文等等‘乳汁’,喂养了我。”[5]郭沫若的《女神》《星空》《瓶》《辛夷集》《前茅》《恢复》等诗作中那雄伟的力量、美丽的辞藻以及强烈的反抗情绪,唤醒了于伶;那基于生活压迫、个人情绪苦闷而生发的战斗性激励了于伶。是郭沫若的“巨灵之手”把于伶这学步的孩子“扶进了文艺的园门”,为于伶拉开了“戏剧舞台的幕角”。而田汉的剧作,“那富于才思的构架,那富于诗意的语言”[6],简直使于伶着了迷。在郭沫若、田汉浪漫主义的影响下,于伶把哀情说部和旧体诗中的“愁绪”转化成了革命浪漫主义诗情,这就从戏剧美学的角度为于伶的戏剧创作留下了诗性的底色。于伶说“每一个故事,临到我笔尖上的时候,我就会兴奋得没有多多思索的余闲,失去感情控制的能耐。我写,我往往被我所写的事件和人物压制与冲动得不暇追求与探索形式或技巧,而像叙事诗一样的抒写了”[7]。像叙事诗一样地写剧本,正是“以剧写诗”的一种呈现,这是于伶从郭沫若、田汉的诗化戏剧中汲取到的营养。
于伶诗人气质的体现,“不止是因为他有很深的古典文学造诣,能作旧体诗词,也不止是因为他的剧本里常有诗的意境,诗的气氛和诗的语言;而是他的坚贞、真诚、坦率、激情,总使人要联想起自屈原以来的许多忧国忧民的杰出的诗人。”[8]屈原以降,杜甫、陆游、辛弃疾等诗人,都有着“兼济天下”的抱负、为国效力的决心,无论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中,他们仍不忘挣扎与呼喊,以“至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坚守着强烈的正义感与忧患意识,决不向腐朽势力低头。于伶不仅喜爱读这些诗人的诗作,学习他们的诗歌艺术及风格技巧,更为重要的是秉承了这些诗人的高尚品格。古代诗人的爱国主义诗情源于诗人没把自己当普通个体而是“士”的情感表达;现代诗人,尤其是郭沫若、田汉则是将自己看作个体,且是遭受过帝国主义欺凌的个体,所以他们的爱国主义诗情是从普通个体走向“士”的情感表达。于伶则兼具了这两种爱国主义诗情,在民族国家危难之际,在困守“孤岛”之时,于伶以坚贞的感情和钢铁般的意志,真诚坦率地直抒胸臆,在剧作中展现出孤愤的忧患意识。
二、诗性追求
洪深曾指出,“对社会的缺陷发生怀疑,对生活的不安感到苦闷,为着国土的沦丧而慷慨悲歌,为着大众的嗟伤而牺牲自我……这是现代中国的时代精神,也可以说这是呼吸着这种时代空气的民众共同的感情和意志。深深地接触到这种感情和意志的潜流而用最民众的形式表现出来,我相信这才是时代和民众所需要的作品。”[9]于伶正是以时代的要求为自我要求,将最崇高的诗性熔铸于剧作中,创作出饱含诗意的时代与民众“需要的作品”。
在戏剧创作中,于伶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戏剧取材于现实,通过诗意的艺术构思和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提炼出崇高的诗性。他的“剧作密切结合时代为政治服务,这种尖锐的即时反映的报道性,加强剧本的思想性,把根扎在现实生活的泥土里,有说服力地规定不修改行动的逻辑。作为‘武器’的戏剧艺术,没有生活打基础,一味夸张,即使能收一时的宣传效果,也容易缺乏持久的力量。于伶的革命现实主义精神对他的富有报道性的戏剧艺术是一种保证。”[10]于伶早期的时事报道剧大多都取材于新近发生的社会事件,《蹄下》取自小剃头匠高丫头子被外国巡捕无辜踢死事件;《回声》直接取材于日商纱厂打死无辜工人梅世钧事件;《撤退·赵家庄》根据“丰台事件”而作;《浮尸》根据天津海河“浮尸事件”所作;《血洒晴空》根据飞将军阎海文轰炸日本旗舰“出云号”的事迹创作;《通州城外》取自“通州事件”;《夜光杯》则取材自“新刺虎”事件。这些剧作是于伶对社会时事进行艺术加工后的创作,是直接受事件刺激而产生的真实的情节与激情的宣泄。
于伶早期戏剧创作的目的很明确:首先是为了政治宣传,表达反帝抗战、反汉奸的主题,号召全民抗击侵略者。无论于伶剧作的题材取自何处,无论其以何种方式进行创作,无论剧作是正剧还是喜剧,是独幕剧还是多幕剧,是现实剧还是历史剧,其剧作的主题和内涵都具有崇高的诗性:“反侵略、反投降、反剥削、反迫害”[11]。随着于伶戏剧艺术的不断成熟,这种时代精神的诗性表达一改报道剧的简洁直白,渐趋于厚重、含蓄以及多声部。
在《女子公寓》《花溅泪》《夜上海》等剧中,于伶用现实主义的笔触写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同情底层妇女的疾苦,其“诗性”的表达不再停留于对革命斗争性急的“呐喊”,而是通过对大家熟悉的社会生活的描写引起大众对社会现状的深思,用含蓄蕴藉的手法激起大众的反抗和爱国情思。《女子公寓》将“女子公寓事件”搬上舞台,揭露国民政府统治的黑暗;《花溅泪》通过对底层舞女悲惨遭遇的描述,最后一幕直接呈现抗战主题;《夜上海》《长夜行》都是对现实生活的再现,其教育意义在于把生活以暗示的力量正面摆在观众和读者眼前;《女儿国》中,作者展开想象的翅膀,“涉猎成趣,指桑骂槐,艺术上的奇趣掩饰着政治上的尖泼”[11]从而达到抗日宣传的神圣目的。《大明英烈传》借古喻今,借历史上抗击外族压迫的英雄事迹,鼓舞人民的抗战意志。《七月流火》中,党的路线贯穿在华素英全部的行动,她把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于伶的多幕剧创作,脱离了直观事件,在长期情感底色和社会思考中慢慢酝酿着有内在潜力的情感,借助于其剧运工作长期隐忍、坚持的特点,在其多幕剧中形成了克制而又有力量的情绪,表达着现实主义的诗性追求。
此外,职业革命戏剧家的身份及其所承担的号召大众抗日救亡、保家卫国的政治责任是于伶诗性现实主义戏剧的深层动力。当下所经历所看到的是现实,而坚守的信仰则是诗性。无论于伶身处什么样的现实,他都从未质疑过自己的信仰。于伶“深刻地反映时代,而善用一种平明通俗和有力的手法来撼动观众的心灵”[9]。他深知戏剧是宣传和教育大众最好的工具,他坚守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理念,他的戏剧所表现的是他全身心所信仰的。于伶的戏剧创作都是在政治信念和政治环境下完成的,他从来不曾放松过发挥戏剧艺术的武器作用,他的剧作“一开始就与政治斗争紧密配合,以纪实性和宣传鼓动性取胜”[12],他自己也说:“生于此时,文章理应报国,戏剧更是战斗的武器。”[13]在《〈于伶剧作选〉后记》中,于伶回顾自己的戏剧创作时曾说:“用剧本这一形式,记录下民主革命时期战斗的现实生活片段,抒发出当时‘为着国土的沦丧而慷慨悲歌,为着大众的嗟伤而牺牲自我’的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感情,‘不为奴隶’的吼声与人民翻身、革命胜利的信心。写作的当时只是急切地一心为革命斗争服务。”[14]当于伶在“孤岛”时期将视线转向市民风俗社会,从中仍然看到的是国家民族,始终表达着反抗,宣传着他的政治理想。于伶这始终如一的坚持,本身就是他最深层的诗性表达。
于伶剧作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崇高诗性主题的提炼和表现,揭露社会的黑暗和不公,更为重要的是给观众以启示和引导,表达着现实之外的理想。“孤岛”时期的创作中,于伶不仅开始区分“说”与“不说”,而且关注“怎么说”,这些都表现在于伶作品“画龙点睛”的人物设定上,以此来达到提炼剧作崇高诗性的目的。“生活不是变态的,心理还是日常的,然而意义却是暗示的。”[15]《女子公寓》中的沙霞(一个体现“走俄国道路”的名字,最后她去了很远很苦的地方——暗指延安);《花溅泪》中的进步舞女丁香以及补习学校的老师;《夜上海》中未出场的游击队队长李大龙等人物都是剧作中那“黑暗中的光亮”。在于伶的剧作中,“处处给人以虽在黑暗的旧社会,然而祖国有希望,国家有栋梁的强烈感受。”[11]李健吾则进一步指出于伶的诗意“不是幻想,而是真实,而是向生活深处掘发的成就。是高度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果实”,于伶的剧作“是朴素的,然而具有激动人心的力量”[10],这力量不仅是于伶剧作要表达的崇高的现实主义的诗意,更是于伶思虑过后的诗情。
三、诗意呈现
真正优秀的剧作家是要超越生活的表象,以诗人般的充沛情感,“通过自己丰富的想象,运用比喻、隐喻、象征手法等所构成独特的意象化的美的艺术语言,形成富有诗意的诗境,进而激发读者或观众的想象、情感与理性发现,使其获得高度的审美愉悦”[16]。于伶用诗人的激情和眼光来结构戏剧,在其剧作中,我们随处可见他诗意的表达,感受他诗人的气质、韵味。
(一)古典诗词汲取诗意
于伶戏剧的“诗性”首先体现在对古典诗词的提炼与运用上。于伶戏剧的剧名有很多都是从古典诗词转化而来的。《乌夜啼》,原名《心狱》,“心狱”二字更能说明剧作关于人性、关于人心自我桎梏的主题,“乌夜啼”则更显诗意。《花溅泪》取自杜甫《春望》中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两句诗恰如其分地反映出《花溅泪》中舞女们身处乱世、身不由己的哀伤感。《杏花春雨江南》出自陆游《临安春雨初霁》中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杏花春雨江南”既是第一幕中对江南农村春日杏花纷飞的环境描写,寄予对祖国大好河山浓浓的热爱之情,更是第四幕中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梅萼辉与储南侬相约明年杏花春雨江南时定能再见,这浓浓的诗意自始至终都贯穿在《杏花春雨江南》这部剧中。《七月流火》引自《诗经》中“豳风”的第一首诗的第一句“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曰觱发,二之曰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于伶借这首诗说明了《七月流火》的内容:为新四军征集寒衣的义卖活动。
除了剧名富有诗意外,多幕剧中的小标题等也饱含诗情。《夜上海》中每一幕的小标题:“何处是桃源”“劫后灰”“归去也”“茫茫夜”“星移斗转”都是对剧情暗含深意的诗意凝练。“何处是桃源”一幕中梅岭春带着全家人逃离家乡,找寻安身之处,带着“何处是桃源”的凄凉;“劫后灰”一幕中在钱恺之的帮助下,萼辉和继母有了安身之处,但却与父亲和弟弟失散;“归去也”一幕中梅岭春带着思乡之情回了家乡;“茫茫夜”似乎是插进全剧的一幕,但却以现实的笔调描绘了底层百姓艰难度过的一个茫茫黑夜;“星移斗转”一幕中梅岭春历经艰险再次回到上海,家乡已发生“星转斗移”的变化,而寄居在上海的他们也面临着生活的“星转斗移”。《杏花春雨江南》中每一幕每一场开始前都引用了诗句,除第一幕前所引诗句的前半句“青山历历乡国梦”出自金代元好问的《梦归》外,其余的诗句均出自陆游的诗。第一幕所引诗句的后半句“芳草也知人念归”出自《怀故山》,这两句诗组合在一起,表达出浓浓的思乡之情。第二幕前的诗句为“灯前抚卷空流涕,重到故乡如隔生”,前半句出自《忆昔》,后半句出自《冬夜不寐至四鼓起作此诗》,表达回到故乡后,看到故乡惨状的哀伤。第三幕第一场前引用的“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出自《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写出了沦陷区百姓生存的艰辛;第三幕第二场前引用的“但愿胡尘一朝静,此生不憾死蒿莱”出自《病中夜赋》,表达出沦陷区百姓坚决抗日的决心和不怕牺牲的精神;第四幕前所引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出自《示儿》,表达了沦陷区百姓对抗战胜利的坚定信心。这些于伶精心挑选的,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与剧作思想高度契合的诗句为剧作注入了浓郁的诗意。孟超评价道,“《杏花春雨江南》的作者于伶,是一个最有现实感的剧作家,同时也是最富于诗趣的诗人……我们从他的剧作中体味到了一种诗情的抒发,而他的最近作品《杏花春雨江南》,更可以说是一篇最优美的抒情诗”[17]。
于伶戏剧的“诗性”还表现为在剧中插入大量诗句和歌词。于伶在剧作中多处引用诗句,穿插歌曲(歌词),与剧情及戏剧氛围相辅相成,融为一体。《花溅泪》中米米唱的《舞女曲》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号召、金石音唱的《松花江上》以及所念的诗“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表达出对沦陷家乡的思念;他给米米写的“情诗”诉说对米米的喜欢之情,更影射出时代的苦闷“夜雾沉沉,重重地压着铅样的心。铅样的心底,深深地浸着无名的哀愁!噙着无名的怅恨!”[18]作者借金石音的诗表达的是自己的情。《夜上海》中街头孤女哀诉的歌声“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喜几家愁;几家夫妻同罗帐,几家飘零在外头”[19]。梅岭春多次念道诗句“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杏花春雨江南》中插入的诗句更多,除了每一幕每一场开始前所引的诗句外,剧中梅岭春多次以古典诗句表达自己的情绪,并以诗句和典故来教育年轻人。如孟子的“壮者散于四方,老者转乎沟壑”①原句为“老赢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出自《孟子·梁惠王下》。,陆游的“但愿胡尘一朝尽,此身不憾死蒿莱”②原句为“但使胡尘一朝静,此身不恨死蒿莱”,出自陆游《病中夜赋》。,“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等,梅岭春经常读的就是陆游的《剑南诗抄》。于伶喜欢陆游诗句中表达的爱国之情,因此梅岭春在剧中多诵陆游的诗句,恰与每幕每场之前的诗句对应,增强诗意氛围,表达作者盼望赶走侵略者的心愿。“这种气氛或者这种情调(有时候也不就是一个东西,一个更多地属于环境,一个更多地属于人物,然而更多的时候,相映生辉)只是他的题材越来越靠近苦难的市民的生活的必然结果。他们处在前进无路、后退无路的暗无天日的统治之下,盼望胜利不到,只能长年吟咏陆游的诗句。”[10]此外,在不知道史砚芬真实身份的时候,梅岭春对她很是不满,于是借着孩子们采回来的野菜“薇”(又叫苓),引出了“采苓采苓,首阳之巅”之句,并向孩子们讲了伯夷叔齐的故事,讲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道理,提醒年轻人决不能失节当汉奸。《长夜行》中也用了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鼓励身在孤岛的知识分子不仅要在黑夜行路中自己不失足,更要跑在人群前面,引导老百姓不失足落水,不停留后退,要在黑暗的时代里放射出光芒。
《七月流火》中小阿罗和华素英哼唱的《莫提起》:“莫提起:一九三一年九·一八,那会使铁人泪下!我们的国,变成了蚕食的桑芽……”;“但是我们肯把功夫浪费在怨嗟?肯让敌人的棋子飘扬在老家?我们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爱自由的同胞,团结起来!……”[20]前一段是小阿罗所唱,唱出了侵略者对中国的蚕食;后一段是华素英所唱,号召同胞团结一致抗击日寇。华素英的母亲猜想女儿已经加入共产党后,询问女儿,因为纪律要求,华素英未能明说,其母说道,“我也应该跟世上的穷人,跟所有的孤儿寡妇相依为命!”华素英道,“妈还是很年轻!”接着外面响起了苍凉悲壮的惊喜老生的反二黄摇板:“恨胡儿,把我的,战马绞倒。不由我,年迈人……”,“叫老军,抬过了,定宋刀……”[20]唱段出自京剧《李陵碑》,是杨继业的唱词,表达老骥伏枥之情,与华母当下的心境相一致。《职业妇女会歌》则道出了“孤岛”妇女们坚强、独立、争取自由、不怕牺牲的精神:“新的女性,不做寄生虫,我们生产的女性,独立的女性,自由的女性……”[20]
将古典诗句和歌词插入在剧作中,以诗性的方式有力地表达了作者及剧中人物的感情,增强了剧作的感染力。于伶剧作中的这些歌词和诗词,有一部分是于伶直接引用或者化用的古典诗词,也有一部分是于伶自己创作的,比如《花溅泪》中的《舞女曲》、《女儿国》中的《采珠歌》以及穿插于整部剧中的歌词。除此之外,于伶还修改诗句表达诗情,如《浮尸》卷头的题词中,作者把李后主的诗句改成:“问君能有几多‘仇’,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所以,郑伯奇在《〈浮尸〉序》中指出,于伶“不断地在‘现代史实’中发掘国民诗歌的题材。是的,他是诗人。他有着昂扬的热情。他的写作不单是现实的表现,而是火一般的热情的流露”[21]。
(二)营造诗意氛围
于伶戏剧的“诗性”更表现为诗意氛围的营造。李健吾指出于伶创作戏剧“善于制造环境气氛的手法”,并且“有重点地、然而细致地说明环境。对话有时候会停下来,让位给周围的声响。你从这些声响听出了地点、季节和人物的心情,同时反衬在你的心里,又称为理解的因素。有时候他们只是色彩,只是气氛,然而更多的时候,他们加深人物的存在。”[10]
诗意氛围的营造首先表现在诗画交融的诗意景致。《夜上海》第一幕中以“秋风吹着梧桐,黄叶无声地飘着”描写环境,贯穿第一幕的就是“秋风,落叶”之景。《杏花春雨江南》中对环境氛围的诗意营造更具诗画美,第一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幕启时的“桐林尽处,远山历历,层峦叠翠/春之原野,辽阔、清丽/落花阵阵/细雨霏霏”,展现出春日细雨中江南农村的景致,同时也映射出沦陷区处在“阴雨”中的现实环境。当两个汉奸在郑根发处没有讨得便宜的时候,大家听到“林中有鹁鸪叫声”,此时“天气放晴”。鹁鸪叫有喜事,喜事的预示和天气放晴形成了呼应。从上海回来的梅珠和郑根发相认之后,“鹁鸪声声/落红如雨/云过天晴”,当大家看到梅岭春回来时“鹁鸪声”再起,“落花”纷飞。第一幕将江南的杏花、春雨美景尽数写了出来,且与剧情及人物的情绪融为一体。
其次是“静寂”氛围的营造。在于伶的剧作中,他会忽而中断对话或者行动,用‘无言’来概括事件的面貌或者心情的变化,一些时候,剧作家只是用一个“静”字或者“静寂”“静默”“空寂”“沉默”“死寂”等这样的两字词来说明一时的情况,表达“此时无声胜有声”的“静寂”氛围。“沉默本身没有什么特征,一切意义的根源全在于沉默在谈话中的位置,以及由此产生的受会话结构影响的预期。”①原为Levinson 的论述,转引自王虹的《戏剧文体分析——话语分析的方法》,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43 页。独幕剧《在关内过年》中,舞台提示中的“静寂”“沉默”,将这种“无声”的氛围展现了出来,很好地表现出了人物的感情,也让观众感受到在这“静寂”之下人物内心的不平静。年三十,奶奶期盼儿子回来,得知妈妈要包饺子准备过年,抑制不住对儿子的思念,责怪妈妈,妈妈竭力压制自己的委屈,抑制住泪水,喊了一声“妈”后:
奶奶怔住,难受得没有言语了。
静寂。
外面卖天竹、腊梅、长生果……声。[22]
屋内的“静寂”让位给外面的声响,屋内与外面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声响对比,更凸显出剧中人物对亲人思念的苦痛以及无可奈何的委屈与压抑。这种“静寂”氛围的营造在多幕剧中的表现尤其多。《夜上海》中“沉默”一词出现了15 次之多。每当谈及家乡的时候,梅岭春都心情沉重、郁闷,几度沉默;第四幕中,周云姑为了母亲的病、欠下的房租和年幼的弟弟苦苦寻找赚钱的机会,多次“沉默”表现出云姑的无奈,同时也反映出底层人民艰难的生活。《夜上海》,“它的主题是明显的,它的人物是存在的,然而那切腹之感,那最动人的语言,我们必须记住,不在它的对话,而在它的沉默。最传情处是无言。作者和导演用暗示来做口号,没有笔直的撼人的力量,然而像佳句一样,给你一种启示的力量”[15]。因为共处在同样的现实,即便演员不说出来,观众也会心领神会。《长夜行》中“静”“默然”“沉默”“沉寂”“死寂”“沉静”等词多次出现,其中仅“沉默”一词就出现了10次。尤其是在第四幕中,杨瑞芳带来多多已死的消息后,杨瑞芳和任兰多多次沉默,对一个小孩子的离世十分痛心,更让她们担心的是想要救活孩子而将自己登报出卖的母亲韩英该如何承受孩子离世的打击。韩英得知消息后,“如雕像一样地静止”,环境则是“死寂”,所谓“哀莫大于心死”,也不过如此。多次的沉默,“死的沉寂”的氛围,将几位女性难以名状的心情衬托了出来,也深深地冲击着读者和观众的心。《杏花春雨江南》《七月流火》等剧中也多次用“静”“静寂”“沉默”等词来营造环境氛围,表现人物情绪。在于伶的剧作中,“气氛和感情,外在和内在在这里织成一幅完整的图画”[10]。正如狄德罗所言“美妙的一场戏所包含的意境比整个剧本所能供给的情节还要多;正是这些意境使人们回味不已,倾听忘倦,在任何时期都感动人心”[22]。
(三)独具诗意的语言和意象
戏剧语言应在“内在节奏”和“外在节奏”的和谐中达到极致。所谓“内在节奏”,即人物情绪的自然消涨,“外在节奏”,即戏剧语言的韵律感和节奏感。于伶戏剧的“诗性”也体现在诗人独具诗意的语言描写上。于伶剧作中的舞台提示及台词都具有古典的诗意美。如《杏花春雨江南》中每幕开启时对环境的描写:“远山历历,层峦叠翠。春之原野,辽阔、清丽。落花阵阵。细雨霏霏,”,“秋云变幻,秋虫鸣唱,黄叶飘零”,“孤星三五中,新月一钩,挂着山尖”等句,这些语句既营造了诗意的氛围,也体现出剧作家对语言的运用能力。诗意氛围的营造就应该用带有古典美的干净洗练的语言来表现,于伶以其诗人的底蕴写出了诗意的语言,为诗意的氛围更添色彩。
《女儿国》第二幕中为了凸显鲛人、珍珍、珠珠与世间欲念过重之人的区别,他们三人的台词以诗歌的形式出现,富有韵律和较强的节奏感,朗朗上口。
珍珍:今天海里嗨,浪儿高,风儿吹,珍珠可难采。
鲛人:今天海里嗨,浪急潮高,风儿吹,珍珠嗨,珍珠窝里躲起来。
珠珠:瞧,春回来,满林桃花树树开。
珍珍:桃花开,春回来,茫茫大海,大好辰光珍珠采。
珠珠:嗨,大好辰光珍珠采,起什么风浪,带来了难和灾。
鲛人:别发愁,别发呆,珍姊姊,珠妹妹,风浪不是难,风浪不成灾,春回来,桃花开,风平浪静去下海,珍珠窝里珍珠采。[23]
在剧中突显意象,也是于伶表达诗意的一种方式。“意象所要求的是情景的和谐统一,是一个有机的内在的和谐完整而富有意蕴的境界。”中国话剧的诗化传统,“便特别注意戏剧意象的营造,追求真实的诗意、意境的创造,象征的运用”[24]。诗意意象的呈现在《七月流火》中的表现最为明显。《七月流火》中的意象便是水横枝。水横枝是江南的栀子花,栀子花“粗生野长,一点儿也不娇生惯养。它不计较土壤,山边水边,甜头路旁,处处生长。年年开花,开得又多又香”[25]。水横枝这意象代表着大众化,生命力旺,斗争性强,是华素英、路冰这样的战士不畏艰险、随遇而安、顽强战斗精神的象征。
田本相指出,“戏剧家应该是一个诗人,他首先应具有一颗诗心,才能有一双诗人的眼睛,去发现人间的诗意真实,发现生活的诗意存在”[26]。无论是在革命浪漫主义诗情的戏剧大师影响下形成的“诗性”底色,还是在国家民族危亡之时急切的“呐喊”,抑或是在“孤岛”时期限于“此时此地的环境”而形成的“含蓄蕴藉”,都是于伶戏剧创作风格中“诗性”的呈现和表达,都为于伶的剧作带来了深沉隽永的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