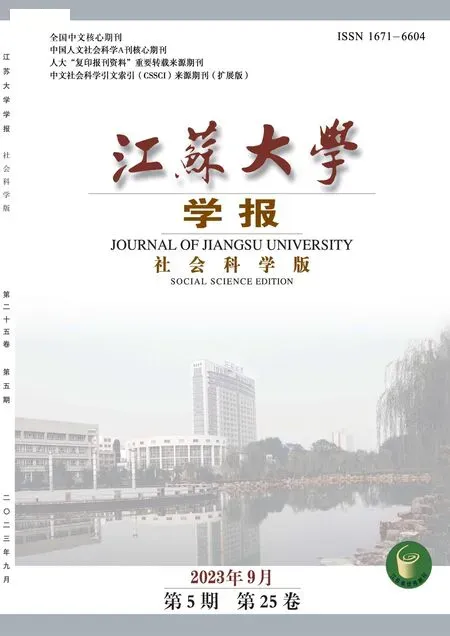数字资本主义中“生命权力”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
马俊峰, 张彦琼
随着资本与数字技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的理性化重构,全球资本主义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从效用上看,数字资本主义无论是对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还是对生活智能化的提高都有着积极意义。但同时,其中的种种弊端已然显现,尤为突出的是,当我们借助“生命权力”理论叙事去切中现实生命时,福柯所揭示的权力作用于生命的暴力特征和强制属性似乎已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并继续施展着它的力量,活生生的生命也并非如数字时代所期许的那样自由与幸福,相反,主体遭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挑战。大数据算法可能导致数据独裁,而大多数人不只是被剥削,还面临着更糟的局面:要么如永动机般迷茫倦怠地自我剥削,要么如草芥般无足轻重地苟且偷生。虽然资本主义推动科技带来了许多美好承诺,但从权力与生命互动角度看,展现出的却是威胁和危险的境况。究其根源,还是在于生命个体,或者说,是总体性人口蕴含着巨大且无穷的潜能和生命的各种可能性上,这有着无限“财富”的生命潜能可为权力持续地保持其旺盛生命力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因此,在主体更加彻底、全面地被数字化权力装置所铸造的背景下,揭露这样的权力装置是如何以全新的方式铸造主体,追问主体自由解放何以在数字时代成为可能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而这也正是我们借助“生命权力”概念进入当下时代的原因所在。
一、 数字资本主义中的“生命权力”叙事出场
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著名学者丹·希勒最早提出“数字资本主义”概念。他认为,所谓数字资本主义就是指“信息网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规模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与动力”(1)丹·希勒.数字资本主义[M].杨立平,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5.,因此,“在扩张性市场逻辑的影响下,因特网正在推动政治经济向所谓的数字资本主义转变”(2)同①:9.。进入21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信息网络空间和数字平台中的数据量更是呈现出井喷式的增长态势,数字革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改变着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伴随着数字技术与资本“合谋”的加深,资本已从实体范式蔓延至虚拟领域,完全实现了自身形态的数字化更新,“数字成为支配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指挥棒,成为攫取利润的数字资本,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3)邓伯军.数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逻辑批判[J].社会科学,2020(8):23-31.此时,一个以数字技术为主要技术支撑,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以数字平台为典型依托的全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扩大到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以至于与全面革新了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也呈现出了数字化新趋势。正如尼古拉·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指出的那样,数字化已经成为人们新的生存方式,“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行,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4)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 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269.。
诚然,数字资本主义无论对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还是对生活的智能化发展都提供了无限多的可能,然而,我们不禁还要追问,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是否能带来现代人生命处境的彻底改善?我们可否借助资本主义形态变革的新趋势探寻出现代人获得自由发展的数字化生存之道?面对“今日之思”,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聚焦到“主体治理”及“主体重塑以及自由何以可能”的问题上来,欲从现代社会涌现出的各种理论出发,探讨它们各自塑型主体、生命的方式,但却少有从“生命权力”的理论叙事进入数字资本主义去反思“今日之思”。那么,以“生命权力”叙事为立足点能否切中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现实问题,并把脉关涉主体的“今日之思”呢?
自福柯起,他开始对传统宏大权力叙事产生怀疑,并在批判传统权力叙事的基础上开启了权力在微观层面上的治理阐释机制。福柯从西方治理术谱系出发,对传统政治哲学中的权力问题进行了重新解读,这是一种散布于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如毛细血管般的权力机制研究。他发现权力不仅具有压制性特质,相反,它还是一种锻造和铸就主体的力量。正是基于这一新的研究路径,福柯将其发现于18世纪下半叶的新权力命名为“生命权力”。在他看来,“生命权力”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权力类型,它是总体上运用于人口、生命和活人的权力,它干预怎样生活,是“对生命,对作为类别的人的生理过程承担责任,并在他们身上保证一种调节”(7)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M].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88.。“生命权力”作为现代社会一种独特权力叙事方式不仅被福柯正式搬上历史舞台,还继而成为之后一大批思想家反思西方现代社会主体生存境遇的主要理论来源和概念工具。具体来看,对“生命权力”叙事的理解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从“生命权力”叙事的权力作用对象看,其主要考量的是作为政治概念“人口”的生命。“人口”作为一个新的政治概念是“生命权力”叙事的核心要素。17世纪之前,“人口”都是以“人群的数量”“居住者的数量”出现的(8)米歇尔·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M].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67.,常与重大流行病以及导致大量死亡的灾难相关。进入17世纪,它逐渐指向了与君主权力相对应的“臣民”概念,成为被统治权所用的事物,是需要被权力干预的、否定的,以及消极的事物。直到18世纪末,“人口”概念才随着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实践而发生了趋向“自然性”的转变,才开始被视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生命体”。随之,权力再也不能以命令、统治等方式加以改变它,而要随着人口自身运作的法则去利用它。这样,利用人口自然性的权力便随之产生,它就是“生命权力”。“生命权力”与之前对肉体的惩罚性权力技术不同,它是权力的另一种技术,即“非惩罚性技术”。这个新技术不排斥前者,“而是包容它,把它纳入进来,部分改变它。新技术指向的不再仅仅是肉体,它开始指向‘人的生命’,针对‘活着的人’”(9)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M].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85.。
从“生命权力”叙事的权力运作领域看,其主要依托实体性的全景敞视性空间。全景敞视性空间是一种建筑学结构,最初来源于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指一种用来严密监视环形建筑里囚犯举动的建筑。它代表着权力的眼睛,一方面可以通过各类监视系统对空间的各个角落进行管控,另一方面可以规训和调整肉体的行为,“不让最细微的事物摆脱其控制”(10)同①:56.。全景敞视性实体空间与主权权力在军队、法庭、监狱等权力机构不同,在传统封闭性惩戒空间内,主权权力所施展的是夺取、占有、控制等“让人死”的惩罚性权力运作模式,而“生命权力”是一种以安全机制为名的保护和提高生命的权力,它的运作领域具有弥散性特征。那种高高在上的权力此时已开始弥散进诸如学校、工厂、医院等具有全景敞视特质的机构中,这些权力机构的主要功能不是消灭生命,而是干预和调节人口及其生命状态。同时,它更创造出一系列可以渗透在多样性机构中的机制,使得所有机构都成为可以利用人口及其相关因素的领域。
鉴于“生命权力”必然锻造和铸就主体的特质,它的叙事方式则以切中“人口”生物性生命的原则,以关照“活着的人”生活和福利的名义,努力摆脱着至高权力强加于生命之上的桎梏。既然如此,我们不禁要问:“活着的人”摆脱至高权力桎梏之后,就真的能够在“生命权力”的安全部署下自由、民主且博爱地活着吗?其实,在福柯看来,“生命权力”所倡导的福利与自由并非纯粹的一种观念,一种意识形态,它其实为资产阶级治理做了精妙布展,它以无法透视的隐性机制散布在政治中,“它不再赤裸裸地施展,它被精心地制定、被改变,被组织,它自身拥有程序,以便或多或少地适应形势”(11)米歇尔·福柯.主体和权力:上[J].汪民安,译.美术文献,2011(4):100-103.。由此,“活着的人”在这种安全部署下无怨无悔地“自由生存”成为主体在新历史阶段最显著特征。福柯通过这一叙事方式,揭示出“生命权力”所隐匿的资本主义虚假性自由和强制性属性。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全面崛起,今天的“生命权力”叙事已并非福柯所描述的那样,它早已被另一种形态所取代。亦或者说,“生命权力”叙事的内涵不应被理解为静态的、固定的,相反,它处于一种动态变化之中,这种动态发展特质使得它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不断得以补充与丰富。数字资本主义的诞生,一方面得益于数字技术发展的助力,另一方面更是资本自身运行逻辑的结果。特别是资本追求价值增值的力量使其自身成功实现了形态的数字化革新,而资本的数字化形态又进一步助推着“生命权力”叙事的数字化演进,这一切都将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生命权力”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新特征提供必要的前提。那么,以资本的数字化形态为入口进入“生命权力”叙事的数字化演进又是怎样体现的呢?
其一,“数字圈地”带来了“生命权力”叙事中的数据人口。正如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资本需要通过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方式占有大量劳动力和原始资本以实现全面勃兴一样,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依旧需要借助“数字圈地”将私人化的生产资料集中,并垄断占有。一方面,对于广大数字劳动者来说,他们是海量原始数据的生产者,但他们的劳动成果却被掌握资本的“霸主”免费圈占并使用;另一方面,作为数字生产重要生产资料的各种数据平台、应用软件的所有权也被少数坐拥世界互联网控制权的“霸主”所拥有。根据2020年度全球十大互联网公司排名来看,其中有8家总部设在美国,但它们却拥有80%在美国之外的用户。因此,较之于传统方式,资本借助“数字圈地”,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和商业营销手段圈养了大量用户,用户数量越多,数据就越多,数据越多,数字资本的力量就越大。借助“数字圈地”,“生命权力”纳入治理和调节的人口及生命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医院、疯人院、监狱中的特殊群体,而已转变为与数据直接相关的数字化人口及其生命。数字化将人们在实体空间的一切存在转译为包括语言、图像、影像为主的数字符号,将人们在互联网上的每一个行动都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将他们的每一个足迹都编译为二进制数据储存起来,使之成为一种可被权力强制干预的对象。换言之,此时,作为数据存在的数字化人口具备了更为强大的生产性力量,可为“生命权力”所用。
其二,数据商品成为“生命权力”叙事纳入的新要素。数据作为数字时代“生命权力”叙事全新的纳入要素在本质上来看,只是数字化人口在互联网上基于生活、工作、社交、娱乐等目的留下的原始数字行为痕迹,或者说,数字化人口的生存通过数据的形式才得以显现,它们数量庞大且无序可循。但当它们具备了现实的有用性,并继而成为可交换的商品之后,便可具备一种生产性力量而成为数字资本源源不断的动力。数据由原始状态转变成商品的关键环节恰恰就是理解“生命权力”何以将数据纳入叙事的关键。这里涉及一个重要概念:二次加工。所谓的“二次加工”,即基于云计算、算法的“大数据”分析,“一种通过分析庞大的数据来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或判断”的概念(12)城田真琴.大数据的冲击[M].周自恒,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3.。 原始数据只有经过专业化大数据分析后,那些不被重视且有价值的信息才能被提取出来,继而整合到业务流程中,成为商业决策与行动指南的依据。也正是因为数据的有用性被提炼出来,它便可以被当作商品而进行交易。其实,数据的有用性归根结底还是数字化人口的有用性,借助二次加工,数字化人口的自然性可以被生命权力认识、干预和诱导,继而被引向一个有利的方向,产生出必要的有益效果。
2组治疗前后SF-MPQ各项评分比较,治疗后及3个月后随诊,2组PRI、VAS、PPI 3项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均P<0.05)。2组治疗后及治疗3个月后随访比较,结合组3项评分均低于针刺组(均P<0.05),见表2。
其三,“生命权力”实体全景敞视空间的透明化演进。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必将创造出一种积累资本的新途径,以此,资本借助数字技术载体进行形态革新而获得新生才能成为可能。数字资本利用“平台”活动场域对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进行重构的同时,又进一步促动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平台,这个数字资本开拓的新领地同样也是“生命权力”实体全景敞视空间透明化演进的形态。“透明化”是韩炳哲分析数字时代权力叙事的新概念,它是指“当被观测者和观察者之间没有任何中介时,当没有任何可以隐藏起来时,一切都能被看到时,社会就会变得透明起来。”(13)LANDZURI M C. Psychopolitics and power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ought[J]. Journal of political power,2019(1):1-12.此处,“透明的媒介不是光,而是没有光的射线,它不是照亮一切,而是穿透一切,使一切变得通透可见”(14)韩炳哲. 透明社会[M].吴琼,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67.。在透明化的平台中,有着全方位的数字监视程序,“生命权力”在其中将数字人口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社会认同等具有社会关系内涵的具体内容通通过滤掉,使真实的生命变成一串串可以被利用的数据,建构起对主体全方位形塑的一套全新数字化透明治理术。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与“生命权力”叙事相关的诸因素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都开始被由数字所构架的世界助推着完成了自身的数字化演进。这个时候,与“生命权力”原初出场直接相连的实体景观的重要性萎缩了,与之相应的原有叙事方式和分析策略的效用性也降低了。因此,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今天,“生命权力”叙事机制得以全新阐释将成为必然。既然如此,“生命权力”在数字时代究竟展现出哪些新样态呢?
二、 数字资本主义中的“生命权力”叙事新样态
“生命权力”在数字资本主义中的叙事逻辑正在发生着深刻的转换。在前数字时代,“生命权力”主要是在相对封闭的实体全景空间中,以“暴力性”和“无声强制性”构序穿透于生命。如今,另一种范式正在形成,即发生在透明化的平台中,“生命权力”正在以一种更加彻底、更加完善、更具有效力的治理技艺作用于生命。尽管以德勒兹、鲍德里亚为主的思想家们已看到原初“生命权力”叙事力度在数字时代的局限和缺憾,特别是韩炳哲,更是用“精神权力”代替“生命权力”以表达他的不满,但就本质来看,“生命权力”在数字时代叙事的诸种新样态并没有改变其就生命过程的二元性建构模式。既然如此,“生命权力”在当下的“新样态”中又是如何展现的呢?
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生命权力”叙事的审视完全不同于福柯、阿甘本等人的阐释逻辑,而是一种新的“全面统摄”力量的展现。在福柯那里,“生命权力”从开始承担起生命的责任,并将其牢牢系缚在权力话语体系中,就已展现出全面统摄的力量。从生物性生命的出生、健康、生殖到死亡,从肉体的规训到生命的调节,权力对所有与生命相关的现实要素加以干预。只不过权力的全面统摄性力量并无涉及生命心理的内部因素。同样,在阿甘本那里,权力的全面统摄性力量是从权力对生命的捕获式压榨与剥削,以及它试图激发生命形式的力量两个维度展现的。正如基西克所言:“我们所谓的全面统摄生命的权力真的只是生命力量的伪装,生命的力量真的只是生命之间的力量关系。严格来说,单个个体的生命本质上既不屈从于权力也不占有权力。”(15)刘黎.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 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197.因此,数字时代对“生命权力”的全面统摄力量的理解就不能仅仅只局限于单一的压抑功能,而应该兼具“生命权力”压抑与生产的双重功能。这就意味着,“生命权力”的全面统摄样态必然是兼具权力的双重功能的。一方面,基于“生命权力”叙事各要素的数字化演进,“生命权力”在平台架构的透明社会中渗透进几乎与生命相关的所有领域,由此形成了一个将生命纳入的“数字权力群岛”。另一方面,从生命的生产性维度看,“生命权力”利用生命本身的力量和潜能对生命实施了一种所谓的“经济人”形塑,将其最大化地依据权力希望的模式进行铸造。
首先,“生命权力”的全面统摄力量体现在“生命权力”对时间的全方位挤兑上。在马克思看来,对人的关照可以放置在对人所经历不同时间的关照之下,正因如此,他始终在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张力关系中探索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发挥的作用。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生命权力”更是以对时间的全方位挤兑布展起对生命的调节机制,具体通过产消合一和流通两个方面体现出来。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尽管劳动作为人类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本质没有发生变化,但其形式的数字化转变已是当下的共识,即一种被称为“数字劳动”的人类新型劳动形式。虽然对“数字劳动”概念的建构众说纷纭,但就这一新型劳动形式来说,它所呈现出的特质却有着共性,即免费性、非物质性、情感引诱性、产消合一性和创造性。特别是产消合一性更是开启了数字劳动研究之新航向,“互联网作为一种传播手段和生产工具已经见证了产消合一的成长过程”(16)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文森特·莫斯可.马克思归来:上[M].“传播驿站”工作坊,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63.。虽然产消合一现象在前数字时代就已经存在,但在数字资本的加持下,传统生产和消费相对独立状态的边界变得模糊甚至消失不见了。产消合一劳动者在某种层面上可以指代所有参与到网络中的用户,即数字化人口。数字资本依托平台,使数字化人口不仅成为数据的生产者,更成为数据的消费者,二者统一于“产消者”的角色。对于数字化人口,不仅是他们的劳动时间,就连娱乐时间和睡眠时间也都被“生命权力”以一种诱惑式方式征用了。福克斯认为,用户的所有在线花费的时间都在生成产消者商品,都是劳动时间。“用户在其上花费的时间就是他们为平台资本家无偿数字劳动所创造的价值。”(17)FUCHS C.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M]. New York:Routledge, 2014:95.尤其是,当作为产消合一者的用户浏览广告或点击广告时,更是将生产价值转换为利润的过程。因此,用户在互联网上花费的时间越多,其劳动时间也越长,相应的,数据商品就变得越有价值。而正是基于平台这一“自然”规律,作为用户的数字化人口在享有“自由”进入各类平台的同时,实则陷入了一套不断吸纳他们产消合一劳动时间的“生命权力”机制。“生命权力”从传统的显性压迫式布展转变为隐性的以娱乐、游戏、消费为主导的生命调节机制。比如,通过精妙的算法法则,平台装置会一直源源不断地推送给用户符合个人喜好的信息,从而引诱用户延长在线时间。再比如,用一种策略将劳动与游戏紧密相连,使得娱乐等游戏形式占用了本该全部拥有的闲暇时间,甚至是睡眠时间。
同样,从流通领域来看,“生命权力”正在努力消除流通时间,以一种时间消灭空间的方式,将生命的实体空间存在彻底挤兑为零。其实就“时间对空间的消灭”,马克思在资本的流通中就有所提及,资本试图与时间一起,“将这个空间消灭,也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程度”(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9.,而这一命题在数字时代彻底得以实现。在这个算法交易主宰的世界,“生命权力”在扶植、看护生命的幌子下,倡导一种遍及于产消领域的加速方式,为数据化人口带来更多的便利。此时,“生命权力”架构起了一套保障数字化人口整体幸福的经济形式,它利用人口有欲望的自然性规律,在放任这种自然性的同时又加速着它的自动运转,以期提升资本的力量。由此,交易时间不再以原有的时间来测量,而是以更快的非人类软件算法,如毫秒级的单位测量,以此,原本存在于实体空间的流通时间被减少到了几乎不存在,巨大的地球实体空间瞬间就被压缩为零。
其次,“生命权力”全面统摄力量体现在对生命所有能力捕获的新样态上。实现了数字化演进的“生命权力”试图囊括仅有的人类能力来生产知识、传播、参与或合作。这些包括认知、情感、注意力、创意的能力是人类所特有的,但现在却被“生命权力”借助种种数字技术直接征用,以期实现对生命最深处的干预与操控。其中,以对人的情感和注意力能力的捕获最为新颖和突出。
“情感计算”(affective computing)或“情绪计算”(emotional computing)是兴起于20世纪晚期的一种关注人的情感或情绪的数字计算,该技术旨在“通过电脑技术来模拟人的情绪能力,以此将情感性嵌入社会技术系统,继而使资本能够利用认知或无形性来实现自我再生产”(19)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文森特·莫斯可.马克思归来:上[M].“传播驿站”工作坊,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65.。对于已经实现了数字化演进的“生命权力”,它正是捕捉到情感在生命互动中无处不在的特质,借由情感计算介入数字化人口的生命,以此操控现实中人的观念、判断和行动。与前数字时代依靠身体的直接在场来调动情感相比,如今的数字化场域比实体场域更能有效地调动和利用人们的情感或情绪。此时,情感或情绪成了外在于人而存在的客体和对象,可被“生命权力”借助数字计算观察、控制和利用。例如,依据玩家情绪状态开发和设计的情感类游戏,就能实现针对玩家不同情绪的游戏内容推送,并进一步将玩家的情感状态推送给第三方,以实现潜在的价值转化,其中,对玩家不同情绪的捕获则直接依赖于玩家的数字化存在。
除此之外,还有人的注意力。注意力在赫伯特·西蒙看来,是一种在市场上可以交换,并受供求规律影响的商品,而克劳迪奥·布埃诺则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入手将注意力理解为一种新的劳动形式,并以此提炼出与之相应的资本主义提取剩余价值的经济形态,即注意力经济(20)CELIS C. The attention economy: labour, time and power in cognitive capitalism[M]. London: Rowman &Littlefield International, 2017:17-21.。在此,我们依据克劳迪奥·布埃诺的观点,将注意力理解为一种能够提取价值新来源的劳动形式,它的主体就是参与到互联网中的所有数字化人口。“生命权力”捕捉到了生命这一曾经不被重视的能力,从而成功将其纳入。具体来看,也就是数字化人口在平台上的所有由注意力引发的行为痕迹都可被转化为元数据,之后再经过大数据的二次加工被出售出去。由此,它们就成为调整生产、分配和销售的重要依据。其实,数字化人口由注意力引发的每一个行为都被“生命权力”纳入的同时,也丧失了其本身具有的专注能力,平台上海量捕获数字化人口注意力的信息不仅不会让人们变得更聪明,反而会让人们产生注意力障碍。
最后,“生命权力”的全面统摄力量还体现在它利用生命本身的力量和潜能对生命实施的一种所谓“经济人”的铸造上。福柯强调,权力不仅有否定性逻辑,还有将个人建构成与权力相关因素的逻辑,即权力的生产性形塑。他认为:“我们不应再从消极方面来描述权力的影响,如把它说成是‘排斥’‘压制’‘审查’‘分离’‘掩饰’‘隐瞒’的。实际上,权力能够生产。它生产现实,生产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21)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218.权力能够生产与铸造主体,而不仅仅是压迫和镇压。因此,他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经济人”(homo oecnomicus)概念,一个由新自由主义权力机制铸造出的“自身的企业家”。作为自身的企业家,其自己成为自己的资本,自身成为一个有效的投资领域,将自己打造为更好的劳动者。“生命权力”此时并不强制和命令,相反,它只是顺应着经济人的自然性,即充满欲望,逐利的自然性,对其加以利用、诱导和放任罢了。
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后,“生命权力”更是诱导着将所有人都铸造成平台中的经济人。它利用人们逐利欲望的天性,借助平台,诱导经济人为自身利益去不断放大欲望,比如,延长参与各种诸如浏览、购物、游戏等在线时间。同时,欲望的不断被放大又会使经济人借助平台以侵占自身时间和空间的方式最大化地投资自己,将自身作为一个有效的投资领域去精心打理。这就是“生命权力”所设想的一种数字化生命的存在样态,即通过在平台提供各类海量信息和商品诱惑数字化人口,实现操纵数字化人口欲望和需求的目的。而作为经济人的数字化人口其实对这种诱惑一点也不反感,相反,他们甚至主动拥抱诱惑,同时他们感受到的也只是自我的流失。与此同时,我们发现,活生生的生命则变成了一个个独立或相互关联的数据,成了受算法隐性控制、支配的数字化奴役者和免费的数字佃农。数字时代生命的隐性压抑生存状态似乎已成为“生命权力”叙事在数字时代的续写,更是福柯在其权力关系理论中展现出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深入批判。
三、 “生命权力”叙事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
今天,依据“生命权力”叙事逻辑,主体似乎已丧失了自由和解放的希望,至少是对于那些只从“生命权力”消极原则出发的人来说,主体已彻底陷入困境之中,除非等待那种“元叙事”意义上颠覆性理论的出现。也就是说,如果仅从“生命权力”叙事的消极原则展开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那我们必会将“生命权力”解读为一种权力本位,并得出主体永远无法逃离权力围墙,只能被再次编码与控制的结论。实际上,“生命权力”叙事遵循的原则并非单一和消极,否则,这样的理解将促使研究者们因错失“生命权力”叙事的积极性特质而造成批判与建构相脱节的局面。如果以更广的历史视野和更深的理论旨趣来分析,“生命权力”叙事应具有更为深邃的核心意旨,那就是兑现其最初“看管与服务”生命的职能、激发出主体的生命潜能,克服“生命权力”对人的宰制、支配、监控,并最终指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积极性内涵。
“生命权力”叙事的积极性内涵有赖于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域下重思其原初叙事逻辑得以展现。“生命权力”与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能进入共同的语境,是因为它们分享着共同的理论视域,都是现代性批判绕不开的话题,但同时,两者在方法和路径上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就为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对现有“生命权力”叙事展开批判提供了可能性。从本质上看,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命权力”反思是对纯粹思辨政治哲学批判的扬弃,它从现代人的现实境遇出发,揭示出权力对现代人制造的肉体压迫和生命调节,这恰恰是现代性批判的独特形式。然而可惜的是,福柯却将马克思从生产方式入手的现代性批判拓展为从政治权力分析入手的生命政治批判,偏离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体是被特定生产关系建构起来的事实,错失了对展现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全貌的“资本”原则揭示。因此,“生命权力”叙事不可避免地成为柏拉图主义的当代注脚,这无疑是该理论最大的局限性所在。
马克思则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奠定了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他以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为线索,在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实现了权力问题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会通,以此表达出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现实的人”命运的深切关怀。由此看来,“资本”与“劳动力”这两个概念是进入“生命权力”叙事之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的关键,以此为前提,才能进一步展开“生命权力”叙事的积极性内涵讨论。首先是“资本”。“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就是以资本是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为主导性话语展开的。在对现代性的诊断上,马克思实现了资本与权力的话语统一。作为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的资本,它必须与作为主体的劳动力互动,“必须要穿透到主体们的身体中,以及穿透到生命的诸种形式中”(23)NITZAN J, BICHLER S. Captial as power: a study of order and creorder[M].Abingdon: Routledge, 2009:3.,才能彰显出其自身的力量。经济视角下的权力力量对主体的纳入,构成了现存世界的根本性质,马克思真实地勾勒出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以及主体被经济权力统治的本质,这种权力关系无处不在。作为一种权力机制,“生命权力”归根结底源自于这种经济权力。其次是“劳动力”。劳动力作为一个活的生命体,它包含着能力、潜能与动力,是唯一能够创造价值的要素,正因如此,劳动力可成为被作为经济权力的资本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中,劳动力身体中所蕴含的生命机制和生存要素成为一种生产要素,以此为前提,生命便开始抵达权力的中心。“生命权力”叙事的本质完全通过资本作用下的生产过程表现出来。
我们看到,要厘清“生命权力”叙事的积极性内涵,就要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最深处,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来反思权力关系中的资本。这一方面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价值,成为我们回到马克思的当代路径;另一方面,为“生命权力”的叙事寻找到了合理性、有效性依据,为探寻到其积极性内涵找到了可行性路径。既然如此,接下来就要继续追问,作为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的资本何以从根基处施展出“生命权力”的运作机制呢?这可从权力穿透于生命的两种方式呈现出来。首先,权力基于生命的暴力性构序。在资本主义的史前阶段,就发生了权力借助暴力手段掠夺人口的时期,即马克思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自此,劳动力作为此时的人口表现为“自由”,但这种自由具有模棱两可的特征。一方面,劳动力摆脱了封建统治者的统治,获得了对自我劳动实现的自由所有权;另一方面,权力借助暴力手段使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使他们成为除了雇佣劳动力外,别无选择的“赤裸生命”。其次,是权力基于生命的“无声强制”性构序。离开原始积累领域,进入生产领域后,权力作用于生命的另一种方式便大行其道。具体来看,权力的“无声强制”主要体现在从劳动形式从属于资本到劳动实际从属于资本的过程中。在劳动形式从属于资本时期,权力对劳动力的规训是“使人活”的身体规训,它通过延长工作日、对劳动作息的精细化管理,以及对劳动过程的监督等“无声强制”手段规训劳动力肉体。到了劳动实际从属于资本时期,权力彻底展开对劳动力生命每一个细节的操控,打造出片面的、附庸性的生命存在形式。
由此来看,与资本合一的权力作为一种将生命纳入并对其实施了从暴力到无声强制的经济权力,其本质上不仅完全与“生命权力”的运行逻辑相契合,而且为认识后者的历史本质提供了基于根基处的阐释机制。既然如此,面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崛起和资本的数字化形态革新,我们更应依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继续深入探究。在马克思看来,对于这个形式上以自由为原则、内容上以资本为原则的资产阶级社会,它注定无法长期存在,在他这里还存着一个基于人类文明历史发展规律之上的解放叙事逻辑。这个逻辑站在一个更为宏大的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上将人类历史的普遍性维度推陈出来。因此,只有基于人类文明历史发展规律去审视权力与现实主体之间的矛盾性关系,“生命权力”叙事的积极性特征才能得到彰显。这正是建立在对现有“生命权力”叙事的批判和反思基础之上的,缺少这种基于根基处的反思,资本主义框架下的“生命权力”叙事就无法突破其消极性叙事逻辑而创造性地塑造和引导积极性内涵。一旦我们将目光转向这个维度,权力照看、扶植生命的职能才能得以真实地显现,它指向人的生命潜能、类存在,以及自由个性的普遍实现,并最终指向每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由王国”。
当我们进入到更为宏大的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中去考量“生命权力”叙事时,才会发现,尽管“生命权力”叙事的消极性原则长期垄断着人们对生命境遇,乃至数字时代生命境遇的认识框架,但却忽视了一个极为关键的要素,那就是生命自身的力量,一种生命内在寻求自由的潜能。“发现生命走向自由的无限力量,在不同种类的生存技艺中探寻出走出权力沉重枷锁的方法,这就是生命力量之所在,是生命本身蕴含的力量的典型体现。”(24)刘黎.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 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192.毕竟,“生命权力”将生命纳入的构序是与生命探寻自由力量同时存在的,我们应该在二者张力间找到“生命权力”积极性叙事的突破口,找到数字时代生命存在的最优样态。尽管哈特、奈格里等人也承认“生命权力”能够将人生产为具有反抗性的另类主体,依据每个人“生命本身蕴含的力量”,一种主体的“自发产生”的动力学可以激发出生命寻求自由的潜能。那么,以此为基础的革命事件为何迟迟没有到来呢?生命的解放潜能如何才能转化为现实呢?
在马克思这里,依据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之上的解放叙事逻辑,不仅可以看到存在于“生命权力”根基处的资本运动轨迹,更能沿着这个轨迹发现资本裂缝中生命的解放潜能。因此,我们不禁要追问,资本的裂缝究竟在何处?只有揭开这个秘密,数字时代“生命权力”的积极性内涵才得以开显。揭开秘密的关键便是劳动,更确切地说,揭开秘密的钥匙存在于资本与劳动的张力关系中。在马克思看来,本来作为生命之自由本性存在的劳动,却造成了劳动者生命自由本性的丧失,而使劳动具备异己属性的力量便是资本。可以说,马克思并未就此停止,而是在揭示劳动异己属性的基础上又获得了批判和超越资本力量的有力武器。我们看到,资本的裂缝恰恰就存在于“资本与劳动的张力”关系中,存在于劳动的自反力量中。主体不仅是从属性的存在,更可以借由劳动的力量拥有反抗从属地位,突破资本力量之网,并使其具有破裂的潜能。正如马克思所说:“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2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3.
然而,劳动逃离资本围墙、冲破资本裂缝后的方向在哪里呢?马克思给出的答案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是一条劳动组织方式的重构路径,一方面,可通过改变劳动者的劳动组织方式打破现有劳动组织方式背后的资本框架;另一方面,可激发劳动背后生命的潜能,从而有效地推进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基于此,一个现实可能性的未来新型共同体——“自由人的联合体”便被呈现出来了,它是一个以自由联合劳动为自身经济基础的共同体,人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26)同①:96.。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4.。因此,人的真正自由发展不能靠从头脑中的虚幻观念来实现,而只能靠建立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真实共同体”中来实现。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所蕴含的逻辑,数字时代“生命权力”叙事的开显可以指向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也就是说,主体的启蒙与觉醒、主体的自由与个性、主体的潜能与创生只有建立在整体性的人类解放的基础上,才是有可能的。在个性和人类、个体和整体、种生命和类生命相统一的基础上,自觉地把个人的自由熔铸在人类解放的历史进程中(28)高海清.找回失去的“哲学自我”:哲学创新的生命本体[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06.。也只有如此,“生命权力”叙事才能在基于原初“看管与服务”生命的职能、激发出主体的生命潜能,通过不断克服与超越资本框架之中的“生命权力”对人的宰制、支配、监控的境遇,在社会历史的革命实践活动之中,使得人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起来,在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中开启人类通向自由与解放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