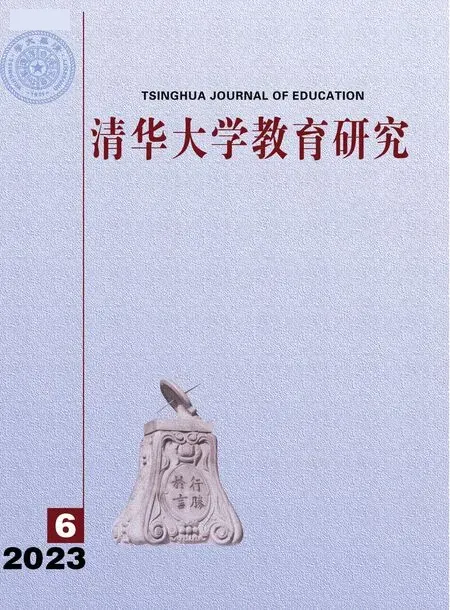虚拟世界的健康代价:网络游戏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的实证分析
孙 浩 苏 竣 汝 鹏
(1.清华大学 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 北京 100084;2.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4)
一、问题提出
人类正在进入智能时代,由赛博空间行为引发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成为时代进步诱发的问题之一,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也越来越成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前进路上的绊脚石。进入21世纪,网络游戏开始在中国流行,我国网络游戏产业发展以及游戏用户消费均得到爆发式增长,与此同时,中国青少年和年轻人的心理健康开始恶化,其中焦虑和抑郁是青少年增长最快的心理疾病。(1)David A.Scott et al.,“Mental Health Concerns in the Digital Ag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 15, no.3(2017):604-613;章正.青年心理健康拉响警报:近三成有抑郁风险[N].中国青年报,2019-04-11(7).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诱因具有多样性,其中网络游戏的流行被很多学者认为是一个重要的促成因素。(2)Kimberly Young et al.,“Cyber Disorders: The Mental Health Concern for the New Millennium,”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2, no.5(1999):475-479; Christopher J.Ferguson et al.,“A Meta-analysis of Pathological Gaming Prevalence and Comorbidity with Mental Health, Academic and Social Problems,”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 45, no.12(2011):1573-1578; Yatan Pal Singh Balhara et al.,“Media Reporting on Deaths Due to Suicide Attributed to Gaming in Digital News: A Case of Misrepresentation and Missed Opportunities,”As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68,(2022):1-4.https://doi.org/10.1016/j.ajp.2021.102955.“对于(中国)年轻人来说,网络游戏与美国婴儿潮一代的电视一样,是一种娱乐。”(3)Nir Kshetri,“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Online Gaming Industry,”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in China 4, no.2(2009):158-179.网络游戏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学生可以将其用于娱乐,也可以作为逃避现实的方式加以放大,以至于网络游戏成瘾。(4)Gi Jung Hyun et al.,“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Online Game Addiction: A Hierarchical Model,”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48, no.7(2015):706-713; Jeroen S.Lemmens et al.,“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Game Addiction Scale for Adolescents,”Media Psychology 12, no.1(2009):77-95.智能社会是虚实融生的社会。从现实世界来看,既有研究指出,同辈群体对学习成绩有积极影响,对学生心理健康有负面影响;(5)曹蕊,吴愈晓.班级同辈群体与青少年教育期望:社会遵从与社会比较效应[J].青年研究,2019,(5):25-33.从虚拟空间看,网络游戏在本质属性上就是网络空间群体性竞技娱乐活动。同辈群体与网络游戏是如何虚实融合地影响学生心理健康?对此,尤其是在中国情境下,明确的因果证据仍然很少,(6)Luciana Lima et al.,“Digital Games and Mental Health: A Scoping Review on Gaming Disorder in the Last Decade,”in Digital Therapies in Psychosocial Rehabilitation and Mental Health, eds. Antonio Marques and Ricardo Queiros(Mediterranean Region: Medical Info Science Reference,2021),142-162.亟需实证检验。
本研究采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2014-2015年)进行实证检验。本文构建一个多层模型以便于清楚捕捉到“学生个体嵌套于学校”的跨层现象对微观个体的影响。我们发现,玩网络游戏的学生比不玩网络游戏的学生的心理健康指数低。我们还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构造一个反事实分析模型,就网络游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进行实验性评估,就玩网络游戏对学生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的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本文主要借鉴教育学与心理学的理论视角,分析网络游戏对青少年心理健康负向影响的因果效应,并借鉴社会学的一些理论,控制家庭、同群、学校等变量,试图在影响心理健康的复杂驱动因素中发现新变量,为智能社会网络游戏政策制定提供经验启发。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心理健康。心理健康是指“个人实现其自身能力、能够应对正常生活压力、能够富有成效地工作并能够为其社区(社群)作出贡献的一种幸福状态”。(7)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Mental Health,”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mental-health-strengthening-our-response.根据观察,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爆发的空间范畴与时间区间,与网络游戏等社交媒介在全球采纳、扩散的空间范畴与时间区间呈现高度的吻合,难免会使学者从历史视角及统计视角猜想前者的危机受到后者流行的影响。(8)Vikram Patel et al.,“Mental Health of Young People: A Global Public-health Challenge,”The Lancet 369, no.9569(2007):1302-1313; Jean M. Twenge et al.,“Age, Period, and Cohort Trends in Mood Disorder Indicators and Suicide-related Outcomes in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Dataset,”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28, no.3(2019):185-199.
相关领域主流文献显示,消费者对网络游戏的消费将对其自身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9)Hunt Allcott et al.,“Digital Addic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2, no.7(2022):2424-2463; Luca Braghieri et al.,“Social Media and Mental Health,”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2, no.11(2022):3660-3693.网络游戏影响心理健康具有不同的作用路径。首先,“暴力涵化路径”。网络游戏是网络欺凌发生的典型场合,特别是暴力游戏,常伴随打斗与谩骂。有实验研究指出,网络欺凌的大学生受害者在抑郁、焦虑、恐惧和偏执狂等方面的得分高于匹配的对照组。(10)Allison M.Schenk and William J.Fremouw,“Prevalence, Psychological Impact, and Coping of Cyberbully Victims Among College Students,”Journal of School Violence 11, no.1(2012):21-37.其次,“逃避现实路径”。“逃避现实”的动机在游戏时间和心理健康之间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玩游戏的时间越长,逃避感越强,心理健康情况越差。玩游戏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联也并非完全由“逃避现实”动机来调节。游戏的“逃避现实”动机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又受到自尊水平的调节,低自尊个体总体上心理健康状况较差。(11)Cian Goh et al.,“A Further Test of the Impact of Online Gaming 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the Role of Play Motivations and Problematic Use,”The Psychiatric Quarterly 90, no.4(2019):747-760.再次,“数字成瘾路径”。在线游戏等活动可能会强烈地激活神经奖励通路,使其产生类似于酒精、鸦片剂和其他精神活性物质的效果,从而对心理健康产生负向影响。成瘾本身是精神疾病的一种。(12)Peter W.Kalivas and Nora D.Volkow,“The Neural Basis of Addiction: A Pathology of Motivation and Choic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62, no.8(2005):1403-1413; Charles P. O’Brien,“Commentary on Tao et al.(2010): Internet Addiction and DSM-V,”Addiction 105, no.3(2010):565.视频游戏等活动为不同种类的精神障碍形成过程研究创造了条件,为强迫症或抑郁症等表现出的异化行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背景。(13)Laurence J. Kirmayer et al.,“Cultures of the Internet: Identity, Community and Mental Health,”Transcultural Psychiatry 50, no.2(2013):165-191.基于这种路径,网络游戏也被视为“电子鸦片”。(14)Alex Golub and Kate Lingley,“‘Just Like the Qing Empire’: Internet Addiction, MMOGs, and Moral Crisis in Contemporary China,”Games and Culture 3, no.1(2008):59-75.最后,“神经发育路径”。基于该路径,青春期边缘系统的成熟度增加,这使得青少年比成年人更有可能参与成瘾行为,并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15)Sun-Jin Jo et al.,“Diagnostic Usefulness of an Ultra-Brief Screener to Identify Risk of Online Gaming Disorder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Psychiatry Investigation 17, no.8(2020):762-768.
评估网络游戏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的因果效应还需要考虑到复杂综合因素的影响。青少年研究中常见的调节变量如同群、家庭、学校等因素同样适合用于此话题的评估。(16)苏竣,孙浩.网络游戏对青少年教育期望影响研究[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185-200.
首先,同群的调节影响。文献表明,游戏的功能部分体现于它是青少年学生建立社会关系的虚拟场合,玩家不仅和现实中的同学一起玩游戏,还可以在网络游戏中与其他玩家交朋友,帮助他们学习游戏的技巧。(17)Castulus Kolo and Timo Baur,“Living a Virtual Life: Social Dynamics of Online Gaming,”Game Studies 4, no.1(2004):1-31.网络游戏形成了同班群组,他们不仅玩游戏,还开设聊天室,与其他玩家“虚拟闲逛”。如果平时交好的同群经常一起玩游戏,那么无法进入游戏或输掉游戏的场景有时会使得青少年经历失败的情绪,当他们被迫离开游戏时,他们会变得易怒、焦虑或沮丧。(18)Louis Leung,“Net-Generation Attributes and Seductive Properties of the Internet as Predictors of Online Activities and Internet Addiction,”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7, no.3(2004):333-348.
其次,家庭的调节影响。缺少家庭监管的孩子容易网络游戏成瘾。据统计,90%的网瘾孩子是因缺少家庭的关爱导致。(19)Louis Leung,“Stressful Life Events, Motives for Internet Use, and Social Support Among Digital Kids,”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10, no.2(2007):204-214.另一方面,父母对孩子监管太严,学生更容易产生逆反心理式回应,对网络游戏就更容易痴迷,也更容易产生心理健康问题。(20)高文珺.青少年网络游戏问题行为的文化-社会-个体三因素分析——基于网络游戏问题行为的91个电话咨询案例[J].中国青年研究,2021,(5):29-37.如果父母等监护人科学适度地对孩子玩网络游戏进行监管,给予及时提醒,有时陪伴孩子玩游戏,那么引起孩子心理问题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特别是当孩子们由于没能玩游戏而导致愤怒情绪加剧时,父母的耐心与陪伴对调节孩子心理更加重要。(21)Mark Griffiths,“Online Computer Gaming: Advice for Parents and Teachers,”Education and Health 27, no.1(2009):3-6.
最后,学校的调节影响。学校是学生增长知识以及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如果学生在学校里结识了更多玩游戏的同学,则极容易玩游戏过度,甚至造成游戏成瘾,进而影响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健康。(22)Alejandro Gaviria and Steven Raphael,“School-based Peer Effects and Juvenile Behavior,”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3, no.2(2001):257-268.特别是在学校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群体往往缺乏社会归属感,其对虚拟世界所提供的“避难所”有更强的归属感,因而易沉迷于网络游戏而不可自拔。(23)卢西亚·罗莫等.青少年电子游戏与网络成瘾[M].葛金玲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74.
尽管以上文献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智能社会时代网络游戏对玩家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以及传导机制,但依然给我们留下了可以拓展与创新的空间。一是样本的代表性,这是空间分布问题。本研究使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査与数据中心负责收集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这一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来检验中国青少年玩游戏行为与他们的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具有更强的样本代表性。二是现实问题的普遍性,这是时间上的问题累积效应。在中国,网络游戏产业已快速发展20余年,但是监管较为滞后,由网络游戏引发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全国层面的普遍现象,这既为本研究提供一个值得研究的大背景,也意味着本研究结论的理论映射面将更为宽广。三是结论的可靠性。在考虑网络游戏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时,很多既有研究并不是建立在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学习环境中,如此就会遗漏诸如个体特征、同群特征、家庭特征、学校特征等控制变量。本研究的分析模型不仅考虑加入这些变量,还考虑了这些变量的层析嵌套性,有助于得出更加可靠的结论。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我们提出研究假设:网络游戏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玩游戏强度越高,对心理健康负面影响程度越大。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样本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简写为 CEPS),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设计与实施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追踪调查项目。CEPS以 2013-2014 学年为基线,以初中一年级(7年级)和初中三年级(9年级)两个同期群为调查起点,以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和流动人口比例为分层变量,从全国随机抽取了28个县级单位(县、区、市)作为调查点。调查的执行以学校为基础,在入选的县级单位随机抽取了 112 所学校、 438个班级进行调查,被抽中班级的学生全体入样,基线调查共调查了约 2万名学生。CEPS分别向学生、家长、班主任、任课老师、学校领导等不同群体发起问卷,收集了被调查学生的基本情况、家庭情况、学校情况等相关数据。本文使用CEPS2014-2015年追访数据,追访对象为基线调查时的初中一年级(7 年级) 的全部 10279 名学生。
(二)变量设计
1.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学生的心理健康,研究单元为学生个体。心理健康的测量,由“在过去的七天内,你是否有以下感觉-消沉地不能集中精力做事”等10个测量焦虑或抑郁的题项组成(24)被解释变量数据来自CEPS(2014-2015)测量心理健康状况的李克特量表。该量表由10个测量焦虑或抑郁的题项组成,分别为:“在过去的七天内,你是否有以下感觉-沮丧”“你是否有以下感觉-消沉地不能集中精力做事”“你是否有以下感觉-不快乐”“你是否有以下感觉-生活没有意思”“你是否有以下感觉-提不起劲儿来做事”“你是否有以下感觉-悲伤难过”“你是否有以下感觉-紧张”“你是否有以下感觉-担心过度”“你是否有以下感觉-预感有不好的事情会发生”“你是否有以下感觉-精力过于旺盛,上课不专心”。,每个题项对应5个答案选项(“1-5”分别代表“从不”“很少”“有时”“经常”和“总是”),数字越大则意味着所对应的心理健康状况越差。为了方便分析,采用逆向编码处理(“1-5”分别代表“总是”“经常”“有时”“很少”和“从不”),利用主成分因子分析和0-1标准化方法从该量表建构了一个取值范围在0-100的“心理健康指数”变量,数值越大,表示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越好。
2.核心自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是学生玩网络游戏时间。数据来自CEPS(2014-2015)对应的上网、玩游戏的问题:“周一到周五,你平常每天上网玩游戏的时间”。统计被调查者填写的玩游戏时间,“没有”=0,“不到1小时”=1,“约1-2小时”=2,“约 2-3 小时”=3,“约3-4小时”=4,“约4小时以上”=5,得到取值为0-5的连续性整数变量。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含4组。第一组是学生个体特征变量,第二组是同群特征变量,第三组是家庭特征变量,第四组是学校特征变量。个体特征变量包括性别、户口、学习成绩、基线调查时的心理健康状态、迁移经历、不良行为、自评健康、认知能力等。性别测量,“男”=1,“女”=0;户口测量,“城市户口”=1,“农村户口”=0;学习成绩测量,2014年秋季期中考试语数外成绩加总,取值0-440;基线调查时的心理健康状态测量,与因变量“心理健康”测量方式相同,取值0-100;迁移经历测量,来源于农村为1,否则为0;不良行为状况测量,由“骂人、说脏话”“吵架”等10 道题目的量表测得,答案选项均为“1—从不”“2—偶尔”“3—有时”“4—经常”“5—总是”,相加后得到一个取值为1-47 的连续变量,数值越大,表示不良行为越多;自评健康测量,题项为“你现在整体健康情况如何”,答题选项“比较好”和“很好”赋值为1,其余为0;认知能力测量,被试者认知能力测试得分,取值0-35。
同群特征变量包括学校排名、班级学业表现均值、班级学业表现离散程度等。学校排名测量,被调查学校校长自评该校在本县的排名,从最差到最好,取值1-5;班级学业表现均值测量,同班同学的语数英三科均分,取值为5.12-124.16;班级学业表现离散程度测量,同班同学语数英三科期中成绩的标准差,取值为1.13-51.85。
家庭特征变量包括亲子关系、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长监督程度、家庭居住安排、课外补习、兄弟姐妹数量等。亲子关系测量,题项为家长是否主动与孩子讨论“学校发生的事情”“孩子与朋友的关系”等8个问题,回答选项均为 “1—从不”“2—偶尔”“3—经常”,加总后获得取值2-24,数值越大,表示亲子关系越好;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测量,题项为被调查父母的受教育年限、职业地位、自评经济地位以及政治身份(是否党员) 等4个问题,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了一个公因子,经 0-1 标准化后,取值为 0-100,数字越大,表明被调查学生所在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家长监督程度测量,家长回答在孩子“作业和考试”“在学校表现”等6个方面的严格程度,选项分为“1—不管”“2—管,但不严”“3—管得很严”,将上述6个题项的答案相加得到取值范围为 6-18 的连续变量,数值越大表示家长的监管越严格;家庭居住安排测量,学生是否与父母同住,“是为1,否为0”;课外补习变量测量,被调查者参加奥数、数学、语文(作文)或英语等四类补习班的数量,取值0-4;兄弟姐妹数量测量,家庭中兄弟姐妹数量,取值0-12。
学校层面的变量包括学校地域、学校类型、学校生师比、教师学历、教师心理健康培训等。学校地域测量,城市学校取值为1,农村学校为0;学校类型测量,私立学校赋值1,公立学校赋值0;学校生师比测量,学校学生数量与教师数量的比值,取值2.8-30.7;教师学历测量,学校本科以上学历教师的占比,取值0-1;教师心理健康培训测量,教师参加过心理健康培训赋值1,没参加赋值0。本研究在变量设计上参照吴愈晓与张帆的方法(25)吴愈晓,张帆.“近朱者赤”的健康代价:同辈影响与青少年的学业成绩和心理健康[J].教育研究,2020,(7):123-142.。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在被解释变量方面,初中生的心理健康的均值为71.17,说明当年初中生平均的心理健康状态一般,处于需要整体上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状态。
在学生个体特征方面,被统计的样本中,学生周一到周五每天玩游戏的平均时间超过1小时,说明玩游戏占用了初中生部分业余时间。男生与女生数量相当(平均值为0.54),农村户口的学生规模明显大于城市户口学生(平均值为0.63)。学生的平均成绩为229.50,在统计意义上偏低,这说明成绩差的学生群体偏多。学生基线调查时心理健康水平的均值为72.57,说明经过一年的初中生活,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有略微下降。迁移经历的均值为0.1,说明经历了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就读的初中生群体数量并不大。学生不良行为的统计均值为13.63,说明学生在学校学习不良行为较少,平时能较好地遵守学校的纪律。学生自评健康统计均值为0.64,说明自认为自己身心健康的学生占大多数。学生认知能力得分的均值为21.05,处于中等水平,初中生认知水平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在同群特征方面,学校排名变量的统计均值为3.95,说明学生在各等级学校的分布比较均匀,在中等以上排名学校就读的学生群体偏多。班级学业表现的均值为75.13,说明同群的平均成绩处于一般的水平。班级学业表现标准差变量的均值为17.31,说明学生所在班级的分布比较均等,也说明学校较好地贯彻了国家均等化分班的政策。
在家庭特征方面,亲子关系的均值为16.30,这意味着父母与孩子之间沟通普遍顺畅,亲子关系良好。学生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的均值为38.8,说明社会经济地位一般偏下的家庭占大多数,标准差为20.17,说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差异比较大。家长监督变量的均值为13.64,说明大部分的家庭对孩子学业监管比较严格。家庭居住安排的均值为0.79,说明初中学生群体与父母同住的家庭结构是主流。课外补习变量的均值为0.61,说明家庭为初中孩子报名补习科目数不多。兄弟姐妹数量的均值为1.24,说明生育一至两个小孩的家庭占主流。
在学校层面,学校地域的均值为0.46,说明样本中城市学校与农村学校处于均等状态。学校类型的均值为0.08,公立初中学校占据主流。学校生师比的均值为11.4,说明我国初中学校人力资源利用效率处于适中水平。教师学历的均值为0.74,说明我国初中阶段教师学历层次较高,师资力量较为强大。另外,教师参加心理健康培训变量的均值为0.87,这表明绝大多数教师都参加了心理健康培训,说明大部分学校对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心理健康要求比较高。
(二)分层线性模型分析
在本文样本中,由于学生心理健康的得分嵌套在学校之中,所以组成了由较低层次的观察数据嵌套在较高层次之内的数据结构。首先,建立一个不含自变量的零模型(指不含任何解释变量的模型)考察个体心理健康得分在学校间是否存在差异,即不同的学校是否会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模型参照谢传波等的方法。(26)谢传波等.多水平统计模型的Stata程序实现[J].中国卫生统计,2014,(1):169-170.零模型所用的stata的命令为:xtmixed心理健康 || 学校id:, mle variance nostderr。表1报告了随机效应部分的运算结果,学生的心理健康在学校水平的变异服从 N(0,20.21)的正态分布,且学生心理健康在学校水平的变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 001)。个人心理健康得分的变异归因于学校的部分占4.81%(27)VPC(variance partition coefficient) = 20.21/(20.21+399.60)=4.81%。。零模型结果显示可以用多层次模型来分析本文层次结构数据。于是,参照劳登布什等(28)斯蒂芬·W.劳登布什,安东尼·S. 布里克.分层线性模型:应用与数据分析方法[M].郭志刚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14.的方法,列出分层模型的表达式:
Level1(学生层次):Yij=β0j+β1j(玩游戏时间)ij……+β18j(兄弟姐妹数据量)ij+εij
Level2(学校层次):βpj=γp0+γp1(学校地域)j+γp2(学校类型)j+γp3(学校生师比)j+
γp4(教师学历)j+γp5(教师心理健康培训)j+μpj
Level1式中共有18个自变量,i表示学生个体样本量;j表示第j个组织(学校),β0j为截距,β1j~ β18j为处理因素的效应参数(又称为固定效应参数)。比如,β1j表示第j 个学校的学生玩游戏时间差异与心理健康得分的关系强度。 Yij表示第j个组织(学校)中第i个学生的心理健康得分。Level2式中有5个自变量、j个组织(学校)。βpj,其中p取值0,1,……18。β0j是第j个学校真实的平均学生心理健康。γp0表示每一学校效应的平均数。
其次,在零模型基础上,引入解释变量建立随机截距及随机系数模型。分层模型运算的核心是清楚数据是分层次的,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清楚高水平层次(学校)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因为可能存在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学生玩游戏时间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不随学校的改变而改变,这时需要采用加入解释变量的随机截距模型,这种模型存在一个公共的回归系数表示解释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它变化的是截距,即不同的学校(自变量)对学生心理健康(因变量)的影响不同;另一种情况是,不但学生的心理健康在不同学校间变化,而且解释变量在不同学校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所起的影响效应也不同,这时需要采用随机系数模型,同一解释变量在不同的学校对学生的心理健康得分有不同的回归系数。以“玩游戏时间”解释变量为例建立随机截距与随机系数模型。其一,随机截距模型Stata命令程序:xtmixed心理健康 玩游戏时间 || 学校id:, mle variance nostderr。表2呈现的结果显示,与零模型相比,在加入“玩游戏时间”这一解释变量后个体水平的残差由 399.60 减少到 393.74,残差更小,统计结果更趋向真实。其二,随机系数模型Stata命令程序:xtmixed心理健康 玩游戏时间 || 学校id: 玩游戏时间,covariance (unstructured)mle variance nostderr。表3呈现的结果显示,较之随机截距模型,随机系数模型的在个体水平的残差进一步缩小,随机效应部分出现了解释变量“玩游戏时间”与学校的协方差项为正,说明若一所学校对学生的心理健康影响越明显,则学生“玩游戏时间”对其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越大。
最后,基于以上两种模型,通过逐步在两种模型中加入不同层次与类别的变量的方式来考察玩网络游戏对心理健康影响的净效应。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


表4报告了分层线性模型的随机截距模型与随机系数模型两种估计的结果。模型1-1与模型1-2 是基准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无论是随机截距模型还是随机系数模型,玩游戏强度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都是显著负效应。性别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户口和心理健康呈显著负相关,来自农村的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更值得关注。学业表现和心理健康是显著正相关,与此相反,不良行为和心理健康是显著负相关。基线调查时的心理健康状况与推后一年心理健康(因变量)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CEPS 追踪调查数据具有优势,模型可以控制一个很重要的前置变量。如此可以尽量减少遗漏变量同时影响学生前一期心理健康与当年心理健康水平的情况发生。迁移经历对心理健康有正相关,不显著。一个原因可能是有迁移经历的学生样本量少,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有迁移经历的学生自我心理调节能力更强。自评健康、认知能力都与心理健康呈显著正相关。自评健康越好的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也越好,认知能力越强的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也越好。
关于同群层面的因素,模型2-1与模型2-2 是加入同群变量的模型,仅估计玩游戏、个体变量以及同群变量的效应。可以发现,无论是随机截距模型还是随机系数模型,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玩游戏强度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都是显著负效应。学校排名与心理健康呈显著负相关,学校排名越高,其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越令人担忧。可能是由于同群层次高更容易引起攀比风气或者心理比较,从而更不利于学生心理健康。学生所在班级学业平均水平越高也越不利于学生的心理健康。班级是学校的基本单位,同班同学之间存在直接的学业竞争与各方面的自我与他人的比较,这样更容易引起心理上的不适。学生所在班级学业差异水平与心理健康呈正相关,但不显著。可能是多样性对心理健康影响的正向推力在起一定的作用,也说明用来解释学业的“彩虹模型”(29)程诚.求同还是存异?——同质性视角下的学业成就研究[J].社会学研究,2021,(1):180-202.扩展到心理层面并不太适用。
关于家庭层面的因素,模型3-1与模型3-2 做了量化估计。无论是随机截距模型还是随机系数模型,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玩游戏强度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都是显著负效应。亲子关系与心理健康呈显著正相关。好的亲子关系不仅有助于提升学业表现,而且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有正向作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心理健康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为孩子提供的成长环境越好,孩子越可能快乐健康成长。家长监管与心理健康呈负相关关系,但不显著。父母对孩子监管太严对孩子心理健康不利,这与吴愈晓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似。家庭居住安排与心理健康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及时得到父母的呵护是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课外辅导与心理健康呈负相关,但不显著。家长给孩子增加更多科目的课外辅导可能对孩子学业成绩提升有帮助,但是对孩子心理健康有不利影响趋向。
关于学校层面的因素,模型4-1与模型4-2 做了量化估计。无论是随机截距模型还是随机系数模型,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玩游戏强度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都是显著负效应。学校地域、学校性质与心理健康呈负相关,学校地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不显著,学校性质对心理健康负向影响显著。说明义务教育阶段公立学校对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起到更好作用。学校生师比、教师学历、教师参加心理健康培训与学生的心理健康均呈正相关关系,但是不显著。这也与吴愈晓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似。这可能是因为学校以及老师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学生的学业成绩上而非心理健康关爱上。国家应该在政策上引导学校与老师加大对学生的心理健康的指导。

(三)稳健性检验:倾向得分匹配(PSM)分析


玩游戏是否会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有不利影响还需要更加准确的估计。为了评估玩游戏比不玩游戏会更加消极地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本研究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构造一个反事实分析模型。图1中的点显示出了玩游戏与不玩游戏的两类学生群体在“从农村迁移”“性别”“户口”“认知能力”“成绩”“学校排名”“家长监管程度”“学校地域”“教师学历”等方面的显著差异。我们使用PSM法来解决这个选择偏差问题。具体流程为,对于玩游戏学生群体中的每一个学生(处理组),根据他们的个体、家庭、同群、学校特征,发现最相似的没有打游戏的群体中的对应个体,形成对照组。然后,通过比较这两组来确定一个更“干净”的效果,为每个受访者生成倾向得分,并使用最近邻匹配方法对处理组与对照组进行匹配。图2说明了配对后处理组与对照组特征的差异。很明显,这两组在大多数关键方面更具可比性,几乎所有处理过的观测结果都是共同支持假设的,因此会较少在PSM 过程中丢失。从倾向评分的核密度图(图3)可以看出,匹配之前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倾向得分概率分布存在差异,如果直接比较难免会有偏差。采用PSM法后,则可以较好地减少以上偏差。
如表5所示,根据PSM模型马氏匹配的分析结果,玩网络游戏的学生与不玩网络游戏的学生心理健康的差异在3.101个单位,且差异在0.01水平上显著(T绝对值4.6,大于临界值1.96,且大于2.58,在0.01水平上显著)。由此可见,玩网络游戏与不玩网络游戏这两个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确实存在显著差异。故玩游戏对心理健康存在负面影响的实证模型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五、讨论与结论
本文研究发现,在2014-2015年时期的义务教育初中阶段,青少年心理健康确实存在显著且稳健的网络游戏负效应。具体来讲,首先,与大多数既有文献的发现相似,从心理健康角度来看,网络游戏消费从整体上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玩游戏时间越长,初中生的心理健康水平越差。另外,在学业竞争激烈的现实环境下,网络游戏中“互斗互怼互虐”的群体环境又可能给青少年带来了虚拟空间层面的心理压力,并负面影响青少年的精神健康。其次,对玩网络游戏的个体而言,当控制其他个体变量时,同群质量越高,反而越不利于学生心理健康;这可能是由于竞争而产生的自卑情绪在起作用。再次,对玩网络游戏的个体而言,当控制其他个体变量与同群变量时,亲子关系越好、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学生与父母同住,更有利于学生心理层面的健康成长。最后,对玩网络游戏的个体而言,当控制其他个体变量、同群变量与家庭变量时,私立学校对学生心理健康产生显著负影响,这说明义务教育阶段公立学校在培养学生心理健康方面有显著优势,也可能与公立学校的国家服务功能定位或者课后服务课程体系有关系。总体而言,从青少年心理发展的角度来看,网络游戏很可能是“洪水猛兽”。尤其在学业激烈竞争的环境“牢笼”下,同群玩游戏产生的心理健康代价值得进一步进行国际比较研究。
本研究的发现表明,关注网络游戏在不同情景控制下的效应变化,对深化理解智能社会时代智能产品消费所引致的个体、组织和社会层面的影响具有积极意义。一方面,在玩游戏情境下,我们的研究依然验证了同辈群体“近朱者赤”效应伴随的心理健康代价问题。另一方面,教育“内卷”问题以及由社会分层加剧导致的学校层次与家庭层次差异等问题正通过智能介质传递到下一辈孩子身上。而网络游戏则可能在这种差异的代际传递上发挥重要作用。
从教学与实践层面讲,心理健康教育已经被纳入学校德育、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孩子的精神基础。自2012年教育部颁布《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年修订)》以来,注重中小学心理健康已经成为新时代教育改革的新方向。2021年,教育部印发《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方案(2021年修订版)》,将包括心理健康在内的九门学科纳入质量监测,每个监测周期为三年,每年监测三个学科领域。要求“中小学要将心理健康教育课纳入校本课程,同时注重安排形式多样的生命教育、挫折教育等”“将心理健康教育作为必修内容予以重点安排”。同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要求引导学生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控制使用时长,防止网络沉迷。本研究的结论对我国义务教育政策与改革有启发意义。2021年两个重要的政策从不同角度对新时代义务教育改革提出了新要求新部署,但是政策之间似乎是割裂的,并没有形成政策耦合的协同效应。本文关于网络游戏消费对学生心理健康产生显著负影响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教育政策制定程序需注重政策耦合因素提供启发意义。而促进功能游戏发展、构建科学高效的网络游戏监管政策体系将是实现政策耦合协同效应的有效途径。
当然,本研究尚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首先,囿于数据的限制,没有将班级作为分层的单元来分析班级的差异对因果效应带来的干扰。由此,无法评估我国普遍存在的“挑选班级”变量对学生心理健康带来的影响。其次,由于缺乏长周期的纵贯数据,本研究只是基于几年前的数据且只估计了玩游戏对学生心理健康影响的短期效应,检验玩游戏对学生心理健康长期影响及其变化趋势有待之后CEPS数据的进一步更新。最后,尽管国外有大量关于网络游戏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但是国内相关研究还是较少,本文只是做了初步的探索,未来需要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群体、不同管理理念的学校类群、不同社会文化的地区差异,来收集大量定性或定量数据,以做出更加全面精准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