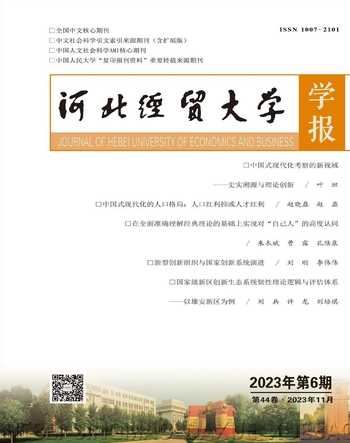马克思工作日理论视域下的“数字零工”就业形态与权益保护
刘勇 项楠
摘 要:
“数字零工”以其“去雇佣化”、灵活自由等突出特征,日益成为重要的新型就业形态。作为资本数字化增殖逻辑的产物,“数字零工”在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背景下,是资本摆脱工作日约束的增殖新路径。资本借助数字技术的强渗透性,模糊了工作日产休界限,依靠算法逻辑突破工作日生理及道德极限,通过“去雇佣化”使工作日隐形化,消弭资本逻辑下的“数字零工”工作日约束。基于此,在“数字零工”人数众多的中国,应通过加快完善零工权益保障、加强平台教育与政府监管职能,创新完善零工维权渠道,引导资本在中国的良性规范发展。
关键词:
数字零工;工作日理论;数字平台;资本数字化
中图分类号:F091.91;F24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23)06-0018-10
收稿日期:2023-03-15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创新的百年道路与经验总结研究”(21JZD008);吉林财经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科研项目重点课题“新发展阶段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研究”(2022WZD009)
作者简介:
刘勇(1973-),男,湖北黄冈人,武汉科技大学教授,博士。
在当代,数字经济已然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1]伴随着数字经济不断发展,数字平台作为数字时代的关键生产组织和资源配置方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推动力。[2]依托于数字平台的灵活性和兼容性,以零工劳动为主的灵活就业形式蓬勃发展起来,其中通过平台企业的中介和组织获取劳动机会,并自主进行计件工作的“独立承包商”[3],即“数字零工”更是成为数字时代零工经济发展的典型代表。作为西方资本数字化发展的必然选择,零工传入我国后也在不断壮大。相关数据表明,截至2020年,我国零工经济从业人员已经突破2亿人,其中依赖于互联网平台工作的零工人群超过8 000万人[4]。进一步对“数字零工”进行归纳发现,我国“数字零工”可以分为基于网络平台产生的“数字零工”和因网络平台对传统就业方式颠覆而产生的“数字零工”两大类[5],前者包含网络直播(抖音直播)、知识付费(微博打赏)等形式,后者则包含交通出行(滴滴出行)、外卖服务(美团外卖)等形式。由此可见,“数字零工”已成为我国灵活就业新样态,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在“数字零工”外在自由、灵活选择的背后,却也因为平台的高度控制和全景监督,导致零工产生“困在系统里的挤压感”[4],各种权益侵害事件频发:一方面,由于零工劳动关系呈现出的“去雇佣化”特征,致使其在职工待遇方面明显不足。以国内某外卖平台为例,政府相关部门与其代表对话时了解到,其现有的1 000万骑手无一正式工,皆是外包关系,因此平台只为骑手投保每天3元从骑手佣金中扣除的商业险,并且由于骑手的非雇佣身份,无法享受医保、社保、五险一金等福利[6]。另一方面,计件工资制和非雇佣制使得数字零工对平台存在着高依赖,这就使平台得以借此加大对零工的限制。以国内某出行平台为例,不仅不断加大对司机的抽成,还制定了各种限制条件,比如最低档司机必须保证在线10小时,保底获得480元,第二档则是保证在线12小时,保底500多元,最高档在线14小时,保底680元的所谓“激励”政策等。
显然,数字零工虽呈兴盛之势,却又困境重重。要想充分保障数字零工的现实权益,必须追本溯源,探清“数字零工”在资本增值驱动之下的生成路径,剖析资本增殖过程中对零工造成诸多困境的现实原因。工作日理论作为马克思对劳资关系进行深入剖析的重要理论,从时间维度为审视去雇佣化的零工提供了可行的理论依据。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背景下的零工工作日进行客观审视,以期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背景下发展数字经济,引导和规范资本数字化,规避不必要的风险,探寻构建资本数字化与零工间和谐关系提供理论参考和镜鉴。
一、马克思工作日理论的理论内涵
“劳动过程所需要的一切因素: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7]208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发展,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相分离,劳动力沦为商品受雇于资本家。马克思将劳动力在一天内出卖给资本家用于进行生产劳动的时间称为工作日。其由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组成,长度在最高和最低限度内变化,并受工人與资本家斗争影响。
(一)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
劳动力商品能创造出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是剩余价值的源泉。[8]为此,资本家如果意图在有限的工作时间内使劳动者创造出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就必须对工作日时间按照劳动者创造价值的不同归属进行划分,具体包括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
对于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认为,它“以工人阶级的经常存在和持续不断的再生产为前提。”[9]在必要劳动时间内,劳动者是以工人而非人的身份存在的,其劳动力是实现资本增殖的重要转换工具。因此,于资本家而言,实现资本持续性增长的前提便是劳动力不断再生产,因而其必须支付给劳动力报酬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这一支付价值在必要劳动时间内创造。由此,工资就成了必要劳动时间的物化表现,成为用于掩盖资本剥削的符号。
剩余劳动时间则不同,它是工人超出必要劳动界限进行劳动的时间。“虽然耗费工人的劳动,耗费劳动力,但并不为工人形成任何价值。”
[7]251在剩余劳动时间内,工人源源不断为资本家无偿创造剩余价值。因此,在资本增殖最大化目标驱使下,想方设法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就成了资本家的出发点和使命。其结果便是资本家财富的日益集中与劳动者贫困的日益加剧。
在马克思看来,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存在动态关系。在相对固定的必要劳动时间基础上,工作日总长度会随剩余劳动长度或持续时间而变化[10]。首先,劳动力能够得以生存、生活进而再生产是资本实现持续增殖的前提,资本家必须支付部分价值(工资)用于劳动者再生产,由此必要劳动时间是必须的。其次,在原有工作日长度不变情况下,通过压缩必要劳动时间长度,或在必要劳动时间长度不变情况下直接延长剩余劳动时间。[11]前者是剩余劳动时间的相对延长,后者是剩余劳动时间的绝对延长。
(二)工作日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
工作日并不是一个不变量,而是一个可变量,[12]其变动始终稳定存在着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利润的最高限度以生理上所容许的工资的最低限度和生理上所容许的工作日的最高限度为界限。”[13]66最低限度是工作日最短时间,其由劳动者必要劳动时间决定,是劳动力再生产能力的外化表现,一旦低于这個限度,劳动力无法再生产,剩余价值生产也将被终结。最高限度则是工人所能达到的工作日最长时间。劳动者作为独立的现实人,其生存发展会受到自身身体和外部道德的影响,因而资本家无法实现对工作日的无限延长。生理极限是指工人劳动力支出达到身体极限的自然限度。道德极限则是指工人在满足基础生存需要前提下,追求自身发展活动需要的社会限度。因此,工资作为“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隐蔽形式”,[14]441就应当包含“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14]56
生理极限和道德极限的弹性化,致使工作日最高限度带有极大不确定性。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首先,通过构筑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坚持他作为买者的权利,他尽量延长工作日”,[13]190不惜“侵占人体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15]254相对地,工人则是贫困的人格化。“工人不仅在身体方面和智力方面,而且在道德方面,都遭到统治阶级的摈弃和忽视。”[7]427-428资本家不仅在身体极限上不断压榨和奴役工人,还在道德层面为压缩和掠夺劳动者生活时间构建“合法”话语体系,“当工人向资产阶级步步进逼的时候,资产阶级就用法律来钳制他们。”[7]428其次,资本家还会通过技术革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不断压缩工作日最低限度。由此,劳动力的再生产价值将下降,必要劳动时间缩短,从而实现剩余劳动时间相对延长。
(三)工作日中的劳资对立与斗争
对于资本家而言,“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15]269对于劳动者而言,“只想在他的正常耐力和健康发展所容许的限度内使用它,使它运动,转变为劳动。”[15]270由此,买卖双方产生二律背反,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显露出来。
在劳资双方的斗争中,资本的力量是绝对性的。首先,资本家具有更强的经济力量。与劳动者被迫进入市场出卖自身劳动力商品相反,资本家是“为了获得最大化的利润,主动进入市场之中。”[10]并且,资本家对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使得工人并不具备独立从事某一项生产活动的条件,只能被迫受制于资本家。其次,资本家还具有更强的技术力量。资本家不仅能通过技术革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来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还通过机器对人的挤出效应不断增加劳动市场中“可供资本主义剥削支配的劳动力的数量”,削减雇佣成本。最后,资本家能通过联合构筑更强的政治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之间通过联合形成资本家集团,利用国家力量来实现对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全面主导,以此维护资本家的利益和地位。“资本家的联合是常见的和有效的,工人的联合则遭到禁止并会给他们招来恶果。”[16]
(四)“数字零工”是突破工作日约束的新就业形态
工作日日益零散化。关于正常的工作日,那是“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家和工人斗争的结果。”[7]312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斗争使得资本家开始审视劳动者的反抗,并探索新的剥削方式。在技术革新的推动下,以人工智能、数字平台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成为主要劳动资料,大量劳动力开始向以数字平台为基础的“数字零工”转变,原有的工作日开始呈现出破碎、零散的状态,这给了资本家以新的启发。
零散化的工作日造就越来越多的零工。当作为“数字零工”核心劳动资料的数字平台等数字化技术为资本主义所主导,看似零散的工作日背后,便是泰勒制借由数字平台对广大零工劳动者的隐蔽和持久剥削。其实质是资本家消解工作日约束,实现对剩余劳动时间“无限延长”的重要途径。一方面,资本家借助于数字技术的便利性不断突破时空约束,模糊数字零工的生产和生活界限,实现对生活时间的不断渗透;另一方面,资本家借助于“数字零工”的非正式劳资关系和算法逻辑,不断构筑对“数字零工”的隐形剥削机制,消解零工的联合力量和议价能力。由此,资本将“数字零工”打造成摆脱工作日束缚的剥削新模式。诚如马克思所言,关于如何争取正常工作日,一方面,要运用“法律来限制、规定和划一工作日及休息时间”,[7]56并且这种立法必须坚持人人平等原则;另一方面,“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15]349数字零工的出现,为资本家从立法和联合层面镇压工人为正常工作日的斗争提供了手段。
二、资本增殖催生“数字零工”新就业样态
继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后,资本数字化作为一种资本发展的必然趋势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相较于传统资本,资本数字化在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等方面都呈现出数字化特征。在资本数字化不断推动技术革新以谋求绝对剩余价值过程中,数字平台作为资本增殖的新场域登上历史舞台。一方面数字平台作为劳动资料,通过直接参与生产过程获取剩余价值;另一方面,数字平台作为中介,通过隐性雇佣关系攫取零工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由此,一种数字时代的新型剩余价值生产路径——“数字零工”应运而生,其本质是一般零工劳动的数字化转型。
(一)资本数字化催生数字平台新工具
资本数字化以数据作为劳动对象,借助于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化劳动资料实现对生产、消费、交换、分配等领域的全覆盖和强渗透,实现对传统零工劳动形式的突破,不仅打破了传统物理层面的时间和空间局限性,还构筑起超脱于现实的虚拟空间。在这里,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生产消费、随心所欲进行娱乐社交。资本数字化利用信息通信技术革命性地推动着数字时代的根本性社会变迁,推动着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重组以及社会生活的重塑。[17]在资本数字化增殖作用下,数字平台作为资本增殖新工具应运而生。
资本数字化的唯一本性仍是实现资本增殖。资本数字化看似助力人的自由发展,其背后实则是资本意图追求更多剩余价值的操纵与谋划。对于资本家而言,数字与资本联姻成了其不二之选。一方面,运用数字技术的开放性与连通性构筑起全球数字网络,并将其纳入资本逻辑的掌控之下,使得“数字成为获取数据资源的权利,也成为支配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指挥棒”,[18]将所有有助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人和物,全部紧密地拴牢在资本增殖链条之上,为生产剩余价值服务;另一方面,资本家利用数字技术的开放性和交互性,不断向广大用户输出数字技术所营造的美好假象,数字技术的高效性与快捷性为人们创造了广阔的自由时间,虚拟平台的海量数据为人们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更多可能,人们与现实世界的疏离感不断加剧。进一步,资本家通过对虚拟世界进行资本逻辑输出,不断向人们传递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从而实现对用户的意识侵蚀与思想控制,为资本向人的日常生活领域扩张扫除障碍,在不断为人们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使得人们自愿沦为资本数字化数据资料的无偿供应商和剩余价值生产者。
数字平台作为资本数字化增殖新工具登上历史舞台。数字平台作为能够实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群体进行实时交互的数字化基础设施,成为资本数字化进行资本增殖的关键载体和重要场域。数字平台以互联网为技术基础、以海量数据作为服务内容,成为广大用户获取信息、进行社交的主要场景,有效实现了数据资料的生产和积累,这也成为了探索“平台社会主义”的可行性依据。[19]资本正是看中数字平台所掌握的海量数据资源,意图通过资本数字化对数字平台进行全盘垄断,把数字平台培育成其获取数据劳动对象的“帮凶”。资本通过数字平台的精准个性服务供给作为“诱饵”,将广大用户纳入平台之中,并且运用算法算力、权限设置等强制手段,实现对用户生产和生活数据的动态监测,实现对数据资源的整合。进一步,资本数字化通过直接雇用劳动者进行数据加工改造获取剩余价值,或者以海量数据吸引零工劳动者,通过缔结短期雇佣合同抽成形式攫取剩余价值两种形式,实现资本数字化的增殖。
(二)数字平台孕育“数字零工”新劳动
数字平台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社会分工和生产方式。在数字平台强扩张性和低准入性的影响下,数字平台将全球范围内的人口全部纳入其虚拟空间中,构筑其前所未有的庞大产业后备军。由此,一种以数字平台为中介和组织获取劳动机会,利用自身闲置资源,自主选择某一特定时间段,提供某种特定服务,并不再长期受雇于某一组织或机构的“数字零工”经济模式形式兴起。[20]零工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初的美国,指代雇佣音乐家演奏的某一特定曲目或持续一晚的演出。[21]在2015年的《纽约时报》中,工人根据个人兴趣爱好、技能和时间,选择接受不同类型工作的劳动形式被定义为“零工”。[20]由于这类工作一般无固定的工作场所和时间,其从业者多为临时工、合同工、个体户或者兼职人员。
传统零工劳动主要是由劳动者通过中介机构或者他人介绍等方式获取就业信息,并按照自身情况自主选择工作,并在特定时间内为消费者提供服务来换取工资。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劳动者自主选择的权利,但受制于供求信息渠道的有限性,劳动者获取工作往往存在滞后性,就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加剧。伴随着数字平台的兴起,这一问题得到了全面解决,借助于互联网的联通性和实时性,零工劳动者可以与消费者之间进行实时交互,有效节省了时间成本,降低了就业风险。这也使得原有的中介机构向数字平台中介过渡,劳工信息数据向数字平台让渡,传统零工劳动实现“数字零工”转型。
“数字零工”继承了传统零工的一般性特征。首先,非固定的雇佣关系。“数字零工”与传统零工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在资方和劳动者之间都不具有固定的雇佣关系,呈现出“去雇佣化”特征。平台和消费者与零工劳动者之间不再具有形式上的直接隶属关系,[22]
零工劳动者形式上可以按照个人意愿自由选择工作、时间以及地点。其次,分配方式上的“泰勒制”,即计件或计时工资制。消费者按照零工劳动者所提供的劳动时间或产品数量来支付报酬,如兼职奶茶员12元/时或口罩包装短期工的0.5元/件。再次,从零工劳动的劳动形式来看,无论是传统零工还是“数字零工”都是以充分尊重劳动者个人意愿为前提,劳动者按需对自己进行“自我雇佣”,在工作时间上表现出“碎片化”特征。劳动者既可以将零工劳动作为主业,如“数字零工”中的“众包”骑手专职配送,也可以将零工劳动作为副业,如传统零工中的兼职员工。劳动者的零工时间是零散的、不固定的,具有明显区别于一般雇佣劳动“八小时工作制”的灵活性。最后,“数字零工”与传统零工一样,两者作为“非雇佣”零工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建立的是一种特殊的合作关系,两者共同提供生产资料用于劳动,中介收取中介费,数字平台收取信息租金,剩余部分则是零工工资。虽然“非雇佣制”给了劳动者更多的自主权,但由于缺失正式的劳动合同关系,使得劳动者的个人权益无法获得有效保障,恶意欠薪、黑中介等扰乱市场秩序的恶性事件频发。
“数字零工”具有区别于传统零工的时代特殊性。数字技术的渗透,使得“数字零工”具有时空超越性,得益于在线平台构筑的虚拟空间,劳动者可以同时接受多个“订单”,合作模式实现了从“个人”到“社区”乃至“城市”与“国家”的扩张,[22]城际闪送、跨国实习等模式诞生,工作模式实现从“单一”到“多元”转变,劳动者获得更广阔的“自由裁量权”。在此基础上,“数字零工”也表现出交流实时和远程化的特征。借助于数字平台,消费者与劳动者之间可以进行实时交互,达成协议,甚至于借助数字平台的大数据分析實现供需精准匹配,有效避免了信息失效的问题,无论何时何地,都能直接商议。除此之外,“数字零工”相较于传统零工在表现出高技术要求的同时也呈现出强包容性。对于“数字零工”而言,需具备和掌握数字化基础设施,如智能手机和APP的简单使用是最基本的要求,这就使得部分数字鸿沟群体被排斥在外;但同时对于能够运用数字技术的群体而言,又能够充分利用数字平台扩张和渗透过程中创造的广阔市场供求信息数据库,快速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就业岗位,从快递、配送到直播、配音再到程序开发、原画设计,人的兴趣和自主性成了选择工作的重要准则。
数字平台成为剥削“数字零工”的隐形帮凶。作为受资本宰制的数字平台,也在劳动过程中沦为了资本的“帮凶”。借助于对供求信息数据等核心劳动资料的所有权,平台通过各种用户协议和隐形条款来加深“数字零工”的实质隶属,从而资本家通过不断提高信息租金和收益抽成来攫取更多剩余价值;而对于广大零工而言,面对着“全职工作正在消失;许多公司不到万不得已,不会选择雇佣全职
员工”[23]的发展趋势,为了在激烈的同行竞争中获得就业机会并谋求更多工资,提高劳动强度和延长劳动时间成了必然趋势,“数字零工”完全沦为依附资本的附庸。资本数字化借助于平台的算法逻辑,实现了对“数字零工”隐形和深度剥削,而对于“数字零工”,“要么算法,要么乌有”[24]成了唯一选择。
三、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数字零工”工作日消弭
“数字零工”劳动在其表象上看来,是“去雇佣化”劳资关系下的自由劳动形式,但从其内在逻辑上,在借助数字平台获取工作信息并支付费用时,在主体关系上已然形成了不对等。“数字零工”由于自身信息获取的贫瘠性而不得不出卖劳动力获取工资,同时在获得工资前又必须给支付平台中介费用或手续费。这一过程是“数字零工”对自身劳动力价值的让渡,平台凭借用户协议等形式占有了零工的劳动力价值,两者之间依旧存在着劳动力的买卖关系,形成了对劳动者的雇佣关系。形式隶属消除的背后是零工实质隶属的加剧。基于此,对“数字零工”工作日状态进行审视,表面自由的背后是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家消解工作日束缚引发的诸多现实困境。
(一)数字技术渗透模糊工作日产休界限
“数字时代的社会变迁之所以是根本性的,是因为数字技术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进而重组了生产组织方式,重塑了生活方式,重建了社会结构,再造了社会运转机制。”[25]数字时代以物联网、互联网等数字化技术为代表的数字化劳动资料在生产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其所具有的虚拟性、高效性、智能型和算法性等特征,为零工劳动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能。依靠数字技术遵照个人意愿租借自身能力进行劳动的零工模式成为当前零工劳动新样态。借助手机等智能设备和数字技术构筑的平台,人们可以摆脱传统劳动的时空界限,以更为自由的方式选择工作种类与工作时间。特别是在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冲击下,零工日益成为新型主流工作形式,为推动国家经济恢复和社会充分就业提供了可能。得益于数字技术,人们的工作状态也发生了质的改变,技术乐观主义学派指出,数字技术发展极大地拓宽了劳动生产的自由性,借助于数字化网络平台,人的劳动不再受制于工厂、机器设备的影响,Facebook、Contently、YouTube等网络平台兴起并为人们所普遍接受。人们在平台上按个人时间和意愿上传视频或文章,通过获取用户流量赚取工资,在此基础上孕育出了视频博主、网络写手等内容创作型零工职业。除此之外,数字技术的互联网络还拓宽了零工群体的信息获取方式和范围,借助于大数据的供需匹配系统,零工可以实时获取范围内的各种供求信息进行接单,极大节省了时间成本,借助于优步、Go-jek、Deliveroo等平台,外卖配送、共享出行等零工职业也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数字技术美好发展、便携自由的繁荣景象背后却是零工自由时间的隐形掠夺,对剩余劳动时间的变相延长。技术革新由资本增殖推动,技术与资本联姻是数字技术的内在发展逻辑。资本数字化将数字技术打造成数字时代资本增殖的主要工具。生产过程作为资本增殖的场域开始向“数字零工”劳动模式变迁,其核心要义依旧是为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数字技术特别是数字平台为资本家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提供了可行路径。
通过零工模式为劳动者提供“自由”劳动模式,并进一步通过技术革新和宣扬“技术解放论”来加剧“数字零工”对于平台的依赖性和黏性,从而打造“数字圈地”,实现“数字殖民”,引发数字时代的“羊吃人”现象。以Deciveroo为例,广大“数字零工”在不断运用平台进行劳动的同时也不断为平台创造数据用于完善平台的算法,从而使平台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零工单笔订单收益,并为不断提高订单抽成提供可能。劳动者为了获取维持生存所需的资料,即便是在等待接单的所谓碎片化的“自由时间”里,也依旧是一种“原地待命”的状态。平台实现了劳动者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从而获得了剩余劳动时间的相对延长。
数字平台致使“数字零工”深陷“自我剥削”,实现了剩余劳动时间的绝对延长。数字平台以其所宣扬的低准入门槛与数字技术对人的挤出效应联合,将广大失业工人转为产业后备军纳入“数字零工”劳动力市场中,并通过宣扬所谓“人人可为、多劳多得”的思想不断加剧零工群体的竞争,对于本就一无所有的“数字零工”群体而言,自由化的劳动模式意味着劳动者权益的舍弃,缺乏雇佣合同加剧了劳动过程的风险性,低准入门槛加剧了就业的不确定性,双重风险与自身贫困相交织,零工群体陷入长期焦虑和恐慌的心理状态之中,在资本诱导下不断加剧“自我剥削”。[26]自愿延长工作时间,自愿降低工资水平,自愿接受资本家制定的种种不合理法规成了“数字零工”的主体选择,从而资本家实现对于“数字零工”剩余劳动时间的绝对延长。
(二)算法逻辑突破工作日生理及道德界限
算法是数字技术得以运行发展的核心,在当前时代,算法权力正在逐渐形成一种“准公权力”改变原有权力格局,权利主体呈现出去中心化、权利作用范围呈现扩张化,权利互动呈现出双向化趋势。[27]“资本由于无限度地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15]306依托于算法决策,资本家对“数字零工”的剥削突破传统道德和身体的双重极限变得更加隐蔽和深层,工作日对于“数字零工”而言成了弹性和隐性剥削的象征。
算法逻辑突破工作日生理界限。依托于算法构筑的“全景敞式监狱”,①“数字零工”的身体极限早已为资本所宰制。“数字零工”劳动的实现必须依托于智能设备和数字平台进行,在此过程中零工必须接受和授权于设备读取劳动者位置、存储等方面的权限。由此,资本家可以通过平台后台获取零工的位置、路线以及工作状态等,通过对零工生成数据的分析,资本家可以有效把握零工的个体状态,进一步依托于数字平台的规模效应,经由算法决策的大数据分析,资本家可以实现对马克思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据可视化,从而为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延长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间提供参照。诚如马克思在资本中说论述的那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15]871同样,在数字時代,资本数字化为了获取剩余价值,也会不惜一切代价去试探“数字零工”必要劳动时间的底限,挑战“数字零工”的剩余劳动生产极限,甚至于突破道德和身体的极限。以外卖骑手为例,凭借导航和交通设施等数字化技术的不断革新,平台以提升用户满意度、助力骑手提升接单效率等借口不断压缩骑手单笔订单的配送时限。其结果是用户满意度获得了有效提升,而零工的危险性也同样大幅提升,失信违规等成了零工生存和发展的重大威胁。零工想要在缩短自己工作日同时获取足够的生活资料,除了不断提升自己的劳动强度似乎别无选择。在平台依旧我行我素地通过提升对服务时长、任务分配以及单笔订单抽成的同时,劳动者则不断预支自己的生活时间,挑战着自己的生理界限。
算法逻辑突破工作日道德界限。在算法决策的“准公权力”主宰下,“数字零工”的道德极限显得微不足道。对于“数字零工”而言,平台的精准匹配为他们提供了更为自由和广阔的生存空间。数字平台的总体吸纳使得劳动者不仅在形式上隶属于资本,而且劳动者的整个社会关系也完全为资本所掌握,[28]在全社会构筑起“算法为王”的道德观。借助于算法决策的便利性和精准性,数字平台实现了对用户粘性的绝对占有。广大“数字零工”在运用平台劳动时,为了享受平台的数据资源,不得不接受平台制定的各种用户协议,即便其中的隐性条款极为严苛和不合理,为了在激烈竞争中获得准入,“数字零工”在进行思想斗争后依旧会选择接受。除此之外,数字平台打着所谓“自由化”“自主化”的旗号,大力推广“去雇佣化”模式,其实质是资本家“去义务化”和“去道德化”。由于缺乏雇佣合同关系等社会契约,平台与零工之间呈现的是一种合作关系,平台对于零工劳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和隐患不承担任何责任与义务,零工必须自费承担社会保险、医疗等费用。即使零工想要维权也会因为关系认定的困难而不了了之。与此同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多劳多得”职业观的影响下,“数字零工”依然沦为算法决策下的“隐形奴仆”。道德极限已然在算法决策下由“数字零工”“自愿”突破。除此之外,受制于传统错误劳动观和平台用户评价机制的影响,社会民众对“数字零工”具有明显的职业偏见,这也使得“数字零工”在劳动过程中即便受到不公正对待也很难得到道德援助,“数字零工”的道德极限突破变得理所当然。
(三)去雇佣化导致工作日呈现隐形化
“去雇佣化”是“数字零工”劳动模式的一大突出特征,体现了数字平台与“数字零工”之间直接劳动合同关系的消失,劳动者与数字平台之间不再是直接的被控制与控制关系[22]。勞动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与时间安排来自由地选择服务种类、时段与场所。劳动者与数字平台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助向”的合作关系,平台为劳动者提供数据信息获取与发布场所,劳动者提供自身劳动力和部分劳动资料进行劳动,订单完成后劳动者与平台进行分成。这一“去雇佣化”的合作关系看似弱化了“数字零工”对于资本的形式隶属,但实际情况却是资本数字化运用数字平台等技术对“数字零工”进行更隐蔽化、全方位的剥削与监视,以更难以察觉的方式加深了“数字零工”对于资本的实际隶属。在表面正式合同关系消失的背后,是资本家通过网络注册和协议同意就可以达成的临时用工协议,是资本家为了绕开传统有利于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劳动关系”法律束缚攫取更多剩余价值的借口,其实质依然是资本通过雇用更多劳动获取更大剩余价值的逻辑[29]。通过借助于数字平台的算法控制系统,资本家实现了“数字零工”工作日时间的延长和强度的提升、生产过程中生产成本的降低和工人工资的变相压低,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主体关系变得更加对立。[22]
“去雇佣化”表象之下剩余时间的延长。
零工采取计时或计件的泰罗工资制,想要获取足够的再生产资料必须自发增加劳动时间或者劳动数量。由于数字平台对于数据信息等核心生产资料的垄断,零工被纳入平台的增殖过程中——先将传统雇佣劳动的完整剩余劳动时间分散到零工的单笔订单完成时间之中,再通过平台抽成的形式实现对剩余价值的汇集。一方面,伴随着零工工作数量和时间的增加,零工群体整体剩余劳动时间总量也获得延长,平台实现对于剩余劳动时间的绝对延长。另一方面,资本数字化通过对数字平台的渗透将其转变成为监视和剥削“数字零工”的工具。通过对数据的垄断与分析,资本家实现对“数字零工”生存状态的全面掌握,并通过递进式缩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方式来不断开发“数字零工”的生存弹性,进而为不断蚕食“数字零工”的必要劳动时间提供现实条件。
“去雇佣化”没有缓和零工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零工与数字平台之间看似合作的背后,依然蕴含着劳资关系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零工劳动得以实现的前提在于市场供求信息的获取,这就使得数字平台与零工之间建立起了不平等的“附庸”关系,零工必须无条件服从平台指令。为了吸引和讨好消费者,平台推出了一系列极具夸张性的服务,从“专人配送”到“私人订制”,看似不可能的背后是平台对“数字零工”“必须可能”的苛刻要求;并且平台还将消费者纳入“数字零工”控制主体的范畴之中,赋予消费者以监管权利,加深了对“数字零工”的剥削;通过将催单、好评等考核机制与数字零工的收入挂钩,加剧消费者与零工之间的主体权利不对等。通过数字技术打造的“全景敞式监狱”,不断制定更为严苛的“游戏规则”,通过低准入门槛形成的庞大产业后备军威胁“数字零工”:要么接受、要么退出。“数字零工”在长期的监视、剥削与内心的焦虑、恐慌中逐渐丧失主体地位,进而完全沦为数字平台的“数字奴隶”[19]。
四、构建“数字零工”工作日权益保障的中国启示
在我国,以“数字零工”为代表的灵活就业形式已经成为当前就业市场中的主流,作为依托于平台发展而形成的“数字零工”就业新形态,在兼具包容性和灵活性的同时,也因为平台企业自身的发展不规范和监管体制不适应等突出问题给“数字零工”群体带来了一系列权益侵害问题。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主义仍处于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各种资本要素、数字平台等数字化技术在相当范围、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存在。与之相伴的,作为资本发展的产物,零工这一新型生产、就业模式也将大范围存在,如何规避资本主义私有制下零工发展的工作日困境,维护零工的合法权益,激发平台经济活力成为推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时代课题。基于马克思工作日理论视角,基于对“数字零工”群体工作日状态的审视,可以为我国在新形势下正确引导和规范资本发展,构建和谐劳资关系提供重要启示。
(一)完善“数字零工”权益保障体制
首先,发挥数字技术对“数字零工”群体的积极作用。技术是一把双刃剑,需要充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借助专门化数字技术收集有关“数字零工”工作状态的相关数据,并对之进行分析,建立“数字零工”工作最高时限预警机制,对违规平台企业进行惩处,充分保障“数字零工”的“休息权”。[29]其次,充分发挥工会及劳动行政部门的监督作用,督促平台企业建立和实行“数字零工”群体权益保护方案,如为平台零工群体购买意外险、医疗险等。同时联合数字平台企业、“数字零工”群体代表进行多方协商,确立“数字零工”群体基本工资红线,有效遏制平台企业无限度提高单笔订单抽成比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数字零工”群体的工作强度。最后,国家应当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打造适宜于“数字零工”群体的社会保障产品,为“数字零工”群体提供基本医疗保险与养老保险,尝试探索政府主导、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的多层次化保险产品,并结合“数字零工”群体收入水平、职业特色等确定参保方式、基金规模和赔付力度等,确保广大零工群体“缴得起、稳得住、能享受”。[29]
(二)加强平台教育与政府监管职能
数字平台是“数字零工”得以兴起和进行劳动的关键。在数字时代要想实现“数字零工”群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必须强化源头治理,从数字平台着手,加快构建数字平台的监督监管机制,保障劳动实质上的自由自觉。
对数字平台进行正确的引导教育。在平台企业家之中大力弘扬“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30]的社会主义企业家精神”。引导平台企业家在组织数字零工群体进行劳动的过程中,关爱和保障数字零工群体的合理诉求。一方面,通过不断创新平台服务,为数字零工群体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服务,帮助其更快匹配心仪工作,更快完成个人劳动,更快取得劳动报酬,拥有更多自由时间;另一方面,运用平台后台的实时数据同步功能,为保障劳动者劳动过程的自由和安全提供技术支持,有效防范数字零工劳动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建立劳动风险防范预警机制。
政府必须承担起监管职能。针对数字平台企业出现的危害零工群体身心健康、违反社会道德的行为,有关部门必须对其进行监督和惩处。政府应加紧制定数字平台用工标准和规章制度,对可能存在的零工工作时间太长和强度过高、零工缺少相关安全设施等行为进行干预,并责令平台企业进行整改。同时成立数字平台监督管理小组,不定期对企业进行抽查,对可能存在的侵权隐患进行排查和防范。再者,还应完善数字零工侵权行为监督举报渠道,为广大零工劳动者遇到的侵权行为提供有效平台,为杜绝平台算法逻辑对零工生理和道德界限的侵蚀与挑战提供行之有效的解决路径。
(三)创新完善“数字零工”权益维护渠道
首先,通过加快探索和确立企业与零工劳资关系认定标准,使“数字零工”具有合法地位,进而为从制度层面消除“数字零工”群体与数字平台主体关系不对等问题奠定基础。其次,依托劳动仲裁部门与司法部门建立专门化“数字零工”仲裁和法律援助机构,为“数字零工”群体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助力,并开展定期普法宣传,增强“数字零工”群体的维权意识,并通过增设网上维权平台等方式不断简化“数字零工”群体维权程序,深入推进实施“最多跑一趟”改革,提升维权效率。最后,相关部门必须加大数字平台企业侵害劳动者行为的违规处罚力度,建立数字平台企业诚信管理模式,将劳资矛盾和争议问题纳入企业征信指标,引导企业自发承担社会责任,从而将各种劳动争议、劳资纠纷化解于未然,推动构建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和谐劳资关系。
注释:
①“全景敞式监狱”是福柯《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借用现代监狱的空间设计典范及边沁的“圆形监狱”提出的一个概念,它作为现代资本主义权力治理的一个象征,代表了对个体进行规训的权力场域。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 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N].人民日报,2021-10-20.
[2]谢富胜,吴越,王生升.平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9(12):62-81+200.
[3]谢富胜,吴越.零工经济是一种劳资双赢的新型用工关系吗[J].经济学家,2019(6):5-14.
[4]零工经济研究中心.数字化零工就业质量研究报告:2021[EB/OL].(2021-12-21)[2023-01-20].https://mp.weixin.qq.com/s/2vmQeXWv7Irod_RfIB4GdQ.
[5]姚建华.零工经济中数字劳工的困境与对策[J].当代传播,2018(3):66-68.
[6]美团:1 000万骑手均为外包公司员工,与我们无直接劳动关系[EB/OL].(2021-05-10) [2023-01-20].https://www.sohu.com/a/465520240_114760.
[7]資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刘凤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力商品理论再认识[J].经济学动态,2017(10):40-52.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94.
[10]刘志国,栾瑞华.我国“996”工作模式的形成原因及治理——基于马克思工作日理论的分析[J].经济论坛,2020(11):137-146.
[11]闫金敏,戴雪红.资本逻辑下的身体异化现象及超越[J].理论月刊,2022(5):26-31.
[12]李洋,徐家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时间尺度[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29-38.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54.
[1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6.
[17]刘庆申.数字资本时代人的生存状况:反思与批判[J].江汉论坛,2022(3):29-34.
[18]邓伯军.数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逻辑批判[J].社会科学,2020(8):23-31.
[19]马云志,王寅.平台资本主义批判和重构平台社会主义——数字时代对平台经济的新运思[J].河北学刊,2022(1):55-61.
[20]闫境华,石先梅.零工经济资本与劳动之间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理论月刊,2021(8):35-43.
[21]FRIEDMAN G.Workers without employers:shadow corporations and the rise of the gig economy[J].Review of keynesian economics,2014,2(2):171-188.
[22]閆慧慧,杨小勇.平台经济下数字零工的劳动权益保障研究[J].经济学家,2022(5):58-68.
[23]戴安娜·马尔卡希.零工经济:推动社会变革的引擎[M].陈桂芳,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Ⅶ.
[24]吴静.总体吸纳:平台资本主义剥削的新特征[J].国外理论动态,2022(1):116-124.
[25]王天夫.数字时代的社会变迁与社会研究[J].社会科学文摘,2022(3):94-96.
[26]崔学东,曹樱凡.“共享经济”还是“零工经济”?——后工业与金融资本主义下的积累与雇佣劳动关系[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9(1):22-36.
[27]林嘉琳,陈昌凤.算法决策下零工经济平台的权力关系变动及价值选择——以外卖平台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12):153-157.
[28]吴静.算法吸纳视域下数字时代劳动新探[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8-15.
[29]韩文龙,刘璐.数字劳动过程中的“去劳动关系化”现象、本质与中国应对[J].当代经济研究,2020(10):15-23.
[30]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11-02.
责任编辑:武玲玲
Employment Forms and Rights Protection of "Digital Odd Job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Working Day Theory
——Taking the "Second
Liu Yong,Xiang Nan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65, China)
Abstract:
"Digital odd job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new employment form with its prominent features such as "de-employment" and flexibility. As a product of the logic of capital's digital multiplication, "digital odd jobs" is a new way for capital to get rid of the constraints of working day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western capitalist private ownership. Capital, with the strong penet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blurs the boundaries between production and rest during the workday, relies on algorithmic logic to break through the physiological and moral limits of the workday. It should make working days invisible by "de-employment", and eliminate the constraint of "digital odd jobs" working days under the logic of capital. Based on this, in China, where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digital odd jobs", we should accelerate the improvement of odd jobs' protection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strengthen platform education and government supervision functions, and innovate and improve odd jobs' rights protection channels, in order to guide the benign and standardized development of capital in China.
Key words:
digital odd jobs; working day theory; digital platform; digitalization of capi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