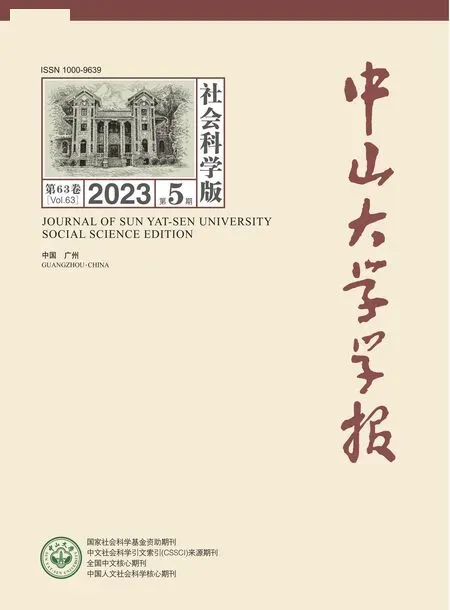重思关系构成的“成人”的主体性*
[美]安乐哲著,董耀民译
一、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意识形态
当代伦理学不加鉴别地使用主体(agents)、行动、属类德性(generic virtues)、品性(character traits)、自主(autonomy)、动机、理由、选择、自由、准则、后果、权利、善好(good)等常见词汇进行讨论,就此而言,它将某种基础性的个人主义(foundational individualism)预设引入自身并作为讨论的起点。个人主义除了深深扎根于古希腊哲学叙事外,在我们这个时代,它还是道义论、功利主义甚至美德伦理学所使用的词汇的预设,尽管在其中肯定不是同一种东西。而且,即便它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也至少成了一种大众默认的常识预设。而我之所以称之为意识形态,是因为当使用分立个人(discrete person)等词汇的某些个人主义变种垄断了我们的意识、排斥任何严肃的替代者时,它就正式成了一个人、一个群体或一种文化的典型思维——这就是意识形态①关于我的强烈主张——在西方哲学叙事中,个人主义实现了对意识的垄断——我们可以引用以下事实作为反例:社会心理学家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及其同道杜威(John Dewey)在他们的时代发展了一个颠覆性的概念“关系构成的人”(relationally-constituted person)作为他们对个人主义的重要替代。但若对这个反例进行考量,我们应当注意怀特海(A.N.Whitehead)所坚持的:在哲学辩证法中,这样的反例必须在考虑它们实际产生了多大的影响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评估。也就是说,它们在改变当下的思想预设方面有多大作用?实际上,我们不得不承认,直到如今,对于“成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的当代思考和常识预设而言,“关系构成的人”这一“米德—杜威”式概念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因此我们必须不无反讽地承认:这个反例实际上成了一个正面例子。这也就是说,一种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在西方话语中广泛流行。只有在如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以及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等当代学者对人的“内在”(intra)—主体进行充分思考时,这些新近的学术才在某些重要的意义上受益于古典实用主义者们在讨论方向上的修正。。
通过与古希腊的本体论(ontology)和分立个体观念进行对比,我们发现早期中国的宇宙观有另一种整全的、“视点—视域”(focus-field)式的秩序,它以“至关重要的关系性优先(the primacy of vital relationality)”以及由此而来的经验之整全性为基础。换言之,由于任何事物都由其关系构成,并且这些关系不管在当下还是在时间的绵延中都没有确切边界,所以一切事物都或多或少地与任何其他特定事物相关联。这种视点与视域的全息图景意味着,总体性存在于每一束独一无二的经验脉冲之中。因此,自我认同(identity)之建构首要考虑的是,对于在独特的关系网络中环绕着自我的他者,应分别赋予什么程度的重要性和优先级,以及自我在这些关系中与他者所形成的联结具有怎样的品质(quality)。
因此,要明确论述儒家角色伦理学,就得援引其自有的、极为独特的、与其宇宙观匹配的“视点—视域”词汇:“在构成长幼代代相传的社群的鲜活角色和关系中,敬重家庭是首要的道德命令”(孝),“在我们的角色和关系中追求完满圆熟(consummate)”(仁),“在我们的角色和关系中极尽适宜”(义),“寻求恰当处理关系的、习熟的行为技艺(virtuosity)”(德),“在我们的角色和关系中追求得体”(礼),“在我们的角色和关系中,通过代代相传来体现传统”(体),“身心着(bodyheartminding)”①将名词动名词化是作者的常用手法,意在强调对该名词的理解应更重视其时间性和过程性维度而非静态本质,对后者的关注乃出于西方实体本体论哲学叙事的常识预设。——译注(心),“培养、发展一种发乎我们自然禀性的叙事”(性),“对我们在自己的角色和关系中的所作所为表示坚决与忠诚”(诚),“在我们多样的关系中极尽和谐共生”(和),“在与他人相处时守信”(信),“感同身受地、审慎地与他者换位思考”(恕),以及“真心实意地按照已决定的最佳方式行动”(忠)和“做更可取之事”(是非)等。儒家角色伦理学以一种(与当代伦理学)根本上不同的预设为基础,这一预设关乎两个方面:一是个人的自我认同如何在我们关于“人”的叙事中形成,二是道德能力如何被表述为一种有关(构成着我们的)角色和关系的习熟技艺。我们对道德行为之性质的理解首先是以范式术语(modal terms)进行明确表述的,即做某事的方法、方式或模式,而非规定具体行动本身。但实际上,若考虑到每个具体情境的唯一性,那么我们在界定典范行为的实质时就很难对这些模式进行一般性的规定。同样,当我们诉诸特定历史事件和具体范例进行批判性反思时,这些模式也常常成为问题焦点。如果我们不能将我所称的“个体”(individual)以及“分立的‘人’”(discrete human“beings”)与儒家的“关系构成的‘成人’”(relationally-constituted“human becomings”)区分开来,那就意味着我们在开始研究之前,就已经有意无意地引入了一种当代的、显然是外来的“人”的观念。
二、“少量的观念”:本体论和生生论(Zoetological)思维
亚里士多德深知,对哲学探究来说,从进行哲学探究的主体(subject)出发是很重要的②黑格尔在《小逻辑》的导言中也对这个问题——哲学始于何处,探究起于何处——进行了详尽的反思。他在其中总结道:由于哲学“没有一个其他科学意义上的始点”,那么其“始点只能与那个决定去作哲学思考的主体有关”。参G.W.F.Hegel,The Encyclopedia Logic,Indianapolis/Cambridge: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1991,p.41。(译文可参[德]黑格尔著,贺麟译:《小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9页。——译注)。在找寻这个起点时,他将“人是什么?”(What is a person?)作为他的第一个问题。正因此,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是标准的《亚里士多德全集》的《工具论》的第一篇文本。亚里士多德《范畴篇》的最初计划就是以他所举的主体“那个在市场里的人”为具体例子,来弄清楚:如果我们要对“我们可以对一个主体谓述些什么”这个问题进行全面说明时,必须提出一整套怎样的问题。“什么”(what)不仅是他的第一个问题,也是首要的问题。其首要性在于这个事实:在亚里士多德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形式质料说的回答中,他首先界定了主体必要的本质(essence)或实体(substance)(古希腊语:ousia,拉丁语:substantia)——一个人“是”什么(What“is” a man)?然后再接着问那些用以辨别此人各种次要的偶性(contingent attributes)的问题:“一个人‘有’什么?”(What is“in” a man)①Aristotle,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The Revised Oxford Translation,ed.by Jonathan Barn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1a25-4a10.由此,他引入了一种本体论上的不平等。
尽管细致谨慎的学者席文(Nathan Sivin)坚定地告诫我们,在进行文化比较时,要避免那种非此即彼的简化。但与此同时,他还观察到:“人类的巨大创造力似乎建立在对相当少量的观念的排列和重组之上。”②Nathan Sivin,“Forward” to Manfred Porkert,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Chinese Medicine,Cambridge,MA:MIT Press,1974,xi.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获得那些“相当少量的观念”,以便我们进而筹划对它们进行排列和重组?
我从追随亚里士多德开始,反思两种似乎非常不同的文化对经验主体的理解。我想假定一组对比:古希腊本体论式的“人”(human“beings”)的概念与《易》过程论式的、我称之为“成人”(human“becomings”)的概念的对比,即作为名词的“人”与作为动名词的“成人”的对比。这一对比透露了这样一些“少量的观念”:作为“存在本身的科学”(the science of beingper se)的古希腊“存在—论”(on-tology)③“ontology”一词在本文其他地方均译为“本体论”。——译注与作为“生活艺术”(the art of living)的、我所称的儒家“生生—论”(zoe-tology)之间的区别。
古希腊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基于“作为存在的存在”(beingquabeing)或“存在本身”(beingper se[to on he on])的实体本体论(substance ontology),它承诺一种永恒不变的主体作为人类经验的基底。由于亚里士多德将不出场的理型和目的(immanentaleidosandtelos)结合起来作为彼此独立的人的形式因和目的因,所以这个“实体”(下面—站着的[sub-stance])也就必然恒立于变化之中。在这种本体论中,同一个术语蕴涵着“去存在”(to exist)和“去是”(to be)两个含义。同一个系动词回答着两重问题:首先是“某物缘何存在”(whysomething exists),即其起因和目的;其次是“它是什么”(whatit is),即它的实体。实体界定着任何特定事物之“是这种事物意味着什么”(what-it-means-to-be-a-thing-of-this-kind),为其设立一个封闭的、排他的意义边界,并为其提供严格的同一性,以使其必然是这种而非那种事物。这种基底或本质④此处的“本质”(essence)即指上述“实体”(substance),因为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换。——译注包含了事物自身存在的目的,并构成了亚里士多德认识论分类逻辑的基础。
要回答“某物缘何存在”的问题,须诉诸作为决定者和始因的、自明的第一原理(古希腊语:arche,拉丁语:principium),而且这一问题还在造物者与被造物之间造成了形而上的分离。“某物是什么”的问题,则由对某物的限定和定义回答,并且导致了本质与偶性在本体论上的不平等。在表达事物的必然性、自足性和独立性时,作为谓词之主词的实体或本质同样也是知识的对象。这就是说,作为一种逻辑上的必然性,“某物是什么”确切地向我们揭示了关于何者为真、何者不真的“真”(truth)之源头何在。
从19 世纪下半叶起,尼采的简洁宣言“上帝死了”宣告西方哲学叙事的内部批判开始了,这种古老的本体论思维方式遭到了持续至今的挑战⑤虽然这种西方叙事内的哲学洞见向变化敞开了怀抱并拒绝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且已然发生一种决定性的生生论转向,但在一个多世纪后,那沉积在哲学语言及其语法中的本体论预设仍固着在我们流行的常识中。。杜威在关注他所谓的哲学谬误时,恰恰就以这种实体本体论及其所诉诸的那种因果思维为参考。他提醒我们意识到自己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在连续性经验中,将其中一个要素去语境化、本质化,然后将它诠释成继它之后发生的事物的基础和原因,以尽力克服一种事后归因的割裂性。对他来说,在本体论思维下,通过假设一种形式和目的因所定义的“人”(human being)的概念,就是这种惯常操作的一个具体例证。我们从连续的、叙事性的生成(becomings)之复杂过程中抽象出“存在”(being),并将它视作先于这一过程本身的原因。杜威反对这种本体论思维:
实在(reality)就是“生长—过程”(growth-process)本身……真实的存在就是这个整全的历史,是历史如其所是的样子。先把它劈成两块,然后不得不通过因果关系的力量将其重新整合,这样的操作是专断且毫无根据的。①John Dewey,The Later Works of John Dewey(1925-53) ,ed.by Jo Ann Boydston,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5,Vol.1,p.210.(译文可参[美]杜威著,傅统先等译:《杜威全集:晚期著作(1925—1953)》第1 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8页。——译注)
当转向早期中国的宇宙观时,我们可以在《易》中找到一套词汇,这套词汇清晰地呈现出一套完全可以替代这种实体本体论的预设,并以如下方式为儒家经典提供了解释语境:将经典置入一种整全的、有机的、生态的宇宙观中。作为变化背后的驱动力,“生”(living)本身乃是这种宇宙观的基始,这种宇宙观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无边无际的“生成”(becomings)世界:换言之,不是“存在”(are)的“事物”(things),而是“发生着”(happening)的“事件”(events)。那种“只有存在存在着”(only Being is)的本体论直觉是巴门尼德的《真理之路》(The Way of Truth)的核心,也是由此产生而来的那种本体论的基础。与此相反,《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生生之谓易”,以此描述至关重要的“道”(way-making)渐次展露的汇点(confluence),变化过程本身被表意地、特定地定义为“生生”(procreative living)。
鉴于“易”(change)这一复杂且模糊的概念在《易》中只是被一般性地定义为“生生”,我们得找一些注释来进一步澄清、理解它。较早的注释将“易”这个字与意为“提高、获得、有益、增加”的、同音的“益”字进行文字游戏般的互训。考虑到与其中“获得”的含义一致,郭沫若提出将“易”这个字理解为其同源字“赐”的简写,而“赐”具有“赠送、交易、交换”的含义,这意味着某种增加或提升。我们由此推断,在《易》的生态宇宙观中,这种作为生长(growth)的、自生的、交互性的“易”,在当下共时地进行、在事物中历时地发生,即在那构成所有经验的、生机勃勃的、情境化的关系中广泛而有利地生长着。诸事物间那种互益的互动在其构成性的关系中生长着,就这些互动能够增益诸事物自身及其世界而言,它们使诸事物实现了“增值”(appreciates)。正如人的成长(flourishing)在于其家庭和社群关系的积极生长,宇宙的发展与此同构,是同样的交互性生长的延伸,只不过在规模上大了许多。
说到亚里士多德关于“事物”及其第二序的(second-order)、外在的关系的学说与儒家宇宙观中相关论述的对比,葛瑞汉(Angus Graham)认为,在中国思想中:
事物是互相依存的而非独立的……将事物彼此隔离的诸问题并不优先于将事物联系起来的诸问题。②A. C.Graham,Studies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ical Literature, Albany 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0,p.395.
葛瑞汉此言意在说明,在儒家宇宙观中,那个回答作为主体的某物“是”什么的、本体论的“什么”(what)问题,与其他那些揭示主体如何与其周遭的他者相关联的偶然性问题,是关于同一现象的两个第一序的(first-order)方面。换言之,某事物的个体性并非外在于其(与他者的)关系,而是由这些第一序的关系所构成。而且,其独特性或“个体性”的品质与其在这些关系中达成的联结之品质息息相关。这不过就是说,人格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ies)与其叙事(narratives)之间的不同,仅仅在于将视点(focus)还是视域(field)前置(foreground)。人自身与其叙事实际上是同一事物,其中并不存在既定潜能与其实现之间、天赋本性与其重复实践之间的那种手段与目的的二分。正如杜威在上面提到的:“实在就是‘生长—过程’本身。”
三、摆脱西方个人主义与东方集体主义之分
我们经常提起“西方个人主义”与“东方集体主义”,以说明分立的人的文化与具有不可化约的社会性的“成人”文化之间的区别。我们通常将其理解为一个手段与目的的问题,东方集体主义强调社群(community)需求的优先性,而西方个人主义则重视个人的权利。集体主义文化崇尚团结、无我和利他的精神,而个人主义文化则宣扬独立、个人选择和个性。即便我们考虑到儒家哲学强调礼仪化家庭和社群中的那种至关重要的关系的优先性,以及儒家“家国天下同构”的政治观念,身处与国家的关系之中的个人,其本性与价值就可以藉由“集体主义”这一概念完全把握吗?
探讨以下对比或许是回答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一方面是对许多个体声音(思考的权利the right to think)的西方自由主义式承诺,另一方面是对作为首要的社会性善好的社群共识(正确地思考right thinking)的传统儒家式关注①参 见Randell Peerenboom,“Confucian Harmony and Freedom of Thought:The Right to Think Versus Right Thinking”,Wm.Theodore de Bary and Tu Wei-ming(eds), Confucianism and Human Right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正是西方政治观念中的这种对思想自由的辩证承诺,奠定了一种健康的多元主义意识、对僵化的保守主义和“正统”的深刻怀疑以及对忠实的反对者的持续尊重。作为对比,儒家承诺的是社会和政治秩序,讲究的是持守“中”道的“变通”以及对“和”的追求,这在以下观念中得到证实:以首要道德命令“孝”为基本原则的等级制家族谱系、宣扬共享价值观的制度化的知识分子、经典文本中字里行间的注释以及杂糅的儒家传统自身所具有的那种极为神圣的连续性。同时,从儒家的角度看,正是这种对社群团结的关注,使我们将对个体自由的许可视为放纵、将看重个体选择视为自私。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关于整齐划一地“正确地思考”的预设,儒家传统中对人的理解含糊其辞,因此我们需要认真地修正。许多诠释作品中有一个令人遗憾的预设:作为手段和目的的社群利益和个人利益是相互排斥的;因此,作为家庭和社群的可靠成员,一个人必须努力变得“无我”(selfless)②例如孟旦(Donald J.Munro)认为:“无我……是中国最古老的价值之一,在道家和佛家中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儒家尤多。”(“The Shape of Chinese Values in the Eye of an American Philosopher”,in The China Difference,ed.by Ross Terrill,New York:Harper & Row,1979,p.40)同样,埃文(Mark Elvin)认为:“个体只有作为旨在消灭个体性的、不断重复的道德努力之发生场所,才具有意义。”(“Between Earth and Heaven:Conceptions of the Self in China”,in The Category of the Person:Anthropology,Philosophy,History,ed.by Michael Carrithers,Steven Collins and Steven Luka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185)我很高兴看到黄勇在他的文章中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对这种常见的思考方式作出了 自 己 的修正。参“Confucian Ethics:Egoistic? Altruistic? Both? Neither”,in 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 13:2(2018)。。不管在古代还是现代,将“无我”归于儒家传统的做法,似乎来源于在“自私”(selfish)和“无我”之间令人遗憾的含糊。实际上,回避私心并不必然导致自我否定(self-abnegation)。
与此相反,作为“四书”之首的《大学》展示了儒家的筹划。它劝告我们,在努力成为完满圆熟之人的过程中,亟需重视的是在构成着我们自身的关系中进行修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正如孔子自己所说,修身的筹划“(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尽管修身是“由己”的,需要自己勤勉的努力,却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件孤独的事;它只能通过修治我们丰富的关系(这些关系使我们置身于家庭、社群和国家中的日常角色)来达成。儒家哲学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政治概念,在思考它时,我们必须以家庭的、政治的和天下的秩序间的同构性为出发点,并充分地重视它,因为这些秩序既根植于、也涌现于关系构成的人的修身之道中。《孟子》明确描述了这种作为政治概念的有机共生关系,在其中,作为扩大版的、自反的修身场所,“国家”和“天下”是对“家庭”的模拟:
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第五章)①同见《孟子·离娄上》第二十七章。
传统儒家认为,由于个人实现在根本上是一种社会性事业,所以阻碍我们的发展和自我实现的排他性的私心应当被否弃。在传统儒家哲学中,有一个可追溯到《论语》的、经久不衰的话题: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第十六章)
对私利的关心被视为小人在道德方面的发育不良,而力求使每个人(包括自己)各尽其宜则是“仁”的核心,是君子之道。
很明显,儒家传统大体上认可一种关系性的、从而也是社会性的人的定义,而非任何关于分立的个体性的观念。我们必须进一步承认,认为人是独立于或优先于社会的利益主体的观点,似乎并没有充分的哲学基础。在这种对人的关系性理解下,人们普遍承认,在传统儒家范式中,个人的、家庭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自我实现是相互关联且彼此依存的,而且,儒家那种不可化约的、社会性的人的观念必须在“一多不分”(being one and many at the same time)的意义上被理解②唐君毅:《唐君毅全集》第11 卷,台北:学生书局,1991 年,第16—17 页。这种“视点—视域”式的而非“部分—整体”式的语言,是对中国宇宙观中普遍存在的相互关系的一种表达。在某些最抽象和古老的重申下,这种相互关系凝结在如下表述中:在“道德”(this focus and its field)、“变通”(changing and persisting)和“体用”(reforming and functioning)宇宙观中的“一多不分”(the inseparability of one and many)。。但这种不可化约的社会性并不意味着彼此间的互相依存要求“无我”。正相反,对“自私”的否弃,绝不意味着“无我”,而是自我实现所不可缺的态度。
经过仔细分析我们发现,鉴于儒家思想具有一种将人嵌入协同共生的社会生态中的范式,那么那种将“无我”作为一种理想归于儒家传统的做法,将会隐秘地带入个人/社会、公共/私人和手段/目的的二分法。因为,若要达致“无我”,就意味着首先存在一个个体“自我”,然后为了某种更高的公共利益而牺牲它,因此个体只是通达更高的社会目的的手段。而且,那种认为在个人一边或社会一边存在着“更高利益”的看法,已然偷偷在二者之间划出界限,并建立一种对抗关系。将“无我”解释为儒家的理想,与儒家所主张的人具有不可化约的社会性之间存在矛盾,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前者是对后者的破坏。
“无我”的理想最终会导致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对抗,以及拥护群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两个群体间的论争,在西方,这在很大程度上将集体主义的思想家与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区分开来,但这与儒家传统并不相关。虽然对传统儒家哲学来说,个人的自我实现不以高度的个体自主(individual autonomy)为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除此之外就只能向普遍意志(general will)投降。更确切地说,成为一个儒者,表明我们一方面要使那个相互忠诚且负责的世界中的所有成员获益,另一方面我们也受益于他们,他们生活在我们周围并与我们遭遇,他们将决定我们自身的价值。儒家哲学在个人修身与家庭和美、国家富强和天下大治之间预设了一种毗连的共生关系,而自由主义的西方将限制国家权力视为实现个体自主的先决条件,两者形成了鲜明对比。
四、“分立个体”与“独特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
我和我的同道们主张儒家式的人由其关系构成——或者用葛瑞汉的话说,它们是第一序的关系的诸样式(patterns)——如果没有这些样式,儒家式的人就不存在。我们的许多对话者在回应上述看法时有一个常识性的直觉,它基于这样的预设:任何关于“人”(a person)的可靠概念,必须有一种自主的、一贯的、独立的、因而也是独特的自我认同(identity)。对他们来说,儒家这种稀散的(diffused)、关系性的人的概念缺乏一个锚定它的、上位的、坚实的自我,这对人保证其自身整全且独特的人格来说是重大威胁。
在为我们提供权威直觉的实体本体论看来,相同的本质或形式(eidos)将所有人类界定为一个整体,这意味着一个物种的所有成员在本质层面都是相同的,只是在偶性上才有差异①我们可能还记得,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开始,这种范畴论思维将种族、宗教信仰和性别上的差异本质化、本性化,由此产生的歧视意识流传至今。。例如,古希腊理型主义者所理解的“人”的人格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是这样一种范式:具有某种完全同一特征的、相互外在地联系着的、分立的个体。依此看,人在本质层面被设想为完全同一,不同处只在于偶性,在这种范式中,每个人的人格同一性只具有一种相对残缺的独特性。
虽然我们的常识可能已经对此有所了解,但完全同一性这种本体论概念,如今却披着一身当代的、更为开放的外衣延续了下来:例如,所有个体,不管在性别、世代、种族、宗教和阶级等方面有怎样的差别,但在法律面前,他们表面上都具有平等的地位。因此,那种认为我们的许多差异最多只是搁浅在共享的本质同一上的偶性的主张,只在相对薄弱的意义上为我们说明了人的独特自我认同和个体整全性(personal integrity)。
由于我们随波逐流地信奉基础性的个人主义,所以“关系构成的人”的概念一被谈起,就常常会被误解为一种非常稀散的人格同一性。但从另一方面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证明,作为个体自主之表现而被高度重视的独特的自我认同,非但完全没有被“关系构成的人”的概念损害,实际上反而为其增强。在构成性关系理论看来,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关系网络,我们无论如何都是如此。相较之下,这种彻底嵌入(关系之中)的“人”的范式,才大大增强了人的独特性。
因此,当我们宣称分立的“个体”才是第二序的、是从第一序的“关系”中抽象出来的,意在明确区分以下二者:一方面是我们可以称之为抽象出的、派生的、分立的“个体”,它是基础性的“个人主义”的大部分变种的预设;另一方面是一种具体的、由第一序的“关系”构成的、独特的“个体性”,它是对儒家式的人的定义②约翰·杜威同样致力于阐述一种“关系构成的人”的概念,我从他那里借用了“个体性”这一新词。我对杜威的观点及其与儒家“人”的观念的相契性的讨论,参Roger T.Ames,Human Becomings:Theorizing Persons for Confucian Role Ethics,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21,pp.260-267。。我们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里所作的区分,且以罗思文(Henry Rosemont)这个人为例。首先,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孤立的罗思文所具有的形式上的法律地位,这样的他不受种族、性别或世代等因素牵扯,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人,他能够与许多其他自主个体达成合法契约。然后,我们再考虑那种关系所构成的独特的人的、第一序的“个体性”,也就是说,有这样一个唯一的罗思文:他是那个我们都深爱着的、与众不同的杰出的人,他所度过的一生塑造了他那复杂的、爱默生式的人格,而他的一生是一种与其家人、学生和朋友共同度过的独特的、典范的叙事。
将我们的角色以及与他人的关系视为内在的,这种学说并不会忽视具体的人的独特个体性,而是想要指出:这种个体性非但不排斥这些关系,而且其自身就与我们和他者所形成的关系的品质息息相关,因为这些关系构成了具体个人的核心人格。罗思文之是其所是,在于他曾经生活于其中的许多角色,也在于他与我们每个人形成的关系的品质。在这些关系中,我们已然成为其人格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我在此用罗思文作例子的原因是,尽管令人悲伤的是他已经去世了,但作为一个有着最为传奇的职业生涯而且对许多人都有重大影响的人,在我们如何继续生活的意义上,他至今仍然亲切地与我们同在。换言之,像罗思文这样的人,他们始终在我们延绵着的历史中被关系性地界定为独特的核心事件,而非被圈定为单独的个体,即使是死亡,也无法削弱他(的存在)。为了明确显示“个体”的两种不同含义,我们需要重视这样一种区分:儒家的关系构成的“个体性”,此乃第一序的、具体的现实,以及仅仅是从现实中抽象出的分立的、自主的“个体”,它是派生的、第二序的。
五、人权:我们想成为何种“人”?
至于“人权”问题,我们同样可以诉诸儒家这种不可化约的社会人(既是“一”也是“多”)的概念,以调和我们在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中发现的不一致。在《世界人权宣言》一开始的21 个条目中得到明确表述的个人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常常被称为“第一代”权利。在保护个人的自主和自治权的意义上,这些条目大体上提供了一种消极的自由。这些权利基本上保障的是我们免受侵犯的自由,其设定的目的在于保护个人的完整性。
但在《世界人权宣言》的最后六个条目中,它还列举了大量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权利,包括安全权、就业权、温饱权、教育权、卫生保健权、体面住宅权等等。这些所谓的“第二代”权利,乃以我们彼此间的义务为基础,它使每个人都有积极的自由和权利去充分参与其社群生活。也就是说,这些社会权和福利权通过要求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对彼此负责,很大程度上巩固了分配正义的基础,而且,这些权利的设定也对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的过分行为提供了必要的遏制。
在“二战”给全世界造成破坏之后,这些所谓“第二代”权利即被纳入《世界人权宣言》,以敦促各国政府致力于在其境内消除贫困。这些追加的经济权、社会权和文化权的提倡者会认为,没有这些权利,所谓自由和自主充其量只是脆弱的概念而已。这些社会权利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们致力于消除通往繁荣社会的社会性的和自然的障碍,并提高我们在家庭和社群中充分自我实现的能力。作为社群的一员,我们应当积极关心这些权利的落实——如果要让其他人都能获得这些权利所保障的利益,那我们就必须有所作为。也就是说,我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必须交更多的税并分享我们的个人资产。换言之,学校、药品、工作、食品安全、可负担的住房、医院等等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们都是人们创造出来的,因此我们都得为此有所付出。
当如此做的理由被理解为自主个体概念具有优先性时,当代人权话语的根本矛盾就浮现出来了。关于帮助他人创造和获得那些“第二代”权利所规定的东西,无论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被视为对此有道德责任,都不可能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我们都是自主个体、享受第一代权利、自由理性地决定并执行我们的规划,而非必须帮助那些不幸的人。“第二代”权利在这种意义上是积极的:如果你或任何其他人想要保障这些福利权益,那么我应当做一些事并在一定程度上让渡一些自由。
为了调和《世界人权宣言》的这个矛盾,我们应当以另一种方式重思“人”,使人们对那些构成其社群的许多他者负责的同时,自身仍能保持一种坚实的个体性。从儒家的角度看,那种“一多不分”的预设在将“人”置入其角色和关系之中的同时,还告诫我们:当我们忽略具体情境,把从中抽象出的东西当作不变者和终极者时,我们就遭遇了“抽象化之险”(the perils of abstraction)。在西方自由主义者对中国的无休止的指责中,我认为第一代和第二代权利之间看似互斥的区别是其中的主要议题,它同时也是中国对此进行愤慨回应的白皮书。从中国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有力地主张,如果我们着眼于第二代人权而非个人权利,那么中国空前的经济腾飞、扶贫计划的巨大成就以及日趋壮大的中产阶级将明确告诉我们:在近些年的人类历史上,至少在促进其民众对人权的理解方面,它比任何其他民族国家都做得多。
六、关系性自主(Relational Autonomy)和“厚选择”(Thick Choices)
在研究世界哲学时,我们常常面临两种选项:要么放弃我们熟悉的哲学词汇,要么重整并延伸这些词汇以适应另一种非西方的叙事。就中国哲学来说,由于它未提供一种古希腊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也没有提供一种亚伯拉罕意义上的“宗教”,因此我们可以选择完全弃置这些术语,用它自己的词汇(即中文)表达它的世界观①当然,由于以下事实,事情被复杂化了:在19世纪下半叶,人们发明了一套新的中文词汇以使亚洲跟得上西方现代性词汇的脚步,它从日本开始然后传遍了整个东亚。因此,如“metaphysics”(形而上学)、“ontology”(本体论)、“religion”(宗教)这些术语如今在中文中都有对应的词,但它们仅仅是对西方词汇的翻译而非传统术语。参Lydia H.Liu,Translingual 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1900-193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或者我们可以尝试修正这套西方哲学词汇,以使其适应那种赋予中国哲学以独特性的特殊预设,并同时让哲学这一学科对自身的术语获得一种更宽泛的理解。
因此,即使我认为儒家角色伦理学对道德生活的理解自成一家,有其自身特定的、专门的词汇,但为了能够在我们自身的哲学语境中更好地理解这一传统,从而就此与当代西方哲学家进行更有效的交流,我们也许需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应如何理解并重构当代伦理学话语中那些耳熟能详的主体性(agency)术语(例如“自主”和“选择”),以便它们能够在解释儒家角色伦理时发挥作用?由于诠释学(hermeneutics)的起点在于承认以下事实:当我们进行解释时,经验的诸种意义结构(我们藉以“理解”[understanding]经验)具有相互依赖性。因此,文化比较的诠释实践应当说明两种传统在哪些方面对立以及在哪些方面相关,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两种传统。对伽达默尔(Gadamer)来说,(“理解”始终产生于其中的)诠释学循环(hermeneutical circle)要求我们不断地努力察觉自己将什么东西带进了新的经验中,因为对自身预设和目的的批判性关注会让我们更深入且精准地诠释所遭遇的经验②参Jeff Malpas,“Hans-Georg Gadamer”,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all 2018 Edition),Edward N.Zalta(ed.),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18/entries/gadamer/。。质言之,我们认为:相较于在两种传统内部各自进行研究,文化比较的诠释实践能够激发出更多的洞见,因为在这个实践过程中呈现出的关联和对比可能产生额外的意义。
作为哲学研究的主体,独立的“人”与互相依存的“成人”之间的差别所蕴含的意义,在关涉到主体性问题时要特别加以注意。个人主义意义上的自主(autonomy)一词是由希腊文的“自我”(autós)和“法”(nomos)组成,字面意思就是一个给自己制定法则的人或自我立法的人。通常来说,自由主义理论中的“自主”意味着自我管理,其理论起点在于一种分立的、独立的和排他的自我。
正如我们所见,在儒家角色伦理学中,像“自主的人”及其“选择”这些术语并不是让我们把人理解为独立的理性行动者,也不是让我们将其选择理解为这些个体行动者自由地选择他们日常的事务。其实从儒家的角度看,“分立的个体”这样一种自由主义概念可能仅仅是一种出于实用考虑的抽象,其有时所宣称的完全自主可能不过是一种误导、是一种至今仍然十分强大的虚构。如果人们相互关联地生活是事实,那么我们的彼此分立就只不过是一种浮于表面的现象,它既不是我们存在的源初境况,也不意味着我们彼此排斥。相反,正是由于我们能够与他者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我们才会变得特别甚至卓越。在儒家看来,“人”的概念是动名词(而非名词)形式的,人是独特的、互相依存的。对这样的人来说,关系性、独特性和社会性都是其个体性(individuation)的来源和表达,而且,这种个体性(独特性[distinctiveness])不仅不排斥人与他者的关系,其形成还与人处理这些关系(这些关系构成着人本身)的技艺息息相关。
“自主”和“选择”这样一些常见的自由主义术语当然也可以适用于儒家角色伦理学,但关键是我们必须重新构想它们,将其视为前置的、抽象的特定视点(focusing particular)以及在社会和伦理活动中相互贯穿的诸位相(phases),这些位相与其自身显现于其中的整体叙事保持一种有机的关联,并为其所影响与渗透。我们将不可化约的社会行为的品质称为“关系性自主”,藉由对共同目的的遵循,它使我们在家庭、教室和社群中凝聚在一起。一种自觉的“关系性自主”描述的是旨在实现完满角色和关系的、自作主宰的行动,而具有批判性自我意识和不可化约的社会性的主体(agents)的“厚选择”描述的则是这些主体在其与他者共同生活的角色中所下的决心和承诺。我们的“厚选择”反映的是我们对自身作为母亲、教师和邻居等角色的持续且一贯的承诺或投入。
在儒家语境中,做出选择的自主行动者就是关系构成的、彻底嵌入(关系之中)的人,其偏好大体上是通过其对特定事件中的角色的投入程度得以表达。如此理解的“关系性自主”并不指涉那种完全掌控其具体独立行动的个体,而是指向自觉的、但又具有不可化约的社会性的主体,他们能够自在地、免于胁迫地行动,因为他们在持续的交互性活动中相互地适应调整。而且,他们所作出的“选择”,并不是分立个体在行使那种不顾他者利益的自由时的、各自为政的重要时刻决策(big moment decision-making)。这种“选择”仍然与具有不可化约的社会性的主体相关,通过“选择”,这种具有批判性自我意识的主体兑现着以下承诺:在角色和关系持守某种一贯的行为模式。
我们在此必须说明,构成性关系的学说并没有剥夺人的主体性及其选择权(preferences),而是让我们以符合相互关联着进行生活这一经验事实的方式,重新构想这些常见的术语(例如“自主”和“选择”)。我认为角色伦理学通过将人置入其生活中的诸事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在经验上更令人信服的人的主体性观念。在这种观念中,人格同一性是自觉的、聚焦的(focused)、有明确目标的且坚决的(resolute),同时在一种重要的意义上,它又弥散于我们的关系性之中。尽管我们核心的自我认同之特殊性是由那种个人决心(resolution)所保证,但它的存在与形成又恰恰与“我们在他者眼中之所是”(what we mean for others)相关联,并紧密依赖于此。比如作为儿子的角色,我对老母亲的所感所想的敬顺,必然塑造着我持存着的自我认同和行为。人格同一性的确是独特的,但它同时也是具有多重意义的,因为它被包含着我们周遭他者的、各种各样的关系所交叠。如此看来,我们的自我认同既始终持存又总在变化,既具有自觉目的又包容且随和,既被个人规划所驱动,又尊重且关心着他者。
在上面讨论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诸特征中,民主与专制、个人自由与权威主义经常被拿来对比,而傅满洲(Fu Manchu)式的东方专制就是对儒家政治文化的脸谱化的夸张描述。但是,在将“正确地思考”作为共识的儒家范式中,任何以强加或其他方式将简单的同质性塞给儒家的做法,都会遭到其以“和而不同”和“义(适宜)”为最高价值追求的反对①我们对《论语》中“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的格言已经很熟悉了,这个重要的主题(君子与小人)在其他文段中也延伸到了更具体的社会和政治语境,并用另一种对称的语言加以重述,例如“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以及“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那种使关系性自主得以可能的对他者的敬顺,与其说它仅仅在要求一种同质化,不如说关涉对彼此差异的包容适应以及相互支持。
在我看来,政治与社会秩序同构的儒家观念,既不是专制者的命令自上而下的强加,也非公共福祉自下而上的表达。儒家设想的是,道德领袖的劝导会产生一种社会和政治共识,并由此促成一个自我规范的社群。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点,那么理想的儒家统治者的表现便是“有(reign)天下”而非“与(rule)天下”②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第十八章)——译注。最好的统治者仅仅“恭己正南面”,儒教国家的理想是“必也使无讼乎”,以及整个国家由一种通过“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来的“有耻且格”的文化主导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繁荣兴旺的儒教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乃是“由内而外”(middle-outward)而非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
由于关系构成的人与他者相互依存且没有明确的边界,因此,在任何特定的情境中,自治(selfgovernance)都涉及一种(由诸关系共同)聚焦的、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弥散的、开放的人格同一性。而且这种交互性的人格同一性也意味着:我们必然将各相关方的利益视为决定自身所实现自治的品质的必要元素。这些互相依存着的诸自我(selves)的关系性自主与“他们在彼此眼中之所是”(what they mean for each other)息息相关,因为他们的特殊差异已经得到协调因而在共同的智性实践中实现一种充满意义的多元化。如此界定的关系性自主,与其说表征某种表面上的独立选择,不如说体现在以下行动中:以对他者利益的自觉敬顺限制我们的目的并使其合理化,从而在日常的共同生活中减少胁迫。实际上,那些被视为君子的人之所以比其他人更具有自主性,是因为作为激励着民众的模范,他们通过敬顺的公共范式感召他们,并感化、影响其社会行为。举例来说,典范叙事下的甘地(Gandhi)、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或曼德拉(Mandela)就有这种关系性自主,他们作为模范的所作所为,确实激励了一代代人,对定义我们时代的价值观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过敬顺并效法他们的价值观,我们便与他们的公共人格产生了内在联系。
七、善养吾浩然之气
我们已经对“关系性自主”以及“厚选择”这些儒家理想观念作出了理论阐述,这些观念与儒家的“君子”模范相关,因为正是由于他者对他们的敬顺才使他们成为“君子”。但在儒家经典中,是否有文本支持我们对自主和选择作如此理解?我想用《孟子》中最出名的一段话及其独特的儒家词汇来论证我的观点。
“敢问夫子恶乎长?”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公孙丑上》)①由于下文的讨论常涉及其中的关键概念,因此我将作者对此段文本的翻译照录于此。——译注“May I ask after your strong points in such things,Sir?” said Gongsun Chou.Mencius replied:“ I realize what is being said( zhiyan 知言),and I am good at nourishing my flood-like qi 气( haoranzhiqi 浩然之气).”“May I ask what you mean by the expression‘ flood-like qi 气’?”Mencius replied:“ It is difficult to put into words.It is activating our qi 气to have its most extensive reach and its most intensive resolution.If we nurture it faithfully and without respite,it will fill up all between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As the achieved quality of our qi 气,it is of a piece with sustaining optimal appropriateness in our conduct(yi 义)and with moving resolutely forward in our way-making(dao 道).Without this moral quality of qi 气,it starves.Flood-like qi 气is what is born of the cumulative habit of optimally appropriate conduct,and is not something that can be had through mere random acts of appropriateness.If one does anything that would cause disappointment in our thinking and feeling,the qi 气starves.”
“知言”(realizing what is being said)之说很可能指的是《论语》中孔子所说的:“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第三章)但此处重要的是去玩味通常翻译为“知道”(knowing)的“知”字的施为含义(performative implications)。这种非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所展示的一个直接含义是,我们所熟知的知识与智慧的二分在此并不存在。正如王阳明那广为人知的论断“知行合一”所示,在儒家传统中,“知”总是意味着有所“行”。因此,孟子此处所说的“知”乃是一持续的实践过程,而非一种已然达成的、独立的心灵状态。这种“知”的能力绝非仅仅局限在认知层面上“知道”些什么,我更愿意在“使某些事物成为真实”的施为意义上把它翻译为“实现”(realizing)。
同样,这也对这样一种通常的思考方式提出了挑战:“知道”所涉及的那种“排他性的客观性”与真理之间具有镜像一致性。另一种“包容的客观性”则认为,“知”必须是对任何特殊情境的全景式观照和全面性参与,以此在其中产生一种多方共享的“客观”(objective)。它不是那种承诺着单一真理的客观性,而是从多方的共识中呈现出来。既然如此,从孟子的“知言”而来的“知人”就意味着协调安排一个共同的目的以感化他者,就算没有现实的改变,也至少对他们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知言”之说与“养吾浩然之气”相似,它们都在表明我们必须以符号学的方式(semiotically)理解人类的关系:在我们始终进行着不可化约地、社会性地“思考与感受”①“思考与感受”即“thinking and feeling”,作者将《孟子》“行有不慊于心”的“心”也译为“our thinking and feeling”,意在强调“心”的关系性和过程性。——译注的意义上,理解我们与他者的“关系着”(relating to),一种相互关照的“关系着”才有意义。在把握了这种关系性的发散本质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理解:构成我们特定的自我认同的那些关系的品质如何,是由我们一直以来与他者所进行的交往的品质所决定的。而我们在家庭和社群中进行有效的、有意义的交往的能力,则直接决定了我们将成为怎样的人。
正如“知言”需要符号和象征的交流一样,孟子的“养吾浩然之气”也是一个人与其周遭环境进行交往和共鸣的一种方式。通过“养”“气”之“至刚”(intensity)和“诚”(resolution)②作者也将《孟子》中“至大至刚”的“刚”翻译为“resolution”。——译注,“气”就会志向化(intentional and deliberate)。孟子谨慎地指出:虽然志通常牵动着气,但有时气也会反过来牵动志。在发散性的关系语境中养气,有助于我们在其中实现个人成长,并锻炼我们的行为技艺。一个人必须在养这种道德性的气上多下工夫,这意味着一个人必须包容适应情境中的他者,以实现对一切相关之人物而言的“义”。在我们的一切行动中实现“义”的努力,会激活我们那表现为目的明确的行为的气。孟子认为,当他恰当地养气并使其达到“至刚”时,就会使他对他所处的世界产生“至大”的影响。
在这段文本中,至刚视点(intensive focus)与至大视域(extensive field)之间辐射状的、共生的动态结构,随后又通过“义”与“道”这对概念得以重述:也就是说,孟子之所以能实现那至大的影响(道),不在于偶然的“义”的行为(义袭),而是靠在构成其人格同一性的关系中习惯性地、坚决地投身于“义”(集义)。对孟子来说,最成功的养气是,在其气的至大场域内实现最大程度的“刚”。如此一来,由于他在与周遭环境中的广泛事物的关系(道)中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影响力(德),因此他也就得到了持久且精湛的行为技艺(道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养气具有浩然的、甚至是宇宙性的影响。
同样的,在我们所使用的“精神”(通常翻译为“神灵”“精力”“活力”“驱动力”)这个常见词中,也可以发现那种与至刚视点与至大视域之间同样的动态结构。通常被翻译为“本质”的“精”,不是某种与偶性相对的本体论本质,而是个人生命力的集中源泉,它既是生理的也是精神的,因而它既来源于父母也可通过各种修养方式获取。“精”是生命的精华,是一种可感知的、赋予生命的能量,是元阳的效能。通常被翻译为“神灵”(spirit)的“神”,不是与物质存在者相对的那种精神存在者,而是与“精”一样指生命力,它是流淌的、涌动的、弥漫的,它在我们身心协同向外辐射的、改变着世界的功能活动中显现出来。在我们广阔而灵动的生活中,“神”是我们的灵魂得以变得高尚的奥秘,正如《系辞》所说:“阴阳不测之谓神。”
儒家哲学提倡一种成长,其核心是努力在亲密的家庭和社群关系中修身,然后一边反身向内、一边辐射向外,以协同地延伸至整个宇宙。这是中心与周遭世界的相互渗透,作为至大者的周遭世界反向向内筑牢至刚者,而作为中心的至刚者也有其至大的影响范围。在上述引文中孟子还有一个重要论断:通过在各种层面的交往中修身,“大人”真实地影响着整个宇宙的道德化建构。孟子认为,我们确实能够对世界的道德品质有“浩然的”“塞于天地之间”的影响,孔子、佛陀、苏格拉底和耶稣都曾如此。
相反,如果不去培养我们那种绝对发散的自我认同——不去养气、不用与我们共享的价值相续的方式构建它,那么我们就会心有所慊,并由此最终丧失(“馁”[starve])任何成长的可能。“生活艺术”(art of living)的“生”(birthing,living,growing)所暗含的生生论,在气之“馁”的比喻中得到清晰展现——生命得以维持和成长的本质在于“养”。
八、作为关系性自主的历史典范的孔子
君子因其关系性自主而在其社群中受到人们的敬顺,但圣人却有着跨时代的影响,因此那种能够作为养浩然之气的终极典范的圣人在历史上并不多见。继上面所引的《孟子》文本之后,孟子将对话主题转向了对比历史上的圣贤人物。孟子的学生公孙丑提到两个古代公认的圣贤人物——伯夷和叔齐,作为讨论孔子的“圣贤性”(sagacity)的参考标准。然而,孟子却直言不讳:“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尽管孔子离孟子的时代并不远,但他不仅再三将孔子纳入古代圣贤的行列,甚至还将其单独挑出以居于其他圣贤之上。这两位周代初期的先贤与孔子之间的对比,显明了孟子对最高人性的看法。在孟子看来,伯夷、叔齐都是“古之圣人”,都有许多可取之处,但同时又是偏颇的、固执的和不完美的。与此相较,孔子不仅是典范之一,而且是其中最佳的。对孟子来说,最佳的典范是在其诸关系中表现得最“全”(comprehensive)的,即对复杂关系中的任何特定情境都能最有效地照察并作出反应①有趣的是,早期辞典中对我们翻译为“comprehensive”的“全”字的训释,表现在品质、数量和审美三个方面。例如《说文解字》将“全”训为“完”(complete),这个字既有数量上“完备”的意义,也有品质和审美上“完美”的意义。而且《说文解字》还将“全”比喻式地界定为纯洁无瑕的玉:“纯玉曰全”。。孔子最杰出的学生们持续地用圣传式(hagiographic)的语言形容他,这些语言虽然不是宗教术语,但也会让人联想到描述儒家宗教性的常见话头:“天人合一”。通观早期文献,我们发现人们总是用与“天”相关的词汇将孔子形容成像日月一样,用自然词汇将他的行为抬升到四季更迭的高度,并且具有山川大地的威严②例参《孟子·万章上》第一章,《论语·子张》第二十三、二十四和二十五章,《中庸》第三十章。。
还有另外一点值得注意——孔子在中国文化之产生发展中起到了独一无二的作用。对于以下情况,孔子是一个最好的示例:在实现一个可能世界的过程中,当我们对经验进行主观转变所产生的效果与经验自身那种受动特征完全协调起来时,这种经验的主观转变是如何逐渐成为那个正在生成的世界的共同目标的。的确,儒家思想和过程宇宙观尽管都有重要的理论义涵,但它们之所以具有说服力,是因为它们产生于对真实人类经验的相对直接的叙述,这也是其根基所在。儒家思想并不作出关于永恒不变的本质或超自然的不死灵魂和救世目的的推断性预设——这些都会将我们抽离经验世界,它关注的是我们在此时此地充实个人价值的可能,而其实现则在于尽心尽力地安顿日常事务。人类日常经验最基本和最恒常的方面,在于家庭和社群角色中的修身、孝顺、敬顺他者、在我们的角色和关系中举止合宜、友谊、有教养的羞耻感、道德教育、正常交往的社群、以家庭为中心的宗教感、文化的代际传承等等。孔子就是围绕着它们来发展他的思想,以此确保其中积累的诸种智慧具有持续的相关性。除了关注这些恒常事务外,儒家哲学的另一个特征在于其通透性和适应性,这一方面恰好体现在孔子自己的言语中,另一方面也使他的教诲在儒学这个活的传统中富有韧性。他的不朽贡献完全在于尽力吸收其所处时代和地域的文化遗产,并将这些自古而来的丰富智慧用以改善其所处的历史时刻,然后托付给子孙后代做同样的事。
九、人人皆可成圣
我们若能记得上面对生生论与本体论之间的对比以及前者对至关重要的关系性的重视,那么就可能对孟子及稍后的荀子所说的“圣人与我同类者”有所理解。考虑到我们对本体论有一种惯常的信奉,因此要切忌将目的论的预设带入这些说法中。在找寻关于事物的合理解释时,杜威提醒我们要防备本体论思维习惯:将任何特定事物的“特性”追溯到它背后的某些东西,并保证此事物乃某些形式种属或自然类别的具体实例而已①“我们都太容易贬黜经院哲学家们按照真正的本质、隐藏的形式和神秘的官能来解释自然和心灵的努力,忘掉了藏在其背后那些观念的严肃性和尊严。我们通过嘲笑那位著名的绅士来贬黜他们,他用鸦片具有催眠功能来解释何以鸦片能使人入眠的事实。但是,我们这个时代流行的学说认为,关于生长罂粟的植物的知识,在于将一个个体的这种特殊性归诸于一个种类、一个普遍的形式。这个学说如此牢固地被人们所接受,以至于任何其他的认识方法都被当作是非哲学的、非科学的。”John Dewey,The Middle Works of John Dewey (1899-1924),ed.by Jo Ann Boydston,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Vol.4,pp.6-7.(译文转引自[美]杜威著,陈亚军、姬志闯译:《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4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页。——译注)。
那么孟子和荀子说所有人都能成为圣贤究竟何意?孟子在他的道德心理学中要求我们反思,自己是如何从家庭和社群中的那些最初较为微弱、相对被动但又复杂的关系模式中开始生活的。他将我们天生的性情倾向(disposition)称为“四端”(four inclinations),一方面,当它们落实为行动时,可以产生有教养的人类之善;另一方面,它们还为孟子的以下观点奠定了基础:由于具备这些天生的条件,所有人都会倾向于像圣人一样行动。通过在那些具身化的角色和关系中努力成为“至刚”的视点,我们逐渐发展出独特且较为连贯的人格同一性。对孟子来说,凭借自强不息的努力而成为我们当中最杰出者的那些人,的确是我们的至大视域中的君子典范,是为我们的社群指引方向的灯塔。这些君子中的最优者,聆听着时代的声音并成为时代的代言人,他们就是我们所说的圣人。
对于孟子和荀子而言,我们并不是“潜在的”圣人——凭借某种定义我们这一物种所有成员的、相同的先天特征,我们就都能成为圣人。而是说,具备某些天生性情倾向的我们在与自身所处的世界的互动中,能够表现出圣人般的行为。注意,这种行为并非英雄主义的或异乎寻常的,而仅仅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做日常的事。
我们说“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成圣潜能”与说“每个像圣人一样行动的人就是圣人”是不同的。成圣的潜能并非现成的,而仅仅只在构成人类生活之实质的交互性事件中才同步地呈现出来,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中的最杰出者始终一贯地、习惯性地像圣人一样行动时,他们才是圣人。质言之,圣人就是圣人所做的事。在孟子指出“正是圣人般的行为使人成为圣人”时,这一点得到了明确:
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孟子·告子下》第八章)
在本文中,我们考察了席文所谓人类巨大创造力背后的“少量的观念”。我们试图阐述本体论和生生论之间的差异,这对我们的讨论有所助益——将二者的不同预设联系起来、形成对比,由此加深对两种传统的理解。然后,我在澄清某些或有效或无效的概括(它们常被用来描述古希腊和儒家的哲学叙事中的不同世界观,以及二者对当代问题的影响)时,探讨了从这种差异中显露出的(观念的)某种“重组和排列”。对我来说,本文的要点可能在最后一节,我在其中表达了与之前的葛瑞汉相同的担心:如果我们未能充分注意不同的诠释语境,忽略古希腊的实体本体论和《易》所明确表达的过程宇宙观之间的差异,那我们阅读经典时就不免含糊两可了。
——由刖者三逃季羔论儒家的仁与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