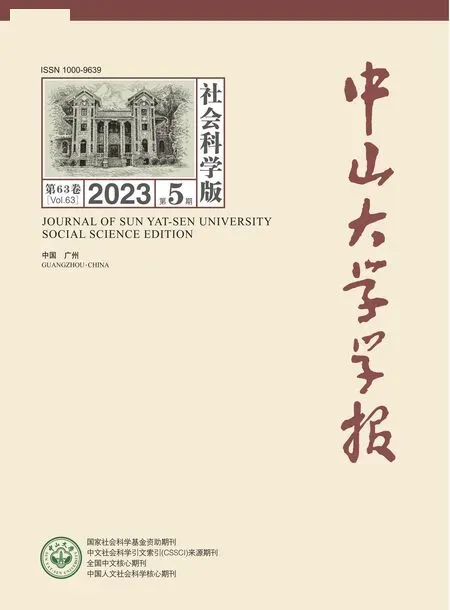历史有无逻辑*
——基于《逻辑学》的黑格尔历史哲学再审视
庄振华
历史哲学在启蒙时代勃兴,二战后逐渐走向学院技术化。在此过程中出现的德国古典哲学家(尤其是黑格尔与谢林)的历史哲学未可简单等同于人类中心主义类型的启蒙哲学,而是一种使历史①严格来说,作为历史事实的历史、作为叙事的历史、作为学科的历史学和作为对历史的哲学研究的历史哲学是四个不同的概念,但现代科学与文化的惯性使得这四个不同的层面都凭借设定性自立。笔者之所以未将四个层面的区分贯彻全文,一方面固然是由于篇幅的限制,另一方面更是出于主题性地考察这种设定性与贯通这四个层面的需要。本体化并上通宇宙秩序的尝试。近年来,国内学者引介沃格林(E.Voegelin)这位承接德国古典哲学余绪的德裔美国学者关于“秩序与历史”的宏大思考,并尝试在中国传统语境下开展此类研究。这类研究同样绕不开长久困扰西方人的一些迫切的问题:历史有无逻辑?历史中的人何以自处?
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历史断裂感使西方人对于过往种种历史叙事(无论好古主义的、进步论的还是末世论的)心怀戒惧,这使得黑格尔历史哲学往往被不加区别地归入启蒙时代常见的抽象“历史进步”一类信念,它的逝去也不过被视作是一座辉煌却又空虚的大厦轰然倒塌罢了。但如今回望马克思、尼采、福柯等在历史哲学上有大作为的思想家,我们会发现,无论他们主观上对黑格尔的态度如何,他们的思想功绩往往与黑格尔的一笔深刻遗产的发扬光大分不开,这笔遗产就是对包括历史学在内的现代科学的设定性(Gesetztsein)的揭示。尤其是自尼采以来,人们热衷于拿生命意志、潜意识、意识原初活动、后结构、赤裸生命等回击历史的设定性,愈益陷入虚无而不自知,根本原因在于以这些原初状态填补传统主体留下的空缺,而最终难脱主体中心主义窠臼①当然,他们的“主体”是以这些原初状态对传统理性主体进行“迭代”之后形成的“类”主体。。
而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则在揭示设定性的基础之上,走上另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即以绝对精神“超越”历史之路②所谓的“超越”,只是那些死守实证主义的狭窄历史观的人的观感。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在根本上其实是内在于历史的,只不过那些不具备高度思辨眼光的人对这一点无从知晓罢了。。就当前历史阶段而言,黑格尔的思路固然过于高远而未必可行,但重新审视黑格尔历史哲学,考察历史中设定性与可完善性的吊诡纠缠对于人类教化的影响,恐怕是一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迫的任务——如今我们或许到了重提“世界历史”问题,重新“究天人之际”的时候。下文先以尼采思想这一关键枢纽为例,考察黑格尔之后历史哲学的命运;然后讨论黑格尔核心著作中围绕《逻辑学》形成的文本群对于世界历史相关概念的探讨;再重新审视《世界历史哲学讲演录》(以下简称《历史哲学》)的一些关键思想;最后探讨黑格尔历史哲学对于未来历史观的启示。
一、历史哲学的衰退抑或重生?
西方人对待历史的态度转变,即从近代对种种历史叙事(如浪漫崇古、超越性末世论或内在性进步论)的推崇,到现当代普遍对历史叙事发生怀疑,最多将其当作服务于生命的某种“必要虚构”,其最典型的理论表述莫过于尼采的《历史对于生命的利弊》(中译本名为《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一书。该书在当时固然只是对人们过于沉重的“历史感”的反思,以及对“历史服务于生命”的呼吁,但客观上却成为后世生活中最强劲的历史虚无化潮流的辩护与奠基之作。然而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
尼采随顺当时知识界的一般理解,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相当不以为然。比如他对黑格尔“历史终结论”的理解就属于流俗的一类误解:“对于黑格尔而言,在他自己在柏林生活的那段时间之中,世界进程也进入了最高和最终的阶段。”③[德]尼采著,陈涛等译:《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7页。该书原名为《历史对于生命的利与弊》,本文中出自该书的引文大体采自该译本,在个别术语上依照德文原文有所修订。Siehe F.Nietzsche,Vom Nutzen und Nachtheil der Historie für das Leben,in ders.,Kritische Studienausgabe.Band 1,hrsg.v.G.Colli und M.Montinari,München: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67-1977,S.308. 关于对黑格尔历史终结论的几类误解与正确理解方式,参见庄振华:《黑格尔的历史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90—205、276—288页。这样兴之所至偶尔为之的揶揄,令人想到的是两人思想水火不容——尼采的主观想法,很可能就是如此。但详审尼采用以颠覆欧洲人历史感的论据,我们又会发现尼采思想与黑格尔《逻辑学》在客观上的隐秘关联。在尼采看来,历史感的误区在于将原本只是由一时的思想或文化设定而成的历史叙事认作永恒真理,从而有反过来戕害生命的危险。说白了,历史感的误区在于遗忘了历史的设定性。而对于现代科学与现代文化的封闭性设定(即下文所说的“二元设定”)揭露最彻底者莫过于《逻辑学》的“本质论”。尼采没有意识到,在颠覆这种设定性时,他与马克思其实是黑格尔思想最深刻的两位传人。他更没有意识到,黑格尔历史哲学在逻辑学上已经以本质论为前提了,即在逻辑学上处在本质论向概念论过渡这一枢纽性位置上,因而在黑格尔那里,历史既然是“世界历史”,便不可以低于此层面的实证主义、科学规律等方式观之,黑格尔自然不会在他误会的那种实证的意义上提出“历史终结论”。换言之,尼采对历史感的反思确实显示出他对《逻辑学》本质论的继承,但在本质论“之后”,二人采取的出路截然不同:黑格尔坚信逻各斯(Logos)本身会将我们引向具体普遍性这一更具思辨性的境界,而尼采则利用逻各斯与历史为生命服务,即返回到生命意志这一源发点。
黑格尔的路径留待后文详论,这里我们有必要详细看看尼采对历史感的剖析。尼采观察到,现代的教育主要是历史教育,相比于希腊人很强的“非历史感”而言,现代教育以历史感见长①[德]尼采著,陈涛等译:《历史的用途与滥用》,第27,21,57,34,48,92 页。很明显,在这里尼采已经奠定了中后期关于知识是“必要的虚构”的思想。。但就当前生活而言,所谓的历史感,看似巨细靡遗地研究并敬重历史,实际上是以过去的名义来巩固现在的生活:“那种最矛盾不过的感受,即一种树干居于树根之上的稳妥感,一种因知道自身不完全是随意的和偶然的,而是某一段过去的继承人并由过去开花结果,还由此在其生存方面得到谅解乃至辩护,而产生的幸福感,不仅为现在辩护,而且为现在戴上桂冠——这就是人们今天愿称为真正的历史感的东西。”②[德]尼采著,陈涛等译:《历史的用途与滥用》,第27,21,57,34,48,92 页。很明显,在这里尼采已经奠定了中后期关于知识是“必要的虚构”的思想。就过去的历史而言,历史感实际上是对历史的敉平和对历史惊奇感的消除:“青年人被踢着走过整个历史,男孩们对战争、外交和贸易政策都还一无所知,人们却认为他们该开始学习政治史了。我们这些现代人匆匆跑过艺术画廊,匆匆去听音乐会,也如同这些青年人匆匆跑过历史一样。人们颇能感觉到一件事与另一件事听起来不同,效果也不同:逐渐丧失奇怪和惊讶的感情并最终对任何事物都感到高兴,这就被称为历史感和历史教养。”③[德]尼采著,陈涛等译:《历史的用途与滥用》,第27,21,57,34,48,92 页。很明显,在这里尼采已经奠定了中后期关于知识是“必要的虚构”的思想。如果说历史本应使人对历史中的崇高事迹保持敬重,以便提升当下生命的高度,那么当时泛滥的这种历史感恰恰发展到了反方向:一方面它敉平过去历史中的可惊奇之事,使人在历史中只见到一连串平淡无奇的“差别”与“效果”;另一方面它凭着这样被整理过的历史,使人因依靠着过去而对当前的生活感到由衷的满足和幸福。换言之,历史感使过去与现在都被扭曲了:过去的历史被描摹为平淡无奇的河流,现在又被埋没于这样的河流。尼采甚至总结了过量的历史会带来的五个危害:历史的敉平化、外在化削弱了现代人的个性;现时代自我膨胀,认为自身含有历史上最多的美德和公正;民族与个体的生命本能受挫,成熟过程受阻;我们将自身当作某个古老时代的幸存者与追随者,这种信仰对每个时代都有害无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某个时代进入自身反讽与自我封闭的自我主义、犬儒主义状态(类似于今天所谓的“内卷”),那是更加危险的④[德]尼采著,陈涛等译:《历史的用途与滥用》,第27,21,57,34,48,92 页。很明显,在这里尼采已经奠定了中后期关于知识是“必要的虚构”的思想。。
初闻尼采此言,我们可能认为尼采故作惊人之论,未免太过夸张。但尼采作为历史学家布克哈特(J.Burckhardt)、欧维贝克(F.Overbeck)的学问至交,加之他本身在希腊古典语文学方面也有卓越成就,足可算作历史学家的“圈内人”,他就历史学说出的话绝非一般泛泛之论,未可等闲视之。他深知历史学家口中的“历史规律”归根结底其实就是常识:“在其他科学中,普遍性是最重要的,因为其中包含了规律(Gesetze)。但如果历史学家的这类命题(Sätze)要充当规律,历史学家的辛劳就白费了。因为在去除我们说过的那些含糊不清和难以理解的零碎之后,真正剩下的不过是最普通的常识。”⑤[德]尼采著,陈涛等译:《历史的用途与滥用》,第27,21,57,34,48,92 页。很明显,在这里尼采已经奠定了中后期关于知识是“必要的虚构”的思想。
那么这一困局的出路何在?尼采认为,真正的知识以生命为前提,也应该服务于生命,它可以将非历史与超历史这两副解药作为“保健”措施,来对治“历史病”(die historische Krankheit),但不可反过来支配生命⑥[德]尼采著,陈涛等译:《历史的用途与滥用》,第27,21,57,34,48,92 页。很明显,在这里尼采已经奠定了中后期关于知识是“必要的虚构”的思想。。由此可见,尼采依然在更深层面落入了他本欲摆脱的窠臼。尼采虽然见凡人所未见,不似寻常头脑那样对市面上形形色色的历史叙事顶礼膜拜,而是洞察历史叙事的主观性、设定性,却依然在流俗的意义上理解设定,即并不将其当作文化的整体形式,而是当作某个主体的行动。因此他依然在这一设定活动⑦这种设定活动其实不是我们所能设想(尤其是人格化地设想)的任何“设定者”的活动,而是一种文化的整体活动。背后再“设定”一个“设定者”(生命),作为其主体。可见他在这个较深层面重又落入了寻常头脑在较浅的历史叙事层面落入的那个陷阱,即“主体如何获利”的思路。
就黑格尔去世后,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尼采所批评的“历史感”或他本人指出的某种原初状态(生命意志、潜意识、意识原初活动、后结构、赤裸生命等)而言,黑格尔式的历史哲学是一去不复返了;但就尼采之后,历史的设定性昭然若揭,西方撰史学、谱系学普遍与过往的历史叙事拉开距离,对历史采取怀疑主义乃至犬儒主义的反思态度而言,黑格尔《逻辑学》的遗产以及基于《逻辑学》之上的历史哲学的遗产(尤其是关于历史与世界本身的某种必然性发生深度关联的思想,详见下文),似乎又以某种吊诡的方式重生了——尽管并非以黑格尔乐见的方式。如今我们与黑格尔、尼采以及历史主义、虚无主义之间都有了相当的历史间距,经过这样的历史间距,黑格尔身后历史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思想“潜能”基本展现无遗,似乎并无太多实质性拓展空间了。因此现在重新审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那些已开发或尚未开发的思想资源及其未来意义,可谓恰逢其时。
二、从《逻辑学》等核心著作看世界历史哲学所为何事
鉴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有着深厚的逻辑学根基,我们要明白世界历史哲学所为何事,就需要先澄清何谓“世界历史”,再回到世界历史哲学扎根其中的《逻辑学》等文本群中去,探讨世界历史的逻辑科学地位与精神哲学任务。
不同于其他思想家从哲学史(谢林、尼采)、政治哲学(康德、费希特)、古典语文学(尼采)等角度探讨历史的做法,黑格尔从理性的角度与宇宙秩序的高度入手把握历史的方式,本身就是空前绝后的,正因此这种方式也显得极为突兀乃至怪异。
首先,对于历史,黑格尔首先关注的是它有无逻辑或有无理性。“认为历史,尤其主要的是世界历史,是以一个自在自为的最后目的为根据,而这个目的实际上是而且将在世界历史里实现出来,即认为历史以天命的计划为根据,也就是说认为一般说来历史中有理性,这种看法是必须从哲学上、并因而作为自在自为必然的来予以澄清的。”①[德]黑格尔著,杨祖陶译:《精神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6页。这个想法也贯彻到《历史哲学》本身的写作方式上:黑格尔各轮世界历史哲学讲座和他去世后各版本《历史哲学》几乎都将四分之一左右的篇幅留给了导论(亦称“世界历史的概念”,或“原则部分”)②如中文学界最新引进的1822—1823 年历史哲学讲演录中,“世界史的概念”就占用了100 多页的篇幅(全书440页)。见[德]黑格尔著,刘立群等译:《世界史哲学讲演录(1822—1823)》,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1—112页。,而这个导论的主要任务就是接引读者看到历史中的理性,或者说引导读者从理性的角度看待历史③在黑格尔研究史与黑格尔著作编辑史上都举足轻重的拉松(G.Lasson)、霍夫迈斯特(J.Hoffmeister)先后将这份导论单独编辑成书,并名为《历史中的理性》。Siehe G.W.F.Hegel,Die Vernunft in der Geschichte.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hrsg.v.G.Lasson,Leipzig:Verlag von Felix Meiner,1917;G.W.F.Hegel,Die Vernunft in der Geschichte,hrsg.v.J.Hoffmeister,Hamburg:Verlag von Felix Meiner,1955.。
其次,这是一种什么理性?或者说历史处在逻辑科学的何种层面上?黑格尔考察的是世界历史(Weltgeschichte),而非断烂朝报、历史规律或宗教哲学意义上的历史(Geschichte)。这意味着黑格尔在历史领域关注的是世界的“绝对必然性”何以能够自我实现(对应于逻辑科学而言是本质论层面向概念论层面的转进关口),而非在更低层面上关注实证意义上的历史事件(对应于《逻辑学》的存在论层面),或历史中是否有规律(对应于《逻辑学》本质论层面的“现象世界”二级层面),抑或在更高层面上关注宗教哲学意义上的绝对者自我实现方式(对应于《逻辑学》概念论层面的“目的论”三级层面)。简言之,这是在精神领域中,从一任人力追求绝对者的局面转向世界的绝对性自我实现的局面——借用我们古人的话来说,这是严格意义上的“究天人之际”。
那么这样的历史哲学的根基何在?若是仅仅局限在《历史哲学》范围内来看,这个问题是无解的。原因在于,《历史哲学》主要致力于在历史撰写的方法、人的自由、国家的理念、世界历史的进程等具体问题上运用和展开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概念,而这概念本身在逻辑科学和精神哲学两方面的奠基工作却分别是在《逻辑学》与《精神哲学》《法哲学原理》中完成的(后两者甚至将“世界历史”作为其固有的一个层面加以论述)。而黑格尔核心著作①仅就专著而言,笔者将黑格尔亲自编定出版的著作称为他的“核心著作”。中,《精神哲学》只是《逻辑学》在精神领域的应用(或曰“应用逻辑学”②[德]黑格尔著,先刚译:《哲学科学百科全书I:逻辑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63—66,248—251,248—251页。),《法哲学原理》又只是《精神哲学》的“客观精神”部分的详尽展开,所以我们在核心著作中为《历史哲学》寻根溯源的工作最终必须落脚于《逻辑学》上,具体而言是落脚于本质论的“现实性”二级层面上(尤其是“绝对必然性”与“交互作用”范畴上)。
这里需要对“现实性”二级层面的逻辑学地位略作交待。“现实性”层面的开篇便以超出前一个二级层面(“现象”)的种种有限规定的“绝对者”自我标榜(以斯宾诺莎实体学说为典型代表)。在“现象”层面,有限规定之所以有限,并不是因为它们受到外来力量的限制,而是因为这些规定置身于“现象—本质”这一结构中,具有一种自认为抓住了本质,并由该本质为自身“背书”的幻觉,而满足于当下的状态,故步自封。但其实有限规定永远只能与其他有限规定发生关联,因而永远无法超出有限性境地。现象以背后被设定的某种本质(它可以体现为极尽“严格”与“科学”之能事的种种规律、公式)为支撑,而本质虽然看似间接(看不见、摸不着),却有眼下这貌似“直接”的现象③其实现象的直接性也是被设定下来的。作为它的表现形式,两者在相互支撑之下同时获得“科学性”与“客观性”。对于这种显得经过“证成”的二元结构,思维极容易满足于它“科学”与“客观”的假象,却遗忘其设定性。而黑格尔在“现象”层面(尤其是“本质性对比关系”三级层面)却挑明了这种设定性。
那么这种设定性的出路何在?“现实性”层面开篇的“绝对者”构想只能算是思维对于突破二元设定的一种抽象设想。它还没有经受从现实性中看出绝对必然性这一难关的考验。而“绝对者”之后的下一个三级层面(同样名为“现实性”)便是在通过这一关口。简单来说,黑格尔为二元设定提供的出路,不是以更深层面上的本质为先前的“现象—本质”二元结构“兜底”,从而变相地延续二元设定④斯宾诺莎的实体概念就有这种嫌疑,至少就他对实体概念的构想方式(即致力于将一切都归结于实体这一根基上)而言是如此。,而是在接纳二元设定在追寻本质、为事物奠定自立之基础方面的良好愿望的同时,培育起对于世界永远给予事物本质这一点(“绝对必然性”)的敬重。比如全世界的水总是能在特定的化合键之下保持在两份氢元素与一份氧元素的平衡态,无一例外,这不是因为人有本事“抓住”水的表面现象背后的某种神秘的主使力量(那是规律思维的“妄想”),更不是因为人能迫使那力量服从自身的安排,而是因为世界“愿意”如此这般向人呈现,是因为世界总是如此这般“配合”思维的二元设定——这还只是水这一个现象而已,一切现象皆有类似的绝对必然性作为支撑。由此可见,世界的可敬重之处在我们身边万事万物、一切现象中都有所体现。
黑格尔在《小逻辑》第147 节讨论如何从最初看似纯属偶然的现实性中看出相对的必然性,最终看出绝对的必然性时,就提到了历史哲学并非宿命论,而是神正论⑤[德]黑格尔著,先刚译:《哲学科学百科全书I:逻辑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63—66,248—251,248—251页。。所谓宿命论,究其原因依然在于,我们对于历史为什么这样发生感到很盲目。但正如黑格尔前文中对偶然性的态度表明的,他心目中的神正论根本不是消除偶然性,给万物一个“上帝为何要使它这般”的理由,而是在偶然性中体察到绝对必然性,在尘世万千现象中体察到宇宙秩序,仅此而已。
在同一个文本中,黑格尔接下来还探讨了历史哲学的一个核心主题,即命运观方面的“古今之变”,并挑明了他自己不同于古今两种态度的第三种态度⑥[德]黑格尔著,先刚译:《哲学科学百科全书I:逻辑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63—66,248—251,248—251页。。古人认为应在(was sein soll)即现在(was ist)。应在乃合乎宇宙秩序的状态,而不是近代乌托邦意义上的未来社会状态,所以它当然就在当下实现着,当然就是现在了。那种认为现在应以被设定在过去或将来的某种状态为尺度来衡量的看法,是典型的历史主义,在古代或许零星得见,但并未形成大规模的思想潮流,更没有像现代那样凝固为整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古代当然不会产生后世那种因历史主义的时代间对照而带来的不自由、痛苦、悲伤等感觉。而今人则使主观性无限膨胀,即强使世界符合人的主观要求,于是失去了包括中世纪人在内的古人对待命运的宁静而崇高的态度。但我们不要因此就认为黑格尔厚古薄今。黑格尔的主张实际上“亦今亦古”又“非今非古”,他要达到比古今两种态度更高明的第三种态度。如果说古代的态度太过实体化,主体性不够,而现代的态度主体性太强,实体性不够,那么黑格尔的态度并不是像和稀泥一样简单糅合主体性与实体性,而是使主体性寓于事情本身之中,即人的主观性也因为顺服绝对的主观性(绝对者、绝对必然性)而同样得到肯定。这当然不是说人要追求成为绝对者,而是顺应宇宙秩序去锤炼、提升人的主观性。
其实黑格尔的核心思想还是克己,而不是狂妄地要跟绝对者合一。这种克己主要是针对现代科学、现代规律思维而言的,而不是针对古代而言的。黑格尔所理解的“每一个人都决定着他自己的幸运”①[德]黑格尔著,先刚译:《哲学科学百科全书I:逻辑学》,第251页。,并不是通常想象的压服他人以及自己生活中种种不符合主观意欲的东西,快意恩仇,胜者为王,而是使自身命运不受偶然因素的宰制。人虽然永远无法彻底摆脱偶然性,但也不在偶然性之海中随波逐流,而要在顺应宇宙秩序的同时达成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逻辑学》“交互作用”范畴对于理解世界历史也极富教益。就整部《逻辑学》而言,这个范畴是本质论向概念论演进的关键枢纽,它意味着一任人力设想和把握宇宙秩序之“本质”的做法最多只能达到“人力设想方式需让位于宇宙秩序自行实现”这一认识,而不能真正进入宇宙秩序的自行实现,后者需要本质论思维服从于宇宙秩序,甘居辅助者地位。交互作用相对于实体性对比关系与因果性对比关系而言的一大进展,便是认识到任何实体都不能将自身当作固定不变的唯一中心,也认识到因果性虽然打破这种固化习惯,但仍然未脱本质论思维“先入为主”的习惯,残留了“主从”“主次”或“主客”的“差序格局”,最终认识到实体与实体实际上互为主动者与被动者(或曰主动者与被动者的同一性)。换言之,交互作用实际上是因果性认识到了作用不仅仅是作用,而且是原因的自身关联:“交互作用仅仅是因果性本身;原因不仅具有一个作用,而且它在作用中是作为原因而与自身相关联。”②[德]黑格尔著,先刚译:《逻辑学II》,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92,192页。这实际上意味着世界在“绝对必然性”的意义上需要被视作其大无外、自由自主的绝对者(或曰“概念本身”)的自我呈现,而诸实体就此而言也是彼此自由的:“必然性的区别和那些在因果性里面相互关联的规定(即实体)是一些彼此而言自由的现实性。”③[德]黑格尔著,先刚译:《逻辑学II》,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92,192页。有了这样的眼光,概念论层面“普遍性—特殊性—个别性”三元架构的具体普遍性便呼之欲出了,只不过目前由于思维仍然处在本质论层面的末端,始终保有人力寻求“本质”这一做法的残余,只能遥望那种具体普遍性,还不能真正进入其中罢了——在精神层面上而言,世界历史面临的正是这样的处境。
由此不难发现《逻辑学》带给黑格尔式“世界历史哲学”的几点教益,或者说黑格尔《历史哲学》不言自明地预设的几个要点是:第一,这种哲学关注的并非存在论层面的“发生了什么事”。换言之,它绝非单纯的断烂朝报或实证性、事实性研究,尽管这种研究构成它的基本材料。换用我们常见的术语来说,历史哲学研究的不单纯是历史事实,而是历史意义的构造方式。第二,世界历史哲学关注的也不是历史规律,后者只是本质论“现象”二级层面的事情。所谓规律,只是用表面的“必然性”(事物似乎总是以规则性方式向我们呈现)掩盖了更深层次的偶然性。这就是说,规律不过是经过科学总结的规则性现象,并未真正揭示现象何以如此发生的根据,只是将现象“是这般”这一偶然事实总结出来罢了④参见庄振华:《黑格尔论规律》,《哲学动态》2017年第1期。。世界历史哲学远比这种规律思维深刻。它不是要通过抓住偶然性“背后”的某种“本质”,来消除这种偶然性,反而是在历史偶然性的大海洋中对于历史“必然”要如此这般(合规律地)偶然存在这一点的敬重。换言之,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选择以人制天,还是敬天法地。第三,世界历史哲学也并非在明了规律思维的有限性以及规律本身的偶然性之后,直接引进一个“绝对者”,来为世界的偶然性“背书”。这种做法依然是以人为制造的假“天”来为人服务,而并不真知天为何物。(与此类似的控制论构想还有尼采式的生命意志,后者被尼采当作从背后生成与控制历史设定性的终极主体。)第四,必须在作为绝对性对比关系的交互作用的意义上看待世界何以需要“概念本身”或具体普遍性,才能既无惧偶然性,又对精神世界含有绝对必然性这一点保持信念。第五,世界历史哲学当然也并非宗教哲学,后者是概念论的“目的论”三级层面才会涉及的问题。
而《精神哲学》与《法哲学原理》中的“世界历史”层面只不过是《逻辑学》的“交互作用”范畴在精神领域的“应用”或具体体现。《精神哲学》中,黑格尔既反对先天的历史写法(即预设一些任意的观念并在历史中求证),也反对不偏不倚的所谓纯客观,尽管他认为历史中的确有客观的目的①[德]黑格尔著,杨祖陶译:《精神哲学》,第355—356、356—357,360,360,361页。。原因在于,按通常要求,历史真理似乎只涉及正确性,然而正确性判断只含质的判断和量的判断,不含必然性判断和概念判断②[德]黑格尔著,杨祖陶译:《精神哲学》,第359页。关于上述四种判断,详见《逻辑学》概念论中的判断学说。质的判断、量的判断又分别被称作“定在判断”和“反映判断”。。而历史哲学所追寻的精神并不漂浮在历史上,而是在历史中以主体的身份活动,是唯一的推动者;精神达到其自身并实现其真理,是至上的、绝对的法;自由乃是精神的绝对规定;具体而言,民族精神是伦理中思维着的精神,而世界历史中思维着的精神则走向绝对精神③[德]黑格尔著,杨祖陶译:《精神哲学》,第359、361、360页,并参见[德]黑格尔著,先刚译:《哲学科学百科全书I:逻辑学》,第51节“说明”,第109—110页。。相形之下,个人只是工具,个人意义上的主体性相比于精神意义上的主体性而言只是活动的空洞形式,个人获得的报酬是历史声誉④[德]黑格尔著,杨祖陶译:《精神哲学》,第355—356、356—357,360,360,361页。。如果说精神是向上帝的攀升,那么人的自我意识在这个过程中便需要克己⑤[德]黑格尔著,杨祖陶译:《精神哲学》,第355—356、356—357,360,360,361页。。黑格尔眼中的真宗教,只能产生于人在尘世的偶然性大海洋中不断克己又不断坚守世界的合秩序性的伦理行动之中,不可能产生于别处⑥[德]黑格尔著,杨祖陶译:《精神哲学》,第355—356、356—357,360,360,361页。。
再看《法哲学原理》。这里的“世界历史”层面比《精神哲学》中更为详尽,出现了四个王国的具体分划,在诸多主题的论述上也更接近《历史哲学》的风格了。这里黑格尔开始提出世界历史是世界法庭,认为在这个法庭上,特殊东西作为观念东西而存在于其绝对普遍性中⑦[德]黑格尔著,范扬等译:《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351,351,358—359,360页。。黑格尔反对像希腊人那样将历史看成盲目命运的必然性,而是主张将其看作精神的自我意识与自由的必然发展⑧[德]黑格尔著,范扬等译:《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351,351,358—359,360页。——正如前述“第三种态度”所示。在四个王国的论述上,黑格尔认为东方王国尚未达到自觉的实体性客观性,即尚未达到有机的合法律性;希腊王国中个人的个体性原则开始出现,但仅仅保持在观念的统一中,这只能带来少数人的自由,而且经济也不是自由人的事情;罗马王国分裂为私人自我意识和抽象普遍性这两端,类似于贵族与平民的对立;日耳曼民族的使命则在于把握住神的本性与人的本性统一的原则、客观真理与自由的调和——即实现他自己非今非古、亦今亦古的“第三种态度”⑨[德]黑格尔著,范扬等译:《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351,351,358—359,360页。。哲学科学带来的最高认识在于,真理王国不在彼岸,真理在国家中和在自然界、观念世界中原本是同一个东西⑩[德]黑格尔著,范扬等译:《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351,351,358—359,360页。。
三、《历史哲学》再审视
熟悉《历史哲学》的读者会发现,如此这般由《逻辑学》纵观《精神哲学》《法哲学原理》相关章节来看,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虽然算不上“纤毫毕现”,却也大体齐备。以往人们单纯局限在《历史哲学》内部阅读时经常会误读的一些关键思想,由此也不难索解。
第一,就“历史有无逻辑”这个总题而言,这里有必要先澄清的“逻辑”的含义。若是将它理解成与人的主观努力毫无关涉的“铁律”,那么历史中没有这样的“逻辑”,因为历史本就是人事之代谢,离开人的努力谈论历史是没有意义的。若是将“逻辑”理解成《逻辑学》意义上的存在本身的逻辑必然性,尤其是“绝对必然性”与“交互作用”意义上的逻各斯,那么历史是有逻辑的,而且在黑格尔看来,能否洞察这种至为可贵的逻辑对于西方文明能否“存亡继绝”至关重要。然而后一种逻辑的实现需要以反思现代性弊病和回向宇宙秩序为前提。
第二,黑格尔的历史进步论与古今自由论常被混同于启蒙哲学意义上的类似论述,这是不了解它们达到的高度所致。在黑格尔这里,衡量历史“进步”与古今自由度的标准既不是尘世中人所能达到的任何物质与精神成就,也不是人主观构想的某种抽象的进步状态与自由状态,而是世界的绝对必然性或宇宙秩序本身(黑格尔也称这种必然性与理念为“概念本身”“绝对者”“上帝”等)。各历史阶段与各种文化实现这一必然性和秩序的程度决定了它们的进步程度与自由度。这里无需赘述的是,黑格尔眼中的进步并非人类对世界的把控能力,他所说的自由也并非人类任意妄为的能力,真正的进步与自由实质上是前述必然性与理念在自我实现时达到的进步与自由。
第三,历史终结论堪称黑格尔被后人误解的“重灾区”。笔者曾在拙著《黑格尔的历史观》中撇清了“历史终结于某个历史时段(包括历史的本原、资本主义状态与末世状态等)”,“历史终结于当时的普鲁士国家”,“历史终结于作为个人思想的黑格尔哲学”等几种典型的误解,指出西方①德文中“西方”一词(Abendland)的字面含义(“夜晚之地”)在彼时常被用来标示这种终结性。参见[德]黑格尔著,刘立群等译:《世界史哲学讲演录(1822—1823)》,第396页。Siehe G.W.F.Hegel,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 Berlin 1822/1823.Nachschriften von K.Gustav J.v.Griesheim,hrsg.von K.H.Ilting,K.Brehmer u.H.N.Seelmann,Hamburg:Felix Meiner Verlag GmbH,1996,S.460.文化固有的“终结性”使得每一个典型的历史时段与思想文化都具有“终结”历史的资格②庄振华:《黑格尔的历史观》,第190—205、276—288页。。但那里的讨论尚有一间未达:历史何以终结?西方文化又何以具有“终结性”特质?黑格尔这里的终结(das Ende),既是终点,又是顶点,而使得它兼具这两种含义的背后义理在于:对事物理念、“是其所是”或形式的领会(即对该事物所处的逻辑学层面的把握)才使得思维达到对该事物最广大也最深刻的观照,从此以后人们对该事物的任何理解,甚至对它的任何扭曲与改变,都超不出这种观照之外;唯一超越这种观照的办法,只有突破该事物所在的逻辑学层面,进入思辨意义上的更高层面。对于黑格尔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的每一个关键阶段而言,前一方面的观照就是“历史终结”,后一方面的超越便是“历史进步”。
第四,“理性狡计”说经常被类比于经济学上的“看不见的手”,然而它的含义恐怕远比后者深刻:后者涉及经济的规律性与经济表面上的杂多性(尤其是每个经济主体的自主性)的共存,主要强调经济后果对个别经济主体而言的不可预料性;理性狡计则是在世界的绝对必然性的意义上,突出偶然事件背后的必然性。
第五,世界历史民族与世界历史个人常被简单等同于“某某文化中心主义”与“英雄史观”,对于未被纳入其中的大量民族、文化与个人而言显得极不公平,看似哲学家的古怪遐想。然而黑格尔的本意并不完全在于表彰他笔下的这些民族与个人,更无意于以“上帝之眼”的姿态裁断一个个民族、文化与众多人民的高低、优劣,他的用意主要是以这些颇具代表性的民族与个人为例,勾勒出过去的一个个关键历史时段上,世界历史曾经达到的最大高度(尤其是最高逻辑学层面),以为后世之镜鉴。正如黑格尔在追寻“绝对必然性”时从不主张彻底抹杀偶然性一样,对于未被纳入他笔下的大量民族、文化与个人,以及曾被纳入他笔下的那些民族的“非高光时刻”,他并不认为它(他)们没有存在的价值,只是觉得它(他)们对于体现当时最高的逻辑学层面而言不具有代表性罢了。同理,对于未来的可能发展,他也从不轻易评判,只是偶尔表达一点期待或担忧(比如对于美洲这片“未来之地”的态度)①参见[德]黑格尔著,刘立群等译:《世界史哲学讲演录(1822—1823)》,第89—90页。G.W.F.Hegel,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in ders.,Werke 12(TWA 12),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70,S.114.,因为他并不自诩具有“上帝之眼”。
四、对于未来历史观的启示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对于以实证史观或分析史观为正宗的人而言显得过于“超越”,似乎难以实行。但如果撇开抽象臧否的做法,以长远的眼光冷静观察黑格尔死后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依然可以从中获得不同于尼采进路的若干启示:
首先,就历史叙事本身而言,要同步考量到历史叙事及其限度。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日,历史叙事便一日不可无。历史叙事的表现,小到家族的荣衰记忆,大到国家与世界的兴亡史,对于凝聚人心、警醒来者都是必不可少的。而所谓同步考量到历史叙事的限度,固然不必像尼采那样采取一种为生命意志服务的“必要的虚构”态度,这种考量也应当成为历史教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
这有利于我们放下过去与现在两方面的过重负担:对于过去,正如自然科学研究中不必认定某种规律绝对为真②因为我们只是叙事、规律的观察与总结者,而历史与自然中何以有这般叙事与规律,则是不具备“上帝之眼”的我们无法洞穿的。,我们也不必认定某种历史叙事绝对为真,不必为无法将历史上所有事件纳入统一的叙事而烦恼,反而可以将其视作新叙事出现的可能契机;对于现在,我们也不必以既有的历史叙事或当下的利益需求为圭臬,执意以某种解释模式消除生活中的一切偶然、无意义、断裂,反而应当放下过多的算计、焦虑,在貌似并无密不透风的历史叙事加以“保障”的情况下承担偶然性,因为偶然性(乃至在当下的局狭眼光看来的“不合理性”)本就是生命中的一种必经的考验。
其次,就更深刻的逻辑而言,我们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观照比一般历史叙事更深刻的“必然性”,从而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建立一种更深刻也更冷静的动态均衡。黑格尔式的绝对必然性、绝对理念、具体普遍性,对于当下深度依赖人工智能、社交媒体、电商平台的人们而言,似乎显得不切实际。但我们至少可以在保持“世界深处有一种根本秩序”和“普遍者就在具体事物中”这类信念的前提下,不因过去而堙灭现在,也不因现在而随意描抹过去,而是使过去与现在都向更深与更高层次保持开放。
人类若是将全副精力都投入到历史叙事与历史偶然性的搏斗之中,便会遗忘“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舍勒[M.Scheler]书名),反而将生命埋没到整个历史上反复重演的“循环场”之中而不自知。一种更为健康的历史观,是以“纪念碑式”(尼采语)的态度将过往最优秀的人物、事迹树立为典范,但同时又不“死”于由此带来的历史感之下,而是以这种典范激励我们比以往(包括比这些典范)更好地成全世界的“绝对必然性”,同时努力避免历史上出现过的一些误区。
再次,综合黑格尔之后的整个历史来看,黑格尔对现代科学的设定性的洞察留给我们的启示是,尼采所揭示的“内卷”性历史感固然对生命有害无益,但一种“诊疗”性历史感却是要保留的。如果说内卷性历史感指的是生命被迫卷入一种貌似对其有利、实则令其身不由己的历史叙事之中,即被迫卷入现在与过去之间相互强化、相互“锁死”的局面,那么诊疗性历史感则是在生命陷入某种强化局面之后,为修正此一局面而正视它,并基于它而采取行动,而不寄望于某种抽象的浪漫图景并逃避该局面。比如要摆脱世界大战、灾荒或大疫对人群造成的身心创伤,就不能简单采取抽象励志的方法,而要设身处地,深入到创伤人群的内心世界中去,以其处境为制定对策的基本前提。
复次,在“人生如寄旅”这个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历史可能只是适应于尘世所见事务的一种偶然的意义编织物,至于人是否有比历史更广阔也更深沉的、宇宙尺度上的使命,则尚在未定之天。未来的历史观是否要向这种可能的使命保持开放,为其留下些许余地?这始终是一个值得考察的问题。此事对于现代人而言可能显得不可思议,因为被我们当作幸福源泉的事业、价值、名誉很可能有着不为人知的限度,将人生的全部寄托于它们的做法很可能是一种执念;而反过来被我们判为“偶然”的那些因素很可能有其更大尺度下的隐秘的必然性,甚至有可能对于我们生命的某种成全而言必不可少。
结 语
在考察历史哲学的当代命运并揭示出黑格尔的历史“设定性”思想在后世的客观影响,提出重新发掘黑格尔历史哲学思想资源这一任务之后,我们将这种哲学回溯到《逻辑学》《精神哲学》《法哲学原理》的“绝对必然性”“交互作用”“世界历史”等范畴上,确定其在人力与宇宙秩序之间“究天人之际”这一根本性质,然后依此重新审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一些关键学说(历史进步论、历史终结论、理性狡计、世界历史民族与世界历史个人),最后提出这种哲学对于未来历史观的几个可能的启示。
黑格尔历史哲学既具有古典的精神追求,又毫不回避现代性的问题,这是当今与未来的历史观与历史哲学最值得珍重的一种品质。一方面,它绝不沉沦于当代种种浪漫情怀与虚无主义之中而不知所归,因此虽然极其重视历史,却很难彻底归入“历史主义”之列。另一方面,它又不主张彻底抛弃现代,遽然投向古典秩序的怀抱。黑格尔在耶拿时期与后来的法哲学发展历程已经表明,直接投入古典秩序的做法在现代是抽象而不可行的,我们必须直面市民社会、现代科学的挑战①参见庄振华:《司法、市民社会与伦理——基于学说发展史的〈法哲学原理〉“伦理”篇要义考论》,《现代哲学》2023年第2期。。黑格尔不仅面对现代性,而且找到了一条合乎逻辑地“穿透”现代性的出路,这种魄力是极为罕见的。我们可以不接受黑格尔的许多具体结论,但简单扣帽子并弃之不顾的做法恐怕损害的不是黑格尔,而是我们自身的视野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