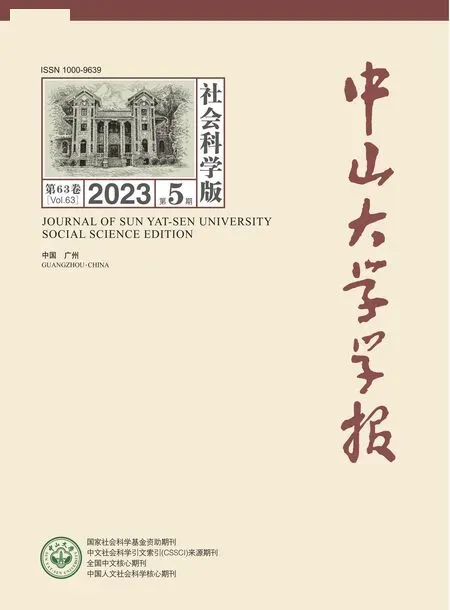编后记
本期含“名家特稿”“法国旧制度时期的日常与治理”等专题专栏,专题导语之外,刊文凡17 篇。
美国学者安乐哲(Roger T. Ames)目前就职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衍诸万端,大要落在对“人”的探讨上。作为一个自在自适的群体,人类的含义兼具明晰性和模糊性,其明晰性容或会再度模糊,而从模糊走向明晰的旅程则往往十分艰难。哲学探究的无止境,给人的思考本身确实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人是自足的存在,人也是关系的存在,前者可谓之“人”,而后者可谓之“成人”,似乎很难在这两者之中做出一种永恒不变的选择,因为这既涉及学术史上层层叠叠的纠葛,也体现在相关观念在其他观念中的受容与兼容情况。主体性总是令人动容的概念,但如何契合作为关系性存在的人的观念,就颇费思量了。这大概是一般人虽然生活在哲学之中,却难以靠近哲学的原因所在。安乐哲《重思关系构成的“成人”的主体性》一文展现了他最新的思考,值得一读。
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别,争相发言者往往是人文学者。但另外一个事实是:无论人文学者怎样强调自己的科学特色,而这种特色被忽视、被轻视仍是一种常态。这种不同科学之间的不平衡现象究竟是如何形成并成为一种较为强固的样态,实在是一件极有意味的事情。巴赫金曾经大致说,自然科学学者面对的是一种无言的客体,彼此之间是主客体的关系;而人文科学学者面对的是文本,文本背后是另一主体。前者的关系大体属于认识论,而后者的关系则属于对话论。主客体之间容有比较明显的强势与弱势的不同,而两个主体之间虽也有一定的强弱区别,但彼此更在乎的是协调与沟通,其冷热不同如此。21 世纪的中国学术对汉学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关注较为深入,但在何以对话、如何对话等方面仍存在诸多夹杂和模糊之处。学术史、学科史总有令人困惑之处,就好像哲学系致力培养哲学家,历史系造就历史学家,这都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中文系居然对是否要培养作家展开讨论,就未免令人啼笑皆非了。金惠敏守护人文科学的精神既辛苦又可贵,但洗去“常识”的尘埃,丰富并升华“常识”的精神,从来是需要兼具一双慧眼和一颗关切人类文明责任感之心。朱熹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人类有了光,才能照亮这个世界。
今夏的苏轼有点热,有的是自然热,有的是蹭热度。有的是专家说,话语自然谨慎一点;有的是媒体说,调子不觉高昂一点。恍然真有点开口不谈苏东坡、纵读诗书也枉然的感觉。苏轼果然是属于整个中国的。但苏轼研究却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事情,需要有如金圣叹“犯之而后避之”的胆识和策略。现任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衣若芬今次在本刊发表有关《东坡笠屐图》的考订与论说文章,从有关苏轼在海南谪居时戴笠穿屐的文本和图像故事以及日本、韩国等对此的接受情况,论述其在东亚文化圈的形象流变,便是别开一途。中国的苏轼如何变成东亚的苏轼,此文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尝试。海南是苏轼贬谪生涯的最后一站,也是其生命临近结尾的时刻。他曾经在海南感叹说:“吾始至海南,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这样的苏轼当然精神强固,来去自如了。只要还能行走在天地之间,便是苏轼的生命意趣已然自足自在的状态了。
诗歌之于中国,亦如星辰之于苍穹,是一种悠久而璀璨的存在。格律一方面为具有节奏与韵律的中国诗歌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因设置了基本的门槛而成为争议的对象。西方诗歌的原生体式与中国格律诗也应有着大致的审美追求,如果这一前提能确立的话,西诗中译应遵循的路径也就不言而喻了。而大凡诗歌词语、意象、结构等的言外之意,往往建立在各自深厚的文化渊源和现实土壤中,从这一意义上而言,诗歌几乎是不可翻译的,除了译者对对译的两种语言都精通到近乎“母语”的程度;否则,顾此失彼就在所难免。但是,文化的交流总是不可阻挡,翻译也就难以回避。而一旦直面诗歌翻译,则将西方诗歌的原来韵律精准地翻译出来,至少应该成为一种方向。王东风近年的努力和思考皆在于此。
在政治学领域,福柯兼具观念意义和方法论意义。他的权力观念以及权力研究的理念,都对后来的研究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他从权力的“毛细血管”切入,对权力的弥散结构和流动机制进行研究,确实打开了一个新的学术视界。在这一理论观照之下,我们回到法国旧制度时期的治理史,日常生活及其底层视野就变得十分重要,从司法君主制到行政君主制这一君主制的转变,就意味着民生和民间的意义得以凸显。本期周立红主持的“法国旧制度时期的日常与治理”专题,从流行病与15—17 世纪法国城市治理体制的转变、路易十四时代谷物管制的理念与实践、启蒙时代巴黎小人物的世界等角度展开研究,沉到了历史的底部,也沉到了历史的深处,然而从学术史而言,却又提升了历史的高度和精度。不仅如此,熊芳芳和周立红的文章还从底层回溯到权力的中枢,考察了近代早期法国的治理权从城市向王权转移的过程和趋势,是对福柯权力观的发展和补充。
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而“为仁之本”则在于孝。孔子说诗歌的作用“迩之事父”还在“远之事君”之前,可见“孝”更具有基础意义。传统的看法是“仁”具有发散性,可以指向广泛,而“孝”则更偏向血缘的内摄性。这一看法无需颠覆,但确实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从生生和万物一体的角度来说,把仁和孝截然二分,倒是局限了思维的空间。“四海之内皆兄弟”,情感的张力有时并没有生硬的边界感,所以恻隐何尝不能包容亲亲?这种同体连贯的特性更契合儒家思想的本然。赵金刚朝花夕拾,旧题新论,读来别有意味。
大凡学术研究,总以守正为第一,而创新为第二,不以守正为前提的创新,很可能如过眼云烟,稍纵即逝。故青春锐气之文,关合多方,意趣横生,自可一时玩赏;而老辈作文,则往往如老僧入定,多是一心探本,而不管身边风云,可知老境例多趋正者。今年八月初,曾与诸生同游肇庆七星岩、鼎湖山,正可谓“山水之间有清契;林亭以外无世情”,因感赋一绝,或可对应文章新境与老境之关系,录以为小记之煞尾。诗云:
平生万物作芳邻,从此湖山我主人。
往事皆从心上过,周旋自在自由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