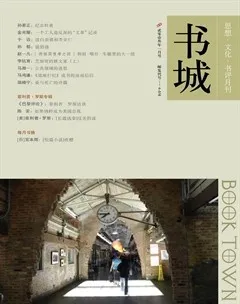凯西克的“诗人角”
史凤晓
在英国西北部湖区的诸多久负盛名的小镇中,凯西克(Keswick)的地理位置算是相对偏僻的。小镇的名字意为“卖奶酪的地方”,说明它很早以前是一个集镇,如今,这里依旧会定期举行集市,人们可以从集市上买到最正宗的凯西克奶酪。从湖区的大门肯德尔小镇开始一路向北,温德米尔、安布塞德、瑞德、格拉斯米尔彼此相隔都不太远,唯独凯西克小镇与上述小镇隔了湖区的第二高峰赫尔维林,以及瑟尔米尔湖,等等。即使是现在,驾车从格拉斯米尔去凯西克,很快便会有进入无人区的感觉。道路两边除了陡峭的山脉、树林、山顶的常年积雪、高处的云朵,以及偶尔的水雾,几乎很少看到人烟。此外,在抵达凯西克小镇之前,手机会一直处于无信号状态,这更给人一种与世隔绝之感。但实际上,一旦进入这个小镇,就会很吃惊地发现,虽然比不上温德米尔、安布塞德这些最热闹的湖区小镇,凯西克的游客似乎也没有少到哪里去。有很多登山客是奔着湖区最陡峭的斯基多峰与斯科菲峰而来,也有很多徒步者,是为了德温特湖(Derwent Water)周围兼具秀美与崇高的徒步小径而来,当然还有一部分游客,像我们一样,是为了小镇独特的文学渊源而来。
格雷塔府
格雷塔府(Greta Hall)毗邻格雷塔河与斯基多山峰,其偏僻的地理位置及其周围的幽静环境是诗人创作、研究的绝佳处所—湖畔派诗人塞缪尔·柯勒律治曾在这里断断续续住了几年,而另一位湖畔派诗人、柯勒律治的连襟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1774-1843)则在这里居住了四十年。这里,因为两位诗人曾居住于此,被称为凯西克的“诗人角”。
这座房屋最初是由一名乡绅威廉·杰克逊所建,最初的名字比现在多一个字母,为“Greata Hall”。杰克逊最初建造这座房子是为了在退休后享受一年二百英镑收入所带来的闲适生活,研究莎士比亚、休谟,以及他平生累计的数目不小的藏书。巧合的是,当时华兹华斯兄妹所租住的“鸽舍”,房东是杰克逊的妹夫约翰·本生;华兹华斯的诗作《马车夫》写的正是杰克逊的马车与车夫本杰明。一八○○年,杰克逊从华兹华斯兄妹那里了解到,诗人的朋友柯勒律治有来湖区的意愿。杰克逊对有学问的人士非常感兴趣,所以非常愿意让柯勒律治租住他家的一部分;而柯勒律治也被杰克逊的图书馆吸引,所以虽然整个大院还没有完工,他就直接住了进去。半年租期到时,杰克逊还以房子尚未完工为由,拒收了柯勒律治的房租。
柯勒律治非常满意自己在此的居住环境。格雷塔府背靠斯基多山峰,面对格雷塔河,可以看到远处的德温特湖滨与洛多尔瀑布,缭绕的山雾,阳光与云朵变化万千,好像天与地在对话。而且,柯勒律治与房东相互欣赏和喜欢,杰克逊的大图书馆对柯勒律治而言仿佛天堂。柯勒律治是如此喜欢这里的风景,他们刚搬进来的那年九月,柯勒律治夫人平安诞下一子,被柯勒律治起名为“德温特”。这样的风光甚至激起了他认为自己快要熄灭的诗人火焰,再次给他带来诗歌创作的灵感。柯勒律治在这里完成了《克里斯德蓓》的第二部分。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柯勒律治借着月光翻过赫尔维林,到鸽舍给华兹华斯兄妹看他写的《克里斯德蓓》,此外当时他们还在筹备《抒情歌谣集》第二版的出版。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人们都认为他能平安地走过如此艰险的山路是一个奇迹。赫尔维林海拔高度为九百五十米,山路陡峭险峻。我曾经在二○一九年夏天爬到过山顶,即使是白天,道路也相对完善,我依然多次差点因恐惧而放弃。
很快,這里迎来了柯勒律治的访客,诗人萨缪尔·罗杰斯,柯勒律治的少时好友查尔斯·兰姆,连襟罗伯特·骚塞,当然华兹华斯兄妹这对常客更不必说。所有来访的人中,只有兰姆这位生长在大都市伦敦很难喜欢坎伯兰郡的山水,对兰姆来说,相对都市的喧嚣,湖区的山水实在是太单调了。但是,兰姆仍然喜欢上了他在柯勒律治的书房里看到的黄昏,这位对湖区的自然风光从来不甚感兴趣的诗人,在写给他的朋友、汉学家的托马斯·曼宁(Thomas Manning)的信中说:“我们(指兰姆和他的姐姐)认为自己进入了仙境……我们进入了柯勒律治舒适的书房,当时恰是黄昏时分,周围的山脉被其上的云朵包裹。我以前看到的所有一切都不曾给过我这样的印象,而且我也不认为我会再次在哪里得到这样的印象。”(E.V.Lucas ed. The Letters of Charles Lamb to which are added those of his sister Mary Lamb. London: J. M. Dent & Sons; Methuen & Co., 1935)被华兹华斯称为“鄙视田野的人”的兰姆尚能被这样的风光打动,即使隔着两百多年的时光,我们多少可以想象其风景的迷人之处。
一八○三年,骚塞的第一个女儿、一岁多的玛格丽特因病夭折,这让骚塞夫人心碎无比,只有妹妹柯勒律治夫人才能给她带来一些慰藉。而就在前一年的十二月,柯勒律治夫人刚生下了小女儿萨拉。骚塞认为,小萨拉可以填补妻子因失去女儿而在内心生出的空白与茫然。于是,骚塞决定留在凯西克,与柯勒律治合租格雷塔府,在湖区安家。再过几年,弗兰西斯·杰弗里会批判以华兹华斯为首的“湖畔派诗人”,本意是讽刺他们居住湖畔,浪费自己才华写一些无关紧要的内容等,但后来这个名字成了美称,主要指的就是华兹华斯、柯勒律治与骚塞。柯勒律治早于骚塞来到格雷塔府,但骚塞却在湖区待的时间最久,这里是他度过四十年的家,去世后也是安息在凯西克的克罗斯威特(Crosthwaite)教堂墓园里。
格雷塔府共有十二个房间,两个厨房。同一屋檐下两栋房子相互连接着,大的那一部分由柯勒律治和骚塞的家人居住,小的那一部分由房东杰克逊居住。一楼是两个厨房所在,这是两个石头铺就的房间,厨房与前门之间有一个过道,过道左边是客厅,也就是餐厅和起居室。一楼的另一部分区域,是柯勒律治的大儿子哈特莱的活动空间,这里被他的家人朋友以及后来的人称为“哈特莱的会客厅”(Hartleyʼs Parlour)。
骚塞的书房在二楼,那是他创作与研究之地,也是他的图书馆与圣地,只有骚塞夫人可以未经允许而入。这里曾是柯勒律治的卧室,被他们的家人称为“彼得”。书房有三扇窗户,透过较大的一扇常可以看到花园、湖水和远处的山脉。另外两扇较小的窗,则可以看到凯西克镇的一部分。柯勒律治的女儿曾经描述姨父的书房里,有带着精美镶边的书,也有放在架子上的书,还有一堆按字母顺序排列的牛皮书卷。骚塞夫妇的卧室也在同一层。二楼有一条过道可以通向房东杰克逊的住处,过道的一侧放满了书。柯勒律治的书房也曾经在这一层,因为杰克逊在那个房间里放了一架古老的管风琴,所以那个房间又被称为“管风琴室”。另一间卧室由萨拉的另一位姨妈罗威尔夫人居住—因为三姐妹(萨拉的母亲与两位姨妈)都居住在此,所以格雷塔府私下又被昵称为“姨妈山庄”(Aunt Hill)。
顶楼有六个房间,一间育婴室,一间奶妈卧室,一间侍女室,另外一间是萨拉的表姐妹凯特与伊莎贝拉的卧室,一间杂物间,一间黑暗的苹果储藏室。一条过道通向房顶,视野开阔。
这栋房子不像华兹华斯的故居“鸽舍”那样为国家信托所有,而是几经转手,改作他用。骚塞去世后,这栋房子空了一段时间,一八五五年,一个华兹华斯的美国传记作家在德温特·柯勒律治的陪同下,游访过格雷塔府。一八七二年至一八八七年间,格雷塔府成为一所女校。教会史学家亚瑟·斯丹利(Arthur Stanley)来访后,给柯勒律治的侄孙写信,认为应该有石板永久性地标明曾经居住者的名字,但也没有下文。后来,格雷塔府又卖给了凯西克学校,成了学校的女生宿舍。如今的格雷塔府被一对中年夫妇买去,和他们的孩子住在那里,同时也把它作为民宿经营。有趣的是,这对中年夫妇的孩子的数量,刚好是当时居住在这里的骚塞与柯勒律治的孩子们的数量。他们很满意这种巧合,也很尊重这里是诗人故居的事实,依然保持着各个房间原来的名字,也欢迎人们去那里居住,或者喝个下午茶。二○一九年夏,我们在大雨中找到了这里,从门口可以看到里面停着的车,还有房子窗户里透出的灯光。当时只觉得可能成了私人住宅,在门口拍照已经是不小的冒犯了,后来才了解到这栋房子的现状。只是受疫情的影响,想去那里体验一下当时诗人们居住环境的计划一再受到影响。如果有一天,格雷塔府可以像“鸽舍”那样为国家信托所有,供全世界的骚塞与柯勒律治的诗歌爱好者们参观,那就最好不过了。
骚塞在凯西克
凯西克因为骚塞与柯勒律治的居住,而成为湖区与世界的文学圣地。
对于柯勒律治而言,他一方面实现了自己在《午夜寒霜》(“Frost at Midnight”)中对儿子“像清风一般/遨游在湖滨、沙岸和山岭高崖下/仰望浩瀚的云海”(杨德豫译)的寄望,一方面也完成了自己生命中二三重要的诗作;除此之外,格雷塔府与凯西克于他,远远比不上鸽舍与格拉斯米尔之于华兹华斯的重要意义。鸽舍成就了华兹华斯创作历程中的“黄金十年”,构建了让他一生幸福的家庭圈子。柯勒律治在此处却创作寥寥,甚至发出了自己体内诗人已死的感慨;柯勒律治与妻子的裂痕与分居也是开始于此,幸福的家庭生活于他而言太过遥远。骚塞在格雷塔府定居的那一年,也是柯勒律治准备离开格雷塔府远去马耳他养病的时间。柯勒律治于一八○四年出发,两年后才回来,其后也住得一直断断续续,终于在一八一○年丢下妻子与儿女,去伦敦寄居直至离世。在这期间,他只在一八一二年回来过一次,是为了从安布赛德的学校送兒子回家。在某种意义上,在格雷塔府久居的真正主人应该是“湖畔派诗人”中最不为人熟悉的骚塞。他在这里创作,也在这里照顾两个家庭和儿女们。
骚塞也并非一开始就决定永远居住在这里,湖区的潮湿让多病的柯勒律治远去更暖和的地方养病,所以对于骚塞来说,他需要思量自己是否要在此待下去—尤其是在柯勒律治越来越远离格雷塔府,留下一大家人需要他照顾的情况下。直到一八○七年,骚塞才决定在这里长住,一八○九年签订了二十一年的租住契约。但是到了一八一七年,虽然契约远未到期,房东杰克逊却已经去世八年,他的家人决定把房子卖掉。骚塞非常沮丧,他咨询了一下,当时这处房产价值两三千英镑之间,相当于今天三四十万英镑。骚塞试图筹钱买下这栋房产,华兹华斯也愿意借钱给他。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并没有必要,因为新主人仍然愿意将房子继续租给骚塞,让诗人继续规律地生活与创作。
在这四十年中,骚塞常常在早晨穿着黑色外套与灯芯绒的裤子散步,早饭后,在书房坐到下午两点;午饭后,带着一本书开始散步;晚饭后,又会回到书房,读报、写信。骚塞生活之规律,会让人想起康德在柯尼斯堡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骚塞在格雷塔府的生活与书密切相关。他对书的热爱一方面是出于创作与研究的需要,一方面跟他在不断失去生命中至亲的痛楚有关。他曾经给兄弟亨利写信说自己之所以痴恋书,是因为与书在一起时有一种特别舒服的感觉,书是他唯一安全的依恋,是他唯一没有失去的危险且一定在他身后还幸存的“朋友们”。骚塞很早就经历失去父母、女儿、儿子等的痛楚,投身于书中对他而言是一种庇护。到他去世前,已经收藏了一万四千本书,在那个书籍特别贵又难得的时代,这是不小的藏书量。
沃尔特·司各特的女婿洛克哈特在一八一九年拜访骚塞时,感觉他的书房是“多么适合诗人的一个书房!初一进入,我几乎感觉自己仿佛步入明静的夜晚中。一种柔和炫目的美扑面而来。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两个壮观的湖—德温特湖和巴森斯韦特湖—和一个葱葱郁郁的山谷……大片山脉在湖水的最上游终结了所有的风景,但是蓝色的巴森斯韦特湖似乎消失于天际”。骚塞在自己的这个图书馆里,向洛克哈特介绍自己的藏书,洛克哈特认为,这是他见过的英格兰所有私人图书馆中,西班牙与葡萄牙文学最丰富的。洛克哈特在这里看到了诗人的灵魂,也看到了他的那些高贵的诗作、渊博的史作,以及生动的随笔所诞生的地方。他认为,骚塞在这里为了人类的利益与他自己不灭的生命辛勤耕作。骚塞本人的诗行则能更准确地描述他与这些书的交流:
我的岁月尽同死者盘桓;
当我举目向四周观看,
无论把目光投向哪里,
都会遇到已逝的先贤;他们是我忠实的朋友,
我天天同他们倾心交谈。
(顾子欣译)
一八一三年,司各特婉拒了桂冠诗人的荣誉,此时的骚塞已经因为韵文体的《马多克》(Madoc)与散文体的《奈尔逊传》(Life of Horatio Lord Nelson) 而闻名。于是,司各特便推荐将这项荣誉授予骚塞。有趣的是,司各特本人拒绝这项荣誉多是出于其荒谬性—桂冠诗人在接受每年来自王室的俸禄以外,要为王室的重大事件写颂诗(ode),蒲柏曾将颂诗诗人描述为失去理智之人,而司各特也认为自己会是一个糟糕的朝臣。但是在他写信给骚塞时,却特别强调自己并非因为荣誉的荒谬性才拒绝的;相反,他告诉骚塞,自己之所以认为骚塞才应该获得这项荣誉是因为,天假以年,骚塞会重现斯宾塞的荣耀与德莱顿的尊贵。而且,他认为虽然自己更受欢迎,但自己清楚地知道骚塞的诗远比他的要好。虽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骚塞并不是特别出色的诗人,尤其是与其他两位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比较起来,但在当时,骚塞在移居湖区之前出版的《毁灭者塔拉巴》(Thalaba the Destroyer),以及《马多克》与《奈尔逊传》等作品,都是非常畅销的诗作。因此在司各特婉拒之后,“桂冠詩人”的荣誉基本上是非骚塞莫属了。
从此之后,格雷塔府与凯西克的访客多了起来,格雷塔府与在其中居住的骚塞,像是多年后瑞德山庄与在其中居住的华兹华斯一样,都成了游客的观光景点之一。但在诸多来此的游客中,有一位的行踪非常让人费解,他就是约翰·济慈。他于一八一八年夏来湖区旅游,他在凯西克几乎走遍了小镇周边的景点,绕德文特湖观看周围的湖水、山脉与其他自然风光,在凯西克的橡树客栈(今天的皇家橡树客栈[The Royal Oak])就餐,从那里到格雷塔府不会超过十分钟的路程,而且济慈也很熟悉骚塞的诗歌,但他却没有任何意愿去格雷塔府拜访这位桂冠诗人,甚至在书信中提也没提,这实在是一件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
骚塞居住于格雷塔府的四十年中,经常独自一人,或是带着他与柯勒律治的孩子们到离家有一点距离(徒步大约三十分钟)的德温特湖野餐。古往今来,来凯西克的人们,包括那些著名的诗人、批评家、科学家,都会来此处驻足观望。所在之处幽静无比,所望之处山清水秀、天蓝云白,悦耳鸟鸣不绝于耳。那些游客们的喧嚣被阻隔在岩下的湖滨。走到附近的猫溪(Cat Gill),便可以将“修士岩”一览无余。那种安静雅致的美丽会让人明白为什么骚塞当年希望自己当时拥有一盏阿拉丁神灯,或福图拿都的钱袋(Fortunatusʼs purse,即取之不尽的钱袋)可以让他在“修士岩”附近盖一座房子。我于今日遥望曾经在此处的骚塞,应该就像骚塞在当时遥望更早之前在此隐居的圣赫伯特(St. Herbert)。一个地方吸引人定居,除了无以言表的自然美,很多时候也因为其中迷人的人文风景。
凯西克的“文学雄狮”
一八三五年,外出的骚塞,回到格雷塔府,发现自己被当时英国的首相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1788-1850)授予男爵的封号。虽然此前他没有太大迟疑地接受了“桂冠诗人”的封号,但是这一次拒绝了男爵的封号,理由是自己收入有限,有限的物质财富不足以让这个封号保留到下一代。骚塞的“格雷塔府”不像华兹华斯的瑞德山庄那样,曾经接待过英国国王威廉四世的遗孀阿德莱德王后这样的贵客,但“男爵事件”是最接近这类性质的发生。如今的格雷塔府,尽管没有作为诗人的故居被保存下来,但凯西克并没有忘记骚塞和柯勒律治。骚塞的大部分作品与书信,以及柯勒律治的部分作品与书信,被安全地保存在位于格雷塔河对岸的菲茨公园(Fitz Park)里的凯西克博物馆里。
著名的古文物研究者威廉·边沁的长女玛蒂尔达·边沁曾于一八○六年和一八○九年两度来格雷塔府为骚塞画像,骚塞最好的画像之一便出自她手。骚塞获得桂冠诗人的荣誉之后,来访的艺术家更多,其中有爱德华·纳什(Edward Nash),还有风景画家威廉·韦斯托尔(William Westall)等,他们也为后人留下了大量关于格雷塔府与诗人骚塞及家人的画作。
一八○三年六月,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1778-1830)受乔治·博蒙特爵士的赞助,来到格雷塔府,为柯勒律治、他儿子哈特莱,以及华兹华斯画肖像。在此期间,哈兹里特遭遇了自己一生中的丑闻。对此,他本人讳莫如深,而我们所了解到的几乎都来自柯勒律治、骚塞与华兹华斯之言—考虑到后来哈兹里特与他们之间的糟糕关系,所以很难了解到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根据三位湖畔派诗人所说,哈兹里特因为在凯西克的酒馆里侵犯了一位女子,所以被当地人骑着马追。根据骚塞对当地人的了解,如果哈兹里特被抓到,会受“浸猪笼”(ducking)之罚,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一开始还当笑话看的柯勒律治态度一下子严肃起来,与骚塞一起为哈兹里特打点行李,催促哈兹里特赶紧跑,资助他去二十公里外的格拉斯米尔华兹华斯家避难。英国著名传记作家杭特·戴维斯(Hunter Davies)曾经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人们至今还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讨论哈兹里特在湖区的这件事情的可能性,并特别指出自己记录这件事情,并非是非要把这件丑闻扯进来。而是想说明,在近二百年后,湖畔派诗人们与朋友们的生活还是如此有吸引力。(Hunter Davies. A Walk Around the Lakes.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9)
回到这一事件,三位诗人一直认为自己有恩于哈兹里特,但哈兹里特在后来的文学批评中,对他们却一个都没放过,尤其对骚塞的攻击最为厉害,从文学创作到政治观念把对方批得体无完肤。很多批评家认为,骚塞之所以在当时以及后来的名声不如另外两位诗人,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哈兹里特对他的批评。但无论如何,在骚塞与柯勒律治早年的诸多访客中,这是特别戏剧化的一幕。骚塞在包括这件事情在内的很多事情上,拥有非常敏锐的判断力。若非骚塞,我们现在可能会少了一名出色的批评家,也未可知。
一八○七年,二十二岁的德·昆西第一次来到格雷塔府,在这里他很受欢迎。德·昆西在《湖区与湖区诗人回忆录》中写道:“骚塞非常热情地招呼我进门。”德·昆西之后几度来此,但后来因为德·昆西在文字中总是不公正地描写湖区诗人与他们的家人,透露他们的隐私,所以并不为华兹华斯、骚塞,尤其是骚塞所容。晚年的骚塞在卡莱尔问他,是否认识德·昆西时,说,如果卡莱尔可以代他转达对德·昆西的观点,他将会感恩不尽;他认为,德·昆西是所有在世人中最混蛋的一个,而且哈特莱(柯勒律治的大儿子)应该拿根棍棒追去爱丁堡(当时德·昆西与家人已经定居爱丁堡)狠狠打德·昆西一顿。其中的愤怒,与这三位诗人对哈兹里特的感觉相差无几,在他们看来,两人都是不知感恩的家伙,而对德·昆西这位与他们交往更密的人则怨恨更甚。
一八一一年冬,还不到十九岁的雪莱与他的新娘哈里雅特,以及妻妹伊莱扎·韦斯特布鲁克来到凯西克,住进了凯西克边缘的赤斯纳希尔农舍(Chestnut Hill),如今这里已经被易名为雪莱小屋(Shelley’s Cottage)。受雪莱喜爱的凯西克的自然风光,到今天也没有改变,还是连绵的高山、美丽的瀑布、万千变化的云朵,以及偶尔出现在人与湖之间的彩虹。雪莱认为,这些自然风光对沉思者来说是极好的。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他描写了被白雪覆盖的山脉,平静如镜的湖面,以及日落;这些景色难以言传的壮丽,让他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美丽平静的天堂。雪莱自己在此行中创作了诗歌。次年一月,雪莱与哈里雅特到格雷塔府拜访骚塞,柯勒律治恰好不在湖区,去了伦敦。后来柯勒律治说:“骚塞帮不到他的地方,我可能对他更有用,因为我应该会能理解他的诗学;形而上学的思想,甚至是形而上学这个词本身都让骚塞无比厌恶,雪莱本会感觉到我是懂它们的。”雪莱在此确实与骚塞产生了分歧,从此之后,这位偶像在他心目中倒塌了。然而,雪莱却因为骚塞而知道了政治哲学家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1756-1836)—玛丽·雪莱的父亲—这位《政治正义论》的作者很快占据了雪莱的思想。
雪莱在书信中表达了对骚塞的讥讽,但他也提到了骚塞对他所说的“等你到了这个年纪也会和我一样想”。当然,骚塞自己对这位年轻人的情绪也并非一无所感。他在给朋友的书信中,将雪莱比作他过去的幽灵,说雪莱就是他一七九四年時的样子。当时的骚塞是法国大革命的支持者与赞颂者,与长他两岁的柯勒律治,以及长他三岁的诗人罗伯特·罗威尔正策划着去美国的萨斯奎哈纳河滨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区。而此时在格雷塔府拜访骚塞的雪莱,刚刚(1811年3月)因为写了《论无神论的必要性》被逐出牛津大学。相比之下已经人到中年、生活与写作都渐渐安稳下来的骚塞,在各方面都已经不再像从前了。但骚塞表示,自己是了解雪莱的思想的,而且他们之间唯一的差别就是,雪莱是十九岁,而骚塞本人三十七岁。总之,这两代浪漫主义诗人在凯西克的对话,不仅拉开了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也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当下或日后两代诗人之间的思想差异。或许也是这种差异让年轻的雪莱更加热血沸腾,他在凯西克完成了《致爱尔兰书》的初稿,很快奔赴都柏林,并在那里为了“唤醒爱尔兰的贫苦人民”(《雪莱政治论文选》,杨熙龄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廉价出版了这篇文章。
不过,雪莱虽然对骚塞的思想很失望,但仍然认为骚塞是一个非常友善与高尚之人。在雪莱拜访格雷塔府期间,于诗人的书房里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骚塞与华兹华斯一样,喜欢给来访的仰慕者朗诵自己的诗歌。雪莱来访后,骚塞把雪莱安排在书房里,悄悄锁上了房门,确定雪莱一定会听他朗诵。骚塞当时朗诵的是他刚完成的诗歌《基哈玛的诅咒》(“The Curse of Kehamah”)。沉浸于自己创作的作品,骚塞用抑扬顿挫的声调朗诵着,而且时不时挑选出他认为写得好的地方,等待着赞美。但很奇怪的是,诗人什么也没有听见。当他把眼睛从朗诵的手稿移开,却突然发现雪莱消失不见了。怎么可能,因为这个房间没有任何出口,而钥匙则在骚塞本人的口袋里。太奇怪了。最后的结果是,秉烛夜读的雪莱因为发困从椅子上无声地滑落在了地板上,躺在桌子下面陷入了深深的睡眠。
以上提到的这些访客,只是其中特别小的一部分,但就像时不时去书房打扰骚塞的、格雷塔府的那些孩子们一样,这些访客从来都能受到骚塞热烈的欢迎,却丝毫不会影响他多产的创作。骚塞为伦敦的报纸写评论,写自己最擅长的传记,写诗歌,甚至还写了一个童话故事《三只熊》(The Story of the Three Bears),后者至今闻名世界。骚塞一生辛勤笔耕,养活了三家人。他对湖区的热爱在某种意义上与那里的风景有关,但更重要的却是因为他在那里失去了他挚爱的两个孩子,女儿伊莎贝尔和儿子赫伯特。为了不离开他们,以及他们所安息的湖区,骚塞甚至拒绝了伦敦邀请的年薪一千英镑的工作。想想,他和柯勒律治曾经的房东杰克逊凭借一年两百英镑收入,就可以过上非常宽裕的生活,这一千英镑对其他人该有多大的吸引力!
骚塞在湖区身有所安,心有所寄。如今,我们或许会说,他是最不像诗人的桂冠诗人,也不像另外两位湖畔派诗人那般,有着让人可以有随时吟诵出来的诗行。但如H. D. 罗恩斯利所言,他是最善良的绅士,若不然,谁会任劳任怨地承担起照顾别人的家庭与孩子的重任?除此之外,骚塞还是一位出色的传记作家,他的《奈尔逊传》与《巴西史》至今依然是最受欢迎的作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巴西政府为了表示对这位诗人的感激,还特地出资修葺了诗人的墓碑。墓碑安置在诗人安息的克罗斯威特教堂墓园里,紧挨着教堂背后,一眼便可以让人注意到。这让人一下子回想到一八四三年的那个下雨天,骚塞永远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七十三岁的华兹华斯,作为唯一幸存的湖畔派诗人,在女婿爱德华·奎利南的陪伴下,穿过二十公里的风雨路程,为这位他一直视为兄弟的诗人送别,并为他写了墓志铭。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无论格雷塔府被保存与否,人们都多少记得这位诗人在那四十年间的生活。如他在诗中所言:
我想我也会在此留下一个名字,
这名字永远不会随尘土消亡。
(顾子欣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