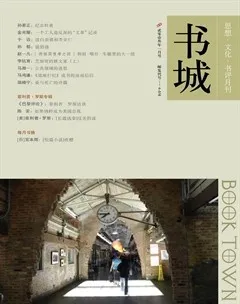极光的语言
木卫二
起初,我以为这是一本自助类的讲野外生存的书籍,提供指南、攻略、干货的那种。总之,从书架上抽下这本《一个女人,在北极》时,我不知作者是何方神圣;而翻开冰雪打底的封面时,我也压根不晓得,在旅行文学的名册上,有过这样一本书。
我与极北之地的最近际遇,是在挪威的特罗姆瑟(近北纬70°)。这个地点出现在本书作者克里斯蒂安·里特(Christiane Ritter)返回欧洲大陆和文明世界的第一站。彼时,我认知苦寒尚且粗略,只晓得挪威有个“种子岛”(即斯瓦尔巴群岛“末日种子库”),也听说过有一个冷僻岛屿,中国公民能自由出入,还有个地方建有北极科考黄河站。我显然没搞清楚,这几处地点,竟是同一个地方,即《一个女人,在北极》的故事发生地斯瓦尔巴群岛。它距离人类文明视野太远,导致我没能将它们联系在一起。
北极点的位置在北冰洋,没有陆地。北冰洋周围,则有一圈岛屿,分属不同国家,它们共同组成了极地世界:格陵兰在其中最具知名度,有原住民;小国冰岛,又最受游客青睐,引领电子乐风潮。我过往的谬误,还将斯瓦尔巴群岛,跟俄罗斯的新地岛和北极群岛,彻底混在了一块,盖因它们真的太少出现在文明世界的新闻报道中。没有消息,就是它们传递出来的最大消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高纬度群岛,其曝光率大多如是。在冰川的作用下,这些岛屿在地图上呈现锯齿状外观,有如造型不同、材质不一的梳篦。在肉眼可见的三维世界中,以有名的挪威峡湾地貌最有代表性。
斯瓦尔巴群岛,别名冷岸岛(来自挪威语“svalbard”)。在微信的国家地区列表里,它可以单独显示,即斯瓦尔巴群岛和扬马廷(扬马廷是位于格陵兰与挪威之间的分界岛)。斯瓦尔巴群岛的样子,像一张缩略比例走形,被撕裂、揉皱的印度地图。由于绘制地图采用的是墨卡托投影,高纬度地区总会变形,直到现在我也记不住斯瓦尔巴群岛的真实形状。
《一个女人,在北极》书名中的“一个女人”,即指作者克里斯蒂安。但她并非真的一个人生活在冷岸岛上。她留驻北极的丈夫发来探亲邀请,于是克里斯蒂安展开了为期一年的极地之旅。扫过故事简介,读者还容易预设,本书是关于一对伴侣在天寒地冻下相扶相助的故事,大谈生存体验。不消说,数百年来,极地冰冷坚硬的事实,未曾更改。
结果,打从登陆北纬八十度的灰岬开始,原来本书人物,不止两位—冲克里斯蒂安招手微笑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年轻的挪威金发小伙卡尔,也跟克里斯蒂安和丈夫一起度过这一年(所以这北极一年,是三人同栖)。缺少人类同伴的情况下,多一个人,就是多一份想象力,多一份生命勇气和生活乐趣。譬如在做饭出餐上,三个人,就具有了三种厨艺。面对单调食材,同样的海豹肉处理,至少可以保证口味上不重样。
克里斯蒂安成行于一九三四年,《一个女人,在北极》初版于一九三八年。但整本书读下来,并无陈腐语气与年代距离,这是一本由文字制造出迷人氛围,行动方式与特殊体验兼备的游记。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灰岬上的那间小屋四四方方,插俩烟囱,更像时下的集装箱。灰岬周围则有一大串仿佛来自极地抑郁症患者的赐名之地,像愁思岬、悲叹湾、狼狈岬、忧愁湾等。
克里斯蒂安的角色,在一个人类、一名女性和一位小屋女主人的多重身份之间切换,她会同情雪狐、绒鸭和海豹,慈爱心泛滥,不忍下杀手;又会在饥饿或者食物危机到来的情况下,关切维生素的摄入。一头海豹可以提供半吨到一吨的鲜肉食材,过于可观。当丈夫为冰原上柔弱小花身上的大自然生机赞叹时,克里斯蒂安的做法却是将它们“统一吃进肚里”。再美的小花,经受完一个人类的赞美,不外是富含维生素的蔬菜。
海明威选择用猎枪获知非洲野生动物的名字。他的勇气,说到底,不过是文明人的包装、粉饰与伪善,跟阿尔谢尼耶夫《在乌苏里的莽林中》里的赫哲族猎人德尔苏是完全不同的。再如《一个女人,在北极》里,用自动陷阱去猎杀北极熊,那是长久以来,极地猎人在荒野冰原上寻觅食物的生存方式,而非现实世界中动物园的观赏互动,或设立国家公园,以体制之臂弯为原生栖息地提供保护。
大自然之手主导一切的情境下,不猎杀动物作肉食储备和补充,人类根本不可能在极地生存(如同薛克顿南极求生的壮志故事中,负责运输任务的雪橇犬,也遭“人道处理”成为食材,读来使人难过)。倘若克里斯蒂安是个猎人,读者反倒会对她的慈悲感慨产生怀疑。但她的北极主妇身份,又令读者对其出于行文方便而产生的人类情感,多了理解的基石,有可垫步与缓冲的空间。
维持生存必需条件之外,书中最美的一些感受体验,全是来自一年之中光线带来的神奇变化。从修辞上,这一年可以描述为一个白天与一个夜晚—漫长的白天与漫长的夜晚。然而在白天与黑夜之间,光线变幻无穷,令人仿佛置身梦幻仙境,探触到永恒。
克里斯蒂安很快发现,自己身在光之帝国,用电影摄影的术语来说—她随时体验着魔幻时刻。其他纬度的魔幻时刻,来自日落西山之时,十五分钟左右的薄暮之光。
当南回的太阳,以不可思议的极低角度,拂照斯瓦尔巴群岛,“说是白昼,其实不过只是由朝霞与晚霞组成”,“万物仿佛获得自己的光”。人不仅渺小,也会自知渺小,固有意识接近消融。这时候的太阳光照射,角度低探,温柔低回。大自然的打光,赛过一切人间顶级豪华摄影棚。此际此刻的人像轮廓,美轮美奂,万物如蒙圣恩,如沐爱河。以天空和大海为尺度的天地舞台中,远山河谷不说,平凡无奇、粗糙简陋的人造物,也像变了一副模样,就如同直接被赋予了生命。
克里斯蒂安断言,这光之戏剧,不是为人类肉眼所造。初到北极,幸运看到极光的人,也会被美撞击,陶醉、喜悦,身体随之轻摆、摇动、变形、幻化,乃至狂喜。然而,用美这样的大词,去化约、表述,虽然确实对光进行了修辞,却也消解了光与光之间时时刻刻的差异與变化之美。要感知极地之光的层次之丰富、力度之浑厚,需要长时间的浸入体验,比如拥有在极地一年的生活体验,而绝大多数人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只能点到即止,望而却步。
当太阳光彻底消失后,群山只剩白影,大海只剩黑影。没有了无所不能的太阳,还有魅力绝伦的月亮。在克里斯蒂安看来,步入极夜的过程,是失去光线,却也催发了人类本能的光之渴望,更加冲动,强烈。她写道,满月之下,月光似乎轻易就会让人发狂。“我们融化在月光中,又像是月光把我们吃个精光”,“月光似乎无所不在地跟着我们,即使我们在月光下漫步后返回小屋也躲不掉”,“海中晃动的碎浮冰块将光碎裂成上百片,再投射回月亮”。享受孤寂,与被孤寂吞噬,似乎只有一线之隔,读者跟着克里斯蒂安出窍又回魂。
可以说,光有描述光之盛况与极夜体验的篇章,《一个女人,在北极》已经是一本出色的游记。克里斯蒂安含蓄地动用着美的修辞,又让读者感受到消解自我体验的灵性快乐。漫长极夜中,由于极端的无聊、冷静和孤寂(男人们出去打猎时),她甚至能辨认风的模样,风暴从北边、西边和东边来,它们的步履,是有差异的。当来自南边的风,从山上往下吹,轻柔而温和地进入小屋,是她“对自己的孤独有着最深刻体认的时刻”。
克里斯蒂安不仅对灰岬小屋的日常,对进入与生活在极地,有着深刻且不凡的观察总结;告别极地之际,她也能敏锐留意到细节上的变化。“食物丰盛,咖啡则过于浓黑”,火车越来越快,报纸越来越厚,人们愈发匆忙。人人都在读报纸,上面好多大新闻,但其实毫无内容。这些观察描述,来自《一个女人,在北极》后记,写于一九九○年—成书五十二年后。一本好书,哪怕你只读后记,也会感受到它的真诚流露。出于对历史的认知,我们当然知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的欧陆,风云诡谲,但它不影响我能深深理解克里斯蒂安从北极南归时的不舍。她迅速感染了匆忙与紧张的病毒。她惊觉,原来自己离开文明世界已经有一年之久。冷岸一年,让他们蓬头垢面,颜如菜色,却幸运地遗忘了欧洲的愁容。身为普通人,很难接收新闻消息背后隐藏的信号,更不可能及时预见后来的战争与暴行。站在更宽容、更富道义的后世人的立场,或许,能不亲身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背向人类黑暗罪恶的深渊,也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选择。毕竟,战争是文明的反面,是缺乏维生素的野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