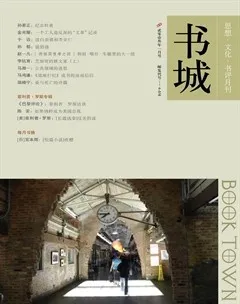巴黎先锋: 女艺术家与现代主义
书玉
卢森堡博物馆
卢森堡博物馆地处巴黎左岸最文艺的地段圣日耳曼德佩区,五区和十三区的交界处,是卢森堡公园的一部分。
卢森堡公园当年是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孀妇玛丽·德·美第奇王后(1575-1642)的私人住所。在她的儿子路易十三执政之前,美第奇王后曾摄政五年(1610-1614),有钱有势,就在那时她开始策划在巴黎修建一个仿造佛罗伦萨娘家花园宫殿的地方。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意大利是欧洲艺术风尚的领军翘楚。玛丽王后出身于意大利艺术豪门美第奇家族,卢森堡花园是仿古典意大利宫廷花园的始祖佛罗伦萨的波波里花园(Boboli Gardens)而建。里面的卢森堡宫则是佛罗伦萨彼提宫(Patti Palace)的复制。经过历次扩建,尤其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巴黎城市改造时,增加了一个英式花园和果园。在这个由大小宫殿、喷泉、众多雕像以及整齐规划的花园共同组成的皇家花园里,最令人流连的是遍布其中的大量雕像,它们的原型是法国历代王后和著名女性,也有文人骚客,最著名的就是纽约自由女神像的原型。如今这个有着浓厚法兰西人文艺术气息的皇家花园已为法国国会所有,对公众开放。卢森堡宫也成为法国参议院的所在地。
卢森堡宫旁边的卢森堡博物馆,看上去不大,其实是巴黎资格最老、声望最高的艺术博物馆之一。从一七五○年开始,玛丽王后私人收藏的意大利、荷兰和法国大师的作品就开始向公众开放。一八一八年该博物馆成为第一个展出还活着的艺术家作品的艺术博物馆,因此对艺术家以及作品的价值评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的永久收藏后来分别分散到卢浮宫(欧洲和世界古往今来的珍品)、奥赛博物馆(主要收集19世纪和之前的艺术品)以及蓬皮杜中心(专藏20世纪的作品)。在短暂的休馆后,二十世纪末议会又重新开放卢森堡博物馆,并在二○一○年把它交给专业机构法国国家博物馆联盟大皇宫(The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Grand Palais,简称Rmn)经营。
在巴黎这样一个画廊博物馆林立、各种艺术展览层出不穷的地方,卢森堡博物馆以主题展览为自己的特色。它每年只做两次展出,规模一般也不是很大,但是在巴黎这个艺术展览之都,卢森堡博物馆以策展方面的世界眼光、独特的展题以及展览水平取胜。这从近些年的展览可以看出。一方面,它有面向世界经典的实力画展,二○一七年的鲁本斯画展,二○一八年意大利复兴时期的丁托列托(Tintoretto)画展,二○一九年英国黄金时代的画家画展,等等。另一方面,它也特别专注于二十世纪初法国作为世界艺术之都的话题,比如二○一八年,介绍活跃在二十世纪初的捷克艺术家穆夏(Alphonse Mucha)的画作,以及新艺术风格的海报设计;二○二一年的“曼·雷与时尚”(Man Ray and Fashion),也是对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视觉艺术家曼·雷新角度的回顾。
卢森堡博物馆对现代和当代女性艺术家也特别关注。去年秋天,我在巴黎时正赶上博物馆办美国女摄影家薇薇安·迈尔(Vivian Maier)的展览。薇薇安·迈尔是近年来摄影圈中的传奇人物。她是法裔,长大后到了美国,在纽约和芝加哥度过了大半生。她生前以保姆为业,但业余拍摄了十万张照片,大部分照片直到她死后才被整理展出,都是纽约、芝加哥这些美国大都市的街头即景。那些日常生活中本不起眼的人物和事,被她观察细致、情感冷静的镜头捕捉,定格成意味深长的永恒和戏剧性的故事。薇薇安·迈尔被认为是美国当代最重要的街头摄影师之一、“改写了摄影史”的人。展期的四个月间,我每次从卢森堡博物馆经过,都看到门口排队的人络绎不绝。
今年卢森堡博物馆的重头戏是展览“先锋:疯狂年代巴黎的艺术家们”,其实,准确地说应该是女艺术家们,因为这次展出的无一例外都是女性艺术家的作品。展览的海报就是当时风头最健的女画家塔玛拉·德·伦皮卡(Tamara de Lempicka)的自画像,那种用立体主义风格勾画的现代女性,自信、丰满、裸露的金黄色身体倚靠在铁灰色的摩天楼的现代都市背景上,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非常先锋。这幅海报吸引了很多人走进卢森堡,了解艺术史上被忽略的一页。
疯狂年代的巴黎
一进展览大厅,最先进入观者视野的就是一幅艺术地图,上面标志着这次展出的巴黎女藝术家们的来源。这三十八位艺术家除了来自美国和西欧,如英国、德国、比利时,还有波兰、北欧国家、乌克兰甚至印度。她们中有已经非常有名的画家,比如苏珊·瓦拉东、塔玛拉·德·伦皮卡、玛丽·洛朗桑(Marie Laurencin),但大部分还不为大众所知,比如也从事装饰艺术的索尼亚·德劳内(Sonia Delaunay,1885-1979),为女性艺术沙龙画肖像画出名的画家罗曼·布鲁克斯(Romaine Brooks,1874-1970),特立独行的摄影师克劳德·卡恩(Cloude Cahun),还有对左岸波希米亚前卫艺术发展至关重要的玛丽·瓦西里耶娃。这个展览不仅展出传统意义上的艺术作品,如雕刻和画作,更是全面梳理疯狂年代女性艺术家们的艺术实践,及其在现代主义艺术风尚中的角色和作用。
法国历史上所谓的疯狂年代(Années folles),指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尤其是二十年代。刚刚经过一次大战的欧洲,经济复苏,机械革命和科技发展的成果运用到城市建设和日常生活,火车、地铁、电灯、电话似乎都在预示着一个现代化机器化的时代的到来。巴黎和欧洲其他大都市一样,充斥着对未来生活蓝图的信心,乐观的社会气氛中弥漫着及时行乐的空气。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国家格言。法国的自由与宽容,吸引着欧洲以及世界上的被放逐者、艺术家以及各种异类们在这里寻找生存空间和同类。无数从家庭走出来的新女性,从四面八方涌向巴黎。正是在这样的社会与思想氛围中,十九世纪末开始出现了现代主义的最初实践。对传统意识形态发起挑战的现代主义包括所有形式的创造性表达,范围极其广泛,涵盖建筑、设计、文学、美术、音乐、舞蹈、诗歌。二十世纪一十年代至三十年代现代主义的实践达到第一个全盛时期。疯狂年代也是现代巴黎的高光时刻,是被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称为“思想的实验室”(laboratory of ideas)的时代。
以往研究现代主义,大家关注的都是男性大家们,如乔伊斯、阿波利奈尔、艾略特、毕加索、马蒂斯、杜尚、海明威等,其间顶多点缀几位女性,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或者乔治亚·欧姬芙(Georgia Totto O’Keeffe)等。但是近年来,在女性主义影响下的文化史、艺术史研究,越来越关注女性艺术家的缺席与被遮蔽现象。从女性主义的角度重写艺术史,一方面,需要挖掘历史上那些被男性评判标准所忽略的、被边缘化的女画家。同时,在学术研究整理和发掘的基础上,通过更多样化和不同的策展标准和展览题目,来彰显这些女艺术家的作品。
卢森堡博物馆这个展览正是聚焦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巴黎,聚焦女性艺术家在现代主义生成过程中所起的多方面作用的一个艺术史展览。它不仅集合了那些进行艺术实践的女性画家、雕塑家、摄影艺术家和刚刚兴起的电影艺术家,还包括了作为现代主义的推动者、同路人和助产士的女性。展品除了绘画、雕塑等艺术作品外,还有书刊、照片以及音像档案等资料。用艺术品、文化物品复原历史情境,展现当时那些刚刚走出家门走向世界的女性们,是如何不仅通过她们的艺术作品,更是通过她们的生活实践,参与了现代主义在各个领域—雕塑、时尚、文学、摄影、表演艺术等—的先锋实践。因为现代主义不仅是艺术以及流行文化的革命,更是一场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革。
虽然这个题目和展品可以说是雅俗共赏,涉及大众文化,但做艺术史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个展览的功夫之深。策展人的抱负是展现女性与现代艺术的关系,重估她们在现代主义和前卫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这是一个需要花很多时间做研究的展览,也是一个不同一般分门别类展览的多媒体、多文类的全方位展览。
女艺术家在哪里?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女性开始走向社会,拥有财产,追求个人独立并职业化,那时领风气之先的巴黎成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新女性的再生之地。反映在艺术上,很多女性从模特摇身一变成为画家。但这个历史过程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巴黎小皇宫是为一九○○年博览会修建的,华丽装潢的室内设计中最有名的是當代画家莫里斯·丹尼(Maurice Dennis,1870-1943)所作的穹顶画《法国艺术史》(History of French Art,1925)。他选择了从中世纪到莫奈之间的三十七位著名画家作为法国艺术史的代表,虽然点缀其间有很多让人难忘的女性,比如自由女神(《自由引导人民》),比如画家多米尼克·安格尔(Dominique Ingres)的妻子,当然还有罗丹的裸女,但她们都是以模特的面目出现,是我们所熟悉的女性原型。
实际上,在丹尼那个时代已经有很多优秀的女性画家,但在他的笔下,当代画家主要是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中坚分子,德拉克洛瓦、马奈、夏塞里奥、卢梭、米勒、库尔贝、莫奈、塞尚、罗丹、雷诺阿、德加……他们都是男性!唯一的一位女性艺术家贝特·莫莉索(Berthe Morisot)怀抱一束鲜花站在背景中,几乎不可见,身上也没有任何显示她身份的画笔或调色板。她不仅没有站在前面的雷诺阿、德加那样的权威,甚至不像塔西提土著女和金发的丰腴模特那样显眼。
其实,莫莉索是一位杰出的印象派画家。她是爱德华·马奈的好友,并在马奈的介绍下嫁给了他的弟弟尤金(Eugène)。从艺术探索到私人感情上,她与马奈兄弟都有很深的交流。莫莉索二十三岁那年,首次在声誉卓著的学院派巴黎沙龙里展出作品,被选中的作品是两幅风景画。从一八六四年开始,莫莉索连续六年都被选为参展画家。莫莉索的作品以描绘日常生活经验居多,尤其是女性的私人空间:一个年轻的女人在给姐姐梳头,一位母亲在照顾她的孩子。画中人物也都是她的家庭成员或朋友。在莫莉索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摇篮》中,姐姐埃德玛凝视着她熟睡的婴儿布兰奇。埃德玛的左臂弯曲,跟孩子之间形成一个镜面效果,孩子睡在薄纱覆盖的摇篮中,让观众一下进入了一个亲密关系的空间。
一八七四年春天,莫莉索应马奈之邀参加第一次印象派展览,那个在摄影师纳达尔(Nadar)私人住宅二层举办的画展中,她是参展画家中唯一的女性。当时印象派画家们的作品都是被学院派唾弃的。艺评人阿尔伯特·沃尔夫(Albert Wolff)在给《费加罗报》(Le Figaro)的一篇评论中写道:这次画展由“五六个疯子组成,其中一个是女人……在精神错乱的情绪中她保持了女性的优雅”。之后,莫莉索参加了一八七四年至一八八六年期间八个印象派展览中的七个,而且在每年的印象派画展中都有突出的表现,仅有一次因女儿出生而错过了画展。保罗·曼茨(Paul Mantz)一八七七年在点评第三届印象派画展时写道:“整个革命性团体中只有一位真正的印象派画家,那就是贝特·莫莉索小姐。”
一八九二年,莫莉索在自己首次个展时,针对女性艺术写道:“的确,我们是有价值的,因为我们的感情、意图和眼光比男人们的要微妙得多。如果我们运气好,不受感情、迂腐和过度精致的影响,我们将大有作为。”
莫莉索尝试了一种独特的、未完成的风格,因为她相信绘画应该努力“捕捉消逝的东西”。莫莉索的画有着活泼大胆的笔触和不同寻常的形象、表现力,几乎跨越了印象派而跳到了抽象主义。当时一位评论家写道:“她的画具有即兴创作的坦率;它确实是一只真诚的眼睛所捕捉到的印象,一只不作弊的手所准确地呈现的印象。”
但就是这样一位独特而优秀的画家,也被丹尼置于“当代艺术史”的边缘。他似乎忘记当印象派在一八七四年开始作为一个团体出现时,评论家们很快就给他们的艺术贴上了“女性”的标签:他们的画布很小、他们的调色板太憔悴、他们的画笔太松了……
所以女性艺术家要在艺术史上留下痕迹,并宣称主体性,就要靠自己为自我造像。
这次展览的重磅画家苏珊·瓦拉东(Suzanne Valadon,1865-1938)就是这样的过渡时期的先锋人物。这次画展中有她几幅著名的画作。
一八八○年,十五岁的瓦拉东在巴黎的蒙马特作为模特首次亮相。随后的十年里,本来就对绘画感兴趣的瓦拉东与很多画家,如德加、雷诺阿等成为朋友,并观察学习他们绘画的技巧。一八八三年,十八岁的瓦拉东生了儿子莫里斯·郁特里罗(Maurice Utrillo),他后来也成为一位画家。经过十余年的自我教育,瓦拉东在油画艺术上颇有心得。一八九四年,瓦拉东成为第一位加入法国美术协会(Société Nationale des Beaux-Arts)的女画家。
一八九六年,一直是单亲母亲的瓦拉东在嫁给富有的银行家保罗·穆西(Paul Mousis)之后,开始全职绘画。她画静物画、肖像、花卉和风景,这些画以强有力的构图和鲜艳的色彩而闻名。她还给儿子画了很多不同年龄的画像。然而,她最出名的是那些坦率自然的女性裸体,从女人的角度描绘女性的身体。这次展出其中的两幅作品,《蓝色卧室》和《穿白袜的女子》。跟那些男性画家笔下的裸女不同,她们更接近现实,不是理想化也不是物化的女性。她们身体健壮,富有生命力,神态姿势自然随意。深处的背景也是日常情景,比如《蓝色卧室》中的女画家,半卧在堆满蓝白花被子的床榻上,她随意的穿着—白绿条纹的睡裤,桃色的吊带上衣—下是丰满圆润的身体。两只丰厚有力的脚掌旁是两本书。画中女子有着不为别人摆姿势的那种自信和自我专注。似乎在读书的间歇中陷入沉思,又像在抽着烟享受自己的闲暇。可以看出,瓦拉东笔下的劳动女性和职业女子,不再需要摆出矫揉造作、取悦于人的姿态,她们展现的是一个正在成长成熟的自己。
瓦拉东在生活上也大胆前卫。一九○九年,瓦拉东开始与儿子的朋友,二十三岁的画家安德烈·乌特(André Utter)发生婚外情,一九一三年与穆西离婚,并与乌特结婚。
瓦拉东从生活到艺术,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二十世纪初期那种的过渡:女性正进入一种新的角色,从画家笔下的模特变成手持画笔的艺术家。
自己的一间画室
艺术家塔玛拉·德·伦皮卡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巴黎艺术界的风云女神,不仅指她那种装饰和立体风格的画独树一帜,她所经营的个人形象也相当成功。画展中有一段当年的录像,这部拍摄于一九三二年的纪录片《一间美好的现代画室》(Un Bel Atelier Modern),就是把这位艺术家作为现代女性的形象代言人。在宽敞的几近奢华的现代房间中,这个有着葛丽泰·嘉宝一般雕塑感面孔的新女性,早餐,为外出化妆,打扮。她就是一部自导自演的电影的主角,光彩夺目。
德·伦皮卡一八九八年出生在波兰华沙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祖母在她少女时期带她到法国和意大利游览,因此爱上艺术。父母离婚后,她住到圣彼得堡有钱的姑母家,有机会结识上流社会的人物时尚,并且很年轻就嫁给了一位律师。一九一七年的革命迫使她一家离开俄国来到巴黎。最初跟那些逃亡的俄裔贵族一样,靠变卖首饰古董维生。同时德·伦皮卡重拾艺术爱好,在蒙帕纳斯的大茅屋画院开始画画。受象征主义画家和她的老师莫里斯·丹尼和安德烈·洛特(Andre Lhote,1885-1962)的影响,非常有艺术天赋的她不到两年就画出了自己的风格:以装饰艺术风格(Art Deco)主打肖像画。她接受作家、演艺人员和流亡贵族的委托画了很多肖像画,成为巴黎挣得最多的女画家之一,而且在艺术圈中声名鹊起。德·伦皮卡的第一场大型展览于一九二五年在米兰举行,由喀斯特尔巴克伯爵(Emmanuele Castelbarco)赞助,在短短六个月的时间里,她为这个展览创作了二十八幅画。通过她不断增长的名声与人脉,她的作品很快在欧洲一些最高级的沙龙中展出。一九二五年,她的自画像《绿色布加迪中的塔玛拉》(Self-Portrait in the Green Bugatti Auto-Portrait)上了德国时尚杂志的封面,短发、长巾、风姿绰约的女画家驾驶着一辆碧绿色的小汽车,是当时最前卫的女性形象。一九二七年,她的《女儿肖像:阳台上的吉泽特》,在巴黎国际美术博览会上获得一等奖。繁忙的社交生活和大量作画,使她无暇顾及家庭,伯爵于一九二八年与她离婚。她也很少见到唯一的孩子吉泽特(Kizette),孩子只是她的画笔下的一个模特。这次画展中的《母子》就是其中之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德·伦皮卡收到了希腊伊丽莎白女王的委托,并为西班牙国王阿方索画画。博物馆开始购买她的作品。一九三三年,她嫁给了第二任丈夫库夫纳男爵(Baron Kuffner),从而确保了她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这对夫妇永久定居美国。在比弗利山庄(Beverly Hills),这个被称为“有两把刷子的男爵夫人”(Baroness with Brush;字面意义:会画画的男爵夫人),为好莱坞的许多明星画过像。事实上,她的画由她自己和女儿经营,非常成功而且高度商业化,因为版权严格,在维基百科上都没法看到这些画作。一九七二年卢森堡博物馆为她举行回顾展“Tamara de Lempicka from 1925-1935”。
德·伦皮卡或者瓦拉东笔下的强健职业女性与这一时期女性生活方式的改变有很大关系。展览特意开辟了一个运动的主题。除了画作,还有很多照片和实物呈现当时新的女性时尚:女性作为运动员,她们在海滩身穿泳衣,她们打网球的矫健身姿—虽然那时候女性还穿着长裙打网球,还有美国歌手号称黑珍珠的约瑟芬·贝克(Josephine Baker)挥杆打高尔夫球。
拥有了自己的一间画室的不止塔玛拉·德·伦皮卡,同一时期跟她一样成功的还有玛丽·洛朗桑。她尝试从后印象派到立体主义多种画风,但同时带着女性特质,很前卫也很受市场欢迎。她与当时男性先锋们,如毕加索和阿波利内尔的友谊也是艺坛佳话。还有一位以女性艺术沙龙画、肖像画出名的画家罗曼·布鲁克斯。这次展览中有她最有名的两幅画作,一幅是她那幅海边黑衣自画像,海岸乌云下的女画家,飞扬的短发,凌厉直视的双眼和黑灰色的长袍外套,即便放到今天也很酷;另一幅是画家给恋人娜塔莉·克利福德·巴尼(Natalie Clifford Barney)画的窗前画像。这幅画像捕捉到巴尼作为活跃知识女性的那种沉静与睿智的瞬间。
与以往艺术画作中对女性的画规和常用的符号不同,这些作品中的女性不再作为装饰性存在,而是意识中心,自我且自信。也因此,女艺术家们往往把自身形象和她们的作品合而为一,而且常常把自我塑造得理想化。
女性作为现代主义的助产士
正如展览中那些女性画作所呈现的,当时漂在巴黎的女性多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出生、在世纪交替的历史时刻亮相的“新女性”,或稍后一些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Flapper”(法语指那些时尚且叛逆的女性)。她们梳着短短的男孩头,穿着短裙,抽烟喝酒,对关于女性的社会成规藐视挑战,很多人还离开家庭和丈夫。英国作家亨利·詹姆斯的小说《黛西米勒》和《一位女士的肖像》刻画的正是这些从英国、北欧、东欧和俄国,还有新大陆美国到欧洲“冒险”的女性。她们多出身上流社会或富裕家庭,受過精英教育,很多甚至有专业的训练,渴望独立,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包括家庭关系。她们一生寻找个人的自由,以及社会和职业上的成就,还有经济上的独立。艺术往往成为她们表达和构建自我的重要手段。
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很重要一个方面就是对自己性别身份的理解与选择。这一时期产生大批写单身女性以及同性恋题材的流行小说和文学作品,小说家柯莱特(Colette)手持香烟,成为《时尚》(Vogue)封面女郎;而男孩式超短发型和衣装,就是因当时维克多·玛格丽特的小说《单身女郎》而流行;还有女摄影家卡恩的很多作品,包括以她自己为模特的,都强调性别身份的双重性、模糊性与流动性。艺术是她们自我的投影、欲望的折射。她们的先锋姿势其实也正是女性自我解放的一部分。这些都是理解为什么那一时期女性创造力大爆发,以及女性风起云涌进入艺术世界的根本原因。
香奈儿(Coco Chanel,1883-1971)的时装最初就是为这些开始活跃在职场和社交场合的独立女性而设计的,不管是香奈儿粗花呢套装,还是简洁优雅的小黑裙。而香奈儿最成功之处在于她自己也是一位時尚偶像和女性先锋,展览中有一幅玛丽·洛朗桑为她画的肖像,用浅粉浅蓝这些温柔烂漫的莫迪色勾勒出一位无比坚强的现代职业女性。
跟香奈儿一样,很多女性艺术家在二十世纪初的艺术市场上也经营有方,比如此次展览中一位从俄国来的女艺术家索尼亚·德劳内,她因和丈夫罗伯特·德劳内一起开启了奥费主义艺术运动(Orphism art movement),而留名艺术史。不过她既是艺术家也是设计师,她的艺术创造也体现在设计、纺织品、时装、戏剧舞台布景等多方面。她把艺术和实用结合起来,是新兴的女性时尚的推动者。一九二五年,巴黎举办国际现代装饰艺术展,索尼亚·德劳内在那里设立了自己时装和家居设计的工作室:“创造力”(Boutique Simultané)。后来德劳内还在巴黎时尚区开了精品店,在艺术和设计领域交叉工作。
从德劳内这个案例可以看出,与以前艺术史只用所谓“杰作”来判断女性艺术家地位的做法不同,这次展览强调女性艺术家在现代主义中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比如她们在演艺、出版、装饰艺术,以及新兴的摄影和电影制作方面的参与和创造。二十世纪的“新女性”有着新的身份,作为记者、作家、画家、摄影师、时装设计师,有她们自己的工作室、精品店、画廊、书店以及沙龙。她们活跃在巴黎的拉丁区,蒙马特和蒙帕纳斯,在画室、咖啡馆、酒吧,还有音乐剧场。她们是各种先锋派的缪斯,红颜知己,甚至是“助产士”。展览中的俄裔女画家玛丽·瓦西里耶娃(Marie Vassilieff,1884-1957)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瓦西里耶娃,二十三岁时移居巴黎,并成为巴黎左岸艺术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九○八年,她在蒙帕纳斯创立了俄罗斯学院(Académie Russe),并于次年更名为瓦西里耶娃学院(Académie Vassilieff)。一九一二年,她开设了自己的工作室。不久之后,玛丽·瓦西里耶娃工作室就成了左岸艺术家聚集的地方,尤其那些来自东欧和俄国的犹太艺术家们。那里挂着马克·夏加尔和莫迪利亚尼的画,还有毕加索和费尔南德·莱格(Fernand Léger)的作品。角落里摆着扎德金(Ossip Zadkine)的雕塑。人们聚集在这里主要是为了寻找同伴,交谈,偶尔才画画。费尔南德·莱格在那儿做了两次关于现代艺术的演讲。但最让人记住玛丽·瓦西里耶娃的是她在一战期间开设的食堂,专门为蒙帕纳斯那些挣扎的艺术家们提供少量餐点和一杯葡萄酒。战争期间,政府实行宵禁,巴黎的饭店和咖啡馆都必须提早关闭,但是,玛丽·瓦西里耶娃的食堂是私人食堂俱乐部,因此不受宵禁管制。结果,她的住所很快就变得拥挤不堪,到了晚上,到处都是音乐和舞蹈。
瓦西里耶娃自己的作品主要是立体派风格,她最有趣的画是那些舞者和她的朋友们的肖像,有让·科克多(Jean Cocteau),还有毕加索和马蒂斯。瓦西里耶娃还因其装饰性家具作品和洋娃娃肖像而广为人知。尽管她的作品从未获得过与她同时代名人一样的地位或价格,但如今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中都可以找到它们。这次展出的就是她为当时的剧场和朋友们设计的木偶和洋娃娃肖像。
女性对现代主义做出的贡献还反映在画廊、书店、艺术市场。就像莎士比亚书店女店主毕奇(Sylvia Beach)为乔伊斯出版《尤利西斯》,斯泰因(Gertrude Stein)为马蒂斯、毕加索和海明威提供沙龙一样,女经纪人和画廊主贝尔特·薇尔(Berthe Weill,1865-1951)也以她自己的方式支持着先锋艺术。
出身犹太中下层家庭的薇尔,年纪轻轻就进入一家古董店做学徒。她在那里学会了经营画廊所需的基本技术,同时也熟知了圈中的艺术家、画廊和经纪人。虽然她最初是学习十八世纪艺术的,但后来发现自己对同时代的年轻艺术家更感兴趣。薇尔是毕加索的第一个经纪人,在一九○○年这个西班牙画家还没来到巴黎时就展览并卖出了他的作品。一九○一年,她用自己的嫁妆在巴黎九区马斯路二十五号开了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小画廊“薇尔画廊”(Galerie B. Weill),称它为“为年轻人开放的地方”。这里主要展出野兽派和立体主义的作品,包括德朗(Andre Derain)、里维拉(Diego Rivera)、马蒂斯都是在这里开始展出,这些作品当时在巴黎也被认为太激进了。一九一七年,她还为莫迪利安尼做了他短暂的一生中唯一的个人展览。
薇尔还经营代理女艺术家比如瓦拉东、沙弥(Emilie Charmy,1878-1974)以及马薇尔(Jacqueline Marval,1866-1932)等人的作品。
薇尔画廊搬了几次家,直到一九四一年因为纳粹的入侵而不得不关闭,目睹并参与了现代主义整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同一时期,薇尔还开了一家艺术书店“librairie artistique”,并定期发行书店通讯。
尽管薇尔手中经营过无数位大师的作品,但她本人一生清贫,晚年生活到了几乎无以为继的地步。一九四六年,巴黎很多画家联合起来拍卖他们的作品为薇尔募捐,让这位令人敬佩的现代艺术的助产士有个比较舒适的晚年。
一九四八年,也就是薇尔去世前几年,法国政府授予她法国荣誉军团勋章(Chevalier de Légion dʼHonneur),以表彰她在现代艺术中做出的贡献。相比同时期有名的艺术商人和艺术经纪人,如沃拉尔(Ambroise Vollard)、卢森博格(Paul Rosenberg)等,薇尔死后几乎默默无闻。但是近些年,人们开始意识到薇尔在艺术史上的意义。二○○七年,毕加索为她画的肖像被定为法国国家珍宝。二○○九年,薇尔一九三三年出版的回忆录在巴黎再版,书名叫《砰,直击!当代绘画幕后三十年(1900-1930)》(Pan! Dans L'œil! Ou trente ans dans les coulisses de la peinture contemporaine 1900-1930),这本书于二○二二年被译成英文,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