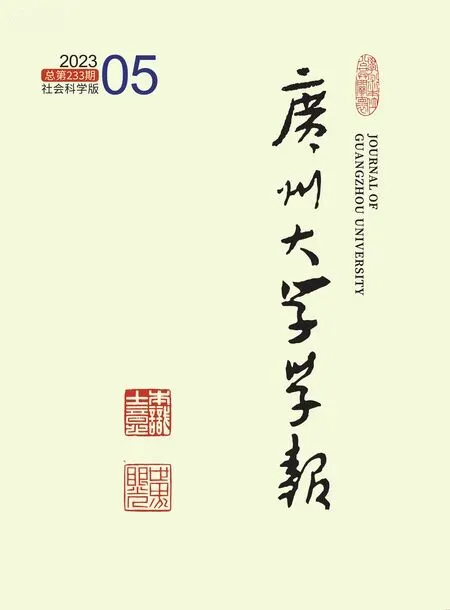犹太作家“见证文学”的圣经根源
王 彪
(《收获》文学杂志社, 上海 200040)
二战后的20世纪40年代开始,世界文坛涌现出一种新的文学形态——见证文学。见证文学的作者都有独特的身份,即自身都经历过重大的人类灾厄:世界大战、种族灭绝大屠杀、集中营、劳动营等等。他们的写作,也都以记录亲身经历的苦难为内容,直抵人类文明与人性的巨大创伤,“见证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自传文学。它指的是那些亲身遭受过浩劫性历史事件的人,作为幸存者,以自己的经历为内核,写出的日记、回忆录、报告文学、自传体小说、诗歌等作品”[1]。
这其中,尤以犹太作家与作品最为引人注目,产生了世界性的重大影响。称得上见证文学杰作的作品,大多出自犹太作家之手,比如普里莫·莱维的《这是不是个人》、埃利·威塞尔的《夜》、凯尔泰斯·伊姆雷的《无命运的人生》、安妮·弗兰克的《安妮日记》等,还有丹·佩吉斯、奈莉·萨克斯、保罗·策兰等诗人的诗作,构成了见证文学的经典,奈莉·萨克斯、凯尔泰斯·伊姆雷和埃利·威塞尔分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与诺贝尔和平奖,更扩大了见证文学的影响力。至于保罗·策兰,现今已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名作《死亡赋格》也已成为见证文学的纪念碑。难怪埃利·威塞尔作为见证文学的代表作家,以犹太人身份在《作为文学灵感的大屠杀》一文中,赋予了见证文学新的文学定义:“如果说希腊人创造了悲剧,罗马人创造了书信体,文艺复兴创造了十四行诗,那么我们的时代则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即见证文学。”[2]
纳粹大屠杀使得600万犹太人失去生命,其中150万是儿童,这为犹太作家提供了最直接的创作资源和动因,让他们拿起笔来,为苦难留下记录。但如果我们仅仅以此作为犹太作家在见证文学中所拥有的特殊位置,而不去考察犹太精神特质与见证文学的特质之间的关系,挖掘其背后更深层的意义,我觉得将会是个严重的缺憾。
本文认为,犹太作家和诗人直面大屠杀苦难的见证文学作品,最根本的内核,乃是犹太民族精神特质的必然表达,有着深刻的犹太历史和犹太文化因素,更有着塑造了犹太历史和犹太文化的圣经根源。
一、记下事实,从记忆开始
真实还原作者亲历的苦难,成为苦难的见证,是见证文学的基本特征,但作者叙写这些苦难经历时,大多时过境迁,须从记忆中汲取,这样,记忆首先成为见证文学的要素;或者说,见证文学首先是从记忆这个入口进入的。犹太人正是被誉为“记忆的民族”,他们从先祖时代开始,一路下来,“亚伯拉罕的信仰、埃及的奴隶生活、先知的言行、贤人的智慧、民族的历史、与圣城耶路撒冷的关系,犹太人靠着‘记忆’将这些继承下来,并告诉子孙过去所发生的一切”[3]。埃利·威塞尔在《作为文学灵感的大屠杀》中论及犹太人与记忆的关系时也说:“我属于记忆的群体。没有人像我们一样记忆,无论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我们的敌人,都没有。我们被告知‘记忆与观察’是同一个词,就像是所有的日子被创造出来,都是为了独一无二的安息日一般,所有的其他词语被创造,都指向一个词——‘记忆者’。”[2]
如此看来,记忆无疑成了犹太民族的精神特质,是颇具“犹太性”的存在。那么,这种精神特质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耶路沙米在他的名著《纪念:犹太历史与犹太记忆》一书中,给出了答案:来源于圣经。耶路沙米说:“希伯来圣经在要求‘要记住’时似乎没有丝毫迟疑。它的命令是无条件地,甚至在没有要求的情况下,记住也总是最关键的。”[4]5
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①
这是圣经《申命记》第六章记载的诫命,经文的语气非常强烈,它可以说是犹太信仰的核心要义,即犹太人的信仰告白,所谓的《听命诵》,犹太人每天都必须诵读,而且类似的意思在圣经中重复出现。耶路沙米分析说:“动词‘记得’及其各种词尾变化形式在《圣经》中总共出现不少于169次,通常由以色列或者上帝作为主语,毕竟保存记忆是两者义不容辞的责任。”[4]5
记忆早在圣经时期就进入了犹太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历史文化,正如哈罗德·布鲁姆所言:“犹太人凭借一种宗教而成为一个民族,而不是从一个民族变成一种宗教。”[5]12宗教信仰先于民族而存在,这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它与记忆的关系也被上帝的话语确定下来,耶路沙米指出:“古代以色列知道什么是从上帝而来的,知道上帝在历史上做什么。如果的确这样,那么记忆对以色列的信仰而言就十分重要,关乎信仰的终极存在。只有在以色列,‘要记住’成为一条宗教命令,要求整个民族遵行,它的影响无处不在。”[4]11
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犹太人失去家园,没有祖国,流散世界各地,遭受无尽的逼迫与痛苦,然而这个民族没有被同化,没有因为分散而消散,反而顽强地传承着自己的信仰与文化,这其中记忆的保存尤为重要。犹太人通过宗教仪式、祷告、节期等把记忆保存下来,反复诵读,铭记,使之进入到他们的生活之中,比如安息日和逾越节对出埃及的记忆,住棚节对旷野40年的记忆,等等,记忆构成了犹太历史,与犹太民族的生存密切相关。耶路沙米这样说:“的确,历史上以色列民族大部分时间都流散于世界各地,若要理解该民族的生存,我认为以色列记忆的历史是十分重要的,尽管大部分记忆已被遗忘,但记忆仍然被书写着。”[4]6
这其中,犹太人的记忆也包含着苦难记忆。从出埃及开始,到进入迦南地后不断受到外敌侵扰,再到大卫和所罗门王朝昙花一现的繁荣,随后南北国分裂,直至北国亡于亚述,南国亡于巴比伦,耶路撒冷和圣殿遭到毁灭,圣经记载了众多先知向以色列人说话,要他们记住犯罪的后果,记住国破家亡的苦难经历。《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等尤为哀痛,“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她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她的”。可以说,犹太记忆也是一种创伤记忆,在他们流散世界各地将近2000年的时间里,这种记忆在他们的信仰生活中与犹太历史融为了一体。
犹太人活在记忆的历史里,记忆也造就了犹太民族的精神特质,使得每一个犹太人都承担着记忆的使命,不仅要记住圣经里的诫命,也要记住上帝的作为,记住犹太人的苦难。记忆铸造了以色列历史,以色列历史反过来也成了犹太人的记忆,进入他们的生活与文化,永存于他们的世世代代。
到了20世纪,二战和大屠杀相继发生,一大批犹太作家和诗人应运而生,扛起了见证文学的大旗,他们的思想情感深处,他们的犹太特性背后,无疑涌流着与犹太人血肉相连的圣经根源。换句话说,犹太作家的见证文学,乃是圣经塑造的记忆民族对苦难所作的现代回应。
汉娜·阿伦特认为,记忆是一种强有力的认知模式。她在《过去与未来之间》里比较了希腊历史观与希伯来历史观,对两者作出区分,她说希腊史学关注的是荣耀与伟大,而犹太记忆与这种历史观相反,他们“认为生命本身是神圣的,比世界上任何事物都神圣,并且人是地球上的至高存在”。[6]
在这样的视野下,记忆又与生命连在了一起。圣经要以色列人记住诫命,记住苦难,目的是为了保全他们的生命。《申命记》强调说:“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
纳粹集中营里的焚尸炉,焚尸炉烟囱上冒出的烟和火星,对犹太人印象至深。这种恐怖的记忆深入骨髓,无论走到哪里,无论过去多少年,犹太人都不会忘记这个噩梦,如同不会忘记犹太历史上任何一场大灾难一样。从灾厄中死里逃生的幸存者们,他们担负起记忆的责任,记下了奥斯维辛,记下了无数个死亡集中营,那些最黑暗的地狱;记下了毒气室,记下了堆叠成山的尸体,记下了被绞死的孩子,记下了活着的婴儿被扔进烈焰滚滚的深沟;也记下了人性的脆弱,囚犯间的彼此伤害,亲情的扭曲,甚至骨肉至亲的背叛……以至于他们发出愧疚的哀叹,在集中营里,最优秀的人都丧命了,最糟糕的人却幸存了下来;受害者反而耻于生而为人,因为正是人类发明了集中营。
一切都恐怖邪恶到了不真实,却又是最真实的,这种真实也构成了记忆之恐怖,记忆所承载的生命之沉重,是人所难以承受的,这些见证文学的作者,都是以自己的生命来记忆生命,用生命来写出生命,也难怪,莱维与策兰最后都选择自杀来给自己的记忆画上生命的句号。
二、遗忘,意味着消灭生命
记忆的反面是遗忘,犹太作家们的见证文学,除了用记忆记下苦难,保存苦难,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反抗遗忘。记忆与遗忘,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在见证文学里,我们常常会看到,犹太作家以“不会忘记”的方式,来强化记忆,反抗遗忘。
威塞尔的《夜》是反抗遗忘的代表作,他亲历父母和7岁的妹妹死于集中营,这一切都强烈地烙刻在他的记忆里,让他永远不会忘记: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夜,我们在集中营度过的第一夜,这一夜让我的一生成为漫长的黑夜,被加上七重封印。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烟。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孩子的脸,在静默的蓝天下,他们的身体渐渐蜷曲。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火焰,从此以后一直在消耗着我的信仰的火焰。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黑色的沉默,永远剥夺了我生的欲望的黑色沉默。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时刻,我的上帝、我的灵魂被谋杀,我的梦想化为荒漠。
我永远不会忘记,哪怕注定与上帝活得一样久。永远不会。[7]
这些排山倒海般的“我永远不会忘记”振聋发聩,散发着骇人的力量,威塞尔坦陈他如此用自己生命来反抗遗忘的目的,他说:“遗忘意味着危险和侮辱。忘记死去的人相当于再一次杀了他们。如果除去屠杀他们的人及其同伙,没有人应对他们的第一次死亡负责,那么,我们必须对他们的第二次死亡负责。”[8]167这也是我们在上面已论述过的记忆与生命的关系,如果我们没有记住,忘记了大屠杀中遇难的人,等于第二次杀了他们。不仅如此,威塞尔还有更深层的目的,他说:“这是一个证人的一生,他相信从道德和人性的角度,自己有义务阻止敌人抹去人类记忆中的罪恶,在死后赢得最后的胜利。”[8]156
威塞尔认为,永远不会忘记,也是反抗纳粹德国抹去人类记忆中的罪恶,如果我们遗忘了的话,纳粹德国便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到了最后,他们的目标则是留下一个成为废墟的世界,在其中犹太人似乎不曾存在过。……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向犹太人发起的这场战争同样关系到犹太宗教、犹太文化以及犹太传统,即犹太人的记忆。”[8]156-157
这便是威塞尔害怕遗忘,也痛恨遗忘的原因,在威塞尔的观念里,纳粹消灭犹太人,最致命的是最终消灭犹太人的记忆。而记忆,正是犹太人在世界上存在的证据。威塞尔要顽强地写下记忆,要成为一个证人来作证。
有关遗忘与记忆的消灭,乃至生命的抹除,犹太作家对此是非常警醒的。诗人丹·佩吉斯以写集中营苦难的“恐怖诗”闻名,其中一首《训诫》,借用圣经《约伯记》里受苦的义人约伯来比拟集中营遇难的犹太人。佩吉斯说,最可怕的是约伯从不存在,而且只是一个寓言。
在犹太人的经典《塔木德》里,有一个注释,辩称说“约伯从未存在过,只是个寓言”。佩吉斯用这首诗予以回应,人受难并非是最可怕的事,受难的事实被抹除才是最可怕的。著名评论家詹姆斯·伍德在为莱维的《这是不是个人》写评论时,把莱维的作品与佩吉斯的《训诫》连在一起,来探讨见证文学反抗遗忘的意义,伍德敏锐地指出:“帕吉斯的诗句意思是:‘约伯的确存在过,因为约伯在死亡集中营里。受难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更可怕的是一个人受难的事实被抹消了。’就是这般,莱维的写作坚称约伯存在过,不只是一个寓言。他的明断是本体论的、有道德意味:这些事情都发生过,一名受害者见证了这一切,这些苦难永远不该被抹消或者遗忘。”[9]
莱维的写作,与威塞尔一样,同样是反抗遗忘,记住死难者,就是记住生命。作为犹太人,莱维与威塞尔等作家所表现出的思想特质,跟犹太民族精神特质息息相关,这背后也有圣经根源。耶路沙米在《纪念:犹太历史与犹太记忆》里,分析了记忆在圣经里的重要意义以及记忆与以色列历史的关系之后,把目光转向了“遗忘”:“而‘记得’的意义也需要凭借它的反义词‘遗忘’去获得补充。当《圣经》严令以色列要记得的时候,同时也是在敦促其不可遗忘。自圣经时代以来,这两条命令在犹太人中具有持久的影响。”[4]5-6
耶路沙米进一步对“遗忘”作了深入的论述,他说:“圣经只知道遗忘是可怕的。遗忘,是记忆的对立面,总是负面的,是首要的罪,其他罪过会因它而来。或许能在《申命记》第8章中找到最权威的章节:
“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申命记》8:11、14、19)
“这里令人震惊的前提是,整个民族不仅被警戒要记得,而且要对遗忘负起绝对责任,这个前提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所有告诫都强调‘要记得’,不要‘忘记’,犹太人正是这样被告知的。”[4]142-144
正因为圣经里的诫命,不可忘记,警醒了犹太人对遗忘的反抗,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记忆与不可忘记,这一体的两面,同时塑造了犹太人的民族精神特质。作为犹太作家,他们身上也不得不打上圣经的烙印,这与他们信不信上帝,是不是敬虔的犹太教徒没有太多关系,只要是犹太人,他们便都活在圣经所塑造的犹太历史和犹太文化中,正如哈罗德·布鲁姆所断言的:“每一位自觉的犹太作家,在他们作品的每一页上都有着希伯来圣经的影子。”[5]19哈罗德·布鲁姆接着拿不信上帝的弗洛伊德来作例证,他说:“只要你能够清除掉弗洛伊德巧妙制造的那些虚假的表象,那么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作品的每一页上也有希伯来圣经的影子。无论在何处,没有任何一种文学文本能像希伯来圣经那样强大。”[5]19
不过,记住与不可忘记,在大屠杀灾难中,或者在集中营的苟且偷生与逃亡的九死一生中,有时却以某种否定犹太身份的方式反讽地表达出来。佩吉斯写过一首诗《对穿越边界的指导》,一个被关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渴望和幻想着逃亡,在记住与不可忘记之间,他的身份发生了错乱。“幻想的人,走吧。这是你的护照。/你不能记忆。”诗人直截了当地告诫,要想逃亡,要想活命,作为一个犹太人,不能对自我有记忆,真实的犹太人的“你”是不存在的,甚至连生理特征也要改变,黑眼睛必须变成蓝眼睛。同时,“你”必须有另一个身份,这个身份却是不能忘记的。“现在你有了一件体面的大衣,/一个修补过的身体,一个在你的嗓子里/准备好的新名字。/去吧。你不能忘记。”[10]
在这里,因着身份的错误而发生了记忆的错乱,也意味着,人之为人,我之为我,已被彻底打碎,作为人的实质被置换了,也即否定了。当这个人已经不是这个人的时候,人也就从本质上消失了。如果从群体角度来看,要一个“记忆的民族”不要记住自己,却去记住别的民族的身份,那么,这个民族的存在还有意义和实质吗?佩吉斯的这首诗,也许真有个体和群体记忆与不被允许记忆之间的双重含意,它的深层意旨,似乎也可看为犹太民族记忆的除灭和肉体的除灭,就像威塞尔在《写给新版读者的话》里说的:“到了最后,他们的目标则是留下一个成为废墟的世界,在其中犹太人似乎不曾存在过。”[8]156-157
这正是“记忆的民族”从圣经根源而来的人性与文化的深度,乃至于人类学的深度。佩吉斯的这首诗从反方向强化了犹太人的记忆与不可忘记之间的关系,也惟有一个生活在记忆历史与记忆现实里的民族,从圣经根源领受到记忆之于生命、之于民族和人类的意义,他才能够切近记忆的本质,也即人的本质。用圣经真理来说,记忆等同于生命。有记忆,便有了生命。
三、记忆传承,面向未来的使命
因为反抗遗忘,就必须把记忆传承下去。阅读犹太作家的见证文学作品,我们会发现,他们的记忆是既向着过去,也向着未来。记住,不会忘记,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把记忆传承下去,也就是为了明天,为了未来。在犹太作家心里,这个明天和未来都是非常具体的,那便是孩子们。
相信这是威塞尔、莱维等纳粹死亡集中营幸存者的共同心愿:留下记忆,反抗遗忘,为了孩子,为了明天。但这话说起来容易,其实对纳粹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来说,具体做起来却是非常艰难的。意味着他们要把自己彻底裸露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包括他们肉体上所受的灭绝人性的折磨,他们内心的恐惧和软弱,甚至人性中的怯懦和猥琐。这无疑是场羞辱的展览。一个暴露集中营黑暗的人,可能而且必然也是暴露自己黑暗的人。
威塞尔不光写下他亲眼看见母亲和7岁的小妹妹离开时,自己的软弱无力,而且他更深刻地揭示了自己的自私阴暗:父亲病重,被集中营军官毒打,父亲呼叫儿子的名字,威塞尔却一声不吭,他甚至为父亲终于死去,自己卸下了包袱而松出一口气。
莱维的写作也是如此,他承认集中营的幸存者是最糟糕的人,最优秀的人都丧命了。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把自己也钉上了耻辱柱,即他也是那个最糟糕的人。如果没有道德瑕疵,他怎么可能在那种邪恶的环境里活下来?要知道,当时他乘坐的那辆共有12节封闭货运车厢的火车上共有650人,他们一到达奥斯维辛,就有500多人被“淘汰”杀死,最后,只有3个人生还,而莱维就是这3个人中的一个。
让他们战胜屈辱,勇敢地成为见证者,我觉得有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圣经传统里的罪人观念。在圣经里,没有完美的人,哪怕是如雅各这样的犹太人的先祖,上帝亲自给他改名为以色列;大卫这样伟大的君王,合上帝心意的人,他们也都会犯罪,他们也都有道德缺欠,不过,有一点很了不起,他们也都愿意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在《纪念:犹太历史与犹太记忆》一书中,耶路沙米论述了中世纪犹太记忆的特点之后,指出他们对中世纪历史灾难最重要的回应,是“忏悔祷文”的完成,“祷文作者通过这样的作品表达出对犹太群体最深的情感,面对神降天谴或是有关神的正义问题,表达出悔悟之情,为苦难的结束而祈祷,为受压迫者的复仇而祈祷。从效果上看,这无疑是对历史事件的‘纪念’”。[4]58
我认为,犹太人的这种历史传统,对犹太作家挺身而出,勇敢袒露一个幸存者的屈辱与软弱,甚至罪孽,是有其民族文化精神的因子的,毕竟,犹太人是全世界唯一有赎罪日的民族,是到今天都要在赎罪日全民禁食祷告的民族,他们的自我省视里有着圣经根源。虽然从圣经角度来看,常常是以色列人自己犯罪,上帝惩罚,需要他们忏悔;而大屠杀的苦难,则是外加的邪恶,他们是无辜的。但无辜者因着邪恶的逼迫而堕落,或者露出道德裂罅,那么,以圣经的圣洁公义标准,他们仍然无法自称为义,这方面圣经有最经典的例子,义人约伯的受苦。约伯坚称自己不是因为犯罪遭受苦难,但却坦陈他也是个罪人,绝非完全。可以说,约伯是义人遭难的圣经故事原型,对犹太人对待苦难的思维和态度有着特别重大的影响。
当然,威塞尔、莱维等犹太作家从他们自己的认知来说,最直接最重要的写下记忆与事实的动因,也就是上面提到的,为了将来,为了孩子们。威塞尔在《写给新版读者的话》里说:“对于一个想要成为证人的幸存者来说,这个问题非常简单:他有责任为死去的人,同时也为活着的人——尤其是下一代——作证。我们无权剥夺他们了解属于集体记忆的过去的机会。”[8]167哪怕为此付出巨大的自我牺牲,威塞尔坚定地说:“如果一个证人不惜自我折磨选择作证,他是为了今天的年轻人,为了明天将要出生的孩子:他不愿自己的过去成为他们的未来。”[8]168
在这里,威塞尔涉及一个观念,即集体记忆,威塞尔是把自己看作所有受害者中的一员,他个人的记忆也属于整个受害者群体的集体记忆,而所有犹太人无疑都是受害者。这个概念威塞尔曾经讲过无数次,他说:“并非所有受害者都是犹太人,但所有犹太人都是受害者。”[11]179
如此一来,见证就不是个人的事,而是为了集体记忆,一个受难的个人也必须为集体的受难负责。威塞尔为了下一代的说法,要是站在犹太民族精神特质的角度去看,其实它的背景与解读跟我们通常理解的是不一样的。威塞尔固然看重下一代,我们今天把苦难揭示出来,为的是防止悲剧重演,让下一代将来不吃二遍苦。但威塞尔这段话的意思,更包含了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关系,记忆的延伸与生命传承的关系。如何保存记忆,永远不会遗忘呢?只有把记忆传承下去,让个人记忆成为集体记忆,让这一代的记忆进入下一代的记忆,然后代代相传,直到永远。保存记忆最好的方式,是使记忆成为历史,成为一个民族的历史叙述,再被孩子们记忆与叙述。
这似乎又回到了圣经,回到了圣经所塑造的以色列的历史传统中。如果我们说犹太人是个“记忆的民族”,同样,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犹太人还是个世代传承记忆的民族,将子子孙孙融入记忆历史的民族。
在圣经里,我们会留意到,有关记住与不可忘记的诫命,常常是对着以色列人说的同时,又要求他们教导儿女,让儿女也记住。比如《申命记》第4章有关遵守诫命的吩咐:“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
如此这般相似的内容,圣经说了无数遍,可以说不厌其烦。而且这样的要求,也常常落实在具体的实际操练中,使得以色列人和他们的子孙都可以在遵守的过程中学习记住。耶路沙米论及犹太人集体记忆的构造方式时,认为是通过诗歌创作与吟诵,比如在“阿夫月初九”所作的哀歌:
有火种在我里面点燃,当我记起——当我离开埃及的时候,
而我作起哀歌,当我想起——当我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
摩西唱着一首永远不会忘记的歌——当我离开埃及的时候,
耶利米在悲痛中哀悼——当我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4]55
耶路沙米指出:“诗歌中最醒目的是从头至尾使用第一人称单数(‘我离开埃及’‘我离开耶路撒冷’)来代替祖先的‘他们’或者代表一种共同体的‘我们’。”[4]56这是“对身份认同的唤起”。于是,“我”就这样被融进了集体记忆里,集体记忆里的群体,这时候也成了“我”的记忆。
犹太人记忆的传承,尤为重视仪式,特殊日子里哀歌的吟唱,就是仪式的一种。再比如节期,也是记忆传承的重要方式,像三大节期中的逾越节,以色列人所遵守的诫命里就有着传承的使命,《出埃及记》教导说:“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礼。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礼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
这便是逾越节的观念与功能,让逾越节成为犹太群体记忆,然后传承下去。逾越节精心布置的筵席也是承载记忆功能仪式的一部分,耶路沙米总结说:“逾越节《哈加达》中有一句重要的塔木德格言最有力地表达出这样的观念:‘让每一代人中的每一个人都要自认为他是从埃及出来的。’”[4]57
四、从民族叙事到人类叙事
我们研究犹太作家的见证文学作品时,会发现一个相当有意思的现象,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是种族灭绝,他们憎恶犹太民族,认为整个犹太民族都是卑劣低下的,必须彻底消灭。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犹太人并没同样用种族主义予以回应,用种族优劣的理论反过来进行辩解,更没有宣扬仇恨,鼓动报复,血债血还。
行文至此,我们不妨来探讨一下犹太人对纳粹大屠杀的看法,他们是从什么角度来看这个悲剧的?首先是有关人性的思考。莱维在谈到自己为什么写《这是不是个人》时说:“本书的宗旨并非为了提出新的诉讼;它无非是提供了一些资料,有助于对人性的某些方面进行冷静的探讨。”[12]一个受了纳粹德国这么多苦的人,他的记忆,他的见证,却是为了帮助人们“对人性的某些方面进行冷静的探讨”,也就是说,莱维最关注的其实是人性问题。
同样,与莱维有相似经历的威塞尔,他的自传性作品《夜》,勇于直面人性的脆弱、扭曲和堕落,有人故意不去照顾自己年老体弱的父亲,想要“摆脱这份负荷,甩掉这个可能会减少自己生存几率的包袱”。[11]122威塞尔用绝大的勇气,同样毫不隐瞒地写出了他自己与父亲在集中营里的关系,包括心理感受,他与那个视父亲为包袱的不孝之子其实是同一种人。
威塞尔还对人类文化进行了反思,在他看来,奥斯维辛不仅是一个政治事实,而且是一个文化事实,是非理性的蔑视与仇恨的顶点。1986年威塞尔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把个人的关注化为对一切暴力、仇恨和压迫的普遍谴责。
200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凯尔泰斯·伊姆雷,他的自传体小说《无命运的人生》也是从文化角度,来反思大屠杀的机制与思维,提出了更尖锐的问题:大屠杀事件结束了,但大屠杀文化也就此结束了吗?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这样评价说:“对于凯尔泰斯而言,奥斯维辛并不是存在于西方历史之外的一个例外的事件,奥斯维辛是现代生存方式中人类堕落的最为根本的真实的表现。”[13]
除了人性和文化等方面的反思与批判,犹太作家的见证文学还把大屠杀看成既是犹太人的悲剧,也是全人类的悲剧。比如佩吉斯的一首小诗《证词》,好像一个人在法庭作证,他为什么被杀死,在焚尸炉里化为一道烟?诗人一开始先肯定杀人者是人,不是别的野兽之类的东西:“不不:他们当然是/人:制服,靴子。/如何解释?他们也是按照/造物主的形状来创造的。”但“我却是一个影子”,虽然造物主“凭着他的仁慈,没有赋予我必死的东西”,然而无济于事,我最终化为一缕烟,飘向天空,“不再具有上帝的形象,与相似性”[10]。对于这首诗,威塞尔说到《夜》的写作时的一段话可以当作注脚:“在那里,无人性的恰恰是人,穿制服、守纪律、有教养的人是来杀人的,而目瞪口呆的孩子、精疲力竭的老人则是去送死的。”[8]158
我觉得,这首诗代表了犹太作家和诗人见证文学作品的起点,他们首先把纳粹和自己都看成是人,这是人对人的毁灭,所以更具悲剧性,而且,甚至进一步说,这还是亲人之间发生的悲剧。
在这些车载货物中
有我夏娃
和我儿子亚伯
如果你看到我另一个儿子
亚当之子该隐
告诉他说我——[14]
这首短诗题目叫作《用铅笔写在封闭式火车厢中》,佩吉斯的名作。封闭式火车厢,显然指纳粹运送犹太人的闷罐子火车,在这列死亡列车里,诗人以人类之母夏娃的口吻诉说,儿子亚伯,此处当是隐喻犹太人,另一个儿子该隐,自然指的是纳粹德国,他和亚伯,也就是犹太人居然是亲兄弟。自相残杀的,原来是一家人,母亲也被装进闷罐子火车,送往万劫不复的地狱。诗句戛然而止,好像还没结束,寥寥数行,把民族苦难上升到人类苦难,以人类叙事而非民族叙事来看待大屠杀灾难。
犹太人的这些认知背后,有着圣经根源,这又是显而易见的。圣经里的创世故事,包括伊甸园的故事,亚当、夏娃、该隐、亚伯的故事,正是人类和家庭最早起源以及犯罪的故事。人类最初是从一个家庭开始的,彼此都是亲人,是完全平等的,而且是相爱的关系,人类的相互残杀是亲人之间的杀戮,是对平等的爱的关系的践踏与毁灭,这是人类的悲剧。圣经提供了犹太作家这样的思想维度,远超纳粹种族主义的偏狭。
这里涉及到圣经文本的特质。一般说来,圣经是以色列民族叙事,但圣经开篇的第一卷《创世记》却提醒我们,其实,圣经首先是人类叙事,或者说,是人类叙事视野下的以色列民族叙事,因为圣经叙事的终极视觉是属于上帝的,圣经叙事理所应当成为人类叙事。这样,我们便能理解,以色列人所讲述的自己民族的故事,包括以色列人的人性、历史、文明,其实也在揭示着人类普世的人性、历史、文明,以色列叙事,也即人类叙事,这是两者之间的关系。所以,当我们研究犹太作家见证文学的圣经根源时,我们总能发现,圣经的故事原型,常常成为他们的叙事方式与叙事意义的文本内核。
上面说的伊甸园兄弟残杀故事,人类的第一桩凶杀案就是典型的一例,另外还有约伯的故事、出埃及的故事等,这些故事原型都是犹太作家将民族叙事转化为人类叙事的关节点与通道,其意义有时候超越了文学,而扩展到文化、哲学、政治等领域。比如奈莉·萨克斯的名作《噢,烟囱》,把《约伯记》里约伯说的话作为题记:“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上帝。”以此表明,所有受难的犹太人都是约伯。
噢,烟囱
为耶利米与约伯的尘土铺设的自由之路——
是谁设计了你们且一石一石地砌筑
这为烟中之逃亡者铺设的道路?[15]
约伯既是义人的同义词,也是苦难的代名词,他变成烟从烟囱里消散,把犹太民族叙事,带入了人类叙事的情景中,因为约伯的故事是普世性的,义人与苦难也都是普世性的,萨克斯因而完成了从犹太民族苦难到人类苦难叙事的转换。
实际上,只要我们追溯圣经根源,总能在犹太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中看到这种转换的出现,有时不一定是故事原型,哪怕一个名字,一个地点,也可触发民族与人类的关联。比如保罗·策兰的诗,使用圣经里的名字,常常点石成金,达到不同凡响的效果。在他著名的《死亡赋格》里,他将德意志民族的金发玛格丽特与犹太民族的灰发书拉密并列在一起。书拉密是圣经《雅歌》里的秀美少女,被看作犹太民族身份的象征,也是美好爱情的象征。《雅歌》里的爱情,也寓意上帝与以色列的爱,特别圣洁。在犹太传统中,逾越节期间要诵读《雅歌》,以此表达上帝与以色列永远的爱。
策兰用“你的灰发书拉密”这个意象,将犹太人在大屠杀中的惨状活生生地揭示出来。美丽少女书拉密的灰发,是焚尸炉里灰烬的颜色,意象的冲击力震慑人心,犹太民族美的生命被毁灭了。书拉密又是爱的少女,也标志着爱的毁灭。进而,书拉密代表着以色列与上帝的关系,盟约里的爱情,诚如《雅歌》所吟唱的:“爱情,众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由此可见,纳粹要摧毁的是何等宝贵的生命与爱。借着圣经《雅歌》这卷爱的经典,也可以说借着人与人之爱、人与上帝之爱的故事原型,策兰把犹太民族大屠杀中的死亡悲剧叙事转化为人类悲剧叙事,并且有着形而上的神学意义。
至此,我们仍需继续探究,犹太人为何能把本民族的灾难讲述成全人类的灾难?他们固然是从一个族群出发,但最后的归结点却不是具体的族群和国家,而指向一个普世的世界。从我的观点来看,同样因为他们的圣经根源,除了圣经的人类叙事视角之外,还有圣经所建造的普世价值观。早在远古时代,摩西在他的《出埃及记》里,便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讲述为一个民族摆脱奴役地位,获得自由的故事,以此昭示了人类的自由之路。
曾任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的阿巴·埃班正是这样表述的,他在《现代以色列——人类精神的一次伟大求索》的著名演讲中,开宗明义地说:“不论以何种严肃的历史眼光审视,摆脱埃及人的奴役都应视为人类前进过程中一个真正的巅峰。用亨利·乔治的话说,就是:‘从狮身人面像(斯芬克斯石像)的脚爪之间迸发出了人类自由,出埃及的号角无畏地宣布了人类的权利。’……出埃及是人类民族解放史的最初一幕,也是经典一幕,以色列人为了争取自由作了首次抗争。对这一事件的记忆一直激励和鼓舞着后世争取民族独立的各种运动。”[16]
从故事原型来说,出埃及也许是人类最共通的争取自由的经典之路,以色列人自己也围绕着这个故事,讲了几千年。从出埃及出发,以色列几度经历国破家亡,圣殿被毁,最终失去家园,犹太人流散世界各地,寄居各国,直到1948年重新建国,回到应许之地,他们出埃及的故事始终没有断绝,故事的内核也没有改变,正如他们在国歌《希望》里所唱的:“两千年的希望,/不会化为泡影,/我们将成为自由的人民,/立足在锡安和耶路撒冷。”这与出埃及一脉相承。
犹太人正是如此看待他们的民族历史和历史叙事的,他们的故事,就是人类的故事。也因此,大屠杀叙事,同样变成了人类叙事。不光是犹太作家和诗人善于把民族故事讲成人类故事,犹太的历史学家写以色列通史,也喜欢把犹太民族历史看成人类历史;或者说,是透过人类历史的大视野去写的。丹尼尔·戈迪斯的历史名著《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其序言的标题即为:一个壮观的人类故事。阿巴·埃班为复国后的以色列发表演说,标题也是《现代以色列——人类精神的一次伟大求索》。
以色列的故事,便是人类的故事,这个问题非常值得关注的另一面是,犹太人为何不是去强调犹太民族的独特性?他们的与众不同?反而更愿意把犹太民族融于全人类之中?像萨洛蒙·马尔卡在《创造:以色列历史的70天》引言里说的:“这个民族与其他民族别无二致,所有民族所珍视的,任何一个民族也都会珍视。这难道不也是那些开拓和向往这片应许之地的人,所梦想的目标吗?”[17]
圣经对以色列人的定义,乃是上帝所拣选的,《申命记》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民数记》则说以色列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这确实是犹太人的独特。但这个独特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让他们与别的民族不一样,恰恰相反,是让他们代表所有的族群。用犹太哲人列奥·施特劳斯的话说:“如果犹太人在一定意义上是被拣选的,那么犹太问题就是人类问题,即社会或政治问题最显著的象征。”[5]2
综上所述,犹太作家见证文学的圣经根源,首先与记忆密不可分,圣经中上帝吩咐和命令以色列人“记住”“不可忘记”,为犹太作家的见证文学提供了记下事实、反抗遗忘的坚固基石。同时,作为被圣经所塑造的“记忆的民族”,犹太的记忆历史也使得犹太作家对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怀有责任,将记忆一代代传承下去,这也成为他们不让悲剧重演的写作动因和勇气的来源。最后,圣经中人类叙事的视角与以色列民族叙事相结合的文本方式,同样成为犹太作家把民族悲剧叙事提升为人类悲剧叙事的圣经根源。
【注释】
① 文中所引《圣经》经文,均出自和合本《圣经》。
——论《约伯记》的“苦难”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