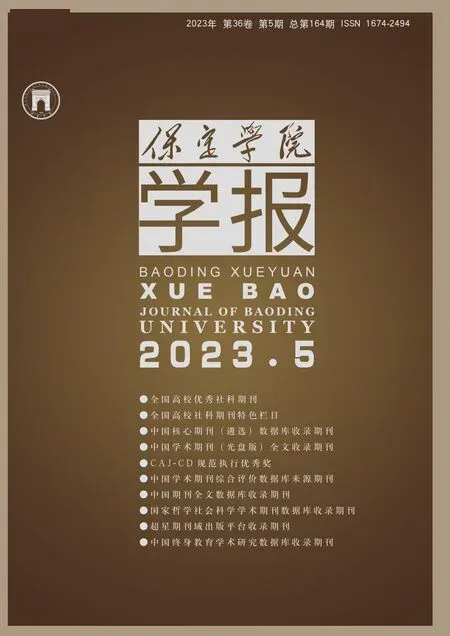清刘宝楠、刘恭冕《论语正义》校雠学论析
孙 靖
(安徽医科大学 人文医学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2)
刘宝楠(1791—1855年),字楚桢,号念楼,扬州宝应人,撰有《论语正义》二十四卷、《汉石例》六卷、《宝应图经》六卷、《念楼集》十卷、《愈愚录》六卷等,与仪征刘文淇齐名,时人号称“扬州二刘”。在学术上,扬州宝应刘氏有研究《论语》的家学传统,刘宝楠从叔父刘台拱撰有《论语骈枝》,为清代《论语》研究力作。刘宝楠少从刘台拱受学,精研群籍,选择《论语》为研究方向自然是情理之中。然刘宝楠撰写之意当始于道光八年(1828)与刘文淇、陈立等人的相约撰著之会,据刘恭冕《论语正义后叙》所言:
及道光戊子,先君子应省试,与仪征先生文淇、江都梅先生植之、泾包先生慎言、丹徒柳先生兴恩、句容陈丈立始为约,各治一经,加以疏。[1]下册797
此后发愤著述,至咸丰五年(1855)完成前十七卷。次年,其子刘恭冕(1824—1883年)接续撰著之业,完成后七卷,并于同治四年(1865)完成全书的撰写工作,共计二十四卷。至于刊刻时间,一般认为是同治五年(1866)①可参杨菁《刘宝楠〈论语正义〉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6年。而陈鸿森经过考证,以为当刊于光绪初年,参陈鸿森撰《刘氏〈论语正义〉成书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5本,1994年。。
刘恭冕不仅完成了全书后七卷的校注工作,更增述八条《论语正义凡例》(下文简称《凡例》),对《论语正义》(下文简称《正义》)的撰写起到了提纲挈领的指导作用,其中多条与校勘有关。据《凡例》所言,《正义》所用经文及注文,皆据宋人邢昺《论语疏》。对于其他版本,如汉、唐、宋三代石经中的文字异同,皆纳入《正义》之中。但对于高丽本和足利本,因其妄增文字而难言可信,故摒弃而罕见征引;至于其中与其他版本相合者,则引以为己用。对于前人征引《论语》及孔子言论与今本《论语》异同之处,由于前人已经进行了相当充足的研究,且考证精博,故《正义》予以省略。《凡例》曰:
古人引书,多有增减,盖未检及原文故也。翟氏灏《四书考异》,冯氏登府《论语异文疏证》,于诸史及汉、唐、宋人传注各经说文集,凡引《论语》有不同者,悉为列入,博稽同异,辨证得失。既有专书,此宜从略。汉、唐以来,引孔子说,多为诸贤语、诸贤说。或为孔子语者,皆由以意征引,未检原文。翟氏《考异》既详载之,故此疏不之及。[1]书前1-2
可见刘氏于前人成就及古书体例极为精熟,这保证了《正义》的高质量校勘水准。
至于刘宝楠撰述的最大动机,则是来源于其对先前《论语》注本的不满。他认为皇侃《疏》“多涉清玄,于宫室、衣服、诸礼阙而不言”,邢昺《疏》“衍文衍义,益无足取”,因而需要复古溯源,探得汉代《论语》之貌,存书中名物典章、文字训诂,并以此发挥疏解义理。《论语》至汉代,有齐、古、鲁三家之说。三家篇章虽各有异同,文字也颇有差异,实则同源异流。郑玄以《张侯论》为底本,并以《古论》校之;而《张侯论》以《鲁论》为底本,兼采《齐论》而成。故郑玄实以《鲁论》为主,兼采《齐论》《古论》;郑玄之后何晏则融合孔安国、包咸、周生烈、马融、郑玄、陈群、王素七家以成《集解》。郑玄遇校改文字,必有注文以明之;而何晏则随意改动,无校改说明——这是造成三家《论语》亡佚的重要原因[2]。因而在整部《正义》中,刘氏校勘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关于齐、古、鲁三家《论语》的异同,尤其是文字上的差别,这也成为我们分析刘氏校勘方法和成就的逻辑起点。
一、荆山之玉:《论语正义》的校勘方法和成就
刘氏父子结合《论语》曾有齐、古、鲁三家不同传本的事实,将三家异文的梳理作为工作重心,并由此而及,推测异文来源,考察他书征引异文,同时对篇章、作者等问题进行了论证,于前人之说多有纠正。
(一)辨析通假
汉代《论语》因手抄口传造成的《齐论》《古论》《鲁论》的文字差异,或为古今,或为异体,或为误字,而尤以通假居多,如《论语·里仁》:“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正义》曰:
《说文》:“择,柬选也。”《后汉·张衡传》:“衡作《思玄赋》曰:‘匪仁里其焉宅兮。’”李贤《注》:“《论语》‘里仁为美,宅不处仁’,里、宅,皆居也。”《困学纪闻》谓《论语》古文本作“宅”。惠氏栋《九经古义》:“《释名》曰:‘宅,择也,择吉处而营之。’是宅有择义。或古文作“宅”,训为择,亦通。”冯氏登府《异文考证》引刘璠《梁典》“署宅归仁里”,亦作“宅”字。[1]上册139
今案:此例之中,刘氏征引唐李贤《文选注》、宋王应麟《困学纪闻》以及清人惠栋《九经古义》和冯登府《论语异文考证》,说明“择”字原文或作“宅”。刘氏所言,与阮元《论语注疏校勘记》所论同。事实上,刘氏所引《困学纪闻》并非全文,在刘氏所引之后,《困学纪闻》又曰:
石林云:“以‘择’为‘宅’,则里犹宅也,盖古文云然。今以‘宅’为‘择’,而谓里为所居,乃郑氏训解,而何晏从之,当以古文为正。”[3]①据考证,“《经义考》载此条,‘石林’下有‘《论语释言》四字’”,王氏原文及考证文字详参王应麟《困学纪闻》,翁元圻辑注,栾保群、田松青、吕宗力校点,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是王应麟赞同叶梦得之说,以为当从古文“宅”。刘氏未引此说,可见其虽然认为古文或作“宅”,然而并未认可古文为正字。至于择、宅二字通假关系,应无可疑。除去刘氏所征引材料外,上古宅和择同音,皆定纽铎部入声,完全具备通假的条件,这是另一佐证。
(二)分析异文
《论语·颜渊》:“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正义》曰:
《史记·弟子传》作“仲弓问政”。冯氏登府《异文考证》以为《古论》,然前后章皆是问仁,不应此为问政,《史记》误也。[1]上册777-778
今案:从语音上来看,上古:政,章纽耕部去声;仁,日纽真部平声。二字古音相差甚远,难言通假。以为此处作“问仁”者,理由有如下几条。其一,敦煌本《论语集解》以及传世文献多作“问仁”。其二,此为《论语·颜渊》第二章,其前有“颜渊问仁”,其后有“司马牛问仁”,此处若为“问政”,则颇为突兀。其三,从内容上来看,孔子所言三事,确实都与政事颇有关联。然而为政之本,莫不与仁有关。孔子表面上论政,本质上是在说仁。所以内容上与政事或有关联,但却无法成为“问政”的证据,而只能作为一个无偏向性的中立证据看待。其四,《论语·子路》:“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后人多称《子路》此章为“仲弓问政章”,这大概和《颜渊》“仲弓问仁章”造成了混淆。传世文献有“仲弓问政”者,后多接《子路》的“孔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可知其引自《子路》而非《颜渊》,只是在文字上有所删减改动。又如《汉书》卷十二《平帝纪》和卷六十五《东方朔传》的颜师古《注》、宋黄震《黄氏日抄》卷二、宋谢维新《事类备要·前集》卷四十《仕进门》、宋祝穆《事文类聚前集》卷三十《仕进部》、元王充耘《四书经疑贯通》卷二“子路问政章”所引皆如此。所谓“仲弓问政章”,则十分罕见,宋郑樵《通志》卷八十八“仲弓问政”后接《颜渊》相关内容,或为误抄,难言确证。总之,此处当以刘氏所言,作“仲弓问仁”更为妥当。
(三)考证篇章
《论语集解》卷末附有何晏《集解序》,刘恭冕在《正义》卷二十四中对此序进行了详细的说解,举凡师承、家法、授受、文字、版本、人物、典章、名物等,皆有精密疏证,可谓汉以前论语学简史。其中关于《齐论》中《问王》篇名的考证,尤为精妙。何晏《集解序》:“齐论有《问王》《知道》,多于《鲁论》二篇。《古论》亦无此二篇,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篇次不与齐、鲁《论》同。”[4]《正义》曰:
《汉·艺文志》:“《齐》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如淳曰:“《问王》《知道》,皆篇名也。”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详其名,当是内圣之道、外王之业。”朱氏彝尊《经义考》斥晁说为附会,谓:“今《逸论语》见于《说文》《初学记》《文选注》《太平御览》等书,共诠‘玉’之属特详。窃疑《齐论》所逸二篇,其一乃《问玉》,非《问王》也。考之篆文,三画正均者为‘王’,中画近上者为‘玉’。初无大异,因讹‘玉’为‘王’耳。王伯厚亦云:‘《问王》疑即《问玉》。’亶其然乎?”案:《说文》引《逸论语》:“玉粲之璱兮,其瑮猛也,如玉之莹。”段氏玉裁《注》云:“张禹《鲁论》所无,则谓之《逸论语》,如十七篇之外为《逸礼》,二十九篇之外为《逸尚书》也。”其《初学记》所引“璠玙”,鲁之宝玉也。孔子曰:“美哉璠玙,远而望之,焕若也;近而视之,瑟若也。一则理胜,一则孚胜。”又《初学记》及《御览》所引:“玉十谓之区,治玉谓之琢,又谓之雕。磋,玉色鲜白也。莹,玉色也。瑛,玉光也。琼,赤玉也。蝽瑾瑜,美玉也。玩,三采玉也。玲、珑、跄、琐、理,玉声也。缴,玉佩也。填,充耳也。躁,玉饰以水藻也。”凡所诠“玉”之辞,与《说文》所引《逸论语》文全不类,朱氏不当并数之。今《家语》亦有《问玉篇》,当是依用《论语》篇名。然则《问王》之为《问玉》,其说信不诬也。宋氏翔凤《师法表》以《问王》为《春秋》素王之事,备其问答,又合《知道》为发挥《尧曰篇》之意蕴,此曲说,不可从。[1]下册485
今案:学者对于《问王》《知道》二篇的考察,千余年来不绝如缕。《说文·玉部》两次引《逸论语》皆与“玉”有关,宋人王应麟以此为依据,首次在其《困学纪闻》中怀疑“问王”作“问玉”,清人朱彝尊《经义考》以及包括《说文》四大家在内的众多《说文》研究者皆赞同此说。然而对于《说文》所引《逸论语》的性质,前人颇有怀疑。《问王》《知道》二篇的亡佚,《隋书·经籍志》有言:
张禹本授《鲁论》,晚讲《齐论》。后遂合而考之,删其烦惑,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当世重之……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注。魏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吏部尚书何晏又为《集解》,是后诸儒皆为之注,《齐论》遂亡。[5]
就文体而言,《逸论语》与今本《论语》差异明显,而与《尔雅》《方言》类似,清人翟灏《四书考异》便以《逸论语》“玉十谓之区”一句为《方言》原文。故陈东《历代学者关于〈齐论语〉的探讨》即持此种观点,反驳《说文》所引《逸论语》为《齐论语》[6]。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第一,许慎所言《逸论语》虽然指涉模糊,但正如段玉裁所言,以《逸论语》作为二十篇之外篇目代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古论》有两《子张》,其篇目实则与《鲁论》同;而《齐论》的《问王》《知道》两篇,在《鲁论》和《古论》中是不存在的。所以,《说文》以《逸论语》代称《齐论》多出的两篇,合情合理。第二,文体方面,刘氏也有观照,这从他对朱彝尊观点的驳斥中可以窥见。除去《说文》外,汉赵岐《孟子章句》、班固《汉书》、桓宽《盐铁论》、应劭《风俗通》、晋陈寿《三国志》、唐孔颖达《礼记正义》、李善《文选注》、徐坚《初学记》,宋《太平御览》等书皆曾征引《逸论语》,这其中并非全是《问王》的原文。刘氏所举《初学记》和《太平御览》所引“玉十谓之区”一句,在文体上确实与《尔雅》类似。刘氏虽未明言,但实际上与翟灏的观点一致,都是从文体的角度出发,认为《初学记》及《太平御览》所引之文与《说文》所引差距甚大,理当不出自《问王》。然而对于《说文》的两处征引,则很难同样以文体为依据,将其归入《方言》之中。因此,并不能简单排除《说文》所引《逸论语》为《齐论语》的可能性。刘氏对文献材料的精密辨析可见一斑。
至于篇名,刘氏则赞同朱彝尊的说法,认为当作“问玉”。考之篆书,虽然“王”和“玉”二字字形相近,但实则字形区别正与朱彝尊所言相反,然而这并不影响二字形近易混的事实。讹混的情况在典籍中时常可见,如《仪礼·士丧礼》:“决用正,王棘若择棘。”郑玄《注》:“古文王为玉。”[7]《周礼·天官·九嫔》:“赞玉齍。”郑玄《注》:“故书玉为王。”[8]《庄子·让王》:“乘以王舆。”[9]陆德明《经典释文》:“一本作‘玉舆’。”[10]《荀子·王霸》:“改王改行。”王先谦注曰:
或曰:《国语》襄王谓晋文公曰:“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玉,佩玉。行,步也。卢文昭曰:或说是。古“玉”字本作“王”,与“王”字形近易讹。王念孙曰:“《群书治要》正作‘改玉改行’。”[11]
加之《说文》所引《逸论语》两处文字皆与玉有关,很容易联想到这两处文字就是出自《齐论语》,并且篇名应是《问玉》而非《问王》。此外,刘氏还从与孔子关系十分密切的《孔子家语》中找到《问玉篇》作为佐证,用以证明《论语》中存在与玉石相关篇章的可能性。
(四)辨析他书
《正义》以《论语》的考证为核心,自是毋庸置疑。不过刘氏在征引他书予以考辨之时,并非不假思索而盲目信从,往往是对他书文字作了精当的分析之后,再进行校注的工作。如《论语·学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正义》曰:
“曰”者,皇《疏》引《说文》云:“开口吐舌谓之为曰。”邢《疏》引《说文》云:“曰,词也。从口,乙声,亦象口气出也。”所引《说文》各异。段氏玉裁校定作“从口、乙,象口气出也”,又引《孝经释文》云:“从乙在口上,乙象气,人将发语,口上有气,故曰字缺上也。”[1]上册2
(五)广征博引,尤重碑刻
《正义》全书广泛运用各种材料,所征引典籍有三百七十余种,而在校勘文字时,则主要参考了《尔雅》《说文》《玉篇》和汉、唐、宋三代石经以及皇侃《论语义疏》、日本正平本《论语集解》、《七经孟子考文》、足利本、惠栋《九经古义》、冯登府《论语异文考证》、阮元刊《论语注疏校勘记》、俞樾《群经评议》等,将《论语》的重要版本和重要的校勘著作搜罗殆尽,实现博采众说、兼收并蓄之效。传世文献之外,刘氏的视野还投向了金石资料。历代石经自然是重中之重,至于其他碑刻资料,也能充分运用。《论语·为政》:“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正义》曰:
《释文》:“错,郑本作‘措’。”汉《费凤碑》“举直措枉”,与郑本合。《说文》云:“措,置也。”措,正字;错,假借字。[1]上册64
今案:刘氏以碑刻作为校勘材料,证明“错”和“措”的通假关系。此例足以证明,在他校材料上,除去传世典籍之外,刘氏对于出土文献也颇为关注,可见其视野之广。
(六)重视理校
《论语·公冶长》:“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正义》曰:
《论语释文》:“崔子,郑《注》云:‘鲁读崔为高,今从古。’”《论衡·别通篇》:“仕宦为吏,亦得高官。将相长吏,独我大夫高子也,安能别之?”亦据《鲁论》。包氏慎言《温故录》:“高氏为齐命卿,与文子同朝者,高子也。崔杼弑君,而《鲁论》书‘高子’者,责其不讨贼也,与赵盾同义。文子去齐而之他邦,其间或欲请师讨贼,而见其执国命者,皆与恶人为党,故曰‘犹吾大夫高子也。’”陈氏立《句溪杂著》曰:“以《左传》崔杼事证之,则《鲁论》信为误字。然文子所至各国,亦何至皆如崔子,而文子亦何至辄拟人以弑君之贼?则下两言‘犹吾大夫崔子’,似以《鲁论》作‘高子’为长。盖弑君之逆,法所必讨。高子为齐当国世臣,未闻声罪致讨,以《春秋》贬赵盾律之,宜与崔子同恶矣。其首句自当作‘崔子’,《鲁论》作‘高子’,则涉下高子而误。”案:包、陈二说微异,皆可得《鲁论》之义。郑以《古论》定《鲁论》,亦以庄公时高子不当权,要与赵盾异,《春秋》无所致讥,故宜从《古论》作“崔子”也。[1]上册195
今案:晋灵公被其国人所弑,太史董狐因赵盾未尽保护义务,而以不作为犯罪的原则书“赵盾弑其君”。至于高子,亦当与赵盾同。从史实上来看,齐庄公被弑,凶手实为崔杼而非高子。然高子为天子所命之卿,与赵盾一样,都有护卫君主的义务,一旦君主被弑,赵盾、高子皆为失职。探其实,则崔杼弑其君;显其名,则高子弑其君。《鲁论》以“崔”为“高”,此即惩恶扬善的褒贬书法,故首句作“崔子”以明其实。而后两“崔子”,实当作“高子”,表示当权者与“高子”一样,与恶人沆瀣一气。戴望《戴氏注论语》、俞樾《群经评议》皆赞同“鲁读崔为高”,即第一处作“崔子”而下两处作“高子”的说法。然郑玄以为当从《古论》,三处皆作“崔”,包咸和陈立赞同郑说,《正义》亦与之同。同时,刘氏还猜测郑玄判断的理由,即从史实的角度出发,以为高子不当权,故与赵盾不同,而不应有刺讥之义。刘氏虽然以“崔”为原貌,然而对《春秋》的书法是毫无怀疑的。刘氏面对《古论》和《鲁论》的文字差异,在充分借鉴前人考证的基础上,以微言大义的书法为基础,并结合史实,进而判断出文字原貌,是理校的经典例证。黄怀信《论语汇校集释》则抛开书法问题,从文义的角度出发,认为三处皆当作“崔子”:“作‘崔’作‘高’,必是一本有误,不必尽以今文、古文说之。崔子弑君而陈文子去,是厌与崔子同朝。至一邦若言犹吾大夫高子,则有是以高子当杀,岂有是理?”[12]黄氏所言,颇有其理。戴望、俞樾等人所论,不但于书法上颇为曲折,在文义的理解上也难言通顺。综上可知,此例当如刘氏所言,三处皆作“崔子”。
二、白璧微瑕:考校中的讹误之处
刘氏校勘虽然精密,然而终究误校、漏校难免。尤其是利用1973年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出土的竹书本《论语》(其抄写不晚于西汉宣帝五凤三年,即公元前55年①因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有《论语·知道》篇,所以被推测很可能是《齐论》。而刘贺卒于公元前59年,故其墓简本《论语》的抄写年代,很可能较定州汉简本更早。由于出版、释读、研究尚在进行之中,本文尚无法予以充分利用,只可俟后加以补充。,实为当今《论语》的最早版本之一),可以在诸多文字的考证上,对刘氏的校勘进行判别和补正,今举例如下。
(一)罗列异文而缺少识断
《论语·为政》:“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正义》曰:
《仲尼孔子列传》作“问干禄”,此出《古论》。《大戴记》有“子张问入官”,即问干禄之义。《鲁论》作“学”,谓学效其法也,于义并通。[1]上册62
今案:关于“问”字,前人已有讨论,程树德《论语集释》引刘开《论语补注》曰:
余尝疑“子张学干禄”之解为不可通,以为子张志务乎外,则诚不能免此,若谓专习干禄之事,恐未必然,岂子张终日所求者独为得禄之计耶?后闻先生某断此“学”字当为“问”字,证以《外注》程子云“若颜、闵则无此问”,是明以干禄为问也。余既信其言之有征,后又得一切证,“子张问行”注云:“子张意在得行于外”,故夫子反于身而言之,亦犹答干禄问达之意。夫既同谓之答,则干禄亦属子张之问可知。然则朱子故以干禄为问也,是“学”字为“问”字之误无疑矣。[13]
可见,宋人所见的版本还是有作“问”的。虽然版本异文数量较少,然而《史记》的“子张问干禄”显然颇具说服力。除此之外,郑樵《通志》卷八十八引亦作“问”。从文例上来看,《为政》同篇问孔子者甚多,如孟懿子问孝、孟武伯问孝、子游问孝、子贡问君子、哀公问、季康子问,“问干禄”正与此同。从文义上来看,子张问而后孔子答,文义畅通明了;若是子张仅仅学干禄,而后孔子主动作答,则显得突兀不合。可见,《鲁论》作“学”实不可通。至于由“问”讹“学”的缘由,大概是“闻”与“学”讹混而来。先秦常常假“闻”为“问”,《诗·大雅·云汉》:“群公先正,则不我闻。”王引之《经义述闻》曰:“闻,犹‘问’也,谓相恤问也。古字‘闻’与‘问’通。”“闻”金文有作(战国中期陈侯因敦,《金文集成》4649),《四声集撰韵海》所录传抄古文作,与“学”字传抄古文相近,如《古文四声韵》。可能因字形相近,《鲁论》进而误“闻”为“学”,以至于出现“学”与“问”异文。
(二)考证有欠精审
《论语·为政》:“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正义》曰:
“孝于惟孝。友于兄弟”,皆《逸书》文,东晋古文采入《君陈篇》,汉石经及《白虎通·五经篇》所引皆作“孝于”。皇本亦作“于”。《释文》云:“‘孝于’,一本作‘孝乎’。”唐、宋石经及他传注所引,皆作“孝乎”。惠氏栋《九经古义》谓:“后儒据《君陈篇》改‘于’为‘乎’。”其说良然。案:“孝于”与下句“友于”相次,字宜作“于”。
《吕氏春秋·审应览》:“然则先生圣于”,高诱《注》:“于,乎也。”《庄子·人间世》:“不为社,且几有翦乎?”《释文》:“乎,崔本作‘于’。”《列子·黄帝篇》:“今女之鄙至此乎?”《释文》:“乎,本又作‘于’。”《庄》《列》二文以“于”为“乎”,与《吕览》同。窃谓此文“孝于”、“友于”字虽是“于”,义则“乎”也。“孝于惟孝”。与《记》云“礼乎礼”、《公羊》“贱乎贱”、《尔雅》“微乎微”、《素问》“形乎形,神乎神”、汉语“肆乎其肆”、韩文“醇乎其醇”相同。《法言》尤多有此句法。
“施於有政”以下,乃夫子语。宋氏翔凤《四书释地辨证》以上文引书作“于”,下“施於有政”作“於”,是夫子语显有“于”、“於”字为区别。包氏慎言《论语温故录》:“《后汉书·郅恽传》郑敬曰:‘虽不从政,施之有政,是亦为政。’玩郑敬所言,则‘施於有政,是亦为政’,皆夫子语。”其说并是。东晋古文误连“施於有政”为《书》语,而云“克施有政”,非也。[1]上册66
今案:刘氏的长篇考证中主要提出了两个问题:关于“乎”字是否应当校改和“施於有政”是否为孔子所言,而这两个问题相互关联、相互支撑。
关于“乎”字校改的问题。为了证明“孝乎惟孝”原文当作“孝于惟孝”,刘氏进行了详密的证明。在刘氏所列的诸多证据中,尤以汉石经颇具证明力,而唐代及宋代石经却作“乎”,这清晰展现了后人校改的痕迹。《经典释文》中亦有一本作“于”,则表现了“于”字在隋唐之际依然不绝如缕。至于改字的依据,则赞同惠栋《九经古义》说,认为是《逸书》的《君陈篇》。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亦引惠栋之说,然《论语注疏》正文仍作“孝乎惟孝”。
正是建立在上述对于“于”字问题的考证上,刘氏认为原文当作“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刘氏认为关于“施於有政”并非出自《逸书》,证据有二:其一,宋翔凤对于“于”“於”区别说明,即用“于”出自《尚书》,用“於”出自孔子;其二,包慎言引《后汉书·郅恽传》郑敬语的解说。
然而,刘氏之说颇有可商榷之处。
第一,“孝乎惟孝”,传世典籍大多与此同,如汉班固《白虎通》、刘珍《东观汉记》卷二《章帝纪》、晋陶渊明《陶渊明集》卷七《卿大夫孝传赞·孔子》、袁宏《后汉纪》卷十一《章帝纪》、梁萧统《文选》卷十六《闲居赋》等等,以至于清代的诸多文献所载,皆是如此。虽然汉石经、梁皇侃《论语义疏》作“孝于惟孝”,与传世诸本不同,但定州汉简本却作“孝乎维孝”。由于定州本早汉石经两百余年,且传世诸本“孝乎”二字连绵不断,故与其认为改“于”作“乎”,还不如认为改“乎”为“于”,在逻辑上更为通顺:原本作“乎”,故最早的定州本以及绝大多数传世本均与此同;后人或改为“于”,然改之不尽,或有残存。
第二,就刘氏关于“施於有政”当非出自《逸书》而是孔子所言的考证,其所列两条证据,第二条较为可信但第一条颇可商榷。从《论语》全书来看,“於”和“于”用法的差异,并非是引文与孔子所言区别的证据。定州本《论语》多用“於”而少用“于”,“于”虽少亦非不可见,全书用“于”凡三次,即《宪问》“到于今”、《微子》“叔入于河”和“武入于”,然皆非引文。介词“于”和“於”在先秦的区别大致有如下几点:“于”是“往”义动词虚化的结果,“於”是从“乌”中分化出来同音假借为“于”;“于”在甲骨中常用作介词,“於”在西周方用作介词;“于”主要用于引进处所,然后是对象和时间,“於”则引进处所和对象并重,亦常用引进时间[14]。所以,以“于”和“於”用字差异作为断定文字出处的证据实为不妥。
第三,从语音上来看,根据曾运乾“喻三归匣”说,中古喻母三等字上古归匣母,于、乎二字上古音音近。所以,二字大概率是音近义通的通假,甚至可能是《齐》《鲁》《古》三家的异文,而非后人据《君陈篇》校改。如果猜测成立,那么异文产生时间也必将较东汉末的熹平石经更早。
结语
刘宝楠在其从叔父刘台拱的影响下,秉承古今并蓄、汉宋兼采的风格,传承《论语》家学研究,接续刘台拱《论语骈枝》,与其子刘恭冕共同撰成清代集大成的《论语正义》二十四卷。刘氏以邢昺《疏》为《正义》经文和注文,广泛参考各种版本及前人成果,广征博引,对经文作了详细的校正。虽然校勘只是《正义》的一方面,但书中关于汉代《论语》经手抄口传而形成《齐论》《古论》《鲁论》三家间文字差异的研究向来被人称道。刘氏以小学为手段,将其对文字、音韵和训诂的精审纯熟精妙地运用到了校勘之中,实现对三家异文的详细梳理,同时细致分析他书征引的《论语》异文,精密论证错讹情形并断其正误,对可并存的情况则合理推测异文产生的原因及来源。此外,刘氏还注重理校方法的运用,考查篇章名称、数目,广泛运用包括碑刻文献在内的各种资料。总之,刘氏能秉持客观、科学的原则,实现绵密精细的考证,取得了丰硕的校勘成果。虽然或有罗列异文而缺少识断等考证不精的情况,但仍旧不能掩盖《论语正义》在校勘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