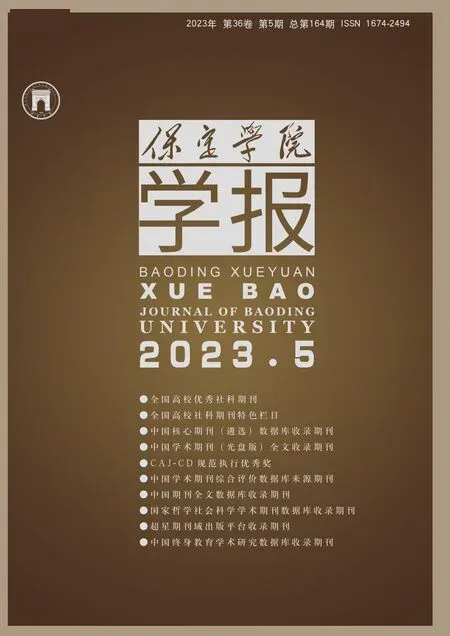中国传统金融机构性质及其转化的几个问题
刘秋根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02)
明中叶以来,商品货币经济乃至中国社会发展、转型的一个主要标杆是粮食、布匹等日常用品的长途贩运的发展,它促进了社会经济分工的发展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学术界对长途贩运乃至相关的市场、商品、技术进步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另外,以日常用品的长途贩运为主体的商业发展,也使得明清以来中国传统金融机构得到较大发展,可以说,正是后者的进步,才有效地支撑了明中叶以后长途贩运的发展及相关商品生产的进步。这种发展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资金市场的进步,各类新的金融机构产生,大致在康熙后期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金融体系,构成一个相对完整、覆盖广泛的金融序列[1]。以山西商人所经营金融机构为例,包括典当、钱庄、印局、账局、放账铺、票号等,这一体系只要正常运转,就能够给各行各业字号甚至普通家庭提供类似银行业所能提供的各种金融服务。二是多数金融机构的业务在保持各自特色业务的同时,开始办理多种业务,尤其是存、贷、汇三类业务,这些业务的办理,再加上跨区域结算的产生,促使这些传统金融机构集中的城市转化成为“区域金融中心”甚至“全国金融中心”,典型如北方的张家口、祁太平地区,南方的上海①河北大学孟伟教授将晚明到前清时期作为时间考察点,从以民族性贸易为基础、以张家口标期为标准的金融市场、与政府官锭接近的白银货币形态、全面的金融机构体系、地域广泛的商贸圈、合伙制、会计体系和会计技术、书信经营模式八个方面论述了成为全国性金融中心的条件,在中国也只有张家口具备这八个条件,是毫无疑问的清代前中期的中国金融中心,然后由山西商人将“张家口模式”复制到山西的祁太平地区,形成了另一金融中心,再到清光绪时期上海才成为新的金融中心。参见杨波等《张家口:清代前中期的中国金融中心——与孟伟、郝平二位教授的对话(三)》,《张家口日报》,2019年6月17日。以此类推,北京一直为明清民国时期的消费中心,近代天津、汉口更多是作为贸易、商业、交易中心,重庆可以算作区域性金融中心,还够不上全国性金融中心。。尤其是存款的进步更值得注意。三是多数金融机构在保持生活性放款的同时,更多地将资金投入生产及流通领域,放款转而更多地投入到对工商业字号的放款②当然这种变化还可以罗列许多,这里不赘述。。
一、关于中国传统金融机构性质及其转化学术成果的概述
关于中国传统金融机构性质及其转化相关成果也有了不少的积累,笔者觉得山西票号研究中一个著名的学术公案,即票号性质究竟是高利贷资本还是借贷资本,抑或是“封建性”金融机构的问题的探讨历程可视为这一学术史的代表①近年来,中国货币金融史研究的进展,相关成果又有了较大累积,但其中所内含的问题却未有明显进展。,故而从这一学术“事件”说起。这一问题主要是几位当年对晋商票号研究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的前辈学者,如黄鉴晖先生、孔祥毅先生、史若民先生等的学术争论,当然如果不限于票号,将视野扩大至“传统金融机构”,可以说洪葭管先生、张国辉先生等也被卷入其中。这一论争历史悠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举行了一次票号学术研讨会,会后在《光明日报》上以“杨荣晖”之名发表了一篇对票号进行评价及定性研究的文章,据说是三位学者联合写的。至八十年代初,以山西财经大学为主体重拾票号研究,重新搜集票号史料,重启六十年代便已联合几家单位进行的《山西票号史料》整理工作,在此后一系列票号乃至晋商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重新作了探讨,等于赓续了这一学术争论。而这一争论从其学术范畴而言,已经超出了单纯的票号乃至晋商研究,而与整个中国金融史、商业史,至少明末以来的中国传统商业金融史的研究产生了联系。以下笔者对主要的观点学说作一概述②本文对两派观点并不特别赞同或者反对,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历史的真实,但也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其薄弱之处,限于当时的资料条件或个人学术视野,有些学者对史料的解释有些偏颇或不足。。
署名为杨荣晖,发表于1961年《光明日报》的《山西票号的性质与作用》一文,对票号作了两个定性。第一,认为由于票号汇票起着信用货币的作用,故而能够把内地的银两汇集于通商口岸,成为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现银的运送机关③这一说法,有点偏离历史实际,因为票号主体还是为内地各商埠之间的资金来往服务,确实也为内地资金输往口岸服务,但同时更多地还是为内地各城市、市镇工商业字号之间资金来往服务。。太平天国后,因为这一汇兑功能,又由商业机关变为清政府财政金融机关。第二,票号资本属于高利贷资本,它因此发挥了两重作用:首先,在商人阶级旁边,形成一个独立的货币财产;其次,它会占有劳动条件,使旧的劳动条件的所有者灭亡,对于产业资本各种前提条件的形成,是一个有力支点。票号集中了货币财产,但未完成这一转化(即向产业资本的转化),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列强侵入导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阻碍[2]。数十年后,山西学术界对这篇文章的观点作了反思,并对票号的业务、功能、作用等作了深入的研究,使这一问题的学术含量大为增加。
黄鉴晖先生是署名人之一,后来他改变了看法,他在文章中写道:山西票号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其资本是借贷资本,并在实质上起到了“银行”的作用[3]。黄鉴晖先生还从近代银行业成长的角度探讨这一问题,他指出:银行业暨借贷资本形成,或者传统金融机构向银行机构转化,不一定要到产业资本最终形成之后产生,尤其不一定要像中国近代那样,要到有一大批近代工矿业企业的折旧基金存到银行中去,才有可能。而是在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形成了银行业机构,这些机构不是原有的典当机构,而是在这一阶段重新形成的,或者说中国高利贷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没有或不可能转化为银行业而从属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也就只能由产业资本或商业资本创造一种自己的银行业,因而在雍正乾隆之交即十八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了经营工商业借贷的银行业——“账局”,随后就是票号。但黄先生对钱铺、银号、钱庄向高利贷资本,最后向近代借贷资本转化的问题却似乎要保守得多,他认为,鸦片战争前,一些钱铺或钱庄开始向官吏、旗兵、市民放账,具有了高利贷资本的因素,鸦片战争后的咸丰年间,部分钱铺或钱庄也或多或少地开始经营工商业存放款业务,此时货币经营业就具有了借贷资本的性质。而且在口岸城市(如上海及宁波)中的钱庄最早开始向借贷资本转化,内地各钱铺、钱庄、银号则要到同治或光绪中期才开始这一进程。转化中及转化后的中国固有金融机构对近代企业是有相当大的支持作用的,正是在账局、票号、钱庄、银号等银行业的发展过程中,中国近代企业才由少到多,逐渐发展起来①以上所引黄鉴晖先生观点见黄鉴晖《中国银行业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31页、第55页、第60页、第65页。按:黄先生在此书中是认为账局在鸦片战争前就具有了“银行业”的性质的。。
黄先生坚决明确地反对从资本来源方面确定金融机构是否属于借贷资本的问题,指出:作为“生息资本的借贷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区别,不在于它们拥有资本的特征,而在于它们贷放出去的货币是发挥货币的作用还是发挥资本的作用。只发挥货币作用的属于高利贷资本性质,发挥资本作用的就属于借贷资本性质”②《中国钱庄史》第93页。黄先生又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论述为证。这一段论述是:“就生息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因素来说,它和高利贷资本的区别,决不在于这种资本本身的性质或特征,区别只是在于,这种资本执行职能的条件已经变化,从而和贷款人相对的借款人的面貌已经完全改变。”此段见《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79页。按:在高利贷资本的前提下,未必全是货币借贷,也能发挥资本的作用,因为高利贷资本的金融机构也对生产者、商人放贷。。也就是说“贷给小生产者是高利贷资本,贷给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就是借贷资本”[4]。从具体时间上看,“可以说清末全国范围内都会有一部分钱庄由货币兑换业转变为生息资本的借贷资本”③两段分别见《中国钱庄史》第74页、第93页。。
在票号的历史评价问题上,与黄鉴晖先生观点类似的是史若民先生④当然史先生只探讨了票号,而未涉及钱铺、银号、钱庄与账局。,这里且不说他的《票商兴衰史》,他还曾专门撰写数文,探讨了票号的性质与作用问题,我们这里引用他《票商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作用》一文中所用的标题就可大致了解史先生的观点,如“三、官商相维,票商借鸡下蛋资助民族资本”“四、建立全国汇兑网,为民族资本发展提供便利”“五、票商是近代许多近代企业的助产婆”。他在近代资产阶级成长的背景下,指出:“与上述这一批最初形态上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同时活跃于中国社会经济舞台上的近代中国银行业的先导——票号商,构成了近代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又一侧面,即金融资产阶级”[5]。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山西票号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成长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完全为商品经济发展服务的金融机构。”它诞生后,曾促进了商业及手工业等行业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与发展。在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前,渐次承担了本应由近代通商银行承担的各种金融业务[6]。史先生还运用票号信稿对票号的利率作了考察,并与传统典当业的利率作了比较,认为票号的利率大大低于典当利率,故而“把票号与当铺相提并论,把票号资本当作封建性高利贷资本,是缺乏史实根据的”[7]。
与黄先生、史先生观点不同的是孔祥毅先生,他在1982年的“山西票号学术讨论会”(太原)上的发言中认为:山西票号是在山西商人资本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从山西商品经营资本中分离出来的。票号前期与商人资本相联系,后期与官场发生了联系,均属前资本主义的生息资本范畴。票号对于近代工业,很少介入。从票号借贷资金的人,一是政府和候补官员,二是较大的封建商人和钱庄;从其资金来源看,是封建商业利润投资与票号积累,另有官款存放,不是产业资本周转过程中的暂时闲置的货币资本,基本与产业资本没有任何联系。所以票号是为封建生产关系服务并存在的,与雇佣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割基本没有联系。因此,票号是封建高利贷的金融机构。并提出“衡量借贷资本和高利贷的根本标志,在于它与什么样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必须从货币信用所体现的生产关系上进行分析”。“票号资本的运动也不符合借贷资本的运动规律,借者不是把贷款转化为资本来使用,而是用于消费和转运贸易。票号财东未参加也不可能参加剩余价值的瓜分”。票号属于货币经营资本,但这个货币经营资本实际上属于前资本主义的高利贷性质[8]。
然而,孔祥毅先生却认为:明中叶以来,中国发生了一场商业革命,引起贸易发展,货币需求扩大,导致了当时金融信用、工具、机构、业务、制度诸方面的创新,金融革命发生了。第一,中国式商业银行覆盖全国城镇;第二,票据流通,在财富转移中代替金属货币;第三,债权债务的非现金清偿网络基本形成;第四,金融机构的企业化管理制度规范动作;第五,金融机构开始为政府融资;第六,中国商业银行介入国际金融活动;第七,金融业同业公会形成并在经济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山西商人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创造了大量金融工具,但可能因为票号业务建立在落后的银两货币(体系的)基础之上,虽然支撑了当时的工商业,但留在现代金融中的东西并不多,支持近代工矿业的任务主要是由江浙财团创办的银行、证券、保险业承担[9]。显然,孔先生对中国明中叶以来商业金融革命的论述与以上对票号的评价似乎是矛盾的,表现在:一方面说票号还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高利贷性质,另一方面又说明中叶以来,中国的商业性银行已经覆盖了全国城镇,并且介入了国际金融活动,创造了大量金融工具。因为有了这样的金融机构网络及工具,难道还不能为中国传统工商业乃至近代工矿业提供金融支撑吗?
与此不同的是洪葭管先生,可能还包括张国辉先生。洪先生以山西票号与上海钱庄为例,认为:“初期的票号和钱庄虽然从事着生息资本的活动,但基本上还是货币经营资本……这种货币经营资本正力图转化为借贷资本,但它没有转化成功。货币资本没有完全分离出来成为借贷资本,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没有产业资本这个历史前提条件,还不可能在产业资本的基础上运动。”[10]又说:“衡量借贷资本是否形成,可以从借贷资本的几个来源进行分析。借贷资本的主要来源有四方面:一是产业资本循环的过程中,会形成一部份暂时闲置的货币资本;二是食利者拥有的资本;三是现代信用制度动员起来的社会各阶层的货币收入;四是通过货币发行所组织起来的社会资本。从这四点来衡量十九世纪的山西票号和上海钱庄,那么它们都远不具备作为借贷资本的信用机构的条件是明显的。”[11]“在中国资本主义企业初步发展的基础上,中国近代的借贷资本兴起来了。从其集中社会货币资本的规模和程度来看,它与职能资本的分离并发挥自己的特殊作用,不在十九世纪末中国通商银行单独一家成立之时,而是在二十世纪初一批银行相继开设之际”[11]。
张国辉先生未参与这一争论,他在将钱铺、钱庄与票号结合进行具体实证研究的过程中,从钱庄存放款业务出现的角度论述了钱铺、钱庄由货币经营机构向信贷机构转化的问题。他认为:“根据有关史料记述,大约到18世纪40年代(约当乾隆初年),钱庄职能还是以银钱兑换为主要业务。”“(乾隆后期)与这一时期商品货币经济进一步发展相适应,钱庄逐渐从银钱兑换业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信贷活动的机构”。他又指出:乾隆以后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对于钱庄来说,货币兑换的职能一旦与借贷职能相结合,并且逐渐地过渡到以借贷为其主要职能时,也就意味着这一行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尤其是钱票的使用)更是说明了到封建社会后期,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的同时,必然发生信用事业”[12]。
二、关于所谓货币经营机构向银行的进化与高利贷资本向近代借贷资本的转化——兼论货币经营资本的各种业务与功能问题
由前辈学者对以票号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金融机构转化问题的论述可见,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思路是:对两大序列的历史过程不加明确区分。第一序列是货币经营机构→银行;第二序列是高利贷资本→近代借贷资本。也就是说,多数学者不论其所论对传统金融机构评价如何,都认为存在一个货币经营资本向近代借贷资本转化的趋势。其论证的基本路径是:货币经营机构,在开始进行存放款业务之后,向信贷机构转化,即向借贷资本转化。如洪葭管先生说:“初期的票号和钱庄虽然从事着生息资本的活动,但基本上还是货币经营资本……这种货币经营资本正力图转化为借贷资本,但它没有转化成功。”黄鉴晖先生论及账局时认为:中国高利贷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没有也不可能转化为银行业而从属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也就只能由产业资本或商业资本创造一种自己的银行业,它就是账局。他谈到钱庄时说:“可以说清末全国范围内都会有一部分钱庄由货币兑换业转变为生息资本的借贷资本。”孔祥毅则认为:票号属于货币经营资本,但这个货币经营资本实际上属于前资本主义的高利贷性质①以上诸位学者数十年来的孜孜探索及其所呈现出来的对中国传统金融机构的学说与观点,我们首先应该肯定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包括史料运用、理论思辨各方面均是如此。对他们有时很谨慎、有时也很尖锐的争论,我们都得表示敬意。但是,前辈学者观点的问题也是要指出来,在此基础上对近二十年来研究成果作出新的概括总结,并且结合新的史料作出新解答,相关学术研究才能继续前进。这里并不想具体就票号或者其他传统金融机构的性质问题再发表看法,而是欲在更广阔的背景中对明清传统金融机构及其转化相关的几个问题作进一步的理论梳理与分析,所要达到的学术目的除要将货币经营机构向银行的进化与高利贷资本向近代借贷资本的转化两大历史过程分开考虑之外,还要从业务角度、新的信用机制角度探讨中国早期银行业。。
以上诸前辈在论述相关问题时,虽然几乎皆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西方货币经营业的一段话,来探讨钱庄银号票号等机构的转化问题,却不同意见迭出,至今无定论,细绎其故,端在于研究马克思货币经营资本理论学说时,未将货币经营机构向银行的进化与高利贷资本向近代借贷资本的转化这两大历史进程分开探讨,故而在以上问题上形成了争论。
马克思这段话是:“一旦借贷的职能和信用贸易同货币经营业的其他职能结合在一起,货币经营业就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这种情况即使在货币经营业的最初时期也总会发生。”仔细体会马克思这段话,可发现,马克思并不是在谈货币经营机构开展存放款业务的问题及其因此向近代借贷资本转化的问题,而完全是在讲货币经营资本的形成及本身职能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352~360页便具体论述了货币经营资本及其各种功能的形成问题,大体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指出:因为货币作为一国铸币及国际货币的职能,货币经营资本便产生了兑换及金银贸易的职能,“兑换业和金银贸易是货币经营业的最原始的形式,并且产生于货币的双重职能:作为一国的铸币的职能和作为世界货币的职能”。
第二,马克思指出:为了不断的购买与支付,必须有货币作为准备金,另外,一些形式上暂时不用的资本、新积累尚未投入的资本皆有可能将货币作为贮藏货币,这就形成了货币经营资本的保管、记账功能等。
第三,货币在购买、出售时的支出、收入,支付的平衡等的需要形成了货币经营资本的作为“单纯的出纳业者”的功能。
第四,在这里,对于第四个方面的功能马克思未能明言,只简单指出:货币的借贷职能及信用贸易还产生货币经营资本的“其他职能”。但最后的这个职能是什么?马克思在这一章中并未具体论述。他还说:“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篇论述生产资本时再谈。”他是在第四篇第十九章中论述这一问题的,但在第五篇中也未详细论述这一问题。
但有幸的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八卷所辑马克思的《资本论》手稿中,可以见到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更为详尽而全面的论述,弥补了以上缺憾。在这里,马克思首先指出:货币经营业,也同样只能从货币的特殊职能中取得自己的内容,而货币的这一职能不同于货币作为商人资本所执行的职能。那么货币又有哪些特殊职能,而货币经营业又有哪些自己的内容呢?在这里,马克思也是分几个方面论述的。
第一,“这些职能首先就是货币贮藏本身,后者不过归结为保管流通中沉淀下来的货币②即“流通中沉淀下来的货币形式的资本、利润或各种收入”。……这就是货币经营者或货币经营业的第一种职能”。这是货币经营业的货币保管功能。
第二,“一方面,贮藏货币作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被花掉,另一方面,它又由于商品不断再转化为货币而不断地被恢复。它始终处于不断的运动中,而决不是货币贮藏者的静止的贮藏货币。因此,货币经营业的第二个职能是:不断地接受来自工业家和商人的货币,把它们作为贮藏货币收起来,又不断地作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交出去。这一活动使簿记、经常性的付款和计算成为必要”。尤其是“货币经营者就必须执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这一职能,必须实现平衡,或者是作为差额而支付货币,或者是作为差额而接受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的这种平衡和中介活动,特别在资本主义生产下日益得到发展”。这就是货币经营业者的货币收付、记账功能。
第三,“因为在国外市场上进行的支付或购买使一些特殊活动成为必要,造成了寄送差额或作为购买手段的货币的特殊形式(汇率等等),所以,这些活动又构成了货币经营业的特殊职能”。这是货币经营业者的汇兑功能。
第四,“同样,货币由产地进入商品交换这一行为,也会作为特殊的活动和职能而独立化(贵金属贸易等等),这又是货币经营业的特殊职能”。这就是货币经营业的贵金属买卖功能。
第五,“最后,闲置的货币,换言之,作为货币资本被投到市场上去的货币,被贷出,被其他的人借去,而这——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贷款、贴现等等)——又表现为货币经营业的特殊职能,而且,这种货币经营业对于借贷货币资本来说,就象商人对于商品来说一样,表现为同样的东西,即表现为中介,通过这一中介,货币资本的供求得到平衡和集中”。这就是货币经营业者借贷的中介功能。
总而言之,马克思这些话的意思是在论证与货币各种功能相应的货币经营资本所具有的不同职能,而货币经营资本本身已经开始存款及贷款业务,这似乎不是问题,因为与其他功能一样,货币经营机构只是媒介货币的这种功能,即作为存款者与放款者之间的中间人,至于这些货币去执行什么具体功能,即它们是执行商业资本的功能、还是产业资本的功能、亦或是高利贷资本的功能,这些都是处于货币经营机构之外,完全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运动,是与货币经营机构无关的。也就是说,即使开展了货币借贷、贴现业务,也还是货币经营资本。
应该说,不是货币经营业以存款的形式集中相当数量的闲置货币资本,同时它的借贷业务也有了相应的扩大,而是货币本身有了存款、贷款的功能,相应地货币经营业便有了作为存与贷的中介的功能。传统钱铺、钱庄、票号、账局、典当也好,近代银行业也好,都是一种货币经营机构。至于在这些金融机构之外,是作为独立于经济运行之外运行的高利贷资本、商业资本亦或作为生产资本的一个组成要素的近代借贷资本,都与这些机构是货币经营业机构亦或银行业没有关系。这两个序列,必须分开考察。
三、从存款业务角度观察“中国早期银行业”
以上学术史概述中,我们发现从存款角度探讨中国近代银行业形成的是洪葭管先生,他提出著名的从四个来源方面探讨中国借贷资本形成,其中三个方面——产业资本循环的过程中形成的闲置货币资本、食利者拥有的资本、现代信用制度动员起来的社会各阶层的货币收入皆与存款有关,当然这是洪先生从近现代借贷资本的整体形成角度来加以论述的。大致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随着中国金融史尤其是传统金融机构研究的深入,多数学者也肯定了明代出现的钱铺、钱庄、银号,清代才出现的票号、账局皆当作中国式的“商业银行”。但对于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达到像一个“商业银行”呢?如张国辉先生所论,是从所谓“货币经营机构”——钱铺、钱庄、银号等在兑换等纯技术业务的基础上开展存放款业务,从而形成信用机构而形成的①如果从后者思路出发,我们就在中国本身的金融机构、业务的研究中暂时撇开了“西方近代银行业”因素。。在此,虽未能专门论及存款因素,但无疑也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我们不拟全面研究存款因素与“中国早期银行业”②所谓“中国早期银行业”主要是指西方银行进入中国之前形成的与西方银行业不同而又接近的中国传统金融业的变迁形态。形成的关系问题,实际上主要是想从整体上考察这一形成过程中“存款”因素的重要性。
理论上,上文对货币功能及货币经营业职能的梳理,已经为此打开了路径:那就是要从传统金融机构的业务本身及运行机制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不是从这个机构与生产流通过程,或者说与生产关系联系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这一点与1908年《大清银行则例》对于“银行”的规定是一致的,此则例言:凡经营存款、放款、汇兑、兑换业务的机构皆应视为银行,故而存在于清末时期的中国传统金融机构即以上所说钱铺、银号、账局、典当、票号等,在则例均属于“银行”,并且要像银行一样注册。
中国学术界原来多认为英格兰银行起源于伦敦金匠,即伦敦金匠由单纯货币兑换机构的单一业务,向在经营兑换的同时开始发行信用货币、发放贷款、接受存款等综合性业务的机构转变,于是便形成为银行。实际上,银行远不止一种起源,在中国如上所言,至少有钱铺、钱庄、银号、票号、账局、典当铺等有可能演变为具有银行业性质的金融机构;在西方,如美国金融史专家金德尔伯格指出:“银行有商人银行、私人银行、票据兑换银行、储蓄银行、贴现银行、公有银行、宫廷银行、合股银行、混合银行、工业银行、投资银行、动产抵押贷款银行、商业银行等等,在意大利,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银行主要有三个类型:典当行、钱币兑换商、存款银行。”具体谈到热那亚的钱币兑换商时指出:“但他们所做的生意主要是兑换钱币,其中不包含信用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钱币兑换商演变为可以汇款的汇兑银行,或者是当地划拨款项,有时发放兑款的存款银行。”他还转引了托马斯·孟的话指出:“交易的变化,迫使热那亚商人由商品贸易转变到货币兑换。”[13]金德尔伯格先生的三段话表述了三层意思:一层是银行根据其主体业务(票据兑换、储蓄、贴现、动产抵押贷款)、所有者(商人银行、私人、公有、宫廷)、服务对象(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工业银行)、资本组织(合股、混合)等区别为各种类型,此处并不是标准分类,故而种类有点乱,但说明西方各国银行的起源是多种类型、多种途径这一点是不错的。在意大利至少有典当行、钱币兑换商、存款银行等三种类型。第二层以热那亚的钱币兑换商为例指出:专门从事兑换业务的机构一开始是没有信用因素的,但随着其从事汇款业务变为汇兑银行,或者从事划拨款项、发放贷款的存款银行。第三层金融机构在热那亚有些是由从事商业贸易的商人兼营的。
其实,这一模式与中国传统金融机构的演变颇有相似之处,中国的典当业自南北朝、钱铺钱庄银号自明中叶、账局自清代前期、票号自清中后期逐渐产生,随着其信用因素的获得,即开展存贷款业务开始,逐渐向早期银行业转变,而其最关键的则是存款业务的开展。
企业或商人或城乡居民在金融机构有存款,本来是件简单的事,是金融机构的一种常见业务,但正如以上所述,又似乎兹事体大,这不由地也使我们想起一段学术往事,这就是当年阅读日本唐宋经济史大家加藤繁、日野开三郎的作品时,发现他们那么不遗余力地探讨唐代的柜坊及柜坊中的钱物存储问题,并为宋代柜坊的变质而遗憾,为此付出诸多的研究心血。虽最终未确定这些存储是否算真正的存款,因为这些存款是否有利息,是否存款之后还用于柜坊的运营,最终也未能确定,故而以后学术界对柜坊是否是金融机构也多表示质疑。同时,他们虽注意到宋代柜坊的变质,还对类似的由唐至宋的一些商铺经营的“寄附”问题也作了详细探讨。但毕竟未能解决唐宋时代是否有真正的存款的问题。因为即使运用现代的电子索引,遍查现存传世文献,也未能找出超出日本学者的记载,来证实柜坊是真正存在有息存款的问题。在马端临的关于《资治通鉴》的注中将唐代文献中描述的所谓“僦柜”解释成与宋元时代的质库业务相似。但如果我们以此为线索,倒是可能发现一些正式的有息存款的线索①依马端临的注,“僦柜”倒真的像是元代的典当业。。据宋代的记载,从北宋中期开始,在官府典当业——抵当库、抵当所之中,及寺院长生库和私人质库之中,均开展了存款业务,至南宋以后得到不小的发展,尤其是私人质库、解库,寺院质库中,存款业务的经营更为普遍。此业务存续至明清时代,清代以后,因为朝廷、各级地方官府、各种社会组织发商生息制度的推行,存款业务更是普遍及深入,尤其是与官府相关的存项,更有详尽的文献记载。其中包括典当业的存款,也有钱铺、银号等的存款,清代以后的账局、票号多多少少也开展了存款业务。当然,各行业商铺字号乃至有信誉的富商大贾、地主等也经营存款。
就存款的需求方面看,有官府、有社会组织、有个人,但最值得注意的是,清代早期的商铺、字号也将经营闲置资金交给其他字号、店铺存储,这种企业存款与私人、官府存款是有不同意义的。因为有了这种存款,金融机构就有可能代客户记账并为之转账,或曰拨账;甚至为客户保管货币资产,利用这笔存款代为客户进行经营谋利。这就转化成了“账户”,有了这样性质的制度,如果金融机构为许多商号商人集中进行(甚至同城所有商户)拨账,这样就不仅是有利于节省贵金属货币,接受存款的机构还能运用这些存款进行其他经营,扩大资本。这就有一个本质的东西内涵其中,即有了信用创造。有了这样的信用因素融入其中,这个金融机构作为“商业银行”机构的条件就更为齐全了①如上对马克思货币金融经营资本理论的疏理可见:单纯借贷、存款业务本身并不意味着银行业的形成,有了信用因素融合于其中才能说是银行业的最后形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金融机构具有大区域性质甚至全国性,并突破共同体性、小众社会性的局限,走向非人格化、大众化交易。当然这还伴随着另一个与实体经济相关的转化过程,就是高利贷资本向近代借贷资本的转化、由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转变成产业资本。金融机构成为整个生产资本的总记账人。。如此看来,至迟清代以来,一大批的中国传统金融机构多多少少都带有商业银行机构的性质。甚至典当业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这一性质,当然主要还是钱铺、银号、钱庄、账局、票号这几种②还有印局、放账铺等金融机构是否带有商业银行性质,还需具体分析。。
最初,存款难免局限在小众范围之内,即受前近代社会共同体社会关系狭隘的束缚,但随着金融机构及其他商业字号规模的扩大,尤其是商品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发展的前提下,专业化商人集团的形成,日常用品长途贩运的发展,商业资本的积累,货币金融的需求膨胀,导致了货币金融供应的变化,存款、贷款业务不但在各金融机构,一般商铺、字号中也普遍经营。同时还表现出两种趋势,一是越来越多的存款由金融机构及那些资本较大、经营历史悠久、信誉卓著的工商业字号经营;二是随着一系列制度的建立,信用因素不断深化,不同地域的金融机构(可能也包括部分工商业字号,当时多商业与金融兼营)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一系列的金融创新③而这种创新与会计制度在清代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会计制度的创新是跟随这种金融创新,还是具有先行性,引领孕育了这种金融创新,值得思考,但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或必不可少的制度是无疑的。。这一系列的创新昭示着传统金融机构的创新转化的到来——即中国早期银行业的形成。目前学术界也注意到了由业务及信用机制角度探讨这一问题,以下我们将举三例加以说明,第一是江南钱铺钱庄,第二是宁波钱庄,第三是山西归化城钱行宝丰社等。
四、从新的信用机制角度探讨“中国早期银行业”
明代中期以后,因为银钱二元货币体制的形成,钱铺钱庄银号形成,三者业务略有不同,但本质上却也相似,尤其是钱铺钱庄开设更为广泛,几乎遍及全国。此前学术界多以为钱铺钱庄银号在刚起源时只经营其特有的银钱兑换业务,以致于一些小微经营者只需一张带有柜子的钱桌便可开张,但实际上钱铺钱庄行业在其初起时,便开始了放款业务,有些还兴起了存款甚至汇兑业务,当然这得是那些有适当规模的钱铺。随着存、贷、汇三大主体业务的综合经营,钱票、银票的运用及这种钱票发行更多向金融机构尤其是钱铺钱庄的集中,某种信用机制形成了。钱铺钱庄银号便开始了向中国早期银行业转化的进程,其时段大体在乾隆,或者在雍正乾隆年间。至少我们可以举出以下三个实例。
第一个例子就是江南地区④此处“江南”指明清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等六府区域。的钱铺钱庄银号。钱铺钱庄银号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普遍出现的信用机构,它活跃于全国各地,相应地,各地钱铺钱庄银号至清代以后也与宁波钱庄一样,发生了同样的带有本质性的变化。江南地区长途贸易及本地坐贾交易均十分频繁,同样相当发达的商镇形成了,城市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形成了引人注目的商业金融中心——苏州、杭州等,还有后来兴起的上海。伴随工商业的发展,江南地区金融机构业务、信用机制发生了变化。范金民在研究江南市场时,对钱铺钱庄银号为代表的江南金融市场也进行了探讨。他指出:“江南银钱兑换活动频繁,数额巨大,大宗贸易的大笔金额往来,市场行情的朝夕涨落,都需要有相应的金融机构为之服务,钱庄因而丛聚于城市中,形成了主要为商业经营活动服务而较典当业更高一级的金融市场。”[14]乾隆以来苏州的钱铺钱庄可能多达150至200家[15]372-374,清末有所衰落,但仍有60余家。上海的钱庄,乾隆年间在城隍庙内园设立了钱市公所。乾隆四十一年到五十年间至少有25家,乾隆最后10年至少有124家[16]254-257。光绪九年(1883),钱庄开始在北施家弄分设南市钱业公所。当时仅上海北市钱庄就“栉比鳞次,无虑数十百家”[16]401,比之清代前期中期,反而有较大发展。
江南钱庄的业务原来也只是从事银两和制钱的兑换①依钱铺钱庄银号,只要规模较大,有比较正式的经营场所,一般业务以兑换为主,但在此同时也会进行存放款业务。不会等到乾隆时期以后才去开展存放款业务。。到乾隆中期,江南地区的钱庄已突破了单纯兑换业务,存放款业务产生了。如在常熟地区,乾隆四十年(1775)便已“广用钱票”[17]。又据咸丰九年(1859)上海钱业重整旧规声称,“上海各业银钱出入,行用庄票百余年矣”[18]。其始用钱票当在乾隆二十年(1755)左右。乾隆中期钱票已在江南普遍使用和流通了。乾隆、嘉庆之交,钱铺用票之风盛行。钱铺经营业务的扩大,兼营存放款业务,吸纳社会游资,使得金融市场更为活跃,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发挥出更大的作用。道光二十一年(1841),上海县的一个告示云:“钱庄生意,或买卖豆麦花布,皆凭银票往来,或到期转换,或收划银钱。”[15]485由此可知,当时上海等地的“商品交易可以通过钱庄签发的票据成交,而且债权债务关系的清理,也可以通过庄票‘到期转换,收划银钱’,相互抵销”[12]。应该指出的是咸丰年以后用的“庄票”与此前道光二十一年及其以前所用的“钱票”“银票”看来是同一类的信用票据。可见清代前期的苏州、上海等地钱庄能够通过庄票为进出口商人提供信贷、结算。
以苏州、上海钱庄为代表的江南地区钱铺钱庄是否在咸丰以前就如宁波钱庄一般有了制度化、专门化的过账制度,并且同城作为一个整体开展过账,还不能肯定。
第二个例子是宁波钱庄。宁波钱庄因与后来的上海钱庄有着血肉的联系,故而影响巨大,对它的研究成果也相当丰硕。而在宁波钱庄与“商业银行”的关系问题上,陈铨亚教授的研究值得注意,他论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他探讨了宁波钱庄的过账制度。此事广为人知,惜材料皆晚出,民国《鄞县志》叙:“市场交易外埠皆用银钱,惟宁波凭计簿,日记其出入之数,夜持账簿向钱肆记录,次日互对,谓之过账。”民国年间的《宁波钱业会馆碑记》有载,云:“海通以来,宁波为中外互市之一。地当海口,外货之转输,邻境物产之销售,率取道于是。廛肆星罗,轮舶日月至,俨然称都会矣。顾去闭关时不远,市中行用,以钱不以银,问富数钱以对。自墨西哥银币流入内地,始稍变其习,然不用银如故。即有需,则准他路银,虚立一名,以钱若银币易之。日有市,市有赢缩,通行省内外以为常。吾闻之故老,距今百年前,俗纤俭,工废著拥巨资者,率起家于商人。习踔远营,运遍诸路,钱重不可赍,有钱肆以为周转。钱肆必仍世富厚者主之,气力达于诸路,郡中称是者可一二数。而其行于市,非直无银,乃亦不专用钱。盖有以计簿流转之一法焉。大抵内力充诸肆,互相为用,则信于人,人故一登簿录,即视为左券不翅也。其始数肆比而为之,要会有时。既乃著为程式,行于全市。其法,钱肆凡若干,互通声气,掌银钱出入之成,群商各以计簿书所出入,出畀某肆,入由某肆,就肆中汇记之。明日,诸肆出一纸,互为简稽,数符即准以行,应输应纳,如亲授受。都一日中所输纳之数为日成,彼此赢绌相通,转而计息焉。次日复如之。或用券掣取,曰畀某肆,司计者以墨圈之,则为承诺如所期不爽。无运输之劳,无要约之烦,行之百馀年,未闻有用此而为欺绐者。虽深目高准之俦,居是邦与吾人为市,亦不虞其他,傥所谓大信者非邪。”②鄞县忻江明撰,民国二十六年本,碑现存宁波钱业会馆。清中后期段光清在其年谱中的咸丰二年(1852),鄞县知县段光清的一份布告里就使用了“甬江过账钱”[19]的说法。咸丰八年(1858)言:“进出只登账簿”,说明运用账本过账的办法已经形成了。至同治三年(1864),有钱业《庄规》言:“议外行划账,其数以三十元起码,多则照数,须于当晚抄录,次早汇集公所划清。”[20]77可见至同治年间,过账制度已经相当成熟。
陈铨亚教授对此十分重视,认为这是传统钱庄走向商业银行的关键因素,在十九世纪早期,“能够产生这一制度,却不能不称其为伟大的制度创建”。为此他根据1932年徐寄安所著《过账须知》对过账制度的具体操作进行了全面概括。然后对这一制度的源起、性质、金融史意义作了全面的考证与分析[21]。
其次,探讨了钱庄贷款种类、直接贷款方式的变化①依以上对学术史、金融史理论梳理,关于贷款种类及其方式变动在此不加论述,因为那是另一历史过程——高利贷资本向借贷资本转化所应探讨的内容,将另撰文论及。及贷款过程中宁波钱庄对于庄票的运用。陈铨亚教授认为:庄票弥补了商业信用的不足,受到了市场欢迎,促进了贸易的繁荣。如宁波乡下的商号使用庄票,也有利于它们之间或与城内商号之间的结算往来。城里商号在过账时,可以在钱庄开设账户,在钱庄领取庄票,然后给债权人签发庄票,作为付款方式,对方收到庄票后向钱庄收款,买家也可用别的钱庄的票支付货款。
再次,他还探讨了所谓宁波空盘市场。陈铨亚教授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创举,如果是实物商品,则是期货,如果是金融商品,则具备金融投资的意义。故而这个空盘市场是中国最早金融投资市场。其交易主体是现水,即以现水的涨落为投资对象。多空双方通过预测现水的变化作投资决策,由现水涨跌中获得收益。其原因在于基础货币供给不足及其与信用货币之间的矛盾,其性质属于虚拟经济。不是期货,不是现代掉期业务,而更像是远期业务;是信用交易,下单时不要相应的资金;有一定的套值功能,这是其合法性理由;是一个凭习惯、信用交易的不规范钱业市场;有经纪人制度;影响扩大至周边地区②陈铨亚《中国本土商业银行的截面:宁波钱庄》,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3页、第95~96页、第97页、第100页、第121页、第125~126页。陈铨亚教授对宁波钱庄研究下功夫很深,也很有新意,但对前辈学者学术观点方法的评介却有点超出学术以外,如说:“很多学者,包括张国辉等,他们对中国近代本土金融的研究实在是很肤浅的,在他们那里,研究问题都采取先画靶再射箭的恶劣作风。他们把钱庄定性为封建性质的金融的理由就是:钱庄只对商业资本贷款,早期没有产业贷款,后期才有生产性贷款产生。”实际上在宁波钱庄那里,生产性贷款是一直存在的,“因而可以粉碎他们的神话”,“他们也可以找出理由说,那些手工业、加工业是工商一体的,既生产又销售,也属于商业资本的范畴”。。
第三个例子是归化钱业——宝丰社。归化城地处大草原和中原地区之间,与张家口一样,是连接草原游牧地区与中原农耕区域的重要结点,同时还是与西北新疆地区贸易的重要枢纽。归化城始建于万历年间。到康熙二十七年(1688),归化城已经发展成为北方重要的商业城镇,是蒙汉贸易的重要汇集地。清代以后,清军对西北用兵,主要的粮草物资就是通过归化城供应。这些商民从归化城出发前往草原,推动了随军贸易的兴起。因此,归化城日益成为北方贸易的重要商业城镇。商贸的繁荣,促进了货币金融业的发展,归化城金融机构应运而生,著名的有钱铺、银号、典当、票号等,据《绥远通志稿》的描述:“乾嘉以后,北路藩商营业日畅,交易纯以银为本位,钱为辅币。同光之交,西路亦通,于是西北两路每年外货输入价值在两千万以上。其时市面现银现钱充实流通。”[20]657但归化城毕竟处于北方边地,铸币的材料,如铜、银等稀少,金融供需产生了较大的矛盾,这种矛盾促使归化城金融业出现了一系列的创新,这些创新集中表现在建立于标期制度基础上的过账制度的萌生及其发展。
因为中国传统商业信用制度(赊购赊销)及资金借贷的普遍化,为了结算的需要,北方及边疆各地商人根据商业运销的季节及周期性,建立了标期制度,具体的标期规定有太谷标、太汾标等③从具体的标期结算的时间看,东口最早,西口较之迟二十余日,之后为太原标,太原标后五日为太谷标,此后为太汾标,这或许与所处地域有所关联。受草原贸易的完成及现银运送需求周期的影响,结算日期自北往南越来越晚。。就内地结算情况而言,可能就是通过账面上的拨兑,余额再以实体货币(银、钱或票钱、票银)支付。这种情况促进了过账制度的萌生,最终发展成为由钱行以过账的形式为同城所有商业字号结算的制度。在此基础上,还有了实体银与记账银之间升水现象,有了因资金借贷而形成的放款利率的有规律性的波动,值得继续详细探究④这种结算有两种情况:一是商品赊销,二是资金借贷。标期制度在广大北方地区皆存在,但似乎都是单个商号与特定的金融机构进行结算,尤其是与票号进行结算,也有与银号进行结算的。但形成同城结算体系的,目前仅见归化城,当然也不能完全否定其他大商镇也在标期制度基础上形成同城结算制度的可能性。关于归化城标期制度为基础的过账制度及因而进一步发展出来的同城结算体系的具体操作规程等,这里不详论,如有机会,欲继续详细探讨。。
那么归化城的钱行、宝丰社及相关的一系列制度与现象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首先随着归化城贸易规模的扩大,为商业服务的金融机构——钱铺也得到了发展,后来组成了同业组织——“钱行”。日本学者今堀诚二认为:“钱行”一词,最早出现于乾隆二十七年(1756)《玉皇阁重建乐楼序》碑,此后嘉庆九年(1804)《重修正殿围墙金装圣像建造山门西楼碑记》碑也有“钱行”捐款记录。嘉庆十一年(1806),《重修龙王庙碑记》中“钱行”遂改成宝丰社①(日)今堀诚二著《中国封建社会の机构———归绥(呼和浩特)におけtf社会集团の实态调查》,汲古书院,1955年,第302页、721页、740页、836页。按:总的说来,民国年间学者所言“绥市钱业昔有钱行社,其组织如何,已不可考,至乾隆年间改组为宝丰社”之说也有几分道理,虽然他没有提出具体史料根据。见《全国银行年鉴》民国25年版。。此后,钱行在归化城的碑刻中,均以“宝丰社”之名出现。
咸丰元年,有归化城副都统整顿钱法的章程言:“谕令钱社与十一社通融,周兑抽拔(拨)现钱,不论现钱、拔(拨)兑,均以四底足钱数。由钱主自便应过帐之家,通行过帐;易换银钱不准勒揹,亦不准行使短数钱文;其十一社如有存钱之家,亦不准勒逼尽数搬取现钱,取具十二社乡总遵结在卷。”②《咸丰元年十月初十归化城副都统衙门钱法章程碑》,转引自吴超、霍红霞《清咸丰元年归化城钱法探析——以咸丰元年十月初十归化城副都统衙门钱法章程碑为中心》,《中华历史与传统文化论丛》,2018年。按:由文义看,其中“抽拔”应为“抽拨”,“拔兑”应为“拨兑”。这里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整顿归化城的铜钱运用中的短陌问题,要求如以前上级政府所要求的那样,“均以四底足钱”,不论是过账的商号用钱,还是钱铺兑换银钱,或者十一社商号存钱均须如此,不准用短陌之钱,也不能强制全部使用现钱。说明到咸丰元年(1851)左右,归化城的过账制度已经实行良久,为社会、政府周知的经济行为。以后咸丰十年(1860)、同治元年(1862)、光绪六年(1880)、光绪十五年(1889)皆有同类章程,即规定短陌定数,不许更低,也不许全使现钱。
结语
由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至十八世纪左右,中国传统金融或者说传统金融机构开始表现出某些新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大体用“商业银行”来表达,或者用“中国早期银行业”来表达,皆无不可。并不是只有宁波钱庄、归化宝丰社、上海钱庄才具有“中国商业银行”或“中国早期银行业”的性质。不是只有几个点,不是机构性、地区性的存在。而是十七八世纪的中国经济大地上,如繁星般萌发出“中国早期银行业”机构,它是一个行业性、区域性的存在。
西方传统金融业或者传统金融机构后来借工业化、近代化或者说资本主义化的强大力量成就强势,对非西方各经济体的金融机构、金融业形成了巨大冲击,但对金融机构、金融业的近代化问题,还得有本土化的、中国化的视角。我们可以在与西方金融业对比的前提下,找到中国传统金融、金融机构的定位。由此发现,虽然中国传统金融业、金融机构因为近代产业的发展缓慢表现出了发展迟滞之势,但长远看来,似乎中西也表现出了相似的发展趋势。中西金融并无本质之别,只有结构之不同,只有发展程度的差异,只有后来才表现出的治理结构的不同。以上论述我们由业务及信用机制角度梳理了学术界的有关研究,从理论厘清了两种思路,并从三个方面对其中一种思路作了宏观的理论的阐述。即由传统货币金融机构走向近代商业银行的历史,探讨这些机构如何在适应经济运行需要而逐渐生成新的业务、形成新的信用机制,当然还可探讨这些机构如何降低利率,如何建立与以前时代不同的经营网络,如何由基层市场调配资金到区域市场调配,再到全国性市场调配资金的历史。这些可以在今后继续探讨。总的说来,这一梳理为中国传统金融机构发展趋势探讨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