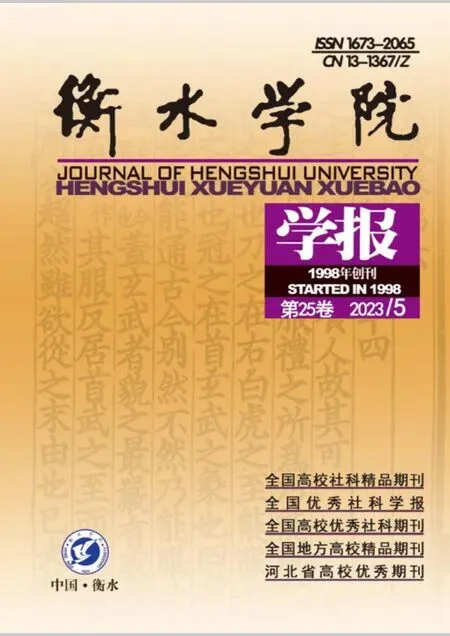《董仲舒与儒学研究》专栏特约主持人按语
台湾著名儒家学者董金裕教授是董子后裔,这些年来一直支持大陆的董学事业,多次莅临衡水参与董学活动,也是董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课题组成员。他比较《史》《汉》之“董传”异同,并分析原因。指出谈、迁父子两代皆曾担任太史令,有机会接触秘府档案,但司马迁受刑后改任中书令,则无法阅览公藏文书,故《史记》的撰作只能依赖前所掌握的文档和搜集的史料,再结合履历见闻、游历访察,对董仲舒所记也只是“学行之大略”;并且,《史记》依赖谈、迁两代之力独自完成,当时并未获得官府认可或协助,只属于“私修史书”。《汉书》起先也经班彪、班固父子两代完成,原本也是私修史书,但最后获明帝肯定并给予协助,因而得以参考秘府史料。天人三策极可能出自中秘之藏,故其“显然较纯粹私修史书详赡周备”。《汉书》虽非设史局所修,不是官修史书,但仍可称“类官修”。考《太史公自序》“余闻董生曰”,又据《史记》董仲舒传记所载语气,“并不易看出彼此有密切之师生关系”。何况司马迁书写董仲舒,并未述其著作;董仲舒传世文献“亦未尝提及司马迁”。可知即使司马迁曾受教于董仲舒,“为时似非甚久,也未必遍阅董仲舒之著述,其对董仲舒之学虽有所了解,可能并不十分深切”。而班固则有机会深度接触董仲舒对策之文字,对董仲舒之学必然有深入的了解,故所记载者较详。其追溯和结论皆十分中肯、精准,语言凝练,分析透当。若能再阐发《史记》只字不提董子三次对策之原因,行文效果则更佳。
董仲舒虽未注解过《孝经》,但其传世文献却屡引《孝经》。除《春秋》外,《孝经》俨然是董仲舒思想体系建构所凭依的重要文本,以至清儒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直称《孝经董氏义》。当代《孝经》研究者中,刘增光副教授出类拔萃,可谓中流砥柱,学术影响盛大。他认真梳理了《春秋繁露》之《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为人者天》《五行对》《立元神》篇与《孝经》的文字渊源和思想联系,并指出,董仲舒之论代表了汉儒对尧舜之道与汉道革命的调和,是对“汉家尧后”的理论证明。董子之“孝”不只是事亲之孝,更是事天之孝,而把“家”“家天下”的事亲之孝提升至“事天”层面,呈现公天下、顺天命之格局。但“圣人之行,莫贵于忠”则是对《孝经》“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的歪曲。董仲舒赋予原本只具道德色彩的《孝经》以鲜明的政治化内容,而成孝治思想。至《五行对》则将“孝经”变成“忠经”,包含浓厚的尊君理念,而从《孝经》“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推演出忠孝皆为天经地义。忠君思想的空前强化显然遮蔽了孝的真义。“无为而治”指尧、舜等圣王皆尊奉天道而治天下,法天而行。董仲舒将“地”等同于“土”,降低了“地”相对于“天”的位置,而仅仅成为天之五行中的一行。“天”作为五行之德、忠孝之德的订立者,地则是施行者。这些都是十分难得的真知灼见,不刊之论,富有重要的启迪意义。通篇述作,文本解读工夫扎实,论证有据有力,结构通透明快。至于把“明改制之义,一统乎天子”仅仅理解为尊王,而断言“与孟子的汤武革命说不同”,则有蔽于董仲舒尊君之理论前提的嫌疑,“君君”则“臣臣”,“君不君”则“臣不臣”。若能对《为人者天》《五行对》《立元神》文本真伪略加考辨说明,分清董子本人的论述与后世董子学派的演绎,文章质量则更佳。
董仲舒传世文献《春秋繁露》之五行编,历来颇有争议。邓红教授撇开真伪考辨而直奔《治水五行》的“七十二日说”,追溯其源头至《淮南子·天文训》、《管子》之《五行》《四时》《幼官》篇、《大戴礼记·夏小正》的“十月太阳历”,一年三百六十日被划分为五个相等的七十二日,对应春、夏、季夏、秋、冬五季,每季两个月,再用五季配以木、火、土、金、水五行。天道以十月之功,而完成阴阳循环的一个周期。但董仲舒也时常以十二个月为一岁,依据的则是当时使用的古历。这“两者属于不同的系统”,就五行而言,十月太阳历七十二日比较好匹配。其反思值得引起重视:一是,按照自然秩序和四季的推移来取舍现实人事,“很难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因为四季是不变的,而人事却因人因时因地而千变万化。更何况,把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仅限定于五行,用五种类型限定丰富的生活,无异于束缚人的想象力和行动的时空。二是,陈久金早在1984 年就出版了《彝族天文学史》,相关论文发表得更早,可自然科学领域天文学史的研究成果三十来年竟然没有引起人文社会科学界特别是中国哲学思想史界的重视,甚为遗憾。诚者斯言,富有启迪,值得深省。
追究董仲舒与公孙弘的关系,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董仲舒传世文献考辨与历代注疏研究》阶段性成果《董子学案》所聚焦的重要问题之一。刘国民教授探寻有力,而指出,在个性人格上,董仲舒是醇儒,品德优良,行为严肃方正,皆合于礼,为人廉直;公孙弘则沉沦于下层,从艰难生活中历练出圆滑、老练、世故的个性特征,外宽内深,内法外儒,表里不一。虽有“曲学阿世”的一面,但也有公义正直的一面,奉命出使匈奴、西南夷后,决不赞同武帝盲目开边而疲敝中国、苦役民众的治理思路,还能够直谏,尽管未能坚持到底;其生活也节俭,善待故人宾客,奉以衣食,养后母孝谨。虽曾欲借胶西王之手而贬抑甚至杀掉董仲舒,但其著《功令》而为博士置弟子员,应该是对元光五年董仲舒兴太学之议的具体落实,功劳不可抹杀。此论平和、端庄,富有理性而客观公允,全面而深邃,近乎历史本来面目,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宋学之于汉学,有突破,也有继承。司马光对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吸收与转化反映了北宋士大夫对天人关系体认,很有代表性。魏涛教授以为,司马光在与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的争辩中阐发出“天人相济”“天人共济”的基本立场和“天者,万物之父也”“天人之际,精祲相感”“君臣上下夫妇朋友,无不以类相应”“违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顺天之命者,天得而赏之”的基本主张,并强调灾异是末,修德为本,天与人各有能力范围和限度,“人必须主动完成人的任务,与天分工合作,才能推动宇宙正常地运行”。司马光的天人观明显吸收了荀子天人相分的思想,实现了对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转化。这种以司马光为个案、以思想承续为线索的研究有利于澄清汉宋之间的学术异同,学术价值可观。
董学重祭祀,不只空言道气心性,还原并接近了早期儒家出身宗教王官体系的本来面目。张树业副教授指出,祭礼不仅承载着人之终极关怀,并且拥有“突出的社会教化效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也有着突出的影响”。唯天子方能举行的郊祀在一切祭礼中地位最尊,象征着最高统治者对天人交通的垄断,也经常成为标榜王朝政权合法性的重要途径。董仲舒一方面坚持郊祀仪制必须以儒家经典所言为准,克服汉前郊祀仪制皆与《春秋》王者之礼不合的问题;另一方面则主张郊礼“为圣人之所最甚重”,力排众议。群臣学者所言民之贫苦饥寒虽是王者所应关注的施政要务,但绝不构成废郊祀的理由。董仲舒郊祀论对武帝朝的郊祀改革起过推动性作用,但并未能真正成为这一过程的主导思想。董仲舒第一次对儒家经典中的郊祀礼制及相关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整合与梳理,也为此后儒家学者郊祀制度改革提供了理论准备。全文述论充沛、征引完备、诠释有力,具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
——从明代朱鸿《孝经》类编著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