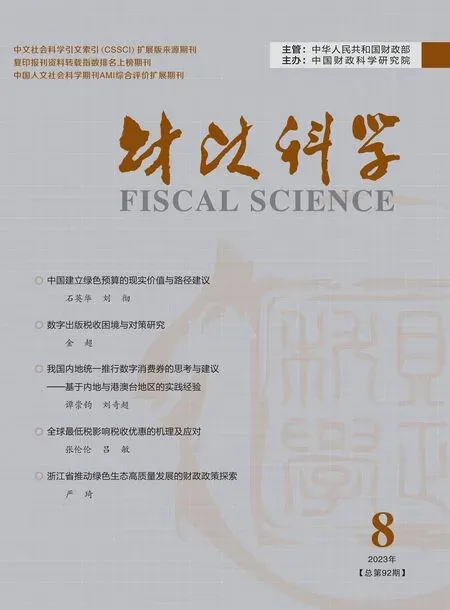全球最低税改革:法理检视与完善进路
陈镜先
内容提要:全球最低税改革的谈判过程呈现出明显的结果导向特征,其设计更多是基于政治驱动和博弈,而非对于最优税收原则的遵循。在此种改革路径之下,全球最低税改革在合法性、合理性与平等性方面均存在着局限性。就合法性而言,全球最低税改革可能对各国的税收主权造成过度限制;就合理性而言,全球最低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BEPS 1.0 阶段提出的价值创造原则;就平等性而言,全球最低税改革由美国和欧盟主导,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规则谈判中缺乏充分的话语权。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当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出发,提出增强全球最低税改革合法性、合理性与平等性的中国方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税收新秩序。
一、问题的提出
2021 年10 月8 日,136 个税收管辖区在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包容性框架下就国际税收制度重大改革达成共识,发布了《关于应对经济数字化税收挑战双支柱方案的声明》。截至2023年6 月9 日,承诺实施双支柱方案的税收管辖区已达到139 个①OECD,“Members of the OECD/G20 Inclusive Framework on BEPS Joining the October 2021 Statement on a Two-Pillar Solution to Address the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 as of 9 June 2023”,https://www.oecd.org/tax/beps/oecd-g20-inclusive-framework-members-joining-statement-on-two-pillar-solution-to-address-tax-challenges-arising-from-digitalisation-october-2021.pdf.。在双支柱中,支柱二将建立15%的全球最低税制度,以打击跨国企业逃避税,并为企业所得税税率竞争划定底线②《G20/OECD 包容性框架136 个辖区就应对经济数字化税收挑战“双支柱”方案达成共识》,国家税务总局,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219/n810724/c5169582/content.html。。全球最低税制度适用于合并集团收入达到7.5 亿欧元门槛的跨国企业集团,如果上述企业在某一税收管辖区的有效税率低于15%的最低税率,则将被征收补足税。
作为国际税法领域的重大变革,全球最低税改革本应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然而,全球最低税改革具有明显的结果导向特征。从OECD 就全球最低税改革发布的一系列文件来看,绝大部分篇幅均是在对全球最低税制度的具体规则进行设计和解释,并由各国对此进行谈判与博弈。因此,OECD工作的重点在于使其主导制定的规则能够在包容性框架下获得通过和实施。
相较而言,OECD 对于全球最低税改革所依据的法理基础并未进行充分探讨,仅在《支柱二蓝图报告》中指出,各管辖区可以自由决定自身的税收制度,包括是否征收企业所得税及其税率水平,但如果所得税低于最低税率,则其他管辖区有权适用全球最低税制度。换言之,如果某一管辖区没有充分行使其首要征税权(Primary Taxing Rights),则其他管辖区有权将这一部分税“征回”(tax back)。
对于此种制度设计的原理,国外学者从目的和手段两个方面进行了解释。从目的来看,全球最低税制度是为了实现单次征税原则(single tax principle)。所谓单次征税原则,是指所有所得都应当且只应被征收一次税(all incomes would be taxed once,and once only)。这意味着既要防止双重征税,也要防止双重不征税。从手段来看,为了实现单次征税原则,当享有首要征税权的管辖区未对所得充分征税时,享有次要征税权的管辖区(secondary taxing jurisdiction)应当对该所得征税(Avi-Yonah,2014)。Ruth Mason 教授将此称为“fiscal fail-safes”,直译为财政失效保护机制,本质上是一种征税不足的补足机制。该机制具有以下四个要素:第一,该机制在不同国家的税收处理结果之间建立起了联系。第二,该机制明确了一国的税收处理结果会引发另一国采取反应措施的条件。第三,在符合触发条件的情况下,另一国将采取特殊的税收措施进行征税。第四,该机制的目的是实现充分征税(full taxation)或避免滥用(Mason,2020)。全球最低税制度正是为了确保当来源国未充分征税时,由居民国征收最低水平的税款,以及当居民国未充分征税时,由来源国征收最低水平的税款(Avi-Yonah,2023)。
虽然上述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论证了全球最低税改革所遵循的基本原理与原则,但单次征税原则和征税不足的补足机制在理论上仍然面临争议,并且与其他国际税法原则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张力,从而导致全球最低税改革在合法性、合理性与平等性方面仍然存在着局限性。从合法性来看,当一个国家未对所得充分征税时,其他国家对该所得进行补足征税是否会损害前者的税收主权?“征税的主权”与“不征税的主权”之间的冲突应如何协调?从合理性来看,如果征收补足税的国家与所得之间并没有充分和实际的联系,是否会违反价值创造原则?在计算补足税时仅对人员工资和有形资产给予排除,而完全不考虑无形资产,是否对于价值创造要素的理解过于狭窄?从平等性来看,此种补足税机制是否在本质上是为了服务于发达国家的利益,而以损害发展中国家的税收政策空间为代价?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一些国家仍会就于己不利的改革作出承诺?对于这些问题,单次征税原则和征税不足的补足机制无法给出有效的回答,现有的研究也未给予充分的阐释。因此,有必要在理论层面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以明晰全球最低税改革的合法性、合理性与平等性。
二、全球最低税改革的法理检视
在结果导向的改革路径之下,全球最低税改革在合法性、合理性与平等性方面均存在局限性:就合法性而言,全球最低税改革可能对各国的税收主权造成过度限制;就合理性而言,全球最低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BEPS 1.0 阶段提出的价值创造原则;就平等性而言,全球最低税改革由美国和欧盟主导,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规则谈判中缺乏充分的话语权。
(一)合法性局限:全球最低税改革对于税收主权的过度限制
根据国家税收主权原则,一国政府有权通过法律确定自己行使征税权的对象、范围、程度和方式,并对一切属于其管辖范围内的人和物进行征税。国家独立自主地行使其征税权力,并不受任何外来意志的干预(廖益新,2008)。基于税收主权,国家既可以选择对其管辖范围内的人和物进行征税,也可以选择对特定的人和物不征税。即便一国选择对特定类型的人和物不征税,同样是该国行使税收主权的体现,并不意味着该国放弃了税收主权(崔晓静、陈镜先,2022)。可见,税收主权实际上包括了“征税的主权”和“不征税的主权”两个维度。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的税收主权并非孤立运行,而是具有溢出效应。由于传统的税收主权观强调税收主权的绝对性,一些国际避税地滥用自身“不征税的主权”,引发了以邻为壑的税收逐底竞争,对其他国家“征税的主权”造成了损害。换言之,虽然其他国家在法律上仍然拥有按照自身的意愿征税的主权,但其征税主权的实现在事实上受到了影响(郑林、陈延忠,2022),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和正当实施。此时,国际避税地行使“不征税的主权”实际上是以损害其他国家“征税的主权”为代价。
出于对其他国家税收主权的正当维护,早在前BEPS 阶段,OECD 就从国内税法、税收协定和国际合作层面提出了应对有害税收竞争的对策建议。在BEPS 1.0 阶段,BEPS 第5 项行动计划专门针对有害税收竞争问题,提出了判定有害税收优惠制度的方法,建立了针对各国税收优惠制度的同行审议机制。在BEPS 2.0 阶段,全球最低税改革首次在全球范围内对各国的企业所得税有效税率划定底线,通过征收补足税来抵消较低的有效税率所带来的竞争优势,旨在通过更加直接有效的方式对国际税收竞争进行多边深度规制。这些举措均是为了限制国际避税地滥用“不征税的主权”的行为,从而恢复自身受到损害的“征税的主权”。
然而,由于“征税的主权”与“不征税的主权”之间往往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国际社会对于税收竞争的规制极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在片面强化“征税的主权”时,对“不征税的主权”造成过度限制。这也体现在全球最低税改革中:在征税不足的补足机制下,当一个国家未对所得充分征税时,其他国家将对该所得进行补足征税。从理论上,这种补足征税是否会损害“不征税的主权”,可以通过考察低税管辖区是否存在有害税收竞争实践而进行判断。如前所述,1998 年OECD《有害税收竞争》报告已经提出了有害税收竞争的识别因素,2015 年BEPS 第5 项行动计划进一步完善了识别因素。据此,如果低税管辖区存在有害税收竞争实践,则其对于“不征税的主权”的行使构成事实上的滥用,其他国家对此采取应对措施正是为了纠正有害税收竞争实践带来的负外部性,因而具有正当性。然而,在实践中,造成低税的原因多种多样,并非所有情形都属于有害税制。例如,各国基于激励研发和创新、促进环境保护等合理目的,制定了各种类型的税收优惠政策,这些税收优惠措施都是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的。特别是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税收优惠仍然是其刺激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崔晓静、陈镜先,2022)。在低税管辖区并不存在有害税收竞争实践的情况下,其他国家仍然征收补足税,则有单方面扩张自身“征税的主权”之嫌。这将会对低税管辖区“不征税的主权”造成损害,限制低税管辖区基于正当目的而选择不征税的权利。就全球最低税改革而言,其实并未明确区分有害税收竞争与良性税收竞争,而是在整体上对企业所得税竞争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态度。因此,在低税管辖区不存在有害税收竞争实践的情况下,全球最低税制度赋予其他国家征收补足税的权利,实际上是以牺牲低税管辖区“不征税的主权”为代价的(Liotti,2022)。许多学者也因此批评全球最低税改革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利用税收优惠措施吸引外国投资的空间(李金艳、陈新,2022a;Liotti,2022;Titus,2022)。
(二)合理性局限:全球最低税改革对于价值创造原则的偏离
价值创造原则是在BEPS 1.0 阶段提出的一项重要理念。G20 和OECD 将价值创造原则作为分配征税权的核心尺度和终极标准(Bal,2018)。根据该原则,利润应在经济活动发生地和价值创造地征税(Profits should be taxed where economic activities deriving the profits are performed and where value is created)①G20,“G20 Leaders’Declaration”,September 6,2013,http://www.g20.utoronto.ca/2013/2013-0906-declaration.html#:~:text=We%20will%20hold%20ourselves%20to,in%20the%20fight%20against%20corruption.。尽管价值创造原则在BEPS 1.0 阶段才被正式提出,但其实际上只不过是对经济忠诚或联结度等更为古老的国际税收理论的现代化表达。价值创造原则的含义包括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从积极含义来看,税收应与经济活动发生地或价值创造地相匹配。从消极含义来看,如果一个国家与经济活动和价值创造缺乏关联,则该国不应享有对利润的征税权(Li et al.,2019)。
在BEPS 1.0 阶段,价值创造原则以不同形式体现在各项行动计划中,特别是在第1 项行动计划和第8—10 项行动计划中体现得尤为明显(Nikolakakis,2021)。BEPS 第1 项行动计划探讨了数字经济背景下无形资产、数据、用户参与等对于价值创造的贡献问题②OECD,“Addressing the Tax Challenges of the Digital Economy,Action 1-2015 Final Report”,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241046-en.,BEPS 第8—10 项行动计划旨在确保转让定价的结果与价值创造相符③OECD,“Aligning Transfer Pricing Outcomes with Value Creation,Actions 8-10-2015 Final Reports”,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241244-en.。
然而,BEPS 2.0 对于价值创造原则并未一以贯之。在双支柱方案中,支柱一根据数字经济商业模式下的价值创造机理来思考和设计利润归属和征税权的划分,创新性地将市场所在地承认为价值创造地(张志勇、励贺林,2021),因此可以说是延续和发展了价值创造原则。然而,支柱二不仅未充分彰显价值创造原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其有所偏离,这种偏离体现在价值创造的地点和要素两大方面。
1.对于征税权分配与价值创造地点一致性的忽视
就价值创造的地点而言,支柱二旨在确保跨国企业的所得被按照最低税率水平征税,而不论其是在何处被征税(即taxing somewhere,no matter where)④Leopoldo Parada,“Taxing Somewhere,No Matter Where:What Is the GloBE Proposal Really About”,September 2,2020,https://mnetax.com/taxing-somewhere-no-matter-where-what-is-the-globe-proposal-really-about-39996.。征收补足税的管辖区既可能是最终母公司或中间母公司所在管辖区,还可能是与低税利润没有任何关联的管辖区。从征税权分配机制来看,收入纳入规则(IIR)相对于低税利润规则(UTPR)的优先适用性以及IIR 自上而下的征收机制主要是基于税收利益的博弈以及可行性和效率的考虑(约阿希姆·恩利施等,2021),而不一定严格地与价值创造地相匹配。
具体而言,IIR 赋予跨国企业集团的最终母公司或中间母公司所在管辖区对在另一个管辖区取得的利润征收补足税的权利,无论这些国家在价值创造和产生利润方面有何贡献(李金艳、陈新,2022a)。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价值创造原则,但尚未达到根本偏离的程度,因为跨国企业集团的最终母公司或中间母公司与低税管辖区的成员实体之间至少还存在间接或直接的控股关系。
相较于IIR,UTPR 则被认为从根本上偏离了价值创造原则。这是因为《经济数字化带来的税收挑战——支柱二GloBE 规则立法模板》(以下简称《支柱二GloBE 规则立法模板》)中的UTPR 并未明确提及“低税支付”,并不要求UTPR 纳税人与低税管辖区的成员实体之间存在导致税基侵蚀的关联支付关系(李金艳、陈新,2022a)。换言之,低税利润不必源自UTPR 管辖区,也不必与UTPR 管辖区有任何关联(如控股关系、关联支付关系)。跨国集团的任何成员实体,只要在UTPR 管辖区拥有员工和有形资产,即为UTPR 纳税人。这反映出UTPR 并不要求征收补足税的国家与利润的产生有任何关联,因而从根本上无视了价值创造原则(李金艳、陈新,2022b)。可见,全球最低税制度并不关注征税权的分配与价值创造的地点是否一致(Nikolakakis,2021),这导致有权根据IIR 或UTPR 征收补足税的管辖区可能并非真正的经济活动发生地和价值创造地。从理论上看,这实际上是全球最低税制度、反混合错配规则等各类征税不足的补足机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只不过在全球最低税制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是因为征税不足补足机制的核心在于,当享有首要征税权的管辖区未对所得充分征税时,由享有次要征税权的管辖区进行补充征税,而享有次要征税权的管辖区与所得之间的联系自然会更加微弱(如IIR 的情形),甚至可能完全缺乏关联(如UTPR 的情形)。因此,尽管此类机制有助于实现充分征税,但不可避免会偏离价值创造原则,带来不合理的结果。
2.对于价值创造要素的狭窄理解
就价值创造的要素而言,全球最低税制度狭窄的公式化经济实质排除规则体现了其对价值创造要素的狭隘理解。该排除规则仅允许排除工资和有形资产的固定回报,而并未对无形资产予以任何排除,主要是考虑到无形资产面临更大的BEPS 风险。虽然此种考虑不无道理,但是却无视了无形资产对于价值创造贡献愈发显著的经济现实。从价值创造要素的演变历史来看,企业在传统经济中主要依赖有形资产进行生产。然而,在新经济中,无形资产在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以及价值创造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Daum,2003)。新经济企业以创新密集型的轻资产公司居多,平台资产、用户数据、品牌等无形资产取代土地、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成为企业价值创造与增长的新驱动力(邱月华、李昱欣,2022)。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统计,2000 年至2014 年期间,无形资产对于制造业产品价值的平均贡献为30.4%,几乎是有形资产份额的两倍①WIPO,“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port 2017-Intangible Capital in Global Value Chains”,https://www.wipo.int/edocs/pubdocs/en/wipo_pub_944_2017.pdf.。可见,经济实质和价值创造并非仅仅来源于有形资产,无形资产的开发、价值提升、维护、保护、应用和推广也是其重要的价值创造活动,并具有相应的经济实质内容。这一点实际上在BEPS 第8—10 项行动计划中已经得到了明确②OECD,“Aligning Transfer Pricing Outcomes with Value Creation,Actions 8-10-2015 Final Reports”,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241244-en.。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时代,专利、算法、数据等生产要素往往是维持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支撑,关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全球最低税制度完全不对无形资产规定任何排除,意味着各国难以通过企业所得税优惠吸引创新密集型的新经济企业。同时,这还会对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投资带来扭曲和歧视效应(Mintz,2022)。早在OECD 就全球最低税制度进行公众咨询时,许多利益相关者就已经指出,在排除规则中仅考虑人员工资和有形资产要素,而不考虑无形资产,将在劳动或资产密集型企业与其他有形资产较少的企业(如金融或保险业)或由无形资产驱动的企业之间产生不合理的差别待遇。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依赖有形资产和劳动力的传统制造业和采掘业,而对新型数字经济的发展不利①Noopur Trivedi,“Pillar Two Substance-Based Carve-Out-‘To Be,or Not to Be’”,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864705;Leopoldo Parada,“Global Minimum Taxation:A Strategic Approach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4280669.。
(三)平等性局限:美欧在全球最低税改革中的主导地位
自20 世纪60 年代以来,OECD 一直在全球税收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然而,由于OECD 被视为“发达国家俱乐部”,其在全球税收治理中的平等性局限长期受到批评②Sieb Kingma,Inclusive Global Tax Governance in the Post-BEPS Era,IBFD,2020,section 6.9.。为了回应质疑,2016 年OECD 在G20 的授权下建立了BEPS 包容性框架。截至2022 年12 月,BEPS 包容性框架共有142 个税收管辖区。按照OECD 的说法,“BEPS 包容性框架的成员遍布全球,除了涵盖OECD 和G20 成员外,还涵盖来自所有地理区域的约70%的非OECD 和非G20 成员。随着包容性和参与度的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观点对于国际税收标准制定的影响正在不断提高”。同时,所有包容性框架的成员都享有“平等参与”(participate on an equal footing)的权利③OECD,“What is BEPS?”,https://www.oecd.org/tax/beps/about/.。
就全球最低税改革而言,截至2023 年6 月9 日,共有139 个BEPS 包容性框架成员就其作出了承诺④OECD,“Members of the OECD/G20 Inclusive Framework on BEPS joining the October 2021 Statement on a Two-Pillar Solution to Address the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 as of 9 June 2023”,https://www.oecd.org/tax/beps/oecd- g20- inclusive- framework-members-joining-statement-on-two-pillar-solution-to-address-tax-challengesarising-from-digitalisation-october-2021.pdf.。如果仅从成员数量上看,全球最低税改革在平等性方面似乎大有改善。但事实上,全球最低税改革仍未摆脱由美欧等发达国家主导的特征,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仍然较为有限。在国际税收治理格局中,“核心——边缘”的结构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西欧和美国等核心区国家仍然掌握国际税收规则制定权,并将其主导制定的规则施加于边缘区的发展中国家(马海涛等,2022)。
从改革动因来看,全球最低税改革提案最初由法国、德国提出,并借鉴了美国的GILTI 税制,其实质是以西方资本输出国为代表的居民国通过税收手段对本国产业外移和供应链外移的系统打压。在资本输出过程中,发达国家面临BEPS 以及产业和劳动机会外移等问题,导致其财政收入减少、产业空心化、失业人员增加(姜跃生,2021)。通过限制边缘区国家的税收主权和税收优惠政策,全球最低税改革能够促使跨国企业利润向发达国家回流,使得利润汇集在核心区(马海涛等,2022)。
从谈判过程来看,OECD 所谓的“平等参与”并未赋予发展中国家实质平等的程序地位和权利。首先,全球最低税制度的文本起草、修改和解释均由OECD 全程主导,发展中国家虽然可以提出意见,但意见能否获得采纳仍然由OECD 决定。一些包容性框架成员的谈判代表曾表示,自己虽然能够自由发表意见,但并不期待自己的意见能对最终决定产生任何影响。其次,由于资金、时间、专业和语言等方面的障碍,许多发展中国家难以有效参与规则的制定,成为“沉默的参与者”(silent participants)①ICTD,“At the Table,Off the Menu? Assess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Lower-Income Countries in Global Tax Negotiations”,https://opendocs.ids.ac.uk/opendocs/bitstream/handle/20.500.12413/15853/ICTD_WP115.pdf?sequence=9.。相比之下,发达国家不仅具有资金技术优势,还通过G7、OECD、欧盟等诸多平台凝聚共识、形成合力。特别是欧盟通过颁布指令率先开展全球最低税的转化立法,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示范性(王鹤鸣,2023)。最后,虽然所有包容性框架成员对于是否同意改革方案享有表决权,但这种表决权的形式意义要大于实质意义,因为即便其对改革方案仍有任何不满,也无法再要求进行修改②ICTD,“At the Table,Off the Menu? Assess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Lower-Income Countries in Global Tax Negotiations”,https://opendocs.ids.ac.uk/opendocs/bitstream/handle/20.500.12413/15853/ICTD_WP115.pdf?sequence=9.。
从规则影响来看,全球最低税改革给发达国家带来的净收益要大于发展中国家。就财政收入而言,许多分析表明高收入管辖区从全球最低税改革中获得的财政收入要多于低收入管辖区,全球最低税改革难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充足的额外收入③OECD,“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Digitalisation-Economic Impact Assessment”,htt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0e3cc2d4-en.pdf?expires=1681980971&id=id&accname=guest&checksum=FD842654A7D78D8D3687FA18B95CD9 F9;South Centre,“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Pillars One and Two”,https://www.southcentre.int/wp-content/uploads/2022/10/RP165_Evaluating-the-Impact-of-Pillars-One-and-Two_EN.pdf.。就主权限制而言,全球最低税改革一方面严格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利用税收优惠措施吸引外国投资的空间,另一方面又为发达国家更为常见的投资基金、国际海运所得、可退还税收抵免、财政补贴等提供了排除或保护规则,从而更有利于发达国家。
可见,全球最低税改革并未从根本上摆脱长期以来全球税收治理存在的平等性局限,而这也成为其面临合法性与合理性质疑的重要原因。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既然全球最低税改革对于一些国家而言并非最优选择,为何其仍会就改革作出承诺?笔者认为,以下几个原因或许能解释为何一些国家会作出“不情愿的承诺”:一是来自发达国家的政治压力。发达国家通过OECD、欧盟、G7 等平台大力推行全球最低税改革,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强大的改革压力。特别是2022 年3 月已有欧盟官员提出将“遵守全球最低税标准”纳入税收制裁标准④Stephen Gardner,“EU Could Write Minimum Tax Compliance into Tax Haven Criteria”,March 17,2022,https://news.bloomberglaw.com/daily-tax-report-international/eu-could-write-minimum-tax-compliance-into-tax-haven-criteria.,而实证研究已经表明欧盟的税收制裁是迫使其他国家加入BEPS 包容性框架的一个重要因素(Oei,2022)。二是征税不足的补足机制产生的倒逼效应。在该机制下,低税管辖区拒绝合作并不会保护跨国企业免于被征收补足税,而只会导致自身的财政收入遭受损失(Mason,2022)。因此,尽管许多低税管辖区本身并不希望征税,但为了避免财政收入损失,仍然不得不选择由自身来征收补足税⑤Heydon Wardell-Burrus,“State Strategic Responses to the GloBE Rules”,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4291190.。这能够解释为何许多典型的国际避税地也就全球最低税改革作出了承诺。三是复杂的规则与紧张的时间表。许多包容性框架成员的谈判代表缺乏必要的专业能力,无法充分理解全球最低税制度复杂的规则,也缺乏足够的时间在签署协议之前向本国的政治领导人通报情况。因此,许多税收管辖区可能仅仅是基于“礼貌”(politeness)而表示同意⑥Jinyan Li,“The Global Tax Agreement:Some Truths and Legal Realities,Osgoode Digital Commons(2022)”,https://digitalcommons.osgoode.yorku.ca/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350&context=all_papers.。四是全球税收治理中的网络效应。长期以来,OECD 一直在全球税收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形成了网络效应。这导致一些国家虽然希望国际税收谈判能够转移到联合国等其他平台进行,却面临高昂的转换成本以及来自发达国家的反对⑦Sieb Kingma,Inclusive Global Tax Governance in the Post-BEPS Era,IBFD,Section 10.3.3,2020.。
三、全球最低税改革法理局限的完善进路
为了改进全球最低税改革的法理局限,有必要深入阐释国际税法的相关理论和原则,并以此为指导对全球最低税的制度设计予以调整和完善。针对合法性局限,需要深化诠释负责任税收主权观,在税收竞争问题上采取更加精细化、差异化的规制立场。针对合理性局限,需要贯彻价值创造原则,从价值创造的地点和要素两个维度对全球最低税制度的设计予以纠偏。针对平等性局限,需要增强全球税收治理机制的平等性,弥补其结构性缺陷与程序性缺陷。
(一)合法性之改进:负责任税收主权观的深化诠释
无论是国际税收竞争还是国际税收合作,都与国家税收主权的行使密切相关(Stewart,2022)。因此,通过深化诠释税收主权观,有助于为国际社会规制税收竞争的合作行动提供理论指引。
从理论上看,“征税的主权”与“不征税的主权”均是中性的概念,“征税的主权”并不必然优位于“不征税的主权”,反之亦然。各国有权根据自身的特殊国情以及公认的国际税收标准选择实施,并应避免滥用税收主权。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二者之间发生冲突时,应如何对其进行协调。传统的税收主权观强调税收主权的绝对性,容易在国家间形成主权对抗(刘剑文,2020)。为此,一些学者提出了“负责任税收主权观”,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税收主权行为之间相互联系、影响日益广泛和深入,税收政策的外部效应使得一国税收政策往往成为双刃剑。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负责任的税收主权观要求一国既要关注本国的税收利益,也要关注他国的税收利益;既要考虑眼前利益,也要协调规划长远利益;既要着力于本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要兼顾国际社会的协调发展。同时,负责任的税收主权并不意味着硬性限制税收主权权力,它赋予主权一种弹性的平衡调整性质,其效果是产生一种结构性的规范约束效力,从而促使各国在享有税收行动自由的同时,与相关各方进行必要的协调平衡(崔晓静,2009)。可见,负责任税收主权观在强调主权的负责任性与合作性的同时,还具有利益协调平衡的属性,这对于协调“征税的主权”与“不征税的主权”之间的冲突尤为重要。因此,有必要在全球最低税改革背景下进一步深化诠释负责任税收主权观。
一方面,负责任税收主权观强调各国行使税收主权应当充分考虑其外部效应,尤其是对他国权益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不利影响,负责任地制定税收法律与政策,并与他国进行充分的协调合作(刘剑文,2020)。全球最低税改革通过补足税机制抵消低税管辖区有害税制的效果,能够纠正有害税收竞争实践带来的负外部性,促使低税管辖区承担其主权责任。另一方面,负责任税收主权观并非简单地对一国税收主权予以硬性限制,而是应当考虑到各国的具体情况和利益需求,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责任能力,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利益和特殊需要。因此,对主权责任标准应严格界定,防止某些国家做扩大解释,从而将其作为攻击其他国家主权的工具(刘剑文,2020)。如前所述,这正是全球最低税改革存在局限之处,因为其既未明确区分有害税收竞争与良性税收竞争,也未合理区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责任负担,导致发展中国家利用税收优惠措施吸引外国投资的空间受到了严格限制。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国际社会可以在税收竞争问题上采取更加精细化、差异化的规制立场。这要求对有害税收竞争与良性税收竞争予以明确区分(Liotti,2022),所有国家均应承担避免参与有害税收竞争的主权责任,而对于良性税收竞争则可以采取差异化的规制立场。例如,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制定专门的豁免规则,使其无害的优惠税制在过渡期内可以不受全球最低税制度的影响(Titus,2022)。又如,在发展中国家被限制参与良性税收竞争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应为其提供合理的补偿和援助,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弥补投资环境存在的先天劣势,实现可持续发展(Chen and Chow,2023)。通过这种精细化、差异化的税收主权责任配置,有助于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正当需求,体现实质正义的要求。
(二)合理性之改进:价值创造原则的指引重塑
关于价值创造原则,虽然一些观点认为其宽泛模糊,但这恰恰是因为其是一项指导性原则而非技术性规则。价值创造原则不仅为现行国际税收体系与规则提供了理论基础,对于国际税收新规则(如保护国家现有税基的反避税规则以及分配新征税权的规则)的发展也应当发挥指引作用(Li et al.,2019)。为了改进全球最低税制度的合理性局限,有必要贯彻价值创造原则,从价值创造的地点和要素两个维度对全球最低税制度的设计予以纠偏。
1.补足税的首要征税权应回归至价值创造所在地管辖区
就价值创造的地点而言,为了实现征税权分配与价值创造地点的一致性,有必要调整完善全球最低税制度的征税权分配机制。由于全球最低税改革的核心宗旨是为企业所得税竞争划定底线,只要相关低税管辖区主动将有效税率提升至15%的最低税率水平,全球最低税改革的宗旨便足以实现,此时不宜再由其他与价值创造关联性更弱的管辖区(即IIR 和UTPR 管辖区)征收补足税。这意味着需要在制度设计上将补足税的首要征税权赋予经济活动和价值创造所在的低税管辖区。只有在该低税管辖区放弃其被赋予的补足税首要征税权时,才可由其他与价值创造关联性更弱的管辖区征收补足税。
在这一点上,合格国内最低补足税(QDMTT)的引入是将首要征税权归还给价值创造所在的管辖区的重要举措。在全球最低税改革的谈判过程中,征税权应如何分配一直是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在《支柱二GloBE 规则立法模板》发布之前,GloBE 规则仅包含IIR 和UTPR 两项规则,其中IIR是首要规则,UTPR 是补充规则,二者均是允许其他管辖区对低税管辖区的所得征收补足税。而2021年12 月发布的《支柱二GloBE 规则立法模板》首次引入了QDMTT,并对其进行了定义。QDMTT 的核心效果在于,如果低税管辖区率先自行要求其境内的跨国企业将有效税率补足至15%,则其他管辖区将不再能够适用IIR 或UTPR 征税。这意味着采用QDMTT 的管辖区在行使征税权方面能够优先于其他原本能够适用IIR 或UTPR 的管辖区。
可见,QDMTT 的引入,实际上对全球最低税制度的征税权分配机制形成了重要变革,使GloBE规则从“IIR+UTPR”的二元组合变成了“QDMTT+IIR+UTPR”的三元组合,并且QDMTT 在适用顺序上属于最优先的规则。这不仅有助于维护采用QDMTT 的管辖区的税收利益,也能够使补足税的首要征税权回归至价值创造所在的管辖区。这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重要,因为QDMTT 有助于保护这些提供了税收优惠且有经济活动发生的国家的征税权①OECD,“Tax Incentives and the Global Minimum Corporate Tax:Reconsidering Tax Incentives after the GloBE Rules”,https://doi.org/10.1787/25d30b96-en.。例如,非洲税收征管论坛指出,由于大多数非洲国家境内都仅有数量非常少的最终母公司,很少有非洲国家能根据IIR 征收补足税。同时,由于UTPR 仅仅是IIR 的补充规则,UTPR 也难以为非洲国家带来充足的补足税收入。然而,QDMTT的引入则为非洲国家提供了优先征收补足税的机会。为了帮助非洲国家实施QDMMT,非洲税收征管论坛于2022 年12 月发布了QDMTT 立法指南①ATAF,“ATAF Suggested Approach to Drafting Digital Services Tax Legislation”,accessed May 5 2023,https://events.ataftax.org/index.php?page=documents&file_id=79¬e=downloadfile.。从时间来看,这一时间甚至早于OECD 发布《GloBE 规则征管指南》(2023 年2 月)和《第二套GloBE 规则征管指南》(2023 年7 月)的时间,足见以非洲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对于QDMTT 的高度重视。
鉴于QDMTT 重要性的跃升,OECD 也在不断推动QDMTT 规则的完善。2021 年12 月发布的《支柱二GloBE 规则立法模板》对于QDMTT 的规定仍然十分简略,仅在第10 章(定义)对QDMTT 进行了定义,规则的详细程度远远不及通过第2 章整个章节进行规定的IIR 和UTPR。而后续发布的《GloBE规则征管指南》和《第二套GloBE 规则征管指南》则对QDMTT 作出了更加详细的规定,不仅提出了判断国内最低税是否“合格”的基本原则,还对QDMTT 的适用范围、征税规定、补足税计算、征管规定、安全港规则等内容作出了系统性的规定。可以预见,在全球最低税的转化实施过程中,引入QDMTT 将成为各个税收管辖区维护征税权的重要措施。
2.低BEPS 风险的无形资产应被视为价值创造的要素之一
就价值创造的要素而言,价值创造原则要求全球利润被分配至生产、营销,以及无形资产的开发、价值提升、维护、保护、应用和推广所在的管辖区,而一个多要素的公式能够更加契合价值创造原则(Li et al.,2019)。全球最低税制度的公式化经济实质排除规则目前仅包括人员工资和有形资产两项要素,而未将无形资产考虑在内。因此,为了承认无形资产对于价值创造的贡献,避免对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投资造成扭曲,有必要将无形资产也纳入公式化经济实质排除规则。
当然,与人员工资和有形资产相比,无形资产通常具有更高的BEPS 风险,因此需要在规则设计上特别防范BEPS 风险。例如,可以将有资格获得排除的无形资产限定为BEPS 风险较低的无形资产,如跨国企业自行研发形成的无形资产,或者从非关联方购入且用于生产经营活动(而非仅仅用于许可使用)的无形资产②“Com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Digitalisation:Public Comments Received on the Pillar One and Pillar Two Blueprints”,https://www.oecd.org/tax/beps/public-comments-received-on-the-reports-on-pillar-one-and-pillar-two-blueprints.htm.。同时,可以与BEPS 第8—10 项行动计划已经确立的无形资产转让定价指导原则进行衔接。BEPS 第8—10 项行动计划区分了无形资产的法律所有权和经济所有权:在转让定价中,仅拥有无形资产的法律所有权本身并不能自然拥有无形资产的收益权,无形资产的收益权归属取决于跨国企业集团内各关联方对无形资产的价值创造所作出的贡献,即在无形资产的开发、价值提升、维护、保护、应用和推广过程中所执行的职能、使用的资产和承担的风险(韩传模、励贺林,2015)。据此,全球最低税制度对于无形资产的公式化排除应与现有的无形资产转让定价指导原则保持一致,要求跨国企业成员实体需对无形资产的价值创造作出贡献才可享受排除。这样既能实现制度之间的协调,也有助于避免仅仅拥有无形资产的法律所有权但未对其价值创造作出任何贡献的成员实体享受排除。
(三)平等性之改进:全球税收治理机制的优化完善
增强全球税收治理机制的平等性,不仅对于弥补全球最低税改革的平等性局限具有积极作用,对于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税收新秩序也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全球税收治理机制的平等性局限大致可分为结构性缺陷与程序性缺陷。其中,结构性缺陷主要是由于不同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巨大差异,导致不同国家的权力和影响力不平衡;程序性缺陷主要是国际税收规则商讨过程中产生程序上的不平等,包括国际治理机构及其进程设计过程排除受其规则和标准影响或制约的部分国家参与,并且产生的结果不一定符合所有受规则影响的国家的利益(洪菡珑,2021)。因此,可以从弥补结构性缺陷与程序性缺陷的角度出发,对全球税收治理机制进行优化完善。
针对结构性缺陷,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增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税收治理的能力。2021 年,OECD 发布的《发展中国家与OECD/G20 BEPS 包容性框架》报告已经承认,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双支柱”改革谈判中面临障碍,难以有效参与。为此,有必要从资金、时间、专业和语言方面帮助发展中国家克服困难。在资金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前往OECD 总部巴黎开会需要产生高昂的开支,有必要为资金匮乏的发展中国家代表参与重要的会议提供资金支持。同时,对于复杂性和重要性较低的会议,可以通过线上方式召开,以降低参会成本。在时间方面,应避免为规则的谈判、表决和实施制定过于紧张的时间表。在专业方面,OECD 可单独或联合IMF、UNCTAD 以及非洲税收征管论坛、“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等全球性或区域性组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专业培训。在语言方面,应确保非英语国家能够及时获得所有重要文件的翻译①OECD,“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OECD/G20 Inclusive Framework on BEPS:OECD Report for the G20 Finance Ministers and Central Bank Governors”,https://www.oecd.org/tax/beps/developingcountries-and-the-oecd-g20-inclusive-framework-on-beps.htm.。
针对程序性缺陷,需要构建更加包容、平等、透明的国际税收规则制定程序。在宏观理念层面,要求所有国家在国际税收规则制定中都享有平等的程序地位,有权平等参与议程设置、规则谈判与最终表决。当然,在制度框架层面,目前存在两种不同的改革方案:一种方案是完善BEPS 包容性框架,进一步增强其成员的多元性,在各层级的机构中增加一名来自非OECD 和非G20 国家的代表作为联合主席,确保发展中国家的诉求能够在议程设置中得到体现,以及公布发展中国家参与包容性框架的信息等②OECD,“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OECD/G20 Inclusive Framework on BEPS:OECD Report for the G20 Finance Ministers and Central Bank Governors”,https://www.oecd.org/tax/beps/developingcountries-and-the-oecd-g20-inclusive-framework-on-beps.htm.。此种方案仍然坚持OECD/G20 主导的BEPS 包容性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完善。该方案的优点在于改革阻力与难度相对较小,并且能够继续借助OECD 在税收领域的专业优势,但缺点在于改革不够透彻,对于民主性的提升可能相对有限。另一种方案是在联合国框架下设立更高级别的税收机构,使其替代OECD 成为全球税收治理的主导力量。目前,联合国在税收领域的工作主要由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承担。该委员会设立于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之下,由各国政府提名的25 名成员组成。然而,由于地位和资源的局限性,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在全球税收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一直较为有限。为此,许多国家一直呼吁在联合国框架下设立更高级别的税收机构,但这些提案屡屡遭到发达国家(特别是OECD 成员国)的反对。虽然发达国家声称的理由是“避免机构重复”,但不难想见其真实意图是避免OECD 在税收领域的主导地位被联合国取代③Sieb Kingma,Inclusive Global Tax Governance in the Post-BEPS Era,IBFD,2020,Section 7.9.。不过,在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的推动下,联合国大会于2022 年12 月30 日通过了《在联合国促进包容和有效的国际税务合作》决议。该决议明确联合国大会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就如何强化国际税务合作的包容性和有效性展开政府间讨论,包括研究开发一个国际税务合作框架或文书的可能性④联合国大会:《在联合国促进包容和有效的国际税务合作》,A/RES/77/244,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financing/sites/www.un.org.development.desa.financing/files/2023-02/A%20RES%2077-244%20Chinese.pdf。。此外,2023 年3 月,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批准在《UN 税收协定范本》中纳入应税规则(STTR)。与OECD 起草的STTR 相比,联合国版本的STTR 适用范围更广,并且更简易①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第二十四届会议报告》,E/2022/45/Add.1-E/C.18/2022/2,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22/371/70/PDF/N2237170.pdf?OpenElement。。可见,尽管在联合国框架下设立更高级别税收机构的方案不可避免会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阻碍,但上述最新实践表明这一方案并非完全不具有可行性。更重要的是,从长远来看,该方案将更有助于提升全球税收治理的平等性,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不过,对于上述方案的选择并非一蹴而就,仍有待于各国与国际组织的博弈与商讨。
四、结 语
正如Tsilly Dagan 教授(2018)曾指出,合作本身并不足以确保正义的实现,国际税收合作并不一定能满足所有参与方的最佳利益。虽然全球最低税改革已在BEPS 包容性框架下获得139 个税收管辖区的政治承诺,并已进入国内转化实施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在理论层面无懈可击。相反,由于全球最低税改革的结果导向特征,其在理论上仍然存在合法性、合理性与平等性局限。从后果来看,这些局限不仅会阻碍全球最低税改革的有效实施,促使部分国家间接规避其约束,更会维系和加剧长期以来国际税收体系不平等的状况。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当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出发,提出增强全球最低税改革合法性、合理性与平等性的中国方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税收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