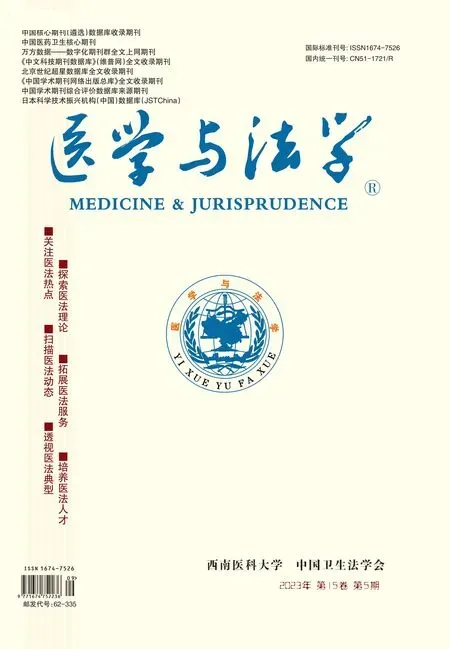美国传染病隔离法律规制的内容评析
毛颖婕 陈绍辉
在美国法中,“隔离”所对应的术语为"quarantine"和"isolation",前者有“检疫”和“隔离”的双重含义,后者则仅指“隔离”。尽管有关的成文法和判例法对这两个概念经常不作区别地交互使用,但两者并不相同,有着严格区别。[1]“检疫”是指为防止疾病传播,对可能接触处于传染期的传染病人但自身尚无症状的人员限制其活动的行为。“隔离”则是指对已患病且处于传染期的人员予以隔开,以防止传染病的传播。[2]因此,检疫和隔离的区别在于两者所针对的对象不同,前者仅限于无症状的密切接触者,后者一般为确诊的传染病病人或具有症状的疑似病人。无论是检疫还是隔离,两者本质上都属于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尤其是检疫措施限制了大量无症状人群的活动和自由,容易引发巨大的法律和道德争议。[3]本文所指的“隔离”(quarantine)既包含检疫也涉及狭义的隔离。由于强制隔离涉及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必要通过立法明确强制隔离权的行使界限与规则,以避免这一权力过度地侵犯个人自由,同时也能规范政府行为以保护公共健康。本文拟通过对美国传染病隔离法律规制的梳理、分析和评价,总结其中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一、美国传染病隔离法律规制的历史变迁和现状
(一)美国传染病隔离法律规制的历史变迁
在美国,有关隔离的立法可追溯到殖民时代。1647 年马萨诸塞殖民地颁布了北美殖民地的首部检疫法,目的是隔离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船只以预防鼠疫。在纽约和波士顿等港口城市,公共健康威胁的主要来源是黄热病和霍乱等传染病,因此要求乘客入境前进行体检,实行强制检疫是十分有必要的。这些地方所在的州政府早于美国联邦政府制定了地方的检疫法,从而确立了地方政府对公共卫生事务享有管辖权的法律传统,这也体现了各州对管理公共卫生、安全和道德权力的宪法保留。[4]
1796年美国国会颁布了第一部联邦《检疫法》,授权联邦政府协助各州实施检疫。内战结束后,联邦政府试图扩大中央的检疫权,但遭到了各州的强烈抵制。1799年国会废除了1796年法案,取而代之的是《检疫法》和《健康法》,随后成立的海军医院服务部,标志着联邦政府开始享有原本属于州政府管辖范围内的检疫权力。[5]1878年,国会修改了《检疫法》,授予海军医院服务部更大的检疫权。1912年,海军医院服务部在1902年更名后再次更名为“公共卫生服务部”,随后原本隶属于各州的检疫站也全部移交给联邦政府统一管理。1944 年,国会颁布了《公共卫生服务法》,旨在进一步巩固联邦政府对州际贸易和国际贸易中流动的货物和人员的检疫权。自1967年以来,隶属于联邦政府下健康与人类服务部的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以下简称“CDC”)负责实施检疫措施。
(二)美国联邦政府有关传染病隔离法律规制的现状
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实施传染病隔离措施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公共卫生服务法》,该法授权联邦政府享有实施传染病检疫等命令的广泛权力。例如,该法第三百六十一条授权CDC 主任制定和实施规则,以“防止传染病从外国传入、传播或扩散到各州或属地,或从一个州或属地传入其他州或属地”①;同时,为防止传染病的传入、传播或扩散,该法授权联邦政府制定“对个人实施逮捕、拘留或有条件释放”的规则②。该法第三百六十一条(c)进一步规定跨国检疫的措施,授权联邦政府“为防止传染病的传入、传播和扩散,对从国外进入任何一州或领地的个人实施逮捕(apprehension)③、拘留(detention)或有条件释放(conditional release)”④;第三百六十一条(d)规定了跨州检疫措施,授权联邦政府“对有合理怀疑感染传染病的任何个人进行拘留和检查,如果该人在传染期内(qualifying stage)(1)正要或将要从某一州进入另一州;(2)能成为传染源,他人一旦感染这一疾病,将从一个州进入另一个州”。相关传染病的“传染期”是指该传染病正处于传染期,或者处于传染前的阶段,如果该疾病一旦传播给他人将可能会造成公共卫生危机;一旦经检查发现该人已经感染的,可以以合理必要的方式在合理期限内将其予以拘留。⑤
根据《公共卫生服务法》的授权,美国健康和人类服务部会同CDC制定了联邦检疫规则,其最新修订时间为2017 年2 月,列于联邦法典第四十二卷第七十条。该检疫规则授予CDC广泛的检疫权力,包括对任何个人实施逮捕、医学检查、检疫、隔离或有条件释放⑥,并进一步明确了实施检疫、隔离的条件和程序。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法律所规定的传染病仅限于总统以行政令(Executive orders)形式指定的传染病。换言之,《公共卫生法》授权联邦政府所采取的检疫措施仅适用于行政令清单上所列的传染病。目前,法定的检疫传染病包括霍乱、白喉、传染性肺结核、鼠疫、天花、黄热病、病毒性出血热,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和引起大流行的新型流感。如果需要增加检疫传染病,只能通过总统颁布新的行政令予以增加。
可见,《公共卫生服务法》授予联邦政府几乎不受限制的隔离权——只要怀疑个人接触了传染病即可隔离或拘留该人,且该法没有规定实施隔离命令所应遵循的正当程序。此外,该法并没有具体规定对隔离命令应适用何种法律标准,也没有规定该命令的有效期限。[6]
(三)美国各州政府有关传染病隔离的法律规制现状
传统上,美国各州政府享有对本辖区符合条件的对象采取检疫和隔离的权力,具体包括在公共卫生领域实施检疫、隔离、接种疫苗、疾病报告、旅行限制、接触者追踪、医学检查、治疗以及扣押财产等权力。在发生传染病大流行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由公共卫生部门决定是否依据州法实施隔离,且多数州都要求只有当州长或其他公职人员宣布出现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时才可以使用隔离措施。[7]
然而,各州的检疫法千差万别,缺乏统一性,且不少州的立法十分落后,不足以应对日益严峻的传染病防控形势。“911事件”爆发后,为应对生物恐怖主义威胁和传染病所造成的紧急公共卫生事件,乔治城大学法律与公众健康中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联合发布了《州紧急卫生权力示范法案》(Model State Emergency Health Powers Act,MSEHPA,以下简作《示范法案》)。《示范法案》旨在扩大州政府所享有的包括检疫权在内的公共卫生权力,并为各州、地方立法机关和卫生当局推进公共卫生改革提供指引。《示范法案》的第六百零四条和第六百零五条对检疫和隔离作了框架性规定,包括隔离的条件、原则、程序等。到2006 年,24个州通过法律将《示范法案》的第六百零四条吸收,作为其隔离和检疫的一般原则;20个州通过法律吸收《示范法案》的第六百零五条,作为其隔离和检疫的正当程序[8],其中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莱纳州全盘采用了《示范法案》的规定[9]。
(四)美国传染病隔离的相关司法判例
无论是联邦法院还是州法院,涉及检疫和隔离的判例数量都有限,大致包括两类:一是确认联邦和州检疫和隔离权的案件;二是涉及隔离法律程序的案件,这部分案件主要由州法院判决。本部分主要介绍第一部分判例,对于正当程序的案件则在后文介绍。
在美国,鉴于检疫隔离权系州为保护公共健康所固有的权力,法院对联邦和州政府行使该权力的行为向来较为支持。这一司法传统可以追溯到1824年的“Gibbons v.Ogden案”,联邦最高法院在此案中确认了州基于其警察权而实施检疫法的权力,从而确立了州行使检疫和隔离权的宪法依据。⑦在1905 年“Jacobson v. Massachusetts 案”中,联邦最高法院确认州和地方政府为防止疾病的暴发和流行,有实施强制免疫计划的合法权力,从而为各州以公共健康的名义限制个人自由提供了宪法依据。⑧在此后的100 余年中,联邦最高法院没有再审理过检疫、隔离案件,对于检疫、隔离所应遵循的正当程序也从来没有发表过意见。然而,联邦最高法院在其他案件中就个人在特定情形下被剥夺人身自由时应享有正当程序的权利作出了大量重要判决⑨,这些判决所确立的正当程序规则是否适用于传染病隔离案件仍有待进一步明确。
联邦地区法院和州法院也很少审理检疫隔离案件[10];在为数不多的案件中,法院也秉持了对政府权力的遵从。在“U.S.cx rel.Siegel v.Shinnick 案”中,原告从暴发天花并大规模流行的斯德哥尔摩回到纽约后因无法出具接种天花疫苗的证明而被强制隔离,但联邦地区法院拒绝了原告在被隔离后的人身保护令申请,认为卫生当局“明显出于善意(good faith)”,并享有充分的裁量权认定原告在斯德哥尔摩期间有机会接触到天花病毒,从而认定隔离的合法性。⑩
同样,在“Reynolds v. McNichols 案”中,法院认可将一名妓女予以拘禁以便使其接受性传播疾病的检查和治疗的合法性,从而拒绝了其平等保护的主张。⑪在上述两例案件后,联邦地区法院仅对两例涉及传染病隔离的案件发表意见,其中,在“Haitian Centers Council v. Sale 案”中,法院认定对HIV 阳性的海地难民的拘禁决定违反宪法。⑫同样,州法院对州所享有的隔离权给予极大地尊重,如在“Barmore v.Robertson案”中,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认为州享有的保护公众健康的广泛警察权力是州所固有的且不得放弃的权力。⑬
二、美国传染病隔离法律规制中的实体条件
(一)联邦法律中的实体条件
《公共卫生服务法》和联邦检疫规则对隔离的实施规定了较为宽泛的条件,公共卫生当局只要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即“合理怀疑一个人感染检疫传染病”,便可以对该人采取包括隔离在内的拘禁措施。
联邦检疫规则所规定的检疫和隔离的条件与《公共卫生服务法》基本相同,只要公共卫生当局基于一定事实“合理怀疑一个人感染检疫传染病(Reasonably believed to be infected)”,即可对该人实施逮捕、医学检查、检疫、隔离或有条件释放。⑭所谓“合理怀疑感染传染病”是指根据有力的事实(articulable facts),公共卫生官员可以合理地推断出个人已经直接或间接暴露于导致检疫传染病的传染源,如与感染者有过接触或接触感染者的体液、接触受污染的环境或中间宿主或传播媒介,并且由于暴露而导致个人体内已经或可能携带该检疫传染病的传染原。⑮根据这一规定,特定当事人是否应采取隔离等检疫措施,要求公共卫生官员根据明确的事实可以合理地推断出某人已直接或间接接触了传染源,而这一推断或怀疑应建立在一定事实和科学依据之上,而非仅仅是主观臆断。
(二)各州法律中的实体条件
各州有关隔离的实体要件宽严不一。以《示范法案》为例,临时拘禁的条件是“迟延实施隔离或检疫将严重危及公共卫生当局防止或限制传染病的传播或传染给他人”⑯。它实际上强调传染病传播和危害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但这一事实的认定完全由公共卫生当局裁量决定,不受法院审查。对于需经法院审查决定的隔离决定,法院许可隔离的条件是“有优势证据证明,为防止或限制传染病的传播或以防有合理心要采取隔离或检疫传染他人”⑰。根据这一规定,只要具有防止传染病传播的合理必要,即可采取隔离措施,且证明标准为最低的优势证明标准,其实施条件十分宽松。同时,《示范法案》还强调隔离和检疫必须是防止传染病传播或传染他人所必须的最小限制方式。⑱当然,也有不少州采取更为严格的实体条件,如迈阿密州规定卫生部门如果要采取隔离,必须以清晰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第一,该人曾接触传染病或有传播疾病的重大医疗风险,并对公共卫生构成严重的、迫在眉睫的风险;第二,没有更小限制的替代性措施。⑲
(三)传染病隔离实体条件的相关司法判例及学说观点
目前,仅有少量判例对传染病隔离的实体要件发表过意见。个别案件中,法院认为对传染病病人的隔离应遵循最小限制原则,即只有在没有其他更小限制性替代措施(less restrictive alternatives)的情况下,方可采取隔离措施。⑳因此,各州立法和判例都倾向于将最小限制原则作为隔离和检疫的条件,其目的当然是避免过度使用隔离这一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在能够达成相同目的的情况下,应采取其他限制性更小的措施。相对于联邦和州法对隔离实体条件持相对“放任”的态度,学界的观点则更为严苛。戈斯金教授认为,隔离应符合以下要件:一是州必须具有紧迫的利益;二是必须是有针对性的干预;三是必须符合最小限制性替代原则;四是必须符合程序性正当程序。[11]也有学者综合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认为在公共卫生领域实施干预措施应包括以下前提条件:一是具有公共卫生干预的必要性;二是干预的手段与目的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三是均衡性,干预措施既不过于狭隘,也不过与宽泛;四是在实现目的的同时,以最小限制的方式限制个人权利,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害。[12]类似观点认为,隔离只有为了保护公共健康利益,在没有其他替代措施且有科学证据的情况下,方可使用;除非具有绝对必要,否则卫生当局应针对特定对象适用隔离措施,避免针对群体或地域作出隔离决定。[13]
(四)总结与评析
综上可见,联邦法律和州法一般对隔离条件的规定相对宽松,其目的恐怕主要是保障政府应对传染病危机享有足够的空间和裁量权。相反,学说观点则对政府以公共健康为名干预个人自由持警惕态度,因而对强制隔离的启动设定更为严格的条件。综合联邦和各州立法及相关学说观点,强制隔离的实体条件可概括为三个原则:第一,必要性原则。隔离应以个人感染或可能感染传染病,若不采取隔离措施将可能导致该传染病传播或扩散的严重风险为前提。换言之,“只有通过广泛的科学研究发现一种疾病具有传染性时,政府才应采取强制卫生措施”,且这一措施只能适用于“那些实际接触到该病的人”。[14]第二,均衡原则。该原则要求实施隔离措施所要实现的公共利益与个人所受侵害的严重程度之间保持合理的平衡,避免以不必要的方式或强度造成个人过重的负担或损害。第三,最小限制原则。根据该原则,应将隔离作为最后行使之手段,如果存在其他限制性更小的替代措施,也就没有必要采取隔离。
三、美国传染病隔离法律规制中的程序性规定
(一)联邦法律中的隔离程序
如前所述,《公共卫生服务法》授予联邦政府在传染病防治中广泛的权力,包括检疫和隔离权。然而,《公共卫生服务法》对检疫隔离的实施程序几乎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如前文所述,基于《公共卫生服务法》的授权,美国健康和人类服务部会同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制定了相应的检疫规则,其最新修订时间为2017 年2 月。新的检疫规则授予CDC 广泛的检疫权力,包括对任何个人实施逮捕、医学检查、检疫、隔离或有条件释放,[21]并对检疫、隔离的程序作出较为细致的规定。
1.隔离决定的作出。
对于患有或可能患有检疫传染病应予以检疫隔离或隔离的个人,CDC主任应签发书面的命令,并在当事人被羁押后的72小时内将该命令送达给本人。在命令下达后的72小时内,主任必须重新评估该人是否应继续采取隔离措施。在重新评估中,应审查签发联邦命令所应考虑的全部信息,并考虑为保护公共健康利益是否存在其他更小限制性替代措施。[22]经重新评估,如果认为应当继续隔离的,应立即签发继续隔离的联邦命令。[23]
2.隔离决定的救济。
联邦检疫规则为被隔离者提供了内部救济途径,即医疗复审程序(medical review)。具体而言,对于延长或变更隔离或检疫的命令,被隔离者可以向CDC 申请医疗复审,而申请复审的请求仅限于确定“主任是否有合理的理由认为该人感染检疫传染病[24]”。根据这一规定,医疗复审以被隔离者的申请为启动条件,且请求审查的事项和范围亦十分狭窄。在收到复审申请后,检疫规则没有规定进行复审的时限,仅规定主任“应尽快进行复审”,并指定1名审查员审查相关医疗和其他证据。检疫规则考虑到了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包括:其一代理。在复审过程中,被隔离者可以自费委托1名辩护人(如律师、家庭成员或医生)提交证据,经审查员的同意,可以申请医疗专家出庭。对于贫困的被隔离者,经本人申请,主任可以决定为其指定代理人。[25]同时,CDC主任应采取合理必要的措施保障被隔离者与其辩护人或代理人的沟通。[26]其二获取证据。在复审举行前,被隔离者的辩护人或代理人有权审查相关可及的医疗及其他资料。[27]其三参与权。医疗复审可根据实际采取电话、视频会议或其他方式,从而保证被隔离者能够参加复审。在复审结束后,复审员应基于其认定的事实和相关证据,向主任提交书面报告,报告应基于其专业判断表明检疫或隔离是否应撤销、继续或变更,并指出否存在其他限制性更小的措施。主任在受到报告后,应尽快对报告和被隔离者及其代理人的意见进行审阅,并尽快签发书面的联邦命令,及时送达给被隔离者及其代理人。[28]
3.总结和评析。
从上述检疫规则的程序看,无论是作出隔离决定,还是对隔离决定的医疗复审,其审查的重点似乎都是当事人是否患有检疫传染病这一事实问题,而对当事人是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这一要件,明显审查不足。[15]同时,联邦法律中的隔离程序规定还存在以下不足:隔离的期限没有明确的时间限制,事实上是一种不定期的拘禁;复审期限也缺乏明确的时间限制,包括复审的举行时间、复审决定的作出等;复审程序偏向于采取职权主义的审查,缺乏对抗性正当程序的要素,如质证、辩论等;对隔离决定的救济是一种内部的行政救济程序,尽管联邦检疫规则也明确表示该规则不影响当事人就其拘禁寻求司法审查的宪法或法定权利,[29]但当事人的司法救济主要依赖人身保护令,但这一救济渠道事实上是虚幻而不可及。CDC 曾披露,州及地方卫生部门对29789人实施相关卫生监控措施,但只有1人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16]
(二)各州法律中的隔离程序
各州有关检疫和隔离的程序并不一致,不少规定差异较大。为统一各州的检疫法,《示范法案》在这方面作出很大的努力。尽管《示范法案》仅仅是推荐和指引性的法案,但考虑到它主要是综合现行各州的规定所拟定,且内容和条款被不少州部分或整体采纳,基本反映了当前各州检疫法的基本概况。为便于从整体上了解各州的隔离程序,本部分主要以《示范法案》为主,旁涉相关州的具体规定,对州的隔离程序综合予以介绍。
与多数州的规定一样,《示范法案》将隔离区分为无须告知的临时隔离和需要告知的隔离,前者是在紧急情况下由公共卫生当局实施的临时隔离,期限为10 日,且无需事先向法院申请许可,这一类型的隔离在一些州又称为紧急隔离;后者则需要公共卫生当局向法院申请,经法院许可方可实施的隔离。
1.临时隔离。
如果迟延实施隔离或检疫将严重危及公共卫生当局防止或限制传染病的传播或传染给他人的,公共卫生当局可以以书面指令形式对个人或群体作出临时隔离或检疫。书面检疫指令必须载明以下信息:(1)被隔离的身份;(2)隔离、检疫的场所;(3)起始日期(4)如果能确定的话,还包括疑似传染病的名称。书面指令的副本应送达给被隔离的个人,如果指令针对群体且无法为每个人提供副本的,可公告于隔离场所。如果需要延长隔离的,公共卫生当局应该在签发书面指令的10 日内向法院申请授权延长隔离。[30]可见,《示范法案》授予公共卫生当局在临时隔离程序中十分宽泛的权力,相关程序规定十分简便和灵活,目的当然是保障公共卫生当局能够及时采取措施应对传染病事件,毕竟在紧急情况下,事先告知和申请法院许可不仅缓不济急,也完全不具有可行性。至于临时隔离的期限,《示范法案》规定为10日,有的州规定更短,例如迈阿密州规定,紧急临时拘留的期限为5天。[31]
2.需要通知的隔离。
首先,这种类型的隔离需要公共卫生当局向初审法院提交书面申请,申请授权对个人或群体予以隔离或检疫隔离。公共卫生当局必须在申请后的24 小时内将向法院申请隔离命令的通知送达给受影响的个人或群体。法院在收到申请后5日内举行听证,除非是在非常情况下,法院才可酌情将听证延长至10 日。[32]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是否准许隔离的决定,《示范法案》采取优势证据标准,即“有优势证据证明,为防止或限制传染病的传播或传染他人有采取隔离或检疫隔离的合理必要的,法院应准许申请”[33]。这一较低证明标准备受批评,实际上不少州采取更高的证明标准,即清晰和令人信服的证明标准。
法院准许隔离申请之后,其作出隔离决定的实施期限不超过30 天;如需要延长隔离期限的,公共卫生当局可向法院申请延长,经审查批准,延长的期限每次不得超过30天。[34]
3.总结和评析。
因为《示范法案》规定的隔离程序仍显简略,所以引起了学者们的批评和质疑,认为它所提供的正当程序保护存在诸多不足,没有反映当前宪法正当程序的规范要求。[17]同时,《示范法案》和相关州法也未明确隔离案件中司法听证应适用何种正当程序,且各州的规定差异较大。例如,不少州规定,临时性隔离不需要向法院申请许可[35];有的州规定延长隔离才需要向法院提出申请,而首次作出的隔离决定无须获得法院批准。在司法听证中,大约有20个州规定应为当事人指定代理人,其他州规定只对肺结核患者隔离的案件中指定代理人。[36]
(三)传染病隔离程序的相关司法判例
对于隔离程序,一些学者主张采取刑事诉讼的程序保护[18];但多数学者认为应采取与民事拘禁相同的程序保护[19];即认为隔离的实施应遵循精神病人民事拘禁相同的正当程序要求,给予被隔离者获得通知、听证、律师代理、质证等程序权利。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对传染病病人的隔离与精神病人的民事拘禁都属于对个人自由的剥夺,且两者对自由的剥夺都以当事人的行为或状态对他人具有某种危险性为前提——前者是因为个人因患有传染病从而可能导致疾病的传播以致危及公共安全,后者在于个人因精神疾病可能对本人或他人具有人身危险性。因此,隔离和民事拘禁具有相似性,应给予相同的程序保护。
上述观点被不少州法院的判决所确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判例是由西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审理的“Greene v.Edwards案”。该案中,Greene因患有活动性肺结核被强制拘禁于州立医院接受隔离治疗,尽管这一隔离决定经郡法院听证,但在听证前Greene没有被告知有权委托律师,直到听证会开始后才被指定律师,但法庭没有休庭以保证当事人与律师之间的沟通。州最高法院认为,对肺结核患者和精神病人的非自愿拘禁都涉及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两者具有相似性,州法应给予相同的程序保护,包括:其一,书面通知,并详细记载作出拘禁的依据和基本事实;其二,获得律师代理的权利,如果贫穷,则获得指定律师的权利;其三,出庭、质证、询问证人和申请证人出庭的权利;其四,适用清晰、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明标准;其五,为上诉目的取得笔录的权利。据此,法院认为,由于没有及时任命律师,原告的宪法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护,应就其隔离决定重新举行听证会。[37]这一判决被下级法院所普遍遵循,例如,在“City of Newark v.J.S 案”中,法院认为各州应当为肺结核患者的隔离提供通知、听证、定期审查和代理等程序保护。同时,州只有基于清晰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一个人具有“对他人具有严重危险”才可以采取隔离措施。[38]在另一起案件中,纽约州有关肺结核隔离治疗的法律为被隔离者规定了通知、代理和听证等程序。法院认为,根据联邦最高法院在“Mathews 案”和“精神病人民事拘禁案”所确立的先例,纽约州的规定符合宪法的规定。[39]然而,上述案件针对是肺结核患者的强制隔离,是否适用于其他传染病的隔离尚不清楚。很明显,肺结核患者的隔离治疗期限较长(至少半年以上),而其他传染病的隔离治疗往往具有紧急性且期限一般短,两者能否给予相同的程序保护不无疑问。
四、对美国传染病隔离法律规制内容的评析
从以上分析可见,联邦法律和各州法律均授予联邦政府和州十分宽泛的实施检疫和隔离的权力,但这一权力的行使仍受到较为严格的法律规制。该规制主要是从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展开,前者要求要求个人患有或可能患有检疫传染病从而可能给公共健康造成严重威胁,且没有其他更小限制性替代措施的情况下方可实施;后者则要求强制隔离的实施应遵循正当法律程序,保障被隔离者的获得通知、听证、代理、获得法律救济等程序性权利。
尽管美国联邦和各州均具有较为完善的检疫隔离法律体系,但这一制度仍然存在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使得检疫隔离措施事实上难以发挥实际效应,其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检疫隔离权力高度分散。在美国,公共卫生被视为是州的内部事务,各州基于其“警察权”有权采取检疫隔离、强制执行安全与卫生标准、强制报告等公共卫生措施。联邦政府为防止传染病进入境内、阻止传染病的州际传播等情形下采取检疫隔离,但无权直接干预各州的公共卫生事务。这就造成检疫隔离等公共卫生权力分散,联邦政府无法统一各州的行动,各州自行其是,相互对立,致使国内防疫措施效率低下。究其根源,美国宪法所设计的分权制度无法适应疫情防控的需要。这一分权制度的核心在于两方面:一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纵向分权,实行联邦制;二是国家权力的横向分权,实行三权分立。设计双重分权制度主要是出于制衡权力、防止“暴政”的考虑,并不是为提高治理效率[20];而疫情的防控具有其特殊性,权力的过度分散和相互制约将使得政府难以迅速作出决策,即便形成决策,联邦与地方之间的对立、各分支机构之间的相互掣肘、政党之间的攻讦也将使得决策难以获得有效执行。另一方面“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对强制隔离的排斥。传染病隔离的制度要求牺牲自我利益以维护社会利益,但美国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已经转化为公众对政府长久和普遍的的不信任,并形成强烈的个人自主和独立取向。[21]因此,传染病强制隔离的公共正当性往往受到来自公众个人的挑战和抵制,这就造成隔离措施的实施效果往往大打折扣。
注释
①Public Health Service Act,§361(a).
②Public Health Service Act,§361(b).
③这里所说的“逮捕”并非是刑法意义上的逮捕,而是将相关个人临时羁押(taking into custody),以便决定是否对其实施检疫、隔离、或有条件释放。 参见42 C.F.R. § 70.1(2017).
④Public Health Service Act,§361(c).
⑤Public Health Service Act,§361(d).
⑥42 C.F.R.§70.6(a)(2017).
⑦Gibbons v.Ogden,22 U.S.1,(1824).
⑧Jacobson v.Massachusetts,197 U.S.11,92(1905).
⑨如涉及程序性正常程序的Matthews 案,参见,Matthews v.Eldridge,424 U.S.319,335(1976).;涉及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案件,参见O'Connor v.Donaldson,422 U.S.563,575(1975)Foucha v. Louisiana, 504 U.S. 71, 80 (1992); Jones v.United States, 463 U.S. 354, 361 (1983); Addington v. Texas,441 U.S.418,425(1979).
⑩U.S.cx rel.Siegel v.Shinnick,219 F.Supp.789,789(E.D.N.Y.1963).
⑪Reynolds v. McNichols, 488 F.2d. 1378, 1382 (10th Cir.1973).
⑫Haitian Centers Council v. Sale, 823 F. Supp. 1028,1050(E.D.N.Y.1993).
⑬Barmore v.Robertson,134 N.E.815,817(Ill.1922).
⑭42 C.F.R.§70.6(a)(2017).
⑮42 C.F.R.§70.1(2017).
⑯The Model State Emergency Health Powers Act § 605(a)(1)(2001).
⑰The Model State Emergency Health Powers Act § 605(b)(5)(2001).
⑱The Model State Emergency Health Powers Act § 604(b)(1)(2001).
⑲ME.REV.STAT.ANN.22.§820(2)(2015).
⑳City of Newark v.J.S.,652 A.2d 265,270-73(N.J.Super.1993). Best v. Bellevue Hosp. Ctr., 115 Fed. App'x. 459, 461(2d Cir.2004).
[21]42 C.F.R.§70.6(a)(2017).
[22]42 C.F.R.§70.15(b)(c)(2017).
[23]42 C.F.R.§70.15(d)(2017).根据该条规定,也可以决定变更或撤销原命令。
[24]42 C.F.R.§70.16(b)(c)(2017).
[25]42 C.F.R.§70.16(f)(2017).
[26]42 C.F.R.§70.16(h)(2017).
[27]42 C.F.R.§70.16(g)(2017).
[28]42 C.F.R.§70.16(m)(2017).
[29]42 C.F.R.§70.14(d)(2017).
[30]The Model State Emergency Health Powers Act § 605(a)(2001).
[31]ME.REV.STAT.ANN.22.§820(4) (2015).
[32]The Model State Emergency Health Powers Act § 605(b)(1)-(4)(2001).
[33]The Model State Emergency Health Powers Act § 605(b)(5)(2001).
[34]The Model State Emergency Health Powers Act § 605(b)(5)(6)(2001).
[35]N.D.CENT.CODE§23-07.6-03.该法规定,为阻止传染病传播的“紧迫危险”,卫生当局可不经法院批准作出隔离决定,但是如果隔离期限超过10天的,应当在作出隔离决定的10条内向法院申请。
[36] KAN. STAT. ANN. § 65-129c ;VA. CODE ANN. §32.1-48.09.
[37]Greene v.Edwards,263 S.E.2d 661(W.Va.1980).
[38]City of Newark v.J.S.,652 A.2d 265,270-73(N.J.Super.1993).
[39] Best v. Bellevue Hosp. Ctr.,115 Fed. App'x. 459, 461(2d Cir.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