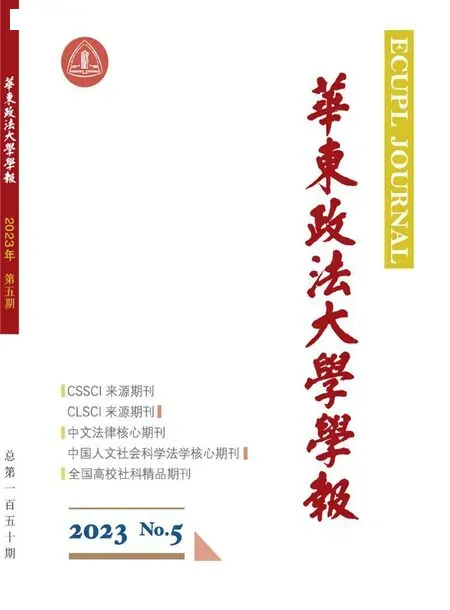论合宪性审查决定的普遍约束性及其限度
段 沁
目 次
一、问题的提出:具有普遍约束性的合宪性审查结论?
二、合宪性审查决定普遍约束性在对象上的限度
三、合宪性审查决定普遍约束性在内容上的限度
四、两种释宪场域的协调:合宪性审查与法规范创制
五、结语
一、问题的提出:具有普遍约束性的合宪性审查结论?
推进合宪性审查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宪法法律尊严、保障宪法法律实施、保证国家法制统一”,〔1〕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暨2017 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载《中国人大》2018 年第1 期,第9 页。是为了实现一种整体客观法秩序上的纠错,那么一旦审查决定认定某项法规范因不合宪而予以撤销,则意味着代表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人大常委会)集中、概括地否定了某种规范创制的内容。这种否定性评价是对世的、普遍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唯一有权机关进行的宪法解释宣告,也是我国宪法的渊源,是宪法的组成部分。〔2〕参见《宪法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0 年版,第28 页。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合宪性审查决定,应当是普遍约束各国家机关的。同时,由于合宪性审查机关与立法机关的合一,合宪性审查决定也具备“法律效力”,即除公权力机关外还约束各类私主体。〔3〕参见田伟:《规范合宪性审查决定的类型与效力》,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 年第1 期,第81 页。
近年来,以备案审查制度为主要支撑、依托新设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4〕参见胡锦光:《论设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意义》,载《政法论丛》2018 年第3 期,第3 页。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协作推进的合宪性审查工作,正取得越来越多的成效。尤其是2020 年的备案审查工作中,首次出现了被工作报告明确认定为与宪法规定不一致的案例。〔5〕参见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2020 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1 年第二号,第353 页。此外,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对于法律案中合宪性问题的审议也越来越普遍和显明。对此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18 年10 月22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18 年10 月22 日。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纠正方式仍然主要延续了“提出意见—制定机关自行纠正”的做法,迄今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未作出过正式的、有对外法律效果的合宪性审查决定。尽管如此,既有的一些案例已经属于实质意义上的合宪性审查,包含实质的宪法解释,〔6〕参见梁鹰:《2020 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述评》,载《中国法律评论》2021 年第2 期,第176 页。并实际上发挥了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纠正了与宪法规定及精神不一致的规范性文件或做法。也就是说,目前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工作中已经出现了具有切实论证内容的合宪性审查结论,包含了对宪法某种程度上的权威解释,蕴含了未来可能通过正式审查决定而外部化的宪法见解。
当前柔性、非对抗式的纠正模式,恰当地尊重了各规范制定机关的专业性和形成自由,通过沟通、协商实现了更全面完整的规范释义上的认识,并且有利于形成共识,充分发挥纠错实效,切实推进纠错进程。〔7〕参见李松峰:《“沟通”与“协商”是符合国情的备案审查方式》,载《法学》2019 年第3 期,第23、27 页。然而,在这种“支持型监督”的备案审查模式下,〔8〕参见蒋清华:《支持型监督:中国人大监督的特色及调适——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为例》,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4 期,第90 页。给出具体的合宪性审查结论和意见的主要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或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前者属于常委会工作机构,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9〕参见胡锦光:《论设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意义》,载《政法论丛》2018 年第3 期,第8 页。后者属于全国人大的常设工作机构,虽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地位,〔10〕参见于文豪:《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合宪性审查职责的展开》,载《中国法学》2018 年第6 期,第49 页。但“其工作任务具有准备和非终结的性质,与常务委员会所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可以独立行使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有着很大的不同”,〔11〕周伟:《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之法律地位探讨》,载《社会主义研究》1993 年第1 期,第56 页。其“不是任何形式的权力机关,它只是人大和人大常委会的助手”,〔12〕《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514 页。“不能直接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名义决定和处理问题”。〔13〕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年版,第161 页。换言之,这两个机构是其隶属的国家机关的“参谋和助手”,〔14〕参见刘松山:《专门委员会为何不能行使立法权和监督权》,载《法学评论》2000 年第4 期,第87 页。其所进行的面向规范制定机关的“沟通”、发出的“书面审查研究意见”等,很难被其他不相关的机关或公民、组织了解,也不具备外部的法律效力,没有宪法所明确配置的权力作为其权威性和强制性的保证。因此,这种囿于内部的合宪性审查结论,在法律上似乎很难被评价为具有普遍约束性。尽管借助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审查结论可以被高度重视和贯彻,可以在政治生活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普遍展开。但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政治目的,恰恰就是要维护党的领导,“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15〕《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第3 条;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2020 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1 年第二号,第350 页。使作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基本原则、重大方针、重要政策在国家法制上的最高体现”和反映着“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宪法,〔16〕参见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2 年12 月4 日。得到有效的贯彻和落实。因此作为“手段”的合宪性审查应不断完善自身的机制和效能,才能有力实现坚持党的领导这一“目标”。
可以想见,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规范合宪性审查问题得到更直接、更深入的处理和回应。但如果这些处理与回应仍然以“书面处理意见”,甚至仅仅是“沟通”的形式进行内部输送与展开,〔17〕参见《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第41 条。那么附随其中的实质性合宪性审查结论和有关的宪法见解,能否具备普遍的拘束效果?这些结论释义是否能超越被审查规范的制定机关而拘束其他适用备案审查制度的国家机关,从而实现“举一反三”和“打包清理”的功能期待?自行纠正后,制定机关能否以“情势变更”为由,再次制定类似的规范,进行“新瓶装旧酒”?审查机关能否在之后的审查工作中改变之前的审查结论和有关见解,进行合宪性审查意义上的“同案不同判”?
出现这些疑问,源自具体实践中实定法的缺位,也源自部分学理的尚未澄清。首先,实定法并未规定所谓的“沟通”和“意见”的法律效力,其内部性也使得其很难如正式的审查决定一般,通过对有关宪法和法律的诠释而得出其具备普遍法律效力的结论。其次,即便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正式的审查决定,不论是在实定法还是学理上,并非都必须是一成不变的。审查决定中的重要说理也往往并不构成一种规范意义上的、约束后来审查的“先例”,更遑论上述的内部沟通与意见传达。最后,合宪性审查始终和法规范创制的民主性、专业性等要素存在或多或少的张力,审查结论需要保持适当的效力范围,并随着社会变迁在合适的时机进行自我修正,避免因追求审查效率而过度排除与时俱进的立法实践,不当限缩对宪法的立法性诠释空间。总而言之,正式的合宪性审查决定本身的普遍约束性就是有界限和例外的,再加上实定法对所谓“沟通”和“意见”的拘束效果的模糊缺失,造成了上述问题。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作为德国的专职合宪性审查机关,亦在实践中遭遇了部分类似问题,如其自身是否受之前裁判的拘束、立法机关是否因受拘束而完全不得重复制定被宣告违宪的法规范等。在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既吸收了司法活动原理,又突出了宪法解释机制的固有逻辑,始终坚持宪法至上的根本追求,与其既作为司法机关又作为专职合宪性审查机关的宪法地位相符,形成了较有说服力的解决路径。对于相同问题的他国方案,我国虽无法直接套用,但不妨一窥方案背后的支配原理与论证思路,探寻对完善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具有启发意义的学理内容。从“功能”和“分工”的视角出发,同为本国专司合宪性审查的最高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权力职责上亦具有一定的可通约性。对此,本文尝试结合我国与德国的有关制度及其原理,对上述问题进行剖析,阐述合宪性审查决定普遍约束性的内容及其限度。
二、合宪性审查决定普遍约束性在对象上的限度
如前所述,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正式的合宪性审查决定,由于包含了宪法解释并具备法律效力,故应当普遍约束各国家机关。但这种普遍约束性也存在被约束对象的例外,需要具体分析。
(一)全国人大是否受到合宪性审查决定的约束
我国《宪法》第62 条第12 项规定,全国人大可以“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加上其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全国人大似乎可不受其常委会作出的合宪性审查决定的约束,但合宪性审查决定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其他决定或一般立法不同,有着相当的特殊性,全国人大并不能像对待常委会的不适当的一般立法或决定那样,不受约束地予以改变或撤销。
第一,合宪性审查决定的作出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行使由宪法直接分配的释宪权,而非立法权。虽然两种权力的行使在结果上都具备普遍约束性的法律效力,但后者是为了在宪法秩序框架下积极形成,前者则是为了厘清宪法秩序本身并以此纠正规范不法,两者的权力使命在根本上是不同的。
第二,全国人大虽具备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但这种地位也是宪法之下的,是一种“被宪法制约”的“最高地位”。宪法基于功能适当的考量,专门将解释宪法的权力分配给更具专业性和更宜进行实际操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18〕参见张翔:《功能适当原则与宪法解释模式的选择——从美国“禁止咨询意见”原则开始》,载《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1期,第116 页。因此,在“涉宪性”权力的分配上,宪法已经明确作出了规定,全国人大不应再通过“改变或撤销决定”的方式干预释宪权的运行,否则既与宪法的明文规定相悖,也与其功能不合。〔19〕参见张翔:《我国国家权力配置原则的功能主义解释》,载《中外法学》2018 年第2 期,第297 页。
第三,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合宪性审查决定,并未排除全国人大的参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作为全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承担具体的合宪性审查论证工作,在实质事务上和解释内容的建构上,搭建起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间的桥梁;同时也通过参与审议各类法律案的合宪性,具体承担起全国人大进行宪法监督的权责。换言之,常委会最终形成的合宪性审查决定,已经是全国人大通过其专门委员会参与形成的决定。这种宪法规定的参与机制,表明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于宪法解释的内容原则上是意志同一的。
第四,全国人大作为宪法明定的最高“宪法监督机关”,在一些极端的宪法危机情形中,仍然有“兜底”手段对常委会作出的可能确实突破宪法的解释进行监督和控制,或者对因社会变迁而造成的突破性宪法解释进行与宪法文本的协调,也即修改宪法。修宪权与释宪权同为“涉宪性”权力,前者显然更强于后者。因此在后者失序时,全国人大应使用宪法赋予其的“涉宪性”权力的方式予以回应和处理。
因此,全国人大除非修改宪法否定常委会作出的宪法解释,否则也宜遵守合宪性审查决定中所作出的宪法解释,按照相应的精神内涵行使权力。接下来的问题是,作为释宪权主体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受其本身所作的合宪性审查决定的约束。
(二)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受到合宪性审查决定的约束
在德国,作为“最高的宪法守护者”的联邦宪法法院,〔20〕BVerfGE 1, 184 (195).同样面临其裁判是否作为“先例”而约束自身后来裁判的问题。〔21〕《德国基本法》第20 条第3 款规定,立法受到宪法秩序的约束,行政权和司法权受到(议会)法律和其他法规范的约束。基于对民主原则的尊重,德国司法裁判主要依据成文宪法与法律,而非英美法系式的判例法。《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第1 条指出,联邦宪法法院是“一个区别于所有其他宪法机关的、独立的联邦最高法院”,其主要功能就是维护宪法至上的地位,并基于宪法控制各个国家权力、裁断各类宪法争诉。对此参见Klaus Schlaich/Stefan Korioth,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11.Aufl., 2018, S.5 あ。但是其裁判和所进行的宪法解释,在实践中往往都被后来法官所遵循,具有一定的“先例”效果。即在没有更高权威的宪法机关的情况下,一国最高的专职合宪性审查机关是否需要受到自身权威的拘束。由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是以司法机关形式运行的专职合宪性审查机关,故总体上有两种路径可对后来宪法争诉产生约束,一是基于裁判本身的司法属性而产生的既判力,二是基于法律特别规定而产生的法定拘束效果。
1.既判力
法治国原则要求法的确定性与安定性,〔22〕Vgl.Steあen Detterbeck, Streitgegenstand und Entscheidungswirkungen im Öあentlichen Recht, 1995, S.328 f.因此司法裁判应当具有确定力(Rechtskraft),从而保证法的和平。形式确定力(formelle Rechtskraft)首先是指司法裁判的不可撤回性(Unwiderruflichkeit),即判决一旦作出,审理法院便不可收回。〔23〕Vgl.Klaus Schlaich/Stefan Korioth,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11.Aufl., 2018, S.368 f.其次是指不可撤销性(Unanfechtbarkeit)。由于联邦宪法法院已经是最高的宪法裁判机关,没有其他的机关可撤销其裁判,〔24〕Vgl.Adreas Heusch, in: Dieter C.Umbach/Thomas Clemens/Franz-Wilhelm Dollinger (Hrsg.),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gesetz, 2.Aufl., 2005,§31, Rn.30.因此其作出裁判即成就形式确定力。〔25〕联邦宪法法院合议庭的裁判不可被上诉至两庭全会,三人小组针对宪法诉愿的裁判(不论是驳回还是支持)也具备确定力,只有临时命令程序是个例外,相应裁判可以被复议,但宪法诉愿程序中的临时命令程序则不行。对此参见Klaus Schlaich/Stefan Korioth,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11.Aufl., 2018, S.368 f.实质确定力(materielle Rechtskraft)也称既判力,是指当司法裁判具备形式确定力后,除就本案裁判内容而对审理法院及当事人形成约束外,还在一定前提下遮断后诉,即“同事不再审”。〔26〕Vgl.Steあen Detterbeck, Streitgegenstand und Entscheidungswirkungen im Öあentlichen Recht, 1995, S.327.由于联邦宪法法院既是宪法机关又是司法救济机关,〔27〕Vgl.Klaus Schlaich/Stefan Korioth,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11.Aufl., 2018, S.19 あ.因此其裁判兼具两种确定力。〔28〕Vgl.Steあen Detterbeck, Streitgegenstand und Entscheidungswirkungen im Öあentlichen Recht, 1995, S.329.但是,由于法治国原则还要求法律救济应尽力达至实质公正,司法过程要避免机械适用法律,尽可能防止法律发展的滞后,使法律在具体的解释适用中得到完善和修正。〔29〕Vgl.Steあen Detterbeck, Streitgegenstand und Entscheidungswirkungen im Öあentlichen Recht, 1995, S.331.因此宪法裁判的既判力并不是无限制的。
基于上述精神以及宪法诉讼作为客观诉讼的主要属性,联邦宪法法院裁判既判力所覆盖的客体范围,只及于在事实上实际进行了宪法处理和审查的诉讼标的,区别于普通法院判决对“本应考虑到的各类事实和法律问题”都可具备既判力。〔30〕Vgl.Steあen Detterbeck, Streitgegenstand und Entscheidungswirkungen im Öあentlichen Recht, 1995, S.333.既判力主要是在当事人之间生效而非普遍生效,〔31〕Vgl.Klaus Rennert, in: Dieter C.Umbach/Thomas Clemens (Hrsg.),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gesetz, 1992,§31, Rn.42 f.拘束对象主要是当事各方、其他诉讼参与人和审裁法院。宪法裁判的既判力止于新的诉讼,即当旧裁判所根据的事实发生改变,〔32〕Vgl.BVerfGE 33, 199 (203).或争诉标的发生变动(即提出新的待决法律问题)时,〔33〕Vgl.Steあen Detterbeck, Streitgegenstand und Entscheidungswirkungen im Öあentlichen Recht, 1995, S.338 あ.旧裁判就不再遮断后诉。换言之,宪法裁判的既判力实际上是一种诉讼阻碍,即禁止由相同当事人对已进行确定裁判的事宜重新提诉并重新裁判以至修改裁判。〔34〕Vgl.Georg Seyfarth, Die Änderung der Rechtsprechung durch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1998, S.186.
有争议的是,如果出现了普遍法律见解的变迁,是否算出现了新的“事实”?联邦宪法法院在涉及此问题的代表性裁判中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搁置态度,〔35〕Vgl.BVerfGE 20, 56 (87); BVerfGE 33, 199 (204).并未明确回答,学界多持肯定说。〔36〕Vgl.Klaus Rennert, in: Dieter C.Umbach/Thomas Clemens (Hrsg.),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gesetz, 1992,§31, Rn.49; Hans Brox, Zur Zulässigkeit der erneuten Überprüfung einer Norm durch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in: Menschenwürde und freiheitliche Rechtsordnung.FS Geiger, 1974, S.809, 822 f.但也有学者强调,所出现的新的法律观点和见解必须足够使人信服并得到充分论证,如此才能使新诉成立并支撑可能的裁判结论的修改,否则不能仅仅以“观点改变”为理由而对同样的情事作出不同判决。〔37〕Vgl.Steあen Detterbeck, Streitgegenstand und Entscheidungswirkungen im Öあentlichen Recht, 1995, S.335.
总而言之,宪法诉讼中既判力产生效果的前提是诉的同一性,即两个诉讼中的原告诉求和争诉问题相同、涉及的核心生活事实相同以及原被告相同。〔38〕Vgl.Steあen Detterbeck, Streitgegenstand und Entscheidungswirkungen im Öあentlichen Recht, 1995, S.345.正是由于既判力有一定的主体、时间和客体方面的限制,且实践中很少有相同的主体向联邦宪法法院重复提起标的相同的宪法诉讼,因此既判力较少发挥作用。〔39〕Vgl.Georg Seyfarth, Die Änderung der Rechtsprechung durch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1998, S.191.但在一些特殊情形中,宪法裁判既判力的“先例性”拘束效果会表现得比较明显,即后来裁判中的某些先行待决问题,是先前裁判中的诉讼标的,且两个诉讼程序的原告或申请人一致,则先前的裁判结果拘束后来诉讼。典型者如在先诉讼为主体性规范审查,后来裁判为附带性规范审查,那么后者就要遵循前者之裁判结果。例如,针对法院判决的宪法诉愿,经审查法院判决之所以违宪,是因为在先的规范审查程序中已裁判作为审判依据的相应法律违宪。对此参见Steあen Detterbeck, Streitgegenstand und Entscheidungswirkungen im Öあentlichen Recht, 1995, S.345 あ.并且既判力的机制功能,也主要是在诉讼被驳回的情况下发挥作用。如果诉愿人或申请主体的诉请得到支持,有关法规范被认定违宪,那么相应裁判会因其法定拘束效果而约束各类公权力和私主体,该规范及其他相同的规范自然就被“一揽子清理”了。
我国的合宪性审查,指向发现和纠正不合宪的法规范,既有实定法下的合宪性审查决定一旦作出就是撤销等消极性决定,并不会以决定的形式进行正式的申请驳回或合宪性确认。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经审查被认为合宪的法规范而言,由于相应的后续处理自动止步于审查机关内部,所以有关的结论无法发挥出如同既判力一般的实质确定力,仍然有可能导致同一主体对相同规范提出重复审查的申请。
为此,有必要丰富合宪性审查决定的类型,如“吁请性”决定等带有特定见解倾向甚至警示的合宪性说明。〔40〕参见田伟:《规范合宪性审查决定的类型与效力》,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 年第1 期,第85 页。在此基础上,可参考既判力的效果,发挥这一司法原理的工具价值,明确合宪性审查决定的确定力,使之能遮断针对相同规范且无充分理由的后来申请。同时,还应注意,不能基于这种确定力而遮断因出现明显的新情事、普遍的法律认识变迁而提起的新申请,也不能遮断对具有相同或相近内容的其他规范性文件而提起的申请。这种申请可在立案阶段被斟酌驳回,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合宪性审查决定具有法律效力、约束各国家机关,已被确认为合宪的法规范在没有引起新疑义的情事或论争时,也应被“一揽子”地予以合宪性确认。诚然,这需要进一步完善合宪性审查的案件筛选过滤机制,不能机械地一概驳回,而应作前置性的考察。
2.法定拘束效果
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有关规范作出了不合宪的审查结论,并决定撤销,那么该决定自然会因其具有的释宪性和法律效力而发挥集中清理功能。可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自身是否也需要遵循这一决定呢?或者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对之进行修改呢?对此德国的经验与理论同样颇具启发意义。《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第31 条第1 款和第2 款也分别对联邦宪法法院规范审查裁判拘束对象的范围进行了扩张,即扩大到所有的宪法机关、司法机关及私主体。
根据这一规定,似乎联邦宪法法院也应受到自身裁判的约束。如此一来,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判就真正具备了类似英美法系判例法的先例拘束力了,但联邦宪法法院曾在多个判决中表明了不受自身判决拘束的观点,宪法法院可以改变其之前裁判中的法律见解。〔41〕Vgl.BVerfGE 20, 56 (86); BVerfGE 33, 199 (203); BVerfGE 70, 242 (249); BVerfGE 77, 84 (104); BVerfGE 78, 320 (328);BVerfGE 82, 198 (205).早在1954 年关于石荷州选举法中5%得票率门槛规定的判决中,联邦宪法法院就并未遵循先前裁判的约束,〔42〕Vgl.BVerfGE 4, 31 (38 f).并指出既判力仅就相同的诉讼标的和在相同的当事人间产生约束,而法定约束效力主要是将裁判约束效果扩张至其他宪法机关和法院,但联邦宪法法院自身并不受到约束,除非相应裁判的既判力得以发挥。〔43〕Vgl.Georg Seyfarth, Die Änderung der Rechtsprechung durch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1998, S.201.联邦宪法法院曾在裁判中判定国家对政党的财政支持是合宪的,〔44〕Vgl.BVerfGE 8, 51.并也在这之后的判决中认为该问题已然得到裁判,〔45〕Vgl.BVerfGE 12, 276 (280).但在1966 年审理由黑森州政府提出的抽象规范审查时,又对该问题进行了修正,认为其自身并不受先前裁判观点的拘束。〔46〕Vgl.BVerfGE 20, 56 (87).
正如联邦宪法法院〔47〕Vgl.BVerfGE 84, 212 (227).和许多学者〔48〕Vgl.Steあen Detterbeck, Streitgegenstand und Entscheidungswirkungen im Öあentlichen Recht, 1995, S.369.认为的那样,对于德国法秩序而言,司法权受由自身发展出的法律见解约束是陌生的。况且作为宪法最高守护者,联邦宪法法院并非普通司法机关,不是衔接所有审级的超级上诉法院,其核心任务是对《德国基本法》作出具有约束性的终局解释,这直接源自宪法的委托。〔49〕例如《德国基本法》第100 条第3 款规定,州宪法法院在解释《德国基本法》时若欲偏离联邦宪法法院或他州宪法法院的裁判,则该州宪法法院应征求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判意见。这一方面再次表明了联邦宪法法院作为专任宪法解释机关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如果确有修正的必要和可能,最适机关依然是联邦宪法法院自身,且其当然具备修正自身裁判的权限,否则就没必要如此规定了。对此参见Karin L.Pilny, Präjudizienrecht im anglo-amerikanischen und im deutschen Recht, 1993, S.186.宪法并未表明宪法法院应受先例约束,其在宪法解释方面的终局权威性意味着其不受任何第三方的约束。因此,立法者如果以普通法律即《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要求宪法法院遵循先例,就妨碍了宪法法院在宪法解释中定于一尊的地位。〔50〕Vgl.Steあen Detterbeck, Streitgegenstand und Entscheidungswirkungen im Öあentlichen Recht, 1995, S.370.宪法法院基于其认为更恰当、正确的见解来修正裁判,在本质上恰恰是对宪法的忠诚和尊崇。如果一方面赋予联邦宪法法院以解释宪法的重要任务,另一方面又排除了其获得更优认识的可能,进而阻止了宪法的正确解释,那么就会非常矛盾。〔51〕Vgl.Thomas Lundmark, Stare decisis vor dem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Rechtstheorie 28 (1997), S.315, 327.修正行为是为了更准确和客观地释清宪法,这也反映出只有宪法本身才是约束宪法法院的根本规范,凸显了宪法规范的至上性。
作为我国唯一享有宪法解释权的国家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一样,都具有由宪法明定的垄断性宪法解释机关地位,除此之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民主合法性基础和政治商议功能还要强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因此,其通过合宪性审查所作出的宪法解释,不仅有极高的权威,也能够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但宪法解释仍然只是对宪法意涵的探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具化甚至续造了宪法,但仍旧受到宪法文本的射程限制,是宪法制约下的释宪。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合宪性审查中的释宪结论虽然应约束其普通立法活动,但不应约束其后来的释宪,因为唯一能对之进行约束的是宪法本身。
三、合宪性审查决定普遍约束性在内容上的限度
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受其在先合宪性审查决定的约束,一方面是要维护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最高法律效力,防止宪法解释异化为不受控制的宪法创造;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证宪法解释始终能够富有弹性,可以保持一种最优化解释的可能。这种目的也反映在,合宪性审查决定中具有普遍约束性的内容应当有所限制。尤其是其中的诸多属于宪法解释的见解、理由等,虽然应当约束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内的普通立法活动,但不应窒息涉宪性权力的活力,过早地排除可能因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而产生的一系列观念变化。
这样的观点也在德国学界有广大的拥趸。例如,支持联邦宪法法院裁判不受先例拘束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要防止宪法的僵化。〔52〕Vgl.Herbert Bethge, in: Theodor Maunz/Bruno Schmidt-Bleibtreu/Franz Klein/Herbert Bethge (Hrsg.),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gesetz Kommentar, 60.EL Juli 2020,§31 Rn.118.宪法裁判不仅仅是类似普通司法程序进行定纷止争的主观诉讼过程,更是一个解释宪法的客观诉讼过程。〔53〕Vgl.Steあen Detterbeck, Streitgegenstand und Entscheidungswirkungen im Öあentlichen Recht, 1995, S.333.宪法诉讼对不断出现的宪法疑义的处理,正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宪法解释,这保证了宪法文本的活力和规范效果的可持续。宪法解释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具备一定的“变动性”恰恰是宪法解释的应有之义。不论是对国家机关还是普通公民,宪法裁判的潜在变动可能都应当落入其预期,因为宪法裁判的唯一依据是宪法规范本身,很有可能会因新的客观事实或认知而对固定规范的解释产生新的见解。
并且,通过解释宪法进而保持宪法的发展与续造,是宪法法院的天然任务。〔54〕Vgl.Peter Badura, Staatsrecht, 7.Aufl., 2018, Teil H, Rn.50.通常而言,如果宪法法院的裁判发生了改变,不是以新判决创制了新的宪法规范,而仍然是对既有法的解释,只不过是新的注解和补充。〔55〕Vgl.Hartmut Maurer, Kontinuitätsgewähr und Vertrauensschutz, in: Josef Isensee/Paul Kirchhof (Hrsg.),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Band IV, 3.Aufl., 2006,§79, Rn.149.宪法法院的裁判除非具有持续重要的影响,并被广泛接受、承认为习惯宪法,才能成为约束后续宪法裁判的宪法渊源,〔56〕Vgl.Hartmut Maurer, Kontinuitätsgewähr und Vertrauensschutz, in: Josef Isensee/Paul Kirchhof (Hrsg.),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Band IV, 3.Aufl., 2006,§79, Rn.141.否则宪法裁判并不会基于所谓的信赖原则而受先例的约束。〔57〕Vgl.Herbert Bethge, in: Theodor Maunz/Bruno Schmidt-Bleibtreu/Franz Klein/Herbert Bethge (Hrsg.),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gesetz Kommentar, 60.EL Juli 2020,§31 Rn.119.
通说还认为,仅对应着诉讼标的的裁判主文(裁判结论)具备既判力,服务于解释主文的裁判说理和对先决问题的附带裁判则不具备。〔58〕Vgl.BVerfGE 4, 31 (38 f.); BVerfGE 78, 320 (328); Herbert Bethge, in: Theodor Maunz/Bruno Schmidt-Bleibtreu/Franz Klein/Herbert Bethge (Hrsg.),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gesetz Kommentar, 60.EL Juli 2020,§31 Rn.94 f.虽然联邦宪法法院曾在一些裁判中表现出欲将其所有的裁判理由赋予普遍拘束力的倾向,〔59〕Vgl.BVerfGE 36, 1 (16); BVerfGE 72, 119 (121); BVerfGE 93, 121 (136).但学界普遍表示了怀疑与反对。〔60〕Vgl.Herbert Bethge, Zur Problematik von Grundrechtskollisionen, 1977, S.416, Fn.591; Klaus Schlaich/Stefan Korioth,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11.Aufl., 2018, S.375 ff.; Josef Isensee, in: Bernd Wieser/Armin Stolz (Hrsg.), Verfassungsrecht und Verfassungsgerichtsbarkeit an der Schwelle zum 21.Jahrhundert, 2000, S.26, Fn.28.联邦宪法法院认为,若证立裁判结论的重大理由包含宪法(而非仅是对普通法律的)解释,则其亦具备普遍拘束性。〔61〕Vgl.BVerfGE 1, 14 (37); BVerfGE 19, 377 (392); BVerfGE 20, 56 (87); BVerfGE 40, 88 (93 f.); BVerfGE 112, 268 (277).这是因为联邦宪法法院将自身视为“宪法的决定性解释者和守护者”和“对宪法问题进行约束性裁断的管辖法院”,〔62〕Vgl.BVerfGE 40, 88 (93 f).乃至有学者认为其参与进了宪法的制定。〔63〕Vgl.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 Die Methoden der Verfassungsinterpretation: Bestandsaufnahme und Kritik, NJW 1976,2089, 2099.其固有职责在本质上是续造宪法并使相应内容形成约束,〔64〕Vgl.Klaus Schlaich/Stefan Korioth,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11.Aufl., 2018, S.374.而宪法争诉只是一种纯粹的诱因。〔65〕Vgl.Dieter Grimm, Verfassungsgerichtsbarkeit, in: W.Hoあmann-Riem (Hrsg.), Sozialwissenschaften im Studium des Rechts II,1977, S.94.因此联邦宪法法院的具体宪法见解反而尤为重要。另外,宪法裁判中的论证技术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判决书在证立裁判结论时,往往先行列出宪法规定和审查的标尺,而后才结合具体事实予以考察分析,其结果是使抽象审查标尺逐渐典范化。〔66〕Vgl.Klaus Schlaich/Stefan Korioth,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11.Aufl., 2018, S.375.
反对重大理由具有拘束性的意见并未否认联邦宪法法院解释和发展宪法的任务,但由此并不能得出应将法院见解典范化的结论。第一,重大理由的范围不清晰,联邦宪法法院对此的描述极为形式化,即“那些不能忽视,否则按照裁判思路就无法得出具体结论的法律话语”。〔67〕Vgl.BVerfGE 96, 375 (404).这种非实质定义无法判定何为“重大”。联邦最高行政法院认为,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判主旨(Leitsätze der Entscheidung)非常关键,它表明了宪法法院的裁判核心和欲形成约束效果的内容。〔68〕Vgl.BVerwGE 73, 263 (268).但是裁判主旨往往是对判决论证中普遍重要内容的抽象概括,重大理由亦可以蕴藏在具体的个别判断中,不论是总体论证还是个别论证都可以被法院认定为重大理由,裁判主旨并不能完全覆盖。〔69〕Vgl.Klaus Schlaich/Stefan Korioth,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11.Aufl., 2018, S.376 f.第二,宪法解释需要在宪法的开放性、动态性和宪法法院解释的刚性约束(本质上是宪法的规范约束性)间取得平衡,妥善处理好两者间的潜在张力。〔70〕Vgl.Klaus Schlaich/Stefan Korioth,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11.Aufl., 2018, S.377 f.因此,不能巨细靡遗地将宪法法院的宪法观点彻底典范化和规范化,否则就窒息了宪法本身与时俱进的可能。第三,裁判理由的典范化会使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判逐渐远离具体的宪法条文,使裁判越来越依赖于一种“整全的法律立场”(übergreifende Rechtsvorstellungen),〔71〕Vgl.Peter Lerche, Grundrechtsverständnis und Normenkontrolle in Deutschland, in: Klaus Vogel (Hrsg.), Grundrechtsverständnis und Normenkontrolle, 1979, S.24, 33.如公平性、合比例性、禁止恣意等教义。一种整全性话语的表现就是,裁判主文中联邦宪法法院不仅仅提及被侵犯的基本权利,还常常提及与相应基本权利紧密相连的社会国、法治国原则等等,甚至大而化之地以“与基本法不符”来表述。〔72〕Vgl.Klaus Schlaich/Stefan Korioth,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11.Aufl., 2018, S.377 f.第四,裁判理由的典范化也损害了联邦宪法法院作为最高司法管辖的持久性,压抑了下级法院的异议空间,损害了审级制度的弹性空间,剥夺了自身根据其他参与宪法生活的国家机关或司法机关之意见而自我检视的可能。〔73〕Vgl.Joachim Burmeister, Vorlagen an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nach Art.100 III GG, in: Christian Starck/Klaus Stern(Hrsg.), Landesverfassungsgerichtsbarkeit, Teilband 2, 1983, S.399, 408.
总体而言,除了既判力产生约束的情形,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判对于其自身在后来的相同或相似案件中的审理判决,并没有强制性的法律约束力,相关在先裁判主要被认为是“先例友好型的智识渊源”(Präjudizien willkommene Erkenntnisquellen),〔74〕Vgl.Dieter Wilke, Die rechtsprechende Gewalt, in: Josef Isensee/Paul Kirchhof (Hrsg.),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Band V, 3.Aufl., 2005,§112, Rn.53.即宪法诉讼中的先例裁判对于后来裁判中相同或类似法律问题的剖解释清提供了思路样本和论证启发,但并不强制后来裁判必须萧规曹随。德国的经验表明,不论是宪法诉讼还是合宪性审查,其核心任务在于宪法解释,在于以此而展开宪法的至上法律效力,并将抽象、固定的宪法同丰富、变迁的社会生活进行调和。因此,宪法解释不应是一成不变的僵死教条,有权的释宪机关应有充分的自由在恰当时予以调整和修正。全国人大常委会既是立法机关又是释宪机关,这种混合权力主体的身份决定其在行使释宪权作出合宪性审查决定时,不应受到自身在先决定内容的约束,但在行使普通立法权时,应依循既有的合宪性审查结论和宪法解释。
四、两种释宪场域的协调:合宪性审查与法规范创制
我国释宪机关的混合权力主体性质,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两种释宪场域,即专门的合宪性审查和通过民主立法而进行的建构性宪法解释之间的张力。立法者通过创制具体的各类法律而表现出的关于宪法的认识,在本质上是对宪法的诠释,而这种诠释应是十分权威与值得尊重的,毕竟立法者是建构性的第一宪法解释者。〔75〕Vgl.Paul Kirchhof, Verfassungsverständnis, Rechtsprechungsaufgabe und Entlastung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in: Harald Bogs (Hrsg.), Urteilsverfassungsbeschwerde zum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1999, S.74.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作为专门处理宪法争议的机关,在面对立法者时同样会慎言违宪,并在相当程度上对立法机关的各类形成自由予以充分的尊重。其目的之一在于避免专任合宪性审查机关进行独断的宪法解释,从而对民主原则造成冲击。毕竟谁也无法保证,由若干法官所坚持的宪法见解就一定会优于代表着全体人民的议会的见解,一定能经受住历史的检验。
因此,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两个审判庭曾对“规范破弃裁判”(normverwerfender verfassungsgerichtlicher Entscheidungen)的拘束效果产生过较大的争论。这类裁判否定了议会立法的合宪性,往往直接和立法者权威及民主原则发生碰撞。《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第31 条第1 款规定宪法法院的裁判约束所有国家机关,故具体争议在于,此类裁判作出后是否可以阻止立法者在之后重新制定相同的规范。第二庭就主张,对于被宣告无效的法规范应施以“规范重复禁止”(Normwiederholungsverbot)。〔76〕Vgl.BVerfGE 69, 112 (115); BVerfGE 1, 14 (37).因为联邦宪法法院曾在具有奠基性的裁判中指出,〔77〕Vgl.BVerfGE 1, 14 (15).根据《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的规定,宪法法院宣告法律无效的判决不仅仅具有法律效力(Gesetzeskraft),还具有约束联邦宪法机关的效力,立法者因此不得再重复制定已被认为是无效的法律。第一庭则认为,宪法法院的裁判不能阻止立法者再度制定内容相近或相同的新规定。〔78〕Vgl.BVerfGE 77, 84 (103 f).因为根据《德国基本法》第20 条第3 款,立法者区别于行政、司法两权,仅受到合宪性秩序的约束,不受到普通法律秩序的约束,因为其自身便是普通法律秩序的缔造者,这属于其基于高度民主正当性的形成自由的范围。〔79〕Vgl.BVerfGE 77, 84 (104).换言之,立法者不会也不能“作茧自缚”,其不会受自身立法所限。再者,宪法法院对于立法活动只能依据宪法进行审查判断,而不能根据自身的先见,且宪法法院如果认为要修正自身判决,还必须有赖立法活动的触发,而不能自行动议修正。〔80〕Vgl.Klaus Schlaich/Stefan Korioth,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11.Aufl., 2018, S.372.允许立法者保留“再度挑战”的可能,在本质上是为了预防法律发展进程的僵化。学界普遍认为第一庭的观点更妥当。〔81〕Vgl.Klaus Schlaich/Stefan Korioth,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11.Aufl., 2018, S.372.诚然,这也不意味着立法者对于宪法法院的裁判可以置若罔闻,相反,立法者仍然要尊重宪法法院的裁判及其权威,并且在实践中立法者也的确“狂热”地遵守了宪法法院的裁判。〔82〕Vgl.Klaus Schlaich/Stefan Korioth,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11.Aufl., 2018, S.372.
民主代议机关在诠释宪法时同样具有极强的优位性,对其具有建构性释宪作用的立法进行合宪性审查时,应当把握好审查密度,避免轻言违宪。即便对某项立法宣告违宪,也不应完全排除再度立法的空间。德国的这种做法,主要就是为了缓解两种释宪场域间的矛盾,保持宪法的活力,同时也是为了避免造成两个重要国家机构间的扞格,酿成宪法危机。但在我国,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时也是立法机关,并同时行使立法权和释宪权,因此由其作出的合宪性审查决定中所蕴含的宪法解释,应当被认为是综合了建构性诠释和审查性诠释的结果。换言之,不论从内部工作机制还是外部的权责分配看,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宪法解释都不存在自身分裂和与其他机关分歧的可能。因此,合宪性审查决定也应当普遍约束全国人大常委会自身的普通立法工作。若因社会变迁等因素而需要调整宪法解释,则全国人大常委会可通过行使释宪权而自行修正,例如,可通过对有关法律案的事前审查改变先前的宪法解释,从而为通过之前被认为是不合宪的法律扫清障碍。同理,全国人大的立法也应受到约束,除非全国人大与和其在意志上高度统一的常委会产生例外性的分歧,并以修宪权的方式进行宪法监督进而纠正审查决定。
需要说明的是,在实践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判常常援引、重复先前裁判的要旨或法律见解,〔83〕在20 世纪末曾有学者进行过统计,高达97%的联邦宪法法院裁判曾援引先例,对此参见Robert Alexy & Ralf Dreier,“Precedent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in D.Neil MacCormick, Robert S.Summers & Arthur L.Goodhart eds., Interpreting Precedents: A Comparative Study, Ashgate Publishing, 1997, p.23.并以此提升当下判决的说服力,很少发生裁判修正。其目的一方面是尊重先前裁判的公信力(而非约束力),〔84〕Vgl.Thomas Lundmark, Stare Decisis vor dem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Rechtstheorie 28 (1997), S.315, 330.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其他宪法机关尽可能提供稳定、可靠的宪法解释。〔85〕Vgl.Michael Sachs, Die Bindung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an seine Entscheidungen, 1977, S.187.因此偏离先例的裁判很少,到20 世纪末也只有约14 件,〔86〕关于这些裁判的介绍和梳理,参见Thomas Lundmark, Stare Decisis vor dem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Rechtstheorie 28(1997), S.315, 331-337.而在这期间共有约78 人担任联邦宪法法院大法官,更可见偏离数量之少。联邦宪法法院认为要有“新的认识”出现,〔87〕Vgl.BVerfGE 2, 79 (92).也就是当“发生事实关系的改变而使规范解释发生变迁”,〔88〕Vgl.BVerfGE 39, 169 (181 あ).出现所谓的“本质性变化”(wesentliche Veränderungen),〔89〕Vgl.BVerfGE 82, 198 (205).或者发生“生活关系或普遍的法律见解的根本性变迁”时,〔90〕Vgl.BVerfGE 20, 56 (87).才能考虑修正先例。〔91〕但联邦宪法法院仅仅是对于是否可着手进行先例修正,给出了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前提限定,并未对修正的程度、方式和边界等问题作出抽象解释,仍借助个案进行具体确定。对此参见Thomas Lundmark, Stare decisis vor dem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Rechtstheorie 28 (1997), S.315, 340.极少修正先例的另一个原因或许是联邦宪法法院运作的时间还较短,社会变迁的幅度尚没有非常巨大,所处理过的一些基础性法律问题大多没有重新检视的必要。〔92〕Vgl.Thomas Lundmark, Stare Decisis vor dem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Rechtstheorie 28 (1997), S.315, 341.社会同质性和很高的受教育水平,也导致了法官群体价值观的相近。〔93〕Vgl.Thomas Lundmark, Stare Decisis vor dem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Rechtstheorie 28 (1997), S.315, 341.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对平等原则、〔94〕See Kay Hailbronner & Hans-Peter Hummel, “Constitutional Law”, in Werner F.Ebke & Matthew W.Finkin eds., Introduction to German Law,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6, pp.43, 69.信赖保护原则〔95〕Vgl.BVerfGE 84, 212.及分权原则等的坚守,虽然允许一定程度上的先例修正,但仍要尽可能地尊重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判机制。法官要尽可能地摒弃以个人的政治或社会价值观来主导裁判乃至与先前裁判对立的做法,避免朝令夕改、昨是今非,从而维护法治的稳定和一贯,维护联邦宪法法院的权威和存在价值。这也警示我们,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行使释宪权时一方面应精耕细作、论证翔实,使每一次的审查结论都能经受住一定历史时期的考验;另一方面也要谨慎稳妥、纵观全局,使合宪性审查工作承继有序地向前发展。
五、结语
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合宪性审查决定,是行使宪法赋予的释宪权对宪法进行解释的结果,其结论应当拘束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活动在内的各级国家公权力机关的活动,尤其是法规范的制定。但决定不约束全国人大行使修宪权进行宪法监督,也不约束常委会因应社会变迁而修正自身作出的先前的宪法解释。合宪性审查决定的这种有一定限度的普遍约束性,有利于高效、全面地推进宪法实施,纠正规范不法,维护法制统一,并有利于保持宪法活力。
目前,合宪性审查工作尚处在内部的沟通和意见传达阶段,虽然具有相当的实效性,但由于实定法缺失,相关审查结论与宪法见解无法拥有明确的法律效力。这很有可能导致备案审查工作必须逐一处理、反复筛查,甚至还会出现“新瓶装旧酒”的现象,极大地增加了备案审查工作的负担,浪费审查资源。未来应积极探索丰富合宪性审查决定的类型,减少作出正式决定的顾虑和障碍,通过决定的普遍约束性而更好地实现宪法监督、推动宪法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