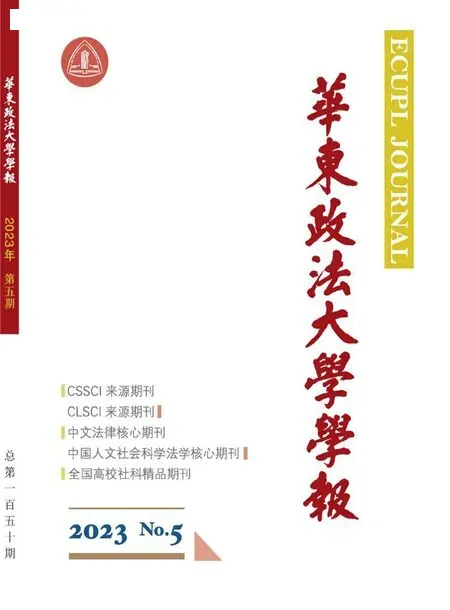劳动合同中的减损义务
——以违法解雇中的中间收入扣除为中心
严 立
目 次
一、问题的提出
二、解雇期间内的工资债权及其实态
三、扣除中间收入的规范依据:减损规则
四、依据减损规则扣除中间收入的具体适用
五、结论
一、问题的提出
《劳动合同法》第48 条前句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所谓继续履行,即指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给付工资之债务(《民法典》第579 条)。而劳动争议往往迁延日久,在违法解雇发生至生效裁判确认解雇系违法的期间内(以下简称“解雇期间”),〔1〕就解雇期间的具体计算方式而言,其起算点一般是违法解雇发生之时,但止点在何处,各国存在细微差异。我国法院一般认为是裁判生效之日,如(2019)黑民再210 号民事判决书。日本法上认为是法庭口头辩论终结,意大利法则认为是解雇之日至实际复职之日,大内伸哉「イタリヤの新たな解雇法制」季刊労働法239 号(2012 年)243 頁参照。劳动者完全有可能受雇于其他用人单位以保证其生活来源。那么当法院判决合同继续履行,并补发解雇期间内工资时,受雇于他处获得的收入(以下简称“中间收入”)是否应予扣除遂成为实务和理论上重要的问题。
扣减中间收入的依据主要有损益相抵与减损规则。《民法典》第591 条的减损规则在非法解雇中是否有适用余地,劳动者是否负有“另寻生路”的对己义务?劳动法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关注非常有限,反而是不乏民法学者认为劳动者负有寻求替代工作机会的减损义务。〔2〕参见崔建远:《合同法》(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402 页;刘凯湘:《合同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年版,第424 页。而一旦认可这种将劳动力利用最大化的替代交易义务,便可能意味着劳动者从其他来源获得的收入,或者本可以获得却恶意不取得的收入将从原工资债权中扣减。
但从司法实践来看,几乎尚未见到法院以减损规则扣减中间收入,从而在劳动者保护与用人单位利益之间达成某种平衡的例子,这不意味着法院判决按照劳动者本人的工资水平补发解雇期间内的工资。在下文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法院一般仅以某种较低的标准(如最低工资标准、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标准等)补发该期间内的工资。〔3〕请参见下文“解雇期间内的工资债权及其实态”部分的具体讨论。由此形成了一种不扣减却胜似扣减的状态。然而这样的做法到底缺乏规范依据,更加凸显了在理论上廓清这一问题的必要性。
本文讨论的减损义务、损益相抵、与有过失等均属于民法长期关注的制度,劳动法领域则较少涉及。但鄙意绝非在于造成一种民法对劳动法的“侵入”,而是主张在劳动法规则付之阙如时,民法至少有一种兜底和补足的功能。这在民法典时代,如何协调民法与劳动法的语境下是尤其值得关注的。〔4〕参见王一帆:《民法典背景下违法解雇救济的体系重构》,载《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3 期,第50-51 页。
二、解雇期间内的工资债权及其实态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生效裁判文书认定解雇违法并要求用人单位补发工资,此时给付工资属于劳动合同给约定的原给付义务的实现,还是因义务违反而产生的损害赔偿的次给付义务,只不过其额度以解雇期间内的工资为准?〔5〕相关的讨论参见喻术红、程凌:《违法解雇期间劳动者所得之性质与范围——兼论民法典相关制度之构建》,载《河北法学》2019 年第12 期,第42-59 页。比较法上,日本、我国台湾地区通说均主张,作为债务人的劳动者保留原合同下的请求权。英美法则认为此时劳动者提起的并非针对原给付义务的偿债之诉(action for debt),而是损害赔偿之诉(damages),若劳动者立刻找到新工作,甚至可能因为不存在损失而排除损害赔偿请求权。〔6〕See Hugh Collins et.al., Labour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828.意大利法上也认为此时劳动者因遭受工资损失而成立损害赔偿请求权。〔7〕大内伸哉「イタリヤの新たな解雇法制」季刊労働法239 号(2012 年)243 頁参照。但在本文讨论减损规则以及中间收入扣除的语境下,无论将之作为实际履行,还是损害赔偿问题处理,似乎都不会对结果产生影响——不管是原给付义务还是次给付义务,均有受到减损规则限制,从而扣减其额度的可能性。〔8〕我国有研究者认为,将解雇期间内的请求权定性为工资债权还是损害赔偿请求权,会对劳动者利益产生重大影响,似有夸大之嫌。察其表述,似乎将之定性为损害赔偿,劳动者得到的金额就少,若定性为工资,则可按本人工资水平得到偿付,其数额往往较多。但根据该文对司法实践的考察,似乎不足以支持这样的见解。譬如其所举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5)三中民终字第02199 号民事判决书,将解雇期间内的请求权定性为“损失”,其结果是按照“本市同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支付了一个较低的数额。而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2 民终8538 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定该期间内的债权系“工资”,却仍然以“本市最低工资标准”支持了较低的数额。参见廖斌、张珂嘉:《违法解雇期间劳动者应得利益的救济路径与范围》,载《四川轻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3 期,第44-45 页。由是观之,将该请求权定性为损害赔偿请求权抑或工资债权,对当事人权利状态似不生实质性影响;质言之,劳动者权利得不到充分保护,其症结并不在于理论上的定性。
(一)工资债权的规范基础
若非法解雇被认定为无效,劳动者选择继续履行合同,则按照《民法典》第579 条之文义,工资债权应当得到支持似无疑问。有论者认为《劳动合同法》第48 条的继续履行救济并未明确解决这一问题。〔9〕参见李国庆:《论违法解雇的法律救济》,载《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1 年第10 期,第87 页。这样的见解似乎过于割裂了劳动法与民法的关系,毕竟劳动合同在本质上仍具有合同的属性。第48 条前句所指“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固然包含解雇被认定为非法后,向后恢复劳动关系,但未尝不可解释成“溯及”地恢复解雇期间内的劳动关系,从而得依据原债权债务关系主张工资债权。《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劳部发〔1995〕223 号)第3 条第1 项规定“造成劳动者工资收入损失的,按劳动者本人应得工资收入支付给劳动者”,其意正在于肯认劳动者的工资债权。虽然有的观点认为本条项后段规定的加付25%工资因与《劳动合同法》冲突而无效,〔10〕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浙民再181 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认为发生冲突的是第85 条,但第85 条并不涉及不法解雇的问题,严格来讲发生冲突的似乎是第87 条。但支付“应得工资收入”的效果却与《劳动合同法》第48 条规定的继续履行无违。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41 号,2016 年修正)第29 条第1 款,《上海市企业工资支付办法》(沪人社综发〔2016〕29 号)第23 条,等等。〔11〕对地方法院文件优秀的罗列梳理,参见喻术红、程凌:《违法解雇期间劳动者所得之性质与范围——兼论民法典相关制度之构建》,载《河北法学》2019 年第12 期,第45-46 页。谨识于此,示不掠美。
自理论言之,劳动者因非法解雇而无法再提供劳务获取报酬,构成给付障碍法上的履行不能抑或受领迟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日本民法与劳动法的通说均认为应构成履行不能。日本《劳动契约法》第16 条规定,解雇客观上欠缺合理理由,或为社会一般观念认为系不相当者,构成权利滥用,解雇无效。〔12〕早在《劳动基准法》和《劳动契约法》明文规定滥用解雇权规则之前,日本法院就已经根据《民法》第1 条第3 款的禁止权力滥用条款发展出了解雇权滥用的法理。濱口桂一郎『日本の労働法政策』(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2018 年)698-700 頁参照。在解雇发生至法庭口头辩论终结的“解雇期间”内,劳动者应可请求原定的工资,其规范依据在于日本《民法》第536 条第2 款,无效解雇导致劳动者提供劳动力的债务陷于履行不能,而不仅仅是受领不能,〔13〕荒木尚志『労働法』(有斐閣,2020 年)341 頁参照。但德国法上似乎认为此时债权人陷于受领迟延。参见李国庆:《论违法解雇的法律救济》,载《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1 年第10 期,第85 页。且此种给付不能系可归责于债权人/用人单位的行为所致(日本《劳动契约法》第16 条),因此用人单位并无拒绝为对待给付之权利,劳动者仍得请求给付工资(原给付请求权)。〔14〕盛誠吾「違法解雇と中間収入」一橋論叢106 卷1 号(1991 年)21-22 頁参照。日本《民法》债编修正以前,第536 条就对待给付的命运系采直接消灭的路径,即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不能,债权人的对待给付义务直接消灭,若可归责于债权人,则对待给付义务并不消灭。债编修订之后的现行法则并未采取直接消灭说,而是赋予债权人一种拒绝履行的抗辩权,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履行不能,债权人得拒绝为对待给付,可归责于债权人的履行不能中则无此种拒绝权。荒木尚志『労働法』(有斐閣,2020 年)137 頁参照。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则倾向于认为构成受领迟延,〔15〕参见侯岳宏:《日本非法解雇期间工资与中间收入扣除之发展与启示》,载《政大法学评论》2012 年第128 期,第374 页。该法第487 条明定“雇用人受领劳务迟延者,受雇人无补服劳务之义务,仍得请求报酬”。受领劳务迟延的构成要件为:1 给付需债权人受领,或为必要之协力,例如对工作内容作出指示;2 债务人已依约提出给付;3 债权人拒绝或者不能受领。〔16〕参见徐婉宁:《论违法解雇下雇用人之受领迟延责任与危险负担法理之交错:以解析台湾实务见解及日本法之比较为中心》,载《台大法学论丛》,第46 卷第1 期,2017 年,第91-94 页。但因为劳务这样的给付无法提存的特殊性质,〔17〕债权人不受领时本应提存以消灭债务,然劳务本身无法提存。参见郑玉波:《民法债编各论(上册)》,三民书局1986 年版,第340 页。今日不为劳务明日无法为双倍之劳务,〔18〕参见林诚二:《民法债编各论(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18 页。因此履行不能与受领迟延/不能本身往往难以区分,〔19〕近江幸治『債権総論』(成文堂,2009 年)103-106 頁参照。“劳务给付义务为所谓的定期债务,具有未服劳务即同时等同于给付不能之特征”。参见徐婉宁:《论违法解雇下雇用人之受领迟延责任与危险负担法理之交错:以解析台湾实务见解及日本法之比较为中心》,载《台大法学论丛》,第46 卷第1 期,2017 年,第114 页。“关于提供劳务之义务,究其定期行为之特质,于雇主受领迟延后,实际上该义务即为给付不能”。〔20〕徐婉宁:《论违法解雇下雇用人之受领迟延责任与危险负担法理之交错:以解析台湾实务见解及日本法之比较为中心》,载《台大法学论丛》,第46 卷第1 期,2017 年,第126 页 。
就受领迟延而言,《民法典》第589 条第1 款仅规定“债务人可以请求债权人赔偿增加的费用”,这显然是以一般的财产性给付关系为模型构建的规则,受领迟延后债务依然存在,只不过债务人责任得以减轻(如免除轻过失责任),因受领迟延增加的负担由债权人负责而已。可见以财产性给付为模型构建的受领迟延规则,直接适用于劳务给付关系,往往可能“水土不服”。因此解释上,《民法典》第589 条似乎未考虑受领迟延后无法再补充履行的情形,一方面可以印证上述观点,即受领不能制度的原型系财产性给付关系,另一方面或许可以认为,立法者暗示了劳务一类的给付受领迟延后不能履行时,可直接委诸履行不能处理。职是之故,不如直接作为履行不能问题处理,反而来得爽利。《民法典》并无履行不能后对待给付之命运归于何处的明文规定,但考虑到第590 条第2 款,迟延履行中即使发生不可抗力也不免除违约责任,若将受领劳务理解为一种义务,〔21〕劳动者从事劳动,除了获取薪酬的经济意义,尚有发展职业能力、实践工作价值、保护人格尊严等抽象层面的意义,因此劳务之提供某种程度上亦属工作权之内容,自然有请求雇用人受领之请求权。参见王利明:《合同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227-228 页;黄立:《民法债编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383 页。则解释上,因债权人原因所致的无法补服劳务,与迟延后因不可抗力造成的履行不能,似可作同等评价,债权人均不免除违约责任。这里的违约责任自然包括继续履行合同约定的债务(《民法典》第577 条、第579 条)。此外,当具备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时,应无风险负担规则之适用。〔22〕“履行不能制度既调整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导致的不能履行,也调整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导致的履行不能。风险负担规则只调整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导致标的物毁损灭失。”显然这里所说的履行不能既调整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不履行,亦调整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不履行,是同时涵盖了给付风险与价金风险的,在可归责于当事人的情形下并不根据给付不能法处理对待给付问题,而是适用风险负担规则。参见于韫珩:《论合同法风险分配制度的体系建构——以风险负担规则为中心》,载《政治与法律》2016 年第4 期,第80 页;江海、石冠彬:《论买卖合同风险负担规则——〈合同法〉第142 条释评》,载《现代法学》2013 年第5 期,第51 页;易军:《违约责任与风险负担》,载《法律科学》2004 年第3 期,第52 页。在本文语境下,债权人具有可归责事由,应属彰明较著之事,以风险负担规则处理本文问题的见解似不值赞同。
(二)司法实践的现状梳理
尽管解雇期间内的工资债权应得到支持,在教义学角度没有疑问,但具体如何实现工资债权,实践呈现的情形却复杂得多。
囿于审级,最高人民法院处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并不多见。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一个案件中,其一方面认可原被告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合同关系,且用人单位并不构成适法的解雇,但另一方面却并未支持不法解雇至劳动合同应当合法终止(因用人单位破产)期间的工资债权,而仅仅以职工平均工资为标准支持了6 个月的赔偿金。〔2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再50 号民事判决书。这个案例鲜明地代表了司法实践中的一种倾向——即使支持解雇期间内的工资债权,也不会以劳动者本人的工资标准为准,而是以地区平均工资或者企业平均工资、〔24〕参见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湘高法民再终字第78 号民事判决书。最低工资〔25〕参见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皖民申2892 号民事裁定书(但需要注意,这个案件是劳动者因涉嫌刑事犯罪被公安机关羁押,用人单位不知该情事,单方面以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但该通知因未向劳动者送达而不发生效力,因此仅系一种程序上违法);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黑民再210 号民事判决书;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民申808 号民事裁定书。等为标准计算一个数额,其结果往往低于劳动者本可以获得的收入。〔26〕参见喻术红、程凌:《违法解雇期间劳动者所得之性质与范围——兼论民法典相关制度之构建》,载《河北法学》2019 年第12 期,第54 页。
从下级法院的判决来看,有的案件直接支持了自不法解雇发生之时至裁决或者判决生效之日期间本可得到的工资。〔27〕且未讨论可能适用的减损规则。参见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陕民申2257 号民事裁定书(这个案件的特别之处在于,解雇期间内劳动者处于待岗状态,工资并不高,仅不足4000 元,这或许是值得注意的事实要素之一);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9)内民再574 号民事判决书(本案中另一个比较特别的事实要素是“郭志平作为失地农民,安排在郭志平在中石油呼市分公司工作,安排就业是对其失地的一种补偿,对郭志平的处罚不能简单等同一般员工的违纪行为来处理,企业应当考虑郭志平个人的具体情况,区别对待……要考虑企业安排失地农民就业的合同义务,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不能简单地将职工推向社会”)。但这样的案件在数量上属于绝对少数。绝大多数案件支持的工资债权与劳动者本应得到的工资相比,均处于一种较低水平。根据限制工资债权的具体进路,大体可分为直接限制、设置上限以及区分违法类型三种做法,以下分述之。
直接限制,即由司法裁判径行提出某一较低工资标准。例如,有的案件以劳动者未实际提供劳动为由,以失业保险的标准计算补发的工资;〔28〕参见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赣民申249 号民事裁定书。或者以未提供劳务为由支付少量生活费;〔29〕参见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陕民申3085 号民事裁定书。在另外一个案件中,生活费的标准是当地最低工工资的80%,参见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冀民申3876 号民事裁定书。或者以未提供劳务为由以最低工资标准计发解雇期间内的工资。〔30〕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浙民再181 号民事判决书。有的案件虽认可工资应当得到支持,同时应考虑劳动部《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第3 条第1 项的规定加付25%的工资,但认为主张补发的工资过高,应当参照最低工资标准计算。〔31〕参见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黑民申536 号民事裁定书。总的来看,法院在补发工资的问题上存在着一种谨慎保守的倾向,若补发工资数额并不高则获得支持的可能性较大;若工资数额很高,则即使认可工资债权成立,也往往会想方设法限制其数额。司法裁量权之大,一至于斯。
设置上限,即以“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作为最高限额。如《天津法院劳动争议案件审理指南》(津高法〔2017〕246 号)第28 条第2 款规定,解雇期间内的工资标准是劳动者12 个月的平均工资,又在此基础上设置了“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上限,其来源无疑是《劳动合同法》第47条第2 款经济补偿的计算方式。但这样的限制似乎无任何上位法的授权依据,不无违法之嫌。
区分违法类型则分别对程序违法、实体违法适用相异的标准,仅在程序违法时采取较低的工资标准。譬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2009 年8 月17 日发布)第24 条即区分了两种情形,若不法解雇仅仅违反了程序性事项,则以最低工资标准支付,若违反实体性规则,以正常劳动时的工资为计算标准。〔32〕参见程阳:《浅析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继续履行》,载《中国律师》,2019 年第4 期,第63 页。学说上也有区分程序性与实体性违法,给予不同类型之救济的观点。参见程立武:《困境与重构:劳动合同的继续履行——以实质性解决纠纷为视角》,载《法律适用》2016 年第2 期,第104 页。
总的来看,司法实践一方面倾向于支持不法解雇期间内的工资债权,但另一方面,这种对工资的支持也并非完全使劳动者恢复原状,令其获得若实际工作本可取得的工资,而是常常以某种较低标准计算。这样的酌情处置欠缺明确的规范依据,无论将解雇期间内的工资损失视为解雇无效溯及既往发生效力后的原给付请求权本身,还是损害赔偿意义上的损失,〔33〕譬如意大利法上倾向于将解雇期间内的工资损失定性为损害赔偿意义上的损失,而不是原定的给付请求权。大内伸哉「イタリヤの新たな解雇法制」季刊労働法239 号(2012 年)243 頁参照。都无法直接推导出以某一平均或者最低水平计算请求权额度的结论。此种最低或者平均标准一则赋予了法院过多的裁量权,似难免擅断之讥;二则不利于劳动者之保护;三则无法起到阻遏非法解雇的作用。反观比较法的经验,无论是英国、美国,还是日本、〔34〕水町勇一郎『労働法』(有斐閣,2018 年)258 頁「労働者は賃金全額を請求できる」参照。韩国、〔35〕野田進「韓国における不当解雇等の労働委員会による救済」季刊労働法226 号(2009 年)250 頁参照。意大利,〔36〕大内伸哉「イタリヤの新たな解雇法制」季刊労働法239 号(2012 年)243 頁参照。其计算解雇其期间内的工资债权或者工资损失无不以劳动者本人的工资作为标准。我国司法实践呈现出“既支持,又不完全支持”的倾向,说明法院实际上也意识到了全面支持解雇期间内的工资债权,至少在结果上有违一般的直觉正义,只不过在技术层面欠缺一种妥当的限制该债权的规范依据。
三、扣除中间收入的规范依据:减损规则
正如上文,司法实践一方面不可公然违抗《劳动合同法》第48 条继续履行救济对给付工资的要求,另一方面全额支持解雇期间内工资有违一般的直觉正义,于是产生了限制工资债权的规范供给需求。在讨论减损规则的具体适用之前,不妨先考虑其他理论或者规范依据对工资债权的限制作用。
(一)对损益相抵的检讨
前揭案例中,许多法院以劳动者并未实际提供劳务缩减工资请求权,是一种损益相抵的思路,方法论上有所欠缺。损益相抵中,因不法行为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可能消极地节省费用,或者积极地获得利益,〔37〕参见杨芳贤:《民法债编总论(上)》,三民书局2017 年版,第387 页;钟淑健:《损益相抵规则的适用范围及其援用》,载《法学论坛》2010 年第3 期,第126 页。以下分别考虑。
1.节省的费用
即使以损益相抵规则作为规范依据,〔38〕类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20 修正)第23 条的规定,即“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因对方违约而获有利益,违约方主张从损失赔偿额中扣除该部分利益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则劳动者从非法解雇中节省的劳动力本身,也不应视为“节省的费用”。因为如果将劳动合同视为以劳动力交换工资的合同,则因非法解雇可以说节省了所有的给付,因而根据损益相抵几乎要丧失全部的对待给付请求权,这显然违背了损益相抵的制度本旨。〔39〕损益相抵本质上也是一个评价问题,而非逻辑问题。参见程啸:《损益相抵适用的类型化研究》,载《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5 期,第28 页。因为适用损益相抵规则将导致全有或全无的逻辑结论,因此即使适用损益相抵,“利益”范畴似乎也应当限定为应支出而未支出的费用,如出租车司机因被解雇而节省的油钱,而不能及于劳动力本身。司法实践中常见的“未实际提供劳动”并不能成为损益相抵的坚实理由。〔40〕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沪二中民三(民)终字第1394 号民事判决书。
2.取得的利益
劳动者因不法解雇事实上从他处获得收入,也可能引起损益相抵规则的适用。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即认为台湾地区“民法”第487 条〔41〕雇用人受领劳务迟延者,受雇人无补服劳务之义务,仍得请求报酬。但受雇人因不服劳务所减省之费用,或转向他处服劳务所取得,或故意怠於取得之利益,雇用人得由报酬额内扣除之。对解雇期间内中间收入的扣除属于损益相抵之适用。〔42〕参见侯岳宏:《民法第487 条但书中间收入扣除》,载《月旦法学教室》2019 年第204 期,第10 页。但损益相抵有严格的因果关系要求,即取得的收入与不法解雇之间,评价上应认为有相当之因果关系,〔43〕参见程啸:《损益相抵适用的类型化研究》,载《环球法律评论》2017 年第5 期,第29 页;赵刚:《损益相抵论》,载《清华法学》2009 年第6 期,第92-93 页;孙森焱:《民法债编总论(上册)》,法律出版社2006 年版,第377 页。在因第三人给付获益时尚须考虑该给付之目的是否包括减轻加害人责任。〔44〕参见钟淑健:《损益相抵规则的适用范围及其援用》,载《法学论坛》2010 年第3 期,第128 页。日本便有学者对日本扣除中间收入的司法实践提出批评,认为典型的损益相抵的例子是建筑物因火灾毁损,被侵权人获得残余之利益,此时损害与利益系出于同一原因事实;〔45〕参见侯岳宏:《日本非法解雇期间工资与中间收入扣除之发展与启示》,载《政大法学评论》2012 年第128 期,第368 页。而在非法解雇场合,前述因未提供劳务而节省的交通费等费用得以损益相抵扣减,〔46〕参见孙森焱:《民法债编总论(上册)》,法律出版社2006 年版,第377 页。而积极获得的利益,其原因在于劳动者本人缔结新合同的意思,且会伴随新的负担(向新的雇主提供劳动),此两种利益显然不应等而视之。〔47〕川口美貴『労働法』(信山社,2018 年)610 頁参照。退一步讲,即使承认一般情况下存在相当因果关系,至少在某些特殊情形下难认为存在因果关系,譬如遭到不法解雇后自己创业得到收入的案例。〔48〕See Cornell v.T.V.Dev.Corp., 17 N.Y.2d 69; Kramer v.Wolf Cigar Stores Co., 99 Tex.597; Timothy Murray, Corbin on Contracts, Matthew Bender & Company, Inc, 2020,§60.7.要言之,在劳动者实际上从他处获得利益的场合,损益相抵因存在严格的因果关系限制,很多时候无法实现扣减中间收入之目的。
3.恶意不取得的利益
损益相抵不解决恶意不取得之假想收入的问题,原因在于损益相抵并不对劳动者提出积极寻找其他工作机会的规范性命令。举例言之,在不考虑竞业禁止的情况下,解雇期间内,其他用人单位提出条件优厚的要约,劳动者并无正当理由拒绝,便可能构成怠于取得甚至恶意不取得的利益。若以损益相抵处理此问题,可能造成寻求了新工作机会的劳动者因重新工作中获得工资收入,原工资债权受到扣减,消极地未采取行动的劳动者反而可以得到全额的工资,显失事理之平。〔49〕川口美貴『労働法』(信山社,2018 年)610 頁参照。
我国台湾地区通说以损益相抵作为扣减中间收入的依据,〔50〕参见林诚二:《民法债编各论(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19 页;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242 页。这就无法解释台湾地区“民法”第487 条何以明定“故意怠于取得之利益”亦应扣除。换言之,积极寻求替代工作机会的法理依据应在减损义务(或者第217 条之与有过失),而非同法第216 条之1 的损益相抵。可作为论据的是,日本法似乎也倾向于将解雇期间内事实上从他处获得的中间收入作为一个损益相抵的问题来处理,并不积极地要求劳动者履行寻求新的劳动机会的减损义务,理由之一正是日本《民法》并无类似于《德国民法典》第615 条第2 句(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487 条)的规定,即并未明确受雇人就恶意不取得的利益不得要求赔偿。〔51〕盛誠吾「違法解雇と中間収入」一橋論叢106 卷1 号(1991 年)26 頁参照。也就是说,若法律并不对当事人提出寻求其他工作机会的规范性命令(日本),即属于损益同销之范畴;反之,如果积极地要求作为非违约方的劳动者寻求替代的工作机会,否则就恶意怠于取得的收入不得请求赔偿(德国、我国台湾地区),即已经逸出损益同销之范畴,进入减损义务的领域。我国学说上有论者认为事实上的中间收入或许应当扣减,但怠于取得的收入似乎不应当归入扣减的范围,〔52〕参见喻术红、程凌:《违法解雇期间劳动者所得之性质与范围——兼论民法典相关制度之构建》,载《河北法学》2019 年第12 期,第56 页。有学者认为解雇期间内(停发工资至裁定或判决生效时)的工资应当全部赔偿,但如果用人单位能够证明劳动者存在其他收入,则应当扣除之。这里仅仅提到了事实上获得的工资应当扣除,未讨论怠于取得的收入是否应当扣减的问题。参见肖进成:《重构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法律责任的思考》,载《西部法学评论》2013 年第1 期,第68 页。这便拒绝了减损义务的适用,本质上是一种损益相抵的理念。〔53〕注意,这里的损益相抵仅认可从其他渠道获得的工资收益系因不法解雇而获得的利益,节省的劳动力本身并不属于获益之范畴。但这样的观点无疑将导致上述悖于法律逻辑及情理的局面,故仍应适用减损规则。
(二)对过失相抵的检讨
减少解雇期间内工资请求权的另一条可能路径是与有过失。典型者如《上海市企业工资支付办法》第23 条规定,应当以不法解雇前12 个月的平均工资计算解雇期间内的工资损失,同时“双方都有责任的,根据责任大小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54〕《上海市企业工资支付办法》(沪人社综发〔2016〕29 号)第23 条。因此,若劳动者的轻过失行为可能引发违法解雇之发生,该过失行为在实质上虽不直接充足过失性辞退的要件,因此解雇仍属不法,但毕竟劳动者的过失行为是引发解雇的原因,有的法院以此为由扣减工资债权,应值赞同。〔55〕参见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0)徐民一(民)初字第3143 号民事判决书。若劳动者的行为满足《劳动合同法》第39 条过失性辞退的要件,但发生程序性违法,本条亦应有适用余地。若仅因解雇程序的瑕疵而给予与无过失之劳动者相同待遇,殊难谓正义。此时在教义学上如何缩减工资损失的请求权,应有《民法典》第592 条第2 款之与有过失适用的空间。
需要注意的是,若属于劳动者并无过错的程序性违法解雇,似也并无直接限制工资债权的依据。《劳动合同法》并未区分实体性与程序性违法而区别对待,其原因在于遏制非法解雇,仅有实体层面的手段犹嫌不足,程序上也必须满足法定要求。譬如英国法对违法解雇的救济分为普通法上的不法解雇(wrongful dismissal)与制定法上的不当解雇(unfair dismissal)。〔56〕制定法创设的新救济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缓解普通法的严苛,为雇员提供更周全的保护。不当解雇的请求权基础并不在于合同,而是制定法本身,劳动者对该职业拥有一种财产性权利(property right)。See Charles Barrow & Ann Lyon, Modern Employment Law, Routledge, 2018, p.116.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不当解雇的救济并不容易获得。按照英国司法部门的统计,2009—2010 年向仲裁庭提出的近五万件申请中,仅有约8%最终获得支持,大量的案件走向撤回申请、和解、被对方瓦解等结局。See Hugh Collins et.al.,Labour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894.前者主要是指违反了解雇应当遵循的通知等程序要求,〔57〕See Charles Barrow & Ann Lyon, Modern Employment Law, Routledge, 2018, p.83.后者则指存在某种实体性违法的情形。普通法针对不法解雇提供的救济旨在使劳动者回复至合同得到正常履行的状态,因此对工资高、合同期限长的劳动者更有利,且并无赔偿的上限;相反,一般的劳动者援引制定法上不当解雇的救济反而更有利,即使存在上限额度的限制,也因为其收入事实上未达到这一水平而可获得全额的工资收入赔偿。〔58〕See Charles Barrow & Ann Lyon, Modern Employment Law, Routledge, 2018, p.83.可见,并不存在程序性违法的“违法性较低”而限制劳动者请求权的做法。对非法解雇的遏制,程序与实体的手段应不可偏废。
综上所述,损益相抵仅可处理事实上取得其他收入是否应予扣除的问题,无法解决怠于取得的假想收入是否扣除的问题,且损益相抵存在严格的因果关系要求,因此不宜作为处理中间收入扣除的依据。与有过失仅在劳动者具有过错的情况下才可作为限制解雇期间内工资债权的手段,劳动者并无过错的程序性违法解雇中,原则上仍应当以劳动者本人的收入水平作为计算标准,因此与有过失的适用范围非常有限。故仍需寻求其他有效手段。
(三)可能的方案:减损规则
以某种最低或者平均标准计算劳动合同继续履行的工资债权,欠缺制定法依据,不无违法之嫌。而想要实现限制工资债权的效果,合目的且符合法律逻辑的手段毋宁是《民法典》第591 条第1 款。详言之,第591 条所规定的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包含了作为非违约方的劳动者在非法解雇发生后,将本应用于此处的劳动力投入彼处以获得收入。倘使坐以待毙,任由劳动力闲置,则可能造成损失的扩大,应获得而未获得的收入即不可要求赔偿。最高人民法院2022 年11 月4 日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部分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征求意见稿)》)第64 条规定“在租赁、合作等持续履行的合同中,人民法院可以……确定非违约方寻找替代交易的合理期限,并按照该期限对应的租金、价款或者报酬等扣除非违约方应当支付的相应履约成本后确定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毫无疑问,这正是减损义务之下替代交易的逻辑,而劳动合同作为一种持续履行的合同,恰恰落入本条的射程。
1.比较法的观察
自比较法言之,扣减解雇期间内获得或者怠于获得的中间收入系各国通例,以此在劳动者保护与不过度制裁用人单位之间达成平衡。《德国民法典》第615 条第2 句即规定(雇佣契约)“义务人因不服劳务所减省费用,或转向他处服劳务所取得或恶意不为取得之价额,应扣除之”,〔59〕台湾大学法律学院、台大法学基金会编译:《德国民法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577 页。即使劳动者不提供劳务也不丧失报酬请求权,惟应当有所扣减。〔60〕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分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295 页。德国《解雇保护法》第11 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487 条亦有相同规则。由是观之,违法解雇发生后,非违约的劳动者负有积极从其他来源取得收入的不真正义务。《日本民法典》第536 条第2 项在债法总则—履行不能的部分处理这一问题,履行不能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时,债权人可拒绝为对待给付;若履行不能可归责于债权人,则其不得拒绝为对待给付;但债务人因免除债务而获得的利益,应向债权人偿还。在非法解雇的场合,通说认为合同陷于履行不能,用人单位虽不得拒绝支付解雇期间内之报酬,但债务人从他处获得的劳动收入应予扣除。上述大陆法系例子虽然系有名合同或者债法总则的规则,其原理仍然可说植根于减损义务。韩国、〔61〕野田進「韓国における不当解雇等の労働委員会による救済」季刊労働法226 号(2009 年)250 頁参照。需要注意的是,根据韩国《劳动基准法》,仅当相对人申请,并查明劳动者在解雇期间内的收入后才可扣减中间收入,换言之作为行政机关的劳动委员会并不会主动开启对中间收入的调查。意大利〔62〕意大利的解雇法体系比较复杂。按照对违法解雇的救济方式,分为劳动者可选择救济方式(可选择1.复职并赔偿解雇期间内工资损失;或者2.替代复职的赔偿金并赔偿解雇期间内的工资损失)的解雇与直接金钱赔偿的解雇,前者的违法程度重于后者。以可选择救济方式的解雇为例,其中又可析分出两种违法程度不同的解雇,姑且称为甲型和乙型。甲型包括歧视性解雇(例如以政治观点、宗教信仰、所属工会以及参加的工会活动等为理由的解雇)、违反生育保障的解雇、不法解雇(根据《意大利民法典》第1345 条判断)以及未以书面形式通知的解雇。除最后一种违反程序性规则的解雇不发生解雇效力外,另外几种甲型的解雇均为无效。此时劳动者可选择复职的救济,法院判决复职的同时会要求用人单位赔偿劳动者因无效解雇遭受的损失,即自解雇发生至实际复职之日的工资损失。但此时应扣除实际上从其他用人单位处获得的报酬。在违法性稍弱的乙型解雇中(例如雇主以劳动者的不法行为为由而解雇,事后证明该不法行为不存在),不仅需要扣除实际上取得的中间收入,还需要扣除本可努力获得却未获得的收入。详细的规则体系,大内伸哉「イタリヤの新たな解雇法制」季刊労働法239 号(2012 年)242-245 頁参照。也存在相同做法。
英美法上的劳动合同同样受制于一般合同法上的减损义务,劳动者事实上从他处获得的收入应当从工资损失中扣除;恶意不获得的收入则属于可避免之损失,亦应扣除。〔63〕减损规则的主要内容包括:1 被告的不法行为发生后,原告必须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减少损失,否则不得要求赔偿本可以合理避免的损失;2 原告采取合理措施减损发生的成本或者损失由被告负担,即使减损并不成功(损害反而扩大)也是如此;3 原告采取规则1 要求以外的减损措施,则成功避免的损失均不得要求赔偿,亦即损害赔偿的范围以最终实际发生的损失为准。See Harvey McGregor, McGregor on Damages(18th ed.), Thomson Reuters, 2009, p.7-001; [英]H.G.比尔:《奇蒂论合同法》(第30 版),商务印书馆2012 年版,第26-101 页;Dan B.Dobbs, Law of Remedies(2nd ed.), West Publishing Co.1993, p.271.〔64〕See Harvey McGregor, McGregor on Damages(18th ed.), Thomson Reuters, 2009, p.7-040; Charles Barrow & Ann Lyon,Modern Employment Law, Routledge, 2018, pp.84-85.英国早期(19世纪初)的普通法曾出现过所谓的“拟制服务规则”(constructive service doctrine)——在非法解雇的场合,只要受雇人在约定的剩余期间内仍然保持着提供约定服务的状态,并且愿意随时提供服务,则法律上视为他已经履行了债务,约定期间届满后即可请求雇主给付报酬。这一项规则早已废止,〔65〕惟在涉及军人、政府雇员时得到有限保留。“依拟制服务规则,军人被非法或者不当解除职务者,应视其仍在继续履行现役职责,直至其职务被合法解除为止。”See Christian v.United States, 337 F.3d 1338; Timothy Murray, Corbin on Contracts, Matthew Bender & Company, Inc, 2020,§60.7.在涉及政府官员(o☆cer)的案件中,美国法上的规则是官员与政府之间并不存在合同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直接由法律调整,官员要求薪酬的权利亦直接本于公法而不是契约。可以认为官员的薪酬是他职位的附属物(incident)。故若该官员在法定任期结束前被解雇,则其在该剩余期间内获得的其他报酬不应当在对政府的请求权中扣减。See Gentry v.Harrison, 194 Ark.916; Timothy Murray, Corbin on Contracts, Matthew Bender & Company, Inc, 2020§60.7.比较特别的是佐治亚州的法典仍然保留了这一规则。See O.C.G.A.§10-6-37.佐治亚州最高法院坦言,拟制服务规则固然已经过时,但修改这一规则并非法院所能越俎代庖之事,而应由州议会决定。See Harvey v.J.H.Harvey Co., 276 Ga.762,.因为这将造成无必要的经济浪费。〔66〕See Timothy Murray, Corbin on Contracts, Matthew Bender & Company, Inc, 2020§60.7.
2.反对减损规则适用的理由
否定适用减损规则的理由主要在于,考虑到前后劳动关系条件的差异、劳动者遭受的精神痛苦、付出的时间成本等因素,应当认为劳动者从其他雇主处获得的报酬与无效解雇之间并不存在相当因果关系。〔67〕山本陽大「解雇の救済方法」土田道夫=山川隆一编『労働法の争点』(有斐閣,2014 年)82 頁参照。倘若扣除中间收入,则意味着劳动者遭受上述不利之后获得的利益,竟归属于不法解雇的始作俑者,难谓公允。〔68〕盛誠吾「違法解雇と中間収入」一橋論叢106 卷1 号(1991 年)27 頁参照。
日本法上还提出另外一条值得思考的反对理由。处理劳动争议的行政机关“劳动委员会”可作出支付解雇期间内工资的救济命令,称为复职付薪(バックペイ,即英文的back pay)。〔69〕劳动委员会是解决劳动争议的行政机关,可作出有效力的行政裁决,其作出的支付解雇期间内工资的命令称为复职付薪,不服该裁决的可针对该命令提起行政诉讼;也可直接针对劳动争议向法院起诉,行政手段并不是必要的前置程序。野川忍『労働法』(日本評論社,2018 年)1006-1007 頁参照。起先法院认为裁令支付全额工资超出了劳动委员会的裁量权,构成违法。但在1977 年的一起案件中,最高法院则认为救济命令的制度目的或许不应局限为对个别劳动关系中个人的救济,同时应保障劳动者的团体活动不受一般之妨害,〔70〕荒木尚志『労働法』(有斐閣,2020 年)766 頁参照。因此中间收入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与不法解雇抗衡的“斗争资金”。〔71〕柴田洋二郎「バックペイと中間収入の控除」土田道夫=山川隆一编『労働法の争点』(有斐閣,2014 年)232-233 頁参照。换言之,不予扣除的中间收入可作为一种对不法解雇斗争行为的“补贴”(subsidy),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不法解雇的遏制。〔72〕只不过后来出现的判例又认为这种对不法解雇的打击实际上收效甚微,扣除中间收入对团体行动的影响也不大,因此仍然应当在复职付薪中扣除中间收入。野川忍『労働法』(日本評論社,2018 年)1019 頁;川口美貴『労働法』(信山社,2018 年)960 頁参照。乍见之下,以上两条理由在我国也能成立,但却禁不起推敲。
3.反对适用减损规则的理由在我国无法成立
日本以及其他国家,为弥补劳动者遭受的精神痛苦、花费的时间等不认可中间收入之扣除,其前提是解雇期间内的工资损失以劳动者实际参加工作可得的工资为计算标准,而不是我国实践中通行的某种最低或者平均标准。在这样的前提下谈论是否应拒绝减损规则以保护劳动者才有理论及实践意义。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主流以平均或者最低标准计算工资损失的情况下,似乎根本没有讨论减损规则是否应予适用的空间——以上述标准计算出来的数额本来已经极低了,实在减无可减,断无过度保护之虞。即使以保护劳动者为由否定减损规则之适用,也只能说是一种“虚伪的保护”。
由是观之,减损规则在我司法实践中未受到足够关注,原因非在于无此需求,而在于司法裁量权的错误运用已经将解雇期间内的工资债权限定在较低水平,故而并无诉诸减损规则之必要。这样的做法因为欠缺规范依据,而不无违法之虞。其可能的弊害首先是忽略了个案事实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譬如一般劳动者与公司高管之间统一适用某种最低或者平均标准,或许难谓允当。另外,最低或者平均标准(或者其某一倍数)本身即不止一种,全委诸司法裁量,当事人将无法预见案件的结果,法的可预测性受到极大妨害。各省市自治区的司法机关各出机杼,以不同的标准算定解雇期间内的工资债权,也与我国统一的司法体制不相容。
四、依据减损规则扣除中间收入的具体适用
正如前文所述,就减损规则的适用而言,其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并不复杂。构成要件方面,至少应当包括:发生解雇,解雇被仲裁委员会或者法院认定为违法,作为非违约方的劳动者的行为不满足合理减损措施的要求。其法律效果则是本可以合理措施避免的损失属于“损失扩大”,劳动者丧失该部分请求权。作为一种不真正义务,非违约方即使违反这样的“义务”也不构成不法行为,〔73〕See Andrew Burrows, A Restatement of The English Law of Contrac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131.相对人/违约方也并不取得一种狭义的请求权。需要注意的是,非但事实上取得的其他收入应予扣除,恶意不取得的假想收入亦须扣除之,从而达到限制工资债权,避免人力资源浪费的效果。减损义务仅要求劳动者以合理的努力寻求替代的工作机会,只要满足了合理之标准,即使未找到新的工作,亦得要求全额的工资赔偿。譬如当就业市场不景气而很难找到新工作时,法律也不应苛责劳动者。就举证责任而言,应由作为违约方的用人单位举证证明劳动者未合理尽其减损义务。〔74〕参见[德]彼得·施莱希特里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评释》,李慧妮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212 页。長谷川義仁『損害賠償調整の法的構造』(日本評論社,2011 年)40 頁参照。See Djakhongir Saidov, The Law of Damages in International Sales: The CISG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s, Hart Publishing, 2008, p.147.
可以看到,减损规则具体适用的难点主要有二:1.在此情境下是否适用的问题;2.劳动者行为的合理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此情境下是否应当适用减损规则扣减中间收入,这也是本文的主要价值所在,前文主要解决的也是这个问题。后者则是一个事实而非法律问题,涉及司法实践中综合个案事实所为的整体判断,几乎无法从理论上抽象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而只能求诸各异的案件事实,委诸法官的裁量权。〔75〕See Richard A.Lord, Williston on Contracts(4th ed.), West Group, 2021,§64:31; Neil Andrews et.al., Contractual Duties:Performance, Breach, Termination and Remedies(2nd ed.), Sweet & Maxwell, 2017, p.24-054; Andrew Burrows, A Restatement of The English Law of Contrac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132;[英]克里斯托弗·沃尔顿,《查尔斯沃斯和珀西论过失》(第12 版)商务印书馆2012 年版,第5-45,6-81 页;Adam Kramer, The Law of Contract Damages, Hart Publishing, 2017, p.15-112.吉川吉樹「履行期前の履行拒絶に関する一考察(二)」法学協会雑誌124 卷11 号(2007 年)2446-2447 頁参照。因此下文将要讨论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典型案件事实所作的类型化分析,其鹄的在于解决劳动者的行为是符合抑或违反了减损义务的合理性要求,进而决定是否应当扣减中间收入及其请求权之范围。
(一)扣除中间收入的具体规则
减损义务指涉的中间收入,包括应取得、实际上未取得的假想收入,亦即怠于取得的收入,与实际上取得的收入,以下分别讨论。
1.怠于取得之收入
减损规则语境下不仅需要扣除事实上已经取得的中间收入(avoided consequences),对应取得而未取得的收入(avoidable consequences),亦应扣除之。减损规则提出的这种规范性命令,旨在鼓励劳动力资源的有效利用,避免经济浪费。就何种情况下认为劳动者违反了寻求替代交易的减损义务,须审慎斟酌以定之。首先对于“怠于取得”,文义上可能存在不止一种理解。第一种是事实上订立了新的劳动合同,只不过劳动者不向新的用人单位主张工资债权,甚至以免除债务的形式放弃工资债权;〔76〕参见林诚二:《民法债编各论(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19-20 页。第二种是存在可以通过合理努力取得的工作机会,却怠于订立新合同。〔77〕参见郑玉波:《民法债编各论(上册)》,三民书局1986 年版,第340 页。第一种方案自然更有利于劳动者的保护,但就文义而言似乎过于狭隘,这样的解释方案也不符合鼓励劳动力之利用的经济理性,不值赞同。
在第二种理解下,新的工作机会应当具体化到何种程度?有论者认为必须存在具体的当事人向劳动者发出新要约的客观事实,而劳动者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之,才可说违反了减损义务,进而按照新要约的工资条件予以扣减。〔78〕参见侯岳宏:《日本非法解雇期间工资与中间收入扣除之发展与启示》,载《政大法学评论》2012 年第128 期,第385 页。在这样的理解下,举证责任分配应更谨慎些,用人单位提出存在新要约的初步证据后,举证责任即应移转至劳动者一方,由劳动者举证证明不存在这样的要约,或者拒绝该要约存在正当理由。相反的意见则是只要存在充足的工作机会,而劳动者无合理理由不获取该等机会,则至少可依类似岗位的工资水平予以扣除,而不必有具体的工作要约存在。〔79〕参见侯岳宏:《日本非法解雇期间工资与中间收入扣除之发展与启示》,载《政大法学评论》2012 年第128 期,第385 页。本文认为后一种理解似更妥当,也更符合司法实践对限制工资债权的实际需求。〔80〕在就业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法院的裁量无疑需要更加谨慎。然而无论采何种见解,劳动者违反减损义务,应取得收入而未取得,结果上的举证责任均应由作为违约方的用人单位承担。而这是相当繁重的举证责任,用人单位常常难以满足,〔81〕吉川吉樹「履行期前の履行拒絶に関する一考察(二)」法学協会雑誌124 卷11 号(2007 年)2445 頁参照。Also see Timothy Murray, Corbin on Contracts, Matthew Bender & Company, Inc, 2020 §57.13.因此不必过于担心对劳动者的自由形成不可估量的限制。在劳动者事实上未订立新合同,可能构成怠于取得利益时,因并无具体的工资数额,应如何扣减中间收入?若用人单位能够举证证明存在某个具体的要约,且劳动者并无合理理由而拒绝之,则可以该要约的具体内容作为扣减依据。若并无具体的要约,而仅存在一种抽象的获得工资的可能性,且劳动者怠于利用其劳动力之时,可依类似岗位本可获得的收入予以扣减。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劳动者在解雇发生后为保障生活来源到其他用人单位就职,竟然常常会导致劳动合同是否无法继续履行的争议,〔82〕参见程立武:《困境与重构:劳动合同的继续履行——以实质性解决纠纷为视角》,载《法律适用》2016 年第2 期,第100 页;喻术红、程凌:《违法解雇期间劳动者所得之性质与范围——兼论民法典相关制度之构建》,载《河北法学》2019 年第12 期,第48-49 页;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民申字第503 号民事裁定书(“而且何蓉目前已在另一中学任教,双方实际已不具备继续履行聘用合同的主、客观条件,故二审法院对何蓉要求顺德一中德胜学校与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鄂民申字第00700 号民事裁定书。从而影响劳动者依《劳动合同法》第48 条前段要求继续履行的选择权。这从减损规则的角度看是不可思议的,从社会福利的角度考虑,法律应当鼓励劳动者将劳动力投入使用,若将另行订立劳动合同认定为继续履行不能的事由,而非合理积极的减损措施,无疑将造成劳动者不敢另寻生路的局面。劳动者可能以实际履行的法律救济将受到新劳动合同影响为由,拒绝缔结新合同,从而不构成怠于取得收入,而排除减损规则之适用。
2.积极取得之收入
减损规则要求扣减中间收入的正当性基础在于,缔结的新合同可视为原合同之替代,若新工作与原工作全不相干,则难免产生后合同是否替代前合同,从而是否应予扣减后合同收入的疑问。
(1)从事其他职业
美国法上的减损义务最为强大,即使新工作与原工作毫无关联,也认为应当扣减中间收入。在一个案件中,受雇人本是某地教育委员会聘用的学官(school administrator),被非法解雇后成为一名直升飞机的飞行员。尽管该州有制定法规定,在非法解雇期间,如果受雇人从其学区或者州的机关获得收入(比如从校长任上被解雇,又获得小学教员的职位,获得教员的薪水),则这部分收入应当从赔偿额中扣减,但法院认为这项规则并不能反面解释出其他收入不应当扣减的结论。其正当性理由在于违约的发生不应当使非违约方的境遇更优,否则将会对违约方产生一种刑罚(penalty)的效果。〔83〕See Bd.of Educ.v.Jennings, 102 N.M.762.相比之下,英国法则采取一种实质性的判断标准,如果新合同下,受雇人运用的技能、付出的努力和时间基本与原合同相同,则即使新合同在形式上不同于原合同,也无妨将新合同作为原合同的替代交易,减少被告的赔偿责任。但如果原告在新工作中需要运用不同的工作技能或者付出更大的努力,法院往往会给予这种不同的付出以补偿(allowance),仅仅扣减一部分中间收入。〔84〕See Hugh Beale, Chitty on Contracts(32nd ed.), Sweet & Maxwell, 2015, p.26-100.相比之下,后一种做法似乎更值得借鉴。经由该实质性标准对减损规则予以缓和与修正,无疑会增强受雇人积极寻找替代劳动机会的动机,〔85〕See Hugh Beale, Chitty on Contracts(32nd ed.), Sweet & Maxwell, 2015, p.26-101.并鼓励劳动者有效率地利用其劳动力。
(2)自主创业
如果原告在遭受非法解雇后,不再受雇于他人,而是开启自己的事业,那么自主创业的收入应否在请求赔偿欠薪时扣除呢?在美国纽约州的一个案件中,原告受雇于一家电视发展公司,被非法解雇后贷款设立公司,进入电子行业。法院认为原告可能从公司获得的利润应当作为中间收入扣除。〔86〕See Cornell v.T.V.Dev.Corp., 17 N.Y.2d 69; Timothy Murray, Corbin on Contracts, Matthew Bender & Company, Inc,2020§60.7.固然,减损义务仅要求当事人以合理的努力采取减损措施,但如果行为人的勤谨程度超出了对一般人的合理期待,避免了更多损失,则所有避免的损失均需扣减,亦即以事实上的损失作为赔偿标准。〔87〕See Harvey McGregor, McGregor on Damages(18th ed.), Sweet & Maxwell, 2009, pp.7-004-7-006; [英]H.G.比尔,《奇蒂论合同》(第30 版),商务印书馆2012 年版,第26-101 页。在这个意义上,通过自主创业事实上获得的利润似乎确实可以扣减。而在哥伦比亚特区的一个案件中,原告主张被告基于性别歧视,对自己晋升合伙人的申请作出缓表决(on hold)决定,并最终拒绝了该申请。这个决定作出五个月后,原告所在部门的合伙人决定不再提名原告晋升合伙人,是年11 月原告提交辞呈,次年1 月被告接受原告辞职。后来原告设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自公司设立至法院判决,经营公司为原告带来的收入为每年4 万到6 万美元不等。但法院认为设立公司尚不能说明原告合理地(with reasonable diligence)尽到了自己的减损义务,因为原告出于自己成为合伙人的执念,拒绝了一些相当的职位,以至于其收入长期低于本可以从类似职位获得的收入。甚至有的单位允诺原告暂时出任高级经理职位(与原告在被告处的职位相同),并且相对优先地考虑她晋升合伙人的机会,也遭到了拒绝。法院最终判决,若原告尽到了合理的努力,本可获得平均十万美元的年薪,故原告之请求权的范围应限制在被告合伙人的年薪扣减每年十万美元的范围,而不应以原告经营公司的实际收入为准。〔88〕See Hopkins v.Price Waterhouse, 737 F.Supp.1202; Timothy Murray, Corbin on Contracts, Matthew Bender & Company, Inc,2020§60.7.要言之,如果创业收入反而低于类似职位可能获得的收入,可能构成减损义务违反,而以后者为扣减依据。〔89〕当然,这个案件确实存在应当予以特别考量的情节,例如有用人单位提出十分有竞争力的要约而遭到拒绝。
但倘若解雇后开创的事业并未盈利,又当如何处理呢?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个案件中,原告被一家烟草公司解雇,随后开设了自己的烟草店。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原告无法获得类似的职位,因为在案件发生的达拉斯,并没有与他受雇的烟草公司相似的企业。法院认为在无法获得类似职位的情况下,受雇人有义务寻找适合自己的其他类型的劳动机会;而如果不存在任何符合条件的职位,问题将转向原告设立公司获得的收益应否从欠薪中扣除。〔90〕See Kramer v.Wolf Cigar Stores Co., 99 Tex.597; Timothy Murray, Corbin on Contracts, Matthew Bender & Company, Inc,2020 §60.7.在本案中,原告的公司尚未实现盈利,其律师主张既然原告已经尽到了获取其他收入的合理努力,却未能盈利,则原告之请求权范围自然不应当受到任何影响。但法院观点认为,尽管公司还没有净利润,但原告的努力已经增加了企业的总体价值,而在确定原告得请求的数额之时,很难说不应考虑这一部分增值。〔91〕See Kramer v.Wolf Cigar Stores Co., 99 Tex.597; Timothy Murray, Corbin on Contracts, Matthew Bender & Company, Inc,2020 §60.7.由是观之,得克萨斯州法院在一般规则的基础上提高了对非违约方的要求,原告的请求权不仅要扣减实际获得或者本可获得的现金价值,还需要扣除企业的无形增值。这与美国法上普遍强势的减损规则相得益彰。
但扣除自主创业所得收益的规则是否合理仍然存在极大的讨论空间。科宾就批评说“尽管若不存在非法解雇,受雇人根本不会开启一项新的事业,但我们能够期待受雇人本来就愿意冒这么大的商业风险吗?这是不合理的。既然她投身商业,注入资本,那么收益和损失都应当属于她自己。”他主张扣减的数额应当以受雇人在类似岗位上获得或者可以获得的报酬为准。〔92〕See Timothy Murray, Corbin on Contracts, Matthew Bender & Company, Inc, 2020§60.7.换言之,如果要求扣减自主创业获得的收益(甚至是企业的无形增值)是合理的,那么相应的,减损规则也要求违约方承担减损措施的费用(《民法典》第591 条第2 款),因创业产生的亏损是否可要求违约方偿还呢?如果后一种结果令人难以接受,那么前一种结果也不应得到支持。但一律以类似岗位可能获得的工资作为扣减标准也将造成怪异的局面。如果无论当事人的自主创业是否盈利,均以其可获得的类似岗位的薪酬作为扣减依据,有过度拟制之嫌,其可能造成的结果就是劳动者因惧怕即使创业不盈利还要扣减类似岗位工资的结果,而打消创业的念头,从而对劳动者自由择业的就业权形成无必要的限制。因此从保障劳动者就业权的角度出发,若创业未实现净利润或者净利润低于类似岗位的工资收入,则以创业收入作为扣减依据,因此前揭哥伦比亚特区的案例不值赞同;若创业收入超过了类似岗位收入,则仅扣除类似岗位的收入。这里也可以看到如何扣减中间收入,进而确定用人单位责任范围,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法律逻辑上全有或全无的问题,而系于对双方当事人利益的权衡以及妥当的价值判断。〔93〕类似观点可参见赵刚:《损益相抵论》,载《清华法学》2009 年第6 期,第93 页(是否适用损益相抵扣减请求权应考虑公平的因素)。
(二)扣除中间收入的限制
减损义务对工资债权的克减并非漫无边际,即使扣减中间收入,也需要受到多方面的制约。
1.副业收入与销量损失规则
劳动合同往往具有排他性,如非用人单位违约,劳动者本没有机会订立新的劳动合同。反面言之,如果原合同并不排斥新合同,则减损规则不应适用,受雇人得享受两份合同的利益。〔94〕See Dan B.Dobbs, Law of Remedies(2nd ed.), West Publishing Co.1993, p.272.从因果关系的角度看,无论是否存在非法解雇,均可获得该副业收入,则可说解雇行为与副业收入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法律上的关联。这就是所谓销量损失规则(lost volume)在劳动合同中的适用。日本最高法院的判例认为,如果解雇期间内获得收入的来源是当事人的副业,即使不存在解雇也当然能取得该收入时,不属于应当扣减的范围。〔95〕「最高裁判所 1962 年 7 月 20 日判決,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 16 巻 8 号 1656 頁」 青木宗也ほか编『労働法判例』(有斐閣、1975 年)224 頁参照。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实践似亦有相同见解。〔96〕参见侯岳宏:《日本非法解雇期间工资与中间收入扣除之发展与启示》,载《政大法学评论》2012 年第128 期,第383 页。比较法上的这一经验,在我国法律适用中无疑值得借鉴。
2.扣减中间收入的最高额限制
依据减损规则对原合同期间内可得工资予以扣减,应当保留一定比例的工资,换言之,扣减的中间收入应该有上限。否则劳动者在遭到非法解雇后另寻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如果全依减损规则扣除之,则实施了不法行为的用人单位便无须承担任何责任,殊失事理之平。
以日本法为例,日本最高法院赞同应从可得工资中扣除解雇期间内从其他来源获得的工资收入,但此种扣除仅以《劳动基准法》第12 条第1 项规定的基本工资为对象,而并不及于同条第4 款所称之非常规工资(一时金),〔97〕包括临时支给的工资,支付周期超过三个月的工资以及非以流通货币形式支付的工资。因此非法解雇期间内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的额度包括(扣减后的)基本工资与非常规工资。而《劳动基准法》第26 条又规定,“因可归责于雇佣人的原因而停业的,雇佣人应向劳动者支付停业期间内60%以上的基本工资”,本条亦被类推适用于一般非法解雇的场合,其结果就是能够扣减的额度仅限于基本工资的40%及以下的部分。〔98〕荒木尚志『労働法』(有斐閣,2020 年)342 頁参照。需要注意的是,通说认为这里的可归责于雇用人中的可归责性,比民法上根据故意、过失判断有责性的范围更广,民法上认为不可归责于雇用人的事由在《劳动基准法》第26 条之下也可能被认为具有可归责性,例如经营策略失当、因母公司经营困难而难以取得生产资料,等等。河合塁「コロナ禍での休業と補償·賃金に関する一考察」季刊労働法271 号(2020 年)18 頁参照。那么如果从受雇于他处获得的收入超过了基本工资的40%应当如何处理呢?日本最高法院的做法是继续扣减上述非常规工资,且对非常规工资的扣减并无比例限制,可扣减至零。〔99〕野川忍「労働判例研究 第1067 回(1147)解雇無効の場合の解雇期間中の賃金支払における中間利益の控除の基準--社会福祉法人いずみ福祉会事件--最三小判平成18.3.28」ジュリスト1329 号(2007 年)120 頁参照。要言之,一方面保障最低限度的基本工资,另一方面当中间收入过高时继续扣减非常规工资,从而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保护之间取得某种平衡。又如意大利法,对出于不当目的的无效解雇以及口头作出的解雇,应当赔偿劳动者自解雇之日至复职的工资损失,即使事实上从他处取得的劳动收入应予扣减,也至少应赔偿5 个月的工资。〔100〕大内伸哉「イタリヤの新たな解雇法制」季刊労働法239 号(2012 年)242-243 頁参照。
我国制定法上并无类似标准,而司法实践常常适用最低工资标准或者职工平均工资标准支持解雇期间内的工资债权,这是否意味着可将该最低或者平均标准理解为一种扣减中间收入之后的底线,从而在教义学上证立司法实践的做法?我国台湾地区因无与日本《劳动基准法》第26 条类似的最低额度限制,也有学者提出或可以我国台湾地区“劳动基准法”第21 条的“基本工资”〔101〕第21 条规定“工资由劳雇双方议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资。前项基本工资,由中央主管机关设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拟订後,报请行政院核定之。前项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之组织及其审议程序等事项,由中央主管机关另以办法定之。”(即大陆地区所称之最低工资)为限。〔102〕参见侯岳宏:《日本非法解雇期间工资与中间收入扣除之发展与启示》,载《政大法学评论》2012 年第128 期,第392-395 页。本文以为不然。一则此两种标准仍然过低,难以形成对劳动者的有效保护,二则欠缺类推适用的规范依据。更稳妥的方案毋宁是参酌《劳动合同法》第85 条第1 项的规则——当用人单位拖欠支付工资时,可要求用人单位加付50%~100%的工资,则或可以此50%的标准作为扣减工资收入的底线。其逻辑在于,工资的迟延履行中,用人单位只受领了“一份”劳务,却至少需支付1.5 份(1+1×0.5)的工资,换言之其中0.5 份的工资没有对应的劳务给付。而在非法解雇中,毫无疑问也存在工资的迟延给付,因用人单位自身的原因受领了0 份劳务,则令其支付0.5 份无对应劳务给付的工资,应当是可接受的方案。
五、结论
违法解雇使得劳动合同陷于履行不能,劳动者原则上不丧失作为对待给付的工资债权;《劳动合同法》第48 条规定的继续履行救济,其所指也正包括劳动者在未发生解雇时本可获得的收入。而我国司法实践常见的做法是以某种最低或者平均标准支持工资债权,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扣减劳动者本人工资债权的效果,但这样的路径欠缺规范依据,有违法之嫌。但全额支持该工资债权又有悖一般的直觉正义,法院常常举示“劳动者实际上未提供劳动”的理由,其意正在于此。限制解雇期间内工资债权的有效手段应当是《民法典》第591 条的减损规则,劳动者事实上从其他用人单位取得的收入,或者可以取得而恶意不取得的假想收入,应当在工资债权中扣减。《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征求意见稿)》第64 条使这一结论变得更加不容置疑。这样的扣减不应全无限制,否则无法达到遏制违法解雇的目的。可类推适用《劳动合同法》第85 条第1 项拖欠工资的规则,以劳动者本人工资的50%作为中间收入扣除之后的底线。从而在劳动者保护、遏制非法解雇以及勿使劳动者获得不正当利益之间取得一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