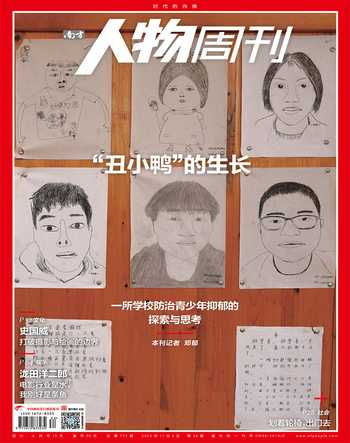逃不掉的,侯孝贤说

如果说“法国电影新浪潮”出了戈达尔和特吕弗这两个大人物,台湾新电影也有双雄,一个是植根本土的侯孝贤,另一个是从美国回来的程序员杨德昌。杨德昌带着西方视角,善于捕捉都市感觉,拍片子更类型化。当时台湾的都市感,属于一个乡土和城市的中间地带,独特的味道在他的镜头里非常有标志性。至今在他们的电影里,仍然可以看到很多社会面相。往大里说,如果不是杨德昌过早离世,“台湾新电影”会是另一种格局。
台湾新电影,以1982年拼盘电影《光阴的故事》在台湾全省联映为序幕,联合导演中就包括在美国学习工作、后来回台湾拍电影的杨德昌。
当时已经拍过三部票房很好的爱情片的导演侯孝贤,是第二年加入的,他和另外两位导演拍了又一部拼盘电影《儿子的大玩偶》——这时的侯孝贤,明显还没找到自己。
一个电影人“见自己”,说具体一些,就是电影拍出来,就能体现出他对事对人持什么态度,骗不了人的。
侯孝贤的风格,最早出现在了1983年《风柜来的人》里。一种非常现代的情感状态,类似惆怅、疏离,在远远的观看中十分明显。几个迷惘的青年人的生活,被固定机位和长镜头,远远地观察着。镜头一下有了态度,有点儿推开观众,让大家冷静下来的意思。

以前的台湾电影不是这样的。20世纪70年代初,台湾是武打片和琼瑶式言情片的天下;70年代末冒出过很多色情或暴力影片,商业不是商业,乡土不是乡土;到80年代,一代台湾年轻人,同时面对中国传统精神和西方现代文化的拉扯,在生活中随风摇摆。
侯孝贤曾在访谈里说:“一个导演只能拍一部电影,关注的方法可以变化,但是角度就是那一个……杨德昌离开台湾去美国那么多年又回来,他的记忆跟他对当下看法的对比。我是台湾南部乡下长大的,我看的是古典的书,自然的成长和生活就是我的眼光……”
现代的概念,在侯孝贤那里表现为杂糅而丰富,东方形式,东方思考,核心的观点又连接西方。当时他还有同龄的几个导演都在探讨这件事,引来了一片赞扬。
在台湾新电影最好的年代,电影平均年产可以达到120部左右,“这场经由新生代电影工作者,以及电影导演激发起的电影改革运动在80年代短短几年之间经历了兴衰成败,也成为台湾电影至今难以企及的高峰,为台湾电影在世界电影史上占得一席之地。”这是我从不少资料里看来的对台湾新电影的一个概括说法。
1987年1月24日,《台湾电影宣言》发表,此时新电影高峰已过,大家开始挣扎。这份宣言分“我们对电影的看法”、“我们对环境的忧虑”、“我们期待的改变与我们自己的决心”三部分。我特意去看了当年这些年轻电影人的忧虑和怀疑,他们提出:我们相信电影有很多可能的作为,我们要争取商业电影以外“另一种电影”存在的空间。
至此,新电影作为一股潮流匆匆消散,此后,大家的创作不得不跟着市场和个人命运转向,比如很多电影人不着眼于台湾本土的现实,不从本土寻找资金(侯孝贤也是这样),这么做好处是可以不受台湾某些政策的影响,坏处是有远离现实、沉溺回忆之嫌。
其实,侯孝贤不算是我的电影启蒙者。2015年,我终于在大陆大银幕上看了侯孝贤的电影——《刺客聂隐娘》。

我看过电影后写下了一段话:
“《刺客聂隐娘》不讲聂隐娘如何成为刺客,而讲她如何没有成为刺客。首先,镜头定氛围。很多导演对着一群说话的人拍照时,侯孝贤关注着站在角落里的人,他在镜头之后,没牵着我们看什么,而是随着镜头的移动,一同去感觉里面藏着的东西,在说话人的附近始终徘徊着一双眼睛。”
近日,导演罹患阿尔兹海默症的消息传出来,家人证实他已经完全回归家庭生活安心休养。其实,侯导患失智症的事在圈子里已经传好几年了。我认为说一个他这样的导演“退休”挺无趣的。
阿城在文章里写过一个场面,说是原本《戏梦人生》里头有一场剪辫子的重头戏,需要一下剪掉一百多条辫子,一镜下来,只能拍一次。拍摄时,大家都很紧张。结果拍到辫子刚一剪断,现场一个女记者的相机闪了一下。大家立刻看向小女生,谁也不敢说话,小女生吓哭了。侯孝贤却什么也没说。“反正白拍了,也不可能再拍就对了。”这段转述来自跟了侯导多年的摄影师姚宏易,其实这挺反映侯孝贤对电影的态度的。
近几年,侯孝贤新片《寻找河神》不时传来消息,但我觉得,可能看不到了。看不到,也无所谓了。他最爱对拍电影的年轻人说:“你什么样的人拍什么东西,这是逃不掉的!”在他的某部电影里,年轻的他,不管不顾地,在违禁情况下拍到了一群年轻人骑摩托,从中正纪念堂前飞驰而过,并远远地把他落在身后。
多年以后,重温这些鲜活、带着几分快意的电影场面,我会产生一种旁人难以理解的感激。已经有那么多侯导的作品可以反复看,还不够吗?恰巧这最后一部电影有个意味深长的命名——“河神”可能就是指他自己。所以,有人揣测这部电影也许可以让他多年培养的后辈代劳……这就是太不清楚侯孝贤是什么样的人了。
从1983年《风柜来的人》开始,侯孝贤在他那条路上,越走越孤绝,直到2015年《刺客聂隐娘》在戛纳电影节拿奖。
电影路上,这样的人几乎绝迹了。这样的人什么样呢?
就是明明可以融入,明明有机会紧随新时代,明明可以煽动年轻人……他都没有。我在这里想到特吕弗的一段话:“如果我的电影与我所处的时代相矛盾,就像我有时会受到指责那样,那或许是因为我同情那些必须努力进入一个自己被排斥在外的世界的人。”
摸不清头脑的年轻电影人,迟早会回过神来。侯孝贤的存在,意味着一种“生态”,电影的世界,至少还留有一道缝隙,这比无数具体的电影重要得多。泡沫越大,越会破掉;希望再微弱,也是希望。也许是我悲观了,不过有的时候乐观都是骗人的。
哪怕他的朋友杨德昌在世,哪怕新电影仍然轰轰烈烈,哪怕艺术片终于打开了自己的一片市场,侯孝贤也可能说出:“一个人,没有同类。”他早看清,所有真正的艺术家,走到最后,身边就不可能有任何人了——那时,他也就变成了“所有人”,所谓“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这是逃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