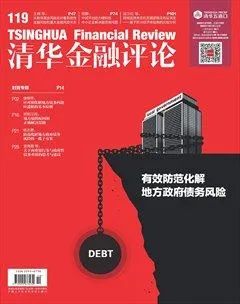经济不稳定、拯救经济副作用与宏观政策治理:全球视角
宏观政策虽有正效应,但也存在负效应,需要付出成本和代价。虽然各界普遍认为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至关重要,但究竟如何实现最优宏观政策组合却并未有比较确切的答案。政策试错、反复调整以及预期不稳定的风险增加,既可能动摇市场主体信心,也可能引发新的经济和金融不稳定。
引言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宏观政策逻辑存在趋同性,但鉴于经济周期、产业周期和市场结构有很大差异,宏观政策的互相模仿和简单套用不但会造成政策扭曲和经济周期错位,而且可能掩盖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制约经济中长期增长。如果仅依靠扩大债务维系经济增长,不但不可持续,而且潜藏巨大危机。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还是金融不稳定假说,这些理论仅是理论模型的某个领域,一旦形成宏观政策,必然需要经过实践检验,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反思宏观政策的目标以及政策组合的有效性、局限性和副作用或比政策本身更为要紧。
从两个层面来看:其一,宏观政策大起大落,破坏经济稳定性。虽然全球经济在经历新冠危机、地缘政治等多重冲击而出现短暂衰退后很快复苏,主要经济体复苏增长韧劲较强,但这一复苏仍主要依靠大规模财政刺激和量化宽松政策,这就决定了债务或货币驱动的经济复苏增长将很难持久,仅是权宜之计和相机抉择的结果。一方面是超大规模刺激政策对经济结构带来的伤害将逐渐显现,主要表现在具有黏性的高通胀、迅速上升的高利率以及不断累积的高债务,另一方面是刺激政策“易上难下”,导致经济复苏的脆弱性上升、不稳定性增加,存在资产负债表加速衰退的潜在风险。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经历经济泡沫后所推行的多轮刺激政策即是写照,突出表现为刺激政策无法退出,经济增长依然处于长期停滞,过高的政府债务仅能勉强维持经济运转,很难抵御外部金融危机或地缘政治危机的冲击。国际金融协会数据显示,日本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从1997年的93.26%上升至2022年的239.87%,增幅超过1.5倍,同期成熟市场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仅为116.45%。显然,不加节制的刺激政策贻害无穷,增加1bI3qKYue1cG85afulCZqQ==了下一步阶段宏观政策治理的难度。
其二,金融体系对刺激政策严重依赖,货币政策本末倒置。从全球范围来看,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存量债务占GDP的比重大幅提高,新增债务持续增长,大型经济体的债务赤字仍在扩张,财政刺激政策很难退出,同时财政赤字货币化又导致货币政策正常化严重受阻,反映在欧美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居高不下,仍很难“缩表”,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对流动性需求不降反增,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下降,一旦退出可能引发流动性危机。以货币管理经济,中央银行的“最终贷款人”的角色无限放大。统计显示,2002年12月—2022年6月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日本银行的总资产规模分别增长约10.3倍、7.8倍、4.9倍。但是,同期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经济实际同比的平均增长率却分别仅为2.0%、1.1%、0.6%。可见,以货币驱动经济增长的效能在不断减弱,即便有效也比较短暂,政策一旦退出便导致经济增速很快回落,愈发凸显传统宏观政策“治标不治本”的顽疾。
阻止经济衰退导致的金融不稳定
1929—1933年美国“大萧条”后,凯恩斯主义开始盛行,“罗斯福新政”更将其声望提升到新的高度,自此以后大规模投资成为刺激经济的主要手段。1975年的深度衰退很大程度上便是依靠投资拉动而引发的衰退。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认为,这种以凯恩斯名义为指导的政策寻求鼓励投资以扩大总需求的做法是错误的,不但引起金融不稳定性和通货膨胀,甚至加大不平等,强调要关注就业和消费政策,而不是简单地依靠投资。现实境况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国无一不是通过大规模刺激政策来阻止经济深度衰退,但最终因长期的低利率乃至负利率政策驱使金融投机和资本泡沫扩散,加剧“脱实向虚”,印证了明斯基的假说。世界银行统计显示,经合组织成员国(OECD)广义货币占GDP的比重从1960年的54.54%迅速上升至1989年的100.24%,2021年这一比值达到137.71%。2020年新冠危机时期,史无前例的刺激政策(巨额财政支出+超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供给)更是将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推向新的高度。到了20世纪70年代,传统的简单的凯恩斯模型不再适用。随着经济周期变化,经济结构嵌入更加复杂的金融系统,具体体现在政府支出、企业投资和家庭部门的储蓄与金融系统的关系不断深化。明斯基认为,面对深度衰退,最终贷款人必须迅速采取干预措施,并确保能够获得再融资来防止金融困难演变成一场能够引致“大萧条”的相互作用且不断累积的衰退。然而,这些干预导致通胀的爆发却引发金融不稳定。虽然说本阶段美联储通过果断的量化宽松暂时拯救经济,而且补偿式的激进加息反映在通胀数据也在逐渐下行,似乎财政赤字和货币宽松政策组合非常奏效,但遗留的诸多问题(巨额赤字、过量的货币以及高利率、高债务)却可能是成为引发下一场危机的重要诱因。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1970—2008年高收入国家私人部门信贷占GDP的比重从51.27%上升至95.09%。反观中等收入国家,1970—2022年私人部门信贷占GDP的比重从20.72%上升至130.28%。随着利率普遍上升且可能短期难以回落,私人部门偿债付息压力将剧增,如果出现经济再度下行或衰退,有可能激化资产负债表期限错配的风险,从而引发金融不稳定度的风险。
明斯基在考察1974—1975年和1981—1982年的经济衰退周期后,提出“大政府”和最终贷款人所发挥的作用。1970年代深度衰退后, “大政府”的救市行动在大幅抬升财政赤字的同时,使得众多企业能持续支付利息,转移支付提高后个人收入也并未在萧条期下降,反而消费也没有垮掉,“大政府”稳定了就业和收入,以及现金流(利润)。同时,政府的紧急救助计划将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从而阻止了存贷款危机,防止因经济衰退以及可能发生的债务紧缩。但是,无论是“大政府”还是最后贷款人的紧急救助计划,短期内的确阻止了经济深度衰退演变更严重的经济危机。明斯基在分析了这两次深度衰退后美国政府的抗通胀政策后认为,遏制通胀的手段——传统的紧缩货币政策,不但导致利率上升,并致使金融动荡(金融混乱)、失业率上升以及产出下降。比较而言,1970年代的救市政策与当前的宏观政策几乎如出一辙,值得深思。虽然“大政府”的模式在危机时期能够起到支撑作用,但却极易造成市场扭曲,主要表现在过度政策干预和指令计划,反而破坏市场的正常功能。
应对金融不稳定的“明斯基经验”
回顾1929—1933年美国“大萧条”至今的屡次重大经济金融危机,凯恩斯的理论在持续演进的同时,其负面效应也在加快显现。明斯基所称的“大政府”和最终贷款人的角色功能虽然短期内能够阻止经济深度衰退,从而防止出现“大萧条”,但与此同时,这些干预措施引发了新的不稳定。如果按照当前的实际情况,政府的支出增加和货币供应的增加造成政府赤字抬升,并引发通货膨胀,这一现象印证了明斯基所讨论的后凯恩斯主义的正反两面性。虽然凯恩斯的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政策指导意义,但这些政策同样也引发了更加恶化的经济状况,从不稳定到稳定,再到不稳定的发展过程中,政策的边界逐渐模糊,政策的规模也在持续扩容,但效率却在下降,而且副作用越来越大。不难发现,由于现代经济的“过度金融化”问题日益严重,金融风险的扩散随时会放大实体经济的风险,侵蚀投资和消费的实体经济根基,金融不稳定已经成为影响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20世纪80年代日本银行破产倒闭潮、2008年美国银行危机以及2023年欧美银行局部危机,从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过激的宏观政策对金融稳定性的威胁在日渐加深。明斯基从两个层面分析了金融不稳定发生的原因。一是投融资内部的不稳定性。内部融资比重的增加和银行短期融资行为,在有利的投资环境持续一段时间后,投资的融资成本将增加,融资的供给弹性可能变得缺乏,短期利率将很快提升,期限长的资产价格随之上涨,将引发投融资不稳定。明斯基认为,只要金融市场属于投资决定机制的一部分,都会存在某些强大的内部不稳定力量;二是银行业资产组合的不稳定性。以货币为债务的银行放贷行为主要基于债务融资业务来充实资本金,银行业作为富于创新的逐利行业,在不确定环境下,这种行为必然会增大不均衡的压力,从而导致金融不稳定。对此,明斯基提出两个思路:一是对银行杠杆率设置一定限制,将银行所有者权益的增长控制在与无通胀的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水平;二是指引和控制金融创新活动,并通过对不同类别的资产设定不同的权益权重率来保证银行保持一定的资本充足率。如今看来,过度的金融创新仅仅表现为虚拟资产的繁荣,却并未解决实质性的经济增长问题,反而这些货币和流动性成为助长资产泡沫的推手,而不是服务实体经济。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各国高度依赖财政扩张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但使用频率更高,而且规模越来越大。经验证明,这些宏观政策短期内挽救了经济衰退,但不断累积的财政赤字和规模巨大的量化宽松却逐渐显现出弊端。一方面,扩张政策的负面溢出效应增强,从局部扩展到经济金融各个领域,从金融体系拓展到实体经济,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债务规模均在持续扩大,杠杆率快速攀升;另一方面,宏观政策日益受到金融稳定性的影响,虽然通过注入流动性避免了金融风险的扩散,却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治理和监管的弊病,进一步扭曲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导致货币政策发挥的效能在不断下降。明斯基曾在1974年提出,我们所处的经济特征就是金融体系在稳固和脆弱之间摇摆,这一摇摆过程是产生经济周期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世界银行统计显示,1960—2021年高收入国家广义货币占GDP的比重从55.57%上升至143.73%;反观中等收入国家广义货币占GDP的比值更高,从1960年的15.81%上升至2022年的159.37%。目前而言,应对危机既要考虑政策的短期效果,更要评估负面效应和外溢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关键还在于防止过度金融化,促进实体经济增长。
“有为+有效”的宏观政策治理
如今,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近乎成为常态,金融不稳定所面临的潜在风险挑战愈发突出。是否存在所谓的“明斯基时刻” ——“债务积累之后发生的资产价格急剧下跌,流动性紧缩将变得普遍”?对此,观察2020年后的全球经济金融状况,可以发现金融不稳定出现的两大趋势:其一,局部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在上升,中小银行的流动性危机或潜在危机存在扩散的可能。2023年以来欧美国家陆续出现的局部银行危机部分暴露了金融不稳定风险;其二,通胀的黏性增强,欧美国家不但为此前的大规模干预付出巨大代价,而且连续大规模激进加息的溢出风险也在扩大。虽然说欧美经济暂未出现快速下行,局部金融风险暂时解除,但并不意味着经济和金融不稳定的问题已经完全解决,而且经济复苏动能在逐渐减弱。可见,如果不对宏观政策加以治理,将可能出现明斯基所提出的论断——“资本主义金融所固有的不平衡趋势将再次把金融体系推向脆弱的边缘”。统计显示,截至2022年12月,新兴市场非金融企业和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分别达到102.31%、46.07%,较2000年的增幅分别达到60%、205.5%。目前还难言是否存在明斯基时刻,但历次危机的发生从来都是猝不及防。
笔者认为,面对内外不确定性和预期不稳等现实问题,坚持“以我为主”的政策导向,短期内仍需要抓紧推出一揽子政策,妥善应对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潜在结构性风险。一是要着重发挥财政收支的调节作用,通过优化财政政策的结构性工具和税收工具,平衡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的财政支出结构,短期内以企业和居民为主,尽快恢复市场主体和居民部门投资、消费信心,增强经济增长预期,分行业和区域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减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财务负担,改善财务状况,提供更具利率优惠、更加普惠的金融服务支持;二是要精准实施货币政策组合,延续对中小微企业的延期付息政策,促进企业扩大投资和提高产能,试点推进刚需型住房家庭存量房贷利率下调或优化利率转换,以此稳步提升刚需型群体的住房购买需求,通过发放补贴、所得税减免、增加失业保险等综合政策举措,帮助更多中低收入群体解决燃眉之急,逐步修复资产负债表,缓解居民部门短期债务压力,增加居民现金收入,尽快修复消费支出预期。
中长期来看,宏观政策治理有赖于通过富有成效的结构性改革稳步推进。一方面,以“宏观政策+结构性改革”的组合模式破解难题,重点在于有序推进各类隐性债务处置化解,平衡好中央财政赤字与地方新增债务的关系,保持经济潜在增速与地方债务增长的合理匹配;合理利用财政资源,适当发挥债务融资工具的积极作用,发挥好资本市场资产配置的特殊功能,扩大民生和公共福利支出的占比,同时要规范财经纪律,通过各种措施妥善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释放地方经济发展活力,稳定中小金融资产负债表,保持大中型金融机构稳健运行,增强金融稳定性。另一方面,回归经济增长本身,尊重市场经济规律,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和中长期规划,注重发挥市场在资产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促进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有机结合,激发要素市场体制机制改革释放的活力,推动经济增长回归到潜在增速的正常水平;因地制宜通过宏观政策组合挖掘、盘活存量资产(例如基础设施、住房以及其他大类资产等)的潜在价值,激发实体部门优质企业和优质资产的增长潜力,拓展估值空间,给资本市场注入新的优质资源,增强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从而为企业和居民部门创造更加稳健的投资回报。
结语与展望
回顾过去30多年来全球经济增长轨迹,宏观政策调整对经济稳定性的影响越来越大。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主要经济体无不依赖财政扩张与货币宽松的刺激政策。越依靠货币大规模供应,经济增速反而在不断下降,可见货币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明显减弱,表明宽松货币政策并非万能。同时,发达经济体严重依赖财政刺激,致使政府债务也随之膨胀。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发达经济体一般政府净债务占GDP的比重从1991年的35%左右上升至2008年的50.3%,这一数值从2009年的60%左右迅速上升至2021年的81.7%。
观察近几年中等收入国家的居民储蓄增速情况可以发现,虽然中等收入国家的居民储蓄占GNI的比重仍保持稳定增长(从1996年的25%上升至2021年的36%),但国民净储蓄占GNI的比重却在2008年到达高点后也在下行。虽然从资产配置的角度可以解释一部分原因,例如中等收入国家的居民配置权益市场的比例上升,但主要原因仍在于居民信贷规模的不断增长。从宏观政策治理来看,按照发达经济体这套模式,不但酝酿巨大风险,而且导致经济增长陷入困境的概率大幅上升。因此,宏观政策应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综合考虑宏观政策与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周期和经济产业结构相匹配、相适应,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
(邓宇为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实习编辑/周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