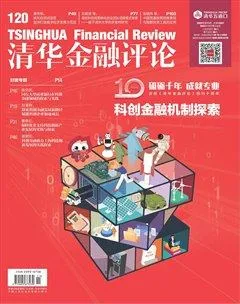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化解之路
本文从隐性显化角度,时间、空间角度,资金供求角度,城投转型角度,央地关系角度,探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化解之路。本文指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化解,关键是把握好“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资产与负债”“时间与空间”“输血与造血”“增速与质量”“扩张与收缩”“无限与有限”等几组关系。
追根溯源: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缘起
若要从根本上厘清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的逻辑,还要从央地财税关系讲起。1994年推行的分税制改革,缓解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财政收入下降的趋势,增强了中央统筹分配与宏观调控的能力,但也客观上导致了中央、地方的财权、事权不对等,除国防、外交等领域由中央统一管理之外,地方政府尤其是市、县两级政府承担了基础建设、医疗教育、公共治安等几乎所有与基层民生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与行政职能,但在资金控制权、支配权与话语权上相对缺失。根据财政部公布的《关于202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中仅有53%左右源于自身财源(本级收入),47%左右依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
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收获期,也是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一方面,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生机勃勃、热火朝天,城镇人口不断新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09ecd6f9489140d07943c8d54ee73955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5.22%,城市数量达687个,全国城镇人口已达9.2亿人(为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3倍);而另一方面,城镇建设需要地方政府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在分税制体系下,市、县地方政府申请上级资金拨款,资金使用的时效性、灵活度受到限制,资金体量也远远未能满足各地实际需要。同时,根据周黎安等学者提出的“晋升锦标赛”和“经济指挥棒”等理论,地方政府官员在晋升与考核压力下,面临着资金分配博弈,需要向上级政府“跑资金”“争资金”,需要奔忙于省级政府与各大部委之间,地方政府资金申请与使用效率不免进一步降低。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复杂背景中诞生的,实际上是地方政府以市场化手段解决经济建设资金来源问题的自谋生路、自主发展之举。20世纪90年代初,以上海城投、天津城投为代表的首批试点城投公司成立,开启了“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城投模式探索之路。2008年,我国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推出了“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和原银监会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鼓励地方政府设立融资平台公司。地方政府纷纷响应,设立城投公司承接财政刺激资金。城投融资规模迅速提升,城投融资成为地方政府重要资金来源,缓解了地方经济建设的燃眉之急。
地方政府以城投为代表的融资模式的蓬勃发展,本是顺应中国城镇化发展时代语境,符合中国财政税制体系的选择,不可否认这一模式对于我国基础建设的历史贡献与功绩。但与此同时,部分地区偏离了城投设立的本意,把城投融资视为“印钞机”“提款机”,不考虑项目实际经济性和地方财政能力,为了经济数据好看而盲目“大干快上”搞工程建设,为满足银行贷款需求,直接将当地土地收益、财政收入作为担保,为城投融资进行背书,有些还在城投和城商行之间进行“左手倒右手”的金融游戏。“过度举债”“无效举债”“成瘾举债”,膨胀的融资泡沫构成了部分地区债务隐患的伏笔。
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下简称《意见》),对地方政府债务规范化提出要求。《意见》指出要“坚决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政府债务不得通过企业举借,企业债务不得推给政府偿还,切实做到谁借谁还、风险自担”。同年出台的新《预算法》也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举借的债务应当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只能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除前款规定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举借债务”,“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为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债务以任何方式提供担保”。
但是,地方政府举债的急刹车并不容易踩,部分地区的地方政府出于对融资的依赖惯性,仍继续在法定的政府债务限额之外违规举债,直接或承诺以财政资金偿还或违法提供担保,形成了不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体系的隐蔽性较高的“隐性债务”。隐性债务的定义最早源于布里克西(Hana Polackova Brixi)提出的财政风险矩阵,根据南京大学沈坤荣、施宇教授的研究,隐性债务具体表现形式可以分为城投等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违规融资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简称PPP)、超出规定范围的政府购买服务、名股实债承诺收益的政府投资基金、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地方国有企业负债、特定情况形成的隐性债务等。
在地产市场风光无限时,“土地财政”与“隐性举债”的模式可以循环延续下去,地方政府融资雪球得以不断滚动,隐性债务规模可以不断扩大。但近年地产市场走入低迷下行阶段;同时,受到疫情与全球经济环境的不利影响,地方政府税收财政收入紧张,一般债、专项债等显性债务和城投债、国企债等隐性债务的还本付息压力逐渐凸显。根据国盛证券测算,2022年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率已达到125%,突破了120%的国际警戒线,而我国城投有息债务已达到54.2万亿元,未来5年将迎来密集的到期偿还高峰。据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估计,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余额在30万亿到50万亿元。
潮水退去,泡沫破灭,方显本质。近年来贵州、云南等地频发的债务舆情热度颇高,尽管难免受媒体情绪渲染,但也让社会逐渐认识到,隐性债务由于存量巨大、难以摸底、难以管控,不仅加剧了单一地区的财政困难,还可能通过关联效应、溢出效应诱发区域性、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甚至对地方政府信用造成损害。
2018年8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明确要求地方政府要在未来5~10年内化解隐性债务。2023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严控新增债务”;2023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这直接表明了中央层面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关切态度与治理决心。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的化解,既迫在眉睫,又长路漫漫;既需要釜底抽薪,又需要抽丝剥茧。
釜底抽薪与抽丝剥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化解之路
对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不能只采取批判的态度,而要辩证地站在政策沿革的历史长河、问题产生的复杂脉络、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等角度来综合审视,寻求出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化解,短期关键在于“还债”,关键在于回答好“还不还、谁来还、还给谁、用什么还、什么时候还、以后怎么借”的问题,而长期则涉及财税体制改革。
举措一——隐性显化角度:厘清存量,阳光置换,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要解决隐性债务问题,为其“正名”(而非“洗白”)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需要“显化”,这里的“显化”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将现有隐性债务的情况一一摸排查清,包括还债期限的轻重缓急、项目用途的合理程度、现金流的健康状况等,要将真实的情况原原本本反映给决策层,让隐性债务不再隐形,给决策层留出响应时间与政策空间;其二,是通过用地方债置换隐性债,将隐性债“收编”,纳入财政预算统一管理的框架中,让隐性债重回阳光下,开正门堵偏门,由于政府直接承担的地方债(刚性兑付)往往利率更低,期限更长,置换可以相应地减轻地方政府偿息压力。
2015年至今,我国已经推行了连续三轮的隐性债置换,分别是2015—2018年的12.2万亿元(重点支持债务负担重、经济底子好的地区),2019年的1579亿元(辽贵蒙湘甘云六省,部分县市竞争性立项),2020—2022年的1.1万亿元(特殊再融资债券置换存量隐性债)。据《财新》周刊消息,我国拟推出第四轮特殊再融资债券,约1.5万亿元规模,对天津、贵州、云南、陕西、重庆等债务压力确实较大的12个省份进行精准帮扶。
值得注意的是,债务置换,本质是通过增加法定债务限额来帮助地方政府渡过还债难关,但并未真正消灭债务,反而会使得明面上的债务规模显著扩大,存在着再融资债券发行规模的“天花板”上限(据中信证券测算为2.58万亿元)。大水漫灌、过度使用将是饮鸩止渴、适得其反,必须因地制宜、精准施策,重点关注支持高风险建制市县化债。
举措二——时间、空间角度:债务重组、展期,借新还旧,应急流动性支持,以时间换空间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的底线,就是防止违约对地方政府信用带来无法弥补的冲击,因此,当务之急是思考如何平稳度过未来几年的偿债高峰期。一方面,通过债务重组、债务展期、借新还旧等方式,平滑债务兑付曲线,例如湖北交投、遵义道桥等典型案例;另一方面,可在国家层面或省级层面设置应急流动性金融工具、政府偿债备付金、金融风险保障基金等,为部分自身难以应对债务危机的地方政府提供流动性支持,以时间换空间。据相关消息,我国央行将设立应急流动性工具——特殊目的载体(Special Purpose Vehicle,简称SPV),将地方政府不良债务剥离、打包、证券化,向主要银行融资,这将产生“类量化宽松”的显著效果。
举措三——资金供求角度:银行体系须有所作为,金融机构须加强监管
政策性银行和国有大行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的“局内人”,也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稳定性力量,必须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化解之中有所作为,承担责任。对于政策性银行而言,需要对相应的高风险地区实施“一地一策”,推出类财政措施的化债帮扶手段;对于国有大行而言,须积极参与央行、地方政府等牵头的协商机制之中,以金融手段缓解金融问题,稳定市场信心与预期,减小地方政府合规新债发行阻力;对其他金融机构而言,要打破隐性债务尤其是非标债务一定会“兜底买单”的幻想,严禁违法违规增信,严肃监管问责机制。
举措四——城投转型角度:城投平台市场化转型,注入优质资产,增强自我造血能力
城投平台自身实现市场化转型,是长期来看解决地方政府违规融资问题的关键。一方面,城投平台需要“刮骨疗毒”,剥离非经营性融资功能,剥离无现金流的“僵尸债”“空壳债”,保持充分的自主权与独立性,审慎考虑项目的经济性,加强债务风控管理,自负盈亏,建立信息的透明化公示机制;另一方面,城投平台须增强自我造血能力,结合地方资源禀赋,通过政府资源整合、优质资产注入,获取持续现金流,同时深度参与城市的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分享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红利。例如,云南国资委将云南白药股份划转注入云投集团,为城投市场化转型奠定资产基础;山西省将山西路桥等省属重点国企整合组建为山西交控集团,以这一主体的经营性收入承担高速公路建设相关隐性债务;合肥城投以“高新产业孵化+科创基金投资”的模式获取了投资收益与产业园区运营收益。城投曾为我国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经济发展从“速度”转向“质量”的新语境下,也应把握机遇,涅槃重生。
举措五——央地关系角度:中央加杠杆,地方缩事权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究其本质,还是要回到本文最初提到的央地关系问题。要想根治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需要做到中央加杠杆,地方缩事权。
从杠杆率的视角而言,我国中央政府要主动适度加杠杆。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数据,2022年末我国中央政府的杠杆率约21%,地方政府杠杆率约32%,这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央政府杠杆率高于地方政府的现象相反,这主要是由“四万亿”财政刺激、隐性债务、影子银行等多重因素造成的。对于部分资源禀赋较差、人口持续净流出的市县,过高的杠杆使得资金无效空转,还加剧了地方金融风险。中央政府集中了最优质的资产,应把握好主动加杠杆的政策空间,从中央层面推动资产负债表适度扩张,实施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例如发行特别国债,为地产纾困、就业保障、医疗教育等关键领域提供资金。
从远期的体制改革与统筹管理的视角而言,要使得中央与地方在财权、事权上权责匹配、协调一致,须深化财政和税收体制改革,并通过更大比例的专项建设资金等手段保障地方政府资金使用的灵活性、及时性、自主性。同时,要完善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账簿,强化风控体系、预警机制与监管问责程序,落实对地方国有资产的整合盘活,在依法依规、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前提下,让渡部分国有资产经营权、收益权、所有权,积极探索股权基金、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简称REITs)、资产支持证券(Asset-Backed Security,简称ABS)等模式,引入社会资本。
从地方政府官员激励的视角而言,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考核要从“经济增速指挥棒”转为“经济质量指挥棒”,使地方政府官员树立正确政绩观,致力于地方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面临着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地方政府官员要从“扩张思维”“增长思维”转向“安全思维”“风险思维”,守好政府边界,不做“躺平政府”,也不做“无限责任政府”,在财政支出上更多聚焦民生领域,而非形式工程,要量入为出,以收定支,开源节流,创造长期性收入,削减非必要支出。同时,中央政府应该继续坚持“谁家的孩子谁抱”的态度,部分政策救济不等于全面硬性兜底,防止地方政府官员隐性举债的道德风险蔓延滋生。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化解之路,已有一定成果,但仍任重而道远,关键是把握好“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资产与负债”“时间与空间”“输血与造血”“增速与质量”“扩张与收缩”“无限与有限”等几组关系。相信我国能推出具有中国智慧、符合中国国情的化债方案,通过体制改革助力我国经济继续长期向好发展。
(周康林为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研究生,汪杰为北京智能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中政智信(北京)经济咨询有限公司外部专家。本文编辑/孙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