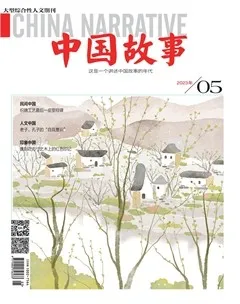《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在德语国家的译介与接受
摘要
中国古代经典故事《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在德语国家的译介历程已逾百年,对德语文学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奥地利德语作家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的诗体剧《白扇记》在该故事基础上改编而成。本文全面梳理了《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在德语国家的译介与接受,重点分析了《白扇记》对中国民间价值取向的本土化重构及“青年维也纳”思潮对霍夫曼斯塔尔改写风格的影响。
关键词
霍夫曼斯塔尔;《白扇记》;《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作者:唐洁,西安外国语大学欧洲学院。
田嘉璐,西安外国语大学欧洲学院。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故事’在世界文学中的征引阐释及启示研究”(20JZD046)
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是奥地利著名戏剧家、散文家、抒情诗人和短篇小说家,他于1897年9月创作了一部名为《白扇记》(Der weiße Fächer)的诗体剧。这部诗体剧讲述了一名年轻的寡妇与鳏夫堂兄互生爱意的故事。尽管“不忠的寡妇”这一母题在德语文学中已屡见不鲜,但在霍夫曼斯塔尔之前尚未有文学作品与“扇子”母题联系如此紧密,这与最早被翻译成德语的中国文学作品之一《今古奇观》中所载录的《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故事密切相关。有德国学者指出:霍夫曼斯塔尔的《白扇记》是中国文学影响下的产物。本文聚焦于《白扇记》对《庄子休鼓盆成大道》这一中国经典故事的接受,着力探析霍夫曼斯塔尔对中国民间价值的本土化重构及文学流派“青年维也纳”对霍夫曼斯塔尔改写风格的影响。
一.《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在德语国家的译介与接受
霍夫曼斯塔尔所著诗体剧《白扇记》情节改自中国经典故事《庄子休鼓盆成大道》。该故事可分为两个部分,即“庄周梦蝶”与“鼓盆而歌”,最早见于《庄子·齐物论》及《庄子·至乐》。及至宋元明清时期,通俗文学兴起,《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演绎出诸多不同的故事,如冯梦龙《警世通言》中的《庄子休鼓盆成大道》、谢国的《蝴蝶梦》以及据冯梦龙《警世通言》改编的《劈棺惊梦》等。目前已知最早外译的《庄子休鼓盆成大道》载于法国巴黎教士、汉学家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编著的《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de l'empire de Chine),其中文底本来自明代抱瓮老人编纂的《今古奇观》。本节将据此简要梳理《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在德语国家的译介与接受及霍夫曼斯塔尔本人对该故事的接受,力图探析《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在德语国家的传播与征引。
(一)《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在德语国家的译介与接受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的介绍最早出现在杜赫德在1735-1737年编纂的《中华帝国全志》中,其后《中华帝国全志》德译本(Ausführliche Beschreibung des chinesischen Reichs und der großen Tartarey)于1747-1749年在罗斯托克问世,是目前已知的《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最早的德语译本。1827年,由法国汉学家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主编的《中国小说集》(Contes chinois Edition intégrale)德译本在莱比锡出版,其中收录了《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之后格利泽巴赫(Eduard Griesebach)将《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从英译版转译为德语,命名为《中国的寡妇》,后于1873年随其论文《不忠的寡妇:一部中国小说及其在世界文学中的演变》(Die treulose Witwe, eine chinesische Novelle und ihre Wanderung durch die Weltliteratur)发表,除1873年初版外,还有1877年斯图加特版、1883年莱比锡版、1886年柏林版、1921年慕尼黑版及2017年诺德施泰特版等。1880年,格利泽巴赫编译《〈今古奇观〉:中国的〈一千零一夜〉中的古今小说》(Kin-ku-ki-kuan: neue und alte Novellen der chinesischen 1001 Nacht),收录了《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迈入20世纪后,鲁德尔斯贝格(Hans Rudelsberger)将《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收录至其编译的《译自原文的中国小说》(Chinesische Novellen / aus dem Urtext übertragen von H. Rudelsberger.)并于1914年在莱比锡出版,该书于1924年在维也纳再版。同年,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编译了《中国童话》(Chinesische Märchen),卷一收录了《庄子休鼓盆成大道》(Dschuang Dsï beim Tode seiner Frau)。1922年,瓦尔特·冯·施措达(Walter von Strozode)翻译并出版了《赵公主的黄柑子》,其中收录了《庄子休鼓盆成大道》。1946年,翻译家库恩(Franz Kuhn)重译了《庄子休鼓盆成大道》(Meister Tschuang tse, den irdenen Kübel als Trommel benutzend, übt hohe Magie),发表在慕尼黑版《各族人民的声音》,后于1979年收入《中国古代故事》(Altchinesische Novellen),1985年又收录于《中国小说》(Chinesische Novellen)。1953年,莱奥·格莱纳(Leo Greiner)与邹秉书合译《花魅:中国小说今古奇观》(Blumenzauber:Eine chinesische Novelle),由苏黎世迪瓦格出版社出版,分别于1979、2011年再版,其中重译《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纵观《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在德语国家百余年的传播历程,可以看出,《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的翻译推陈出新,其译介高潮集中于20世纪上半叶,且译者多为汉学家,其中以卫礼贤与库恩为最。但与19世纪相比,德语国家对《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的接受停留在翻译与阅读层面,再创与专题研究较少。总体而言,《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在德语国家的传播与征引呈现以下几种倾向:
首先,作为了解异域风土人情的中介物。抱瓮老人《今古奇观》中编纂的《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充斥着大量的中国元素,如道家思想、民间婚嫁观念、传统道德习俗等,生动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现实生活,同时也符合传教士想要将中国描述为理想的“礼仪之邦”的愿景,能够引起欧洲人对“中国”的想象及向往。
其次,作为道德教化与思想解放的指引物。《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反映了宋明理学的许多思想,如女子应当忠贞不二、为夫守节等,带有道德教化色彩。彼时的欧洲将中国作为改良社会、构筑理想“乌托邦”的参照系。选取《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有利于道德思想的传播与教化。
最后,作为宗教学说的阐释体。杜赫德编著的《中华帝国全志》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部带有论战性质的著作。当时正值欧洲“礼仪之争”等待罗马教廷裁决的重要时刻,杜赫德及其供稿人试图捍卫耶稣会士在“礼仪之争”中的观点,因此,其选译的文本带有突出的宗教色彩,力图证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彼此相容。而《庄子休鼓盆成大道》讲述了庄子如何斩断情缘、修得大道的故事,其中所囊括的庄子身死与庄子复活情节与基督教中耶稣受难故事不谋而合,这是促使杜赫德选译该篇的重要内因。
(二)霍夫曼斯塔尔对《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的接受
据相关学者考证,霍夫曼斯塔尔并非直接取材于《庄子休鼓盆成大道》,而是经由法国作家法郎士(Anatole France)的作品《白扇女郎的故事》(L'Histoire de la dame à l'éventail blanc)了解到《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并在之后将该故事置于西方文化价值背景下进行创作。但法郎士的《白扇女郎的故事》与《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有何出入呢?厘清这一问题,是TmNnOflEfc7yiuyMvUOtsA==分析霍夫曼斯塔尔在何种程度上对《庄子休鼓盆成大道》进行改写与重构的前提。
《白扇女郎的故事》主要讲述了年轻寡妇陆夫人与亡夫陶先生的学生互生爱意,但陆夫人不愿背弃自己在亡夫床前许下的誓言,因此手执白扇,想要扇干丈夫的坟前土以尽早改嫁的故事。法郎士在故事中为年轻寡妇增设了一名仆人,借仆人之口向庄子诉说事件缘由。与《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相比,法郎士将庄子置身事外,把故事焦点集中于年轻寡妇,重点描绘了年轻寡妇扇坟的起因经过。
据记载,霍夫曼斯塔尔早在1892年就在其写给玛丽·赫茨菲尔德(Marie Herzfeld)的信中提到了法郎士,此后,在1900至1902年间霍夫曼斯塔尔也多次在信中提到法郎士,并认为与法郎士会面是有趣的。而《白扇记》与《白扇女郎的故事》在主题、情节设置等方面既有相似性,也有迥异之处。
相似性首先体现在两部作品对青春的表述上。法郎士在其《白扇女郎的故事》中写道:“青春是短暂的,欲望的刺激为年轻男女装上翅膀。”霍夫曼斯塔尔的在《白扇记》中则写道:“青春总爱用宏大的词汇做搏斗的姿态,却又太过虚弱。”此外,两部作品对扇子的运用也一脉相承。法郎士写道:“她的灵魂似乎已完全进入到挥扇子的手。”《白扇记》中,霍夫曼斯塔尔也将扇子置于一种内心独白式的、戏剧性的场景中心。不仅如此,霍夫曼斯塔尔与法郎士对故事结局的处理也具有高度相似性。两个故事的主人公都没有像庄子一样看破情爱、修得大道,而是以宽容的微笑接纳了现实。法郎士笔下的陆女士在丈夫床前发誓永远忠贞,但在丈夫去世后却迫不及待地想要扇干他的坟前土。《白扇记》中的米兰达想要抵抗自己的梦境,最终的选择却同梦境如出一辙。二者都极具讽喻性。
两部作品的迥异之处则体现在故事的背景设置上。法郎士将故事背景设置在中国,保留了庄子的角色,为男女主人公起了中国名字,并在结尾处表示“这是给欧洲妇女提供的一个例子”。而霍夫曼斯塔尔将故事设置在意大利,故事背景中也未出现明显的中国元素。此外,法郎士的故事更加贴近《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着力刻画年轻寡妇的见异思迁。但霍夫曼斯塔尔并未在《白扇记》中刻意丑化女性。
综上,霍夫曼斯塔尔的诗体剧《白扇记》在法郎士《白扇女郎的故事》基础上改编而成。剧作保留了故事的主要情节,将背景设置在西方语境中,同时隐去了主人公庄子,将焦点集中于寡妇与鳏夫的“忠贞”行为上,体现了霍夫曼斯塔尔对《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中“土未干,不二嫁”的不同理解。
二.霍夫曼斯塔尔《白扇记》对中国民间价值观的本土化重构
霍夫曼斯塔尔的《白扇记》并非完全照搬《庄子休鼓盆成大道》,而仅吸纳该故事的主题及主要情节。在改写过程中,霍夫曼斯塔尔借助这一故事来解决其为自己设定的问题。本节将从《白扇记》中“白色扇子”这一意象与其所代表的忠贞观念及《白扇记》与《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中对女性角色的不同刻画来探讨霍夫曼斯塔尔对《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的本土化重构。
在《白扇记》中,“白扇”是全局的焦点,其颜色也隐含深意。中式语境下,白色作为哀悼的颜色存在。但霍夫曼斯塔尔并未将戏剧背景设置在中国。从文中出现的蜂鸟及文艺复兴诸多名词可以看出,该戏剧的背景应为意大利,因此,白色更像是婚礼的颜色。就此而言,《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中表示哀悼怜惜的重要饰物“素扇”所蕴含的中国民间价值在霍夫曼斯塔尔《白扇记》中已大不相同。此外,两部作品中扇子的状态也不尽相同。在《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中,庄子之妻为表忠贞不渝,将年轻寡妇赠与庄子的“素扇”撕毁,以此表达自己的志向,即“从一而终,誓无二志”。但在庄子身死之后,她见到前来拜访庄子的楚国王孙,立起怜爱之情,想要与他结为夫妻。反观《白扇记》中的米兰达,即使她在梦中误扇丈夫的坟,感到害怕与惊惶,但面对侍女递来的白扇,她仍选择接过,她认为:“不,我就是要拿上它。这样虚妄的梦一开始就得抵抗住,不然它们会增长太多力量。”扇子的不同状态代表了两位女主人公迥异的心境。田氏在《庄子休鼓盆成大道》语境中被描绘为一位忘恩负义、见异思迁的女子,而霍夫曼斯塔尔笔下的米兰达则是一位为丈夫守寡多年、压抑自己的内心、最终决定奔向新生活的女子。除此之外,两个故事中也出现了其他女性角色,但作者对女性角色的刻画大不相同。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中,一共出现了四位女性,分别是庄子的三任妻子和手执素扇的少妇。这四位女性的命运分别是:庄子第一任妻子因病去世;第二任妻子因过被休;第三任妻子即田氏,因见异思迁而羞愧自尽;以及新寡少妇手执素扇想要尽早改嫁。这四位女性在冯梦龙和抱瓮老人的笔下尽遭厄运。而两位作者对女性的消极刻画也表现出明朝封建思想对女性的压迫,故事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观念及女性应“三从四德”的贞洁观念表现得淋漓尽致。
反观霍夫曼斯塔尔《白扇记》中的四位女性:福图尼奥的祖母、米兰达及两位侍女,作者并未有意对女性进行丑化,这四位女性身上展露出的品质是守信、负责、坚贞、温柔与坚强。
首先,米兰达并非如田氏般轻易见异思迁。在见到福图尼奥之前,米兰达已独自守寡两年,并非如同《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中的少妇和庄子之妻田氏一般,仅在丈夫故去数十天内就要改换门庭。而米兰达在梦到自己“深夜扇坟”后,紧随而起的是羞愧之情。在梦中,米兰达看到丈夫的面庞从他坟墓的鲜花中一闪而过,因而用扇子扇开花朵,想要寻找丈夫的身影。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米兰达在此之前并未有任何改嫁的心思。
福图尼奥的祖母是一位精力旺盛的老太太。在与福图尼奥询问她到墓地的原因时,她表示:“在最近那株柏树下葬着你的父亲,我的儿子;再下⼀株柏树下是你的祖父,我的丈夫。还有⼀些坟墓,墓碑上的名字你念都几乎念不出来了,那里躺着我的各个友人。在这儿,让我挂念的坟,比你嘴中牙齿还多。”尽管她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兄弟和友人,但她仍然乐观,劝福图尼奥和他的朋友不要一直待在墓地,不要沉溺悲伤,要享受生活,热爱生命。这与福图尼奥的回答“这样的坟我只有一座,可这已经足够”形成鲜明对比。此外,霍夫曼斯塔尔借祖母之口表达了对女子的赞誉:“我看到过这个国家最上等人家的年轻女子将自己的清誉出卖给一个卑鄙小人,为了让自己的丈夫免上绞刑架,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不忍饥挨饿。”《白扇记》中另外两位女性,米兰达的两位女仆穆拉亭和卡塔丽娜也是衷心为主的好姑娘。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与《白扇记》对忠贞观念及女性角色的刻画完全不同。这与两部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明代中期,通俗文学兴盛,白话小说在文坛中占据重要地位。抱瓮老人以“三言二拍”为基础,选录其中精品数篇,经过加工润色后单独集结出版,即《今古奇观》。而《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故事发展至抱瓮老人时期,其哲理性不断弱化,宗教性及世俗性不断增强。作者将故事中心放在善恶伦理观念的阐释上而非哲思辨析。脱胎于《今古奇观》的《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中蕴含了中国民间价值观,如善恶观、贞洁观等。作者将更多的笔墨着力于刻画女性的“不忠”,并将这种“不忠”行为强化,使得女性在故事中作为“阻碍”男性“成大道”的力量存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小说既符合封建统治阶级推行的儒家道德标准,又满足大众的审美趣味,集中体现了明代中国民间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而在世纪之交的奥地利,对女性的道德教化并非作家们的写作重点。作家们将目光集中于“世纪末”,他们对现实感到失望,着力描写人的内心世界和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因此,霍夫曼斯塔尔在写作中将中国民间传统价值放置在西方语境中,将女主人公的孀居时间由七天延长至两年,把故事背景巧妙地穿插在对话中。不仅如此,霍夫曼斯塔尔在《白扇记》中设置了序幕与闭幕,并将变化不定的瞬息印象与空间印象设置其中,突出“自我”观念,将女性角色米兰达设置为其“自我”思想的承载体。此外,他还增设祖母与女仆三个女性角色,用以佐证其“自我”思想。
总体而言,《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中蕴含的这些“时代基因”在霍夫曼斯塔尔的改写与重构过程中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写作过程中,霍夫曼斯塔尔不仅褪去了《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的中国外壳,还将其中所蕴含的中国民间价值观念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将中国经典故事与德语文学相杂糅,在迥异的时代背景与价值观念下创造出了代表中西文化交流的经典剧作。
三.“青年维也纳”对霍夫曼斯塔尔改写风格的影响
中国经典故事《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激发了霍夫曼斯塔尔的创作灵感,但霍夫曼斯塔尔对该故事的改写风格则更多受到“青年维也纳”思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创作形式、创作主题及创作思想上。在创作过程中,作家将故事中的中国元素与本土风格相结合,将《庄子休鼓盆成大道》重塑为一部揭示理想与现实世界矛盾的诗体剧。
首先,在创作形式上,霍夫曼斯塔尔虽采用了戏剧形式,但其使用的表达则更偏向诗歌。据记载,霍夫曼斯塔尔对于《白扇记》作为戏剧进行演出并未抱有很大期望,因为霍夫曼斯塔尔认为,这部戏剧并未满足戏剧形式的诸多要求。因此,霍夫曼斯塔尔将戏剧形式作为抒发诗情的工具,《白扇记》也可视为霍夫曼斯塔尔创作的具有戏剧形式的抒情诗。这种形式受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青年维也纳”的影响。“青年维也纳”时期,多种风潮并行,这一时期的霍夫曼斯塔尔受到象征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影响,注重作品的形式,追求隐晦朦胧而扑朔迷离的情调意境,注重诗句的音乐性,欣赏纯粹的、脱离日常生活的文学。这就不难理解为何霍夫曼斯塔尔以诗体剧的形式讲述这个故事。
其次,在创作主题上,霍夫曼斯塔尔并未延续《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中强调的“为妇之道”与“忠贞观念”,而是从“忠诚”角度来阐释自己的思想,即关于“自我”的论断。世纪之交,德国哲学家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在其著作《感觉分析论》(Die Analyse Der Empfidungen)中提出,自我是时间流逝中不断变换的感觉思想等元素的合成物,是人所虚构的单元架构而非实在存在之物。这一论断给当时活跃的“青年维也纳”作家们带来深刻影响。赫尔曼·巴尔(Hermann Bahr)更以“不可拯救的自我”为题,论述“自我”只是一个为了让我们的观念有秩序而出现的一个辅助工具,它只是连接各种元素的一个名字。霍夫曼斯塔尔则认为“自我”分为忍受痛苦的自我与观看痛苦的自我,二者相互作用。这种思想在《白扇记》中也有所体现。
剧中,福图尼奥面对亡妻的早逝迟迟不能释怀。坟墓对于他而言就是一面黑暗而深邃的镜子,他认为一个人对损失的哀悼程度并不取决于一个人的年龄,而是取决于损失的程度。即使面对好友利维奥的安慰与祖母的劝告,他仍流连于墓地,任哀伤占领“自我”。在遇到儿时的表妹米兰达后,他发现二人境地相似,他希望米兰达改变她的生活。这部剧中,米兰达与福图尼奥二人可以构成一种非对称的镜像。二人的伴侣均早逝,且都沉浸在伴侣早逝的哀痛之中。不同的是,福图尼奥的自我觉醒于外部力量,通过与米兰达的相遇他想要奔向新生活,而米兰达的自我则在内心世界(梦)觉醒。米兰达的梦与现实构成了霍夫曼斯塔尔所认为的分裂的自我。梦中的米兰达代表观看痛苦的自我,它预示着米兰达的命运。现实的米兰达代表忍受痛苦的自我,它表示米兰达的主观决策力。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此外,在创作内容方面,霍夫曼斯塔尔在《白扇记》中加入大量似是而非、具有前瞻性的文字和内心独白,如福图尼奥中所述:“这生活不过就是一场影子戏:若只是让目光滑移而过,倒也聊以度日,但如果要牢牢抓住不放,它就会在你指尖碎裂消散”以及“因为执念倒是一真切存在之物”。这两句话不仅是福图尼奥对生活的感叹,还影射了后文福图尼奥与米兰达对早逝伴侣的执念。不仅如此,霍夫曼斯塔尔极力描写米兰达的梦境,这也离不开“青年维也纳”的影响。“青年维也纳”们厌恶现实,致力于表现人的内心世界和梦幻世界。而梦作为表现人的内心世界的一种创作元素,在霍夫曼斯塔尔的改写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一点具体表现在米兰达对“梦”的态度及其最终选择。
剧中,米兰达即使通过梦境知道了自己有另嫁他人的可能性,仍认为自己不会做出“扇坟”的举动,但最终还是如同梦中所现一般芳心另许。在对女仆穆拉亭诉说自己的梦时,穆拉亭对米兰达说:“但是我知道,这样的梦是怎么来的。”梦是内心的反应,此处,梦就是米兰达理想世界的投射。之后,霍夫曼斯塔尔又借女仆穆拉亭之口说:“深夜和安眠有何关系,青春与忠诚又有何相干?”闭幕时又写道:“可你们视为幸福的,你们正以之为生活的,便是如此⼀个绚丽的空无,由梦编织而成。”此处看似说明米兰达挣脱束缚、进入生命新阶段,实则反复提及“梦”,暗示女主人公米兰达在几经犹豫之后,仍踏上了由“梦”规定好的道路,这种着重强调也体现了霍夫曼斯塔尔听天由命的思想,说明自我不可拯救,命运不可打破,充斥着浓厚的“世纪末”意味。霍夫曼斯塔尔借此揭示了理想与现实世界的矛盾。作为《白扇记》故事发展的基石,米兰达的梦在霍夫曼斯塔尔笔下既具有预示作用,又含有反讽意味。
结语
霍夫曼斯塔尔的诗体剧《白扇记》虽取材于中国经典故事《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但并未完整保留这一故事,而是将故事中所蕴含的中国元素加以改造,对中国经典故事进行本土化价值重构。霍夫曼斯塔尔在“青年维也纳”思潮的影响下,从形式、主题、内容三个方面对《庄子休鼓盆成大道》进行改写,将中国本土的价值文化移栽到西方文化的土壤之上,使中国经典融入本土文学。霍夫曼斯塔尔《白扇记》对中国经典故事《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的改写与重构是中国经典融入世界文学的典型案例,对于研究世界文学视域下“中国故事”的传播转向与价值变异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1] (奥地利)胡戈·封·霍夫曼斯塔尔著.李双志.译风景中的少年:霍夫曼斯塔尔诗文选[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
[2] (明)抱瓮老人. 今古奇观[M].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
[3] 宋丽娟.《今古奇观》:最早译成西文的中国古典小说[J].明清小说研究,2009(2).
[4] 卫茂平.《今古奇观》在德国[J].寻根,2008(3).
[5] 卫茂平. 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6] France, Anatole. La Vie littéraire, 3: quatrième série (Vol. 4) [M]. Calmann-Lévy, 1892.
[7] Hofmannsthal, Hugo Von. Gesammelte Werke in zehn Einzelbänden. Reden und Aufsätze Ⅰ[M]. Frankfurt a. M.: Fischer Taschenbuch, 1979.
[8] Hofmannsthal, Hugo Von. Briefe, 1890-1901[M]. Berlin: S. Fischer Verlag, 1935.
[9] Lorenz, Dagmar. Wiener Moderne[M]. Stuttgart, Weimar: J.B. Metzler, 1995.
[10] Mayer, Mathias u. Werlitz, Julian (Hg.). Hofmannsthal-Handbuch. Leben – Werk – Wirkung. [M]. Stuttgart: J. B. Metzler Verlag, 2016.
[11] Ritter, Ellen. Die chinesische Quelle von Hofmannsthals Dramolett Der weiße Fächer[J].arcadia,1968,Vol.3: 299-305.
[12] Schuster, Ingrid. China und Japan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1890-1925[M]. Bern[u.a.]:Francke, 1977.
[13] Strohschneider-Kohrs, Ingrid. Poesie und Reflexion: Aufsätze zur Literatur[M]. Berlin, Boston: Max Niemeyer Verlag,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