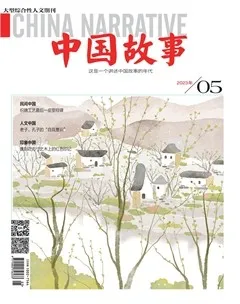中国民间故事“聚宝盆”在民主德国的变异与传播

摘要中国民间故事“聚宝盆”在20世纪初期由卫礼贤译入德国后,经不断改编变异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其中,尤其令人关注的是民主德国的三个德语改编本,它们在特定的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下被重新表述,并附着全新的价值规范,进而迸发出宏阔的无产阶级革命情怀与斗争精神,印证了中国故事的感召力、世界性和跨时代性。
关键词“聚宝盆”;中国故事;民主德国;故事变异;故事传播
作者:陈丽竹,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
牛金格,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故事’在世界文学中的征引阐释及启示研究”(20JZD046)的研究成果之一。
在灿烂的世界民族及民俗文化中,中国民间故事以其悠久的历史、庞大的讲述谱系和丰厚的文化土壤占据重要地位,并在数个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成为标定东方美学和文化体系的一个重要坐标。其中,包含“偶得宝物”和“行善”等情节要素的“聚宝盆”故事在20世纪初期传入德国后出现数个改编本,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其中,尤其令人关注的是民主德国的三个德语改编本,它们在特定的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下被重新表述,在原有的道德训诫之外衍生出具有社会主义文化特色的教育性质。本文将梳理“聚宝盆”故事在德国的传播路径,并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民主德国三个版本的变异特征及背后独特的讲述维度。
一、“聚宝盆”故事在德国的传播及不同版本
据学者考证,“聚宝盆”故事最早出现在宋代的吴淑《秘阁闲谈》和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中,情节相对简单,已初具“偶得宝物”“因之致富”的核心情节;到了明代,宝物名称被确定为“聚宝盆”,并以沈万三为固定主角;明代以后,聚宝盆故事的传播范围不断扩大,在中国各个地区出现变异版本,故事类型和情节更加丰富、曲折。近代以降,随着中西文化交流增多,中国的民间故事逐渐受到西方汉学家的重视。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从中国的《三国演义》《封神演义》《搜神记》《今古奇观》等多部典籍中选取100个故事进行翻译,并辑录在1914年出版的《中国民间童话》(Chinesische Volksmärchen)中,中国民间故事由此进入德国读者和学者视野。其中第五则《魔桶》(Das Zuberfaß)便是“聚宝盆”故事在德国的异文名称,全文剧情简单、行文凝练,共233词,剧情可概括为“偶得宝物——因之致富——宝物失灵”,卫礼贤译本被视为“聚宝盆”故事在德国的首次译介。1952年,《中国民间童话》更名为《中国童话》(Chinesische Märchen)再次出版并广受欢迎,仅20世纪50年代便再版4次;1985年,为“庆祝‘世界文学童话’丛书中最受欢迎的一卷发行量突破10万册”,出版社推出《中国童话》纪念版;进入21世纪后,本书再版9次,截至2018年已以实体书、电子书和有声书等形式再版共计逾20次,可见本书在德国读者群体中经久不衰的魅力。
1952年,穆勒(Karl Müller)择取“聚宝盆”在内的三则中国民间故事进行改写,并以《魔桶》为名在民主德国出版,这一版本基本保留了“偶得宝物——因之致富——宝物失灵”的核心情节要素。1955年,由里希特(Manfred Richter)创作的剧本《魔桶——一部基于中国主题改编的三幕六画剧》出版。该版本在原有的核心情节上融入爱情、阴谋和阶级斗争等元素,并对旧版本中的人物关系和人物形象进行了补足和拓宽。1957年,由舒尔茨(Herbert K. Schulz)导演的动画《魔桶》在民主德国的电视台播出,并在动画说明中标注“参考自中国童话”。1988年,民主德国广播剧作家戈策尔(Rolf Gozell)将“聚宝盆”故事改编为一部长约30分钟的同名广播剧,并在民主德国广播电台播放。除画外音(叙事者)外,全剧仅出现穷苦的农夫、妻子与祖父三个角色,重点突出了试验宝物的过程以及因宝致富后农夫堕落为贪婪凶恶之徒的经过。1989年,该剧获得民主德国儿童广播剧听众奖第一名(DDR-Kinderhörspielpreis)。
21世纪以降,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聚宝盆”故事的传播渠道也更加多元化。经考察,“聚宝盆”故事在视频平台上拥有至少五个德语版本。该故事的教育与警示意义使其非常适合儿童及青少年阅读,有学习网站将其设计为阅读材料,并针对故事来源与内容设置一系列问题,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儿童领会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好事这一道理。此外,“聚宝盆”故事还走进了德国中小学。2008年,职业故事家福格尔魏德(Eberhard Vogelwaid)在德国一所小学为学生表演童话故事,并以“聚宝盆”故事作为开场,深深吸引了当时在场学生的注意力。该故事还被改编为面向8-12岁孩子的圆圈游戏,可供儿童集体玩耍。
由此可见,由于卫礼贤的译介及后人的不断推陈出新,“聚宝盆”故事在德国的接受从未间断。老少咸宜的读者群体、丰富的传播载体和巨大的加工余地让它突破时空桎梏,以其对大众文化心理的迎合和教育意义走进德国千家万户,伴随无数德国儿童成长,成为中国故事在德国传播的成功范例。
二、民主德国三个改编版本的情节单元比较
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采取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将故事拆解为具体的事件序列,并从中分离出故事的构成性单元,这些基本单元以不同的顺序被编排择取,成为叙事的基本要件,他认为神话故事是一种“具有高度稳定的叙事核心以及高度变化的叙事边际的故事”。普罗普(Vladimir Propp)在大量收集和分析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得出相似的结论,认为它们“既是多样态的,丰富多彩;又是统一样态的,千篇一律”。在流传变异的过程中,“聚宝盆”故事的样貌逐渐发生变化,但各个版本都遵循最基本的剧情骨架。笔者从故事的结构形态入手,梳理民主德国三个改编文本的情节单元,以A(故事发生)、B(故事发展)、C(故事结束)进行归纳,通过相对封闭的提炼和归纳法得到如下表格:
就具体的剧情单元而言,对于故事发生(A),民主德国的三个版本均无明显修改,但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主角是“贫苦农民”。此外里希特版本还额外加入“精灵”这一元素,让精灵在登场时主动说明自己的能力,这一剧情设计既与德语译名“魔桶”相契合,同时在剧情上又补足了人物行动的逻辑:地主柴翁奸邪、狡诈而懦弱,被精灵吓得瑟瑟发抖、不敢直视,雇农毛特以智慧、勇敢的英雄形象出现,他通过与精灵对话揭开聚宝盆生物的秘密。在试验宝物(B1)方面,各版本与卫礼贤版相差无几;对于致富(B2)情节,其他改编本均为因宝致富,里希特版本则基本放弃这一剧情。即使已经获得聚宝盆,柴翁仍执意拆散雇农毛特与女儿莲花,欲将莲花高价卖给军阀。为突出阶级矛盾,里希特着意塑造了脸谱化色彩浓重的“恶”地主与“勇”雇农形象,从而将戏剧推向第三幕高潮。所有版本都将结尾安排为宝物失效(C),具体而言,卫礼贤版本简单地交代为桶破掉,穆勒版本则将桶的魔力限制为3次。这一改编被后来两个版本沿袭,但各有发展:里希特版本中,军阀带着士兵冲向柴翁的庄园,众雇农奋起反抗,随即在魔桶中被复制出的两个柴翁是魔法第三次显灵,被精灵吞噬(“能变三次,不能更多。其中两个,当属于你。而第三个,入我腹中!”),全剧在雇农们的胜利凯歌中落幕。里希特版本淡化了伦理教化色彩,转而将诉诸暴力的阶级斗争置于核心位置,使敬老、戒贪的普适性伦理正义从属于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正义。通篇观之,戏剧这一表现形式提出了与其他版本截然不同的要求,同时里希特版本强烈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亦使得它在众多版本中与众不同。戈策尔版本同样将能力次数限制为3次,但跌进聚宝盆的祖父并未死去,而是活了下来,农民良心发现,自此善待两位祖父。这一设置将原本的“恶有恶报”改写为皆大欢喜的“浪子回头”结局,淡化警诫意味,强化说教性质。
由上可见,“聚宝盆”故事从卫礼贤版本到民主德国的三个改编版本,由人物关系清晰、故事结构单一的简单序列演变为情节复杂的复合序列,分化出多样的情节线索。同时,它们在落地生根的过程中受到时代背景和精神风貌的影响,被不同程度地赋予社会主义文化印记,这不仅是对中国本土“聚宝盆”故事的全新突破,亦是民主德国借助中国故事进行自身意义建构的叙事尝试。
三、民主德国三个改编版本背后的时代表征
本节将在前文基础上进一步提取故事背后的文化因子,选取“偶得宝物”(A)和“宝物失效”(C)两个情节元素中的细节,剖析民主德国三个改编版本如何将这则远道而来的中国故事编织到自身的政治话语体系中,并最终服务于民主德国对自我和历史的解释框架,使“聚宝盆”故事在德国焕发全新的生命力。
(一)“偶得宝物”
民间故事往往取材于日常生活,又在日常生活中讲述,开篇往往直切主题,并不重视某一个具体故事中人物形象的个性化塑造,这导致人物原本的差异在故事发展过程中“成为职能相同的数种类型”,而类型化角色往往超越了“个体的差异”,譬如卫礼贤译本几乎放弃对人物的深描与心理刻画。但民主德国的三个版本则不同程度地打破了这一原则。针对“偶得宝物”,穆勒版本开篇即交代:“一位贫穷的中国农民在田间劳作,这块田地是他从村里最富有的农民那里租来的。”作者以此向德国读者表明中国传统封建制度下的人身依附关系和生产关系,并通过对动作和心理的描绘进一步刻画农民形象:“农民十分节俭,他小心翼翼地挖出圆桶”,回家后“农民正拿着小烟斗,在门前坐着,幸福地做着梦,从一整天的劳累繁忙中恢复”。一个节俭、勤劳、质朴又梦想美好生活的农民形象跃然纸上,丰富了卫礼贤版本中以“一个男人”一笔带过的主角形象。1988年的戈策尔版本与之相似,尽管广播剧并未留出太多余地进行人物描写,但剧本开篇便两次强调“贫穷的农夫”。这两个版本中的农民形象处于政治人格上的中间状态,他们既具备一定的阶级属性,同时又未完全超出民间故事的叙事模式。里希特版本中的角色则具有鲜明的阶级印记。戏剧伊始,说书人如此刻画地主柴翁(反角):“柴翁是个又懒又恶毒的东西。……他用大把的时间来思考通过怎样敲诈别人来养活懒惰的自己,甚至变得更加富有:当村子的穷人快饿死时,柴翁只肯借给他们大约四把大米、小麦或谷子。但当地里有收获时,这些穷人就必须从微薄的收成中拿出满满八把还给柴翁。通过这种手段他勒索到了两倍的粮食,赚得盆满钵满。”雇农毛特(主角)则是勤劳坚忍的正面形象:“勤劳的毛特心甘情愿地替柴翁耕地,因为他和莲花彼此相爱。他早出晚归地干活。”当阿常感叹工作辛苦时,毛特鼓励:“坚强的人从不抱怨。”里希特对主角和反角的塑造使正义与邪恶披上阶级的外衣,泾渭分明地展现双方的对立关系,为雇农反抗地主的斗争结局埋下线索。此外,里希特版本还穿插着对中国旧社会女性地位的描写。当柴翁的妻子试图说话的时候,柴翁“粗暴地将她推到地上”,厉声喝道:“你坐在这里干什么?这是一个集会,你不知道女人和集会无关吗?滚开!”相对的,雇农们对莲花的态度则截然相反:
“柴翁:你们听听,他想要打破我们的老规矩!我们的村子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从来没有女人能在集会上说话。
阿常:现在,我这样问你们,乡亲们:莲花是一只愚蠢的,只会吃草不会讲话和思考的山羊吗?
雇农们:他说得对!阿常很聪明!把莲花叫来!”
柴翁获得聚宝盆后,并没有立刻利用聚宝盆实现暴富,而是坚持把女儿莲花卖给军阀获得财富。这种出于“恶”的必要而展开的剧情虽并不符合行为逻辑,但正如施密特(Carl Schmitt)在谈到政治意义上的敌人时曾指出:政治敌人与朋友的区别提供了“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定性,而非详尽的定义或内容说明”。同样地,在服务于政治叙事的人物框架下,对敌友形象的描述放弃思辨性的探讨,转而遵从绝对的二元法则,因此对柴翁的行为进行合理性阐释的并非叙事逻辑而是政治伦理。作者利用这一剧情在固化阶级印象(正/邪)的同时,更进一步激化双方矛盾。若阶级印象服务于标准化的政治审美,提供读者熟悉的人物框架和情节发展,矛盾冲突则负责制造紧张、引起情绪,最终在成功反抗的大团圆结局中将压力一次性释放。这种“确认—不信任—确认”的一波三折剧情框架往往出现在追求情绪刺激的通俗文学中,里希特版本作为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改编剧本,在保留“聚宝盆”故事核心的同时,剧情上大幅度突破了原有内容和表现形式的束缚,用情绪化和个人化策略突出阶级矛盾以激发观众的激愤情绪,从而赋予本故事中的阶级斗争以合理性、必要性以及正义性。
(二)“宝物失效”
卫礼贤版本中,对于宝物失效简单地交代为“当他完成这一切(埋葬两个祖父)时,魔桶破了,他又和以前一样贫穷了”。后续的改编本不仅明确了宝物失效的方式(次数用尽),还在这一创新改编背后加入了全新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
在穆勒版本中,祖父跌倒并死在桶里,见到这一幕,农民清醒了过来,“他怎么能让贪婪迷惑了自己的神智,以至于忘记了爱和敬重!他悔恨不已,浑身发抖”。伴随主角意识到自己的过错,故事已经完成对不劳而获和目无尊长的批判。但穆勒的改编并未止步于此,当农民埋葬了所有的祖父并发现宝盆已经失去效力时,他终于认识到:“除非自己努力,世上没有任何魔法可以减轻穷人的苦难命运。只有当一个意愿将众多贫苦农民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拥有美好生活的梦想才能成真。”穆勒借农民之口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将劳动与“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观点结合在一起。这一思想意境契合了《国际歌》中“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的歌词,把民间故事与人民史观紧密结合起来,强调农民的阶级团结。总体而言,穆勒版本一方面利用民间故事发出号召斗争的政治豪情,对“聚宝盆”故事在思想境界和政治功能上进行全面的升华;但另一方面,主角的回顾与总结并没有相应剧情的铺垫,主题的神圣化缺乏感情的递进,因此,穆勒版本对于“所有农民团结起来共同奋斗”的号召并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
里希特版本中,要求冲突和矛盾的戏剧形式恰好弥补了前述不足。随着故事发展,地主柴翁与军阀达成协议,用女儿莲花换取一个肥差,“没有哪个父亲能像我一样爱他的孩子。只有得到税吏这个差事作为安慰,我才能把我的莲花从花园里摘下来。”随即,军阀带着士兵冲向柴翁的庄园。与此同时,众雇农齐心协力,把莲花从囚笼中救出,与屋外的士兵对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里希特版本借雇农之口首次表达了对聚宝盆的批判。在危急关头,莲花朝着聚宝盆绝望地哭诉:“你那巨大的力量不能帮助我们吗?漂亮的硬币现在又有什么用呢?”毛特却说:“想想吧,这是个充满污垢和肮脏不堪的桶,它让柴翁变得富有,却让我们变得贫穷!”在其他故事中,聚宝盆都被视为“宝物”,它迎合和代表了追求暴富的大众文化心理,遭到惩罚的往往是贪心不足的主角本人。但在里希特笔下,这个聚宝盆却如同潘多拉的盒子,“飞来横财”不仅不值得追捧,反而是危险的诱惑。这一批判使得“聚宝盆”故事的警示意义得以升华,从批判好吃懒做的行为上升到对不劳而获思想的抨击,颠覆了聚宝盆在此前故事中的功用,将它从宝物变为邪物,以自食其力的劳动观有力地驳斥了不劳而获的普遍心理。随即,军阀手下的士兵冲进屋内,毛特将自己作为诱饵,带着他们冲进关押莲花的囚牢中,再飞快地溜出,将牢门关上,所有的士兵都被关在铁笼中。这一战胜的逻辑体现了毛特的机智勇敢与临危不乱,塑造了一个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英雄,在他身上传递出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和追求自由与真爱的反抗精神;同时,依靠人民的智慧而非借助魔桶的法术击败军阀,与穆勒版本一道传递了“唯有自救”的革命理念。这一战胜逻辑唤醒了农民的斗争意识和自救意识,唤醒他们在政治上的感知力与组织力。里希特通过毛特这个普通农民启迪农民阶层,要实现真正的富裕和自由,必须自己站起来与旧社会和压迫者做坚决斗争。随即,柴翁前倨后恭,祈求雇农们的原谅,他慌不择路,躲进魔桶中,桶里出现两个柴翁。这已是第三次使用魔桶,精灵再次出现,高唱着“……第三个,入我腹中”,将其吞噬。柴翁作茧自缚,他的结局回归到“罪有应得”的一般伦理,同时也深刻讽刺了地主阶级贪得无厌的嘴脸。说书人在结局处再次出现,总结道:“……有一天,农民们的命运将彻底被颠覆。那汹涌的浪潮抹平所有农民经受的苦难。到了这一天,所53bd4ec59ef94839e21f96bb9831868617b019e5319217d271cfa7895a1e153e有人张开双臂拥抱自由——如同一个闪闪发光的黎明!”这段话喻指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征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它既是预言又像回忆,戏里戏外两个世界的错位映照让观众站在已被实现的当下,回看过去人们的未来展望,这是对曾经奋斗的正义性和合理性的再次确证,更是对革命取得胜利的庆祝、对当下社会的肯定。里希特将故事舞台设置在中国,增进了民主德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与同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将两个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用革命友谊统摄文化、语言和地域的差别。里希特版本在穆勒版本的基础上,继续尝试将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民间故事结合,无论在剧情结构、人物塑造抑或表达深度上都更加成功和完整。
结语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民间故事中,有的故事带有强烈的地域色彩和文化色彩,并非每一个中国故事都可以成为德国故事。正如“聚宝盆”故事,在德国讲述者笔下,它既是一个遥远东方的民间故事,在新的文化理解中又化身为一份颇有意趣、贴近人民的政治传单,用朴实的故事情节传递革命斗争的精神动力。它的世界性意义和普世价值不仅在于满足了世界人民都渴望美好生活的共通愿望,同时还生发出无产阶级革命情怀与斗争精神,拉近中德两个遥远民族之间的文化距离。百川汇海,殊途同归。“聚宝盆”故事在德语世界长达百年的不断改编,彰显了中国故事的感召力、生命力和创造力。
参考文献
[1] 李杨. 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2] 叶舒宪. 结构主义神话学[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 张璐. 聚宝盆故事研究[D].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2020.
[4] Blumenberg, Hans. Arbeit am Mythos [M].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79.
[5] Gozell, Rolf, Täubert, Manfred. Das Zauberfass [M]. Berlin: Rundfunk der DDR, 1988.
[6] Lévi-Strauss, Claude. Die Geschichte von Asdiwal [C].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92.
[7] Menger, Michaela. Der literarische Kampf um den Arbeiter. Populäre Schemata und politische Agitation im Roman der späten Weimarer Republik [M]. Berlin/ Boston: Walter de Gruyter, 2016.
[8] Müller, Karl. Das Zauberfass. Märchen aus China [M]. Berlin: Kinderbuchverlag, 1952.
[9] Richter, Manfred. Das Zauberfass. Ein Spiel in drei Akten und sechs Bildern nach chinesischen Motiven [M]. Berlin: Henschelverlag Kunst und Gesellschaft, 1955.
[10] Schmitt, Carl. 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M]. Berlin: Duncker&Humblot, 1991.
[11] Wilhelm, Richard. Chinesische Volksmärchen [M]. Jena: Eugen Diederichs, 1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