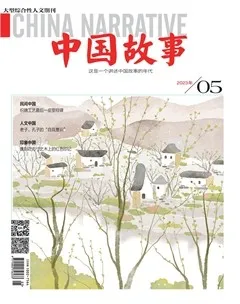论“五四”后期国民性改造思想的转向
导读
“五四”后期,国民性改造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转向。这种转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由“个人”到“社会”的转向;由“理论”到“实践”的转向;由“改良”到“革命”的转向。本文以国民性改造思想的产生与发展为线索,对列举的三个转向进行分析,并指出其中积极意义以及历史局限性,以期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五四”时期国民性改造的思想之本及其内涵。
作者:鲁松婷,吉首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变化,持续紧张的民族危机促使社会矛盾加剧,器物、制度等方面频遭挫折,“国民性改造思想”应运而生,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群体眼中新的“救命稻草”,他们依据中国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因素对国民性形成的原因做了深刻的剖析,并在国民性改造的主体、内容、方式、目标等方面做出了许多新的尝试。“五四”后期,先进知识分子群体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国民性改造思想开始表现出之前所不具有的马克思主义转向,本文拟对此作简要的论述。
一、国民性改造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民族危机的深化为国民性改造思想的产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鸦片战争战败,中国独立自主的政治主权逐步遭到列强的破坏,在清政府持续妥协、退让、无能与腐败的统治下,当时的中国四分五裂、满目疮痍,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社会秩序混乱,天朝上国的优越感消失殆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开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开始开眼看世界,主张学习西方,摒弃不合时宜的封建伦理道德;资产阶级维新派采取文艺、戏剧等方式,进一步推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民所具有的的开放、自由、创新等品格,试图以此潜移默化国人的心理。
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国人痛定思痛,决心唤起国人自由、平等、独立的意识,康有为指出欲救中国,则需根除愚昧、迷信等毒害;梁启超发表《新民说》《中国积弱溯源论》《十种德性相反相成》等,主张新民德、开民智、鼓民力,通过教育、报刊等新型途径培养新型国民意志。辛亥革命后,更多的国人从救亡图存的梦中惊喜,“国性”“民性”“国民自觉”“改造国民”“培育新民”等新名词不绝于耳。恰逢西方进化论传入中国,中西国民特性优劣之比较,使国人再一次敲响了培育新民的警钟。
基于以上认识,国人对于国民性改造问题的探讨逐渐深入,随着帝国主义侵华加剧,国家政治、经济等主权进一步被干涉,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中华民族被前所未有的危机所笼罩。“五四”时期,早期的知识分子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主要从国民性存在的弊端来思考国家和社会的整体病因,着重批判国民劣根性,并期望于此发掘摆脱困境与危机的良策,于是一场与救亡图存紧密相连的国民性改造思潮陡然兴起。
到“五四”后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初步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体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分析批判中国传统国民劣根性存在的根源,着手构建具有无产阶级意识的新型国民,国民性改造思想的目标、路径等都表现出之前所不具有的马克思主义色彩。
二、国民性改造的马克思主义转向
由“个人”到“社会”的转向。“五四”以前,救亡图存的任务日趋紧迫,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维新派等早期知识分子群体在挽救民族危亡的驱使下,开始希冀以西方传来的个人主义本位思想取缔家族本位主义思想,都着重于强调个人的主体地位,个人的独立与尊严,认为新民仅为个人意义上的新民,“国民性”仅指称国人特性,亦无改造之说。在以国民性为题的《论中国之国民性》中有载“四千年此中国,今日依然此中国之国民性,绝不偶被外界势力所破坏。”国民性被冠以相同且亘古不变的特点。在西方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影响下,多数国人更注重个人的生存与发展,陈独秀在论述国民性时指出“国家何物,政治何事,所不知也”,认为旧宗法、家族制度致使许多国人眼中没有国家意识、政治观念、自私、寡耻更无全局观念。李大钊指出“惟在上流阶级, 以身作则”,认为当时的国人没有责任意识,虚伪、堕落、卑微等劣根性充斥于国民之中,救亡图存的任务也只能落在上流阶级、知识分子群体等肩上,忽视了普通民众所付出的微薄之力,模糊了不同阶级在国民性中所存在的差异,导致“国民性”被频繁地与“奴隶根性”等词对举使用,致使“国民性”几近成为劣根性的代名词,夸大了国民劣根性的程度,家族本位主义思想猛烈地受到个人本位主义思想的挑战。
“五四”后期,在十月革命胜利的感染下,民族、民主主义精神日渐高涨,国民性改造不再局限于爱国先进知识分子群体对国民劣根性作出的批判,更多普通民众逐渐认识到国民性改造问题的重要性。“国破家亡,四字相连,若国大乱,家何能保”,陈独秀借此呼吁国人“笃行自好之士,为国家惜名誉,为国家弭乱源,为国家增实力”,认为普通民众需主动起来,自己解放自己,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注入力量,使个人的国民性改造能与国家社会进步相互融合。李大钊指出“重新改造一个普通广大的新组织。一方面是个性解放, 一方面是大同团结。”认为国民性改造过程中不仅需要重视个人的个性解放,还需要组织团结更多的力量,才能更好地促进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国人价值观开始发生转变,普通劳动群众的力量逐渐获得更多的认可,团结互助的集体主义思想得到更多的肯定,片面的个人本位主义思想遭到质疑,其维护者在精神领域充满信任危机与价值困惑。初步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先进爱国知识分子群体意识到单纯拿来的西方个人本位主义思想无益于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适时将眼界转向马克思主义,开始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的社会现状和日趋紧张的民族危机,以期实现个人和国家、社会的协调。
由“理论”到“实践”的转向。“五四”前期,先进知识分子群体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中派生出改造国民性的历史副题,并以理论批驳为主对其进行了较多的揭露。康有为指出当时国人涣散、愚昧无知、迷信之风盛行,国民精神亟需重塑;梁启超亦认为当时国人闭目塞听、麻木不仁、妄自尊大,固步自封,守着老套的“三纲五常”“忠孝仁义”。
陈独秀更是激烈地指出“简直是一盘散沙……完全没有公共心……如此堕落,即人不伐我,亦有何颜面,有何权利,生存于世界?”他认为传统国民劣根性遮蔽了公共心,致使民心涣散,国家和社会仅有堕落且自私的奴隶而无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可言,并认为导致民心与民德沦丧的原因在于专制主义盛行、偏重神权、厌世的人生观、惰性太重、缺乏同情心、对妇人轻侮等。除了对国民劣根性的批驳与揭露以外,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亦在理论中阐明了新型国民性应当具有的品质,如:有独立的人格、公德意识、家国思想、权利观念等,为新型国民性指出了方向,但由于内忧外患的社会条件制约,先进知识分子群体只能真诚呐喊,期望能够通过理论上的国民性改造思想来唤醒众生,并认为这一问题若不解决,那么政治等“枝叶问题”将愈发繁茂。
“五四”后期,救亡图存的形势愈发紧张,单靠从理论中指出国民性所存在的弊端已无法满足于救国救民的需要,启蒙与救亡并行的局面难以实现,接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洗礼的知识分子群体,受唯物史观的影响,开始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辩证看待国民性,不再笼统地进行理论上的国民性批判,不再以国民劣根性一以概之,积极肯定普通劳动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正视上层贪官污吏以及恶绅的劣品行。除此以外,国民性改造开始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政治问题、经济等问题不再被视为“枝叶问题”,国民性改造开始成为全方位系统改造的重要任务,创办刊物、广兴演讲、推行文艺教育、法制宣传等新型国民性改造途径为更多普通民众所接受,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指出“启蒙”与“救亡”不仅要互为一体,还需要争取更多具有无产阶级意识的“新人”,报刊、学校等逐步承载起部分国民性改造实践活动,更多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将思想解放、政治解放、经济解放、民众联合作为国民性改造的共同努方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国民性改造的新型理论武器,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创造性地使马克思主义与国民性改造联结起来。
由“改良”到“革命”的转向。“五四”时期国民性改造经历了由改良到革命的曲折过程。“五四”前期,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以以西方文化价值观为参照,以报刊为主要阵地来反思旧的纲常伦理道德,批判国民劣根性,由西方引进的“德、智、力”等成为当时衡量“新民”的标准。个人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企图以“文明”的改良方式达到唤醒、教化国人,构建新民。胡适在提到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的初衷时指出“大家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通过教育思想文化等非政治途径对国民思想人格进行教化,由此达到优良政体的目标。然而这些努力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当时积贫积弱的现状,政治日益衰微,时局愈发黑暗,亟需开辟一条新的救亡之道,“改良”之道最终也被放弃。
在日益紧迫的民族危机面前, 先进知识分子群体意识到专注于改良的国民性改造方式难有成效。到“五四”后期,适逢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徜徉于中国大地,初步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逐渐厘清“思想文化变革”与“社会革命”之间的关系,李大钊指出“不改造经济组织,但求改造人类精神, 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他认为国民性改造必须是“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把改造经济组织与改造人类精神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认为改造国民性要与改造社会齐头并进,要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革心,更要用阶级斗争的手段进行革命。陈独秀亦激励民众“你们要参加革命,你们要在参加革命运动中,极力要求在身体在精神上解放你们自己,解放你们数千年来被人轻视被人侮辱被人束缚的一切锁链!”“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改造社会制度不可……可以说除阶级战争外都是枝枝节节问题”国民性改造中的“枝”与“叶”问题得以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理论”与“精神”“,改良”与“革命”的关系得到平衡,在他看来,中国只有团结起来,通过革命手段,才能彻底地实现国民性改造。
结语
在国民性改造思潮中,由于不同时期的依据不同、主体不同,对其作出的回答亦大相径庭。“五四”后期,初步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先进爱国知识分子深入人民群众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国民性改造思想逐步与马克思主义碰撞交融,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国民性改造经历了由“个人”到“国家”,“理论”到“实践”,“改良”到“革命”的转向,中国社会逐渐显现出一条全新的国民性改造之路。
参考文献
[1] 社论.论中国之国民性[J].东方杂志,1908.
[2] 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M].北京:三联书店,1984.
[3] 朱成甲.李大钊早期思想和近代中国[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4] 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M].北京:三联书店,1984.
[5] 陈独秀.独秀文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6]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7]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8] 胡适. 胡适文存[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3.
[9] 吕明灼.李大钊思想研究[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
[10]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1] 韩一德.李大钊研究论文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
[12] 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