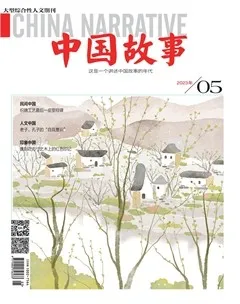以中国古代文学视角发掘“非虚构叙述”的价值
导读
非虚构叙述是当代文学内部的嬗变,对它的研究大都限于现代文学理论。中国古代有丰富文学资源和独特发展路径,从中国古代文学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一概念,或能得出新的启发。
作者:张震,平邑县融媒体中心。
对非虚构叙述的通俗理解是“用小说的技法来写真实的故事”。这个概念兴起于20世纪后期,是一种依据真实素材,以文学手法进行创作的新模式。相比于一般小说而言它们是真实的,被称为“新新闻主义”;相对新闻,它又不拘于直叙,大胆使用文学构思和心理探索,更类于小说;与此同时,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又与小说划清界限:内容中大量使用一手资料,细节上更留意于第一手资料的完整性。它的出现强烈冲击传统认知:究竟是真实多一点还是艺术多一点?或者两者兼具,更艺术也更真实?
在西方文化路径里,虚构和非虚构的实践分别从两个系统里出来的。非虚构最初并不在文学,是在历史和自然哲学的叙述里。近代新闻业诞生以后,在新闻与文学的过渡地带形成了最初的“非虚构”文本,然后再回溯到文学这条河流中。所以很多人把“非虚构”看作是继小说、戏剧、散文之后的“第四类写作”。
“非虚构”作为一种新文体,定位看似合情合理,但总觉隔了一层,因为它与传统分类很难并立,它是对传统样式的覆盖升级,其中或有文学发展的密码。那么,“非虚构”的实践在我们古代是否早就有过?如果有,是否存在一种新的路径,可以重新理解“非虚构”的价值?
事实上,中国古代创作里不但有“非虚构”,而且其与“虚构”并非分立,而是你中有我、相辅相成,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发展路径。
在开始阐述之前,本文还要规范一下用词。“虚构叙述”和“非虚构叙述”是两个欧化词,为适合古代文学语境,以下行文以“虚构”代“虚构叙述”,“纪实”代“非虚构叙述”,两者合一用“叙述”。
一、来自上古的纪实心理
中国古代虚构产生的时间非常久远,从《山海经》等残存的上古神话里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古人却不会用“虚构”这个词来形容正当写作。在今人看是神话,在古人眼里却真实。上古有虚构实践,却无虚构创作动机,神话背后往往反映了真实事件。如: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神话当然也包含大胆的想象,但不同于今天所谓的“虚构”,它们是在纪实的动机下进行的。中国古代叙述的开端包含了强烈的纪实心理。
中国人记录历史的传统非常悠久。司马迁在《史记·三代世表》中说:“孔子因史文次春秋,……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秉笔直书一直是古人撰史的基本原则。以现代观点来看,史著不属于文学,但以中国古代文史哲一体特点看,历史写作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在古人历史写作中,最让今人叹服的,莫过于驾驭叙事角度的能力。
叙述视角一般分为全知视角、内视角和外视角,外视角又分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中国古代史著的叙述角度往往有多种视角巧妙穿插配合,恰如其分地展示事件。例如司马迁《李将军列传》。飞将军事迹流传甚广,虽震铄中外,却因“难封”令人疑,又以“自刭”为人诟。所以“写李广”不单是传记,也是一桩公案,司马迁明白这点。
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萧关,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
徙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战。典属国公孙昆邪为上泣曰:“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恐亡之。”
这里使用汉文帝和典属国公的两个角度,可见广之勇猛。
望匈奴有数千骑,见广,以为诱骑,皆惊,上山陈。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之诱,必不敢击我。”广令诸骑曰:“前!”
这一段视角来自于战役经历者,离人物更近一步:世人知广勇,却未识其足智多谋。
以上叙述视角由远及近,由声名而入军营,无形中建立论点。整篇叙述虽以时间为序,但内中藏着“李广难封”的隐线。为回答疑问,作者巧妙牵出历史节点:
程不识故与李广俱以边太守将军屯……
通过与程不识对比可以看出,李广虽然善战,却喜欢险中求胜;善于带兵,却不重视规章法令,这体现李广性格中豁达的一面。这种性格展露是一个伏笔,交代了他为什么不能被提拔。
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甚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
本文认为这里面蕴含两个因素:一是李广孤傲于官场潜规,二是刻板的军功制度。战争是复杂的艺术,军功考核未必反映出真实的军事价值,尤其对于李广来说。李广承担了战争中最艰绝的部分,虽逊于彰表,却有实功于边庭:
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
更可悲的是,李广对此没有觉悟,反而求问于术士,得出了一个“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的结论。此结论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李广“命运不好”说法从此被传开,这反而真的影响了他的命运。公元前119年汉匈决战,封狼居胥,李广因“命运不好”被调离前锋,结果迷途于东路。
至莫府,广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
司马迁的叙述所引出的历史节点非常巧妙,剪裁、勾勒、环环相扣,又形成论证过程,李广气质、功绩、性格悲剧一一引出。不夸大,无虚言,角度回转可信,辩护公正,令人佩服。
二、诗言志,一以贯之
民谣是百姓的声音。从民歌产生的原因和从官方采集的目的来看,纪实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内在品质。
先秦准备材料,两汉剪裁材料,汉代儒学深度塑造了中国古代诗歌的面貌。《汉书·艺文志》云:“《书》曰:‘诗言志,歌永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时,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这段话记载了中国早期的文学理论,朱自清先生认为这是中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诗言志”把纪实品格深深镌刻在诗的内核之中。纪实融入时代命运,就有了建安风骨、正始之音,融入隐逸玄思,就有了山水诗、田园诗。
诗至唐繁盛至极,一是继承魏晋南北朝传统,二是因科举取诗。科举取诗既考察文辞又考察见识,寓政见于文采,所以唐诗虽融汇虚实,而“诗言志”理念仍为正统。如杜甫辗转而吟,纪录时事,喻为诗史。唐人诗的另一个源头是楚辞汉赋,风格瑰丽奇想,比如李白、李商隐。但有一个现象不可不察,就是唐人的诗题、诗序、诗注都蕴涵着丰富的纪实信息,无论被称为浪漫或者现实主义,都有纪录现实的功能。
诗题就是题目,唐人作诗常有人先拟题目,然后依题而作,常见于游宴、奉和、应制、考试等。如上官仪《奉和过旧宅应制》、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都是应题而作。还有著名的李白《清平调词三首》,记载贵妃轶闻,生动体现了唐人应题而作的传统。
诗序又称记、引,是写在诗题和诗文之间的短文,多交代所咏故事的有关内容或作诗的缘起。
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因为长句,歌以赠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
——唐·白居易《琵琶行序》
题注是注释的一种,有的是后人加的,有的是原来有的。唐诗在最初题写、寄赠过程中,出于社交礼仪的需要,常记录创作的背景信息,包括时间、地点、缘起等,被后人录在诗题下面,称为“题注”。
唐·元稹 《汉江上笛》
题注:“二月十五日夜,于西县白马驿南楼闻笛,怅然忆得小年曾与从兄长楚写汉江闻笛赋,因而有怆耳。”
题、序、注对唐诗来说非常重要,有些诗只有在序和注的背景下才能看清原貌,离开这些,则情致大减。题、序、诗、注共同构成完整作品。题、序、注如交响乐的开端和结尾,诗是中间狂想的部分。从纪实开端,经过中间高潮,再回到现实世界,这是唐诗的基本心理结构。这样,唐诗就如狂想的风筝,有一条线牵在手中,无论诗绪如何飞扬,所兴所比皆有所指,是为实也。缘起于实事,落笔于真情,情真意切则虚构亦不能掩之,这是古人诗歌动人的关键。
从行为艺术的角度再作观察,唐人作诗其不光为“诗”,在题、序、注的这些事情上花费精力,是“诗言”与“人志”的整合,与先秦诗道一脉相承。
三、实之美恶,其发不掩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散文与诗齐名,堪称殿堂之作。刚才已经说过,在文学的开端里文史哲不分家,史著是纪实,诸子是义理,史著和诸子对后世影响巨大。中唐以后儒学开始向义理转变,义理觉醒反映在散文上就是唐宋著名的古文运动,开创了散文写作的全新局面。
韩愈是中唐古文运动的领袖,“文以载道” 是唐宋古文运动的纲领。复古言道,何以开新?原来奥妙就在于——名古而实新,切入点就是“慎其实”。韩愈主张从真实世界里观察,实之美恶,其发不掩。这是韩愈纪实理念的关键,所以他并非空言明道,而是关注时事,发“不平则鸣”之音,所以夹叙夹议、情景交融是其散文一大特点。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与吴郡张籍阅家中旧书,得李翰所为《张巡传》。翰以文章自名,为此传颇详密。然尚恨有阙者,不为许远立传,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
——《张中丞传后序》
这个开头挺有意思,本来要说张巡,却先要为许远鸣不平。原来当时坊间流传着“许远畏死”和“城之陷自远所分始”的说法。但通过分析,韩愈明确了“蔽遮江淮,沮遏其势”的战略价值,把世人眼光从狭隘的城池夺予提升至历史全局,他犀利地指出:
“当是时,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不追议此,而责二公以死守,亦见其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也。”
后面“南霁云乞师救睢阳”这段描写非常精彩。因为睢阳保卫战发生的时间距写这篇文章的时间只有40年,作者亲自进行了信息采集。
“愈尝从事于汴徐二府,屡道于两府间,亲祭于其所谓双庙者。其老人往往说巡、远时事云……”
然后的叙述来自张巡身边侍从,属第二人称近距离视角。
“张籍曰:‘有于嵩者,少依于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围中。’籍大历中于和州乌江县见嵩,嵩时年六十余矣……籍时尚小,粗问巡、远事,不能细也。云:巡长七尺余……”
作者最后提到了张巡就义前的细节,叙述同样来自这名侍从,并与上一段作者亲自采集的信息相印证。文章通过巧妙剪辑,把事件中不易觉察、内在的、惊心动魄之处勾勒出来,场面感人,论证有力。所以纪实剪辑并非以假入真,而是敏锐捕获,良知与慧眼不可缺一。
除人物以外,唐宋写景、游记类散文数不胜数,《醉翁亭记》《岳阳楼记》《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名篇,皆为古代纪实之典范。诸子雄辩、史著明鉴、义理辨析、辞赋豪情、笔记博物,诸多要素汇集,最终成就了唐宋锦绣文章。
四、虚构有纪实笔法
由史书传记至各种笔记,文人笔记自南北朝以降蓬勃发展,之后又出现了唐宋传奇。鲁迅说,小说至唐而有一变,唐传奇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真正开始。 “实”乃“虚”之母体,唐传奇作为虚构小说的开始,纪实手法却早已达到极高的水平,呈现出一种“伪纪实”创作的样态。其手法本文归纳出三条:
(一)叙述角度多变
唐传奇继承了中国史著的优点,而且在此基础上运用的更加纯熟。
柳氏自门窥之,谓其侍者曰:“韩夫子岂长贫贱者乎!”……酒酣,李生曰:“柳夫人容色非常,韩秀才文章特异,欲以柳荐枕于韩君,可乎?”翊惊栗,避席曰:“蒙君之恩,解衣缀食久之,岂宜夺所爱乎?”
《柳氏传》中的韩翃故事,和《霍小玉传》一样,极有可能是一个真实事件。真实记录叠加戏剧性剪辑,效果非同一般。柳氏、李生、韩翊三个外视角,人人所知有限,而造化弄人。如电影蒙太奇手法,画面随视角转换,事件在流动中发展。
(二)以外写内
虚构作品常以人物心理描写来展现心理活动。在纪实中,只用外在描写也可以准确映画出人物的内心:
张氏以发长委地,立梳床前。公方刷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驴而来。投革囊于炉前,取枕欹卧,看张梳头。公怒甚,未决,犹刷马。张熟视其面,一手握发,一手映身摇示公,令勿怒。
——《虬髯客传》
“投革囊于炉前”,一个“投”字可见其嚣张;“取枕欹卧,看张梳头”可见其无礼;“公怒甚,未决”,可见其心如箭压弦上;红拂女“熟视其面,一手……一手……”有须眉不让之气度。在叙述中抓住了关键信息,以精准的语言刻画,人物内心展现得淋漓尽致。
(三)通过细节层层披露复杂人物
复杂人物内心世界,对纪实而言,难度更升一级,而古人仍驾驭自如,如《李娃传》的叙事。李娃是一个复杂人物,作为妓女,她有职业诈骗性质,常色诱富家子弟,直至对方破产。她对许多纨绔子弟毫不手软,但面对同样被她诈骗过的郑生,却一改故辙,赎身相救。两种反差人格集于一身,拿捏不好就会分裂失真。
《李娃传》中,作者通过“惊艳、入彀、计逐、歌赛、鞭弃、护读”系列事件步步设悬,又通过关键细节逐一披露,反差人格在迂回中展开,使人物真容于层层面纱中显现。
先看“惊艳、入彀”的经典桥段,散发瑰色幻影。
生曰:“此谁之第耶?”侍儿不答,驰走大呼曰:“前时遗策郎也!”娃大悦曰:“尔姑止之。吾当整妆易服而出。”
生闻之,私喜。
精心骗局与才子佳人二象合一,骗了郑生,也骗过了读者。充分发挥小说的悬疑作用,同时也为李娃形象预留空间。
他日,娃谓生曰:“与郎相知一年,尚无孕嗣。常闻竹林神者,报应如响,将致荐酹求之,可乎?”
生不知其计,大喜。
行文中第一次语露“诈”意。
生谓娃曰:“此姨之私第耶?”笑而不答,以他语对。
此处李娃演技一流,冷酷无情。
音响凄切,所不忍听。娃自阁中闻之,谓侍儿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连步而出。
此处可见李娃内心伤迹。
当然,后面李娃 “敛容却睇”之议论是点睛笔,完整呈现了人物本质,但全篇以细节层层披露出人物复杂性,稍用“心语”而波澜可见,奇中生奇,不愧为传奇中的传奇。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纪实非常独特:古人没有“非虚构”概念,却在敏锐捕捉中,真正诠释了“真实里有最动人情节”这一核心理念。这不仅启发我们的非虚构创作,对于虚构创作也很有教益。
“非虚构”并非一种文体,也不是“现实主义”。并非只出现在历史传记和新闻报道,书信演讲、小说、戏剧……任何一种叙述都可以出现。如果说众多文体是列列山峰,横过来再看,“非虚构”却如蜿蜒在所有山峰之上的脊线,它是隐现于所有叙述的一种观点、方法和写作状态。本文认为它包含了“真实的心理动机、把真实作为原则、对虚构的反躬自醒”三层含义,这也是“非虚构”产生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上古出现纪实动机。这是人类叙述的开始。
第二阶段,人类建立“秉笔直书”的原则。出现历史学,出现了 “非虚构”实践。
第三阶段,当“虚构”和“非虚构”并入眼帘,“虚构”成为文学主脉,又在对“虚构”反思中产生了“非虚构”写作的理念。这时“非虚构”不仅是一种原则,更是一种审美的价值倾向。
这三层含义决定了“非虚构”是文学之原力,应该为所有书写者所留意。借助古人遗存,找到“纪实”之力,可以持续焕发我们创作的内在力量。
参考文献
[1] 杨新秋.卡波特与非虚构小说《冷血》[J]. 意林,2007(19).
[2] 刘建明 王泰玄.宣传舆论学大辞典[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
[3] 山海经[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1.
[4]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5] 诗经[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1.
[6] 朱自清.诗言志辩[M]. 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7] 周敦颐.通书·文辞[M].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
[8] 胡晓静.谢·多甫拉托夫的伪纪实主义叙事研究[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