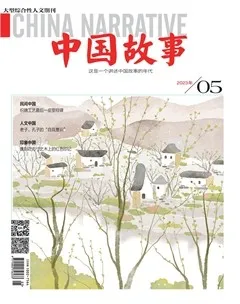细说乡村“老物件”
导读
乡村,是农耕文明的载体。乡村中的煤油灯、面罗筛、粪箕子、木轮大车等“老物件”,是乡村记忆的载体,记住它们,就是记住乡村的发展史。
作者:乔加林,笔名乔乔,江苏省作家协会、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乡村,是农耕文明的载体,记住乡村,记住过往,记住农民的文化,就是记住乡村发展史。
煤油灯
在20世纪70年代,最能反映人们生活质量的就是照明,从我能记事起,家家户户都是靠煤油灯照明。一根长长的棉线从一根用铁皮做的细长管子里面通上来,火柴一点,灯就着了,亮或不亮,可以用挑长或挑短露出的细线加以调节。
煤油灯,也叫“洋油灯”,毫无疑问,那煤油是从外国进口的。人们用“如豆的灯光”来形容油灯的亮度再恰当不过了。在我小的时候,农村还没有电,家家户户都备有一个或几个煤油灯。煤油灯的结构极其简单,我家的煤油灯是用一个白色玻璃瓶做灯座,上端覆盖一个圆形的铁片,中间穿过由多股细线捻成的油捻子,一直拖到盛油的瓶肚子里。瓶肚子里的透明液体我们叫作煤油(老人们通常叫做洋油)。
我出生在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尤其是在比较闭塞的苏北乡下。在那里,我曾经历了无数个靠煤油灯度过的日落后的时光。煤油灯昏黄的光环时常像一粒萤火虫般飞进我的记忆,点亮一个个深藏在心底的旧梦,让我又看到了父母摸黑劳作的身影,看到了一灯如豆的饭桌上,认真写作业的孩子,也看到了他们的成长。
有关煤油灯的俗语也很多,比如:“灯不拨不亮,话不说不明”“灯盏再小能照亮,油篓再大不搁舀”“灯苗虽小,能照亮间屋;羊蹄虽小,能走出条路”等,深奥的道理被说得通俗易懂。
时过境迁,煤油灯悄然退身,逐渐演变成老物件,消逝于漫漫时光长河中。如今,那些煤油灯已深藏在心底,化成一盏永不泯灭的心灯照我前行。
面罗筛
那时,农村还没有电气化粮谷加工机械,碾磨坊承担着农村人把原粮加工成米面的重要角色。经过碾磨加工出来的粮食面粉,都要用面罗进行加工,不同的粮食要使用不同的面罗进行筛面。白面罗孔眼最细,筛小麦粉、荞麦粉,高粱面罗居中,玉米面罗最粗。
每次家中需要磨面的时候,母亲都会提前几天把需要碾磨的粮食淘洗干净,待晒干后,背着粮食去东庄王大娘家碾磨坊进行磨面。
记得小时候,我最喜欢看着母亲推磨、筛面。光线幽暗的厢房里,磨盘转动的声音格外响亮。阳光从木头门的缝隙打进一束,正好照在磨道里。磨盘一转,整粒的粮食倏然破碎,然后成为齑粉,光束里就有了飞动的颗粒,像精灵。到筛面的时候,母亲把门敞开,阳光无遮拦地透进草屋子。她在地上摆好一块大塑料布和面罗,以迎接面的降生。磨成的粉末被细心地捧到罗里,然后她弯下身子,端起面罗轻轻地左右摇晃,细细的面粉便乖乖地落下去,一层又一层,唰唰的。金光如缕的空气中,也飘满喜气洋洋的精灵们。
到了夏天,如果家中储存面粉多的话,面粉里总会悄悄生出些小黑牛儿、小肉虫。母亲就会用罗重新把面粉过滤一遍,把面粉里那些小黑牛儿、小肉虫清理干净后,一点也不影响食用。
随着社会发展的脚步提速,大家食用的面粉直接在集市上或超市里购买,谁还有耐心再一圈又一圈去推碾子、推磨,再用面罗筛呢?有时候回老家与庄上老人们闲唠起过去的往事来,老人们还是啧啧地回味石磨年代粮食的原味与醇香。
粪箕子
粪箕子,顾名思义,盛放粪便肥料之用,大多用腊树条或桑树条编织而成,结构与其他筐相同,长和宽皆三四十公分,前面为出口,后及两侧壁成半圆,高二三十多公分,上有隆起之丁字形筐系儿,高出筐壁十多公分,结构与背筐近似,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粪箕子是农村家家必备的农用工具。它那个大肚子里,什么都能装,土、石子,粮食、蔬菜、柴草……更多的是用它来盛粪。在装粪时,先在粪箕里面垫上一块破纸板或撒上一层土,那样可以减少粪便粘在粪箕上。
农谚说:“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粪是庄稼宝,少了长不好”,狗粪、猪粪、马粪、牛粪、人粪,只要是粪便,粪扒子就会把它扒到粪箕里。在粪被人们捡拾的年代,拾粪要赶早。拾粪可以在村里村外、田间地头,拾粪的人都希望能在村口路上,遇到牛拉粪的时刻,一坨牛粪有半粪箕子。
我从小学三年级时开始拾粪,一直拾到读初中。就我们这些孩子来说,最希望冬天拾粪。粪上了冻,尤其是稀粪上了冻,就不那么脏了,粪扒子轻轻一扒,整块粪便像敲冰一样敲下来,不臭,还不沾粪箕子。为了能多拾到粪,天麻麻亮我就起床,有时月亮还在高空,把田地里照得明亮明亮的。有时运气好能捡拾到几坨牛粪,可以把粪箕装得满满的,一粪箕粪便,压得让我咬牙过,肩上还留下一道深深的压痕,皮肤几欲磨破,回到家父母都会好一顿夸奖。
后来,我参军入伍,不用再背粪箕子了,粪箕子彻底地离开了我的生活。和许多农具一样,它渐渐地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成为一个时代的印记。
木轮大车
20世纪80年代以前,农村都是过着大集体生活,运输都是靠木轮大车。那个时候,每个生产队里都有一辆“大车”,大车长度约5米,宽3米,车轮直径1.5米左右;两个车轮大多用厚厚的榆木或槐木板拼成,像两块巨大的车轮饼,车架、车轮、车腿全是木头。
大车十分笨重,由于没有轴承,车轱辘和轴是固定在一起的。行走的时候,轮子和车轴一起转动。大车没有车厢,更没有车棚子,只有一架车架在车轴上,车架两边的下面和轴接触的地方,安着两块开有凹口的木头,凹口内嵌一块弧形的铸铁,叫车沟心,耐磨。和凹口接触的车轴的周围,嵌入几根铁条,叫车键,也是为了耐磨。大车在运行时,驾车人要经常给车轮轴的地方上油,方言叫“膏油”。大车前面一年四季都会挂着一个黑不溜秋的塑料油桶。油桶里插一根膏油用的扁刷子,每行走三四里地,就得膏一次油。
夏秋收割时候,大车就派上用场。妇女们在田里用镰刀收割麦子,打好捆放在地里,父亲和几个劳力负责装车,再用大车将收割好的麦捆拉回生产队里的晒场上。只要在大车上堆放好,一大车可以拉一亩多地的麦捆,装好车后,再用大绳扎紧。牛拉的木轮大车在平展的沙土地上慢腾腾地滚动着,那两个巨大的木轮子,像两个大碾盘,碾压泥土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巨大笨拙的车轮承载了庄稼人太多太多的希望!
实行承包责任制后,木轮大车由于太大太笨重也就无用武之地,取而代之的是独轮车或平板车(也全是木头制作的)。后来,木制的独轮车、平板车逐步被胶轮木板车替代。再到后来,手扶拖拉机、四轮拖拉机出现了,胶轮平板车、驾辕的老黄牛也不知都跑到哪儿去了。
人们常用“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这句话来比喻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时代前进的车轮一刻也没有停留过。如今,一辆辆客车来往于村巷、街头,那悠扬的汽车嗽叭声,萦绕在每一位老百姓的耳边,让每一位出行的人都喜笑颜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