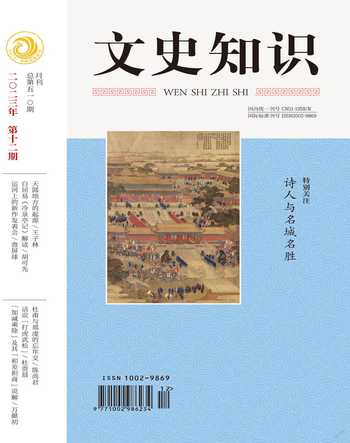《饮马长城窟行》“枯桑”“鲤鱼”新析
刘青海

常言道,诗无达诂。如何欣赏诗歌,也并无一定之规。而其大要,正如陶渊明所说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奇者赏之,疑者析之。近来重读《饮马长城窟行》,颇觉其中“枯桑”“鲤鱼”之意,前人之解,仍有可议之处。
《饮马长城窟行》是一首传统的思妇之诗:
青青河边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jiào)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可见。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上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长相忆。(《文选》卷二七)
前八句为一段,写闺中少妇的春思,因思成梦,醒后惘然情状。情极真,一气直下,如盘走珠,是极流丽之笔。《楚辞·招隐士》说:“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在古典诗歌的语境中,常用春草兴起念远之情,“青青河边草,绵绵思远道”也是如此。细密如絲的春草,沿着河岸绵延不绝,触动了闺中人绵绵不绝的相思。春草随着河水、沿着河岸的道路,延伸到那遥不可及的远方;相思也如同春草,将要绿遍天涯。这里的“远道”,既指远方的道路,也包括远行在外之人。从“绵绵思远道”,到“远道不可思”,从修辞来说是顶针格,是顺接,采用了歌谣的修辞方法。就句意来说,从“绵绵思远道”到“宿昔梦见之”,因思成梦,是递进。从“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到“他乡各异县,展转不可见”,仍是顶针格。就句法而言,则是倒叙:先说梦里相见醒来暌隔,接下来才补充远人辗转在外之情状。“他乡”两句,写客子漂泊他乡之苦,也透着思妇辗转反侧的相思之情。
“枯桑”四句为第二段,起兴的景物也由春草而变为枯桑,见出时序的推移,抒情的节奏也随之变化。“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两句,历来解释不同。如《文选》李善注:
枯桑无枝,尚知天风;海水广大,尚知天寒;君子行役,岂不离风寒之患乎?
首先要指出的是,李善“枯桑无枝”的说法是不符合常识的。秋冬树叶凋零,枝干犹在,所以今人余冠英的注,就改成了“枯桑虽然无叶”(《乐府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32页)。这种错误的发生,也并非偶然,因为在古典诗歌的语境中,树木之“枝”谐音知己之“知”,所以在创作中,常以草木之有“枝”来兴起人之有“知”(有情),如《诗·桧风·隰有苌楚》“隰有苌楚,猗傩其枝,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以及《越人歌》“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苌楚之“(有)枝”与“无知”,与枯桑之“无枝”与“(有)知”,何其相类!而且在典籍中,也确实有以“无枝”来形容树木的,例如《山海经·海外北经》记载在欧丝之野东,有三桑木“长百仞,无枝”,又《海内经》记载在九丘有建木“百仞无枝”。枚乘《七发》也说:“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所谓“无枝”,主要是为了突出树木高大,百尺、百仞之上,总还是要分出枝条来的。何况诗歌中的比兴,用以起兴者,都是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事物。所以,李善犯了一个想当然的错误。那么这两句是说思妇还是征夫呢?李善认为,是用枯桑知风、海水知寒,来兴起征夫的风寒之苦。这样解,“风寒”两个字落到了实处,但在海水、枯桑为主语的两句中,硬加入征夫寒苦的意思,让原本自然平顺的句子,在理解上变得这样的曲折,不无增字解经之嫌。通篇都是思妇之辞,突然插入征夫所遭受的风寒之苦,章法上多少有些突兀。清人何焯应该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对李善注做了一些改变:
桑常经风,虽枯犹知之;水常经寒,到海犹知之。若新少年不通人情,各自媚悦于君子,谁为我言离思之苦乎?(《义门读书记》卷四七,中华书局,1987,920页)
何焯认为这两句,是以枯桑、海水能知自然之风寒,来兴起思妇的“离思之苦”。换句话说,就是以自然之风寒来比喻思妇在现实中的遭际,而不是指游子实际所遭之风寒。这也可以说是对李善之说的一个修正。西晋诗人张华《情诗》“巢居知风寒,穴处识阴雨”两句,即从此二句脱化而出,以虫鸟对风雨的感知来兴起夫妇离别后的相思之苦(“不曾远别离,安知慕俦侣”)。西晋去汉未远,故能深得古辞之本心。
另一个影响较大的注解,是《五臣注文选》李周翰注:
枯桑无枝叶则不知天风,海水不凝冻则不知天寒,喻妇人在家不知夫之消息也。
相比李善注,意思完全相反。但更加牵强了。这个注解有三点值得注意:(一)重点放在“枯桑”和“海水”的物性上。(二)解“知”为“不知”“岂知”,也就是将这两句作反问句。(三)认为这两句是说思妇不知道征夫的消息。先看第(一)点,到底枯桑知不知天风呢?我们不妨来看诗人怎么说:
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陶渊明《桃花源诗》)
送别枯桑下,凋叶落半空。我行懵道远,尔独知天风。(李白《鲁城北郭曲腰桑下送张子还嵩阳》)
可见,所谓枯桑知天风,并不像李周翰理解的那样—叶子掉光了,桑树就感觉不到天风;而是正好相反—桑树的叶子在大风中落了个干净,正是它感知天风的明证。《古八变歌》“枯桑鸣中林”,王维《送陆员外》“阴风悲枯桑”,孟郊《苦寒吟》“北风叫枯桑”,都是将枯桑悲鸣与天风相联系。海水又是否知道天寒呢?我们再看古人的诗:
被空眠数觉,寒重夜风吹。罗帷非海水,那得度前知。(萧纲《杂咏诗》)
天寒海水惯相知,空床明月不相宜。(江总《姬人怨》)
可见,海水不但知天寒,还能够提前(即“度前”,六朝人常用)知道天寒的消息。既然枯桑早知天风,海水早知天寒,那么(二)(三)条的解释也就不攻自破了。纪昀(字文达)、余冠英等注家意识到了这一点,对李周翰注做了这样的完善:
纪文达曰:枯桑似不知天风,海水似不知天寒。然叶虽不落,而未尝不为风摇,水虽不冰,而未尝不受寒侵。比己之甘苦自知,茕茕无告。入门二句则言同事之各为身谋不相顾也。(转引自徐仁甫《古诗别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81页)
余冠英《乐府诗选》:枯桑虽然无叶,对于风不会感不到,海水虽然不结冰,对于冷也不会感不到。那在远方的人,纵然感情淡薄,也不至于不知道我的孤凄、我的想念啊。
纪昀以“甘苦自知,茕茕无告”八字概括思妇所处之情境,可谓能得诗人之心。相较而言,余冠英之解不免隔膜,他错误地认为“枯桑”两句兴起的是远人之“知”思妇,章法突兀不说,以枯桑无叶、海水不冻对应远人情感的单薄,以天风、海水对应思妇的孤凄和想念,不免比附的痕迹,显得有些生硬。
这样看来,还是李光地(别号榕村)、吴景旭两家之解较胜:
李榕村曰:惟树知风,惟水知寒,喻己有情,人莫之知,各自为媚而已。(转引自徐仁甫《古诗别解》)
吴景旭《历代诗话》卷二四:枯桑自知天风,海水自知天寒,以喻妇之自苦自知,而他家入门自爱,谁相为问讯乎?(陈卫平、徐杰点校本,京华出版社,1998,217页)
“自苦自知”,即“甘苦自知”。二说深谙诗之比兴,故能抉发其神理。要之,从“青青河边草,绵綿思远道”,到“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两处都是触物起兴,但景色已经从“青青河边草”这样生意勃发的春景转入萧条的冬季,可见自从春日分别之后,直到冬天,丈夫始终音信全无。在“春与秋其代序”(《离骚》)的时光流转中,思妇的容颜也如同桑树一样,经历了从“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到“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诗·卫风·氓》)的盛衰之变,而她的内心,正如那被寒风席卷的海水一样,越发地苦涩。然而此刻看上去,掉光了叶子的枯桑和永不冻结的海水,似乎已经对外界的风寒无动于衷了。正如经历了长久离别的思妇,似乎也习惯了相思煎熬,外人或许觉得她已不以之为苦了。“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是说别人家纵使有人回来,也都各爱自己的所欢,谁愿意将良人的旅况告诉我呢?正所谓“目见他家之团聚,弥形一己之孤独,此其思之所以绵绵也”(王文濡《古诗评注读本》卷上)。这四句写人情之冷暖自知,可说是神来之笔。没有怨,只是平静地体认和陈述,反而格外令人动容。
正是在这样哀哀无告的困苦中,忽然有客带来了远人的消息,其喜当如何呢?“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还记得第一次读到时大吃一惊的心情:把书信藏在鱼腹中,这是真的吗?尺素上的信,应该是以笔墨写就。从鱼肚子里拿出来,不仅容易濡湿,而且湿淋淋的一股腥臭。再说,路途遥远,鱼应该早已腐烂了。可是,唐代注释《文选》的吕向却很认真地告诉我们,这是真的:
《文选》吕向注:相思之甚,精诚感通,若梦寐之间,似有所使自天所来者,遗我双鲤鱼。鲤鱼者,深隐之物,不令漏泄之意耳。令家童杀而开之,中遂得夫书也。
据《史记·陈涉世家》,陈胜、吴广在称王之前,为了威服众人,故意假托鬼神,为鱼书、狐鸣之事。所谓鱼书,即先将“陈胜王”三字丹书于帛上,再将此帛书“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可见以鱼传书之事,本出于造作,不料吕向竟以为实!而且如果真的有鲤鱼传书之事,为何是两条呢?难道是信太长的缘故?不然的话,又如何解释书入鱼腹而无损于鱼体,还要家童再杀而开之,才能取出书信?说不通的地方实在太多了,所以注者只好来一句“精诚感通,若梦寐之间,似有所使自天所来者”,天上的使者来传信,自有一番神通,于是问题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这样的疑问,自然非我所独有。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较早的质疑,来自明代的顾元庆和杨慎:
顾元庆《夷白斋诗话》:“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童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鱼腹中安得有书?古人以喻隐密也,鱼,沉潜之物,故云。(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796页)
杨慎《升庵诗话》卷一三“双鲤”条:古乐府诗:“尺素如残雪,结成双鲤鱼。要知心中事,看取腹中书。”据此诗,古人尺素结为鲤鱼形即缄也,非如今人用蜡。《文选》:“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即此事也。下云烹鱼得书,亦譬况之言耳,非真烹也。五臣及刘履谓古人多于鱼腹寄书,引陈涉罩鱼倡祸事证之,何异痴人说梦邪!(《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901页)
二说都扬弃了吕向的鱼腹藏书之说,杨慎直斥为痴人说梦。两人的年代相近,难以判定先后,或正表明吕向之说在当时已被普遍地扬弃。杨慎根据古乐府(其实是唐代女诗人李季兰《结素鱼贻人》诗),解双鲤鱼为“古人尺素结为鲤鱼形”,也就是用打结的方式将信封缄(不像后世用蜡,或今天用胶水),由此得出“烹鱼得书,譬况之言”的结论,是合乎情理的推论,可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明清之际的吴景旭直接沿用了杨慎之说,但未标明出处:
五臣《注》:“相思感通,梦寐之间,若有使来遗者。”又云:“命家童杀而开之,中遂得书。”不知此乃想象之词,借枯桑海水,以喻他乡异县,字字神境。若说杀鱼,无乃病騃。按,汉时书札相遗,或以绢素结成双鲤之形,即缄也。非如今人用蜡。唐李氏季兰《结素鱼贻人》云:“尺素如残雪,结为双鲤鱼。欲知心里事,看取腹中书。”盖其遗制。(《历代诗话》卷二四)
吴景旭《历代诗话》在解诗时,常引述他人之说,所以应该不是有意掠美。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自明人注意到李季兰《结素鱼贻人》一诗之后,以双鲤鱼为“以绢素结成双鲤之形”就成为当时一种普遍的认识,杨慎也并非此说的首创者,或许更接近事实的真相。
那么,是否杨慎之说就是确定的事实呢?也很难定论,毕竟李季兰是唐代人,距离汉代也近千年。近人黄节就反对杨慎之说,认为烹鱼得书只是用典:
《诗·桧风》:“谁能亨鱼?溉之釜鬵。谁将西归?怀之好音。”烹鱼得书,古辞借以为喻。注者或言鱼腹中有书,或言汉时书札以绢素结成双鲤,或言鱼沉潜之物,以喻隐秘:皆望文生义,未窥诗意所出。(《汉魏乐府风笺》卷四,中华书局,2008,50页)
黄节所引《桧风·匪风》中这四句,孔颖达疏云:“谁能亨鱼者乎?有能亨鱼者,我则溉涤而与之釜鬵以兴;谁能西归辅周治民者乎?有能辅周治民者,我则归之以周旧政令之好音。”(《毛诗正义》卷七,十三经注疏本,114页)老子说“治大国若亨(烹)小鲜”,小鲜就是小鱼,所以诗人用烹鱼之事兴起治国之事。这里当然与《小序》所谓“思周道”无关。但古人用典,很多时候只是用其字面。显然,黄节认为“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用的就是“谁能烹鱼”“怀之好音”的字面。这样说,好像也有他的道理。《饮马长城窟行》虽说是乐府旧题,“青青河边草”这一首,或认作古辞,或以为蔡邕所作,一直没有定论。但无论谁是作者,大约总属于汉代的士大夫阶层。而汉代《诗经》立于学官,读书人是很熟悉的,故汉乐府中化用《诗经》处也不少。
然而,如果我们翻开现在一般的选本,又会发现第四种解释,即将“双鲤鱼”作为信函的代称。此说的首创者应该是闻一多:
双鲤鱼,藏书之函也,其物以两木板为之,一底一盖,刻线三道,凿方孔一,线所以通绳,孔所以受封泥。(详傅振伦《简策说》,载《考古》第六期。)此或刻为鱼形,一孔以当鱼目,一底一盖,分之则为二鱼,故曰双鲤鱼也。……呼儿烹鲤鱼,解绳开函也。(《乐府诗笺》,《闻一多全集·楚辞编 乐府诗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757页)
发函取书,要将合在一起的两块鱼形板分开,如同将鲤鱼剖开一样。说得生动一点,就成了“呼儿烹鲤鱼”。尺素书,就是书信。此说其实是受到杨慎说的启发。今天大部分的选本,如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参考资料》等,都采用此说。它的好处是结合了实物,给人以切实可感的想象。
上面是围绕“双鲤鱼”的一些讨论。“双鲤鱼”究竟是否实指鱼呢,还是一种指代?我倾向于后者。如果是后者,那究竟是书函(闻一多说),还是封缄(杨慎说)呢?我们看六朝时人说到书札:
有朋西南来,投我用木李。并有一札书,行止风云起。扣封披书札,书札意何有?前言节所爱,后言别离久。(萧统《饮马长城窟行(一题拟青青河畔草)》)
故人倘书札,黎阳土足封。(庾信《任洛州酬薛文学见赠别诗》)
前一首,“披書札”之前,先要“扣封”,这里的“封”是名词,指的是封泥。据《中国文物考古辞典》“封泥”条,指的是古代封缄简牍并加盖印章的泥块,也称泥封。封泥产生于春秋末年,是随着玺印的出现而出现的,盛行于秦汉魏晋,至唐以后消失(参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297页)。“黎阳封”即用黎阳出产的青泥封书,事载《东观汉记》卷九《邓训传》。又《陇右记》:“武都紫水有泥,其色亦紫而粘,贡之用封玺书,故诏诰有紫泥之美。”(《太平御览》卷七四引)所以后世用紫泥封代指诏书。相较于鲤鱼形的木函、将尺素打成鲤鱼形结,我更倾向于认为所谓“双鲤鱼”所指为泥封上的鲤鱼形印记,毕竟后者更常见。虽然也是一种猜测,但似乎要更近情理一些。据王伯敏《中国绘画通史》,古肖形印盛行于两汉,其样式,“有的两面,一面刻姓名或吉利语,一面刻图像,如汉代李贤私印,一面刻李贤,另一面刻虎。……还有一种刻麟、鹿、羊、双鱼的吉祥通用印”(三联书店,2018,115页)。其中著名的像“日利”双鱼印,所刻正为双鲤鱼。“日利”两旁为双鱼,鲤即利之假借,鱼即馀之假借,取有馀之意。可见在汉代,不仅有双鱼印,而且有双鲤鱼印。当然,这仍是一种假说。
绕了一个圈,我们重新回到诗歌的本文上来。“客从”四句,是说客人带了一封信给思妇,封信的青泥上钤着双鲤鱼形的印,其中应该也寄托了夫妻双飞比目的婉娈情谊。接此信札,小心地打开捺了双鱼印的封泥,怀着激动的心情,长跪而读,也见出一种郑重。“长跪”两句节奏舒缓,内里实包含一种迫切的期待。这八句的内容,与《古诗十九首》“孟冬寒气至”中“客从远方来”四句的内容大体相类,但有繁简之别: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上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长相忆。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古诗十九首》)
前面相思煎熬,所以两句一转,声调急促摇曳。到了“客从远方来”六句,因远客带来书信,心情为之一松,情调亦变为舒缓。读信之后,又转为激越,无一字之怨,而怨已深矣。虽然只睹文字,而声情如见。这是乐府诗独有的魅力!
有人认为“客从远方来”以下八句都是虚写,像吕向所说,是思妇意中事。因为如果精诚所至,思妇所盼,是良人的早早归来,书信只是不得已求其次,何况还是要她“长相忆”(也就是仍不能回来)的书信呢!这样说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总觉得太造奇了,就艺术效果而言,反而有一种“过奇则凡”之感。而乐府诗的奇,多是凡中见奇,比如这一首写思妇之情,短短二十句中,叙事有数层转折,富于戏剧性:因思成梦到跌回现实,是一转;再叙其相思之苦,到远人送信,是又一转;从得信之喜到披读之失望,再一转—可谓愈出愈奇,读之却浑然不觉,此所谓以情动人,大巧若拙。这种汉乐府独有的浑朴,是后世文人拟乐府艺术很难企及的一种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