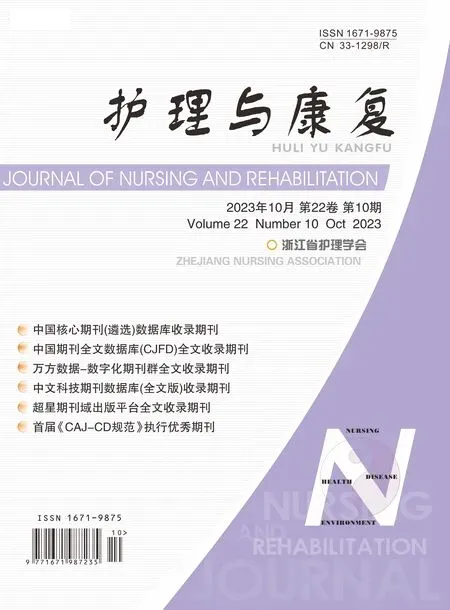健康心理控制源在健康管理中的应用现状
张玲红,蒋智丽,张明月,黄丽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浙江杭州 310003
据WHO报道,全球60%的过早死亡与个体不良行为及生活方式有关[1]。在我国,2019年因慢性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8.5%,大部分慢性病患者均表现出特征不同的不健康行为,其中未注意健康饮食和锻炼身体者占50%以上[2]。此外,慢性病患者在心理上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压力,容易导致情绪低落、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健康管理是指一种对个人或人群的健康危险因素进行全面监测、分析、评估的过程,以便在发现健康恶化早期迹象时及时介入,改善人体健康状况的策略[3]。尽管研究一直致力于全方位探索健康管理的影响因素,以提高人群健康行为改变的依从性,改善其生活质量,但只有20%~35%的居民保持其健康行为处于较好水平[4]。研究[5]显示,健康心理控制源(health locus of control,HLC)作为影响心理和行为的一个重要变量,能根据个人的信念体系对健康或疾病的原因归属进行测定,从而更好地反映健康行为背后的心理状况,为实施个性化干预提供理论依据。鉴于国内外对HLC在健康管理领域中的作用认识尚少,本文就HLC的定义和常用的评估工具,以及其在健康管理方面的应用进行综述,旨在今后为从HLC角度开展个性化护理服务、实施健康管理提供借鉴。
1 概述
控制源(locus of control,LOC)作为理解健康行为和信念的重要概念,由Rotter[6]于1954年在社会学习理论中提出,是指个人是否认为能够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反映一个人将自己行为的后果归因于内部或外部因素的程度。当个体认为健康结果取决于自己行为即表现为内控型,当个体认为健康结果取决于自己控制之外的力量即表现为外控型。1978年,Wallston等[5]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HLC,并将其扩展为内部控制型(internal health locus of control,I-HLC)、权威人士控制型(powerful others health locus of control,P-HLC)和机遇型(chance health locus of control,C-HLC)。I-HLC指的是个体认为其健康由自身行为决定,I-HLC水平高者较多表现为积极健康行为;P-HLC是指个体接受他人的指导,与健康行为的联系较为模糊,可以是相关的,但需要权威人士的指导;C-HLC表明个体偏向“听天由命”,不会主动采取健康行为,C-HLC水平高者较多表现为消极健康行为。
2 主要评估工具
2.1 多维健康控制源量表(Multidimensional Health Locus of Control,MHLC)
MHLC被认为是健康心理学研究中使用最广泛的工具之一,分为A、B、C三种形式。MHLC-A由Wallston等[5]于1978年编制,含I-HLC、P-HLC和C-HLC三个维度,共18个条目。采用Likert 6级评分法,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赋1~6分,最终得分是每个分量表得分的总和,分数越高则认为某一特定因素对被研究者的健康影响越强。但该量表在心理学测量方面仍存在一定局限性,特别是内部一致性,均低于理想水平,未达到现行健康测量工具指南推荐的质量标准,有待今后在心理统计学测量中进一步完善[7]。MHLC-B在MHLC-A基础上于同年编制,不同点在于计分以各维度单独呈现,每个维度最低得分6分,最高得分36分,得分越高说明该维度控制水平越高[5]。国内学者李彩红等[8]将其本土化后,重测各维度Cronbach's α系数为0.68~0.78,效度为0.90~0.94。尽管该量表的以上两种形式均广泛用于临床和非临床目标人群中,但其等效性仍存在争议。MHLC-C是于1994年开发的第三种形式的量表,进一步将P-HLC分量表细分为健康权威人士控制(医生)和健康权威人士控制(其他人),主要应用于医疗情境中年龄18岁及以上患者心理控制源的测量[9]。
2.2 心理健康控制源量表(Mental Health Locus of Control Scale,MHLCS)
MHLCS由Hill等[10]于1980年编制,用于测量个体关于心理健康问题的信念。分为内控型和外控型,共22个条目,采用Likert 6 级评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越倾向于将自身心理健康结局归因为外控型。采用该量表对226名中学生进行测量,结果显示总体Cronbach's α系数为 0.84。该量表应用人群广泛,可测量不同环境下人群的HLC,但量表结构有待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
3 在健康管理领域中的应用
3.1 药物依从性
我国的慢性病患者普遍存在对慢性病相关药物认识不足的情况,并且长期服药依从性差[11]。研究[12]表明,HLC是药物依从性的有效预测指标,为监测临床用药提供参考性价值。服药早期阶段,患者相信健康是由个体控制并积极主动采取健康促进行为[13],在此过程中受高等教育和职业性质等因素的共同作用[14]。随着病程的延长,相信自我控制健康的能力减弱,患者由内控型逐渐转变为外控型,主要表现为医生控制型患者对健康团队的信任和依赖程度高,药物依从性高[15];C-HLC的患者,不相信自己能够控制健康,更相信命运,药物依从性低[16]。Silva等[17]应用MHLC对88例接受免疫抑制药物治疗的肾移植受者进行调查,发现与低依从性患者相比,高依从性患者的自我效能和内在宗教信仰得分较高。因此,要充分理解HLC与依从性之间的关系,仅考查子维度的主效应可能是不够的,探索内部HLC以及外部HLC子维度对医疗方案依从性的相互作用可能更有成效。HLC作为监测药物依从性的新靶点,患者对个人能力的信念以及对健康的控制也应体现在他们对医生在疾病管理中的作用的认可上,未来药物依从性干预方案的制定需平衡该结构的关系与人口学和疾病特征。
3.2 疾病筛查
早期疾病筛查对识别高危人群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癌症患者,可以明显降低其发病率和病死率,然而人群对疾病可控性的消极态度可能导致其未能采取疾病预防行为。Saei等[18]在一项探究女性健康控制点与巴氏涂片信念的相关性的研究发现,250名已婚女性中,I-HLC、P-HLC和C-HLC的平均得分分别为(22.59±5.32)分、(24.54±4.28)分和(22.84±4.65)分,巴氏涂片信念与I-HLC(r=0.209,P=0.001)和P-HLC(r=0.216,P=0.001)显著相关,线性回归分析显示I-HLC、P-HLC和C-HLC是巴氏涂片信念总分的预测因子,可能与在伊朗文化中,强调保护个人隐私并对检查抱有负面看法,从而导致筛查的参与度低有关,提示医护人员在制定教育干预计划时,应侧重于强化疾病控制信念和纠正信念,以提高妇女对子宫颈抹片检查的依从性。此外,Saei等[19]对德黑兰325名妇女进行横断面研究,使用MHLC、乳腺癌筛查信念问卷和人口统计学问卷收集数据,结果显示I-HLC、P-HLC和C-HLC得分每增加1个单位,乳腺癌筛查信念问卷得分则增加0.54分、0.31分和0.57分。
3.3 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是整体幸福感的核心组成部分,有助于积极发挥社会功能和实现人生目标。一项调查研究[20]表明,我国成年人的精神疾病(痴呆除外)终生患病率为 16.6%。目前HLC与心理健康的相关性仍存在争议,Giblett等[21]对224名成年人的横断面研究发现,一般自我效能是心理健康显著的正预测因子,而HLC与心理健康无关。相反的,Aflakseir等[22]对108名老年人的调查研究发现,健康控制点得分最高的是内在控制点,而I-HLC对抑郁症有显著预测作用,I-HLC水平越低的老年人越容易出现抑郁症状。陈瑶等[23]对云南省12所医学院校就读的护理专业学生进行调查,发现I-HLC与特质焦虑间呈负相关,与焦虑总分间呈负相关;P-HLC与状态-特质焦虑各维度间无相关性;I-HLC与状态-特质焦虑各维度间均呈正相关。此外,HLC也可以预测心理问题严重程度。Tsionis等[24]发现难民在MHLC量表I-HLC维度得分较低,在P-HLC和C-HLC维度得分较高,抑郁症的严重程度与I-HLC评分呈负相关,与C-HLC评分呈正相关,并且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严重程度也与其呈正相关。但这些研究均为横断面研究,不能提供控制点如何随时间变化对个体抑郁影响相关信息,后续在纵向研究中需进一步研究。
3.4 营养管理
营养管理贯穿全生命周期,是健康管理的核心部分,而缺乏营养管理会引起各种形式的营养问题,包括营养不足、超重和肥胖、微量营养素缺乏症等,严重影响个体的健康和生活质量。研究[25]发现,外部健康控制点是营养管理的危险因素,外部倾向明显的个体容易出现超重或肥胖的现象,超重或肥胖女性更容易受到他人和机会的影响,而男性更多地受他人的影响。因此,营养宣教内容的设计和实施应根据健康控制源的人格特征进行调整。对I-HLC人群提供以有关健康行为的特定技能和知识等为主的健康信息,尤其是对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个体;而对P-HLC人群实施的干预方式,则以知名卫生专业人士提供的健康生活方式建议等干预为主,尤其是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积极有效的营养干预方式,反过来也能进一步提高I-HLC,从而实现良性循环[26-27]。此外,在营养管理计划监测方面,倾向于I-HLC的个体能促进营养管理计划成功实施,而倾向于P-HLC的个体营养管理效果不佳。McLaughlin等[28]对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进行调查,发现P-HLC方面得分较高的人因为过度依赖他人,而忽略了自我营养管理的重要性。
3.5 运动锻炼方面
研究[29]表明,HLC与运动锻炼密切相关,能够影响运动锻炼的参与度,常见的健身项目包括散步、步行、快跑和瑜伽等,参与者的I-HLC倾向越明显,个体参与锻炼的可能性更大,并进一步能影响运动锻炼的强度、频率和时间。赵婷婷[30]研究表明,在老年人群体中,与别人一起锻炼的、每周锻炼5次以上的老年人HLC更加内控,每天锻炼1 h以内和参加低强度运动的老年人HLC更倾向于有势力的他人。此外,是否患有慢性疾病对坚持运动锻炼具有重要影响。姜敏敏等[31]研究表明,老年人的高运动量与高水平P-HLC和低水平C-HLC相关,可能与老年人患有各种慢性病,担心运动后出现不适有关。
3.6 物质成瘾管理
物质成瘾被认为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疾病,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常见的形式包括吸烟、酗酒等,然而临床上仍然缺乏有效的治疗药物。Lassi等[32]进行的一项大型前瞻性研究数据表明,外部健康控制点水平高的个体在17岁和21岁时每周吸烟的风险更高,在17岁时危险饮酒的风险更大。Duplaga等[33]开展的回顾性调查发现,P-HLC和C-HLC与过去使用电子烟行为有关。而Mercer等[34]针对心血管疾病患者的研究发现,C-HLC倾向增加吸烟可能性,P-HLC倾向者能降低吸烟的风险,而随着时间推移,较低的I-HLC又与饮酒水平下降有关,这可能由于随着病程的延长,受到医生等其他人的积极影响,从而使P-HLC倾向增强。因此,早期HLC评估为临床预测物质成瘾行为提供了新思路。此外,HLC可用于改善物质成瘾的管理。Prakash等[35]研究表明,酒精依赖症患者的HLC会因为依赖程度发生改变,处于缓解期的患者往往会出现内部控制源,但一旦他们恢复饮酒,可能会恢复到外部控制源,因此在物质成瘾管理时要考虑时机的重要性。也有研究表明,通过HLC倾向的转变也可以促进物质成瘾管理,Soravia等[36]在一项以禁欲为导向的住院治疗计划的研究中指出,在治疗期间饮酒风险高的患者I-HLC得分较低,有必要通过实施健康宣教等积极的干预措施,提高外部健康控制点水平,而高度的外部控制可以补充高度的内部控制,以改善治疗期间的饮酒行为。
4 结语
尽管国外有关HLC在健康管理领域中的研究相对成熟,但国内相关研究较少,处于起步阶段。目前,MHLC是评估HLC最常用的量表之一,但该量表在不同人群的适用性和信效度检验应进一步完善。HLC的横断面研究较多,但应进一步开展多中心、大样本调查,扩大相关性研究,探究其HLC水平的变化特点,真正反映出HLC在健康管理干预中的应用价值。后续护理人员应在充分评估个体HLC的类型和水平的基础上,制定个性化的干预措施,以期改善其心身健康,进而改善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