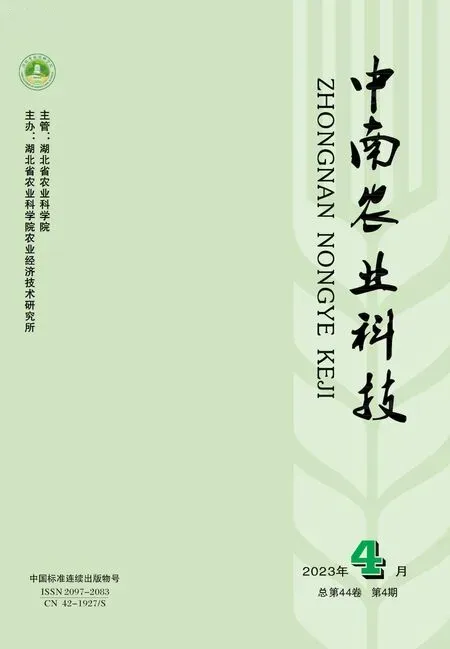畜禽肠道菌群的营养代谢及其代谢产物研究进展
李玉莲,杨雪瑶,蔡翠翠,2
(1.宁夏农林科学院固原分院,宁夏固原 756000;2.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科技学院,陕西杨凌 712100)
肠道菌群是由微生物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它们维持着胃肠道的稳态并通过产生生物活性代谢物来发挥作用。肠道微生物系统作为动物肠道内最复杂的微生态系统,其大量微生物参与其营养物质的吸收、分布、代谢以及机体的免疫,并影响动物生长和健康。肠道菌群的失调可引起多种疾病,如顽固性便秘、炎症性肠病、肠易激综合征和代谢综合征等。因此,了解畜禽肠道菌群的营养代谢及代谢产物,对调节肠道菌群平衡对动物体健康有重要意义。
肠道菌群是研究其在宿主代谢和免疫(包括消化吸收、营养吸收、维生素合成和预防病原体定植)方面的热点领域[1]。其与宿主的相互作用发生在许多层次上,包括复杂的信号通路和一系列微生物来源的生物分子,这些分子可以影响远端组织部位。如大量微生物产生的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可以增加肠道通透性,增加循环中的脂多糖水平,从而导致脂肪组织的低度炎症反应。研究表明,血浆中LPS 水平的增加可以改变内源性大麻素系统的色调,从而进一步改变宿主的脂代谢水平,导致宿主过度进食。多食可促进脂多糖产生物质的生长,最终形成恶性循环[2,3]。因此,肠道菌群与宿主脂肪组织和能量代谢的相关性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本研究探讨了畜禽肠道菌群的营养代谢及其代谢产物的研究内容及进展,以期为相关的研究提供参考。
1 畜禽肠道菌群
动物肠道可为多种微生物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研究发现在动物肠道中存在约500 种细菌,总数量高达1 014 个。肠道菌群是微生物多种群有机整体,肠道微生物与宿主共同构成了相对稳定的内环境,互利共生[4]。有研究发现,肠道菌群的平衡有利于提高动物免疫力,保证动物体的健康。初生动物的肠道处于无菌状态,之后细菌可从动物的口、鼻和肛门进入到动物体消化道内,2 h 便可从其肠道内检测到肠球菌、链球菌和葡萄球菌等需氧菌的存在[5,6]。不同种类动物的肠道微生物与相同动物不同肠道部位的微生物组成及数量均存在差异,日粮、环境、生理状态、遗传因素等均可影响动物肠道微生物的组成及数量。
鸡大约在出生40 d 后肠道菌群达到稳定状态,人大约在出生1 年后肠道微生态环境趋于稳定。40日龄鸡的肠道菌群主要由粪链球菌、大肠杆菌、拟杆菌亚种和乳杆菌属亚种构成,但其小肠内的优势菌群为乳酸杆菌,其次是梭菌、粪链球菌和大肠杆菌;盲肠内梭菌为优势菌属,其次是梭杆菌属、拟杆菌属和乳杆菌属[7]。
43 日龄健康仔猪肠道内的优势菌群以乳杆菌、肠球菌和梭菌等厌氧或兼性厌氧菌为主,其次是双歧杆菌,但其胃和十二指肠内的优势菌群为双歧杆菌,其次为乳酸杆菌;回肠内的优势菌群为双歧杆菌,其次为肠球菌;盲肠内优势菌群为双歧杆菌,其次为小梭菌;直肠中优势菌群为双歧杆菌,其次为乳酸杆菌[8]。
反刍动物的瘤胃微生物复杂多样,包括瘤胃细菌、厌氧真菌、古细菌和瘤胃原虫,还有少量噬菌体,每克瘤胃内容物中细菌数量为1 011 个,约有200 个种类;每克瘤胃内容物中瘤胃原虫105~106 个,覆盖24 个属;此外瘤胃内还存在数量较少,但对营养物质的发酵降解有重要作用的厌氧真菌[9]。
动物肠道菌群可促进宿主对营养物质(维生素、氨基酸、短链脂肪酸等)的消化、吸收和利用,并能够抑制有害菌增长,阻止病原菌、致病菌的入侵,增强宿主免疫功能[10]。不同动物之间肠道菌群组成及数量差异较大,肠道菌群多样性对动物生长以及健康均具有重要作用。
2 肠道菌群与营养物质代谢
在日常饮食中,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是机体消耗的3 种宏量营养素,但它们在体内不是完全被消化。一旦营养素的摄入量超过消化率,就可以逃逸初级消化,机体不能完全消化的饮食中的营养素就会作为微生物代谢的底物,产生发酵副产品,从而影响宿主健康。
2.1 肠道菌群与碳水化合物代谢
由于饮食对肠道微生物菌群变化的影响大,饮食结构与短链脂肪酸(Short chain fatty acids,SCFAs)的组成密切相关。根据微生物群落在营养和生理需求方面的差异,特定的饲粮或促进微生物群落的特定成员,或抑制其他成员。这些影响也可能直接影响SCFAs 的类型和丰度。对小鼠的研究表明,与瘦的个体相比,肥胖个体产生丁酸盐微生物的宏基因组丰度较低。特别是在高脂肪饮食(High fat diet,HFD)饲喂后,乙酸和丙酸产生菌均被抑制[11]。总体而言,高脂饮食降低了肠道细菌的多样性,尤其是那些参与SCFAs 生成的细菌,而高碳水化合物和高纤维饮食则有能力逆转这一效应[12]。在另一项研究中,Tay 等[13]比较了高碳水化合物、高纤维、低脂肪饮食(HC)与低碳水化合物、低纤维和高脂肪饮食(LC)对SCFAs 产生的影响,发现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LC 处理,每种SCFAs,尤其是丁酸盐都显著下降。Fei 等[14]进行了粪便微生物菌群移植和高纤维饮食试验,以研究微生物SCFAs 与宿主糖代谢的关系。无论采取何种干预措施来增加SCFAs 的产生,肠道生态失调得到改善,宿主的健康状况得到恢复[15]。
2.2 肠道菌群与蛋白质代谢
氨基酸分解代谢中,宿主对蛋白质的消化代谢比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更易变,对蛋白质的消化代谢受蛋白质来源、食品加工等因素的影响。氨基酸发酵产生大量的副产物,包括胺、酚类、吲哚类和含硫化合物等有毒物质,但是氨基酸代谢最丰富的终产物是SCFAs[16]。肠道菌群在氨基酸分解的起始步骤中发挥2 种重要作用,即脱氨生成羧酸和氨,或脱羧生成胺和二氧化碳。氨可以抑制线粒体耗氧量,减少肠上皮细胞(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s,IECs)的SCFAs 代谢,因此过量的氨会对宿主产生负面影响。然而,宿主IECs 可以通过转化为瓜氨酸和谷氨酰胺来控制氨浓度,所以尚不明确蛋白质分解代谢的有毒界限。
含硫氨基酸中,含硫氨基酸蛋氨酸和半胱氨酸的分解代谢产生硫化氢和甲硫醇。许多不同的细菌物种在其基因组中均包含含硫氨基酸必需的降解酶,包括芽孢杆菌属、梭状芽孢杆菌属和双歧杆菌属[17]。硫化氢可以甲基化为甲硫醇,然后甲基化为二甲基硫醚,这个过程是解毒过程,因为形成产物的毒性逐渐降低。甲硫醇也可以转化为硫化氢,然后氧化为硫酸盐以进行解毒。硫酸盐可被还原硫酸盐的细菌利用,这是肠道硫循环的一部分。
芳香族氨基酸中,芳香族氨基酸降解可以产生多种吲哚和酚类化合物,它们可以作为毒素或神经递质发挥作用。色氨酸(L-tryptophan,Trp)是哺乳动物必需的营养物质,其内源性代谢物参与肠道免疫稳态和多种免疫疾病。Trp 的分解代谢可以产生色胺和吲哚[18]。吲哚是多种拟杆菌和肠杆菌科细菌产生的Trp 的主要细菌代谢物,在宿主防御中发挥重要作用。苯丙氨酸经肠道菌群代谢可以产生苯乙胺和反式肉桂酸。苯乙胺可以通过促进儿茶酚胺和5-羟色胺的释放提高情绪和能量代谢,但是摄入过量苯乙胺会产生负面影响。有研究表明,苯乙胺在肠道内的产生与克罗恩病的定位呈正相关,与粪大肠杆菌的相对丰度呈负相关[19]。
碱性氨基酸中,肠道内的多种细菌如双歧杆菌、梭菌、乳酸菌和链球菌等可以使碱性氨基酸脱羧形成胺副产物。精氨酸可以通过脱羧作用转化为呱丁胺,还可以转化为其他氨基酸,如鸟氨酸和谷氨酸,谷氨酸可以被脱氨生成4-氨基丁酸(4-Aminobutyric acid,GABA)。组氨酸分解代谢可产生组胺。
2.3 肠道菌群与脂质分解代谢
新鲜水果、蔬菜、豆类和谷类富含膳食纤维,主要由植物多糖和木质素组成。事实上,大多数哺乳动物不能产生消化这些复杂多糖所需的酶;因此,纤维素等纤维组分的降解主要依赖于宿主肠道内微生物的代谢活动。在结肠中,膳食纤维由肠道菌群发酵产生,主要产出SCFAs,包括乙酸、丙酸和丁酸,其摩尔比约为60∶20∶20。每一种SCFAs 都可能是由不同菌株的细菌产生的,由每个物种所包含的相对独特的代谢途径介导[20]。研究表明,在不同的个体内,肠道微生物群表现出独特的模式,可以分为特定的类群,称为“肠道型”[21]。个体肠道菌群的组成容易受许多内外因素的影响,如个体差异、饮食摄入或抗生素暴露等,这些因素可能导致功能电位发生转变,进而影响SCFAs 的产生、组成和丰度。Ang 等[22]将人类样本的粪便微生物菌群移植到C57BL/6J 无菌小鼠中,作为模拟人类肠道生态系统的工具,试图揭示饮食成分与肠道微生物群落成员和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给小鼠喂食不同类型的食物(低脂、高脂和低碳水化合物生酮饮食),然后研究其对肠道微生物的影响。在1 d 的饮食中,不同饮食组肠道菌群的初始结构迅速改变,聚类分析也清楚地区分了高脂饮食和生酮饮食之间的微生物群落。此外,Reijnders 等[23]研究证明,当肥胖人群的粪便微生物群落平衡被抗生素破坏时,粪便SCFAs 的总丰度、类型和分布都发生了显著改变。研究表明,通过基因富集分析,高纤维饮食有助于增加肠道菌群中产生丁酸盐的相关基因,而HFD 在转录水平上可以逆转这些积极作用。这些发现可能进一步揭示了饮食结构如何影响肠道微生物产物,如SCFAs[24,25]。
3 肠道菌群代谢物的作用
机体的丙酮酸主要来自碳水化合物,是糖酵解途径的终产物,在糖、氨基酸和脂肪的代谢联系中起重要作用。宿主肠道微生物可以发酵丙酮酸产生琥珀酸、乳酸和乙酰辅酶A,这些中间产物可以进一步代谢为SCFAs[26]。
SCFAs 包括乙酸、丙酸、丁酸和戊酸,是膳食纤维细菌发酵的产物。SCFAs 通过以下机制促进宿主-微生物群代谢,它们很容易被用作产生宿主内源性代谢物的碳源;作为激活宿主G-蛋白偶联受体(G-protein-coupled receptors,GPCRs)的信号分子,通过抑制组蛋白脱乙酰酶(Histone deacetylases,HDACs)影响宿主基因的表达[27]。SCFAs 可以通过减轻炎症、改善自身免疫性疾病和过敏、维持肠道屏障和介导肠道病原体的定植抗性来增强宿主的健康,调节多个系统的功能,如肠道、神经、内分泌和血液系统。有证据表明,SCFAs 在维持肠道健康、预防和改善包括癌症在内的多种非传染性疾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关键介质直接或间接在机体多个器官和组织中发挥着重要的生理作用。
肠道微生物分解Trp 产生含吲哚的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通过激活调节免疫的配体门控转录因子芳香烃受体(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AhR)来调节宿主免疫系统。Trp 代谢产物对AhR 的刺激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抗炎反应,有助于维持宿主-肠道微生物群的稳态。Trp 代谢物能增加肠屏障功能。吲哚能够通过增加顶端连接蛋白的表达来增加肠屏障功能,从而改善与肠道炎症相关的疾病。5-羟色胺也是肠道微生物Trp 代谢的产物[28]。
次级胆汁酸中,原发性胆汁酸由肝脏产生,以溶解小肠中的膳食脂质和脂溶性维生素。原发性胆汁酸主要循环回肝脏,但其中一小部分胆汁酸(约5%)进入大肠,在肠道微生物的作用下进一步代谢为次级胆汁酸。调节宿主代谢的2 种主要胆汁酸受体是G 蛋白偶联胆汁酸受体1(G protein-coupled bile acid receptor 1,GPBAR1/TGR5)及法尼醇X 受体(Farnesoid X receptor,FXR)。胆汁酸的合成、代谢和在体内的分布是通过胆汁酸、其受体FXR 和TGR5 以及与肠道微生物群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调节的[29]。胆汁酸在脂质平衡、碳水化合物代谢、胰岛素敏感性及先天性免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次级胆汁酸可以驱动肝癌,但也可以维持肠道屏障,防止肠道病原体的定植。
丙酮酸是由膳食纤维细菌发酵产生的,并可以进一步还原生成乳酸。细菌丙酮酸和乳酸诱导小肠CX3CR1+单核细胞向肠腔伸出树突,捕捉肠腔抗原,促进抗原特异性免疫反应,从而对沙门氏菌感染产生抵抗力[19]。乳酸、精胺和组胺对维持肠上皮细胞屏障完整性有重要意义。乳酸通过GPR81 依赖机制促进肠干细胞分化。精胺和组胺通过抑制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样受体蛋白3(NLRP3)炎症小体降低IL-18 水平,从而降低肠道上皮屏障的完整性。
除了SCFAs 外,丙酮酸代谢的最终产物还有少量醇,包括乙醇、丙醇和2,3-丁二醇。醇类转运到肝脏,其中涉及转化为SCFAs 的生理过程,在此过程会产生有毒醛。因此,高浓度的内源性醇被认为是导致非酒精性脂肪肝(Non-a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发生的因素。甲醇可作为甲烷和乙酰产生的底物,乙醇可与丙酸偶联以发酵为SCFAs、戊酸。戊酸是研究较少的代谢物,但已证明它在体外和体内都能抑制癌细胞的生长和某些梭菌的生长。微生物代谢物作为肠道微生物的信号,可以激活或抑制内源性信号途径,或作为宿主细胞的营养源。这些化学信使调节肠道微环境以耐受或不耐受特定的共生微生物[30,31]。
4 展望
动物健康是高效生产的前提条件,对机体的认识长期集中在对营养物质的消化和吸收上,肠道菌群作为宿主重要的生态组成部分,通过多种信号途径在维持宿主代谢和免疫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肠道微生物对宿主某些生理功能的影响已被阐明,但这些研究为随后的研究提供了指导,为克服肥胖和其他慢性炎症疾病的微生物来源干预提供了指导。在众多肠道微生物的积极作用中,维持肠道微生物稳态已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重视,了解畜禽肠道菌群的营养代谢及其代谢产物的研究,对后续维持宿主肠道稳态、改善机体健康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