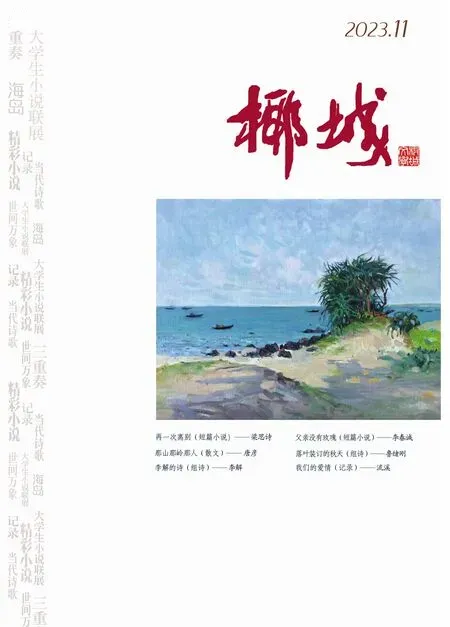爹娘在哪里啊
◎钱翰涛
岁月悠悠,星移斗转,时间的泡浸染白了勃发的黑发,沧桑岁月揉皱了朝气的脸,点滴的亲情汇成绵绵的长河,在我的心间流淌。无限的相思缓缓流过,让我回味无穷,既漾起甜美的笑容,也充满无限的惆怅,也充溢着许多无奈与亏欠。
打开记忆的大门,五味杂陈,神思凝重。爹娘的身影浮现在我眼前,往昔的点滴让我难忘。
我爹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生坎坷,命运多舛。他十一二岁时爷爷就撒手人寰,奶奶一生守寡,母子相依为命。子疼母,母爱子,双方感情深厚。我小的时候常听奶奶说起旧社会那段艰难岁月的往事,用现在人的话来说是忆苦思甜。家里没地,租地主的田地来耕种,还替别人推磨谷子挣点大米,但一年下来还填不饱一家人的肚子,还得挖野菜、翻别人地瓜地找遗落的毛毛根根回家充饥。我爹小小的年纪就很懂事,帮家里干这活干那活,还替地主放牛……说到伤心处,奶奶总是抹着眼泪,我爹坐在一旁也红了眼、低着头,好像沉浸在昔日痛苦的回忆中。最后,奶奶总是说,新社会好,共产党好!小时的我,对旧社会有了多多少少的认识,庆幸自己幸福地生长在新社会里。
解放后,穷苦农民翻身做国家主人,我爹也得以背上书包上学。他聪明好学,学习成绩很好,后来还考上了县重点中学读书。因为家里经济条件差,他上学都带上咸菜、萝卜等自家菜,以此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后来,家里实在没钱缴交学杂费,我爹才被迫退学。那段光辉灿烂的求学历程,我爹常挂在嘴边,常在我面前津津乐道。我听多了就觉得腻烦,反问道:“县中学生又怎么样,还不是回来当农民,还不是没有工资领?”他悻悻地说:“当农民有什么不好,城里人还不是靠农民来养?再说,要不是家里经济困难,我执意退学,说不定我现在就坐在办公室办公呢,你小孩懂什么?”他边说边瞪着我,接着沉默不语,自个儿在一旁抽闷烟。现在想想,我那时说的话太伤他的自尊心了。
我爹第一次婚姻并不如意。听村里老人讲过,我爹年轻时也是英俊潇洒的小伙子,十里八村的姑娘都投来爱意的目光,后来他看上了一个相邻大队的梁氏姑娘,也是我的大娘。婚后,他俩过上了一段甜蜜美好的时光,婆媳关系非常好。
大娘长得虽不能说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但也可说百里挑一、风姿绰约。大娘爱唱琼剧,且唱得也不错,故被选入大队剧团当演员。那时,我爹也算是有知识的人,苗正根红,故被推送到东方八所港工作。当时交通不便,路程遥远,我爹一年下来回来探亲不了几次。大娘留守空房,忍耐不住寂寞,就和剧团一个跑龙套的小伙眉来眼去,日久生情,背叛了我爹。我爹回家探亲知道大娘红杏出墙之事,痛苦万分,毅然和大娘离婚。奶奶劝阻也无济于事,一百个不舍也无可奈何。谁愿意戴绿帽子,谁忍受得了心爱的人与别人投怀送抱?神仙恐怕都忍受不了,何况我爹这个凡人呢。
遭受失败婚姻的打击,我爹并没有倒下。他考虑再三,决定辞职回家务农,照顾好年老多病的奶奶。
后来,我长大懂事了,常看到离婚再嫁的大娘带一些吃的用的东西回来,还和奶奶唠唠家常。曾经的婆媳关系变成了母女关系,两人有说不完的话,唠不完的语。我爹在家时也从不干涉,偶尔也和大娘拉拉几句,只当作一般的走亲戚来对待。他站得端立得正,当然不会旧情复发,更不会关系暧昧。
我爹第二次婚姻不算是一帆风顺。经一个同庚介绍,他认识了同大队的隔河那边村子的一个陈氏姑娘,也是我的生娘。双方恋爱,男情女愿,谈婚论嫁,岂料棒打鸳鸯。娘家人嫌我爹家穷,且是二婚。可我娘心意已决,非我爹不嫁,和娘家人闹僵后偷偷地收衣服跑到我爹家来。娘家人气打不到一处,纠集一帮人拿着木棒跑过来闹起来。骂我爹尖嘴猴腮,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泡泡尿照照自己。他们翻遍家里角角落落找人,可哪里知道我娘已跑到别人家躲起来了。找不到人,娘家人不肯善罢甘休,撂下狠话:生不见人死要见尸。但是,不管怎么闹,我娘已吃了秤砣铁了心,说生是钱家的人死是钱家的鬼。后来啊,生米已煮成了熟饭,娘家人只好承认这门亲事。婚后,我爹虽然心里疙疙瘩瘩,但也尽到了做女婿的一些义务责任。
爹娘一生相濡以沫,恩恩爱爱。在我的记忆中,小的时候爹和娘只吵过一次架,红过一次脸,孰是孰非我也不清楚。只记得那天傍晚我爹大声喝斥我娘,让我娘滚回娘家去。我娘抱着二妹在门外哭哭啼啼,伤心无限。奶奶大声训斥我爹,数落我爹,我爹低着头一言不发,像做错事的小孩那样。要知道,我爹是附近有名的大孝子,自己做对做错被奶奶骂了从不还口。此后,爹和娘再未爆过口角,夫唱妻随,互相关心,互相照顾。我娘干活回家晚了,我爹做好了饭菜后总是站在村边大声喊叫我娘名字,我娘如听到就赶紧回家。娘回到家,爹总是责怪她干活不看时间,不会自己照顾自己,如累倒了谁人知道,谁人看见?要知道,那是丈夫对妻子的关心和爱护啊!
后来,我爹在生命弥留之际,望着我娘很不放心,再三叮嘱我带上我娘到镇上一起生活,照顾好她的衣食起居。我点头应声,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人世。
爹娘一生勤劳俭朴。打我记事起,他俩每天早出晚归,忙忙碌碌。大集体劳动计分时代,他们工作勤勤恳恳,从不偷懒,但一年下来挣得的工分换来的粮食还不够一家人吃。有一年,遇到洪涝灾害粮食减产,全生产队人均分得九斤谷子,劳动力多的家庭还填不饱肚皮,劳动力少且孩子多的家庭更甭提了。
树上知了声鼓噪,家里孩子肚下凹。春天和夏天,午后蝉声大作,我们小孩的肚皮也正在闹空城计。那时,如果能饱餐一顿,满嘴油光,那么真的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可惜,那只是一种奢望。
我家兄妹四人,属于孩子多劳动力少的人家。爹娘为了填饱孩子们的肚皮,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他们顶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险,利用早中晚空余时间苦心经营家里那块自留地,还开荒垦地种种蔬菜、种种地瓜、种种西瓜等等。至今,我还记得地里的西瓜长得滚圆滚圆的,切开来瓤红红的,吃一口香甜香甜的。我爹为了换点钱补给家用,还请几位乡亲一起挑着西瓜爬山越岭到集市上出售。
爹娘辛勤劳作,操持着这个家。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在精打细算中艰难度过。过年了,他俩给四个孩子买新鞋新帽新衣服,买对联、鞭炮等年货,唯独很少为自己买新衣服。
我爹说:“小孩过年开心就可以了,自己穿什么衣服都无所谓,反正不穿打补丁的衣服过年就可以了。”
爹娘想到的是家里人,想到的是为家里节省开支,想到的是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可怜天下父母心呐,他们为儿女倾尽了全部的心血!
他们很疼爱自己的子女,处处为自己的子女着想。
记得我三四岁的时候,大人们都上工了,我套着红色肚兜,在村里转悠了一圈找小朋友玩,可没有找到。我失落地转回家,可大门关上了,只能自个儿坐在门槛前的大石块上玩,玩累了就躺下来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爹娘干活回来了看到此景,把我唤醒,娘还把我抱起来亲了又亲,眼里还泛着泪花,说:“小宝贝真乖,真听话。”此后,为了我的安全,为了我不孤独寂寞,他们出去干活时就把我托付给有孩子的邻居家照看。
还记得,我上小学二三年级时,学校种甘蔗,搞勤工俭学,要求每个学生每天必须挑一担土杂肥料到校。我爹听后就要帮我挑,被我制止住了。他只好挑满满的一担土杂肥倒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让我分多次挑进学校。
中午,我完成任务后就在学校和同学玩,不回家。我爹干活回家看不到我,就跑到学校找我回家吃饭。他一脸怒气、骂骂咧咧。爹大声嚷嚷:“孩子如麻雀般大就干大人活,还要不要人活?”
午睡的校长听到我爹的话后手拿红皮本子,在校门外跟我爹理论起来。我爹据理力争,毫不示弱。双方剑拔弩张,引来不少学生围观。后来,经过几位过路人的劝解,双方偃旗息鼓,草草收场。
当时,我看到此架势,吓得面如土色、瑟瑟发抖,担心校长找我秋后算账。但是,后来那位校长并没有上告,也没有找我麻烦,不了了之。
唉,我爹的做法固然不对,影响不好,但他是爱子心切,心里装的全是孩儿哪!
随着我逐渐长大,后来我得离开家到县城读高中。那时交通不发达,从家里到镇上得翻山越岭走十里路,然后从镇上再乘客车往县城。本来我和同村的一个同学约好了一起上学,可开学的那天,爹执意要送我,说我上学他不放心。
那天,我们起得特别早,爹扛着木箱行李走在前面,我背着包走在后面。走了一段路,我已气喘吁吁,我爹也汗流浃背。我望着他的伛偻的背影,不知怎的,鼻子一酸,眼泪很快地流了下来。我爹回头一看,不屑地说:“年轻人要多锻炼,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再说,我还活得好好的,你哭什么鼻子?”
我连忙拭干了眼泪,紧跟着他继续往前走。
到了学校,我爹给我报了名,安置好了宿舍,然后他再三嘱咐我在校要好好学习,该花的钱要舍得花,然后往车站的方向走去。我望着他的背影不知不觉地流下了泪水。这泪水是感动之泪还是悲伤之泪,我也说不清楚。
后来,我高考落榜回到穷山窝,觉得愧对家人,心情跌入了低谷。这时,爹娘并没有责怪我,而是安慰我。我爹说:“高考是千里挑一的,考不上很正常。人生的路有千万万条,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何必走一条路到天黑呢?人们常说,是金子总会发光。”我娘只是一个劲儿地点头,口里只说对对对。
我爹的话给我指点迷津,给我生活下去的勇气。慢慢地我走出了迷雾,重见阳光。后来,我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再后来,我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回老家的次数也少了。
可是,每次回老家,我总给爹娘买一些吃的用的东西,还给爹娘几百元生活费。特别是带孩子回去时,他俩总是高兴得拢不住嘴,忙前忙后为我们准备一大桌好吃的饭菜,一家人其乐融融。
临别时,他们总是送我们到村口,目送着我们远去,才依依不舍地回去。
随着岁月的流逝,爹娘也越来越老,身体状况也大不如从前了。爹的胃病经常发作,娘的脑血栓病需要吃药来控制。我要带爹到县医院检查治疗,可是他总是说:“小病吃点药就好了,没啥,不必花大钱上医院。你要好好教孙儿,好好教你的学生。”
他心装的是家人,心装的是别人,唯独没有心装自己。他强撑着病弱的身躯,直到病重才无奈地让我送进医院做手术,可已经回天乏术了。
我爹走后,我遵照他的遗嘱,把娘接到镇上一起生活,尽尽儿子的一片孝心,让娘享受一下天伦之乐。几年后,娘除了脑血栓病外又得了老人痴呆症,而且越来越严重,几乎认不出我们了,尽说胡话。有一次,我们不在镇上,她大半夜还搂着被子跑到单位大门口,说是到兴诗村去看琼剧,幸得一位同事看见并拦住了她。我闻讯赶回问她戏好看吗?她说好看,还说奶奶也来了,爹爹也来了。我妻子听了毛骨悚然,我听了暗自悲伤。我知道,娘的大限之期恐不远矣。
我又把娘送进医院,医生说这种病打针也没用,治好是不可能的,你最好带她回家照顾,她能活多久就多久了。
后来,娘瘫痪在床,时而昏迷,时而清醒,且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在老家,我和三个妹妹轮流照顾了近三个月,娘才安然离去。
人们常说,爹娘在,家也在;爹娘不在,家也不在。现在想想,很有道理。爹娘在时,儿女都有牵挂,逢年过节回去探望,相聚聊聊家常,说说心里话,分享彼此的快乐。爹娘不在,儿女们也很少回家或不回家,只是家有红事时兄弟姐妹才相聚在一起。
现在,爹走了,娘也走了,我好像失去了什么,心里一片空荡荡的。回到老家打开斑驳的院门,门庭冷落,落叶遍地,喊一声爹娘,谁人来应答。打开尘封的房门,屋里冷冷清清的,布满了灰尘,撒满了蜘蛛网。
爹娘在哪里啊,孩儿想您们了。通往天国的路宽阔吗,在天国过得称心如意吗,烦恼和忧愁还在吗?捎去的衣服是否收到,烧去的冥币是否入账,建造的纸房是否入住?
爹娘在哪里啊,孩儿有千言万语要对您们说。您们恩重如山,孩儿今生无以报答,如有来世再续父子情、母子情,报答您们的养育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