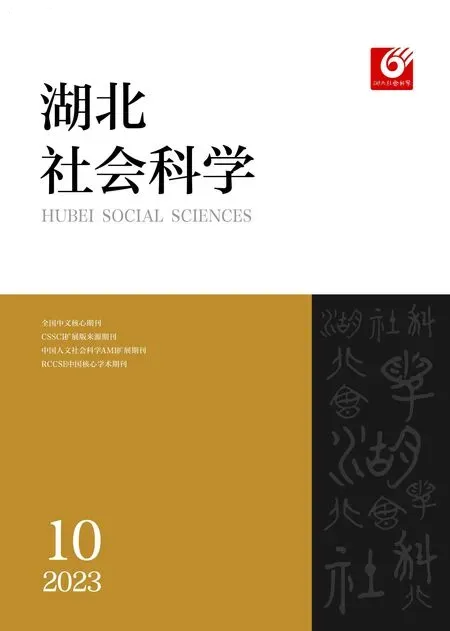西式民主制度的再分配危机
——经济不平等的制度分析
郇 雷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一股市场至上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迎面袭来,伴随着经济私有化、市场自由化、金融弱管制化世界性浪潮的发展,市场在重新焕发活力的同时,社会阶层贫富状况的急速分化也相伴而生。在考察了20 世纪世界经济史的变化之后,英国学者约翰·米尔斯总结说:“在刚刚逝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存在一种退步现象,即从收入和财富分配方面较低程度的分化状况退步到较高程度的分化状况。而那种较低程度的分化状况是人们在20 世纪经过整整四分之三世纪左右的奋斗才得以实现的。”[1](p58)进入21世纪,在当前许多西方国家,社会财富的不平等分配不仅没有得到政治制度与公共政策的限制,反而加速迈向极端不平等并且成为民粹主义、极化政治、逆全球化思潮和新保守主义的渊薮。为此,我们必须要反思长期以来普遍流行的传统民主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西方民主制度受到选民偏好的压力、投票机制的影响,倾向于施行有利于缓解经济不平等的再分配政策,来认识西方民主制度与再分配政策的复杂关系。
一、一种新的政治现实:“新镀金时代”的来临
世界不平等研究机构(World Inequality Lab)长期关注世界范围内长波时间段的经济不平等现象。根据该机构的统计数据,从1980 年到2016 年,虽然全球各地区之间贫富分化发展情况有所差异,但是几乎都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持续恶化的阶段。1980 年以来,世界收入前1%的成人收入增长总额是后50%增长总额的两倍。具体来说,2016年全球收入前1%成人的收入份额为22%,而后50%个人的收入份额仅为10%。而1980 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16%和8%。①参见Thomas Blanchet,et al.eds.,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https://wir2018.wid.world/,最终访问时间2023年5月20日。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通过长时间波的数据测量发现,经济不平等的扩张就像瘟疫一样不仅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盛行,而且也能够在北欧、南欧以及日本这些国家寻找到它的足迹,只是程度不同而已。[2](p241-267)经济不平等的发展几乎是一个全球性现象。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ECOSOC)2014 年提供的一项年度报告表明,“亚洲的不平等现象增加,已经达到与拉丁美洲相近的水平,而拉丁美洲是迄今为止世界上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区域。1990年代期间,欧洲国家(包括俄罗斯联邦和东欧转型经济体)不平等现象急剧增加,而北美和大洋洲国家自1980 年代起,不平等现象显著增加。”②参见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2014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减少不平等,促进可持续发展概述》。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在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经济不平等的增长是极为显著的,而这些地区很长时间以来声称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可以带来民众福祉水平的增长,抑制住非民主国家无法克服的贫富恶性分化现象。现在这种观点正在不攻自破。如果把视角转移到美国和西欧,我们会发现收入差距演变趋势的差异程度更为极端。根据世界不平等研究机构的数据,1980年美国与西欧收入差距几乎无异,收入前1%群体的收入总额均占国民收入的10% 左右,2016 年这一比例在西欧增长至12%,而在美国则增长至20%。同时美国收入后50%群体的收入份额从1980 年的20%下降至2016年的13%。③参见Thomas Blanchet,et al,eds.,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https://wir2018.wid.world/,最终访问时间2023年5月20日。另外,经济政策机构(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研究也表明,1978 年美国大公司执行总裁的薪资及红利是一般员工的26.5倍,而2011年却是206倍。1978年起至2011年,美国执行总裁的薪资及福利增幅是725%,同时期普通员工薪资及福利的年平均升幅是5.7%。④参见https://www.epi.org/research/inequality-and-poverty/,最终访问日期:2023年5月20日。也就是说,在国民经济的“蛋糕”再分配中,经济地位占优势的少数群体相对于数量占优势的多数群体而言具有更强的政策影响力,从而导致经济不平等呈现出制度性的升级趋势。
长期以来,西方自由民主理论一直宣称中产阶级是民主政体最大的稳定器,而且促进越来越多的低下层收入者跨入到中产阶级行列被看作是自由民主体制改善社会总福利水平的最佳例证。但是,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数据,通过比较1983 年至2013 年间高收入者与中等收入者社会财富的中位数之比,就可以看出高收入者所获得的社会财富正在以几乎是十分稳定的速度增加,而相比而言中等收入者的收益则相形见绌。除了个别的时期,如从1989 年至1992 年以及2004 年至2007 年,两者的财富中位数之比都处于上升阶段。总体上看,在1983 年,高收入者的财富中位数是中等收入者的3.4 倍,而到了2013 年则几乎增长了一倍,达到了6.6 倍。⑤参见Pew Research Center Tabulations of Survey of Consume Finances Public-use Data,https://www.pewresearch.org/,最终访问日期:2023年5月20日。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旗帜鲜明地认为,由于金融寡头对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全方位控制,美国的民主正在从林肯所构想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演变为1%的富人所有、所治、所享的政治。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家解释道:“美国上层1%的富人现在每年拿走将近1/4 的国民收入……现在代理人与政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事实上,所有美国参议员和大多数众议员赴任时都属于金字塔尖1%者的跟班,靠塔尖1%者的钱留任,他们明白如果把这1%者服侍好,则能在卸任时得到犒赏。”⑥参见Stiglitz,Joseph E,“Of the 1%,by the 1%,for the 1%”,Vanity Fair,May,2011.约翰·米克尔思韦特(John Micklethwait)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则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是一个天生的“右派国家”(The Right Nation),“过去30 年间,美国的不平等异乎寻常地增加了,在许多方面,这种不平等回到了‘镀金时代’的世界”。[3](p284)糟糕的社会财富分配关系正在恶化美国的民主环境,使得美国民主制度不得不面临新的环境考验。
无独有偶,在大西洋的另一侧,英国也面临着经济不平等持续恶化的挑战。根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的研究,自20 世纪80 年代新自由主义隆兴以来,英国社会总体上呈现出经济不平等逐渐上升的趋势,这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保持着一致性。以收入水平的百分位制来统计,在1980 年,收入最高的10%社会群体收入占英国社会总收入比重达到28.59%,而这一数字到2017 年经过长期的缓慢增长在不知不觉中攀升到了35.46%。中间收入水平的40%社会群体所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则从1980 年的47.92%下降到2017 年的43.93%,这表明英国中产阶层的收入水平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从而威胁到了中产阶层的稳定性。而处于收入水平最低端的50%的社会群体的收入占比也在萎缩,在1980 年时占比为23.49%,到2017 年就缩小到了20.61%。那些收入水平最顶端1%的极富群体则迎来了收入扩张的变化趋势,在1980 年时这部分经济贵族阶层的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6.93%,而到了2017 年则几乎翻了一番,达到了12.61%。①参见https://wid.world/data/,最终访问时间2020年3月29日。著名的国际救援组织乐施会(Oxfam International)在一篇题为“两个英国的故事”的报告中也指出,英国的经济不平等状况已经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在英国,最富裕的五大家族——杰拉尔德·格罗夫纳(Gerald Cavendish Grosvenor)家族、大卫·鲁本(David Reuben)家族、西蒙·鲁本(Simon Reuben)家族、查尔斯·加多(Charles Cadogan)家族和迈克尔·阿什利(Michael Ashley)家族——控制的财富比英国中下层20%的民众的财富总额还要多出1 亿多英镑。而在收入增长速度方面,占人口比重0.1%的富裕阶层是占人口比重90%的绝大多数社会群体的近4倍。②Oxfam International,“A Tale of Two Britains”,参见乐施会官方网站https://www.oxfam.org/,最终访问时间2023年4月15日。
经济不平等的现象在欧洲大陆的法国和德国虽然不如美国和英国严重,但是经济不平等同样呈现出逐步升级的趋势。以社会阶层收入水平的百分制十分位来看,根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的统计,德国收入水平最高10%的社会群体收入在全国总收入中的占比从1980 年的29.23%上升到2017 年的36.76%,而在法国则是从1980 年的30.63%上升到32.99%;德国收入水平中间40%的社会群体收入在全国总收入中的占比从1980年的46.71%下降到44.72%,法国与德国同样保持了相对较缓的下降趋势,从1980 年的45.95%下降到44.61%;而在收入水平最低的50%社会群体中,德国的数据下降同样更为明显,从1980 年的24.06% 到2017 年的18.52%,法国则是从1980 年的23.42% 下降到22.40%;对于收入水平最高1%的极富群体而言,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德国都经历了一个收入占比不断增长的过程,德国是从1980 年的10.22%增长到12.53%,法国则是从1980 年的8.17% 增长到11.15%。③参见https://wid.world/data/,最终访问时间2023年4月15日。这表明,虽然欧陆传统与英美传统存在着较大差异,但是自1980 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同样在德国和法国的社会阶层的收入差距分布中得到了明显体现,即经济收入呈现出不断集中化的特征,社会阶层的经济分化越来越明显。
显然,资本和劳动对再分配政策的影响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平衡,资本在占据主导位置的同时,劳动要素的影响力越来越弱并被边缘化,这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政治经济公共议程的控制密不可分。基于此,哈佛大学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Breeman)指出,过去20 多年,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变得日益普遍和残酷,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要剖析不平等的原因和后果,而是要真正解决不平等的产生机制,提高工人阶级的收入,并且鼓励地方公民组织重新唤醒民主的活力。④参见Richard B.Freeman,The New Inequality:Creating Solutions for Poor America,Boston:Beacon Press,1999.显而易见,这种在财产分配上的贫富鲜明分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关系的表达,而且越来越具有社会支配和政治统治上的意义。
二、经济不平等的制度主义反思
为什么在西方民主政治的决策体制和政策环境下会产生持续性的生产经济不平等?或者从抽象意义上说,西式民主制度与社会阶层财产分配关系是如何相互影响的?需要指出的是,社会阶层的贫富差距和经济不平等是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关注的焦点。事实上,进入现代化的学科分类体系以来,经济学几乎垄断了我们对于贫富分化如何产生以及如何认识的基础知识。在经济学的传统理论看来,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源于市场要素的变化、资源禀赋条件的改变、经济全球化的刺激、科技进步引起的总供求变化、世界金融的发展、对外直接投资(FDI)、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以及财政税收政策变革等方面。①代表性文献参见Gregory Mankiw,“Spreading the Wealth Around: Reflections Inspired by Joe the Plumber”,NBER Working Papers from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Inc.No.15846.Facundo Alvaredo,Anthony B.Atkinson,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The Top 1 Percent in Internation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27,No.3,2013,pp.3-20.Nathan J.Kelly.The Rise of the Super-Rich: Power Resources,Taxes,Financial Markets,and the Dynamics of the Top 1 Percent,1949 to 2008.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77,No.5,2012,pp:679-699.Steven N.Durlauf,“A theory of persistent income inequality”,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Vol.1,Iss.1,1996,pp.75-93.Pandej Chintrakarn,Dierk Herzer and Peter Nunnenkamp,FDI and Income Inequality:Evience From A Panel of U.S.States.Economic Inquiry.Vol.50,Iss.3,2012,pp.788–801.这种基于市场机制形成的逻辑分析存在两个显著缺陷:一是分析主要侧重于经济活动中的生产或交易环节,相对缺少分析再分配领域对于收入差距的重要影响。而这里所说的再分配领域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活动,更是政治活动的重要内容,体现着政治领域内的权力关系;二是由于经济学分析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契约自由假设之上,因此缺乏对于那些经济活动之外的强制性结构要素的分析,也即缺少作为权力因素的有关社会整体性安排的政治制度的分析。
我们在分析民主政治与社会财富分配的关系时,主张采用一种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首先,我们强调作为政治制度的权力因素的重要作用。由于我们关心的是为何在标榜实行民主制度的政治体系内出现了经济不平等日益升级的现象这一问题,所以所谓的政治制度的权力因素限定在民主制度的范围内。显而易见,这种分析带有明显的政治学色彩。我们注意到,现代社会的收入差距问题,越来越多地与个人能力和市场机制之外的公共因素密切相关。一个人处于什么样的财富分配地位,越来越取决于他在再分配领域中的权力关系。简言之,国家运用再分配政策手段调节社会财富在社会阶层中的分布状况,已经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这些再分配手段包括:(1)公共财政中的税收政策、转移支付、公共开支、财政补贴等内容;(2)社会建设领域中的最低工资制度、就业制度、教育体制、养老金制度、医疗保障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等;(3)存在于各行各业中的政治准入门槛制、关于行业垄断以及政治寻租的相关规制;(4)规定行政、立法、司法之间相互关系及其互动规则的制度,在西方国家主要包括选举与投票规则、立法游说制度、选举政治献金制度等;(5)在有些国家甚至还包括移民政策等。这些公权力范围内的相关问题,纯经济学的分析视域很少涉及。正是因为如此,一个由著名政治学者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劳伦斯·雅各布斯(Lawrence Jacobs)、拉里·巴特尔斯(Larry Bartels)等人组成的“不平等与美国民主”(Task Force in Inequality and American Democracy)工作小组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对不断变化的经济不平等,与政治行为、统治机构和公共政策的变化间的联系所知甚少。”②参见Task Force on Inequality and American Democracy,“American Democracy in an Age of Rising Inequality.”Perspective on Politics,Vol.2,No.4,2004,pp.651-666.
在再分配的政治学分析方面,一种流行的理论观点认为,民主制度有助于缓解社会阶层间的经济不平等状况。这种分析以民主社会中选民的理性投票为逻辑起点,强调随着公民政治权利的不断扩展,越来越多的中下层社会成员被纳入选举投票的公民范围。基于这种变化,在一种多数决的民主决策体制下,选民依据理性判断必然在面临再分配政策方案时,倾向于实行那种促进社会财富从上层向中下层转移的再分配政策。①相关文献参见Meltzer Allan and Scott F.Richard,“A Rational Theory of the Size of Government”,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89,No.5,1981,pp.914-927.Jess Benhabib and Adam Przeworshi,“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distribution under Democracy”,Economic Theory,Vol.29.No.2,2006.Cheol-Sung Lee,“Income Inequality,Democracy,and Public Sector Size”,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70,No.1,2005.该理论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向我们展示了民主政治是如何对由市场机制提供的初次分配所造成的经济状况差异进行调解或补偿的,从而达到保护社会免遭因贫富冲突陷入阶层对立的境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流行的民主观点,实际上承认民主政治是祛除经济不平等恶性发展之社会痼疾的良方妙药。
按照既有民主理论的以上逻辑,民主制度的实行对于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分布而言其潜在的影响是,有利于稳定的中产阶级社会的存续。公共选择理论假设在一种两党制的选举环境下,同时假设选民的偏好呈正态分布——即多数选民支持非极端化的中间观点或政策,公共选择学派认为这种状况是民主社会的常态,此时参与竞选的政党为了迎合选民需求,进而赢得多数选票支持,其合乎理性的策略便是提供一套可供多数选民接受和支持的中间化的政策方案。这种多数选民的集体偏好对于选举政治议程的控制,被公共选择学派称为中间人投票定理。[4](p224-225)受中间人投票定理的逻辑支配,传统的民主再分配理论倾向于支持以下结论——民主社会的财富调节政策客观上具有“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激励导向,从而促使形成一种中产阶级化的再分配政治结果。
然而,民主必然导致经济不平等下降的明确观点遭到后来研究者的反对。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等人在2013 年重新检验了学术界讨论已久的民主与再分配、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民主体制被寄予增强再分配效应与减弱公民群体间不平等的广泛期望,但是民主制度所产生的再分配能力是十分复杂的,当民主被社会极富群体俘获时,它的再分配能力迅速下降。当然,民主在特定的时期也会迎合中产阶层的利益期望,民主甚至也会补偿那些在前民主时期利益不被代表或者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而他们的研究却表明,民主对税收(影响GDP的重要因素)具有很强烈的影响,但是对不平等却没有如此强的影响。对于不平等而言,最重要的因素反而是基础教育与社会结构的变化。民主造成不平等增长仅仅在以下情况下才会出现:民主化导致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而这个社会恰好又存在严重的土地不平等所有制以及中产阶层与穷人之间的经济差距微乎其微。也就是说,民主并不会必然导致社会群体税后不平等的统一下降,但会导致财政再分配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从而对不平等产生模棱两可的影响。②参见Daron Acemoglu,Suresh Naidu,Pascual Restrepo,James Robinson.Democracy,Redistribution and Inequality,NBER Working Papers from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Inc,No 19746,2013.
另一方面,一种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中产阶级是民主政治的稳定器,民主政治是中产阶级的助产士,中产阶级与民主政治的这种“亲密关系”在传统的民主再分配理论那里被增添了新注脚。然而,已经有大量的经验数据并不支持传统的民主再分配理论,中产阶级与民主政治的积极正向关系也并没有得到数据印证。一方面,虽然许多发达经济体的民主制度系统完善,但是依然无法阻止经济不平等状况的日益恶化。而且,在那些已经实现了民主转型而迈入民主国家行列的社会里,社会阶层间的经济不平等也并未表现出比非民主政体时期有明显的改观。不管是在先发民主国家还是民主转型国家,都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状况:对于那些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群体而言,虽然公民选举权利得到了宪法保障和其他社会群体的广泛认同,但是其社会经济地位并没有随之产生明显改变。另一方面,在当前多数民主社会,社会阶层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仅仅表现在上层社会与底层社会之间,而且同样表现在上层社会与中产阶层之间。对于自身社会经济地位不满的人群中,既有那些处于生活窘境中的底层民众,也不乏那些被认为生活体面的中产阶层。中产阶层正在成为社会抗争运动的生力军,在他们看来,他们向上流动的机会正在变得稀缺。另外,由于社会财富向极少数富裕阶层集聚趋势的加强,那些处境相对优渥的一般富人阶层也发现他们与那些极富精英的收入差距在拉大。
为了解释和回答西方民主国家缘何出现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现象,我们必须要回到构建起传统的民主制度再分配理论基础的理性选择主义,深刻分析理性选择主义关于阶级投票的逻辑机制,还原复杂社会政治因素和强制社会权力状态下投票逻辑的悖论。
三、西式民主制度下阶级投票的式微
选民的投票选择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自身的经济地位和从政府再分配中获得的福祉?阶级投票(class voting)——选民根据自己的阶级地位来选择支持与其意识形态立场相接近的政党及其候选人,并且反对或不赞成那些显然与其阶级地位所秉持的意识形态立场相左的政党——是投票类型学的主流。传统投票理论认为,政党认同(party identification)——即选民依据其经济社会地位所决定的阶级属性忠诚于认为代表其利益的政党——是解释投票选择的关键性因素。①参见Bruce Miroff,Raymond Sidelman&Todd Wanstrom.The Democratic Debate: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olitics,Boston,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Company,2002,3rd edition,p.192.选举政治提供了不同阶级地位的选民选择所支持政党的机会。政党不仅仅是一个围绕选举而产生并运作的竞选机器,而且政党本身坚持某种意识形态原则和公共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政党的竞选主张和选民的投票决定是可预期的、较为稳定的。比如,在再分配政策领域,不同阶级地位的选民冲突越来越集中地体现在有关国家干预经济的政党性及其范围问题上。左翼政党主张高水平的福利再分配,以及国家对经济的大规模干预;右翼政党则强调自由市场的结果具有福利最大化的特征。
受到阶级投票的影响,公共选择理论认为选民偏好是外生性的且固定不变的,而政党则是回应性的“受动者”,他们通过策略性地选择政治纲领,使自己的政治诉求最大化。因此,在公共选择理论模型中,投票以“议题汇聚”概念为核心。据此,选民选择那些政策倡议与他们自己的偏好最接近的政党,而政党则会制定出能够吸引最大数量选民的纲领。这是一种类似于选举市场(voting market)②参见Arthur Denzau,Robert Parks.“Existence of voting-market equilibria”,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Vol.30,No.2,1983.的结构,选举被视为一种市场机制,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就是通过这种选举政治进行分配的。
理性选择主义的阶级投票理论认为,社会经济因素在选民投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选民运用自由民主体制所赋予的投票权利来表达经济诉求和追求利益福祉。确实,就像传统投票理论所指出的那样,根据克里斯托弗·魏勒岑(Christopher Wlezien)的统计,在一系列所关注的影响投票的因素中,经济问题在选民眼中的重要性一直高于教育、税收、外交和其他议题,只有在经济发展长期保持良好态势时,选民的关注焦点才会逐渐向其他议题倾斜。③参见Christopher Wlezien,On the Salience of Political Issues: The Problem with Most Important Problem,Electoral Studies,Vol.24,No.4,2005.民主的责任政府意味着,民选政府必须要对选民要求改善收入状况的呼声作出必要的回应,由此选民也获得了以经济地位的提高为理由变更所支持的政党及其候选人的正当性。迈克尔·阿尔瓦雷斯(Michael Alvarez)、乔纳森·纳格勒(Jonathan Nagler)、詹妮弗·维莱特(Jennifer Willette)等人的研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们发现,在选民关心的诸多事项中,社会经济方面的信息是最引人瞩目的,经济状况的“风吹草动”立即会在下一次的选举活动中得到反馈;而在政府的经济绩效之外,选民的诉求表达就会降低,他们甚至会容忍政府在某一些方面的政策失当,只要这种政策失当无损于经济状况的改善。①参见Michael Alvarez,Jonathan Nagler and Jennifer Willette,Measuring the Relative Impact of Issues and the Economy in Democratic Elections,Electoral Studies,Vol.19,No.2,2000.
然而,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至少从20 世纪70年代末开始,选民的政策偏好分布逐渐转变,其中最关键的变化,就是传统意义上经济维度上左右之间断层的重要性不断下降,阶级投票的结论遭遇挑战。在很多国家,由于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念的变迁,以及政党意识形态的调整,传统的、以阶级为基础的投票行为渐趋衰落。关于投票行为研究的范式,必然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有的学者就此提出,社会阶级分析虽然没有消亡,但是它的政治意义在下降。阶级属性已经不再那么重要,相反的那些非阶级的社会属性——文化观念的、职业化的、族裔化的、少数群体的权利、个性化的、环境保护的新社会运动议题成为选民关注的焦点。许多学者将这种趋势称为阶级分析范式的衰落或者阶级政治的式微,他们试图用新的范式来解释选民的投票行为逻辑及其公共后果。②参见Terry Nichols Clark,Seymour Martin Lipset,Michael Rempel,The Declining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Social Class,International Sociology,Vol.8,No.3,1993 以及David Harvie,The Death of Class,London: Sage Publications,1996.
让选民从其关注的物质利益中转移目光,或者用选民的其他社会需求来冲淡和降低选民物质利益的诉求强度,是诸多西方政党在长期的选举政治环境中习得的生存法则。关于这一点,美国共和党精英直言不讳地指出:“共和党人在1992 年选举后就已经将他们的竞选的主要观点不再与人们的经济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而是与美国人的政治生活、价值观念挂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共和党人宣称自己代表的是一种最典型的美国生活方式。不仅如此,共和党人还利用美国有很多的教徒,通过宣称党的理念与基督教义的相通之处,获得了美国民众的认同……因此,美国的选举争论焦点就逐渐从经济利益转移到人的价值观念之上”。[5](p159)除了政党的主动性调整之外,有的学者也认为,经济投票的式微是后现代主义价值观时代投票行为逻辑的必然结果。根据政治文化学者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的研究,在发达的西方国家,随着选民代际结构的演化以及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的转型,公民的价值观念序列也会发生显著变化:在工业化社会,传统的选民关注的是经济和人身安全层面的物质主义价值;而在后工业化社会,青年一代选民登上选举舞台,他们更关心自我表现、个性观念、生活质量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6]在英格尔哈特研究的基础上,安东尼·希思(Anthony Heath)等人进一步指出,后工业化社会改变的不仅是公民价值观,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了选民的政治存在方式和集体行动能力。具体来说,后工业化社会的选民丧失了工业化时期的群体性特征,转变为个体化的、符号化的政治身份。作为群体的选民实际上是一种组织化了的“阶级社群”(class communities),他们有组织地形成集体行动,提出群体化的明确政治诉求,对政党形成持续的政治压力。而在后工业化社会,选民成为零散的、飘落的个体公民,不再是“阶级社群”的成员,他们的个性化诉求未经组织就无法形成集体行动,从而也对其阶级属性产生了认同疏离感,政党因此而减轻了回应经济投票的压力。③参见Anthony Heath,John Curtice and Gabriella Elgenius,Individualiz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Class Identity,M.Wetherell (ed.),Identity in the 21st Century: Identity Stud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2009.由此可见,阶级投票能否构成主流的投票行为模式成为一个受到质疑的结论,阶级投票的弱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选民群体通过选票改善经济条件的机会和能力,投票行为与社会阶层收入再分配的关联度也随之被削弱了。
当前,票决民主已经进入到算法时代。而实际上,民主却无时无刻不深受现实条件的塑造。民主一直是在一定的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现实利益的约束下运行的。因此,如果把票决民主的合法性界定为聚合式偏好的形成机制,那么民主的权威一定会受到质疑。在这种情况下,票决民主不得不从票决结果的合理性上退却一步,把自身的正当性建立在投票方法上。如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就认为,既然票决民主的结果与初衷存在严重的背离,那么民主的特性就只能体现在投票这种决策形式上了。“我认为,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一个决策是通过投票作出的,参加投票的人数高于一个最低标准,投票人没受到胁迫,那么,这个地方就实现了民主。”[7](p14-15)也就是说,如果承认票决民主的投票方式的话,也必然承认投票悖论的存在。在此意义上,达尔也指出现代选举民主制只能存在于理想状态,而在经验层面上选举民主只能接受某种牺牲。虽然说,选举民主制无法实现公共偏好的最大化,难以满足选民的集体愿望,但是反过来看,“这些制度已经足以使政府不至于强制推行那些受到多数民众反对,并且会积极运用自己被赋予的权利与机会来加以颠覆的政策”。[8](p223)所以,投票悖论意味着民主无法形成有效的多数决策,它使得民主只能去为那些损害多数偏好的决策出台制造障碍。
如果说形成有效多数决策的票决民主是标准意义上的民主的话,那么只能依靠票决方式而不是票决结果构建起正当性、只能对损害多数偏好的决策起抑制作用的票决民主,只能算得上是最低限度的民主。
四、经济不平等的民主制度实质
“新镀金时代”的现实需要我们重新梳理与认识民主票决机制下政治经济的互动关系。传统的民主再分配理论,将不同社会阶层围绕再分配政策展开的投票竞争视为一种稀释了的、调和式的选举活动,实际上忽视了不同社会阶层影响和控制政治议程的资源不平衡性、能力以及集体行动的差别。西方民主政治虽然从宪法法理上赋予了公民平等的投票参与权——传统的民主再分配理论就是以这种“一人一票制”的平等权利为逻辑起点,但是不同社会阶层基于利益而展开的政治斗争充斥于票决选举的整个过程以及选举之外的其他政治领域,在这些领域中所谓的公民平等权利荡然无存。
近年来,关于美国经济不平等的研究兴起反映了学术界对传统的民主再分配理论的质疑。拉里·巴特尔斯(Larry M.Bartels)对美国近年来的经济不平等状况做了深入考察,从政党政治、阶级政治、公民投票偏好等层面解释了票决体制下政治制度导致经济不平等分配加剧、社会阶层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①参见[美]拉里·巴特尔斯:《不平等的民主:新镀金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伊恩·夏皮罗(Ian Shapiro)则将民主与分配的关系视为民主理论研究的新课题,他试图解答“为什么随着普选权的逐步扩大,反而出现了收入分配差距加剧的现象?”其解释维度主要包含三个层面:一是为什么政治家和政治精英不愿意提供更多的惠及底层群众的公共政策?二是为什么底层群众并不期待从民主政体的政策制定中获取更多利益,反而能够忍受不平等的增长?三是不平等的加剧对民主政治的运行带来哪些损害,这些损害本身是否抑制了民主制度的再分配能力?②参见[美]伊恩·夏皮罗:《民主理论的现状》,王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罗伯特·达尔(Robert Alan Dah)则针对美国的政治实践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在一个成人几乎均可投票,但知识、财富、社会地位、与官员的接触和其他资源都不平等分配的政治系统中,谁在真正统治?”[9](p3)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D.Putnam)提醒我们,“谁在统治”和“统治得怎么样”是政治学的两个基本问题。③参见[美]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榕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政治系统论的倡导者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也认为,政治系统的一般特征在于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并用强制力保障其实施的行为或互动行为。④参见[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而在政治系统的强制性结构中,衡量社会成员权力地位的标准在于政治影响力,政治影响力是观察社会成员权力地位的重要标尺。而政治的现实,正如所言:“所有政治体系普遍公认的特征之一是,政治影响力的分配是不公平的”。而这种政治影响力的差异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政治资源分配的差别;二是个人使用政治资源的技能和效率的差别;三是个人为政治目的使用资源于不同方面的差别。遵循达尔的逻辑,在民主制度所提供的规则面前,不同个人或群体受到以上三种差别的影响必然表现为政治影响力的差异。①参见[美]罗伯特·A·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陈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传统的民主再分配理论很大程度上否认了社会成员的这种差异,忽视了隐藏在民主规则背后的政治权力不平等。在这一方面,正如舒姆彼得所观察到的:“在一个社会中,各种集团各有不同的利益,那么,应以谁的利益为主?政治斗争就是说服某些集团,使他们相信他们所认为的利益并不真正比其他利益重要。也可以说,政治斗争多少可以看成是粗暴地使用权力来压服一个集团,使它的利益服从另一集团的利益。不言而喻,政治还包括讨价还价,搞妥协。不过,这并不是真是未受过专门训练的普通人在那里动脑筋,企图从某一纠缠不清的社会政策问题的杂乱价值中推论出一个真正的‘公众利益’来”。[10](p34-35)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丁·吉伦斯(Martin Gilens)搜集了美国自1930年大萧条之后联邦和州政府的立法和政策制定资料,发现作为多数的选民并没有真正影响立法和政策制定的能力,公共政治主要反映了美国最富裕10%的精英偏好,尤其是最富裕1%的偏好。所以,所谓“中间选民定理”以及中产阶层的民主的论调在现实中都是不存在的。②参见Martin Gilens,Affluence and Influence:Economic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Americ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国内学者的研究也持有相类似的观点,“在西方民主国家,经济不平等被政治因素所强化,而不是被修正。基于分配政治在公共民意、政治参与、政党政治与政府回应性四个领域的最新研究,可以发现经济不平等导致政治不平等,而后者进一步加剧贫富差距,进而形成动态的经济不平等陷阱。”[11]也就是说,在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社会阶层收入差距悬殊化的情况下,民主并没有通过民众权利的行使矫正或控制这一局面。
社会财富再分配实质上是由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生产关系及其由这种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政治关系来实现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系统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分配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分配正义观。他认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资料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12](p436)观察社会财富再分配,既要从这个社会所规定的国家与法的关系上来理解,更要看到现实的物质生产过程。“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13](p524)因此,社会财富再分配既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既存在所有制的决定性,这种决定性又受到政治权力关系的巩固。当然,政治权力关系也不是消极地、被动地、完全地反映经济所有制的全部情况,它试图影响甚至是调整经济所有制的结果。所以,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是经济社会运行的一种基本规律,而传统的经济学对于社会分配问题的研究却忽视了这一点。林德贝克就指出:“新左派批评了传统经济学家忽视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特别是,据说传统经济学家回避了经济中的权力分配问题及其对国内外政策的影响。特别是传统经济学家还被指责说,他们倾向于暗示社会中存在着某种‘社会平衡’和‘和谐’,从而掩盖了个人之间、集团之间和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权力斗争这种现象。”[14](p29)
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为我们理解西方国家为何在自由民主体制下产生了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现象提供了理论基础。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不平等首先是私有制决定的,经济不平等的增长如果长期得不到制度性的补偿或调整,那么就会带来社会结构的破坏性变迁以及阶层矛盾的升级对立,从而对民主制度的运行带来坏的“社会资本”。这样,就形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不平等与民主制度的一种互动逻辑:在一种不被约束的自由化的经济环境里,人们在市场中的地位取决于其实现资本繁殖能力的差异,虽然自由民主体制赋予了选民通过普选权来限制资本拉大贫富分化的机会,但是这种机会也是受到限制的,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当下,作为抑制资本自由化繁殖的机制——政府决策、劳工力量、人民权力、社会运动等——都被削弱了,都被看成是不正当的或不适宜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美国经济不平等有着深刻的政治根源,其中公共政策、政党政治、利益集团等要素在影响美国收入和权力分配上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它们之间又相互关联,彼此作用。”[15]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自由民主体制的再分配能力必然受到资本主导的政治经济结构的决定性影响。以此来观察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就会发现,危机的持续深化不仅没有冲破资本的权力结构,而且使得资本的自由化得到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化的论证。相反,自由民主体制在这场危机中深受其害,丧失了调整社会阶层利益冲突的功能和话语优势地位,而不得不自受其辱,转向保守主义、民粹主义、逆全球化浪潮的港湾寻求庇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