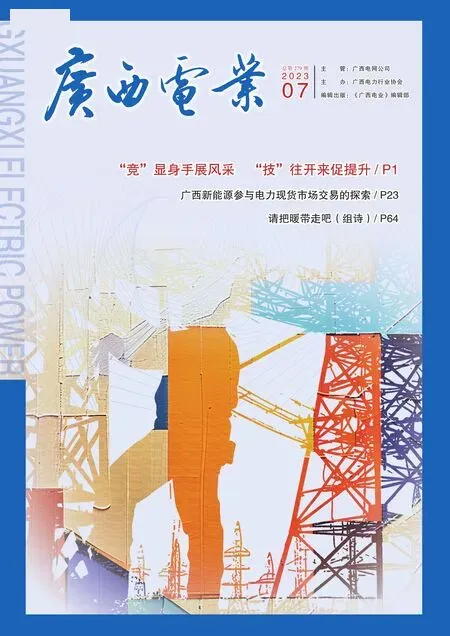请把暖带走吧(组诗)
姚 瑶
疼痛
三年前,我们在埋葬奶奶的坟山地
亲手埋葬了你,你羸弱的身体
却藏下人世间所有的黑。我含着眼泪
狠心地填下泥土,一同埋下的
还有三十多年的亲情,旧事
三十多年的情感
轻如一纸风筝,轻轻一拽
线就断了
三年前,我栽下的桔子树
已经挂果。记得小时候
你一瓣一瓣地,喂给我
我也一瓣一瓣喂你
此刻,在我手里也有一瓣桔子
可我,再也无法喂给你
像一剂苦药,我怎么也咽不下去了
桔子树栽在你的坟边,原想
可以为你,遮挡毒辣的太阳
长势很好的桔子树,茁壮的根系
一定伸入了你的体内
伸入你体内的,肯定还有
一起长起来的杂树杂草
疼了吗?父亲,你一定很疼
每到清明,我都在你的坟头上
覆上一层新土,狠狠把那些杂草
掩埋。我动作很轻,生怕
不小心压疼了你。而我自私的做法
反而让杂草,长得更加茂盛
什么时候,你才回来
在尘世间的某个角落,与我
再次相遇
一场雨过后,杂草又长满了你的坟头
我恨这隐晦的天气,雨水多
适合万物生长,却长不出你
父亲,请理解我,我没有办法
让你重新,像一株桔子树一样长起来
生锈的镰刀割破我的手指,疼
破烂的瓦砾划伤我的脚踝,疼
钻心的痛。你不在了
我们离开了老家,你孤零零守着
那栋被雨水潮湿的老屋
还有,我一直以来潮湿的心
黄昏
我端坐在村头的晒谷场
黄昏,影子拉得很远
猫在树枝里的夕阳,像我此刻的心情
一点点坠落
从村头到村尾
那些低矮的木房,斑驳老去的岁月
父亲的脸也模糊不清
那头老牛,是不是迷失了回家的路
从某栋木屋传出来的笛声
击破小溪的浪花
遥远的声音,带给我
无数温暖的颜色
吹笛者早已作古,坟头长满了野草
穿透岁月的笛声,在某个黄昏
抵达,内心的苍凉
与哭泣无关
父亲过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我偷偷躲着哭泣,深夜
经常从梦魇中醒来,然后大汗淋漓
想父亲生前的很多场景。我那些
干瘪的文字,不能描述梦中境况
只能任泪水,盈满我的眼眶
我一直认为,这是父亲深夜归来
在山上劳动,打着哈欠
带着满脸的倦容、委屈或许还有责怪
他还调皮地把手伸进我的被窝,嘿嘿的笑
我从梦中笑醒
我一直想给父亲写一首诗,透明的文字
可以解救我,日渐消沉的心情
多少次,父亲在梦中打断我的一厢情愿
我要写给父亲的祭诗,还遗留在故乡
在那块干瘪的土地上,没有生根发芽
我有着幽怨的眼神,女儿都快七岁了
我吝啬自己的眼泪,生怕在孩子面前
丢脸。假装的坚强,心里藏着的哭
逃不过孩子的眼睛
我咬着嘴唇,克制。每次从梦中醒来
我都像小孩一样偷偷哭到天亮
失眠
夜,静得听见黑的声音
埋葬祖先的后山,磷火闪过我的梦境
无人照料的坟头,寂寞、孤独
他们的后人,正在千里之外
挥霍着时光
我是在夜幕降临时刻抵达圭研
打开手机百度地图,信号消失
偌大的版图上,我找不到熟悉的字眼
是谁把我,一脚踢回了圭研
像只小狗,可怜巴巴
再一次,我迷失在自己的故乡
翻遍我的电话号码簿
那些名字全部陷入陌生
我知道,我的躯体已经被钉在床上
我瞬间拥有了强大的夜晚
一根时针,划破黑夜的帷布
露出失眠的两只眼睛
诡秘地笑。在黑色的屋子里
我不知道门在哪里
窗外是生养我的植物
黑夜到来的时候
早已经进入了睡眠
连牛都反刍三遍了
黑夜,如约而来
黑夜,如约而来,滑入我的记忆
陈腐的味道,弥漫在小屋里
我的心情,泡在来苏水里
还没有醒来。来不及
说出最后的一句话
父亲的咳嗽声,在那个黑夜里
显得异常的持久,让我心酸
一口痰,卡在前世的喉咙
钟摆,孤零零的静止在墙上
并且落满了灰尘
墙的背后,挡不住时光流走
一匹调皮的马驹,不知疲倦
从两年前,跑到现在
父亲去世的时间里,泪水
侵蚀了我的诗行
这是怎样的一种血缘?我一直不懂
我们都没有文傻子的魅力,会让父亲
紧锁的眉头,绽开太阳
文傻子可以不计时间成本,陪父亲
整整一个下午,甚至深夜
父亲守着泥土的故乡,像文傻子一样
把寂寞和孤独,装进透明的玻璃瓶子
一同装进去的还有,溪水干净的灵魂
然后一声不吭,老去
醉酒者
他就这么坐在路边石凳子上,整整一个下午
耷拉着脑袋,闭着眼睛,身上弥漫着酒气
偶尔说几句胡话。当然,没有人注意
说了些什么?谁会去关注
一个醉酒者的呓语,当然
也没有人去关心,路边的醉酒老人
那个下午,我是个例外
我就在对面的凳子上坐着
我生怕,一不小心他就跩在地上
我得耐心守着他。就在那个下午
一个醉酒者遭遇了一个醉酒者
这个醉酒者让我强烈思念另一个醉酒者
我突然觉得眼前的他就是父亲
父亲经常这样,坐在路边或者是故乡的田坎上
姿势一样,但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老是醉酒
酒里的苦和辣,能否渗入我的脾脏
渗入我的血液,这样我与父亲的距离会更加近
我常常以醉酒的方式,与父亲握手
我们同病相怜,我们同仇敌忾
我们是酒场上的生死兄弟
眼前的醉酒者,我真想走过去扶起他
与他握手言欢,每当看到父亲那般年龄的醉酒者
来苏水的味道,留在房间
长久被尿毒症折磨,父亲的遗像
慢慢老化,失去颜色
如父亲钙化的双肾。有许多爱
还藏在昨天,或者更加远的以前
又一个春天逝去,又一个黑夜来临
我和父亲,仿佛短暂的相遇
刚启幕,便坠入深渊
在那间小屋,黑压压的夜色
关闭了我所有的呼吸
文傻子陪父亲坐了一下午
文傻子什么都不懂,和父亲一样的孤独
父亲抽烟,文傻子围着父亲转圈
用手去接父亲抖下来的烟灰。他们就这样
傻乎乎呆一个下午,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
父亲不说一句话,整整一个下午
就这么看着文傻子,傻笑
我离开故乡后,亲人们陆续离开
陪伴父亲最多的是文傻子,只有他
才不会挪开故乡一步,连乡场都没有去过
像屋后那株老得蜕皮的古树,懒得动一下了
也只有他,深刻理解父亲的孤独
很多时间,像死一样沉默
偶尔父亲会讲故事给文傻子听,当然听不懂
偶尔父亲会唱歌给文傻子听,当然听不懂
文傻子听不懂,但他会傻傻的笑
只要文傻子笑,父亲的眉头就绽开一轮太阳
我都有一种冲动,这样的幻想持续了两年
父亲已经离开我两年,我常在酒醉后痛哭
把眼泪当着酒,咽下去
父亲怎么老是醉?是不是
父亲把生活的苦,当成了酒
父亲的镰刀
父亲说过不太喜欢调皮的孩子,比如我
当然,我也不喜欢父亲
父亲忠厚得有些过分,经常吃亏
有些傻蛋的父亲,要求我也像他一样
人本份一点,像株庄稼老实生长
父亲总是喜欢在黄昏里
默默无闻,在屋檐下磨镰刀
像一架生锈的机器,机械、迟钝
我无法用诗歌来形容父亲
当然,也无法形容我的人生
镰刀磨得再锋利,甚至可以吹断一根发丝
也是无法收割自己的,比如我
这株不成气的庄稼,总是漫不经心
父亲这种愚笨,无限传染着我
我知道视死如归的决心:一刀斩断
自己年轻的几年,迅速把自己送到中年
诸如我现在,也步入中年
才理解父亲当时的心境
肉体、生命的赐予,父亲给了我茁壮成长的躯体
也给了毫无掩饰的丑,一个丑小孩
在阳光下玩着泥巴和多余的时光,我的目光
只有巴掌大的天空
从不夸大其词,父亲磨着生锈的镰刀
要割断两辈人的恩怨
父亲在墙上,挂着
对面就是他不争气的孩子
哗啦啦落下的白霜,父亲安然看着我
眼睛都不眨一下,微笑着
仿佛一下,天黑了
如多年前,在屋檐下磨刀的情景
一转眼,天就黑了
来得太突然,剧烈
请把暖带走吧
父亲说,天气凉了
把这些木炭,这些暖带走吧
父亲从炭窑里爬出来,他的痰
比木炭还黑。咳嗽声
刺痛整个冬天的喉咙
我粗鲁拒绝了父亲的好意
双脚踩在城市钢筋水泥上
渗入骨头里的寒,挂在眉毛上的冰
后悔没有带上父亲的暖
请允许我在空调房里,烧一钵炭火
暖,会让我找到天堂的火柴
故乡,往西三十米的坡地
每一次走上那块坡地,都要弯下腰
以几何角度亲近土地,四十五度还是九十度
取决于山的陡峭,这类似于向父亲鞠躬
冬天萧条、辽阔,泥土更加寒冷。被砍伐的树木
所有的荆条伸向我,整个冬天
我躲在自己收敛的身体之内
把心包裹,在故乡往西三十米的坡地
渐次打开,毫无保留
我知道,我已经被故乡抛弃
父亲也在抛弃我。他像多年前
毫无经意剥去手上的老茧、死肉,剥去的还有
我们对他的思念,在故乡往西三十米的坡地
只要一弯下腰去,距离土地越近
越接近父亲
深夜的风声
母亲说,风这么大,一定是你父亲
跟在风的背后,回来了
大风把屋檐吹翻,肆无忌惮
还有一阵阵狗叫声。母亲说
狗看得见亡人的影子
那些风声,像尘世间的哭泣
低沉、幽怨,丝丝入扣
在圭研,我有用不完的时光
尽情挥霍深不见底的无聊
深夜,我在那扇木窗口前面
发呆,看风吹过田野、溪畔、树林
父亲就在不远的山岗上,守着磷火
他一定与萤火虫较上了劲
他不服输,他肯定会在风的后面
匆匆忙忙走回苍茫的人世间
他撵着那些狂叫的狗,滚远一点
最好在视线之外。风很大
他依然轻轻的替母亲擦去,腮边的泪痕
父亲一生忠厚,连风都不愿意打扰他
他小心翼翼,生怕得罪任何人
哪怕是无影的风。他悄悄跟在风的背后
悄悄来到我们身边,连梦都是
悄无声息
父亲的泥土
翻耕的,种植庄稼的泥土
潮湿的,养育一家六口的泥土
最后,父亲埋进了泥土
没有出走的,没有流失的泥土
还遗留在故乡。父亲珍惜泥土如口粮
口粮一样的泥土,像糯米团一般
困住父亲悲苦一生,父亲老在故乡
埋葬父亲那天,天空下着雨
我埋下泥土,埋下瘦瘦的父亲
狠狠地埋下父亲的前世今生
我眼泪汹涌澎湃
我要用一生的泪水,洗去
父亲卑贱的、屈辱的、无望的
生命劫难
埋下泥土,埋下父亲的口粮
小心翼翼,生怕
打扰了父亲,打扰休息的父亲
轻些,再轻一些,或许这样
父亲会有一天醒来
然后翻耕泥土,种植庄稼养家糊口
但是,父亲已经无法伸出粗粝的手
捧一把泥土,奔跑在田野之上
或许,父亲不愿意醒来
他怕看见,天空下着的雨
淋湿我不争气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