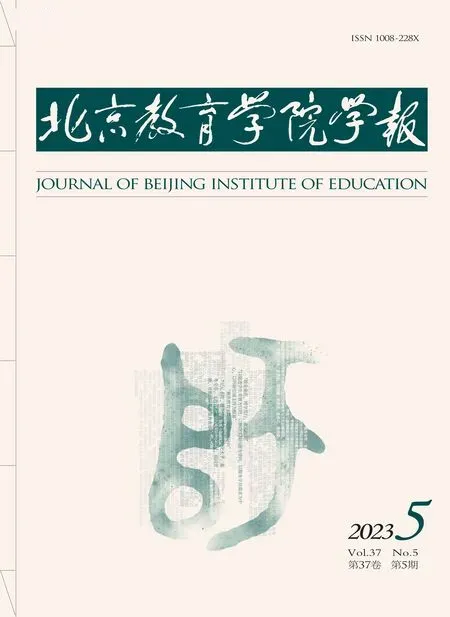两宋国子祭酒的教育贡献
黄一庆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上海 200062)
有宋一代,重文轻武、官吏繁冗、党争不断,使得朝廷国力衰微,“兵多而不能战,财用竭蹶而不易支持”[1]140,因此,急需各类人才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情势,朝廷遂寄希望于教育,积极推动教育改革与发展。北宋经过三次兴学以及科举考试制度调整与完善,建构了以四书为核心的经学教材体系,以张载、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著名教育家涌现,产生了以理学教育思想为主导、各派教育思想争鸣的局面,以书院和私塾为代表的私学得到快速发展。而国子祭酒作为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最高长官,对教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史料记载,两宋国子祭酒官员共163人,其中包括判监61人、国子祭酒92人和大司成10人。(1)宋初国子祭酒并不常设,国子监主要由朝廷派差遣官管理,其名称有判国子监事、判国子学事、判监事、判国子监、权判国子监、同判国子监、管勾国子监(公事)、管干国子监、同管勾国子监和提举国子监等,本文将以上种种差遣官名称统称为“判监”。大司成,全名辟雍大司成,后改名为太学大司成,始设于崇宁二年(1103),于宣和二年(1120)被废除。大司成地位和职务与国子祭酒基本相同,因此也将大司成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与判监、国子祭酒一起统称为国子祭酒官员。他们继承自唐以来作为国子监最高长官的角色和引领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使命,在坚持贯彻落实尊儒重文教育政策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中央官学建设、科举制度改革和地方教育发展。目前学界虽已关注到两宋国子祭酒官员的价值,并对此官职的沿革、职责、选任标准以及任职官员的基本信息进行了考证和分析,但忽视了国子祭酒官员在宋代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有鉴于此,本文以国子祭酒官员为研究对象,通过系统梳理他们在推动国家教育指导思想转变、促进国家教育体制的形成与完善、推动国家教育重心下移等方面的作用与价值,总结概括其对两宋教育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一、推行尊儒重文的教育政策
(一)推动儒学发展变革
五季离乱,儒学中衰,伦理纲常被破坏。逮至宋有天下,借国子祭酒官员之力,颁布并落实崇儒诏令,复兴传统儒学。宋太祖首次视学时即诏国子监画先圣、先贤像,以判监崔颂监之,并撰赞书于孔、颜座端。崔颂又聚徒讲学于国子监,得太祖所赐果酒,开国子监讲学之先。太宗、真宗和仁宗主持修孔庙、理经籍、刻石经。江阴至圣文宣王庙重建完毕后,范仲淹特为作记,载“荡荡乎惟道为大,如斯而已者也”[2]424;孔维、邢昺和孙奭先后主持九经、《孝经》《论语》《孟子》《尔雅》等文本校勘工作;田况知成都府时,为蜀石经增《公羊》《谷梁》二传,补其九经之缺,等等。
经过宋初几朝的复兴与发展,新儒学逐渐形成。其中,以二程洛学、张载关学和王安石新学最为强盛,一时呈三足鼎立之势;[3]6后随着神宗至徽宗三朝文教改革的推进,荆公新学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神宗时期,王安石同判监吕惠卿等人发起熙宁兴学运动,认为“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莫肯承听,此盖朝廷不能一道德故也”[4]907。神宗遂颁行王安石《字说》及其与王雱和吕惠卿共同编撰的《三经新义》,使之成为当时学校教育的教材和科举考试的唯一标准。哲宗和徽宗二帝力图延续、推广熙丰之制,敷扬神宗之志。借此之机,国子司业龚原奏请,重新颁行《字说》,并鼓动天下学子传习。“一时学校举子之文,靡然从之”[5]11152,“自是先儒之传、注悉废”[6]375。可见,北宋中后期,在国子祭酒官员的推动下,传统儒学向新儒学转变,特别是荆公新学,渗透进文教改革诸层面,使官学教育内容和科举考试标准无不以之为依据,在北宋中后期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内长期占据统治地位。
迨夫靖康之难,北宋覆灭,荆公新学跌下神坛;后赵构即位,聚宋室、立南宋,待宋金和议、兵戈偃息,即绍休圣绪、始复文教。当时程颐、王安石之学争执激烈,高宗出于稳定政局的需要,不取程、王之学,而以传统儒学为尊,亲自书写六经与《论语》《孟子》,并将其“刊石于国子监,仍颁墨本赐诸路州学”[7]2747。此时国子司业高闶正重定太学考试制度,遂规定太学私试首场试“大经义三道,《论语》《孟子》义各一道”[7]2746。高宗至宁宗嘉定前,在国子祭酒官员的助力下,传统儒学仍占据主要地位,并被落实到国家文教体制的建设中。这使得北宋中后期衰落的传统儒学重获生机,却阻碍了新儒学的发展,特别是程朱理学思想,在庆元党禁时期陷入沉寂。
但在民间,仍有部分国子祭酒官员坚持传播程朱理学思想。例如,“南夫子”林光朝“通六经、贯百氏”“以伊、洛之学倡东南”[5]12862。又如刘爚早年受学于朱熹,至嘉祐初方受诏回京执掌国子监。此时恰逢朝廷政局发生巨变,刘爚遂抓住时机,先后多次上疏请开伪学禁、颁行其师朱熹四书,并要求将其与白鹿洞书院学规一起引入太学。自此之后,朝野上下推崇程朱理学之声愈演愈烈,宁宗追谥周敦颐、二程和张载;理宗下诏,列周敦颐、张载和二程从祀。国子祭酒官员纷纷敷扬其说,徐鹿卿任南岸军学教授时,了解到周敦颐、程颢和理学大师杨时门生张九成皆讲学是邦,遂摭其说,申明理义之学。江万里特创宗濂书院,专祀周敦颐。在国子祭酒官员的共同努力下,程朱理学成为南宋中后期朝廷的御用哲学,并对元明清三朝的文教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颁布文教政策,形成尚学风气
国子祭酒官员通过多种方式,推动颁布一系列文教政策法令,在社会上形成尚学风气,笼络士人读书入仕,彰显文治盛世。其主要内容有:第一,广开科举取士之路,在竭力保证科举公平公正性的同时,给予远方苦寒之士特殊优待。依照国子监旧制,所举参加科举考试的士人中如有无户籍者,需要京朝官担保。同管勾国子监梁适极言此举对远方寒士不利,称他们因路途遥远,抵达汴京时已近秋试,又人生地不熟,难以求保。朝廷遂扩大可保任官员的范围,“在铨幕职、州县官,非伎术、流外及历任有赃者,并听为保”[8]3138。第二,降低国子监招生标准,将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大门向普通民众敞开。开宝八年(975年),国子祭酒官员向朝廷建议,允许“未入于籍而听习者,或有冠裳之徒不居乡里”[7]2742补监生之缺,旨在打破国子监只招收品官子弟的规定。庆历二年(1042年),为解决士庶子弟冒称品官子弟的问题,王洙等提议,专为八品以下至庶人子孙设立四门学,取消了国子监招生标准中官品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教育平等。第三,开展各类文献的整理工作。史书方面,有冯元修《三朝正史》,王洙校定《史记》《汉书》,孙奭发起《后汉志》的校勘和雕印工作等;诸子文献方面,孙奭主持校定与雕印郭象注《庄子》和陆德明所撰《庄子释文》;文集方面,李昉等官员采前代文章之精要,编纂《文苑英华》;类书方面,李昉等官员受命编纂《太平御览》,“杂采经史、传记、小说,自天地事物迄皇帝王霸,分类编次”[9]968;书目方面,张观、宋祁和王洙等官员受命校定馆阁书籍,以解决书籍谬滥不全的问题,书成名曰《崇文总目》。总之,在国子祭酒官员的助力下,图书事业大兴,大量文献被重校、刻印、颁行,特别是北宋四大类书,在此时皆已成书。
二、变革科举取士之法
(一)考试内容侧重策论和经文
宋初朝廷在继承前朝科举制度形式的同时,也继承了其取士重诗赋、轻策论的观念,导致考生“只务雕刻之工”“不晓经义”[10]5286“不近治道”[10]5291。为解决此问题,统治者多次颁布诏令,强调取士要重经术和策论,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转变重诗赋的取士之法,科场风气一如从前。因此,国子祭酒官员逐渐意识到,必须全面革新科举制度,通过制定全新的贡举条例以确立经术和策论的首要地位,才有可能恢复科举为国家选拔治世之才的功能。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率曾任国子祭酒的宋祁等人掀起庆历兴学运动,开始对科举考试内容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为强调经术和策论的重要性,降低诗赋的地位,他们遵循“先策论过落,简诗赋考式,问诸科大义之法”[11]316的改革思路,提议进士科帖经、墨义并罢,先策论后诗赋,且“诗赋论于九经诸子史内出题”[11]318。该提案很快得到了落实,但实行不久即被废除。此后虽有如判监吕公著上言“乞令第一场试论,第二场试策,第三场试诗赋”[12]346,但都并未得到落实,科举考试内容依然维持旧制。直到熙宁兴学,王安石领导判监吕惠卿等官员再次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规定仅进士科和明法科接收应举考生;进士科完全删除诗赋内容,仅以经义和策论取士。此项改革措施虽然在熙宁兴学结束之后有所变动,但是其重经术和策论的核心理念被继承了下来,使得经学教育在学校教学中的占比大幅提升,甚至在熙宁兴学和崇宁兴学时期,太学只设置经学课程。
(二)考试制度强调发挥学校的教育作用
宋初,朝廷重科举而轻学校,官学的发展情况极其糟糕。中央官学仅有国子监,而且监生多系藉不至,导致国子监教学作用无法发挥;地方官学则由于没有朝廷颁布兴学诏令,更是一片空白。国子祭酒官员遂试图利用科举来发展官学教育,听读日限制度就此产生。
听读日限制度最初是国子监的一种教学管理制度,由王洙于庆历二年提出。当时,为恢复国子监的教学功能,王洙向朝廷提议,学员须在监内学满五百日,并参加每月举行的两次考试,按照考试排名获得解试资格。该提议一经施行即挽回了国子监的颓势,提高了其教学水平。鉴于此,宋祁等人在庆历兴学期间将此制度向地方官学推广,规定地方发解的举人需是在学的本地籍贯生,并且要在地方官学内学习一定时日。在此制度的影响下,士人纷纷涌入地方官学,极大地促进了地方官学的发展。仁宗朝听读日限制度虽一度废止,但出于维持学校教学活动的需要,后又恢复,不过对其进行了调整,如对听读时间满规定期限和不满规定期限的学生采取不同的取解之法、缩短听读日限的时长等。可见,由国子祭酒官员制定、实施的听读日限制度,在科举和学校之间建立了必要且稳定的联系,即通过改变科举报考资格的方式,强制要求考生进入官学学习。此种做法保证了官学在校生员的数量,使学校教学活动得以正常开展,充分发挥了学校的教育作用。
三、振兴中央官学
如上所言,宋初中央官学的发展状况并不理想,不仅讲学久废,而且学官多由品官子弟充任。为振兴官学,执掌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政令的国子祭酒官员,试图打破建国以来国子监只招收品官子弟的既定规则,将关注重心放在面向一般士人的中央官学。其中,以八品以下及庶人子弟为教育对象的太学,经过一系列改革,逐渐取代国子学,成为宋代中央官学实际上的最高学府。[13]150
(一)规范太学的教学、教材、官员选拔制度
1.推行太学三舍法
庆历兴学时期,随着国子监入学人数的增加,其教学空间狭小的问题愈发凸显。判监王拱宸等人遂请求将接待外使所用的锡庆院改建为太学。虽然该提议随着范仲淹的离朝和反改革派人士对新政的抨击而落空,但在仁宗的主持下,太学还是得到了扩建,即以马军都虞候公廨为太学,并置内舍生二百员。这标志着太学结束了与国子学、广文馆和律学共用国子监二百楹的境况,开始拥有独立的教学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太学内舍生的设立表明三舍法在此时已显露苗头。
熙宁四年(1071年),在神宗的大力支持下,王安石同判监张璪、常秩和吕惠卿等人掀起熙宁兴学运动,开始正式推行三舍法,即将太学分成外舍、内舍、上舍三部分。外舍生成绩优良者升入内舍;内舍生成绩优良者升入上舍;上舍生学行卓异者由主判直讲荐之中书,得免乡试、省试,直接补官。四年后,由于熙宁新政的改革措施有损在朝权贵的利益,加之旧党人士的强烈反对,王安石被罢相,三舍法也随之被搁置,但神宗锐意改革的决心却并没有因此动摇。元丰二年(1079年),他颁布由曾任判国子监事的李定与张璪、蔡京等人拟定的太学教学法,史称“元丰法”(又名“元丰学令”)。“元丰法”以法令的形式将三舍法固定下来,并在延续原有规制的基础上完善升舍考试制度。此时,张璪正判国子监事,贯彻“元丰法”的诸项内容,将三舍法真正落到实处。太学由此迎来第二个发展高峰。自此之后,宋代太学的改革基本上都是对“元丰法”的补充和完善。例如,崇宁兴学时期形成学校升贡制度和南宋时期重建、调整太学教学考试制度。其中,南宋太学教学考试制度的重建和调整主要是在国子祭酒官员的领导下完成的。南宋初年,太学因战事一度停废。直至绍兴十三年(1143年),随着宋金战事的缓和,朝廷开始着手重建太学。此项重任落在了当时尚任国子司业的高闶身上。他在沿用北宋“元丰法”的基础上,根据当时国家教育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太学课试法和补试法,搭建起了南宋太学教学考试制度的大体框架,为南宋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注重教材建设
宋代太学自设立之初,就以经学教育为主,其教材的编撰、整理和选择工作都有国子祭酒官员的参与,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北宋建国到熙宁八年(1075年),教材以传统儒家典籍为主。此时,唐末五代战乱初定,传统儒学典籍逸散问题和内容疏漏、错编问题严重,导致教材的规范性和权威性严重下降。鉴于此,朝廷多次委托国子祭酒官员对其进行校勘。建隆三年(962年),判监崔颂等上新校《礼记》释文;开宝五年(972年),判监陈鄂与姜融等人校《孝经》《论语》《尔雅》释文。[9]410端拱元年(988年),孔维受命主持校勘《五经正义》,并于七年后告毕。但是,由于判监李至认为其义疏和释文还有讹谬之处,祭酒邢昺遂接管《五经正义》的校定工作,主持“校定《周礼》《仪礼》《公羊》《谷梁传》正义,又重定《孝经》《论语》《尔雅》正义”[9]413,并在咸平二年(999年)校勘完成。次年,此七经校定完成并被颁行官学,标志着十三经正义正式成为太学法定的经学教材。[14]5自此之后至天圣八年(1030年),朝廷反复对上述典籍进行重新校定和刻印。如景德二年(1005年),邢昺协同两制官员再次详定《尚书》《论语》《孝经》《尔雅》文字;天禧五年(1021年),由于刻本年久失修出现文字错漏,朝廷从管勾国子监刘崇超之请,派官员重新校定、刻印诸经。总体而言,宋初儒家典籍的大规模校勘工作,经历校刊释文、校刊《五经正义》、校刊七经疏义和重校重刊四个阶段。[15]48在此期间,国子祭酒官员数次主持儒学典籍的校勘工作,解决了教材错漏百出的问题,提高了教材的规范性和权威性。
第二阶段从北宋熙宁八年至南宋嘉定初,“熙丰法”和“元祐法”交替进行。所谓“熙丰法”,是指《三经新义》在熙、丰时期取代部分传统儒学典籍,成为太学的官方指定教材和科举取士的唯一标准。这使得当时士人纷纷学习荆公新学,传统儒学典籍被逐渐荒废。面对此种情况,朝廷在元祐时期听取有国子祭酒任职经历的范纯仁和吕公著等官员的建议对其进行了修正,太学教材兼容传统儒学典籍与《三经新义》,即为“元祐法”。此后,朝廷交替使用“熙丰法”和“元祐法”:哲宗亲政至北宋灭亡,使用“熙丰法”;南宋建国至嘉定四年,使用“元祐法”。
第三阶段从嘉定初至南宋灭亡,程朱理学典籍成为太学教材。嘉定初年,随着庆元党禁的解除、韩侂胄等反道学派人士的下台以及提倡道学的史弥远拜相,复兴程朱理学的时机逐渐成熟。以刘爚代表的一批理学臣子遂不断向朝廷建言“以熹所著《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之说以备劝讲”[5]12171。对理学思想充满热忱的理宗采纳了此提议,下诏赞朱熹四书集注“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5]789,并将其颁于太学。这标志着程朱理学著述“首次成为官方指定的学校教材”[16]212。从此,周敦颐、张载和二程等程朱理学奠基者的著作逐渐进入太学。
3.优化学官选拔制度
宋初朝廷极其看重学官的资质,反复强调学官须“儒术该博、士行端良”[8]1373,并任用以邢昺、孙复为代表的一大批硕学鸿儒。可惜好景不长,随着国子监的衰落,朝廷选任学官的标准大幅降低,至真宗末期,国子监学官完全沦为品官子弟之初仕者转阶的工具。这种转变使得学官群体的学术素养出现断崖式下滑。为扭转这一局面,国子祭酒官员屡次向朝廷提议严选学官。如李至在淳化五年(994年)奏请进廷规定学官由京朝官任职,以经术教诸生,希望通过抬高学官的准入门槛来保住学官群体学术素养的下限;叶清臣在康定元年(1040年)上奏,“今后国子监学官有缺,令本监官于外任州县幕职官内,举实有文行者充”[17]3752;吕惠卿在熙宁年间乞选“通经术、晓政事之人主判太学,令侍从举有学术行艺者为教授”[18]2041;南宋徐侨与司业许应龙建言,学官选任应当以“资格”为先。
除了提高学官选任标准外,国子祭酒官员还积极向朝廷举荐德才兼备者充任学官。范仲淹推举文学素养深厚的李觏、“宋初三先生”中的孙复和胡瑗等人充任学官;在张璪的推荐下,杭州州学教授梅灏等人被任为国子监直讲;高闶推荐曾“掌进读书史,讲释经义”[5]3815的陈夔为权太学录、“临安府府学教授林大鼐权国子正”[19]2418、熟悉条令和用例且文字功底深厚的魏元若为权太学博士、学识渊博且深谙经术的师维藩为学官。
(二)推动其他中央官学建设
1.更改武学教学管理制度
在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的影响下,南宋武学自建立之初即陷入窘境,屋舍颓弊,甚至全无士人。为振兴武学教育、吸引士人入学,朝廷听取杨椿的建议,放宽升舍标准,岁终预校定的外舍生公试合格即可升补。该方案虽使得升舍人数增加,却没有扭转武学发展困境。直到孝宗临政,由于其意图兴兵北伐,武学遂受朝廷重视,就补人数和生员数量随之增加。这使得武学招生额度紧缺与补试人数众多之间的矛盾、升舍标准太宽与在学人数增多之间的矛盾凸显出来。为此,程大昌提议提高补试报考条件和升舍标准,规定武学下省人和兵部曾请解人亦需同待补生参加补试;外舍有校定人公试入上等、第一次公试中下等但再试入中等的校定人、私试四次入等且无大过的曾经在学满三季以上且参考入上等者,方可升补。然此法所定的升舍标准太高,两年仅升舍一员,挫伤了学生的积极性。芮烨遂请恢复杨椿旧制,却使得烂进之弊复现。鉴于此,朝廷决定折中杨椿和程大昌之法,规定公试入上、中等者皆可升补。自此,武学考试制度大致成型,直至南宋灭亡。
2.详定律学条例
熙宁兴学时期,朝廷颇重刑名之学,遂听取吴充的建议改革明法科,并为之配律学,颁布由国子监详定“课试条约及应合节次试行事件”[6]2791,主要内容有:以命官和举人为招生对象,入学向国子监投纳家状,举人额外需要两位命官保任;学生先听读、再补试,补中者给食,未补中亦可以留学听读;补试考试科目有断案、律令和大义,其中断案试案一道,律令和大义试大义五道;实行公私试制度,每月一公试、三私试;公试分断案和律令大义,断案考试如补试法,律令大义试律令三道;私试三者皆考,其中案一道,刑名三到五件,律令大义两道;日常教学内容为讲律,每日一条。该律学条例一经颁行,就成为定制,直至北宋灭亡。可以说,由国子祭酒官员主持制定的律学条例对北宋律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3.制定画学补试法
出于对绘画的喜爱,徽宗于崇宁三年(1104年)创办画学,实行三舍法,“入学条三年,经大比,定夺等第,方分三舍”“以五十人为上舍,十人为内舍,其外舍止各十五人”[7]2802。与之配套的补试法却迟迟未制定,直到崇宁五年,在大司成薛昂的提议下,朝廷才下令国子监详酌立法。次年,国子祭酒官员上补试法,对报名、考试和出榜等流程进行了规定:考生向考官出示公据或有一名命官委保,并投纳家状和试卷,审核通过后,即可参试;参试考生被分为士流和杂流,二者的考试内容除试画外,士流还需“试本经义二道或《论语》《孟子》义”[7]2802,杂流则诵小经三道或读律三板;录取标准为先经义、后作画,“取文理通者为合格,俱通者,以所习画定高下”[7]2802。自此,画学的教学管理制度搭建完毕,一直实施到大观四年(1110年),在画学并入翰林图画局后才被废除。
4.推动在京小学设立三舍法
北宋在京小学的发展极为缓慢,至元丰末“止有就傅、初筮两斋,差教谕一员,即无立定官吏并直学等”[7]2761。直到政和四年(1114年),在大司成刘嗣明等官员协助下,朝廷才仿照太学,为在京小学立三舍法。其主要内容为:根据学生的年龄及其对经书与文字的掌握情况,将其分为外舍、内舍上下等和上舍上下等五个程度不同的等级;每一季度开设一场考试,考题从大经和小经中出,其中大经出三十、小经出二十,成绩在七分以上即为合格。除此之外,在京小学三舍法还有两条特殊规定:一是若低等学舍的学生对经书和文字的掌握情况已经达到高等学舍的要求,无需考虑年龄,随及补等;二是如果遇到能写文章但诵经不达标的学生,国子监需要通过考试的方式对其文理掌握情况进行考查,文理稍通者补内舍上等,优异之人补上舍下等。其具体考核方式为:考本经义,采取封弥制度,博士只有考校权力,最终决定权归国子监管理人员。可惜的是,在京小学三舍法仅实施了九年,就被中书省以有害乡举里选为由废除,但其在小学教育上的价值不可忽视。
四、发展地方教育
(一)建设地方官学
如前文所述,宋初朝廷对地方官学并不重视,导致地方官学数量稀少、规模狭小,其建设基本上靠地方长官的自觉。例如,孙奭在天禧五年(1021年)知兖州时,在文宣王庙内修建学舍,其日常花费基本上均由己出;回京后为防止州学废散,还特意奏请给兖州州学置学官和学田。宋人将此作为宋代州学之始,“本朝国初未建州学,乾兴元年(1022年)兖州守臣孙奭私建学舍聚生徒,余镇未置学也”[7]2762。又如,范仲淹在景祐二年(1035年)到任苏州,在“南园之地”[20]776建学,聘请孙复和胡瑗来此任教。后人评价,“天下郡县学莫盛于宋,然其始亦由于吴中,盖范文正以宅建学,延胡定安为师,文教自此兴焉”[21]828。总的来说,宋初地方官学整体上处于一种低迷的状态,其建设主要依靠以国子祭酒官员为代表的一批重视教育的地方长官通过自行建学的方式完成。此举虽未能对地方官学的发展起到实质性的帮助,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特定区域内地方教育的发展,同时也让他们了解到地方官学的困境,促使他们回京后竭力上奏朝廷发展地方官学。
正是由于国子祭酒官员的力谏,北宋地方官学才得到大规模兴建和增扩。庆历兴学期间,在范仲淹的主持下,原任判监的宋祁等人制定了一套详实的地方办学之法:各级地方行政单位都必须建学;无法建学舍的州县,暂以文宣王庙或者官衙场所代之;教授由路转运司及本属长吏于幕职州县官内选任,或者令举人推选品学兼优之人担任。值得一提的是,该法还照顾到了僻远小郡,考虑到它们难以独自立学,规定由转运司代管。可以说,该法直接推动了北宋地方官学发展进入繁荣期,是“宋代州县学校全面建设发展最重要的法令”[13]197之一。
自此之后,北宋地方官学大兴。前往地方任职的国子祭酒官员纷纷响应朝廷的号召,致力于兴建地方官学,发展地方教育。张璪任缙云令时,为改变当地儒士稀少、百姓尚未完全开化的现状,他召集民众上山伐木以修建学舍。学舍建成,来者甚众。陈襄任浦城主簿时,恰逢中央发布兴学诏令,遂召集当地富人,要求他们出资建学。学校建成后,他亲自入学讲授,远道而来的学者数百人;任职陈州时,他亦扩建当地学舍,亲自入学讲解《中庸》。葛胜仲任兖州州学教授时,学舍破败,师生日常饮食无法得到保证。为此,他上书当地转运使,得三十万建学经费后重修州学,“学校之盛,遂冠一路”[22]22。
(二)开办私学,讲学授徒
宋代国子祭酒官员大多学术造诣极高。他们凭借自己深厚的学术根柢,出于为国家培养人才或传授学术主张的目的,开办私学、讲学授徒,培养了一大批硕学鸿儒,弥补了官学教育的空白,推动了文化知识的传播和国家教育的发展。
经学家孙奭作为宋初颇负盛名的私学家,在进入仕途之前跟随后唐同光三年(925)的科举状元王徹学习。王徹死后,孙奭继之,为求学者讲解经书的微言大义。学者叹服,登门求学者日众。当他入朝执掌国子监时,称赞时任国子监教职的贾昌朝讲学有师法,并特意致信提点,希望他向唐宰相路随、韦处厚学习,研读儒家经学,将经术作为其一生的志业。贾昌朝不负所望,通晓经术、大公无私,从国子监教职一路升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死后被英宗冠以“大儒元老”[5]9620之名。
天圣四年(1026年),范仲淹丁忧回乡,受应天府知府晏殊的邀请,担任南京应天府教职。任教期间,他以身作则,对学生严格管理;讲授六经,鼓励学生勇于发表自我见解;以自己的文章作为范文,训练学生书写各类体裁文章的能力,推动南京应天府书院“成为北宋第一书院”[23]26,并为北宋培养了一大批经学家和文学家。值得一提的是,范仲淹在此期间与“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孙复结下一段师徒之缘。考虑到孙复因赡养母亲而无法潜心在书院内求学,范仲淹决定聘其为书院学职,并时时给予指点。孙复不负所望,钻研经学,终成为一代《春秋》学大师。
在理学发展过程中起承上启下作用的杨时,在政和年间来到无锡,建立东林书院,招收弟子,传授二程学说,为程朱理学思想在南方的传播铺平了道路。南宋建国后,他选择退隐山林、著书立说、讲学授徒。南宋经学大家张九成、东莱先生吕本中和五峰先生胡宏等人皆从其学,“东南学者推时为程氏正宗”[5]12743。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国子祭酒官员在担任地方官职时亲自教导当地学生,向他们讲解儒家经书中的微言大义,培养学生忧国忧民的思想意识。例如,沈季长响应朝廷以经术为先的号召,在担任南京国子监教授时亲自为诸生讲解群经之理,引导他们理解群经内涵,造就当年“礼部岁所贡士,多公弟子”[24]53的盛况,助力北宋走出“国人多不知学,学者多不知经”[24]53的困境;北宋词人葛胜仲任教兖州州学期间,每日与学生谈论经文,并作《策问》十七篇,给学生讲授法律、官制和教育等内容;南宋文坛领袖江万里知吉州时,仿照白鹿书院创建白鹭洲书院,亲自为学员讲学,并聘请欧阳守道来书院任教。
五、结 语
综上可知,两宋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离不开绝大多数国子祭酒官员的参与。他们因循既定职守,在振兴官学教育的同时又超越自身职责,关注与人才培养相关的诸项事业,改革科举制度,发展地方教育,促使国家指导思想由传统儒学向理学转变,助力国家教育体制的形成与完善,推动教育重心下移。面对宋初儒学衰微的情势,以师儒之道立世的国子祭酒官员怀着尊崇儒术的思想诉求,在朝野之间通过修孔庙、理经籍和刻石经的方式复兴儒学,同时又顺应时代发展需求将传统儒学改造为理学,并通过改科举、兴学校、谏诤言、编教材和讲学授徒等方式将理学融入国家教育体制,先后将荆公新学和程朱理学推上国学神坛,使得国家指导思想从传统儒学向理学转变;国子祭酒官员在保持以科举和学校为核心的国家教育体制的基础上,通过改革科举制度、发展中央官学和兴建地方学校的方式改变重科举轻学校的做法,将科举与学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又试图将学校从科举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进而推动国家教育体制的形成与完善;为帮助国家摆脱教育衰微的困境,国子祭酒官员打破以权贵子弟为主要教育对象的制度限定,在科举层面广开取士之路,保证科举的公平公正性,优待远方寒士,以吸引大批士庶子弟入仕,在学校层面开设专以八品以下及庶人子弟为招生对象的太学,并通过三次兴学运动,使太学成为国家实际上的最高学府,将国家教育的大门向平民百姓敞开,推动教育的平民化、大众化。总之,国子祭酒官员有着强烈的作为国家最高教育行政官员的角色意识,肩负着引领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使命,为两宋教育思想和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推动宋朝成为我国历史进程中的又一个文化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