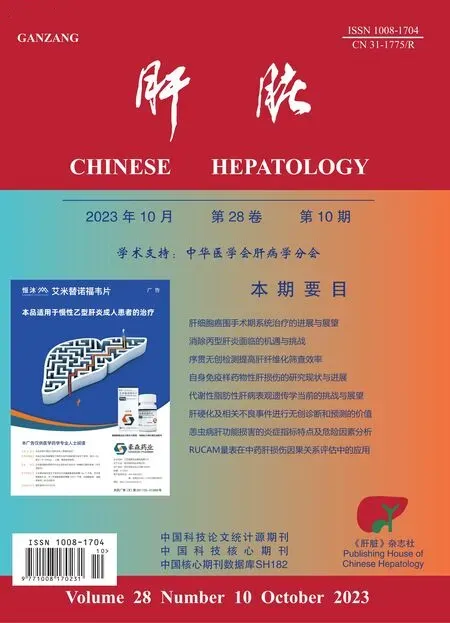自身免疫样药物性肝损伤的研究现状与进展
次白 邓晓玲 侯淑惠 徐可树
药物性肝损伤(drug-induced liver injury, DILI)是由各种不同类型的化学药物、生物制剂、传统中药,以及各种保健品、膳食补充剂和代谢产物乃至辅料等所引起的肝毒性损伤的总称。根据化合物的作用机制,DILI可分为固有型药物性肝损伤、特异型药物性肝损伤和间接型药物性肝损伤[1]。其中,一种较为复杂的亚型为自身免疫样DILI(autoimmune-like DILI,AL-DILI),进展缓慢,体内可能出现多种自身抗体阳性,可表现为类似自身免疫性肝炎(auto-immune hepatitis,AIH)的特征,故在临床上难以与AIH鉴别[2]。
根据现有文献和临床经验,有学者将AIH和DILI 的关系分为3类:合并DILI 的AIH、药物诱导的AIH(drug induced auto-immune hepatitis, DIAIH)和免疫介导的DILI(即AL-DILI)3种类型。其中第一类为已经明确诊断为AIH的患者出现DILI;第二类为患者本身有轻微AIH 的表现,但不能确诊或者有AIH 的易感因素,因为服用药物后出现典型的AIH,停药后仍有AIH表现,并需长期的免疫抑制剂治疗;第三种为药物诱导的具有AIH 血清学和组织学特征的肝损伤,通常在初始停药和保肝治疗后缓解,并且没有复发,大多无需长期的免疫抑制剂治疗[3]。由于DIAIH与AL-DILI都因服用药物导致,并均有AIH的血清学和组织学特征,有学者将两者归为一种疾病。2022年3月在欧洲召开的DIAIH国际专家共识会中,全球有30多位专家针对DIAIH如何分类界定、不同亚群的定义以及相关临床管理等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讨论,然而,目前无准确定论。由此,本文将重点阐述AL-DILI的发病机制、导致的药物及其特点、诊断、鉴别诊断和治疗等,以期帮助临床医生对AL-DILI有全面的了解。
一、发病机制
AL-DILI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目前可总结为新抗原的形成、遗传易感性、免疫耐受性受损和性激素影响等多个方面。
(一)新抗原的形成 与经典的AIH发病机制相似,AL-DILI的发病机制可能是针对自身的误导性免疫应答所致。细胞损伤释放的药物-蛋白质加合物可作为半抗原被宿主免疫系统识别,与特定人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HLA)蛋白结合形成新抗原,而后去激活CD8淋巴细胞,对新抗原敏感的B淋巴细胞进一步产生参与药物代谢的细胞色素P450的抗体,从而导致肝细胞凋亡。药物代谢物还可以抑制肝细胞小管外排转运蛋白,如胆盐输出泵,导致细胞内胆汁酸浓度增加,损害线粒体。线粒体损伤可以激活内在的凋亡途径,从而使半胱天冬酶裂解肝细胞的染色体脱氧核糖核酸并诱导细胞死亡,同时影响基因的锰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的宿主特异性多态性,促进线粒体释放活性氧,进一步加剧肝细胞应激和凋亡[4]。
(二) 遗传易感性 遗传特异性也是AL-DILI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遗传特异质型DILI与个体组织相容性抗原、药物代谢酶和转运体等方面的遗传多态性密切相关。两大类基因的多态性:编码抗原呈递蛋白的6号染色体上主要组织相容性位点中的高度多态性基因,以及编码药物代谢酶的各种多态性基因,与AL-DILI的遗传易感相关。并且可能有几个遗传位点同时发生突变导致DILI的发生,包括药物代谢酶突变和组织相容性分子突变等[5]。最近,Masaru等利用全基因组相关联研究衍生的风险等位基因信息为DILI制订多基因风险评分(polygenic risk score,PRS)[6],揭示了该病存在与每种特定药物的化学性质无关的共同DILI易感性。研究发现在PRS值较高的受试者中,参与线粒体和蛋白质翻译的基因失活率较高,并指出DILI易感性是由于肝细胞中的几种生物学途径引起,包括氧化应激和未折叠蛋白反应[6]。因此,研究AL-DILI的遗传易感性需要对单个药物的整个生物学途径进行分析。
(三)免疫耐受性受损 大量研究证据表明,特异性DILI通常取决于个体的适应性免疫反应,由HLA多态性和其他决定新抗原(半抗原肽)呈递的因素决定[7]。在很多情况下,独特的HLA类型是对反应性代谢物或母体药物免疫反应的重要决定因素,但大多数具有特定药物相关风险HLA单体型的患者不受药物暴露的影响,这表明还涉及其他因素。因此有学者提出适应性免疫系统在特异性DILI的发病机制中起主要作用[8]。适应性免疫系统可被半抗原激活,从而限制HLA编码的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MHC)蛋白对肽类加合物的呈递。在极少数情况下,药物可能直接与某些MHC分子或T细胞受体结合,并激活免疫反应。药物或其代谢产物在肝脏中的近乎普遍的应激作用达到或超过剂量阈值,可能会导致低于检测阈值的肝脏损伤,或与轻微的丙氨酸转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升高相关,并随着持续接触药物而消失。因此,抑制最初毒性应激的适应性反应的发展,可能会抑制其进展为显性肝损伤。理论上,这种适应可以在肝损伤的任何迹象出现之前或在最开始检测到免疫介导的肝损伤之后(ALT水平无症状升高),被称为临床适应。因此,AL-DILI导致的明显的肝损伤可能是因为免疫耐受受损所致[5]。这种假说也在动物模型中得到验证,并且该研究认为恢复耐受性可能是DILI的治疗目标[9]。这些理论对未来AL-DILI分子机制研究和治疗提供了思路。
(四)性激素的影响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的AL-DILI发生于女性,同时女性患者表现出更严重的肝脏损伤,高达90%药物性肝衰竭患者为女性,发生药物性肝损伤后需要肝移植治疗的女性患者显著多于男性患者,这都提示我们性激素可能在药物性肝损伤的发展中发挥作用[2]。也有学者认为女性的细胞色素CYP3A活性和底物清除率增加,这一发现表明女性可能存在基于性别的代谢差异,影响代谢物的产生,女性免疫反应增强可能会将这些代谢物作为新抗原,并诱导免疫介导的肝损伤[10]。Thomas[11]等建立了一个实验性的雌性BALB/c小鼠模型,具有类似于患者免疫介导的DILI的特征。在此模型中,他们发现白介素-4启动的CD4+T细胞直接针对细胞色素P450 2E1的表位,并诱导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和肥大细胞浸润。但其具体关系目前尚不明确,未来仍需更多的实验数据来证明。
二、导致AL-DILI的药物及其特点
据报道,迄今为止,有1000多种药物诱发DILI,但已明确能诱发AL-DILI的药物却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主要包括抗生素、降脂药、抗肿瘤坏死因子、草药和膳食补充剂(Herbal and dietary supplements,HDS)等。
(一)抗生素 米诺环素、呋喃妥因导致的药物性肝损伤较为常见[12]。米诺环素是治疗痤疮的常用抗生素,有研究报道它可能是导致AL-DILI的最常见药物[13]。呋喃妥因是一种主要用于治疗尿路感染的抗生素。米诺环素和呋喃妥因诱发的肝损伤在女性中发生率是男性的两倍以上,且呋喃妥因的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14]。大多数情况下,这两种药物停药后临床相关肝损伤可缓解,但自身抗体阳性可持续1年以上[15]。近年来,随着呋喃妥因在临床上使用变少,相关的肝损伤也较少见。
(二)降脂药 贝特类药物与特异质性急性肝损伤相关,典型潜伏期为5~8周,常合并自身抗体的改变,且比自身抗体阴性DILI相比损伤更严重[14]。 阿托伐他汀、瑞舒伐他汀和辛伐他汀都有导致AI-DILI的相关报道,但发生率较低,其中大多数患者具有自身免疫性表型,以及18%的患者可表现为持续性或慢性损伤,肝细胞损伤患者更容易出现自身抗体。他汀类引起的DILI首发症状通常与急性肝炎一致,包括黄疸、厌食、恶心、腹痛、疲乏和瘙痒[16]。
(三)抗肿瘤坏死因子α抑制剂 英夫利昔单抗是一种肿瘤坏死因子α抑制剂,是特异型或间接型DILI和AL-DILI的已知病因。在Bj?rnsson HK的研究中[17],约50%的英夫利昔单抗诱发肝损伤患者在停药后ALT改善缓慢,同时接受皮质类固醇治疗后反应良好,经过长时间随访,皮质类固醇逐渐减量后未观察到肝损伤复发,表明英夫利昔单抗引起的AL-DILI,接受类固醇治疗反应更快,不易复发,预后好,这也是与特发性AIH的差别。
(四)HDS 近年来,HDS引起的特异质肝损伤越来越受重视,HDS相关性肝损伤的典型临床表现是急性肝炎,伴血清转氨酶水平显著升高,但自身免疫特征并较少见[18]。其中,麻黄、大柴胡汤、Hydroxycut具有自身免疫现象。Hydroxycut是一种用于减肥和增肌的膳食补充剂(dietary supplements,DS)产品,其配方有许多变化,主要为藤黄果、四角蝴蝶、咖啡因、麻黄和绿茶,复合制剂配方复杂,成分不明,这也是研究HDS相关性肝损伤面临的挑战[2]。Nagral 等报道了一系列 6 名疑似在食用心叶宽筋藤后出现肝损伤的患者,这6例中有5例有自身免疫血清学标志物的证据,例如ANA升高、平滑肌抗体(smooth muscle antibody,SMA)和/或免疫球蛋白G(Immunoglobulin G,IgG )升高。植物成分DC的肝脏毒性也不容小觑,心叶宽筋藤起源于印度,被当作含有植物成分的市售糖浆,用来对抗急慢性炎症以及提高免疫力,作为一种“免疫助推器”,最近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越来越受人们的欢迎[19]。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传统药物消费国之一,也是中草药诱发性肝损伤发病率最高的国家[20],然而确诊AL-DILI的具体中药目前尚未见相关报道,但HDS引起的肝损伤应该予以重视,临床医生询问病史时不能忽视询问HDS服用史。
三、诊断与鉴别诊断
AL-DILI目前尚无明确的诊断标准,缺乏完整的共识。和普通的DILI一样,是一个排除性诊断。因此,首先需要评估用药与肝损伤之间的关系,目前主要使用Roussel Uclaf因果关系评估法(Roussel Uclaf causality assessment method,RUCAM)。近期研究也验证了自1993年以来,RUCAM是评估DILI因果关系是最广泛使用的方法[21]。其次需要自身免疫标志物的升高,据报道约72%的抗核抗体(antinuclear antibodies ,ANA)水平升高,60%的平滑肌抗体(smooth muscle antibody,SMA)水平升高,39%的病例IgG水平升高[22]。其中ANA阳性最常见,而抗线粒体抗体(antimitochondrial,AMA)阳性的DILI可能更严重[23]。最后需要严格排除其他肝病原因,ANA和SMA 抗体是AL-DILI常见的血清学标志物,而它们的存在与经典1型AIH的表型相似,鉴别起来十分困难,根据现有的文献报道,认为疾病的潜伏期、组织学、影像学、对皮质醇的反应、风险等位基因、免疫球蛋白等临床特征有助于判断患者是否存在AL-DILI、AIH或是DILI。
(一)潜伏期 AL-DILI发病的时间差异很大。一般来说,大多数AL-DILI潜伏期超过2个月,也有文献显示AL-DILI的潜伏期超过12个月,平均潜伏期为143天,而DILI患者平均潜伏期仅为32天[24]。
(二)组织学 AL-DILI活检可能有汇管区和肝小叶嗜酸性粒细胞浸润。然而,该发现并不具有特异性,因为它们也可以在AIH中出现。AL-DILI活检还包括淋巴细胞和浆细胞的混合炎症细胞浸润,分散的嗜酸性粒细胞、汇管区和肝小叶状巨噬细胞浸润,斑片状胆管增殖伴或不伴中性粒细胞浸润,以及界面炎症活动。某些病例中还可见胆汁淤积和非干酪样肉芽肿[25], 有研究指出AL-DILI往往有更多的嗜酸性粒细胞浸润,但这在其他研究中没有被证明[26]。在另一项使用肝组织切片免疫组化的研究中,DILI和AIH两者汇管区均是以CD8T 细胞为主,但AIH汇管区成熟B细胞比DILI更多[27]。此外,也有文献指出汇管区和腺泡内浆细胞浸润、玫瑰花结形成是更倾向于AIH的组织学特征,而汇管区中性粒细胞浸润和肝细胞内胆汁淤积在DILI中更为普遍[28]。
(三)影像学 与AIH相似,DILI的肝脏声像图随病情严重程度而变化,轻度患者一般提示无器质性改变;中度患者形态大小正常,实质回声低于正常,呈细颗粒状,密度较稀疏;重度患者形态失常,实质光点增粗,回声增强。急性DILI患者CT /MRI检查易出现门脉直径增宽、肝各叶比例失调,而慢性患者肝各叶例基本正常,可出现胆管扩张。此外,DILI 患者肝损伤较轻时CT表现为小片状病灶,肝损伤较重时CT可出现大片融合病灶及肝左右叶比例失调,若坏死区域较大时可造成肝裂增宽。而AIH的CT/MRI以表面结节最常见,引起肝硬化还可出现肝内胆道扩张、静脉曲张和腹水等[29]。
(四)对皮质醇的反应 有研究表明ALT 对皮质类固醇治疗的短期反应有助于鉴别DILI和AIH,在皮质类固醇的治疗下AL-DILI患者ALT水平降低比AIH更显著,并且一般不会再复发,而AIH会复发,这是早期鉴别AL-DILI和AIH的主要方法[26]。还有一项研究显示,AL-DILI患者在诊断时和之后的随访期间均未发生肝硬化,而AIH病例中有42.1%存在肝硬化[30]。相比AIH患者,DILI患者倾向于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清转氨酶完全正常化,而且不易出现肝硬化。
(五)风险等位基因 特发性AIH的风险等位基因,如HLA DRB1 DRB1*03:01或DRB1*04:01在AL-DILI中并不常见,如果检测到,可能有利于诊断AIH[31]。 而存在 DILI 风险等位基因将支持AL-DILI的诊断。DILI风险等位基因包括DRB1*15:01、B*57:01、B*57:01、DRB1*16:01-DQB1*05:02、A*33:01、B*35:02 DILI。其中风险等位基因之一HLA DRB1*15:01与AIH相关的发生率较低,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基因检测有助于决策[2]。
(六)免疫球蛋白 有文献显示,AIH 的IgG和免疫球蛋白M(immunoglobulin M,IgM )均升高,而AL-DILI只有特异性抗体的IgM升高,这可以作为区分AL-DILI 和AIH的特异性指标[32]。并且,一项研究中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分析,来评估自身抗体在区分AIH与AL-DILI以及AL-DILI与DILI的预测价值,得出着丝粒蛋白B(CENP-B)、染色质、抗线粒体抗原、肌球蛋白和核小体抗原的5种IgG自身抗体,能够以高精度区分AIH和AL-DILI。 dsDNA、SCL-70、ssDNA、U1-snRNP-BB 的4种IgM 自身抗体,能够从DILI预测 AL-DILI[32]。
通过以上鉴别点区分AL-DILI与AIH仍较为困难且复杂,因此寻找DILI诊断和预后的可靠生物标志物一直是研究热点,多项研究表明miRNA-122可能有助于识别死亡或肝移植高风险的患者[32, 33]。最近的一项前瞻性研究表明,谷氨酸脱氢酶(glutamate dehydrogenase,GLDH)在识别DILI患者方面似乎比micro RNA-122更有用,而细胞角蛋白18(Cytokeratin 18,K18)、骨桥蛋白和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受体与急性DILI结局相关[34]。Llewellyn等还证明,由GLDH、K-18和miR-122组成的组合模型能够比单独的单个生物标志物更准确地检测DILI,并区分DILI、健康志愿者和非肝细胞器官损伤患者[35]。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生物标志物研究能够完全将AL-DILI与AIH区分开来。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临床研究和实验室研究找到鉴别AL-DILI和AIH的特异性指标。
四、治疗
与DILI相同,AL-DILI的治疗首先需要停药,应充分权衡停药引起原发病进展和继续用药导致肝损伤加重的风险,及时停用可疑药物是终止肝损伤进展的必要措施。如果病情严重,可以选择皮质类固醇治疗,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γ-谷氨酰基转移酶(gamma-glutamyl transpeptidase,γ-GGT)等指标会降低,而且一般不会复发[26]。但需要注意的是,皮质类固醇治疗必须个体化,有禁忌证的情况下慎用。
根据 DILI的损伤类型选择适当的药物治疗。轻-中度肝细胞损伤型和混合型DILI,可选择水飞蓟素、甘草酸制剂和双环醇等[36]。胆汁淤积型DILI,可选择促进胆汁排泄的药物如熊去氧胆酸和 S-腺苷甲硫氨酸,但其疗效和效益成本比仍不确定[37]。肝功能衰竭的患者,需要考虑紧急肝移植[26]。
近年来,肠道菌群与DILI的关系逐渐受到关注。有研究报道,异甘草酸镁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可显着缓解甲氨蝶呤诱导的肠道和肝脏损伤[38]。也有研究指出,肠道菌群可能通过改变免疫细胞的比例或功能参与异烟肼导致的DILI,益生菌如双歧杆菌可能在异烟肼导致的DILI及其适应现象中发挥重要作用[39]。此外,还有研究建立D-GalN诱导DILI的小鼠模型,再将给予了布拉酵母菌+D-GalN的小鼠粪便移植给D-GalN小鼠,与D-GalN 组对比,粪便移植组D-GalN组小鼠肝脏损伤的程度明显减轻[40]。这些发现可能为DILI反应差异的潜在机制提供新的见解。靶向肠道微生物群可能是预防和治疗DILI的新策略。但目前针对DILI与肠道菌群的关系多为动物研究,且缺乏AL-DILI的动物模型,期望将来有研究能填补这项空缺,同时也需要有临床研究的支持,不断探究肠道菌群参与DILI的机制将有助于DILI机制的深入研究,且有望从根本上预防和治疗DILI。
五、总结
AL-DILI是DILI的一种特殊亚型,主要由几种特定药物引起,以自身免疫标志物上升为主要特点。目前对于AL-DILI确切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现有的主要解释包括新抗原的形成、遗传易感性,然而临床上个体对AL-DILI的易感性差异很大,但遗传因素对于AL-DILI的解释有限,因此提出了免疫耐受受损机制,而肠道微生物群对具有个体差异性的复杂疾病具有显著预测能力,并有研究指出肠道菌群可能通过免疫调节介导DILI,粪便移植能减缓DILI,因此研究肠道菌群与DILI的关系是目前研究DILI的主流方向,将有助于预防、诊断甚至根治DILI。 AL-DILI的诊断无特异的标志物,目前主要依靠排除其他肝病,通过有无用药史和停药后有无复发与AIH鉴别,因此找到AL-DILI的生物标志物也是目前的研究热点。目前miRNA-122 被证明比ALT有更高的特异型,但还需更多的研究支持。总体而言,AL-DILI的研究尚不充分,随着DILI发生率的增高以及人们对AL-DILI的重视,希望未来在AL-DILI的发病机制、诊断、治疗等方面有更多的研究进展和突破。
利益冲突声明: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