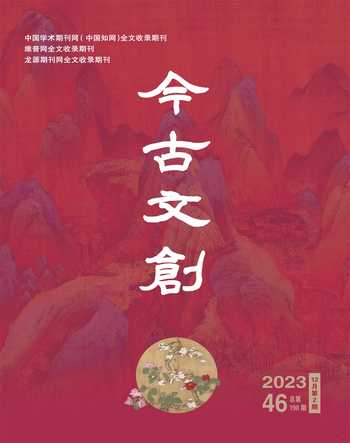《一日三秋》中花二娘形象塑造方法的 多重性探析
【摘要】在最新长篇小说《一日三秋》中,刘震云再次将目光投向家乡延津,作品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乡土、历史等元素相融合,赋予日常生活以神秘色彩,进而营造出了一种奇异、朦胧的氛围。在这篇既是“笑话”又是“血泪史”的故事中,主角花二娘的形象是复杂且多层次的。从表面上看,她是一个依靠笑话生存的悲剧人物,但其本质上又承载着作品的多重主题。本文试从花二娘形象塑造的戏仿手法、反讽艺术以及隐喻意义三方面来探析其塑造方法上的多重性,一窥作品背后刘震云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所做出的探索与创新。
【关键词】刘震云;《一日三秋》;花二娘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46-0004-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6.001
长篇小说《一日三秋》出版于2021年7月,是刘震云自《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四年后的暌违之作。作品以作者的故乡河南省延津县为背景,围绕着花二娘、樱桃与明亮三位主角展开,勾勒出了他们各自别样的人生图景,书写了樱桃和明亮两代人长达半个世纪的悲喜春秋以及花二娘千年求索的血泪史。无论从作品主题,还是从叙事结构上来看,《一日三秋》似乎都像是一种向《一句顶一万句》的复归,对“延津叙事”模式的延续为《一日三秋》的书写留下更多辗转腾挪的空间与时态可能性。而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刘震云则一改以往惯用的“双主角”模式(如《一句顶一万句》中的杨百顺与牛爱国、《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的牛小丽与李安邦等),创造性地加入了第三个主角“花二娘”。一方面,刘震云积极从民间传说和志怪传奇中寻觅灵感,并通过类似于《红楼梦》的布局手法,以花二娘神话开篇、结尾,将其作为故事的背景,体现出作者向民间文化和古典文学靠拢的倾向。另一方面,刘震云又以后现代主义的技巧塑造花二娘形象,使其融入“画里画外、戏里戏外、梦里梦外、故乡他乡、历史当下”的时空体验之中,同时也承载了作品的多重主题。“花二娘”以其独特的方式存在着,串联起了整个文本,展现出了“真实”与“虚拟”的交织与重构。探析花二娘形象塑造的多重性,对于发掘作品意义、把握刘震云塑造人物的走向有重要作用。
一、颠覆原型的戏仿
加拿大文学批评家弗莱在著作《批评的剖析》中将那种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称为原型,并用“原型”一词来表示“把一首诗同其他的诗联系起来并因此有助整合统一我们的文学经验的象征”。[1]自文学革命以来,西方各种文学思潮的传入对中国作家的文学观念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思想深入人心,与此同时,一些带有戏仿因素的作品开始出现。例如在《故事新编》的《补天》《奔月》《理水》等篇中,鲁迅就通过颠覆崇高、消解神圣的戏仿手法对中国古代的“女娲造人”“女娲补天”“嫦娥奔月”“大禹治水”等神话原型进行了戏拟式的重写。20世纪80年代后,“戏仿”作为后现代主义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进入中国,许多作家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进行戏仿创作,这在以刘震云的“故乡系列”为代表的“新历史小说”中尤为明显,例如让曹操、袁绍、慈禧太后等人跨越时空与其他人物同台登场。刘震云这种以戏谑态度塑造人物的特点延续至今,但不同的是,在《一日三秋》中刘震云不再一味地解构历史人物,而开始从民间文化宝库中汲取养分。
从《一日三秋》的第一部分和第四部分中有关花二娘前世今生的叙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花二娘形象对“望夫石”神话原型的改写与戏仿。“望夫石”故事广泛存在于古代文献之中,且版本较多。最早的“涂山氏女望夫石”记录了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其妻涂山氏女终日眺望丈夫治水的方向,最后化作望夫石的故事,此版在《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和《吕氏春秋·音初》等文献中已有端倪。[2]三国时期曹丕的《列异传》和南朝刘义庆的《幽明录》则记录了另一版本的望夫石故事—— “武昌阳新县望夫石”:“武昌阳新县北山上望夫石,状若人立,相传昔有贞妇,其夫从役,远赴国难,妇携弱子,饯送此山。立望夫而化为立石,因以为名焉。”[3]除此之外,在江西、浙江、山西、安徽、广东等地还流传着各种版本的望夫石故事。[4]综合来看,望夫石故事拥有一套相对固定的模式,即丈夫出于建功立业的目的或因各种外力(战争、灾害、政治等)的干预而出走,妻子在家等待并望向丈夫所去方向,最终丈夫并未归来,妻子也化作石头(山)。望夫石故事所昭示是一种针对妇女的相对传统的道德观,其恪守贞节与自我牺牲往往是为了映衬丈夫献身于家国事业的崇高形象。[5]
在《一日三秋》之中,刘震云则通过戏仿的手法消解了“望夫石”原型中旧有的价值观。作者在第四部分《精选的笑话和被忽略的笑话》细致地介绍了花二娘的前世和名称的由来这个“被忽略的笑话”:古时西北有冷幽族,冷幽族以说笑为生,犹如吉普赛人般居无定所,当族人行至活泼国后因受到国王赏识而定居于此,但后来遭到不喜幽默的新任国王的屠杀,全族仅柳莺莺(花二娘)与情郎花二郎二人因在城外野合而幸免于难。柳莺莺与花二郎在逃亡過程中相约在延津渡口见面,但花二郎因意外死亡未能赴约,改名为花二娘的柳莺莺在延津渡口久等不来,最终化为“望郎山”。在这个故事里,刘震云首先颠覆了望夫石故事中丈夫的伟岸形象。丈夫的出走动机由捐躯赴国变为狼狈逃亡,而花二郎因听笑话没喘上气,最终被鱼刺卡死的死因则更是荒诞不经。其次,刘震云改写了望夫石故事中所存在的“等待”母题。《一日三秋》中花二娘久等情郎无果,后听从他人建议而更名,将“望郎山”改为了“忘郎山”,寓意忘掉花二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名是对望夫石故事中以女性牺牲为代价的“浪漫”的一种祛魅。再者,作者刻意将花二娘与旧有望夫石故事中妻子的贞洁形象以及传统的道德体系相疏远,花二娘同样具备七情六欲,她不但不忌讳、排斥明亮所讲的黄色笑话,甚至在高兴之余也会同意与浪荡子弟翻云覆雨的无理请求。相较于望夫石故事,此处的花二娘更多的有着古典艳情小说人物的影子,就连“花二娘”这一名字也与明清艳情小说有着某种关联性:明代西湖渔隐主人所著的短篇小说集《欢喜冤家》的第一回“花二娘巧智认情郎”中就存在一个同名的花二娘;而在《金瓶梅》中,作为花子虚妻子的李瓶儿亦被人称作“花二娘”。此外,在由人化山再变为鬼神之后,花二娘通过梦境向延津人“压榨”笑话并肆意掠夺人性命的存在方式也不可谓之“道德”,反倒与《聊斋志异》等志怪传奇中骗取人精气的鬼狐形象如出一辙。
由此可见,花二娘形象的塑造是在戏仿“望夫石”原型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民间文学——如志怪传奇、民间传说等元素的组合、罗列与堆叠,这样所产生的犹如拼贴画一般的效果也恰好是《前言》中“我”对六叔画作中“后现代、变形、夸张、穿越生死、神神鬼鬼和日常生活”[6]9的表现与协调。
二、倒置“狂欢”的反讽
反讽是刘震云创作的特色之一。在《塔铺》之后,作家将反讽作为其创作观念和重要的叙事话语来进行定型和深化。刘震云的作品中常常会出现各种类型的反讽,如情境反讽、语言反讽、结构反讽等,黑色幽默渐渐取代了其早期作品所流露出的略显刻意和笨拙的悲剧气息,并巧妙地达到了喜剧意识和悲剧意识的平衡。正如英国学者D·C·米克在其著作《论反讽》中所提到的:“反讽的发展史也就是喜剧觉悟和悲剧觉悟的发展史。”[7]从作品所达到的反讽艺术效果上来看,《一日三秋》似乎已具备了超越前作《一句顶一万句》的笔力,甚至不亚于他的后现代主义长篇《故乡面和花朵》,后者曾被视为是“一种被推向极致的反讽叙述”[8]。通过一个个戏谑而荒诞的“笑话”,刘震云完成了《一日三秋》的反讽空间的建构,而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串联起整个文本的、“笑话”的接收者和需求者——花二娘这一角色。
花二娘形象的反讽艺术体现在其本身所指向的一种社会心理,即对“民间狂欢话语”的模仿。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在《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等著作中谈到了狂欢理论,其中包含狂欢节、狂欢式和狂欢化三个内容。巴赫金把狂欢节视为一种全民均可作为一个自由平等的主体所参与的节日,并指出了狂欢节对应官方世界所建立起来的第二世界和第二种生活;狂欢式则意味着狂欢节脱离固定时空而向人们日常生活的蔓延和渗透;狂欢式转化为文学的语言即是狂欢化。[9]在日常生活中,笑话作为人们缓解现实压力的一种独特方式,其叙述行为和呈现过程本应是更为轻松愉悦的,与此同时,作为现实世界的颠倒、充斥着笑话的梦中世界也更应是欢快的,是具有狂欢节性质的并且能够满足大众自我表达的心理和践行狂欢精神的第二世界。然而在小说里,原本现实世界中的等级观念和威权制度却在花二娘所把控的梦中世界出现。在梦中,花二娘有一套荒诞而恐怖的执行标准:讲得不好、未能把花二娘逗笑的人会被要求背着花二娘去喝胡辣汤,最终被花二娘压死;讲得好、可以把花二娘逗笑的人会被花二娘奖励一个红柿子,得以继续生存;对于一句话便能把花二娘讲笑的人,花二娘则会“赏给他两个红柿子,及全家三年免说笑话的权利”[6]13。于是,笑话便只能在那些本不具备压抑性的梦中以压抑甚至扭曲的声音讲了出来。例如,当明亮第一次在梦中遇到花二娘时,因为未曾提前准备笑话,而不得不将妻子以往从事妓女职业中所发生的糗事当作笑料将给花二娘听。对于这样畸形的笑话,“来自明亮一辈子的伤痛;这样的笑话多了,明亮早就活不下去了”[6]292。而对书中的延津人而言,讲好笑话恰恰是为了不再讲笑话。
花二娘肆意地行使着自己的权力,以笑话的可笑程度决定人的生死,攫取人的生命,是延津人最大的梦魇。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常常畏惧做梦,畏惧这种倒置的“狂欢”,但又不得不在入睡前提前准备几个笑话来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花二娘。与此同时,原本较为封闭的且具有森严等级制度的现实世界反而成了延津人的庇护所。在逢年过节时,“花二娘也让所有延津人休假。端午节、中秋节、春节等,延津人可以不讲笑话。延津人过节很严肃,大家走在街上,个个板着脸;相遇,冷峻地盯对方一眼,并不代表不友善,恰恰是亲热的表示;冷峻就是親热,严肃就是轻松,源头也在这里。”[6]14这看似矛盾的逻辑背后实则是对现实世界与狂欢世界的再一次颠倒:现实中的节日失去了形式上的狂欢,真正的“狂欢”则以严肃的形式表达出来。在现实世界与梦中世界的镜像呈现中,气氛严肃的现实节日才再一次成了实际意义上的“狂欢广场”。
此外,花二娘寻求笑话这一行为本身同样具备反讽意义。在《精选的笑话和被忽略的笑话》这一部分中,“我”在花二娘故事的结尾便明确指出:花二娘对情郎的无望的等待“才是延津最大的笑话”。然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延津最大的笑话”对于延津人来说却是极大的禁忌,没有人敢将它当作笑话讲给花二娘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部以喜剧基调书写血泪史的《一日三秋》本身就是一个反讽的“笑话”。[10]这点从小说的英文标题可以清晰地看到:Laughter and Tears: A Novel(笑与泪:一部小说);在书中的第五部分《〈花二娘传〉的开头》,小说更是直接点明了《花二娘传》——同时也是《一日三秋》的主题:“这是本笑书,也是本哭书,归根结底,是本血书。多少人用命堆出的笑话,还不是血书吗?……”[6]306
在花二娘形象所串联起的文本空间中,讽刺性素材不断地重叠在一起,其环环相扣最终赋予了小说一种非凡的深意,最终达到了别样的反讽艺术效果,这也与刘震云本人的“拧巴”与“绕”的“说话”哲学密不可分。
三、寄寓乡愁的隐喻
自20世纪末的“故乡系列”开始,刘震云不断赋予延津以更多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这些作品犹如藤蔓与枝丫一般构成了一个扎根乡土、悲悯世情的“延津宇宙”,而《一日三秋》的问世更是对“延津宇宙”的一种丰盈与突破。刘震云笔下的延津诸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陕西商州等,已渐渐成为当代文学中的一个“文学地标”。但刘震云对于故乡延津的情感却是复杂、矛盾的,刘震云曾不止一次地在文学作品中展现自己对于故乡的拒斥和疏离的态度,他本人也承认:“故乡在我脑子里的整体印象是黑压压的一片深重和杂乱……我对故乡的感情是拒绝多于接受。”[11]然而,这种拒斥和疏离并不来源于作者本身对于故乡的厌恶感,相反之,正是由于他对故乡包含着巨大的眷恋,才让他在创作中显现出自己宏大的叙事野心,想要通过文学性的想象来实现对现实的颠覆,从而构造一个想象中的延津。《一日三秋》中刘震云对花二娘形象的塑造正是基于作家的这种乡愁。
一方面,花二娘形象可以看作是现实的延津对于虚拟的延津的一次“临水自照”。刘震云曾提到两个“延津”的差别:“我书中的延津,跟现实的延津,有重叠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都叫延津,容易引起混淆。”[12]例如,现实中的延津其实并没有“望郎山”和《一句顶一万句》中所多次写到的“津河”。在刘震云拓展他的“延津宇宙”的过程中,作品中的虚拟的延津却与真实的河南省延津县渐行渐远,最终成了一个类似于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一样的“蜃景之城”。同样的,“故乡”也并非一个具体、单调的地理名词。“故乡”显然已超越了某个具体的实存,而衍变、抽象成了一种类似“世界观”般的逻辑力量。[13]花二娘便是在这种力量的驱使下诞生的,这个延津的“介入者”通过与延津的“量子纠缠”使得“延津与世界发生了联系,使延津知道了世界,也使世界知道了延津,也使延津知道了延津。”[12]于是,刘震云对于故乡的矛盾而复杂的情感便通过花二娘这一形象投射在了虚拟的延津上。花二娘兼具悲喜剧色彩的经历以及其所呈现出来的平易且专横、爽朗而孤僻的性格对应着故乡带给刘震云的双重体验。
另一方面,花二娘又作为一种乡愁的象征影响着文本中的其他角色,成了“故乡”延伸的触手。在小说中,延津是花二娘的“辖域”,花二娘通常只会在延津人的梦里出现,但有时也会有特例。明亮从骗子手中购得“一日三秋”牌匾的当天夜里,人在西安的明亮梦回延津,明亮的梦汇集了他一生之中最珍贵、最难忘的记忆。枣树、奶奶、爷爷、算命的瞎子老董、奶奶故事中的黄皮子和犟牛、家犬孙二货、延津渡口的中年猴子……构成了一个人神鬼兽共存的世界,至此,明亮完成了他诗意的精神返乡。在梦的结束,花二娘突然出现并前来寻找笑话,此处的花二娘已不再是一个具有立体形象的神鬼或是梦魇,而是作为一种乡愁的象征,是明亮怀念故乡的精神寄托。[14]梦里的花二娘道出了明亮美梦的虚假性,面对花二娘的驳诘,明亮则通过理性的反思对比梦之真与生活之假,诉说着人性的真挚:“梦是假的,梦里的事又是假的,但负负为正,其中的情意不就是真的了吗?人在梦中常哭湿枕头,您说这哭是不是真的?人在梦中常笑出声来,您说这笑是不是真的?有时候这真,比生活中的哭笑还真呢。”[6](289)明亮和花二娘两人对于梦与现实生活的辩论,实则也是对于真假故乡的辩论。现实的延津与文学的延津或是梦中的延津的差异被暂时搁置,明亮或者说是作家需要的仅仅是一个用来排遣乡愁情绪的幻想世界。
不得不承认的是,尽管刘震云反复诉说着他的乡愁,但他所寄寓乡愁的“延津”却是仅存在于作家记忆中的、早已被时间改变了样貌的故乡。在作品中,无论是陈明亮还是樱桃,神出鬼没甚至有点喜怒无常的花二娘像是捆缚他们精神的绳索,也是无法割断他们乡愁意蕴的情感寄托。一方面,他们渴望摆脱这种羁绊,渴望摆脱活在世上的那种困苦和不能掌控自己命运的窘蹙,他们背井离乡,忍辱负重,但却始终没有掐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萦绕在他们内心深处的孤独感和人生的幻灭感又促使他们寻找一个回不去的故乡,寻找一个用来安放灵魂的栖息地。不管是跟随父亲陈长杰去武汉生活抑或是自己前往西安打拼,明亮时刻都在惦念着故乡,然而在明亮“故乡梦”的结尾,花二娘却禁止明亮在梦里返乡,否则便要“梦去西安”让他喝胡辣汤。当乡愁被覆盖上原罪之时,故乡最终只能渐渐地消隐在他乡之中。
对比《一句顶一万句》和《一日三秋》,可以看出刘震云对作品人物形象塑造与作品主题之间关系的处理方式的不同:如果说前者是由杨百顺和牛爱国的出走与归来编织乡愁的话,那么后者就是由乡愁出发来塑造、充实人物形象,从中可以看出刘震云在创作上的一些转变。
四、结论
在《一日三秋》发布后的座谈会上,刘震云把创作长篇小说看作是一场“不匀速的长跑”,并强调故事的结构和人物的结构对于作品节奏的带动。结合刘震云的创作历程来看,人物形象塑造手法的革新的确是伴随其创作的转变而进行的。《一日三秋》中花二娘这一形象的塑造就具有很强的开拓性与创新性,相较于明亮形象对《一句顶一万句》中杨百顺的部分特征的继承与保留,花二娘形象则是耳目一新的,是在刘震云小说中前所未见的新型人物。一方面,花二娘形象根植于深厚的民间文化土壤,是小说将现实神话化、神话现实化的产物,是刘震云借助小说和人物观照现实生活的又一成就。另一方面,花二娘形象的这一特性使得它足以容纳文本所赋予的多重意义,在与故乡深度绑定的过程中,花二娘本身就被建构成了故乡的象征。在更广泛的层面,花二娘形象还承载着数千年未曾改变的民族的精神灵魂,[15]即苦中作乐的自嘲精神和坚韧不拔的生存意识。花二娘形象塑造的复杂性和多重性也正反映出了作者对民间、民族、生活、生命、故乡等的哲学性思考,这是刘震云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创新,也是刘震云以哲学为底色创作小说的一次大胆尝试。
参考文献:
[1]叶宪舒编选.神话——原型批评[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0.
[2]李道和.试论作为望夫石传说原型的塗山氏传说[J].民族艺术研究,2003,(02):43-45.
[3]刘义庆撰,郑晚晴辑注.幽明录[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183.
[4]鐘敬文.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册)[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5]朱恒夫.望夫石传说考论[J].江海学刊,1995,(04):167.
[6]刘震云.一日三秋[M].广州:花城出版社,2021.
[7](英)D·C·米克.论反讽[M].周发祥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117.
[8]傅元峰.一种被推向极致的反讽叙述——试读《故乡面和花朵》[J].小说评论,2000,(04).
[9]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6,161-165.
[10]李杨,崔涛等.《一日三秋》:走不出故事的城与人[N].文艺报,2022-2-21(08).
[11]刘震云.整体的故乡与故乡的具体[J].文艺争鸣,1992,(01):73.
[12]刘震云.延津与延津[N].农民日报,2022-1-7(08).
[13]李丹梦.文学“乡土”的地方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313.
[14]周菠.故乡书写、荒诞精神与命运主题——三个维度解析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日三秋》[J].名作欣赏,2022,(27):133.
[15]孙雯.刘震云:幽默源自苦难,它能融化严酷[N].钱江晚报,2022-6-19(03).
作者简介:
左金朋,男,河南襄城人,宁夏师范学院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