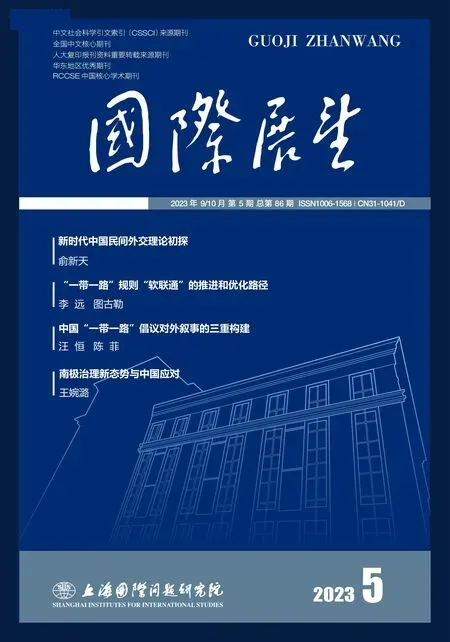欧美对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重塑∗
——从“气候俱乐部”到“碳边境调节”
关孔文 李倩慧
国际社会一直致力于寻求建立公平、合理、科学的气候治理机制,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的治理有效性却备受质疑。这突出表现为“减排承诺”与“法律约束力”的二元困境难以突破,加之核心领域政策难以明晰,使得国际治理体系在以“软性”和“硬性”为特征的制度安排之间徘徊,国际合作陷入迟滞。①Sebastian Oberthür, “Hardening and Softening of Multilateral Climate Governance Towards the Paris Agreemen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 Planning, Vol. 22, No. 6, 2020,pp. 801-802.为强化全球层面减排雄心并降低国家行为体履约的边际成本,包括欧盟、美国在内的主要发达经济体以增强不同治理主体间减排贡献的透明度和可比性为由,通过碳定价和碳排放交易等方式突出市场机制的作用,提出建立“碳边境调节机制”或“气候俱乐部”,并以此回避发达国家的气候治理责任。
作为全球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致力于推动构建气候变化命运共同体,提出自己的“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以此表明中国的治理决心。如何全面理解欧美国家对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重塑的尝试,有效疏解随之而来的国际压力,并将其转化为国内相关产业发展和碳金融机制完善的动力,是中国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互动,推动国际治理体系变革并提升整体气候外交能力中亟须解决的问题。
一、“气候俱乐部”和“碳边境调节”的政策含义
自进入“京都时代”以来,国际谈判与合作即围绕责任分配展开。其核心议题包括治理体系的囊括性、约束性、可比性等,导致排他性的主权制度与竞争性的政治制度成为实现全球气候治理合作的桎梏。《巴黎协定》明确,国际社会减缓气候变化行动的目标为“在21 世纪末将升温幅度控制在2 摄氏度以内并尽可能将升幅限定在1.5 摄氏度”,这也就意味着全球须在2025年前实现总体“碳达峰”,2030 年比2017 年至少减排47%,于2050 年实现“碳中和”并自此转向“负排放”。②IPCC, “Special Report Global Warming of 1.5 ℃,” October 8, 2018,https://www.ipcc.ch/sr15/.但是,国际社会的减排努力与长期目标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因减排成本多由国家承担而减排成果却由全球共享,使得全球气候治理的“搭便车困境”难以避免。①Miquel Oliu-Barton and Simone Tagliapietra, “COVID-19 Policy Response Can Inform the Design of a Climate Club,” Intereconomics Review of European Economic Policy, Vol. 58, No.1, 2023, pp. 2.
当前,能源安全问题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短期内的优先议事日程和重要议题合作领域。德国政府在2022 年6 月召开的七国峰会上提出建立“气候俱乐部”的设想,②Susanne Dröge and Marian Feist, “The G7 Summit: Advancing International Climate Cooperation? Options and Priorities for the German G7 Presidency,” SWP Comments, No. 34, May,2022, Berlin: 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SWP-Deutsches Institut für 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d Sicherheit, pp. 1-2.以期通过加强去碳化转型和国际气候治理合作来解决能源短缺和价格上涨问题。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构建成员数量有限的“气候俱乐部”,被视为解决全球治理有效性不足和减排雄心缺乏问题的重要措施。《巴黎协定》通过“国家自主减排贡献”(INDC)建立“自下而上”的温室气体减排分配体系,赋予国家行为体更大的空间以选择适合自身的治理方式,来实现合理的减排目标。然而,全球气候治理本身具有较强的公共产品属性,治理行动很难摆脱囚徒困境的影响,由主权国家基于共同治理意愿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意志联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③Thomas Hale, “A Climate Coalition of the Willing,”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4,No.1, 2011, p. 100.似乎可在一定程度上弥合全球整体行动力不足的缺陷,并推动全球层面治理目标向区域、国家和次国家层面下沉和分解。当然,内向型治理和外向型治理最大的区别是,全球公共产品的缺失无法通过市场或政府手段予以解决,这也使得国际合作机制变得日益重要。因此,“气候俱乐部”被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等在内的学者视为解决气候治理集体行动困境的终极措施。④Indra Overland and Mirza Sadaqat Huda, “Climate Clubs and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s:a Review,”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Vol. 17, No. 9, 2022, p. 1.
“气候俱乐部”是具有相似立场的国家自发组建的应对气候变化联盟,俱乐部意味着成员国所获报偿将远大于其为换取准入资格和履行联盟义务所承担的交易成本。⑤William Nordhaus, “The Climate Club How to Fix a Failing Global Effort,” Foreign Affairs, Vol. 99, No. 3, 2020, p. 14.该俱乐部具有典型的“胡萝卜+大棒”特征,①Kasturi Das, “Climate Clubs Carrot Sticks and Mor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No.34, 2015, p. 26.俱乐部成员身份是获得奖励或惩罚的主要判断依据。一方面,加入该俱乐部意味着成员国可以获得排他性资金、技术、国际合作、市场准入和安全保障等收益,即“胡萝卜”政策;另一方面,对非成员国采取包括贸易壁垒、禁运和惩罚性措施,即“大棒”政策。“气候俱乐部”旨在改变国家行为体参与气候治理的动机以降低全球谈判的交易成本,②Robert Falkner et al., “Climate Clubs: Politically Feasible and Desirable?” Climate Policy,Vol. 22, No. 4, 2022, p. 485.强调通过补偿性支付手段维系“气候俱乐部”的相对稳定和有序运行,并对非成员国形成吸引力和向心力,实现成员规模的扩大和气候治理政策的扩散。
“气候俱乐部”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规范型俱乐部,即成员国为达成某种气候治理目标而建构行为标准或规范,其成员身份往往通过共享相同治理理念或减排雄心而获得(如净零与碳中和目标),故开放性特征显著;二是谈判型俱乐部,即成员国为增强基于共同治理目标的谈判有效性而形成的国家集团,成员国的议题影响力是俱乐部准入的重要条件(如“基础四国”等);三是变革型俱乐部,即成员国为寻求参与治理行动所获报偿结构调整性的联盟。③Robert Falkner, “A Minilateral Solution for Global Climate Change? On Bargaining Efficiency, Club Benefits, and International Legitimacy,”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14, No. 1,2016, pp. 88-91.
碳关税被视为“气候俱乐部”成员身份的重要标识,但与传统经贸同盟不同的是,关税工具并非用来协调内部成员的一致性对外贸易政策,而是对非俱乐部国家因未作出可比性气候治理贡献而采取的惩戒性措施。事实上,包括美国和欧盟在内的发达行为体都不约而同地将“碳边境调节”(BCA)作为后疫情时代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政策工具。
美国政府早在拜登竞选时就提出通过贸易和关税的形式确保所有进口货物在入境时已由出口国完全承担了全部的气候污染费用(即碳税),并要求联邦层面的进口许可必须将气候变化影响纳入关税制定范畴,以此作有别于共和党的政策打算。“碳边境调节”作为拜登绿色新政的旗舰项目已在参众两院讨论多次,备受关注的“昆斯—彼得斯法案”(Coons-Peters Act)甚至提出如何限定美国碳边境调节的适用范围(贸易对象国和贸易部门)和计算方法(直接排放部门和多排放部门的计算)。①The U.S. Congress, “Fair, Affordable, Innovative and Resilient Transi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S. 2378, 117th Congress, July 19, 2021.
相较于美国,欧盟在“碳边境调节机制”推进方面的态度更为强硬,2019年出台的《欧洲绿色协议》(European Green Deal)和2020 年发布的《增强欧洲2030 气候雄心》(Stepping up Europe’s 2030 Climate Ambition)不仅提出将2030 年的减排目标设定为55%,②European Commission, “The European Green Deal,” COM (2019) 640 final, Brussels,December 11, 2019; and, European Commission, “Stepping up Europe’s 2030 Climate Ambition Investing in a Climate-neutral Future for the Benefit of Our People,” Brussels, COM (2020) 562 final, September 17, 2020.而且将“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明确纳入欧盟气候政策一体化进程。③European Commission, “Questions and Answers: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CBAM),” Brussels, July 14, 2023.2023 年5 月10 日,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共同通过“建立碳边境调节机制”(Regulation on Establishing of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的决议,并于5 月16 日正式生效。
“碳边境调节机制”是欧盟解决“碳泄露(Carbon Leakage)”的重要手段,旨在强化气候治理政策有效性的同时解决经济增长缓慢的问题。根据欧盟立场,独立的碳税或碳排放交易体系会导致碳排放密集型产业因生产成本的上升而转移至碳排放标准较低或无强制性碳排放成本的国家;这不仅无法在全球总体层面实现有效的温室气体减排,也将由于经济收益的减少而降低国家的潜在减排意愿。④Antoine Dechezlepretre and Misato Sato, “The Impa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Competitiveness,” Review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Policy, Vol. 11, No. 2, 2017, pp.184-185.若转移后的生产者依然可以在不承担任何额外税收支出的情况下将产品重新输入,因所承担碳排放成本远低于高减排标准国家的同类产品,将获得相对价格优势并占据更大市场份额,进而削弱高标准国家的贸易竞争力。“碳边境调节”的核心机理是以市场手段构建具有普遍囊括性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通过贸易互动倒逼第三方国家政府采取更为绿色的政策取向,并借由政策和立法手段推动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调节过程主要体现在对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中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评估并通过碳定价拉平国内、国际同类产品价格,以此确保国家行为体减排承诺的可比性,并在总体上实现全球气候治理目标。
事实上,该调节机制涉及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对外贸易、海关与税收、财政预算和经济增长等诸多政策领域,①European Parliament, “EU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Implications for Climate Competitiveness,” PE698.889, June 2023.使得相关法律基础、议题属性和决策过程较之其他气候治理方式更为复杂。欧盟已就“碳边境调节机制”的持续有效推进设立明确时间表,该机制将于2026 年开始全面运行,并在2034年完全取代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ETS),②Alice Pirlot,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asures: A Straightforward Multi-Purpose Climate Change Instrumen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 Vol. 34, No. 1, 2022, p. 29.以避免因“碳泄露”造成经济效益和气候治理的“双输”困境。
二、“气候俱乐部”和“碳边境调节”的共性和差异性特征
“气候俱乐部”和“碳边境调节”被主要发达国家视为突破当下全球气候治理僵局的重要方式,因都以关税手段作为协调内向型治理和外向型治理的政策工具,故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常被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讨论。③参见:Biying Yu et al., “Review of Carbon Leakage under Regionally Differentiated Climate Policies,”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Vol. 783, No. 3, 2021, pp. 3-4; and Indra Overland anf Mirza Sadaqat Huda, “Climate Clubs and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s: a Review,” p.5.虽然欧盟力推的 “碳边境调节机制”被认为在实践层面基本与“气候俱乐部”相同,④Bierbrauer Felix et al., “A CO2-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as a Building Block of a Climate Club,” Kiel Policy Brief, No. 151, 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 (IfW), March 2011.但欧盟仍然尽量避免在官方文件中提及“气候俱乐部”并将其与“碳边境调节”联系在一起。⑤Indra Overland and Mirza Sadaqat Huda, “Climate Clubs and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s:a Review,” p. 1.值得关注的是,即使德国在担任“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期间曾力荐“气候俱乐部”,但《七国集团气候俱乐部宣言》(G7 Statement on Climate Club)中也未明确提及“碳边境调节”,只提到合作性气候俱乐部在国家间合作层面应对碳泄露是其主要职能之一。⑥G7 Germany, “G7 Statement on Climate Club,” June 28, 2022.
相比较而言,“气候俱乐部”和“碳边境调节”都面临共同的机遇和挑战,这尤其体现在法理和伦理层面。虽然两者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源流有所差异,但既有学术层面的探讨并未明确对其进行区分,也未就政策工具的联系和互动进行深度探讨。总体上,“气候俱乐部”和“碳边境调节”在政策目标、政策类型、政策工具和政策扩散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共性和差异性特征。
第一,在政策目标层面,“气候俱乐部”和“碳边境调节机制”皆以增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为核心宗旨,但因实现的方式不同而导致政策具体表现形式有所差异。
“气候俱乐部”是避免“搭便车行为”和提升全球气候治理水平的有效路径。其通过构建俱乐部为成员提供排他性报偿,并向非成员实施普遍性惩罚措施,如美欧力推的“绿色钢铝贸易同盟”即为俱乐部成员提供贸易便利措施并限制非成员国的钢、铝市场准入机制。①“Joint US-EU Statement on Trade in Steel and Aluminum,” White House, October 31,2021.补偿支付手段是俱乐部公共产品提供的重要前提条件,借此可有效增进成员国对俱乐部的忠诚度并提升履约意愿,进而鼓励更多成员加入。②HåkonSælen, “Side-payments: An Effective Instrument for Building Climate Club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Politics, Law and Economics, No. 6, 2016, p. 911.然而,不同国家参与气候治理的意愿并不相同,因此很难要求所有行为体按统一方式和进度参与治理行动;而“气候俱乐部”寻求组建立场相近国家的集合,是一种多边框架下的多边合作模式,也被称为“俱乐部中的俱乐部”。③Makane Moïse Mbengue and Elena Cima, “Clubbing in the Club: Could Climate-related Trade Arrangements Set the Pace for Future Climate Cooper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16, 2022, p. 219.
“碳边境调节机制”本质上是对碳排放交易体系运行的一种政策性回应和完善,④Bernice Lee and Richard Baron, “Why the EU’s Proposed CBAM must not be Used to Launch a Carbon Club,” World Economic Forum, June 2, 2021,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1/06/eu-carbon-border-clubs-climate-cbam/.通过建立“碳边境”来调节内、外部碳定价差,并平衡国际供应链的经济报偿。欧盟选择通过取消免费配额的形式提升成员国减排雄心。一方面,迫使重工业发展面临更高的碳价;另一方面,通过碳边境调节来有效避免外国生产商的贸易竞争优势。
总之,“气候俱乐部”的政策目标更倾向于寻求国际合作的扩大,因而更具“多边主义”特征;而“碳边境调节”是内部单向性政策调整措施,更多体现“单边主义”特征。
第二,在政策类型层面,“气候俱乐部”和“碳边境调节机制”都包含经济政策领域,但因政策类型的具体表现形式与政策目标密切相关,“气候俱乐部”则体现更多政治特性。“碳边境调节机制”的界定更多限制在经济议题领域,预计其每年对欧盟的税收贡献多达140 亿美元。①George Morsdorf, “A Simple Fix for Carbon Leakage? Assessing the Environmental Effectiveness of the EU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Energy Policy, Vol. 161, 2022, p. 8.当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碳边境调节”不仅是内向型气候治理政策和对外贸易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体现“气候俱乐部”的几乎所有特征。有效的调节机制不仅可以给予成员国承担气候治理责任的福利保障,同时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经济工具惩戒非俱乐部成员。②Kacper Szulecki et al., “The European Union’s CBAM as a de Facto Climate Club: The Governance Challenges,” Frontiers in Climate, Vol. 4, 2022, p. 3.“碳边境调节”引发的国际贸易紧张风险将随着俱乐部规模的扩大而降低,跨国界的碳泄漏也会随之减少。③Guntram B. Wolff, “Europe Should Promote a Climate Club after the US Election,” Bruegel, December 10, 2020, https://www.bruegel.org/2020/12/europe-should-promote-a-climate-club-after-the-us-elections/.但是,从“成本—收益评估”的角度来看,“碳边境调节机制”所增加的贸易成本不一定足以达到刺激非俱乐部成员加入集体行动并承担更高温室气体减排成本的意愿,④David G. Tarr et al., “Why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s will not Save the Planet but a Climate Club and Subsidies for Transformative Green Technologies May,” Energy Economics, Vol. 233, No. 4, 2023, p. 5.而影响补偿支付的最主要障碍是政治可行性,⑤HåkonSælen, “Side-payments: An Effective Instrument for Building Climate Clubs?”也因此赋予“气候俱乐部”以鲜明政治属性。如果借鉴以往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议题联系经验,把“碳边境调节”的突出经济特性融入“气候俱乐部”,政策影响的空间范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扩大,⑥Michael Mehling et al., “The Form and Substan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Border Carbon Adjustm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16, 2022, p. 218.“气候俱乐部”的属性也将从“规范型”和“谈判型”发展为“改革型”。
第三,在政策工具层面,“气候俱乐部”和“碳边境调节机制”都以基于碳定价的税收作为主要政策手段,但政策工具的选择和作用范围有所区别。据世界银行数据,碳定价政策已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刺激温室气体减排的有效工具,国际社会已有39 项各类碳定价制度在国家层面得到落实,33 项在次国家层面得以实施,总体上覆盖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8.8%。①The World Bank, “Carbon Pricing Dashboard: Key Statistics on Regional, National,National and Subnational Carbon Pricing Initiative(s),” https://carbonpricingdashboard.worldbank.org.因此,是否可以依据既有碳定价机制构建“气候俱乐部”或“碳俱乐部”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新焦点。②Bernice Lee and Richard Baron, “Why the EU’s Proposed CBAM must not be Used to Launch a Carbon Club.”然而,国内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建立与俱乐部的组建之间并不构成因果关系,除欧盟已确定推行“碳边境调节机制”外,只有加利福尼亚州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涉及电力输入方面的碳边境调节。③OECD, “The Climate Challenge and Trade: Would Border Carbon Adjustments Accelerate or Hinder Climate Action?”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39th Round Table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ebruary 25, 2020.倘若未来全球碳定价机制的一致性难以达成,碳排放交易体系和碳边境调节措施将更易通过政策扩散的方式在全球推行。④European Parliament, “EU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Implications for Climate Competitiveness,” PE698.889, June 2023.与“碳边境调节机制”以单一税收手段作为主要政策路径不同,“气候俱乐部”更加强调复合政策工具的联合运用,换言之,“气候俱乐部”的政策工具可涵盖多议题领域,包括经贸、财税、环保、政治、社会福利、技术转让等,甚至“碳边境调节”本身也能成为俱乐部可采取的政策措施之一。此外,“碳边境调节”将碳税视为合作性工具,旨在借此促进基于统一碳定价的国际贸易互动和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行动的有效合作;而“气候俱乐部”则将其看作是惩罚性工具,以此作为一种威慑力,使非俱乐部成员对潜在惩罚措施产生畏惧,⑤William Nordhaus, “Climate Clubs: Overcoming Free-riding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5, No. 4, 2015, p. 1339.且为避免被惩罚而选择加入俱乐部并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
第四,在政策扩散层面,“气候俱乐部”和“碳边境调节”都以多边路径为价值取向,但因内在运作机理的区别导致最终发展路径呈现明显差异性。就“气候俱乐部”而言,成员身份的确定是整个俱乐部得以有效运转的关键性因素。通过参与闭合型俱乐部而获得排他性报偿,俱乐部以解决全球气候治理困境为目标,但并未解决如何作出贡献的问题,其实质是通过关联相关政策议题以达成小范围的气候合作,从而实现分解全球气候治理的目标。“气候俱乐部”之所以在国际社会备受关注,原因是通过俱乐部可以使有限国家行为体通过合作促使国家间治理协议得以强化,但因俱乐部所提供的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资源往往较为有限,为保障成员国所获报偿的规模,限制俱乐部成员规模就成为必然选择。“气候俱乐部”被视为多边框架下的“小多边主义”路径(Minilateralism),体现独特的结构性优势,可有效按部门和层级分解治理任务,使气候治理的整体有效性得以强化。①Robert Gampfer, “Minilateralism or the UNFCCC? The Political Feasibility of Climate Clubs,”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 16, No. 3, 2016, p. 62.“碳边境调节”则通过赋予不同行为体新的治理动机以重新定义治理行动,②Makane Moïse Mbengue and Elena Cima, “Clubbing in the Club: Could Climate-related Trade Arrangements Set the Pace for Future Climate Cooperation?” p. 221.以贸易作为基本载体、以碳定价作为调节基础、以碳边境作为调节方式,可通过全球产业链的传导性倒逼其他与之有贸易互动的国家采取类似方式实施碳关税并据此设置相同的碳定价。这种政策扩散方式并非完全主动,但“单边性质”的碳边境调节却在客观上推进了“大多边路径”的政策目标。综合来看,“气候俱乐部”更具有“小多边”属性,成员国在俱乐部扩大和参与气候治理的过程中非自主性特征显著,气候治理行动的扩散效应受到限制;“碳边境调节”则更具“大多边”特征,成员国在选择被动接受或主动实施调节机制方面自主性较强,③Simone Tagliapietra and Reinhilde Veugelers, “Fostering the Industrial Component of the European Green Deal: Key Principles and Policy Options,” Interecoonomics, Vol. 56, No. 6, 2021,pp. 305-306.相关治理路径的扩大潜力较大。
三、“气候俱乐部”和“碳边境调节”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
气候治理的主体是主权国家,但因气候变化的弥散性特质赋予国内政策以显著外部性。在国家层面,国家行为体通过组建科学评估机构、气候治理立法、参与国际气候合作机制等形式塑造国家的气候治理决策程序、界定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并在日程设定、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等方面形成国家独特的治理行为方式。①Johnathan Guy et al., “National Models of Climate Governance Among Major Emitters,”Nature Climate Change, Vol. 13, No. 2, 2023, pp. 189-190.在国际社会层面,气候治理包括全球性政府间机制设置(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具跨国性质的正式或非正式有关气候议题机制安排(如二十国集团),通过建立实质性规范影响国家和其他行为体的气候治理行动,并提供交流、谈判和决策平台。②Sebastian Oberthüret et al., “A Sectoral Perspective on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Analytical Foundation,” Earth System Governance, Vol. 8, 2021, p. 2.
随着国际气候治理的不断扩散和相关机制互动的日益频繁,制度设置的功能性重叠和规则交叉使全球气候治理行动变得日趋复杂。当然,有学者认为,多中心、多层级的复合治理机制可提升全球层面集体行动的有效性,③Robert Gampfer, “Minilateralism or the UNFCCC? The Political Feasibility of Climate Clubs,” p. 63.但也有学者强调政府间跨国机构之间相互作用的有效性难以评估,且随着全球气候治理的日渐分散和复杂化,全球多边规则设置与总体治理目标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④Joshua Philipp Elsässer et al., “Institutional Interplay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Lessons Learned and Future Research,”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Vol. 22, No. 2,2022, p. 373.《巴黎协定》通过“国家自主减排贡献”强化国家减缓性工具选择和自愿合作的合法性,“气候俱乐部”和“碳边境调节”也对既有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第一,削弱联合国框架下多边气候治理的有效性,加剧全球气候治理的碎片化和复杂化趋势。“气候俱乐部”和“碳边境调节”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型互动工具,其机制设置和法律约束力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以何种法律形式存在,即与既有全球气候治理框架的法理关系;二是通过何种磋商机制而达成一致,即如何使决策和决议获得合法性基础;三是如何维系国家间的有效合作及其范围,即实现程序上和政策实践的气候正义。作为气候治理的基础性规范和原则,《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巴黎协定》体现国际社会治理的基本共识,并确定包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等核心原则。因而,如何处理新型气候治理工具及据此形成的新型治理体系与联合国框架下相关机制的关系,成为国际社会亟须解决的重要议题。
在制度层面至少存在两种可能的互动形式。一是以气候治理的特定议题领域为治理限度,将政府间合作机制或调节工具作为联合国框架下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补充部分;二是机构设置与联合国框架下的制度平行,但在治理目标上与既有框架保持一致或超过国际社会的平均水平。①Lutz Weischer, et al., “Climate Clubs: Can Small Groups of Countries Make a Big Difference in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Review of European Community &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Vol. 21, No. 3, 2021, p. 191.
然而,碳税作为“气候俱乐部”或“碳边境调节”的核心政策,在支付对象上并未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且未考虑支付额度是否符合国家能力要求,这不仅有悖于联合国框架下全球气候治理的核心规范,事实上也模糊了温室气体减排责任分配的公平性原则。
“气候俱乐部”以惩罚性措施作为俱乐部集体行动的选择性激励手段,其受众包括所有非俱乐部成员,在进行惩罚性措施及据此所获收益的分配过程中都将涉及如何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责任的问题。“碳边境调节机制”不论是以统一碳定价为核心的“欧盟方案”,还是以国内生产排放量作为依据的“美国方案”,都在客观上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技术、温室气体排放和治理政策与发达国家作趋同处理(且美欧均为全球绿色技术领先国家),直接造成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成本激增、治理意愿下降。
第二,引发新一轮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力的争夺,加速国际社会治理权威的分解与重置。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多边气候治理行动中的领导力是有效实现减缓性和适应性目标的充分必要条件,②Kajsa-Stina Benulic et al., “The Meaning of Leadership in Polycentric Climate Action,”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 31, No. 6, 2022, p. 1016.可有效引导其他行为体在特定时间内采取相似或共同的行为方式以实现同一治理目标。③Jon Birger Skjærseth,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Shifting Climate Leadership,”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 17, No. 2, 2017, p. 85.气候治理领导力的塑造不仅与国家经济和科技实力、国际话语权和地位、国际社会的认可度和影响力有关,也与其所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格局中的位置和绿色技术、投资的转移规模密切相关。在2022 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排在前五位的行为体中,中国占比为32.9%,美国为12.6%,欧盟为7.3%,印度为7.0%,俄罗斯为5.1%。④European Commission, “CO2 Emissions of All World Countries,” EUR-31182, 2022, p.12.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占比情况不仅体现经济发展水平,也决定了它的气候治理议题影响力。这也意味着,不论是以“碳边境调节”来提升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行动的有效性,还是以“气候俱乐部”重组政府间气候治理合作机制,中、美、欧、印四个主要行为体是任何气候治理集体行动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国都加入同一俱乐部或采用共同的调节手段,这必然会直接激励国际社会其他行为体的参与,但同时也会加剧全球气候治理的分裂和机制设置的碎片化。
综合而言,增强内外部减排雄心是获取气候治理领导力合法性的主要方式。①Kacper Szulecki et al., “The European Union’s CBAM as a de facto Climate Club: The Governance Challenges,” p. 5.“气候俱乐部”和“碳边境调节”的实质上是以治理雄心和政策工具选择作为气候意识形态来区分“敌我关系”并进行势力范围划分,再借相关政治和经济手段强化和维系这种国家集团的对立,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欧美的气候霸权。俱乐部或碳边境调节机制的惩罚性措施会在客观上对欠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就业、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和国家发展造成消极影响,从而加剧南北关系的对峙。加之长久以来愈演愈烈的美欧领导力之争,以及欠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对发展中工业大国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的不断施压,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也是矛盾重重,造成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力角色和治理权威界定的困难。
第三,气候外交的单边主义倾向进一步凸显,重塑既有双边气候外交与多边治理机制的双向互动方式。全球气候治理虽以多边方式为主,但以欧盟、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往往为谋求自身利益和权力空间采取单边主义措施。但是,两者单边主义气候外交的表现形式有所差异,美国更易采取单方面退出既有全球治理秩序的方式,而欧盟则更倾向于以其内部规范塑造全球机制的方式推行单边主义气候外交政策。
关于“碳边境调节”,学术界基本认可其单边主义特征,②参见周亚敏:《单边气候规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以美欧为例论绿色霸权的构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 年第12 期,第69—74 页;TimothéBeaufils et al., “Assessing Different European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Implementations and Their Impact on Trade Partners,” Communications Earth & Environment, Vol. 4, No. 1, 2022, pp. 1-9。即具有外部效应的单方面措施,特别是欧盟以单一立法形式确定通过国际贸易进口货物的管辖权,其中并不涉及任何欧盟同其他全球气候治理主体进行磋商和达成一致的过程。事实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产业结构中“高耗能产业—绿色新产业”之间的发展张力不同,也使得气候治理目标和路径选择呈较强差异性。通过构建欧盟层面气候治理机制与全球层面机制设置的联系和有效互动,以期用欧盟内部的能源消费习惯影响其他国家的生产和消费行为,①Ingo Venzke and Geraldo Vidigal, “Are Trade Measures to Tackle the Climate Crisis the End of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The Case of the EU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CBAM),” Amsterdam Law School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 No. 2, 2022, p. 46.从而实现其治理目标和政策的趋同性。
作为一个经济和环境收益驱动的行为体,欧盟在维系其所塑造的融合规范性、示范性和结构性要素的气候治理领导力的过程中,气候单边主义也是其对外气候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盟通过实施“碳边境调节机制”限制联盟整体的市场准入,并依托全球贸易网络强化结构性领导力,②Eva Pander Maat, “Leading by Example, Ideas or Coercion? The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as a Case of Hybrid EU Climate Leadership,” European Papers, Vol. 7,No. 1, 2022, p. 60.其实质是以治理“示范者身份”影响他国气候政策塑造的过程。然而,仅作为第一个践行者并不足以吸引国际社会的其他追随者。通过既有贸易合作,欧盟努力将贸易政策与温室气体减排结合在一起,通过跨国企业将相应政策规范传导至其他国家并影响其税收、碳排放和气候政策。根据“碳边境调节机制”,在贸易对象普遍建立碳交易体系和碳定价制度的前提条件下,所有涉及水泥、钢铁、铝业、化肥、电力和氢能领域的产业部门须与欧盟框架下碳排放交易体系的碳价保持一致,③European Commission,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July 2023, https://taxation-customs.ec.europa.eu/carbon-border-adjustment-mechanism_en.或者根据欧盟碳市场同类产品的平均碳价缴纳“调节费用”。为保持同欧盟的贸易关系且避免向欧盟缴纳“碳边境调节费”,其他国家也就不得不按照欧盟方式建立碳市场、边境调节制度并实行统一的碳定价,从而导致原有气候外交互动发生变化。
第四,改变既有绿色贸易规则,造成国际贸易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兼容性困境。“气候俱乐部”和“碳边境调节”的贸易工具如何与世界贸易组织(WTO)核心条款兼容也是欧盟、美国等倡议者必须回应的议题。所涉问题至少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俱乐部成员内部的贸易行为或实施碳边境调节的国家是否能确保同类产品市场竞争的中立性,即符合非歧视原则;二是“碳边境调节”是否具有财政工具属性,即决定其适用于何种关税贸易协定义务;三是“碳边境调节”是一项仅适用于特定进口产品的专门机制,还是适用于所有进口产品的普遍性政策手段;四是解决“碳泄漏”并增进全球气候治理的有效性是否为“气候俱乐部”和“碳边境调节”的主要目的。①Ingo Venzke and Geraldo Vidigal, “Are Trade Measures to Tackle the Climate Crisis the end of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The Case of the EU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CBAM),” p. 8.比如,欧盟实施“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实际目的也是刺激经济发展,②Juan Antonio Samper et al., “Climate Politics in Green Deals: Exposing the Political Frontiers of the European Green Deal,”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Vol. 9, No. 2, 2021, p. 12.通过调节机制所获税收也并非主要用于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和技术援助,而是进入欧盟财政系统,支持欧盟层面和成员国层面的经济复苏及气候治理行动。当然,该政策工具可在短期内为欧盟及其成员国获得可观关税收入,也因此获得成员国的普遍支持。③Bierbrauer Felix, et al., “A CO2-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as a Building Block of a Climate Club.”
欧盟、美国等一直以来致力于将市场机制融入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从而通过全球产业链和贸易结构的布局来动态调整气候治理责任的分配,并降低发达国家参与气候行动的成本。惩罚性关税措施是“气候俱乐部”和“碳边境调节”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以“碳边境调节机制”作为惩戒手段的“气候俱乐部”不仅可以强化共同监督平台以降低“搭便车行为”的可能性,也能通过征收边境调节费用保证成员的收益以维系俱乐部的存续。因此,在一定数量的国家行为体加入俱乐部后,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将被重构,且俱乐部内部运行规则也会对全球贸易秩序和贸易格局产生影响。加之欧盟、美国在碳边境调节方式上如何采取市场经济的手段仍存较大分歧,④Giulia Claudia Leonelli, “The Long and Winding Road Towards the Creating of Climate Clubs: Transatlantic Negotiations, Potential Regulatory Models and Challenges Ahead,” Review of European Coope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No. 4, 2023, p. 1.这使得两者在“气候俱乐部”的组建方式和合作程度等议题上很难达成一致,从而增加了新型气候治理工具与既有国际贸易体系兼容的难度。
四、中国气候外交的应对策略
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相关气候治理与外交政策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包括“气候俱乐部”和“碳边境调节”的机制设置也都强调与中国的合作或将中国视为共同施压对象,使中国面临更为复杂的全球气候治理形势。在国际层面,发达国家试图迫使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和国际谈判中作出更为激进的减排承诺并为气候治理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在国内层面,中国也须平衡经济发展和气候治理之间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当前,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气候治理模式日益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与气候外交的基本出发点。中国在致力于推动构建气候变化命运共同体的同时,提出“2030 年国家自主减排贡献及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和“力争2060 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积极构建国内相关产业发展框架和碳金融机制,以此展现大国担当。
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及产业结构的升级,全社会去碳化转型已成为必然战略选择,以利益共容界定气候外交的基础,可有效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嵌于全球治理机制的创新过程中,以此实现中国气候外交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变革的双向互动。
第一,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并积极落实“三大全球倡议”,通过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增进国际社会气候治理雄心。全球气候治理核心涉及发展、安全和文明要素,且三者相互促进、彼此支撑。①刘建超:《深刻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三大全球倡议”的内在关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人民日报》2023 年8 月8 日第9 版。“气候俱乐部”和“碳边境调节”都是西方发达国家提出的治理措施,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和需求,也模糊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国内绿色低碳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积极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大力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②于宏源:《中国生态文明领导力建设——基于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视阈的分析》,《国际展望》2023 年第1 期,第24 页。中国倡导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界定后疫情时代气候治理,平衡国际合作收益,使行为体对利益目标予以部分妥协,降低集体行动困境的风险,并激发就更多议题合作的意愿,形成基于功能性合作的外溢。不同领域的合作外溢也可充当再平衡手段,通过跨议题的补偿性支付措施弥补两者利益分歧和分配失衡,从而起到稳定既有国际合作的作用。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中国致力于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网络性合作,增进信息、技术等要素的跨国流动,促进国际层面相关治理理念和规范的网络型扩散,提升国际社会的整体治理能力。
第二,坚持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气候治理路径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进“巴黎协定”下气候治理政策工具的专业化转型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改革。国际冲突的发展以及其他因素的长期叠加影响,对涵盖全球、区域、国家和次国家多层治理体系产生冲击,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集中体现为保守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中心主义的兴起,造成超国家机制式微和国家权威回归,且因气候议题尚未被完全安全化并纳入国家核心安全战略,国际社会现实政治干扰依然严重,导致现行气候治理体系的法律约束力较弱,政治不确定性尤其显著。然而,政治权力博弈和国内政治干扰都有可能成为全球气候治理机制良性互动的负面因素,治理资源的配置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促使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面临维系和改革的双重压力。事实上,“气候俱乐部”和“碳边境调节”是为弥补“巴黎协定”下部门性和专业性治理政策工具不足而提出的,①Sebastian Oberthür et al., “A Sectoral Perspective on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Analytical Foundation,” Earth System Governance, Vol. 8, 2021, p. 8.通过拓展并细化既有制度的功能,协调相关的不同机制间的互动与合作,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框架下新建特定机制,都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全球气候治理困境。
第三,抵制单边主义措施和贸易保护主义,强化国际绿色合作,倡导公平、公正的碳中和秩序。通过“气候俱乐部”或“碳边境调节”的方式调整既有全球贸易互动关系,不仅压缩了生产者的经济收益,更易引发国际争端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②庞军、常原华:《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对我国的影响及应对策略》,《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2023 年第1 期,第32—35 页。特别是欧盟以单边主义方式强制推行“碳边境调节机制”,因部分机制设置有悖于WTO 原则,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和贸易出口产生持久的负面影响。现实情况是,“碳边境调节机制”极易转化为新型贸易壁垒,引发国际贸易冲突,并影响国际社会的正常贸易秩序。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全球气候治理和温室气体减排的决定性力量,通过“南南合作”“基础四国”等多边合作平台强化新兴经济体气候治理的影响力,寻求基于碳市场和碳定价的合作,共同抑制发达国家的施压行为,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不仅应该积极参与开放包容型气候俱乐部、警惕和防范封闭排他型气候俱乐部对华造成的负面影响,①胡王云:《〈巴黎协定〉下全球气候治理的俱乐部模式及其功能和风险》,《太平洋学报》2023 年第2 期,第27—41 页。也应在联合国框架下推动以发展中国家为中心的“气候俱乐部”,在捍卫公平秩序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同时,强化发展中国家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贡献。
第四,加快完善国内碳金融和碳市场秩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强基于绿色技术和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国际合作。欧、美分别是我国第二和第三大贸易合作伙伴,贸易额占我国贸易总额的26%,也是主要贸易顺差来源,占全部贸易顺差额的90%。②李岚春、陈伟:《欧美碳边境调节机制比较及对我国影响与启示研究》,《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23 年第3 期,中国知网“网络首发”。纵观当下全球碳排放格局,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实施“碳边境调节”已成必然、而其重点调节的领域包括钢铁、水泥、铝业、化工等,均为中国主要出口产业部门,且这些领域碳定价机制设置尚不成熟,因此短期内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导致中国碳密集型产品出口成本剧增并进而扩大到整个能源密集型行业。“双碳”目标的实质是通过中长期气候治理促使绿色产业快速发展,并通过绿色技术的创新和国际合作,推动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碳排放交易体系和碳定价机制方面的经验,加快国内碳市场的建设并完善碳税立法,发展绿色金融和相关衍生产品,通过金融工具为气候治理融资,并为碳排放企业生产结构调整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同时,为避免绿色贸易壁垒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应积极推进双循环绿色经济的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构建绿色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加速碳减排进程。
结 束 语
“碳边境调节”是“气候俱乐部”的一种表现方式,也是一种妥协手段,在未来进一步推动的过程中仍有较多困境难以突破。在机制设置层面,如何与既有国际贸易制度和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兼容并获得合法性,以及如何平衡国家间的互动关系,仍是摆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面前的棘手议题。作为解决全球气候治理“搭便车行为”的政策手段,其本身仍为“集体行动”,如何避免在成员国规模扩大过程中的内生性困境也是相关政策付诸实施的重要前提条件。因此,虽然欧美等不惜通过单边主义方式力推相关制度安排,但短期内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际行为体影响有限。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西方发达国家行为体通过“气候俱乐部”或“碳边境调节”重塑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有关中长期去碳化目标的提出,可有效推动在后疫情时代完成绿色复苏和发展的转型,并通过跨领域、多维度气候外交途径,与主要行为体合作建立伙伴关系型气候变化合作体系,使其实现与全球层面机制设置的有效功能互补。这不仅可改善由于主体多元化所造成的国际合作交易成本提高的问题,也有助于形成双边外交的新增长点,弥合传统气候外交的发展困境,体现中国的全球气候治理的责任与担当。